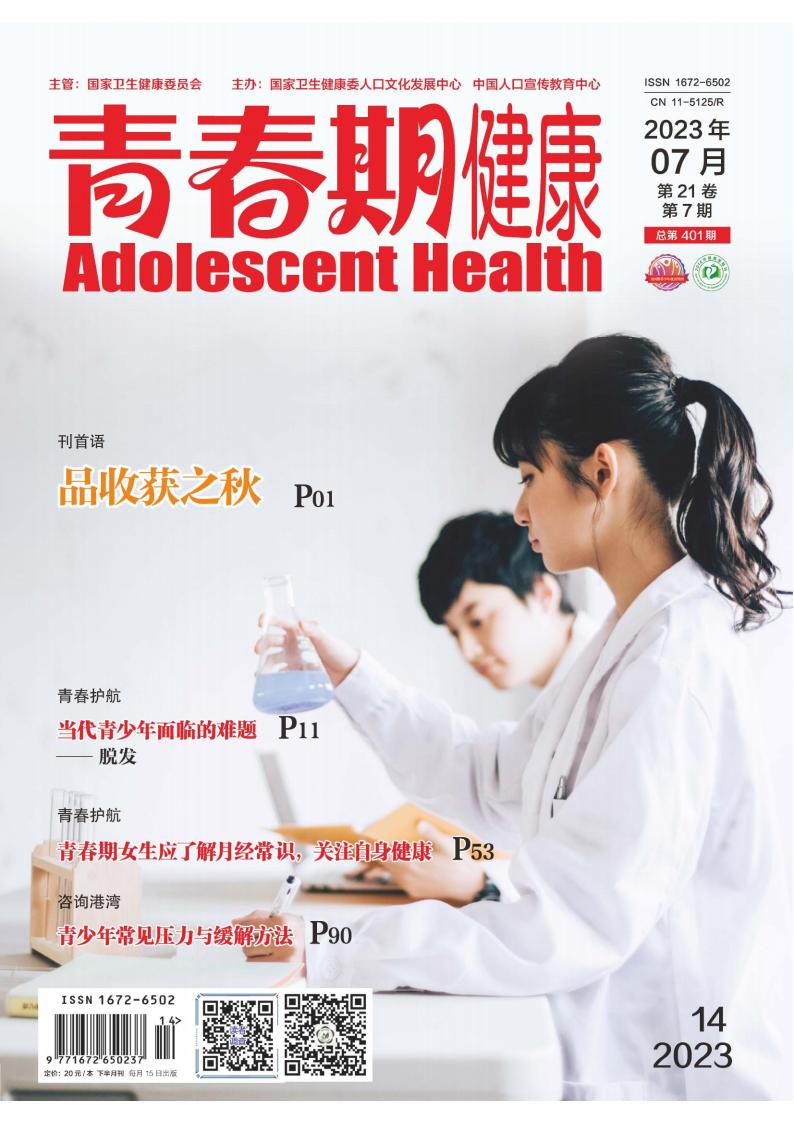清代八旗駐防將軍兼統綠旗的問題
定宜莊
【論文提要】清代的額設制兵,主要由八旗與綠營兩大部分組成。由于二者間具有相互獨立、互不統屬的性質,所以以往研究清代兵制者,都是談八旗者專談八旗,論綠營者僅論綠營,本文從八旗駐防將軍兼統綠營的問題入手,詳敘八旗“軍標”設置的原因、時間、過程與性質,重點在剖析清朝統治者建立軍標的深層用心,從而探討清前期八旗漢軍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與綠營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八旗 駐防將軍 綠營 軍標
有清一代的額設制兵,主要由八旗與綠營兩大部分組成。[1]八旗是清朝自關外帶入的勁旅,綠營則是清入關后改編明軍降將降卒及后來陸續招募漢人組成的部隊。因二者間具有相互獨立、互不統屬的性質,所以以往研究清代兵制者,都是談八旗者專談八旗,論綠營者僅論綠營,而很少注意到二者之間的關系。 將軍,作為清代八旗駐防的最高將領,所統領的當然都是八旗官兵,但在特定的情況下,也會有部分綠營軍隊歸其統屬,史稱其為“軍標”。《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制”謂:“將軍兼統綠營者惟四川”(3891頁),屢為后來談兵制者沿用,[2]以訛傳訛,忽略了清代曾在另外幾處重要駐防地點設置軍標的事實。因而本文寫作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澄清有關史實,并詳敘軍標的興廢之跡。而分析清朝統治者建立軍標的深層用心,進而探討清前期八旗漢軍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與綠營之間的關系,則是本文的主題。
討論具體問題之前,首先有必要將清代綠營與駐防八旗的體制作一簡單說明。 先談首言八旗駐防與八旗駐防將軍。 將軍是八旗駐防的最高統帥。清軍入關,在固有八旗制度的基礎上,結合明代戍防的作法,將其從非經制發展到經制,從邊疆擴充到腹里,形成有清一代特有的八旗駐防制度,并使之成為清朝得以統治全國近三百年的得力工具。八旗駐防按其駐地的性質、額兵的數量而有高低不同的等級,最高一級駐防單位由將軍統領,駐地多在省會等重要城市,兵額均在千人之上,多者達六七千人;其次由副都統統領,則情況各異,有與將軍同城者,內省各城大抵如是;有與將軍不在一城而受將軍管轄者,北部邊疆各處均如是;還有由中央直轄以及由它城將軍兼轄者。再低一級設城守尉,最次一級為防守尉,統領額兵最少時僅十數人。迄至康熙末年(1722),全國已設駐防將軍11名,即西安、江寧、杭州、京口、福州、廣州、荊州、右衛,以及盛京、吉林和黑龍江。雍正朝添設2名:青州、寧夏。乾隆朝對八旗駐防有較大調整,增綏遠城、伊犁、成都共3名,裁撤京口、青州和右衛3名,總數為13名。另有察哈爾都統,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于烏魯木齊增設的一名都統,可視為與將軍同級的高層次駐防單位。因與本文關系不大,不另。 在乾隆朝八旗漢軍出旗為民以前,八旗駐防有滿蒙與漢軍合駐、滿蒙合駐和漢軍單駐等幾種形式,其中西安、杭州等地為滿蒙漢軍合駐,京畿各處以及江寧、荊州等,或因其地位特殊,或因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而為滿蒙合駐而無漢軍,則漢軍單駐之處有三,最早的是京口,其次是廣州和福州。至于成都、伊犁等乾隆朝之后建立的駐防點又另當別論。 再言綠營 綠營兵制基本上完整地沿襲明制,在內地十八省“隨都邑大小遠近,列汛分營,立之將帥,授以節制,于涉海、瀕江又各設水師營以守之”[3]。綠營隸禁旅者惟京師五城巡捕營步兵,此外額兵60余萬,以標、協、營、汛的組織系統分散駐扎于全國大大小小的城鎮、關隘、水陸交通要沖,由總督統轄的稱“軍標”,巡撫統轄的稱“撫標”,提督統轄的稱“提標”,總兵統轄的稱“鎮標”,駐防將軍統轄的則稱“軍標”,是本文中擬詳細考證的問題。標以下設協,由副將統領;協以下設營,以參將、游擊、都司分別統領;營以下設汛,由千總、把總、外委分別統領。兵分三種:馬兵、戰兵、守兵。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一個完整而又細密的軍事控制體系。 由此可知,所謂軍標,就是由八旗駐防將軍統轄的綠營軍隊。八旗與綠營既屬兩個不同的軍事體系,而且在綠營正式建制以后,清廷曾有明確規定,即綠營歸總督節制,駐防將軍沒有直接統率綠營之權,這是將軍與地方官員互不干預內容的一部分。在這一大原則之下,何以又有由八旗駐防將領統率的綠旗,具體情況又是如何,這就是尚未引起治史者注意,而本文擬詳細討論的問題。
四川設將軍級八旗駐防時已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史稿》所謂“將軍兼統綠營者惟四川”,用于這一段時期大致不錯,用來闡釋有清一代兵制則不是事實。羅爾綱在《綠營兵制》中以乾隆朝《會典》為主要依據作《綠營行省營、官、兵數統計表》,其中雖將各省軍標一一列出,但因未作特別說明,一眼看過去也很容易被忽略。[4]實際上,早在順治、康熙朝時即已有駐防將軍兼統綠營之例,均設置于由八旗漢軍單駐的幾處,即京口、福州與廣州。不過,這里所說的,都是載于康熙朝以后歷代官書的正式建制,臨時性的由漢軍將領兼統漢軍及綠營的情況則不預其內。[5]以下分別言之: 第一個以將軍兼統綠營之處是京口。 京口位于鎮江城外,控扼長江下游,距江寧(即今南京)不過200里之遙。“襟江帶海,上承淮泗,下控吳會,西接漢沔,東南鎖鑰,實在于茲”。[6]順治十一年(1655),清廷命江寧昂邦將軍管效忠移駐鎮江,次年又命固山額真石廷柱為鎮海大將軍,統率八旗官兵駐防京口,旋撤。順治十六年(1660)九月,復命都統劉之源掛鎮海大將軍印,統八旗官兵共甲二千副,并左右二路水師駐扎鎮江,鎮守沿江沿海地方,這是京口正式設置八旗駐防之始。 這里所說的甲二千副即八旗額兵2000名,無庸議。至于左右二路水師,則文獻語焉不詳。據最早的康熙二十九年修《會典》卷九一“兵部”記:
江南·鎮海將軍一員,駐扎京口,標下左右二營(原設隨旗前后左右四營,康熙二十一年以四營官兵歸并提督管轄,本年仍歸將軍管轄。二十三年裁前后二營)。 左營 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右營 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同卷又記:
京口鎮·鎮守京口水師總兵官一員,駐扎江陰縣,標下中左右三營。原系左路水師總兵官,屬京口將軍管轄,康熙二十一年歸提督管轄。
僅從這兩段看,仍不是十分清楚,茲再引雍正十年修《會典》:
鎮海將軍一員,駐扎鎮江府京口,標下左右二營,兼轄京口水師協(原設隨旗前后左右中營,康熙二十一年以四營官兵歸并提督管轄,本年仍歸將軍管轄。二十三年裁前后二營,三十六年裁京口水師總兵,改設副將,歸將軍管轄)。 左營(原設左營副將,康熙三十八年改設中軍副將,兼管左營事) 京口水師協(原設左路水師總兵官,屬京口將軍管轄,康熙二十一年改為京口水師總兵官,歸提督管轄,標下設中左右三營,三十六年裁總兵官,改設副將,仍屬京口將軍管轄。其三營內裁右營,將中左二營改為左右二營。[7]
這就比較清楚了,京口將軍除統領八旗官兵之外,還兼轄左右二營綠旗兵,此外并兼管綠營水師。從《會典》看,康熙中期以前,將軍標下這幾營綠旗的統領權也曾一變再變,或交由綠營提督或水師總兵,不數年又回歸將軍,或增設,或裁撤,應是八旗駐防與綠營均未明確定制的表現。 第二個設立軍標之處為廣州。 廣東與福建地處沿海,為清初時的抗清基地,從鄭氏一家到康熙末年的朱一貴,這一帶的抗清斗爭此起彼伏,迄未停息。順治七年(1650)耿、尚進入廣州,后耿移駐福建,二藩曾叛應吳三桂,旋又降清,終于康熙十九、二十兩年(1680、1681)先后被誅。耿、尚死后,部屬“分入旗下,另立佐領”[8],大部撤回京師,其余被分散納入八旗漢軍之中,而只留其中一小部分,與另外派遣的將軍、副都統所統八旗兵丁一起,組成由中央直接統領的駐防八旗。廣州設八旗駐防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將尚藩舊有15佐領兵丁分入上三旗,[9]人數共1125名,令駐廣州,命漢軍正紅旗人王永譽為八旗駐防將軍。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從京師增派下五旗漢軍1875名,合為3000之數。 康熙、雍正兩朝《會典》均未提到廣東將軍兼領軍標的具體時間,有明確記載的是光緒朝《會典》:“康熙二十一年設將軍標左營兼中軍副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外委六人。”[10]這個時間,恰處于廣州駐防建制、改編尚藩舊兵與從京師派遣八旗官兵之間,是值得注意的。 廣州將軍標下有左右前后四營,各設游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其中惟左營游擊于康熙三十八年被裁撤,改設中軍副將,兼管左營事。守備、千總與把總之設仍如其舊。總的說變化不大。 第三個是福州。 福州設置八旗駐防早于廣州,為康熙十九年(1680),綠旗兩營的增設則晚于廣州,為康熙三十年(1691):“四旗兩營駐扎省城,控扼上下游各府,為閩省之中權”,而福州將軍的職掌即“以四旗而兼統綠旗”。[11]四旗,指的是八旗的鑲黃、正白、鑲白與正藍。兩營,即將軍標下的左右兩營綠旗,建制為左營:中軍副將一員,原系銅山營副將,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屬將軍標下。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右營:游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京口、廣州與福州是清前期僅有的由八旗漢軍單駐之處,駐防將軍均由八旗漢軍充任,也為清前期各省駐防所僅有。關于三處軍標的設置經過,官書記載不僅簡略,而且散亂不全。三處駐防雖然都留有駐防志,但成書于光緒五年(1879)的廣州《駐粵八旗志》,記載詳于后期而略于初創。同為光緒五年編纂的《京口八旗志》更是明言咸豐三年(11853)之前事已無案可稽。惟由駐防將軍新柱領銜纂述的《福州駐防志》,成書時間既早(乾隆九年,1744,為清代所有八旗駐防志書中最早的一部),記載內容又完備,所以這里以福州駐防將軍兼統綠營的情況為例,敘述“軍標”設置時的具體背景。 為何讓將軍兼統綠旗,雍正帝有過明確解釋:“當日各省設立漢軍駐防,因(旗兵)人數不敷,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令該將軍管轄”[12]。對于這一經過,福州將軍石文炳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請增綠旗兩營疏”,講得更為具體明確。石文炳請求由福州將軍兼統軍標的理由有三。 第一,閩省綠旗水陸營兵統計64700有余,而旗營額設僅止馬甲1683副,步甲347副,旗營兵單。而福建又是形勢特別復雜之處,“自我朝定鼎以來,一叛于鄭成功,再叛于耿精忠,兵民習見悖逆,人心機變異常。繼自征討臺灣之役,添設營兵不下十數萬,原督臣姚啟圣募養戰士不下萬人,四方不逞之徒又復強半入閩”。可見當時閩省之民,許多也是由兵轉化而來,率多強悍,且與綠營兵勇存在各種聯系,這使閩省的綠營之兵,比它處更不可靠。區區二千余兵的八旗駐防,對付這六七萬時降時叛的綠營,尚且戰守不敷,更遑論承擔鎮守全省地方之任。 第二,閩省駐防八旗兵丁雖然都是漢人,畢竟以北方人居多,長于弓矢而短于火器。而閩地卻平原絕少,不是高山叢樹,就是深溝水田,騎射難施之處,必資火器為先。“臣欲請改火器,則失我之所長;欲專恃弓矢,又非地之所宜”。 第三,從福建的地理位置和軍事形勢看,重要性并不遜于廣東和京口,而兵額獨少。 此疏得到朝廷重視并于翌年正式于福州添設軍標兩營。 京口、廣州與福州,這三處清初僅有的以八旗漢軍將軍統領,屬下官兵也皆系漢軍的駐防點,有其共同之處。從地理位置說,廣州、福州瀕海,京口也是襟江帶海之地。明末清初的抗清運動,就以東南沿海一帶持續時間最久,斗爭最為激烈,形勢也最為繁雜,加上后來“三藩之亂”中有兩藩即在福、廣,可以說京口、廣州與福州三處,直至康熙中葉以前,一直處于清朝統治的最前線。而這幾處抗清斗爭所以激烈,也與水戰重于陸戰,水戰卻是八旗無論滿蒙漢軍的弱項有關。如果派遣滿洲、蒙古八旗進駐,一則長途跋涉,水土不服,二則語言不通、技藝亦無處施展,這正是八旗勁旅的“軟肋”,也是清朝政府不能不往這幾處派駐旗兵,但又不能派遣滿蒙重兵而只能以漢軍充數之故。 但問題還可以再深入一步:即使不能派遣滿兵而非由漢軍出面不可,又何以不增派八旗漢軍而要由將軍統領綠旗,如果真的如雍正帝所言,僅僅是因八旗兵力有限,為什么軍標只出現在以漢軍將軍統領駐防的這三處? 三處將軍所統兵丁的額數,應是揭示這一問題的入手處。幾朝《會典》均未備載將軍標所統綠營的額數,這里謹以石文炳《請增綠旗兩營疏》[13]中的數字為準: 廣東駐防額設馬步甲3000副,將軍兼統的綠旗兵丁4000名,共計額兵7000。而軍標多于旗兵。 福州八旗駐防馬、步甲共2000名,將軍兼統的綠旗兵丁2000名(馬兵400,戰兵600,守兵1000),共額兵4000。旗兵與軍標相等。 京口將軍額設馬步甲3000副,將軍兼統的綠旗兵丁2000名,共額兵5000。旗兵多于軍標。 通計起來,這三處將軍統領的綠營總數已超過八旗,這當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數目。 我們可以將其與當時屯駐八旗甲兵最重的西安、江寧作一對比: 西安將軍:據雍正元年滿文朱批奏折記,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僅馬兵就有7000名,其中4000為滿蒙馬甲,另有3000 漢軍。[14]乾隆二十八年(1763),西安的滿蒙馬甲已達5000名,較前又有增加。[15] 江寧將軍:滿、蒙馬甲共4000,與西安同,不同者為江寧無漢軍。 用設置軍標的三處與江寧、西安相比,結果是耐人尋味的。 首先,如果將三處漢軍將軍所統旗兵與綠旗合計,則廣州將軍統領額兵總數與西安將軍相同,福州與江寧同,京口介于西安與江寧之間。這就是說,三處額兵都已達到八旗駐防屯兵的最高數。 其次,如果僅從八旗兵數看,京口等三處則遠遠少于西安與江寧兩處。 已經很清楚,京口等三處駐防將軍領兵甚重,是出于當時當地軍事控制與鎮壓的需要,這突出地反映了清前期八旗漢軍在政治與軍事統治中所發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由駐防將軍兼統軍標,在使將軍的兵力得到加強的同時,更體現為對將軍權限的一種控制。 八旗與綠營既然為兩個系統,綠營各級中下層武官與八旗有不同的統屬,更何況清代綠營兵與八旗的不同之處又是“八旗駐防兵由于世籍,綠旗各營兵由于招募”,[16]即使是屬下軍標,將軍對于各級官員尤其是兵勇的權限亦相當有限,這就使這幾處的漢軍將軍,與統領同樣數量八旗官兵的滿蒙駐防將領,在兵力與權限上都不可同日而語。 綠營既然由總督、巡撫和綠營將領各自統領幾標,將軍標只是其中一部分,這就在將軍與當地綠營將領之間,設置了一道明確的界限。將軍雖能統領幾標綠營,但仍不得干預民事,也并無超越軍標干預其它綠營軍隊之權。 在京口、廣州和福州這三處舉足輕重之地,卻不得不重用并不敢完全信賴的八旗漢軍,滿族統治者自不敢掉以輕心,由將軍兼統綠營,正體現了清朝統治者對八旗漢軍將軍的權力加以制衡的深層用心。 雍正帝對于在漢軍單駐之地設置軍標,解釋為是因八旗“人數不敷”而采取的權宜之計,這確實是原因之一,但卻不可盡信,如果看不到清廷對漢軍旗人深深疑忌并千方百計加以控制的一面,對于清初漢軍將軍兼統綠營一事,就做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雍正朝以后,駐防八旗人口日漸繁衍,初期“人數不敷”的情況已不復存在,而京口、廣州與福州幾處的局勢也早已相對穩定,軍標的作用也不如初設時那么明顯。筆者曾在另一文中提到,駐防八旗出現生計問題,多以漢軍為最突出,這是因為清朝政府施行“首崇滿洲”政策,八旗漢軍的挑甲機會要少于八旗滿蒙的結果。廣州、福州等地漢軍八旗最集中,生計問題也最嚴重,駐防將軍遂在標下綠營兵身上打主意,希圖讓得不到挑甲機會的漢軍余丁挑補軍標額缺,這一建議幾經反復,終獲朝廷批準并加以推廣,軍標遂成為緩解八旗生計問題的一個“蓄水池”: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內閣抄出奉上諭:“……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當日各省設立漢軍駐防,因人數不敷,是以添設綠旗兵丁,命該將軍管轄。今漢軍余丁繁衍,足供差操之用。嗣后將軍標下綠旗兵丁缺出,即將漢軍余丁頂補。如綠旗兵丁之子弟內有祖父食糧年久者,著于本省督撫等標營名糧,準其充補。此朕再三籌劃辦理者,蓋以當年漢軍人數不足,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今漢軍余丁日多,仍令充補本將軍標下綠旗之缺,于情理實為允當。……[17]
乾隆朝令各省駐防漢軍出旗,大多數出旗漢軍都挑補了綠營額缺,所沿的也是這一條思路。因有專文撰寫,不另。[18] 軍標的裁撤,與此三處八旗漢軍的出旗為民緊密相關。八旗駐防漢軍的出旗,最早從福州開始,繼而就是廣州。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命福州原設四旗漢軍官兵陸續出旗,翌年(1755)輪到廣州,因廣州將軍力請,其3000名漢軍僅出旗一半,尚余1500名。[19]漢軍空出的額缺,由京師派遣等額的八旗滿、蒙官兵充補。乾隆三十年(1765),福建駐防內的另記檔案人戶1000名亦被放出為民。[20]至于京口駐防,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已被從將軍級下降到副都統級駐防單位,僅留的一名副都統駐鎮江,歸江寧將軍管轄。與此同時,京口鎮海標營亦奉旨令江寧將軍兼管。[21]這應視作軍標被裁的開端。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諭:
京口駐防漢軍三千三百余名,雖系水師營缺,不可裁撤,然今太平無事,無需眾兵駐守,而去歲皇上南巡時,檢閱其操演,技藝甚劣,徒有虛名,并無實效。江南現有駐防滿洲、蒙古兵近六千名,數額極多,若從中揀派熟諳水師營事宜者千余名駐守京口,將京口漢軍兵缺概行裁汰。其額缺給予索倫、察哈爾丁,派駐伊犁,則于海疆、新疆地方均得勁旅,而索倫、察哈爾等獲食錢糧,于其生計亦大有裨益。[22]
因將京口駐防漢軍領催、馬步甲共3000名,以及炮甲、匠役等悉數裁汰。 漢軍既經裁撤,軍標的裁撤也是勢所必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下令將這三處的將軍標悉數裁撤。廣州“因系省會重地,若將將軍標四營全裁,兵額稍單”,所以僅裁前后二營,酌留千余名,撥歸撫標570名,廣州協825名。京口將軍標左右二營,實裁馬步守兵855名;福州軍標左右二營,裁兵1553名。[23]同時又將京口水師營撥歸總督專管,從此不再隸于八旗。[24]三省軍標至此不復存在。 福建、廣東的漢軍旗人出旗和軍標被裁,不僅不意味著兩處軍事地位的下降,反而是這兩處在乾隆朝以后地位愈形重要的表征,這是與京口的不同之處。此時用來換防的八旗滿蒙官兵已在京師居住幾代,對于漢地的語言與生活,都遠較清初時更能適應,已具備了前往福、廣等海疆駐防的能力。而一旦條件具備,就由滿蒙旗人取代漢軍,盡管有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考慮在內,但也表明了朝廷對這兩處的特別重視。 而且,雖然廣東始終留有半數的漢軍未曾出旗,原隸福州駐防、建于雍正七年(1729)的福州三江口水師旗營的漢軍也一直沒有出旗,當其中的開戶、另記檔案人出旗時,還曾派7戶漢軍另戶頂補其缺[25],這應是出于海防的考慮,但這兩處的八旗駐防將軍,卻已由漢軍缺改為滿缺,也就是說,此時的統兵之權已從漢軍旗人轉到滿洲旗人手中。 駐防將軍既然已是滿缺,朝廷原有的對漢軍將軍的種種制衡也無存在意義,于是在這兩處軍標被裁不到40年之后,清廷復命兩處駐防將軍節制綠營。 嘉慶十年(1805)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諭:諭內閣,廣東地方緊要,廣州將軍除統轄該省駐防滿營之外,別無應管事件,所有廣東省陸路鎮協各營均著交該將軍節制,著為令。[26] 嘉慶十一年(1806)三月二十三日朝廷又命福州將軍亦從廣州將軍之例,節制綠營。見《清史稿》載:
福州將軍除統轄八旗駐防官兵外,兼轄福州城守營,節制福寧鎮標、福州城守及同安等營。 …… 廣州將軍除統轄八旗駐防官兵外,節制南韶連鎮標、潮州鎮標、高州鎮標、瓊州鎮標、惠州協標、肇慶協標、廣州城守協、三江口協、黃岡協、羅定協、增城各二營,南雄協、欽州各一營,雷州左營、前山、永靖、連陽、惠來、驍平、潮陽、廉州、儋州、萬州、和平、四會、那扶、永安、興寧、平鎮、潮州城守、石城、陽春、三水、徐聞、綏瑤等營[27]。
但這不是“軍標”,具體地說,這兩省的綠營除督標、撫標、提標各有專轄外,其余陸路各鎮協均交該將軍與總督一體統轄。凡各營任卸、操防、巡輯、差遣及一切弁兵升調,均由各鎮協具文申詳,將軍查考其軍政舉核咨商會題,至升調拔補則由總督移知。[28]這是從加強全省軍事部署的角度考慮的,將軍的實際兵權,比起獨自控制幾千“軍標”之時,反而有所加強。此時的駐防將軍已經改為滿缺,所統官兵大部也是滿兵,是解釋這兩處將軍事權何以加重的關鍵。
八旗駐防中設置最晚的兩處將軍級單位是伊犁和成都。由于駐地戰事甫定,以及形勢、環境的特殊需要,這兩處的將軍亦被清廷賦予部分節制綠營之權。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平定天山南北,因其地究屬新征服之區,加上距離遙遠,地域廣袤,軍事控制、軍事鎮壓遂占據最突出位置,所以伊犁將軍之權特重,所轄包括在新疆各地的參贊、領隊、辦事、幫辦各大臣,掌天山南北路之軍政,專任邊防之事及統轄“外夷”部落。“凡烏魯木齊、巴里坤所有滿洲、索倫、察哈爾、綠旗官兵,應聽將軍總統調遣。至回部與伊犁相通,自葉爾羌、喀什噶爾至哈密等處駐扎官兵,亦歸將軍兼管”。[29]舊時人將清廷在新疆的統治制度稱之為“軍府制度”,以與內地各省設總督、巡撫之制相對應,正是從清廷在這一地區實行的特殊的軍事統治制度中顯現出來的。 成都是全國十余個將軍級駐防單位中唯一設在西南的一個,其事權、建置等各方面與內省和北部邊疆各駐防都有差異。四川屬新辟地區,打箭爐以西均為“改土歸流”屬地,當地少數民族既不同于內地漢族,也不同于北部邊疆那些與滿族頗有相同之處的諸蒙古、索倫和錫伯等部落,清廷總結了大小金川事變的教訓,認為“皆由歷來地方官釀成”[30],并不諱言設置滿洲駐防將軍的用意就是要監視、彈壓當地大小官員。加上這一地區特殊的軍事位置和與西藏的關系,所以清廷賦予成都將軍的事權,也重于內地駐防將軍:“所設之將軍,若不委以事權,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統屬考核,仍于內地之江寧、浙江等處將軍無異,尚屬有名無實……自應令成都將軍兼轄文武”,“凡番地大小事務,俱一稟將軍,一稟總督,酌商妥辦。所有該處文武各員,升遷調補,及應參應汛,并大計舉劾各事宜,皆以將軍為政,會同總督提奏,庶屬員有所顧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機宜,亦歸畫一”[31]。成都駐防設置于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設成都將軍標中軍副將一人,裁中營游擊一人,改設中軍都司一人。[32] 這就是史料所謂以駐防將軍統綠營者惟四川,或謂惟四川與伊犁的由來。而這兩處軍標無論從制度建立的歷史背景上還是自身的性質上,都與前述三處具有明顯的不同,那就是后兩處將軍之統綠營,都以權力特重作為前提。清廷之所以敢給這兩處將軍委以重權,主要因為所派遣的將軍是最為清廷信任的滿蒙軍事統帥,兵丁也都由滿蒙八旗和東北的部落兵組成,而此時清朝統治已經穩定,對這些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施行的軍事鎮壓也已取得決定性成功,清廷對于在這些地區加強駐防將領的事權,亦就可以更無顧慮。 可見,清初在漢軍駐防地區建立軍標、軍標被撤之后又在福、廣兩處命將軍節制綠旗,以及成都、伊犁兩處的將軍兼統綠營,這三個看似并無關聯的問題,細察起來卻有一脈相承之跡。 八旗與綠營的關系,說到底是旗人與漢人的關系,這是清代滿漢關系的一個重要側面。有清一代,滿族統治者一再標榜“滿漢一家”,但對漢人、哪怕是曾為他們打天下立過犬馬之功的八旗漢軍,其歧視與提防之心也一刻未曾放松。通過“軍標”從設置到被裁撤的過程,我們一則可以看到漢軍對于清朝建立政權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一則可以看到清朝統治者對漢軍表面信任、實則疑慮和限制的做法,這對于評價八旗漢軍在清代的實際地位,也許是一個有用的實例。
[1]這里系指同治朝以前。 [2] 參見鄭天挺《清代的八旗兵和綠營兵》:“將軍統轄的稱“軍標”(只四川、新疆有之)”(載《探微集》中華書局1980,175頁)。關于新疆的軍標,是又一個問題,下文還將詳述。 [3]《清朝文獻通考》卷一八二,頁6425。 [4]羅爾綱:《綠營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版,頁115-202。 [5]由漢軍將領臨時性地兼統綠營之例在清順治初期甚為常見,如順治三年(1646)清廷令付喀禪、李思忠率領八旗滿兵于西安坐鎮。付喀禪授為昂邦章京,提督滿兵;李思忠則授為昂邦章京,提督漢軍及綠營兵。又如張大猷,順治三年授昂邦章京,鎮守江寧,提督漢軍及漢兵等。但均非定制。二人于翌年(即順治四年)便被分別授為陜西與江南的提督總兵官。 [6]《京口八旗志》“序”,光緒五年刻本,頁1。 [7]《大清會典》(雍正十年內府刻本)卷一二六“兵部職方司”。 [8]《康熙起居注》二十年八月二十日,頁744。 [9]八旗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上三旗即鑲黃、正黃與正白,為皇帝直接統領的旗分,其余為下五旗,歸王公統屬,地位低于上三旗。 [10]《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本)卷五五四“兵部·官制”,頁8。 [11]新柱纂:《福州駐防志》卷首“福州將軍新柱為福州駐防城修竣奏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6年點校本,頁533、584。 [1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蔡良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福州駐防志》卷十三,頁652。但從后來軍標裁撤時的文件看,似無如此之多。 [14]《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235頁。 [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一日。 [16]《清朝文獻通考》卷一八二,頁2。 [17]《福州駐防志》卷一“圣謨”,頁545。 [18]參見拙著:《清代八旗駐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清代綠營中的八旗官兵》,載王鐘翰主編:《滿族歷史與文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83-102。 [19]《清高宗實錄》卷四九三,乾隆二十年七月己亥。 [20]《軍機處錄副奏折》乾隆三十年七月三日。 [21]《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本)卷五六零“兵部·官制”,頁17。 [22]《軍機處滿文議復檔》,轉引自《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譯編》,頁32。 [23]《清高宗實錄》卷八一八,乾隆三十三年九月戊子;卷八一九,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庚戌;《清高宗實錄》卷八一六,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丁巳。 [24]《清高宗實錄》卷八一八,乾隆三十三年九月戊子。 [25]黃曾成:《琴江志》卷五“八十一戶之裁汰”,民國十一年鉛印本,頁7。又按,福州三江口水師旗營并非全由旗兵構成,而“多半系老四旗及綠營或召募而集”,其中的“老四旗”即福州駐防八旗漢軍,綠營系指:“立營之始,由省來營領催兵等,有由軍標、督標、撫標撥來三百名。……海壇、閩安撥來一百名”(卷一第二編;卷四第九編)。 [26]《清仁宗實錄》卷一五四,嘉慶十年十二月庚辰。 [27]《清史稿》卷一三一,頁3918-3920。 [28]《駐粵八旗志》卷五“經政略”,光緒五年刊本。 [29]《清高宗實錄》卷六七三,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壬子。 [30]《清高宗實錄》卷一零零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已。 [31]《清高宗實錄》卷一零零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已。 [32]《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本)卷五五三“兵部·官制”,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