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生水》與先秦儒家性情論
歐陽禎人
[摘要] 先秦儒家的哲學(xué)構(gòu)架是始于性情論,而又終于性情論的。在先秦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人的性情是天玄地黃、陰陽大化、風(fēng)雨薄施的摩蕩結(jié)果。先秦儒家吸收了《太一生水》的自然哲學(xué)思想。這不僅體現(xiàn)在儒家哲學(xué)的表述方式上,更為重要的是對(duì)儒家性情論,乃至整個(gè)儒家哲學(xué)的整體架構(gòu)的建立,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關(guān)鍵詞] 陰陽大化 太一生水 神明 儒家性情論
《太一生水》不僅構(gòu)建起了“太一→水→天地→神明→陰陽→四季→滄熱濕燥→歲”的宇宙模式,把這個(gè)模式設(shè)計(jì)為一個(gè)周而復(fù)始的動(dòng)態(tài)過程,而且,這個(gè)過程中的每個(gè)環(huán)節(jié)本身,又是既相對(duì)獨(dú)立,又相對(duì)開放的體系,它們彼此依持、激發(fā)的態(tài)勢(shì)具有明顯的有機(jī)性。《太一生水》是道家思想史上很重要的一篇文字,因?yàn)椤肚f子》等其他道家要籍都很明顯地受了它的深刻影響。筆者想要特別指出的是,既然郭店楚簡(jiǎn)都出自一個(gè)墳?zāi)梗S多篇章是不是可以相互發(fā)明,相互詮釋呢?《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論,與儒家的性情論是不是也具有某種聯(lián)系呢?本文試圖借助先秦儒家的傳世文獻(xiàn)和郭店楚簡(jiǎn)的文本本身,對(duì)這種可能的聯(lián)系進(jìn)行一些探討,以就教于同仁專家。
一
在深入思考之后,筆者以為,《太一生水》的文眼在“神明”兩個(gè)字上。對(duì)“神明”兩個(gè)字的理解,也許是我們參透整個(gè)郭店儒家竹簡(jiǎn)文獻(xiàn)的肯綮。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文本:
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
□□[復(fù)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fù)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fù)相輔
也,是以成四時(shí)。四時(shí)復(fù)相輔也,是以成倉熱。倉熱復(fù)相輔也,是以成濕
燥。濕燥復(fù)相輔也,成歲而止。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者,倉熱之
所生也。倉熱者。四時(shí)者,陰陽之所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
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於水,行於時(shí)。
(《太一生水》第1-6簡(jiǎn))
“太一”生水,是萬事萬物的最終源頭。天地生于“太一”;天地摩蕩,生發(fā)出“神明”。我們的問題是,天地為什么能夠摩蕩,何以又能生出“神明”呢?《莊子·知北游》中的一段話對(duì)我們的理解是有啟發(fā)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shí)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dá)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nèi);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shí)運(yùn)行,各得其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于天矣!”莊子說過,“至精無形”,所以這里的“神明”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它是天與地,陰與陽,以及與“百”物,相摩相蕩,而“化”出的一種神靈之境,是一種天地、陰陽、乾坤、上下、內(nèi)外的感通。“六合為巨,未離其內(nèi);秋豪為小,待之成體”,無影無形,卻又無所不在。
神明的出現(xiàn)是天地摩蕩,陰陽感通的結(jié)果,是生命緣起,靈氣交會(huì)的象征。《太一生水》文章不長,但生發(fā)的“生”字卻一口氣用了八次,對(duì)宇宙生成的過程進(jìn)行了認(rèn)真的探討,(《易傳·上傳》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并且提出了“上,氣也,而謂之天”的重要判斷,把“天”、“天道”與“氣”直接聯(lián)系起來了。在漢字中,氣是一個(gè)象形字,輕微如云翳,流動(dòng)如野馬,層層疊疊,變化萬千。在中國哲學(xué)史上第一次從“氣”的角度,把天道與人的性情聯(lián)系起來的似乎應(yīng)該是《左傳》,這就是著名的“天生六氣”說:
六氣曰陰、陽、風(fēng)、雨、晦、明也。分為四時(shí),序?yàn)槲骞?jié)。過則為災(zāi),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fēng)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昭
公元年)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
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zhàn)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
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
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xié)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昭公二十五年)
在這里,不僅人的喜怒哀樂的情感直接來源于“六氣”,而且人的生老病死也是“六氣”鼓蕩變化的結(jié)果。因此,只有與天道、“六氣”相“配”合,與天地之性合而為一,人的生命才能長久,人的性情才能得到伸張,人的心志才能最終達(dá)到理想的境界。
自然的、天道的“六氣”之所以能化解為人的情感,關(guān)鍵是由于陰陽變化、天道流行引發(fā)的天與人的感通。這種感通,用《太一生水》的話來講,就是“神明”。在先秦時(shí)期的典籍中,“神明”一詞主要只有三個(gè)意思,一是神靈、神祗;二是人的精神;三是不可知的高深莫測(cè)、宇宙玄機(jī)。在先秦儒、道兩家的哲學(xué)體系中,如果僅僅從自然哲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來界定這個(gè)詞的定義,那么主要是第三個(gè)意思。《太一生水》也正是在這一點(diǎn)上取“神明”之意的。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還是來翻一翻目前儒、道兩家學(xué)者聚訟不已,都視為己有的先秦著作《易傳》上面的相關(guān)記載吧: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依此齋
戒,以神明其德夫。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cè)嵊畜w,以體天地之撰,以
通神明之德。
在《易傳》中,始終貫穿其中的是一種天地相摩相蕩,陰陽相推相成,剛?cè)嵯噍o相成的思維定勢(shì),而這種相摩相蕩,相推相成、相輔相成只是一種下學(xué)上達(dá)的手段,天人冥合的途徑,它的真正目的在人,不在自然。準(zhǔn)確地說,在于人與自然的“通”、“會(huì)”、“變”、“化”,一句話,就是“以通神明之德”。把《太一生水》與《易傳》的整個(gè)文本一比較,我們會(huì)驚異地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在思想上的深刻聯(lián)系如出一轍,不僅天人、陰陽、剛?cè)崮κ幍乃季S方式完全一樣,而且有些詞匯出現(xiàn)的順序、頻率,甚至氛圍、語境,都有相通之處。
據(jù)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曾問學(xué)于老子;在《論語》中,也多次反映出孔子具有道家思想,或者說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shí)。竊以為,《易傳》中凡是有“子曰”的地方,也許都可以肯定是孔子的思想。中國科學(xué)院的李學(xué)勤先生甚至還說:“孔子晚年對(duì)《周易》十分愛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傳》(至少其中一部分)。”① 孔子是否創(chuàng)作或參與了《易傳》的寫作,筆者暫時(shí)擱置不論,我們大家還是先來看一看孔子本身的哲學(xué)體系中,有關(guān)“性與天道”的思想。
孔子思想的總框架是“與命與仁”,由此伸發(fā)開來,最高深的學(xué)問就是“性與天道”了。徐復(fù)觀先生說:性與天道“是孔子在自己生命根源之地——性,證驗(yàn)到性即是仁;而仁之先天性、無限的超越性,即是天道;因而使他感到性與天道,是上下貫通的。性與天道上下貫通,這是天進(jìn)入于他的生命之中,從他生命之中,給他的生命以道德的要求、規(guī)定,這便使他對(duì)于天,發(fā)生一種使命感、責(zé)任感、敬畏感。”② 但是,不論從天灌注而下,還是人在現(xiàn)實(shí)中的下學(xué)上達(dá),都是要有一種至真至純的修煉功夫,來體認(rèn)天道、回歸天道、“與天地參”的。
“天地”以“神明”為精神,生發(fā)出陰陽、四時(shí)、滄熱、濕燥,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在《禮記》的《郊特牲》中有“交于神明之義也”,“交于神明者”,
《樂記》有“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jīng)也。禮樂偩天地之情,
達(dá)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雜記》有“交神明之道”,《祭義》有“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祭統(tǒng)》有“交于神明”,“配天地之神明”等等,這些文獻(xiàn)中,“交”“達(dá)”“配”三個(gè)概念的反復(fù)運(yùn)用,生動(dòng)地說明了在先秦儒家的思想體系
中,在天地、天道、天命與人的精神、性情之間,“神明”是人經(jīng)過不斷的努
力,“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的結(jié)果。“神明之德”就是會(huì)通,就是變化,就是天地玄黃、陰陽大化、風(fēng)雨薄施、天道流行的結(jié)果。這是孔子性與天 ① 李學(xué)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頁。
② 徐復(fù)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發(fā)行1969年初版,第99頁。
道思想的擴(kuò)展。
另外,孔子把性與天道聯(lián)系在一起來思考問題,人的性就只能是善的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孔子是崇尚天、天道的。他說:“巍巍乎!唯天為大。”(《論語·泰伯》)滋潤大地,生長萬物的天,是生命的源頭,也是人的性命的皈依,因此,十全十美的“天”灌注而下而成為人的“性”,當(dāng)然就是人性的范本。《性自命出》的“四海之內(nèi),其性一也”(第9簡(jiǎn))說的就是天道之性,就是善性,因?yàn)樗挥幸粋€(gè)來源,那就是天命、天道。當(dāng)身心修煉導(dǎo)致人的內(nèi)在人格最后與天道融為一體的時(shí)候,就與天地感通,達(dá)到了“神明之德”。這應(yīng)該是從孔子、曾子到子思、孟子的一貫性理路。
二
《性自命出》不僅構(gòu)建起了一套由天命灌注而下的“性情”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它把人的生命直接屆定為“性情”與外物的摩蕩,把“性”定義為“喜怒哀悲之氣”,(第2簡(jiǎn))是一個(gè)“好惡,性也”(第4簡(jiǎn))的動(dòng)態(tài)過程。在《性自命出》中,“性”是生命的本質(zhì),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nèi)在資源。但是,由于它依托于天命,生發(fā)于心志,假借于“情感”而意氣風(fēng)發(fā)、搖曳多姿,因而使人的“性”“情”個(gè)性化、感性化、情感化(先秦時(shí)期,“情”字的外延和內(nèi)涵往往比現(xiàn)代漢語中的“情”字寬泛),凸顯了個(gè)體存有的理據(jù):“凡聲,其出于情也信。”(第23簡(jiǎn))“凡人偽為可惡也。”(第48簡(jiǎn))“凡人情為可悅也。茍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茍有其情,雖未之為,斯人信之矣。”(第50、51簡(jiǎn))把真性摯情提升為衡量一切是非善惡的標(biāo)準(zhǔn)。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性自命出》把“性”與“氣”聯(lián)系了起來,人生內(nèi)在的資質(zhì)與外界的好惡摩蕩,就像“氣”的吞吐、伸縮、變化、飛動(dòng)一樣,因物而動(dòng),因情而發(fā),因志而歸。所以,人的“性”就成了一種可以修煉、提升、掌握的東西。
這種動(dòng)態(tài)的真性摯情在整個(gè)儒家哲學(xué)體系中最終的來源實(shí)際上是“天道”的精神,《性自命出》的性情論只不過貫徹了《禮記·禮器》中“天道至教”的一貫性思想而已。這種思想的一貫性,從《周易》、《易傳》、《禮記》一直到郭店楚簡(jiǎn),草蛇灰線,千里伏脈,是有跡可循的:《周易》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shí)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shí)。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易傳》載:“是故剛?cè)嵯嗄Γ素韵嗍帯9闹岳做瑵欀燥L(fēng)雨,日月運(yùn)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禮記·禮運(yùn)》亦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huì),五行之秀氣也,......天地之心也。”人既是宇宙精神的結(jié)果,也是宇宙精神的體現(xiàn)。性情的搖蕩,更是天地陰陽感動(dòng)于人的心志而生發(fā)的結(jié)果。人生的一切,在先秦儒家看來,實(shí)際上只是“天道”“天命”在世界上的投射,人的生命由天命灌注而成,人在社會(huì)倫理中的各種關(guān)系,在郭店楚簡(jiǎn)中被稱之為“天常”,就是天經(jīng)地義的“天道”復(fù)本。
因此,長期以來,在先秦儒家的筆下,人的性情從來都是與宇宙的陰陽大化、天道流行交織在一起的。在筆者看來,這是先秦儒家受到并吸取了道家《太一生水》以及相關(guān)文獻(xiàn)的啟發(fā)而把自然哲學(xué)的成果引進(jìn)了人文學(xué)科的領(lǐng)域:
“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zhuǎn)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shí),列而
為鬼神。”“故圣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shí)為柄,以日
星為紀(jì),月以為量。”(《禮記·禮運(yùn)》)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兇,吉兇生大業(yè)。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shí),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易傳》)
凡禮,始乎托,成乎文,終乎樂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
代勝;其下,復(fù)情以歸太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shí)以序,星辰以
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jié),喜怒以當(dāng);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
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荀子·禮論》)
在《禮運(yùn)》中,“太一”很顯然,是一個(gè)高于陰陽的終極性的本體論概念,是宇宙的終極起源。由太一而天地,而陰陽,而四時(shí),而日月,而寒暑濕燥,其思維的理路與《太一生水》是完全一致的。《荀子·禮論》不僅在思路上與《太一生水》完全一致,而且把“禮”、“情”、“文”與天地、日月、四時(shí)、星辰相提并論,而復(fù)歸于太一。特別是《荀子·天論》中的一段話,應(yīng)該引起我們高度的注意:“列星隨旋,日月遞,四時(shí)代御,陰陽大化,風(fēng)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圣人為不求知天。”這段話從精神的深處繼承和發(fā)展了郭店楚簡(jiǎn)《太一生水》的神韻,雖然沒有明確地論述人的性情是何以生成,但是,這段話是包含了人的性情的,它以中國哲學(xué)特有的表述方式說明了人的生命特別是性情與大自然相互摩蕩的狀態(tài)。與《太一生水》“天地復(fù)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既出,則萬物生發(fā)的理路如出一轍。先秦儒家的這種人學(xué)思維理路,奠定了儒家人學(xué)的基礎(chǔ),從自然哲學(xué)的角度說明了人的性情生發(fā)的天道根據(jù)。儒家哲學(xué)始于茲,終于茲的思想是值得我們認(rèn)真反思的。③
以上各段文獻(xiàn),或以為時(shí)代太晚,并不足以說明什么問題。但是我們從上面的文獻(xiàn)中已經(jīng)分明看到,至少在戰(zhàn)國時(shí)期,儒家思想已經(jīng)全面融會(huì)了“太一”的思想,或者至少說明,儒家思想的《太一生水》的聯(lián)系,已經(jīng)從郭店儒簡(jiǎn)開始。
在《性自命出》中,性情、心志都是在與外界的取予、摩蕩之中生發(fā)出來的:“喜怒愛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shì)也。凡性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人之雖有性,心弗取不出。凡心有志也,無與不可。性不可獨(dú)行,猶口之不可獨(dú)言也。”(第2-7簡(jiǎn))這里有兩點(diǎn)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性情、心志不是僵死、固定的不變之物,而是“見于外,則物取之”的動(dòng)態(tài)之“氣”;第二, 性情、心志,沒有外在事物的誘發(fā),就不可能搖曳多姿地釋放出來。這種因外感而動(dòng)的性情論,在先秦時(shí)期的儒學(xué)中實(shí)際上并非肇始于《性自命出》。像孔子“迅雷風(fēng)烈必變”(《論語·鄉(xiāng)黨》)的判斷提出疾雷大風(fēng)一定會(huì)改變?nèi)说男郧椤⑸裆粯樱吨芤住ふ鹭浴肪兔鞔_地說,巨大的雷聲滾滾而來(“雷索索”),就會(huì)使人產(chǎn)生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驚恐情感,“震驚百里,驚遠(yuǎn)而懼邇也。”(這是一種特殊的宗教情感,但筆者以為,儒家的宗教情感是以自然情感為基礎(chǔ)的)因此,“君子以恐懼修省”。可見,《周易》的作者已經(jīng)深諳感動(dòng)于大自然的雨雪風(fēng)霜、驚雷閃電,可以產(chǎn)生各種主體性情變化的道理,并且提出了以一種“恐懼”的心態(tài)來自我“修省”以及“恐致福也”的心性論主張。
————————————
③ 儒家哲學(xué)以性情為出發(fā)點(diǎn),又以性情為歸宿的理論走向是由儒家人文主義的內(nèi)涵決定了的必然走向。一方面它提倡親親,另一方面它又提倡慎終追遠(yuǎn)。這都是儒家思想的宗教情懷。在《性自命出》中干脆提出了“反善復(fù)始”的命題,以實(shí)現(xiàn)本始的原初實(shí)在。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中借助先秦儒家的思想,發(fā)揮得更為徹底:“人之形體,化天數(shù)而成;人之血?dú)猓熘径剩蝗酥滦校炖矶x。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shí)。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達(dá)也;怒,秋之達(dá)也;樂,夏之達(dá)也;哀,冬之達(dá)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董仲舒的性情論是秦漢時(shí)期儒家哲學(xué)中比較徹底、全面、深刻的一家,他的論述應(yīng)該說是先秦儒家性情論的總結(jié),他根源于《周易》,融匯了孟子與荀子的思想精華,與郭店楚簡(jiǎn)《太一生水》導(dǎo)引出的性情論具有邏輯聯(lián)系。人的性情來源于天,而又復(fù)歸于天,天與人最終融為一體,天人合一,天人冥合,是中國哲學(xué)是最根本的理論形態(tài)和特點(diǎn)。
走筆至此,我們就不得不提及《孟子·公孫丑》關(guān)于心志氣化的論述了: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dòng)心,與告子之不動(dòng)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心,
勿求于氣,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dòng)氣,氣壹則動(dòng)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dòng)
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管子·內(nèi)業(yè)》說“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nèi)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楚辭·遠(yuǎn)游》中又有“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露。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這似乎就是孟子的“日夜之所息”的“平旦之氣”,就是稷下黃老學(xué)派的“氣”,也就是《太一生水》“上,氣也,而謂之天”的“氣”,是客觀存在的。由孟子的思想體系來看,他的“浩然之氣”有一個(gè)由“平旦之氣”到“浩然之氣”提升、修養(yǎng)的過程。孟子所追求的是一種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的精神境界,但是,這種“氣”的形成,顯然有生物性、自然性的基礎(chǔ),是天地“六氣”與人的性情摩蕩的結(jié)果。然而,孟子的“浩然之氣”的理論中最為關(guān)鍵的是“明道”與“集義”,是仁義禮智信圣的融入,并最終成為“浩然之氣”的主體。這當(dāng)然是孟子的哲學(xué)提升。
孟子的“配義與道”的命題還點(diǎn)明了生發(fā)于心志,充滿于身心的“氣”,一方面是個(gè)人不斷努力,長期積累、修習(xí)而成的,其核心是一個(gè)“養(yǎng)”字,因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另一方面,它也告訴我們,這種積累、修養(yǎng),最終要感動(dòng)于天地、神明。“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本來就是與“天”融為一體的。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志壹則動(dòng)氣,氣壹則動(dòng)志”,至誠無欺,感動(dòng)“神明”,就可以氣化流行,上達(dá)于天,“氣化而成天”,與天地精神相冥合,徹底完成由《太一生水》等道家的“氣”到孟子“浩然之氣”的飛躍。孟子的“養(yǎng)氣”論,在先秦儒家學(xué)說的發(fā)展中有它邏輯性的發(fā)展路徑,而正是這種理論發(fā)展的路徑,透露了《太一生水》與郭店楚簡(jiǎn)其他儒家篇章的關(guān)系。
先秦儒家哲學(xué)最高深而又最凡俗的學(xué)問,就是“惇于反己”的“為己之學(xué)”(這是郭店楚簡(jiǎn)中最為突出的特點(diǎn)之一,至少有《五行》、《窮達(dá)以時(shí)》、《唐虞之道》、《成之聞之》、《性自命出》、《尊德義》等都正面地論述了這種學(xué)問),它的至高境界就是要培養(yǎng)出一種“至大至剛”的“氣”,用帛書《五行》“說”的話來說,就是要通過“獨(dú)”、“一”、“集大成”達(dá)到“舍體”而超生。這里的“舍體”就是上達(dá)于天地精神的境界,這種境界就正是天道、天命灌注于人心的遙契之機(jī)——神明的獲得。認(rèn)識(shí)到了這一點(diǎn),我們就知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理路,本來是離不開《太一生水》中的“神明”的。《五行》的心性論[仁之思也精,精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仁。智之思則長,長則得,得則不忘,不忘則明,明則見賢人,見賢人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智。圣之思也輕,輕則形,形則不忘,不忘則聰,聰則聞君子道,聞君子道則玉音,玉音則形,形則圣。(第12-16簡(jiǎn))] 和《性自命出》的身心論[君子執(zhí)志必有夫光光之心,出言必有夫柬柬之信,賓客之禮必有夫齊齊之容,祭祀必有夫齊齊之敬,居喪必有夫戀戀之哀。君子身以為主心。(第65-67簡(jiǎn))],是必須通過“神明”才能最終下學(xué)上達(dá)的。
學(xué)報(bào).jpg)
報(bào).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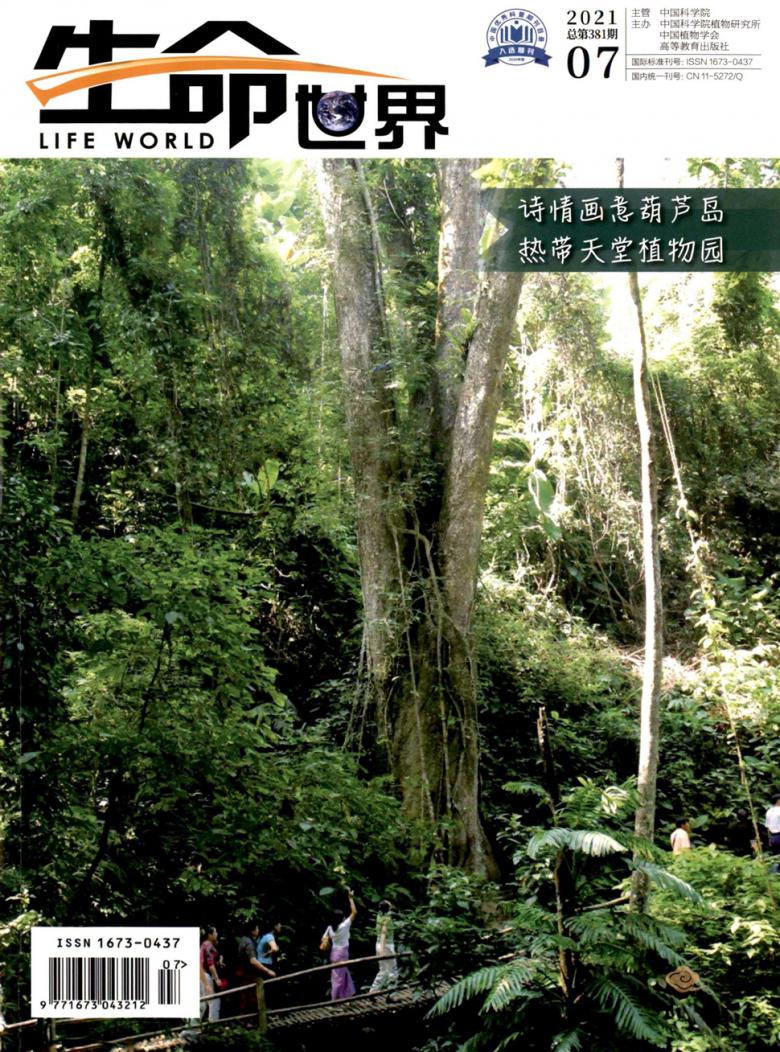
濟(jì)學(xué).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