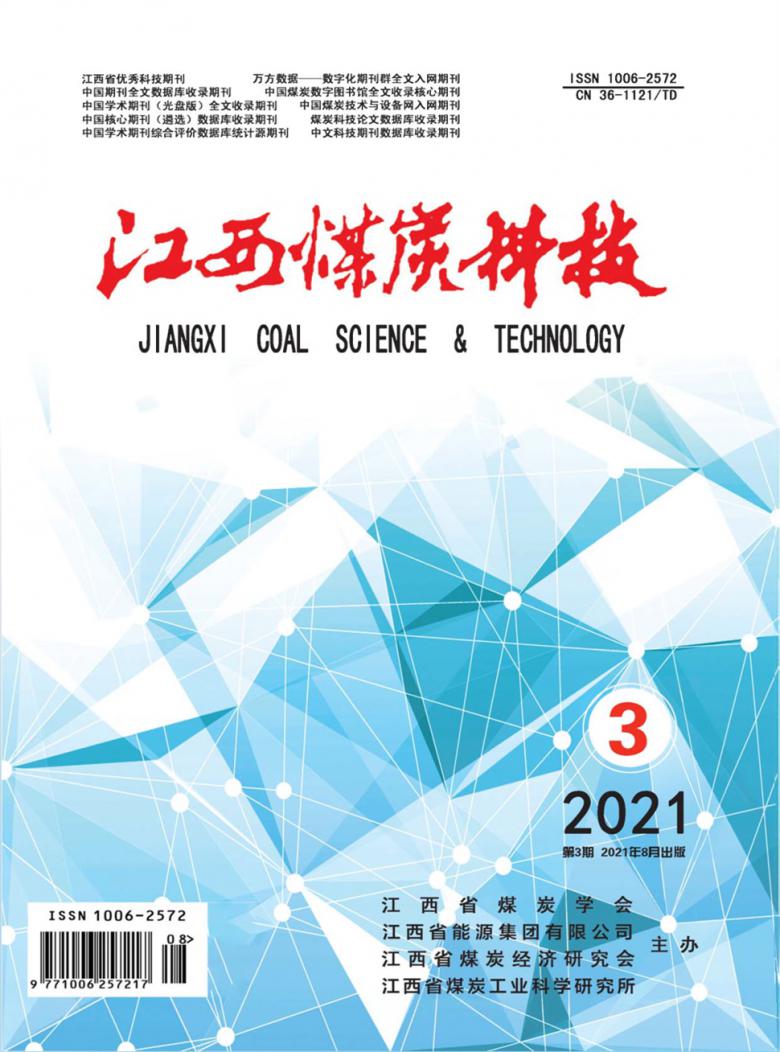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
張家炎
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地區同屬長江中下游平原,光、熱、水、氣、土等自然條件亦大致相當,但兩地的經濟水平卻頗有差別,其原因復雜多樣,本文僅以明清時期兩地農業經濟的發展為比較對象,討論了以下問題:1.農業經營重點的次第轉變;2.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結構轉變的正負作用;3.城、鎮工商業經濟對當地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
"蘇湖熟,天下足"或"蘇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時代,"湖廣熟,天下足"則流行于明清之際,這兩句略帶夸張的諺語表明了蘇湖(常)和湖廣地區糧食生產不同時期內在全國的重要地位。"蘇湖(常)",代表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所謂"湖廣"其實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內的沿江瀕湖平原地帶,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吳越文化,后者則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長江三角洲地區有國人引以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遺址,而兩湖平原也有令人驚異的彭頭山水稻遺存,這表明兩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獨立起源,且發展難分伯仲。實際上戰國時期荊楚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均一度領先于吳越,只是后來荊楚經濟漸衰而吳越日盛,到宋元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發展水平已居國之首,其時的兩湖地區在不少人眼中卻仍是"火耕水耨"、"地曠人稀"的化外蠻邦。明清兩湖平原農業經濟的勃興有漸振昔日雄風之勢,"湖廣熟,天下足"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斯時湖廣地區漸成全國新的米糧中心,但還不能說該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超過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對這兩個地區明清時期農業經濟的發展已有不少學者作了大量卓有見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無意對"蘇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廣熟,天下足"二諺本身及其傳布進行詳細的考證與詮釋,而想從這兩條諺語的轉變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含義,對諸如發生這種轉變所代表的農村經濟結構變化的異同及產生這種變化的內外條件、結果與影響等問題進行粗線條的勾勒。如果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兩湖平原可以作為封建晚期發達地區與已發展地區的各自代表的話[①b],則這對發達地區與已發展地區的經濟發展與互補似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一、農業經營重點的次第轉變
在開始比較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兩湖平原明清時期農業經營重點轉變之前有必要簡要引述一下兩地的自然經濟地理條件。從全國地理區劃角度來看,這兩個地區同屬于一個經濟地理單元,即長江中下游平原區,光、熱、水、氣、土壤等條件大致相當,差別甚微。
長江三角洲地區通常是指圍繞太湖的蘇、松、常、鎮、杭、嘉、湖諸府所屬(明清時期行政區劃),擴大時有時也包括寧紹平原。該地區地勢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為主。蘇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2-5米,寧紹平原也低于20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1700毫米;水源豐富,太湖集水面積19000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達43億立方米;土壤條件好,有機質含量高,熟土層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熱量條件好,年均氣溫15-19℃,年均無霜期230-280天[②b]。
兩湖平原主要指江漢-洞庭湖平原及鄂東沿江平原。江漢平原及鄂東沿江平原地勢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35米,較高亢平原與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帶狀相間排列;年均降雨量1100-1400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長期內;無霜期250-280天;區內大部分耕地系沖積土,富含有機質與礦物質,自然肥力高,土質疏松易于耕作[③b]。洞庭湖平原亦屬湖積平原,土層深厚松軟,富含有機質;年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無霜期250-280天;年均氣溫16.5-17℃。[④b]
這兩個地區的共同優勢是宜農、宜漁,水上交通便利,貿易條件優越。
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唐末以迄宋元時代不斷發展漸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所在,盛產米糧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蘇湖(常)熟,天下足"之諺的廣泛流傳,該時期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種植是當地種植業,也是當地農業生產的主要內容。明代中葉這種情況發生改變,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漸次下降而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漸次上升,不但如此,農民投入經濟作物生產的人力也更多,技術更細膩,農戶農業經營的重點已不在種植糧食作物的"田",而在種植經濟作物的"地",有所謂"多種田不如多種地"的新的價值取向[⑤b]。這種轉變在不同的小區域內側重點又有所不同,農業生產總的發展態勢表現為多樣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東、以北的水鄉地帶仍基本以種植水稻為主,并輔之以麥類、油菜、席草等糧食、經濟作物;在瀕江臨海的岡身沙土地帶則以棉花、水稻為主,雜植麥、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邊及浙西平原地勢高亢而近水的地區則以植蠶桑、水稻為主,并兼植麥豆、煙草、烏桕等糧食、經濟作物;蘇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帶以植旱地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當地農民在種植上述不同經濟作物時往往有與之相宜的生產活動互為關連,如植棉與紡紗、栽桑與繅絲等,并漸漸在不同自然區域或生產個體間形成分工,甚而演化為專業性生產,其收支盈虧與市場需求大小緊密相連。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結構演變的主要內容即這些多樣化生產及由此而導致的農業生產綜合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發展趨勢。[①c]。
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復雜多樣,人多地少也許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間人均尚有耕地3.5畝,所產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僅1.2畝左右,以當時平均約2石的畝產量估算,人均得糧僅2.4石[②c],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論稅糧、飼料、種子等其它方面用糧。
以常理論,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當更應加強糧食作物的生產,如擴大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提高復種指數、提高單產以盡量增加糧食總產量。但該地卻恰恰相反,他們反常規的作法主要基于利益的考慮,因為種植糧食尤其是水稻不僅花工多、對季節要求嚴格,受自然條件如水旱影響大,且在生產技術未有重大突破的傳統農業前提下,水稻增產潛力有限(御稻在蘇南推廣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不合算,農民對它不感興趣,封建帝王出面推廣水稻品種也竟然無果而終,這說明當地民眾對實際利益看重的程度),而種植經濟作物如栽桑,用工雖多但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較小,更主要的是潛在產出值高,可獲得比種糧食高出數倍的收入。有的地方最初只是在土壤條件較差的田塊或田旁路邊植桑,后來干脆用上好的稻田栽桑,即所謂"桑爭稻田"。桑樹部分取代水稻不僅僅是作物種類的簡單置換,它更主要的是體現了農業經營重點從集約化程度較低的生產部門向集約化程度相對較高生產部門的轉移,由于栽桑比種稻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因而又有從勞動力密集向資金密集轉移的特點,已經出現了質的變化[③c]。類似情況還有因改種棉花、煙草而出現的"棉爭稻田"、"煙爭稻田"等。
當地農民用在經濟作物上獲得的、遠遠超過種植糧食作物的收益不僅可以完納賦稅(一條鞭法施行后可以以錢代糧),也可以從市場上購得自己糧食需求中的不足部分。顯然,要到市場上購買糧食就必須有足夠的糧食進入流通領域作為前提條件,即要有充盈的賣方市場,此時的兩湖地區正好充當了這一角色。
弘治以后兩湖地區能大量輸出米谷同樣有復雜的社會經濟原因,主要基于該地農業生產的勃興和中轉沿邊省分米糧[④c];其次是該地人均耕地較多,賦稅漕糧負擔較低,米價較低等[⑤c]。明代初期,兩湖地區開始大興垸田,并在明代中葉形成一個高潮,垸田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土壤特性較適宜于種水稻,因此垸田的大量墾辟實際上即不斷擴大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種植面積[⑥c]。這是明清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結構演變中最為矚目的事情。盡管明清時期總體而論兩湖地區的水稻生產技術水平及單產量均不及長江三角洲地區[①d],由于在有明一代兩湖平原人口密度相對較低,得以有大量余糧輸出;沿邊省分如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亦藉此地(主要是漢口米市)轉運,其相對較低的價格吸引了大量以營利為目的的商人將其轉運各方;加上漕糧、軍米等官糧的大量調拔,遂給朝野人士形成"湖廣熟,天下足"的感覺。
"湖廣熟,天下足"一諺中的"湖廣"經今人考證并非整個兩湖地區,而主要是兩湖境內糧食生產最發達的幾個農業經濟區,即今湖南境內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湖北的江漢平原和鄂東沿江平原(按有的劃分方式,這其中的大部分亦可歸為江漢平原[②d]),亦即廣義上的兩湖平原。所謂"天下"則主要指南半個中國,尤其是長江、珠江兩流域對湖廣米糧的依賴[③d]。當然其中也有相當數量逆漢水而上陜晉中原[④d]。
"天下"皆賴"湖廣"的態勢在清中葉后發生蛻變,兩湖地區由于人口日多、水災頻仍等原因出現生產停滯,其米糧輸出也盛極而衰,雄風不再。雖然兩湖米糧濟運江浙的現象直至解放前并未停止,但其可使"天下足"的米糧濟運規模與聲勢已成昔日黃花[⑤d]。如果兩湖平原在水稻生產達到一定程度難以再有突破時能循長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軌跡開始結構轉型亦屬理想,然而兩湖平原在此方面雖有發展趨勢,但沒有取得成功。該地區明清時期在發展糧食作物生產的同時其實并未偏廢經濟作物的生產,兩者甚至可以說并行不悖,并終至形成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為輔的總體生產格局[⑥d](洞庭湖平原的經濟作物比重較小)。雖然兩湖境內經濟作物種植比例超過糧食作物的地區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帶及沿邊山區,平原湖區鮮有這種情況發生。而且該地經濟作物的種植以棉花和麻類為主,均屬勞動密集型種植生產,需要資金投入的蠶絲業則極不發達。麻類主要以原料形式自用或出售,棉花則用于家庭紡織或直接進入流通領域[⑦d]。當湖廣棉布行銷天下時,長江三角洲地區并未在棉布上與之一爭雌雄,而是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轉向效益更高的蠶桑業[⑧d]。兩湖地區的農業發展較之三角洲地區總是慢一拍,但當清中葉之后兩湖平原出現嚴重的農業人口相對過剩時卻沒有發生如當初三角洲地區由糧食作物向經濟作物生產的大規模傾斜轉移,糧食作物生產始終占主導地位,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農業生產性質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完全不同。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種糧自食、經作換錢,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分離,副業商業化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向;而兩湖平原糧食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二位一體,糧食商品化亦即主業商品化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向,兩者存在本質的區別[⑨d]。
二、兩地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結構轉變的正負作用
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人口的相對過剩現象出現較早,這些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出路大致有內外兩種消化途徑。內部消化或稱內部轉移是指農民并不離開土地拋棄田作,而是在努力經營好大田生產的同時利用閑暇時間從事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包括絲織、紡紗、編織、燒窯等業。這些家庭副業、手工業在當地農村經濟生活中作用甚巨,不可或缺,農家既以其收入維生計、納賦稅,還要靠它反哺農業,誰家的副業和手工業收入高,對農田投資就多,田也種得好,反之則否。從事農村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的有農閑的青壯勞力,也有勞動力機會成本幾乎為零的婦女兒童,他們晝耕夜織終歲辛勞,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富庶正是建立在農戶日夜勞作的基礎之上,甚至有以此而致富者[①e]。
外部消化或稱外部轉移是指農民離開土地,向其它行業或異地謀生,這種途徑的農民又可細分為三類:1.離土不離鄉,指被迫淪為奴仆,依附于富家大族賣身過活者,總人數當不多;2.流入城鎮成為工商人口,這些失去土地的城鎮新成員不僅為繁榮當地工商業經濟作出了歷史貢獻,其中在勞工市場上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生存的人還是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濫觴;3.流向開發中或未開發地區,既有政府的強制移民也有向未開發地區或開發中地區尋求拓展的自然移民,其流向地便包括兩湖地區[②e]。以上各種轉移方式或途徑當然并非涇渭分明,更多的情況下往往是多種形式交錯發生,其中以亦工亦農亦商型的轉移方式或稱"不完全轉移"的比例最大,屬于可農亦可非農的過渡形態[③e]。
兩湖地區開發滯后在移民上亦有所體現。西晉八王之亂及唐中葉安史之亂時大量北方移民遷居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他們對該地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直至明清時代兩湖地區才成為移民出入的主舞臺,在這次始于元末止于清代的長江流域內東西向移民運動中,遷入兩湖地區的移民來自十余省分,而主體源于長江下游,尤其是江西。與此同時,大量的兩湖人又移居四川,在這一進一出的過程中兩湖地區人口結構與數量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移入者多集中在平原湖區和河谷地帶,而移出者多是毗鄰川省的居民[④e]。外地移民入籍之后增加了對耕地的需求,而兩湖境內平原地帶的大量湖荒正是在這一時期得到不斷開發,康熙末年至嘉慶年間兩湖人口高速發展而垸田開墾也達到高峰并及至于濫。兩湖地區勞動力轉移與此密切相關。乾隆初年兩湖平原的農業人口相對過剩已表現明顯,"湖廣熟,天下足"之說漸失其往昔誘人之魅力,該地農業人口相對過剩之后的出路也有內外兩種消化途徑,內部消化主要通過更多地墾殖進行,外部消化主要是向平原沿邊山區移民[⑤e]。
靠擴展耕地面積、增加復種指數、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等農業內方法消融日益增長的人口的糧食需求是傳統的解決方式,但在某一具體地區當耕地擴展告罄而無重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其容量受到限制,當人口增長到一定臨界點之后必然會降低人民的生活水準,因此更積極的方式是依靠農業外的力量如進行擇業的改變(其前提是整個社會有糧食供應,哪怕是洋米)來消融相對過剩的農業人口。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與努力,他們放眼于狹義的以種植業為主要內容的農業之外,或者雖仍不離農業,但徙居生產條件相對落后的異地,以先進者身份帶動當地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并同時獲得相應的酬報,這些無疑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顯然遜色不少,入城鎮務工商的農業外擇業變化極其有限,主要靠的是墾荒與向外移民。從宏觀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兩種方式不僅不具備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積極作用,反而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無窮的后患。兩湖平原跨荊江而立,荊江乃長江水文最復雜、矛盾最多的地段,江南洞庭湖平原并無巨大堤岸屏護,向系長江自然調蓄池,但明清沿湖不斷被墾,湖面日漸縮小并阻壅洪水自然渲泄,洪災年甚一年,化解人口壓力的惡果是環境的嚴重破壞與生命財產的不斷損失。江北江漢平原襟江帶漢,以堤為命,一旦堤決則漫漶無邊、積水兼旬,恢復生產較難。明清由于不斷濫圍濫墾,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堤防壓力,結果使得荊江兩岸在清代后期幾乎無年無災。向平原沿邊生產條件較差、生產水平較落后的山區移民效果亦極不理想。川陜楚交界地帶、湘鄂西山區均曾掀起過墾山的高潮,雖則初期的墾荒為移民換得了一時之溫飽,然而墾山對環境破壞的負面影響卻是深刻而久遠的,其后果用"災難"一詞形容并不為過。首先,毀林開荒得來的耕地由于水土流失嚴重,表土層侵蝕殆盡,幾年之后人們只好棄地他往,與藉此地化解人口壓力的初衷背道而馳。其次,也是更為可怕的是盲目的毀林開荒不僅大大降低了長江中游大小支流兩岸地帶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頻發,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壓力,且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荊江河段沉降淤積抬高水位又增加對堤防的威脅;不斷的泥沙淤積還迫使堤岸不斷增高,致使漢水、長江部分河段成為地上河。因此,即或無災之年,由于水懸地上,許多地方地下水位偏高,極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長,兩湖平原水災之多、之重鮮有能匹。到清代后期,該地水患已嚴重到阻滯當地經濟發展的程度[①f]。其結果受害最重的竟正是輸出這些移民的兩湖平原地區[②f]!直至今天洞庭湖區及荊江沿岸地帶仍飽受潴水之苦而乏解決之良策。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業相對過剩人口的出路實際上代表了兩種具有本質區別的轉移方式。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屬于平面拓展耕地的最低層次,主要屬內部轉移,也是同一時期內中國農業的普遍和典型代表方式,這種方式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時間為前提,它要求耕地面積(或至少是作物播種面積)與人口成線性比例增加,當可利用耕地增加到極限程度而轉移方式不變的話,人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總爆發,降低生存標準、社會劇烈動蕩等情況都有可能相隨而生。
長江三角洲地區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則已開始突破單純內部轉移的方式向外部轉移過渡,并在局部地區取得成功。它并不要求耕地數量的等比例增加,但強調收入的等量增長,它僅代表了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個農業經濟區(另如珠江三角洲地區),由于其外部轉移是建立在內部轉移已成熟或完備的基礎之上,因此三角洲地區農村相對過剩人口的轉移方式當更具有借鑒意義。
在粗略比較了兩地相對過剩農業人口轉移方式及作用后,這里附帶提及一下兩地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差異。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不僅經濟繁盛冠于全國,亦是天下人文淵藪,整體文化素質較高,這不但表現在純思想、文學等方面人才之多,作品之盛,即或地主小農亦多以"耕讀傳家",有一部分士紳由于不同的原因參與了農業生產并記下心得要點,以農書形式傳世。在王毓瑚先生《中國農學書錄》中指明著者為江浙籍人的便有130部之多(全書共輯錄存佚農書545部),其中屬于反映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著名地區性農書有《沈氏農書》、《補農書》、《浦泖農咨》等(姑不論松江人徐光啟所撰之集大成的煌煌巨著《農政全書》)。這些農書記載了當地較其它地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掌握了這些先進生產技術的農民其素質亦當較其它地區農民素質要高。
明清兩湖地區雖曾有公安三袁、湖湘學派等領一時之風騷,但就農業文化而言,其地的農書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卻都無法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兩湖地區未曾見有發生重大影響的綜合性傳世農書,寥寥數部小型專業化農書亦且散失殆盡,所保存者其價值無一堪與《補農書》之類農書相比較。如果從各地農書多寡與質量高低可以判別各地當時業農者農業技術水平高低的話[①g],則兩湖地區農民文化素質低于三角洲地區也是影響兩湖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②g]。從這項比較可否引申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人口的多寡并非一地經濟落后與否的決定條件,人口作為一柄雙刃劍,既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也可以阻滯其發展,這其中包含一個適度的問題,在適度的前提下人口素質的高低則起主要作用,相同密度但相對較高素質的人口顯然能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反之則否。 三、城、鎮工商業經濟對當地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相對過剩農業人口部分移入當地市鎮,一方面減輕了對有限耕地的壓力,一方面也促進了市鎮經濟的繁榮,該地區市鎮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周圍農村的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的,一地市鎮數量的多寡往往與當地農村經濟的盛衰相輝映[③g],而市鎮的類型及發展規模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當地農村副業、手工業的特色與發展水平。農業生產保證了城鎮非農產業人口對農副產品如糧食、菜蔬等的需要,不足部分才輸自外地;農業生產同時也為當地市鎮手工業、城市工業提供了原材料及半成品,包括供紡織印染用的棉花、棉布,供絲織用的蠶繭等,也正是因為當地城鎮工業、手工業對絲、棉等原料或半成品的不斷需求才保證了周圍農村的農民能盡心于栽桑養蠶種棉織布等屬于傳統農業中副業部分的生產(實際上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這些副業在許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已成主業)[④g]。研究表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主要農村市鎮按重要性依次為絲綢業市鎮、棉布業市鎮及糧食業市鎮[⑤g],其與農村經濟的緊密相關程度不言自明。
明清兩湖平原的農村市鎮無論從規模、數量還是功能上都無法與同一時期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同類市鎮相比擬[①h],影響較著、稍可比擬者唯幾個大中城市。按照區域市場經濟理論,每個經濟區都有它的中心市場,長江三角洲地區充當此類角色的大中城市較多,如蘇、錫、常、杭、嘉、湖皆然,滬、寧作用更大。尤其是上海,晚近曾是遠東第一大城,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有強大的經濟輻射作用,該地許多新鎮即由于設立新工廠、出現新行業而形成[②h]。漢口是兩湖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國也享有盛名,其名不在生產而在流通,因其處江、漢交匯之寶地,扼"九省通衢"之要沖,舟楫往來、百貨充積,通過該地轉運的絕大多數是糧、棉、茶、木材等農業初級產品,兩湖產品在其中占了相當的份額[③h]。江漢平原是兩湖境內的富庶之地,其境內的沙市在宜昌、漢口等城市未崛起前是荊江兩岸即兩湖腹地的重要中心市場,該城也是一座貿易城[④h]。兩湖地區的大中城市極少具有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相同的生產功能,它們的單純轉口貿易性質未能形成足以自立的手工工場或大型專業化手工業市場,也沒有發生大量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⑤h],因而未能有效吸納周圍地區的相對過剩農業人口,未能形成相當規模的早期產業工人后備軍,未能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初級產品加工增值,整個地區的經濟格局亦完全未能突破傳統農業的樊籬。至于散處各地的市鎮功能更形單一,除了是政治中心以外,商業功用多僅交換貨物而已,鮮有從政治、軍事功能分離出來成為以經濟功能或生產中心面貌出現的市鎮,而這樣的市鎮在長江三角洲地區顯然較多[⑥h]。
由于兩湖地區的市鎮主要只能吸納當地農村的農業初級產品,極不利于該地農業過剩人口的非農轉化和農業生產結構的深層次變化,農民主要是追求如何多墾荒地來增加總產而較少考慮擇業的變化,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業(又主要是水稻種植)一直是該地農業生產的主要內容。其經濟作物生產的大宗是種植棉花,兩湖平原地區(尤其是江漢平原)雖亦以輸出棉布聞名于世并曾一度擠占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產棉布的市場[⑦h],但細究發現這幾乎全是農余的手工制品,它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其產品用于到墟市上交換農戶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或完納賦稅,個體生產規模未能擴大,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轉運貿易主要是靠賤買貴賣套取利潤,無助于商業資本向生產的轉移,它可以更多地利用閑暇時間,尤其是婦女兒童的時間,反正他們的機會成本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幾乎為零。這一點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較相似,但此類勞動的使用在兩湖平原地區并未導致青壯勞力從農業中分離,而且當兩湖平原地區所產棉布擠占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產棉布市場之時,后者也已向經濟收益更高的產業如絲織業進行轉移了,倒不是這一地區棉紡織技術落后了或產量降低了[⑧h]。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地區農村經濟結構的演變是相輔相承、次第進行的。當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將經營重點轉向經濟作物種植、進入城鎮成為工商業者時,依賴的正是以兩湖平原為代表的地區的米糧供應,或者說兩湖平原地區大力發展糧食生產正是因為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經營重點發生改變而提供了機遇。兩者經營重點的次第變化雖說是當時經濟條件下專業生產在不同地區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國形成一個完整的市場,但這兩個地區的發展卻相差了一個層次并對以后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兩湖平原農民以低效率、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支持了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結構的逐漸轉型。
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與兩地農村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不同轉移方式及市鎮經濟對農村的不同反饋作用密切相關。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剩余勞動時間的農業外轉移(這里的農業主要指狹義農業即傳統意義上的種植業)有利于當地農村經濟結構向專業化、商業化轉變和整個地區工商業經濟的繁榮,而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平面轉移(即盡量擴大作物種植面積)不僅融納程度有限,墾山圍垸反而帶來阻滯當地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同時,長江三角洲地區發達的市鎮工商業、手工業經濟無疑也有助于當地農村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兩湖平原地區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長江三角洲地區明清時期農村經濟結構向多樣化、專業化和商業化的緩慢轉變及由此形成的相對發達的整體社會經濟基礎,為以后的工商業發展創造了條件,該地區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萌生的鄉村工業及8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強大的鄉鎮企業均與明清時期形成的傳統一脈相承。相反,兩湖平原直至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仍依然以農業為主,只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農村工業的艱難起步。
————————————
①a本文所指明清時期下限在鴉片戰爭前,鴉片戰爭后涉筆不多。
①b按郭松義《清代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分類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4.2)將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列為發達地區,包括兩湖平原在內的絕大多數傳統農業區列為已發展地區。
②b轉引自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③b本書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b湖南省農業區劃委員會編著:《湖南省農業區劃》,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
⑤b張履祥:《補農書》。
①c陳忠平:《論明清江南經濟的多樣化發展》,《中國農史》1989年第3期。
②c范金民:《明清杭嘉湖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
③c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中國農史》1985年第1期。
④c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第3期。
⑤c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論述》,《中國農史》1987年第4期。
⑥c最近龔勝生撰文(《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2)否認了這一公認的觀點。他認為垸田集中的洞庭湖和鄱陽湖(沒有提到江漢平原)湖區州縣水田比重的均較周圍地區低,而且愈往湖區中心比重愈低,其原因是①怕水淹而植麥非植稻;②洲渚漲塌無常宜旱作。但作者同時指出"湖區成為重要的稻米產區并不在于其水田比重高,而在于其墾殖指數高,水田絕對數量多和水稻單產高"、"水田絕對數量多"實際上佐證了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種植面積隨垸田擴大而增加的觀點。
①d對此有爭議,本人對清代江漢平原的研究(《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詳析》,《中國農史》1991年第2期)持此論,對兩湖地區的考察待刊。
②d本書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d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④d譚天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4期。
⑤d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第3期。
⑥d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3年第2期。
⑦d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2期。
⑧d這是中國學者的主流觀點,但美籍學者黃宗智先生在其近著《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就耕地面積的總收入而言,栽桑養蠶顯然比種水稻要高得多,但如果考慮單位勞動報酬則養蠶的工作日均毛收入遠低于種稻,極少例外,這并不排除勞動力年收入(而非日收入)和家庭總收入(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因為許多閑暇時間和沒有機會成本的家庭成員都得到了利用。在這樣的前提下,在耕地嚴重不足的地區發展蠶桑業亦是勢在必行。該書提出了許多類似與中國主流學者相左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對其進行詳細的介紹與討論顯然已超出本文的范圍。
⑨d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論述的是湖南四川小農,但筆者認為在糧食商品化方面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區地帶比較相似。旱作區或經作區則當別論。
①e范金民:《明清杭嘉湖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
②e從翰香:《論明代江南地區的人口密度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e馬學強:《試論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內變遷"與勞動力轉移》,《史林》1993年第1期。
④e張國雄、梅莉:《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的地理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期。
⑤e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
①f張建民:《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1987年第2期。
②f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開發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
①g大致當正確,但不盡然,同時代的四川盆地及江西地區均有較有影響的傳世農書,而兩湖地區沒有。此點同事王利華先生提及,惜未深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
②g農業人口素質高低與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此暫不申論。
③g吳仁安《明清上海地區城鎮的勃興及其盛衰存廢變遷》,《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g張華:《明代太湖流域專業市鎮興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4期。
⑤g樊樹志:《明清長江三角洲的糧食業市鎮與米市》,《學術月刊》1990年第12期。
①h與長江三角洲地區明清市鎮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的盛況相反,學者們對明清兩湖地區農村市鎮的研究較為冷漠,與該地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不甚相稱。此處提出的說法原自一些附帶性的研究,如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第4期;等。
②h詳見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附錄),中華書局,1992年。
③h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④h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⑤h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⑥h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⑦h李伯重:《明清江南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⑧h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