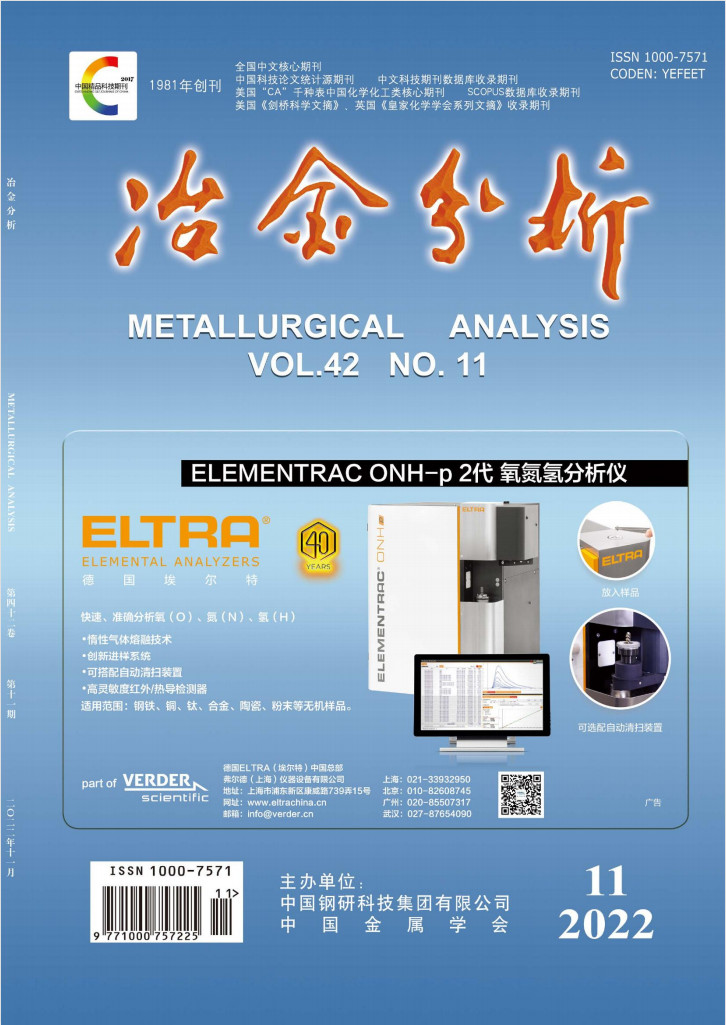謠言傳播的心理分析——以汶川大地震期間的謠言為例
蘇濤
關鍵詞: 謠言傳播 心理 汶川地震
[摘要]: 本文在對汶川地震期間的謠言傳播現象及其特點分析的基礎上,試圖從傳謠者和受謠者兩方面揭示謠言傳播所特有的心理機制,以求加深我們對謠言傳播現象的認識,進而減少其消極影響。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read phenomenon about rumors during the earthquake of Wenchuan, I trying to reveal aspects of specific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bout the dissemination of rumors by the person who spread rumors and the person who to accept rumors, in order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rumors, and then To reduce their negative impact.
[Key word] Rumor Dissemination Psychology Wenchuan Earthquake
北京時間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以我國的四川省汶川縣為震中,發生了8.0級大地震,地震波及大半個中國,甘肅、陜西、重慶、云南、北京、上海、天津等20多個省、市、自治區都有強烈震感,“據民政部報告,截至8月18日12時,四川汶川地震已確認69225人遇難,374643人受傷,失蹤17923人。”[1]汶川大地震呈現出巨大的破壞性并給我們的國家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我們的社會所每每發生的重大災變往往都會成為滋生謠言的溫床,同樣,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各種謠言也很快在社會上傳播流布開來。然而,與2003年的SARS危機期間各種謠言的流傳給社會所造成的恐慌相比,由于政府的信息公開和大眾媒體的廣泛參與,在整個汶川地震期間(地震后100天)不僅大大減少了謠言的滋生,而且即便是某些謠言在傳播開來以后,也會很快地止于政府的信息公開和社會信息傳播渠道的暢通。至今,汶川地震已經過去整整100天了,適時地對地震期間的謠言傳播現象及其心理機制進行分析和總結,將有助于加深我們對謠言傳播現象的認識,從而增強對謠言傳播的應對,有效消除其不利影響。
一、謠言的定義
“無論覆蓋面寬或窄,持續時間長或短,它的影響是和平的還是破壞性的,謠言話語存在于每一種文化的篇幅中。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謠言。”[1](p114) 的確,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和傳播現象,謠言隱匿于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發生于每個社會歷史時期,任何人都無法忽視它對我們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正是由于謠言傳播之于我們社會的重要影響,曾有許多學者從各種角度對謠言傳播現象進行了研究。但是,究竟謠言是什么呢?由于研究的切入點和關注的角度不同,學者們對于謠言的定義也大相徑庭。
對謠言林林種種的定義,從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強調它的信息特征,另一類則強調它的心理特征。學者卡普費雷曾對謠言的定義做過整理:“這個領域的兩位奠基人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認為,謠言是一個‘與當時事件相關聯的命題,是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傳媒介的方式在人們之間流傳,但是卻缺乏具體的資料以證實共確切性’。而納普則認為,謠言是一種‘旨在位人相信的宣言,它與當前時事有關,在未經官方證實的情況下廣泛流傳’。彼得森和吉斯特對謠言所下的定義是謠言是一種‘在人們之間私下流傳的,對公眾感興趣的事物、事件或問題的未經證實的闡述或詮釋’”。[5](p6) 按照卡普費雷的說法,這三種定義首先都確認了謠言是一種信息,突出的是謠言的信息特征。然而,“將謠言定義為正在流傳而未經‘證實’的消息,公眾將更難以辨認謠言,尤其是謠言的出現往往伴隨著最為理想的證明,即直接的證明:‘我有一個朋友親眼看見從愛麗臺宮駛出一輛救護車。’謠言總是通過朋友、同事或親戚傳到我們身邊的,而且他們往往并非他們所敘述事件的直接見證人,他們的朋友才是目擊者。還有什么比目擊者更為可靠的呢?還要等什么更好的證明呢?”[5](p9)因此,這些強調信息特征的定義的問題就在于:“所有以‘未經證實”來作謠言的定義時,邏輯上總是說不通的。而且無法將其與眾多其他通過口傳媒介或大眾傳播媒介流傳的消息區分開來。”[5](p9)
強調心理特征的定義認為謠言給人消息和情緒上的滿足,或是“一群人的智慧匯總的結果,以求對事件得出一個滿意的答案”,或是“一種集體行動,目的是為了給無法解釋的事件尋求一種答案。”[5](p11) 然而,這種對心理因素的強調卻會導致另一種邏輯上的后果,那就是將其簡單的歸為一種社會精神病:“事實上,如果謠言僅僅是因為有人相信而流傳,沒有存在的任何理由,那么謠言就是不理智的,是一種發瘋的行為,相當于社會學中的幻覺。因此,對謠言的解釋只能從屬于精神病學:誰相信謠言誰就是瘋子。”[5](p14)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些定義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當一個虛假的信息流入社會時,它的傳播完全和一個真的消息一樣。它的傳播并非由于集體發瘋或集體幻覺,而完全遵循著構成社會生活的規則。”[5](p15)
由此看來,無論是對信息特征還是對心理特征的強調都是片面的,因為謠言不僅是一種信息傳播現象,更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和心理現象。而且,就大多數謠言的產生來說,大都有一定的原因或觸發事件,謠言產生和傳播最為繁盛的時期也往往是某些社會重大事件的發生、發展期。所以,本文認為謠言是由社會重大事件觸發的一種特殊的信息傳播與社會心理現象。
二、謠言產生的原因
我國社會學者鄭杭生認為謠言不僅是一種集合行為,而且是集合行為的信息渠道。[6]所謂集合行為,就是。一般認為,集合行為的產生需要三個基本條件[7](參閱p96):一是結構性壓力,例如在自然災害、經濟蕭條、失業、物價不穩、政治動蕩、種族關系惡化等危機狀況下,社會上普遍存在著不安心理和緊張情緒,這些結構性因素是集合行為發生的溫床;二是觸發性事件,集合行為一般都是由某些突發性事件或突然的信息刺激引起的,例如這次引發大量謠言的汶川大地震;三是正常的社會傳播系統功能減弱,非常態的傳播機制活躍化。
由此可以說,作為一種集合行為,謠言產生的原因也不外乎這三個方面。所以,從總體上來看,一個謠言的產生往往包含一下幾方面的因素:一是社會結構性因素,例如這次地震所引發的人道、生存、救援等方面的社會危機;二是心理因素,例如地震后整個社會所存在的悲憤、緊張、憂慮、不安、懷疑等等方面的情緒和心理;三是觸發性因素,汶川8.0級大地震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危機無疑是此期間謠言傳播的最大觸發因素,然而,就此特定的時間段(汶川地震期間)大量謠言傳播來說,還有另外一個觸發性因素,即即將召開的北京奧運會(關于這一點,將在下文詳述)。四是信息因素,在社會發生危機或重大變故的時候,也是人們迫切需要信息以消除不確定性的時期,而往往在這個時候,或由于危機后正常的信息傳播渠道遭到嚴重破壞,或是在某些社會(政治)勢力壓制下,正常的信息傳播機制無法發揮作用,所以,也就造成了謠言——這種非常態的信息傳播方式大行其道。
三、汶川地震期間的謠言傳播特點
“作為一種特殊而復雜的社會現象的謠言,其特點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加以認識。從謠言的內容上看,它具有虛假性特點;從語言所反映的問題和它所采取的形式上看,它且有誘惑性特點;從謠言的結果上看它又有危害性特點;從造謠者和傳謠者的情感上看,它又具有傾向性特點;從造謠者的動機和目的上看,它還又有攻擊性和誹謗性特點。”[3](p17)實際上,由于觸發謠言的各種因素(如前文所述)不盡相同,具體到每一個時期的謠言,其呈現的特點也就千差萬別。就汶川地震期間的謠言傳播而言,它具有以下特點:
(一)圍繞著地震這一重大事件產生了大量迅速傳播的謠言。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由于其巨大的破壞性及所造成嚴重的損失,立即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各種與地震有關的謠言也很快流傳開來。在這些流傳的謠言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地震謠言。大地震發生當天,“北京就盛傳當晚會有2~6級地震,重慶網上傳言晚上會有余震,上海也謠傳滬浙交界處發生5.7級地震,……震感也引起貴州一些群眾的猜測和不安”[2]此后,各種版本的地震謠言更是不斷,比如“針對網上流傳廣州近日將發生大地震的說法,廣東省地震局稱未監測到任何異常,地震說法純屬謠言。”[3]“汶川大地震后,一條從巴西傳過來的所謂預言又開始在中文網站上流傳:‘9月13日,南寧與海南島之間將發生9.1級大地震,引發海嘯,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并可能沖到日本’。聯系到印尼海嘯與四川地震,一些人開始感到恐慌,一些人甚至打算離島避險。”[4],“(汶川大地震)震中將向西安發展”[5]等等。
二是與地震相關的謠言。比如“成都警方24日通報,所謂‘女警及其家人搭建救災帳篷,在帳篷內喝酒、打麻將’純系不實之詞。因散布謠言或圍攻、謾罵、毆打民警,16名嫌疑人先后被抓獲。”[6]“四川衛生廳廳長沈驥在正在召開的四川省抗震救災的情況通報新聞發布會上,非常痛心地向相關網站發出呼吁,這幾天在網上瘋傳四川省衛生廳干部在災區毆打志愿者的傳聞,純屬謠言。”[7]“福建云霄縣謠傳四川地震造成生態破壞,鹽被污染而出現搶購潮。”[8]“廣元市政府就‘安置房防火隱患大被責令拆除’辟謠”[9]
(二)地震謠言與奧運謠言的結合。
如前文所述,謠言產生與傳播大都有一個觸發性事件。汶川大地震發生后,2008年對于中國人來說,除了抗震救災之外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將召開的北京奧運會。于是,隨后而來一些謠言竟然將二者奇妙的結合在了一起。其一是在網上廣為流傳的“奧運福娃謠言”,將福娃與中國2008年發生的天災人禍聯系起來:“2008年是中國奧運年,但是2008年卻是令人傷痛,令人難忘的一年,本來自然災害的發生是屬于正常的現象,但是如果你和五個福娃‘貝貝’、‘晶晶’、‘歡歡’、‘迎迎’和‘妮妮’聯想起來就會發現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晶晶代表的是大熊貓,然而就在熊貓的家鄉四川發生了8.0級大地震;歡歡代表的是奧林匹克圣火,然而就在奧運圣火在全世界傳遞的過程中,發生了搶奪圣火事件;迎迎代表的是藏羚羊,然而就在藏羚羊的家鄉西藏出現了3.14藏獨份子‘打砸搶燒’事件;妮妮代表的是燕子風箏,然而就在風箏之鄉山東出現了4.28膠濟鐵路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貝貝代表的是魚兒,接下來……”[10]
其二則是“奧運數字謠言”:即“1月25日的低溫雨雪災害,3月14日的西藏暴力事件,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地震,三者年月日各自相加,即為三個八,影射北京奧運開幕儀式的時間--08年8月8日。而更是有心人能觀察到5月12日地震離奧運開幕儀式正好是88天,別有用心的人用所謂的‘歷史的巧合’、‘不得不信的數字巧合’等主題進行廣泛的散謠”。[11]還是借用這位名為“蝶戀花”的網友的話來對這些謠言加以評論:“只要稍微有點天文地理知識的人都能解釋導致南方雨雪災害和汶川八級地震的原因,火車脫軌相撞也完全是有關部門管理不當人為所致,拉薩事件更是達賴集團有準備、有預謀、精心策劃煽動并勾結境內外狼狽實施的惡劣暴力事件,至于火炬在境外傳遞遭到襲擊,這就更不需要我來解釋,只要稍微有點奧運知識的人,就都知道,火炬遭竊遭襲的史例數不勝數。”[12]那么,對于那些造謠、傳謠者,除了愚昧和無知外,就不得不讓人懷疑其叵測的用心。
(三)傳播方式以網絡、手機等新媒介為載體的大眾傳播為主。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謠言的傳播方式也和其他訊息的傳播方式一樣愈來愈趨于多樣化。不同的傳播方式,其影響和危害也各具特點。就目前來說,謠言的傳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口頭傳播,二是文字傳播,三是電訊傳播。上述三種我們又可以把它們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人際傳播,這類傳播只有當人與人發生聯系和接觸時才能發生,這是一種原始的、傳統的傳播方式;另一類是大眾傳播,人們在接受這類傳播時,需要有一定的物質條件和能力條件,如需經過媒介(報紙、收音機、電視機等)作為載體,而看報需識字,看電視、聽廣播需有設備等。”[3](p157)
實際上,相對于傳統的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和人際傳播等謠言傳播方式,現代謠言的傳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汶川地震期間,謠言主要的傳播載體是網絡,包括各種網頁、論壇、博客、聊天室和QQ、MSN等網上即時通訊工具。另外,謠言借助手機短信的迅速傳播也是期間謠言傳播的一大特點,筆者就接到過前文提到的那則福娃的謠言短信。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新媒體在傳播信息上的迅速和便捷,另一方面,作為大眾媒體,它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將信息傳播到各個角落的廣大受眾,從而造成很大影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手機短信這種傳播方式,更是將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優勢集于一身。因為手機短信首先可以通過一傳十、十傳百的方式將信息迅速而廣泛的進行傳播;其次,它無疑又是一種人際傳播媒介,當我們接到一位熟識的朋友發來的信息的時候,對這一信息的信任程度和其所具有的說服力往往大大高于通過其他媒介傳來的信息。
四、謠言傳播的心理
正如本文在給謠言定義時所認為的,謠言不僅是一種信息傳播現象,更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心理現象。謠言傳播的全過程,不僅涉及到人們不同的個性心理傾向和難以捉摸的心理活動,也是相互重疊的傳播者、受傳者的之間的心理,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同構過程。
(一)傳謠者的心理
1、事件的重要性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各種形形色色的謠言層出不窮,但無論是直接的地震謠言還是與地震相關的謠言,都是緊密圍繞著“地震”這一主題而展開。對于這一特點,美國學者奧爾伯特的研究給出了合理的解釋。他認為,問題重要性和與涉及該問題證據的含糊性這兩個重要條件與謠言的傳播密切相關,并由此給謠言的強度歸納了一個表達公式:[1](p17)
R=i×a
其中,R指流言(Rumor)的泛濫程度,i指傳聞對傳謠者的重要程度(importance),a指傳聞的模棱度(ambiguity),用語言表達就是:“流行謠言傳播廣度隨其對相關人員的重要性乘以該主題證據的含糊性的變化而變化,重要性與含糊性之間的關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因為,如果兩者之中有—個為0,也就沒有謠言了。”[1](p17)
可見,越是重大事件,越容易成為謠言傳播的話題。這首先是因為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往往會影響到這個社會整個國家的利益,進而也影響到了人們的切身利益,所以事關重大,人們不得不千方百計的通過尋求與此有關的各種信息。然而,在這種非常時期,往往由于事件正在發展之中,大量的有關信息不能及時的傳遞到廣大受眾那里或者正式的傳播渠道受損,人們轉而通過各種非正式信息渠道尋求信息,因而圍繞著所關注的主題,出現了各種猜疑、歪曲、編造,最后使得謠言也不脛而走。
2、興趣的交集
謠言的力量和影響只有通過傳播才能得以體現。但是,謠言為什么能不斷的進行傳播,為什能不斷的在“傳謠——辟謠——再傳謠”的怪圈里循環呢?“謠言的傳播有一定的規律。任何謠言的傳播都不是平均地傳結社會上的每一個人,而是傳給那些對謠言內容密切關注的人,傳給那些對謠言內容有濃厚興趣的人,傳給那些與謠言內有牽連關系的人。”[3](p117)因而謠言總是先由對它的主題感興趣的人進行積極地傳播,然后在一定的共同興趣群體中逐漸傳播開來。就汶川地震期間的謠言而言,人們對于地震更多的是恐懼和憂慮,而對于此后即將進行的奧運會來說,更多的則是希望與期待,就是在這種復雜的情緒當中,二者都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然而不管是憂慮還是期盼,二者在那段時間也都占據了人們的主要話語空間,成了人們的興趣所在。可能也正是為此,才有了地震謠言和奧運謠言的奇妙組合,有了此類謠言在網絡世界的飛速傳播。
3、尋找事情合理的解釋
“謠言既是一種信息的擴散過程,同時又是一種解釋和評論的過程。”[5](p11)謠言的傳播是個復雜而奇妙的過程,一個謠言產生之后,在傳播的過程中不可能始終保持它的原貌,而是在傳播中不斷的演化和發展,待到它回到其源點的時候,可能就連最初的傳謠者都無法辨認出來。在這個奇妙的過程中,是一個接一個的傳謠者和受謠者為了使謠言變得更讓人信服而不斷的添油加醋。不管是在傳播謠言還是在傳播其他信息,也不管傳謠者是否完全信服謠言的內容,傳播者的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說服受傳者相信自己的傳播內容,為此,他就要對謠言的內容進行新的補充與排列組合,對謠言所闡述的事情進行更加合理的解釋。“謠言的傳播者與其所帶來的信息被視為完全同一,拒絕相倍謠言或對謠言產生懷疑,就是拒絕傳播者本身。”[5](p57)所以,為了使下一個受謠者不至于懷疑自己的傳謠,為了證實自己所說的是事實,說服別人相信,每一個傳謠者都在不斷的給謠言添加自己認為的合理的解釋。比如上文提到的福娃謠言,在流傳的過程中,有人覺得五個福娃中只有福娃貝貝沒有明確的象征指向,于是便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解釋能力,將福娃貝貝(魚)與我國今天先前發生的南方雪凝災害聯系起來,于是福娃謠言就有了一個更“完美”的版本:貝貝——魚(南方雪災)、晶晶——熊貓(四川地震)、歡歡——火(圣火傳遞)、迎迎——藏羚羊(西藏藏獨)、妮妮——風箏(山東火車)。
另外,尋求事情合理解釋的過程,有時不僅是為了說服別人,也是為了說服自己。從奧爾伯特的謠言傳播公式可以看到,謠言的產生跟謠言事件的模糊性有很大關系,事件越是含糊不清,越是能引起人們對它的進行探究和傳播的興趣。在對事件的探究過程中,由于個人的知識結構和經驗范圍非常有限,再加上往往這時候又得不到與事件相關的有效信息,人們對事件的解釋就不可避免的添加上了濃厚的個人主觀色彩和非理性的色彩,最后這種所謂的“合理解釋”也就必然走向了謠傳。
4、釋放壓力
汶川大地震不僅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和財產損失,而且由于隨后急需進行的繁重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任務,以及接連不斷發生的余震,給人們的心理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這時候,有些謠言的傳播并非完全出于惡意,人們總是希望抓住一則能減經并解釋他潛在緊張情緒的謠言。比如前文提到的福娃謠言和奧運數字謠言,2008年我國發生了這么多天災人禍,確實讓人難以接受,而通過一則謠言將這些所有的災難都扣到福娃身上或數字上,總算為那些難以解釋的現象找到了一個替罪羊,人們的緊張情緒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謠言提供一種能供排解緊張情緒的口頭發泄途徑。它們通常能為這些情緒的存在作辯解,而如果直接面對這些情緒,當事者也許難以接受;它們有時能為周圍環境個令人費解的現象提供更廣泛的解釋,從而在使周圍世界變得可理解的理智駕馭過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p20-21) 所以可以說,謠言的傳播有時是出于人們緩解精神壓力的心理,通過傳播一些相關的謠言,人們緊張的情緒得以舒緩,心理也達到了一些平衡。
(二)受謠者的心理
1、信源的可信性
在汶川地震發生的幾天之后,由于進入重災區的公路被嚴重損毀,救援部隊只好搭乘直升機進行空降。災區山大溝深,地理條件惡劣,再加上當時天氣陰霾能見度很低,極不利于空降作業,這些情況都是為大家所知的。但是,迫于當時緊迫的救災形勢,救援部隊還是毅然決然的實施了空降。于是,一條關于救援部隊謠言很快流傳開來:“第一批實施傘降的部隊中有四名戰士不幸遇難”。筆者是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這個謠言的,當時他說的煞有介事,再加上對當時對災區惡劣地理條件的了解,我也就信以為真了。然而很快有關部門通過媒體進行了辟謠,傘降部隊成功實施了空降,沒有一個戰士犧牲。但是這樣一條謠言為什么會使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信以為真了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對傳謠者的信任。
著名心理學家霍夫蘭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曾提出了“可信性效果”的概念,即:“一般來說,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說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說服效果越小。”[7](p202)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往往都會以非常權威的面貌出現,正如前文曾引用過的卡普費羅書中所舉的例子:“謠言的出現往往伴隨著最為理想的證明,即直接的證明:‘我有一個朋友親眼看見從愛麗臺宮駛出一輛救護車。’謠言總是通過朋友、同事或親戚傳到我們身邊的,而且他們往往并非他們所敘述事件的直接見證人,他們的朋友才是目擊者。還有什么比目擊者更為可靠的呢?還要等什么更好的證明呢?”[5](p9)在這么權威信源面前,使人無法不相信謠傳的內容是真實的。
2、心理預期——希望得到的某種信息
在獲取信息的過程中,人們都有一種預期心理,即希望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時,那些符合自己心理預期,與自己的主觀愿望或價值傾向的相一致的信息也更容易被接受。“心理學家奧爾波特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向一些人展示一幅畫,表現的是紐約火車站發生爭吵的情景。畫面上一個白人手里拿著一把刀,與一個黑人爭吵。以后則要求接受實驗的人向其他人轉述畫面的內容,并不斷傳播下去。在最后表述的內容中奇跡出現了,刀子的主人已經變了,成了黑人手里拿著刀子準備刺死白人。殺人刀子由白人手中轉移到黑人手中……”[3](p120) 正如這個實驗給我們所展示的那樣,在人們獲取信息時,即使信息所顯示的內容不符合自己的心理預期,受傳者也會根據自己的意愿而進行再加工,等到信息再一次傳播時,它已經變成了謠言。預期心理一方面說明了人們為什么會很容易接受一些謠傳,同時也能說明謠言為什么在傳播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以及人們為什么去積極的傳播謠言。
3、重復的力量
在我國古書上有這么一段記載:“龐蔥與太子質子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戰國策?魏策》)這就是重復的力量。在謠言剛開始傳播時,或許相信的人并不多,但隨著謠言一遍一遍的傳播,人們的信念就會發生動搖,直至最后信以為真。“重復為什么可以發生較大作用?有兩種解釋引入注目。其一,重復地看到某一刺激物的出現在情緒上可能會引起人的好感,而逐漸變成適應直至喜歡;其二,重復可以導致熟悉,而這一變化可能有助于對此一被重復的刺激物產生良好評價。”[3](p163-164)謠言的一再反復傳播或者說大范圍的傳播并不能使謠言變成事實,但是借助重復的力量,謠言完全可能誘使更多的受眾相信而進一步傳播謠言。
五、結論
1、重視謠言對社會心理的影響
謠言給我們所帶來的危害都是通過對社會心理的影響而發生作用的。因為謠言所涉及的主題往往都是與人們利益相關的重大事件,比如這次汶川大地震,所以,謠言傳播開來以后,必定會給人們的心理帶來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在個體心理上:“謠言對個體心理的影響,是作為一種社會情境對個體發生直接的刺激作用的。謠言產生并廣為傳播之后,就會成為一種社會心理環境,人處在這種心理環境個,難免不受其影響。”[3](p102)在謠言廣泛傳播之后,其影響力也隨之迅速增強。這時,它不僅影響到個體心理,而是隨著謠言傳播進而對整個社會心理都造成巨大的壓力,引起整個社會的情緒反映。在大的災難發生之后,謠言對社會心理的影響更為嚴重,如果不對其予以足夠重視,及時的進行辟謠,必定會引起社會的恐慌甚至社會的劇烈動蕩。
2、信息公開透明
汶川地震發生之后,不同于以往(特別是SARS危機期間的報道),我國的主流媒體迅速展開了全方位的報道,媒體的報道涉及到方方面面,準確而及時,幾乎是不受限制。所以,主流媒體成為震后全國人民獲取準確信息的最佳渠道。這種信息的公開透明不僅使人們及時的得到了各種急需的信息,也大大減少了謠言的滋生和社會恐慌情緒的蔓延。傳播學者杜駿飛認為,汶川地震事件中這種信息公開的模式,是汶川地震帶給我們最珍貴的一份傳播學遺產,它至少包括以下5點經驗:“1、政府積極主動地發布信息;2、大眾媒體(包括網絡媒體)的平等的全方位參與;3、對國際媒體與國際公眾的新聞開放;4、媒介議程與公共政策之間的及時、有機的互動;5、對公民新聞及其正向的新聞運動的幾乎無壁壘的允準。”[8]
3、傳播渠道的暢通
“這次汶川地震的報道,多數媒體打破了這種慣性態勢,反應之迅速、報道規模之大、報道力度之強都是歷史上罕見的。5月12日14點46分,新華網最早發出快訊,隨后各報紙和廣播電臺、電視臺,都反應很快,發揮了各自信息傳遞的特長。下午15時,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播出四川地震的新聞,隨后開始直播報道。十幾分鐘后,央視一套和新聞頻道正式啟動24小時直播,打破原有的節目板塊,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災、眾志成城”特別節目,影響全國。同時,各地方電視臺也迅速反應,紛紛加入抗震救災報道,關注營救進程。”[9]汶川地震期間的信息渠道始終保持著暢通,主流媒體每天都定時公布關于震災的傷亡數字、救援進展等各方面的情況,民眾也可通過媒體及時獲得有關災區的各種信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謠言才沒有大肆的傳播,整個社會也保持了整體上的穩定。
4、權威部門利用現代傳媒進行及時辟謠
在這次地震中,網絡、手機等現代傳媒成為傳播謠言的最佳工具。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我們進行及時辟謠的時候,卻同樣也離不開現代傳媒這種最有利的方式,制止謠言的傳播,必須借助現代傳媒的力量。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述,我國的主流媒體在地震期間都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不僅及時發布各種相關信息,在一些謠言流傳以后,也都進行了及時的辟謠,這大大減少了謠言的傳播。
5、普及科學知識,鏟除謠言滋生的土壤
前文曾介紹了奧爾伯特關于謠言傳播的基本假設,而后來的研究者在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提出另一個關于謠言傳播的改進公式:
R = i× a/c
C指公眾對謠言的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這個公式用語言來表達即:公眾越認為重要的訊息,越感到模棱不清的訊息,傳播得越快越廣;而公眾的批判能力越弱,則謠言的傳播量越大。
所以,各種看似不值一駁的奧運謠言卻大肆流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國民間文化中固有一種神秘主義的文化傳統,諸如相面、算命、看風水、測八字等神秘主義文化一向熱衷于將各種原本不相干的事物聯系起來。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我們的廣大受眾缺乏對信息的應有的判斷和批判能力,從而助長了謠言的大量傳播。讓我們來看下面一篇報道:
“1982年3月21日,日本浦河近海發生了7.3級強烈地震,當時,浦河町的大黑座電影院里正放映電影。一百多名觀眾中絕大多數是附近中、小學的學生,又大多是女孩。隨著大地的搖動,電影放映機顛上顛下,銀幕的畫面也錯亂開來,這些女孩,平常在媽媽面前還要撒嬌,這時卻表現得沉著冷靜。電影院里沒有人大喊大叫,也投出現蜂擁而出的局面,大部分人安然地坐在位子上,繼續望著銀幕,因為她們受過災害文化的教育,知道這個時候跑出去是造成員大傷亡的選擇。浦河是地震活動頻繁的地區,僅這次地震發生的前一年就記錄了有感地震299次。許多人認識了地震,體驗了地震,他們不再恐懼地震,他們采取了一些抗震措施,把家具固定在房間,給建筑物采取加固措施,他們養成了良好的習慣,如果來了地震,瞬息間就能處理好用火,瞬息間就能關掉電源。防災知識的普及以及人們對待災害的心理準備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這樣的強烈的地震沖擊下,沒有造成一個人死亡,火災、水災等次生災害也沒有發生。即使余震還沒停止,地面還在不停地搖動,人們進行震后修復的工作就已經開始了。這就是浦河町的人民,就是浦河町平時進行災害文化教育所發揮的作用。”[4](P134-136) 所以,謠言止于智者,要制止謠言的大肆傳播,就必須對增強對國民的文化知識教育,提高人民群眾的認知能力和識別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鏟除謠言滋生的土壤。
[注釋]
[1]轉引自 中國新聞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根據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授權發布《四川汶川地震已確認69225人遇難17923人失蹤》,2008年8月18日。
[2]轉引自 新華網評:《這次,真相跑在了謠言前面》,2008年5月13日。
[3]轉引自 新華網:《廣東省地震局澄清廣州近日地震謠言》,2008年6月4日。 [4]轉引自 新華網?地方聯播:《專家駁斥海南將發生9.1級大地震引發海嘯傳言》,2008年07月03日。
[5]轉引自 人民網:《西安市長回應地震謠言:西安是個安全的城市》,2008年06月23日。
[6]轉引自 四川新聞網:《成都警方稱女警搭救災帳篷打麻將純屬謠言》,2008年5月25日。
[7]轉引自人民網:《四川衛生廳長澄清干部毆打志愿者謠言》, 2008年5月26日。
[8]參見 中國新聞網:《6月中國十大謠言:民間收童男童女純屬無稽之談》,2008年06月30日。
[9]同上
[10]轉引自 SunDay的博客,《將福娃與中國的天災人禍聯系起來純屬謠言》,2008年6月3日 ,http://blog.sina.com.cn/kw9992
[11]轉引自 蝶戀花,《謠言可以休矣》,2008年06月20日,http://qqq6187330.blog.163.com/blog/static/8876028200852004345770
[12]轉引自 蝶戀花,《謠言可以休矣》,2008年06月20日,http://qqq6187330.blog.163.com/blog/static/8876028200852004345770
[
[1] 謠言心理學[M]. 奧爾波特. 劉永平, 梁元元, 黃鸝譯.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3.
[2] 黑寡婦:謠言的示意及傳播[M]. 勒莫著,唐家龍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 謠言透視[M]. 江萬秀,雷才明,江鳳賢. 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11.
[4] 地震謠言[M]. 陳煥新. 北京:地震出版社, 1990.
[5] 謠言[M]. 卡普費雷. 鄭若麟,邊芹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8s.
[6] 社會學概論新修[M]. 鄭杭生.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7] 傳播學教程[M]. 郭慶光.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1.
[8] 杜駿飛. 通往公開之路:汶川地震的傳播學遺產[J/OL].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780. 2008-07-16/2008-08-19.
[9] 陳力丹. 汶川地震報道的實踐帶給我們的新思維[J/OL].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789. 2008-07-24/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