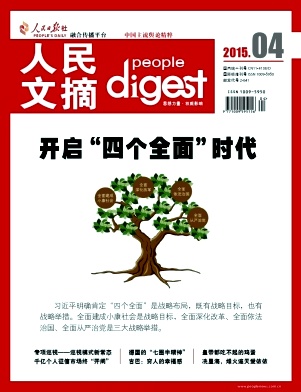關于網絡事件背后的群體狂歡--從郭美美事件看網絡的娛樂化生存
時運斌
回顧2011年來的網絡風云,風頭最健的莫過于郭美美事件,網絡上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最終在網友的圍觀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演變成一層層巨浪,甚至連大名鼎鼎的郎咸平教授也被“拉下了水”。
2011年6月,新浪微博上一個名叫“郭美美Baby”的網友頗受關注,這個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的20歲女孩,在微博上多次發布其豪宅、名車、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網友發現,被指炫富。博主的認證身份居然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其真實身份也眾說紛紜,有網友稱她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的女兒,由此引發很多網友對中國紅十字會的非議。
同年8月3日,郭美美母女首次面對媒體,接受郎咸平獨家專訪,郭美美在節目中流淚道歉,承認是出于虛榮心和攀比心認證了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并強調一切與紅十字會無關。但是,網友對這樣的答復似乎并不滿意,簡短的聲明會不會是欲蓋彌彰的敷衍之詞?冰冷的回應會不會是對社會公信力的又一次摧殘?網友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尋找真相。于是,人肉、曝光、辟謠,微博又火起來了。
微博引爆后,經過傳統媒體放大,然后再回到微博平臺進一步深挖、爆料,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微博傳播路徑。這也是郭美美事件能夠將微博平均15分鐘的生命周期延長到超過1個月的原因。自2011年6月22日晚郭美美閑極無聊在微博上曬自己的新禮物開始至今,郭美美事件還在發酵進行中。其間歷時盧美美、達芬奇家具、動車出軌而熱度不減。直至今日,只要有郭美美的名字在,就能在網絡上吸引數以千萬計的點擊量。
網絡圍觀:一種網民力量的釋放
縱觀2011年,微博圍觀成網絡最熱點的話題。校長撐腰體、丹丹體、藍精靈體、TVB體、咆哮體、淘寶體,各種各樣的體肆意橫行網絡。無論是五道杠的少年(黃藝博),還是口無遮攔的明星(呂麗萍);無論是對撞傷兒童視而不見的冷漠(小悅悅事件),還是對結發妻子拳腳相加的瘋狂(李陽家暴事件),都在微博平臺上接受著公眾的圍觀和民意的評判。
微博走紅的原因在于其充分利用了讀者的時間碎片和便捷的轉發機制。在物質條件日益豐富和發達的今天,公眾的物質需求逐漸被更多的精神需求所代替,心理需求發生很大的變化,獵奇心理日益強烈。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件,只要準確抓住了網民的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就能取得無論是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中的轟動效果。炒作也好,作秀也好,網民們似乎不需要去理解什么,網絡似乎也不需要網民理解什么,隨波逐流,娛樂至死才是網絡生存的王道。
因此,不管網絡構建的是不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發生的事情都會對人類的認知產生影響。當然,郭美美和盧美美事件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在網絡上迅速蔓延,與專業的媒體從業者跟風炒作、網絡媒體追求高點擊率、網民心智發展不成熟等也有著莫大的關聯。如果放任網絡中的種種行為大行其道而不加約束,我們的現實世界必將被重創,陷入美國文化傳播學家波茲曼所描述的“娛樂至死”的境地。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這樣寫道:“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1]安德魯·基恩將娛樂改為了網絡,他在《網民的狂歡》中寫道:“伴隨著網絡的繁盛,愚昧和低品位、個人主義和極權統治也大量涌現。”
網絡媒體追求的是“眼球效應”,在網絡浩渺的信息中,空間和內容都是海量的、過剩的,甚至大部分內容都是重復的,只有那些稀缺的資源才能吸引更多的網民圍觀。而當一個網絡人物或者網絡事件成為某一時期的焦點時,網民的積極性就被極大地調動起來,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參與進來,他們自身也從中得到被關注的滿足。在這一點上,網絡和電視具有相同的共性,它們都拒絕和排斥思考,所有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即把網民的人氣想方設法聚集起來。每一個網民都渴望被別人關注,互聯網只有滿足網民的這個要求,才能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的頁面上來。
網絡時代:我秀,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被“我秀,故我在”所取代,在網絡時代,一種新形態的自我暴露主義大行其道,曬生活、曬工資、曬照片、曬裝修,點點滴滴、雞毛蒜皮之類的小事都可以在網上拿來曬,從電影的喜好、熱愛的偶像,到心情故事、日常的流水賬不一而足,無所不包、無所不秀,零成本零代價地在網絡上橫行,成千上萬的網友自愿或是被迫分享著陌生人的生活細節,在分享的同時,網民的“偷窺”心理也被極大地滿足著,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艷照門”、“獸獸門”等各種“門事件”,能吸引眾多網友圍觀的緣故了。只要網民愿意,輕點鼠標,就能名正言順地窺視別人的私生活。
網絡的發展讓數以千萬計的網民有了多種多樣的表達渠道,他們通過論壇、博客、微博等方式宣泄著自己的情感。從芙蓉姐姐、鳳姐到小月月,從郭美美、盧美美到各種各樣的“美美”;從“艷照門”、“獸獸門”到各種各樣的“門”,每次網絡事件的背后,網民們都以空前的熱情圍觀,思考已經變得不再重要。這些事件絲毫不會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在網絡上的所有行為有著有意或者是無意的娛樂或清醒,戀網成癖,觸碰到底線的隱私暴露,防不勝防的策劃事件,網民被愚弄并快樂著,盡管他們在事后知曉自己被愚弄,但是他們好像對此并不介意,一批又一批網民在網絡中載歌載舞地狂歡。
網絡生存:全民狂歡〓娛樂至死
騰訊網副總編輯王永治認為娛樂時代需要互動、參與,需要一個全民發泄、吐口水、狂歡的平臺。[2]沒有任何媒體能像網絡一樣提供這樣一個自由開放的平臺。每個人在網絡中隨時隨地都可以被來自全球各地的“大事件”,或者是經過網絡轉發被放大的“小事件”綁架,很多人在網絡中迷失了自我,個體娛樂化,放棄了理性的反思,跟隨著網絡中的輿論潮流,不由自主地被網民或者別有用心的網絡推手推動著,沒有確定方向地飄蕩。
新浪網總編輯陳彤不擔心媒體被娛樂化,不擔心事件過程被情緒推動,從而無助于理性的形成。他說:“絕大多數新聞是不需要理性的,比如說某地大火,不需要理性思考。”[2]新聞僅僅只是網絡這個龐大體系中的一個構件,另外還有海量的難以計數的微博信息、視頻、圖片等等,對于既定的新聞事實不需要太多理性的思考,前提是網絡能保證這些新聞的真實性。而對于像網絡中爆炸式增長的信息,網民們又會選擇什么樣的閱讀方式呢?王永治在“新西安·新形象”2011全國都市報總編輯年會暨中國報業品牌年會上,作題為《全媒體時代的微博平臺》的演講時總結了五種閱讀方式,首先是娛樂化閱讀,其次是淺閱讀、快閱讀、碎片式閱讀、文化閱讀。娛樂化閱讀,這是網友首選的閱讀方式,娛樂化閱讀即是娛樂化心態下的娛樂化網絡生存方式。
網絡作為一個時代新的傳播媒介,本身并無對錯可言,網絡出現的娛樂化傾向均在于使用網絡的網民的不恰當運用。而在當下,網絡新聞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都得不到保證,網絡媒介的公信力也一直不被認可。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媒體,它們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都是一樣的,“自由便意味著責任”,這是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通行的法則。目前,網絡媒體正逐步步入主流媒體的行列,但是,網絡媒體究竟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還沒有明確地確立下來。當海量的即時信息與媒介的有效把關發生沖突時,當信息的真實性與傳播的時效性相對立時,網絡媒介是選擇節節攀升的點擊率,還是并不輕松的社會責任呢?
最后,尼爾·波茲曼在《赫胥黎的警告》一章中憂心絕望之致、感人之致:“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1]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赫胥黎說流水線將毀掉我們,波茲曼認為是娛樂,基恩則指向了網絡。以如今的現狀看來,前兩者并未能毀滅我們,那么網絡會嗎?
財新網記者王勇在博客中這樣寫道:“這一年,郭美美這個名字真紅,貫穿始終。我非常不幸地在辦公場合被人家強迫聽她的所謂單曲,捏著的嗓子背后,我只記住兩個字的歌詞——叮當,也許有些媒體覺得那是郭美美示好的風鈴,其實那是敲給這個社會的警鐘。”[3]
[1]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 [2]侯繼勇.新媒體“球事”:娛樂至死?[N].21世紀經濟報道,2010-07-12. [3]王勇.叮當郭美美〓永不磨滅的恥辱[EB/OL].http://wang-yong.blog.caixin.cn/archives/24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