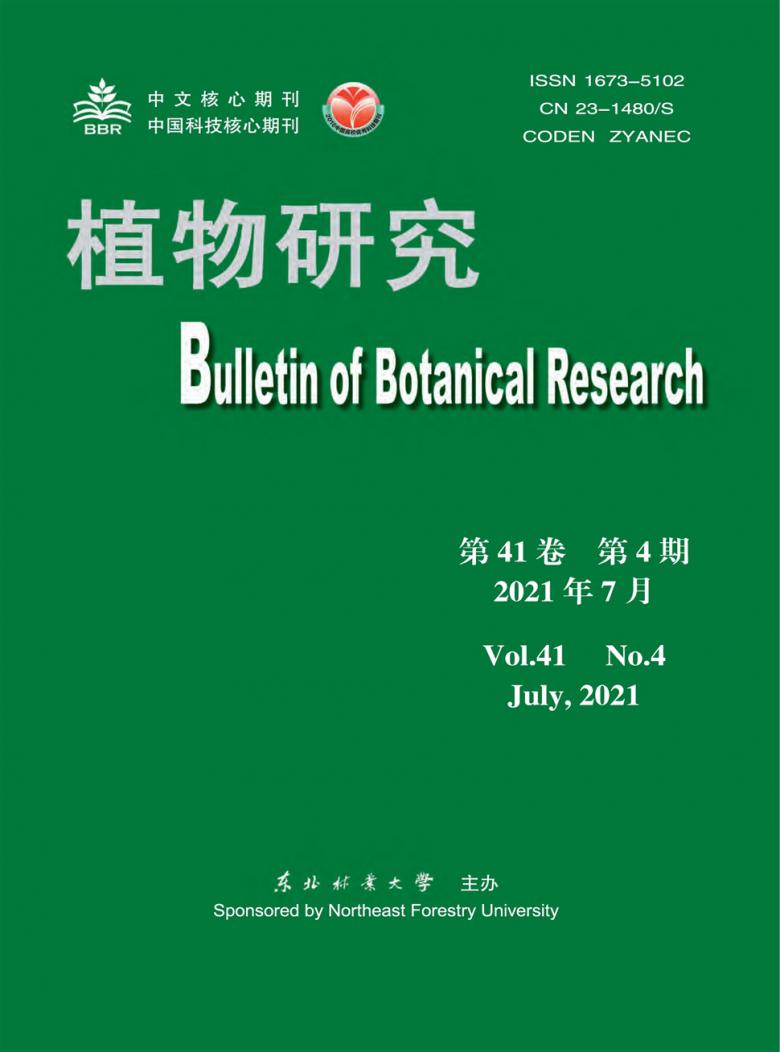清代民法語境中“業”的表達及其意義
未知
“業”是清代民間契約中經常使用的一個基本概念,中國法學界對于這一概念尚無深入的研究。(注:日本學者對有關“業”的概念的討論,參見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97頁以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學術界滿足于用現有的民法概念體系去分析中國古代民事法律制度,因而無需從中國古代的現實生活中去把握自己的研究對象。正是基于這種方法論的立場,臺灣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古代法中,“稱動產為物,財或財物,稱不動產曰產、業或產業。物之所有權人為物主或業主”,(注:潘維和:《中國民事法史》,臺北:漢林出版社,1982年,第354頁。) 大陸學者也贊同對動產和不動產的這種劃分,并認為古代稱“動產所有人為‘物主’或‘財主’;不動產所有權人為‘業主’、‘田主’、‘地主’、‘房主’”。(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2頁。) 但是事實上,無論是在法律制度中還是在社會觀念中,中國古代均不存在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對于“業”這一概念的使用也未必嚴格限于不動產,“業主”則更非專指物之所有權人或不動產所有權人。厘清“業”這一概念在清代民法中的確切含義,將有助于我們對中國古代民法整體框架的理解。因此,筆者試圖以清代民間契約為基礎,結合清代制定法的規定,對“業”這一概念做初步的探討。
一“業”在民間契約中的幾種表達及其含義
在很多情況下,清代民間契約中的“業”是與土地和房屋權利相聯系的,這也許是中國學術界認為“業”是指不動產的原因。因此本文也首先從土地契約出發,考察“業”的含義。 清代的土地制度較為復雜。從土地權利的歸屬看,大體上可以分為官田和私田兩種類型。清王朝初期通過圈地,以后又通過開墾荒地、查抄地等方式占有了大量土地,這些土地稱為“官莊”或“官田”,其地權歸國家所有,但后期已出現私有化的趨勢;私田的地權則分屬于官宦貴族、地主、宗族以及農民所有。(注:參見孔慶明、胡留元、孫季平編著:《中國民法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90—593頁。) 從土地權利的內容看,大體上可以分為“田骨”和“田皮”兩種類型。清代由于永佃權的發展,形成了“一田二主”的現象,即“同一塊土地的上層稱為田皮、田面,由佃戶享有它的使用收益權,是為皮主”;“下層稱為田根、田骨,由原田主所有,是為骨主、田主”。(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第116、85頁。)這里所謂同一塊土地的“上層”、“下層”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其實質是說在同一塊土地上分別有對田皮的權利和對田骨的權利兩種權利并存的現象,與現代法律制度中的概念相比較,大體上可以看作是對土地的所有權和用益物權(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相分離的狀態。(注:但也有學者認為清代的永佃權作為用益物權是對所有權的分享狀態。參見李志敏:《中國古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84頁。)清代官方的制定法并不承認永佃權的合法存在,因而田皮的買賣是被禁止的;同時,官田也不允許買賣。(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第116、85頁。)此外,在土地的買賣中還存在“絕賣”和“活賣”兩種情況,兩者的區別在于活賣土地允許賣主向買主“找贖”,即賣主在土地交易完成后一定時期內還可以要求買主再付一部分地價,并放棄對土地的全部權利,而絕賣則不允許找贖。通常習慣上找贖以一次為限,經找贖后活賣即變為絕賣。但是事實上找贖次數并非嚴格限于一次,在清代民間契約中可以看到多次找贖的實例。清代官方制定法規定絕賣須使用官方印制的契約,即所謂“紅契”,并向政府交納契稅;而活賣則無須交納契稅,也不是必須使用紅契。此外,絕賣土地在交易完成后通常要將稅賦“起割”、“推入”過戶,而活賣卻無需改變稅賦責任歸屬。制定法和習慣法的這些規范可以幫助我們解讀清代民間契約中“業”的含義和性質。 從最接近現代法律制度的角度看,清代“業”的概念含有不動產所有權的意義。乾隆十五年(1750),閩南人張萬卿所立斷賣契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立斷賣契人張萬卿,有承祖應分民田租并佃壹段貳大丘,載租玖石大,每石重壹百陸拾斛,共配產米伍畝玖分,坐在南門天妃宮邊本衙門口……今因欠銀,奉母命托中送賣與尤衙上為大宗祠內十二房祀業,價銀捌拾兩九城駝,折紋銀庫駝陸拾玖兩貳錢足。銀即收訖,田并佃聽銀主前去召佃耕種,管掌為業,日后永無言及貼贖等情。保此田并佃的系承租應分物業,不干房親□□兄弟,亦無重張典掛為礙。如有不明,賣主抵當,不干銀主之事。其產米伍畝玖分,就發圖壹甲捌戶張升云名內推出,付尤收入場圖叁甲貳拾伍戶尤世昌戶內納糧,永為己業。今欲有憑,立斷賣契為照。(例1)(注:《閩南契約文書綜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9頁。) 在這一契約下,張萬卿將其繼承自祖上的土地一段賣給尤氏。按照清朝的習慣,這一契約出賣的標的是完整的土地權利,既包括田骨也包括田皮,即“租并佃”;契中稱“日后永無言及貼贖等情”,表明該契約行為的性質當屬絕賣,即斷賣。契約言明,錢已收訖,該地聽由買主“管掌為業”。這里的“業”顯然是指該土地的全部權利,也就是學者所稱的“土地所有權”。然而,在清人的心目中并不存在“土地所有權”的觀念,甚至連對田骨的權利也并不被看作是一種對土地的所有權。關于這一點,請看順治八年(1651),安徽省休寧縣許阿吳所立賣契的例子: 廿四都一圖立賣契婦許阿吳,今自情愿將承祖鬮分田乙號,土名廿畝,系敢字乙千乙百四十三號,新丈字號,計租八□零十井□,計稅乙畝乙分六厘。其田東至西至南至北至。今將前項四至內田租,盡行立契出賣與許名下為業,當日憑中,三面議定時值價銀捌兩整。其銀隨手一并收足。共田今從出賣之后,一聽買人自行管業收留受稅為定……其稅奉例即行起推無異。(例2)(注: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139頁。) 例2是一個賣契,標的是許阿吳從祖上遺產中分得的,且有中人作保,因而其權利當是沒有問題的。契約提到了“其稅奉例即行起推無異”,指的是土地納稅的義務因該交易而從賣方按照慣例轉到買方,自土地交易后即由買方負責納稅,因而可以認定為是將契約標的絕賣的行為。因此,依現代民法的觀念判斷,立契人許阿吳賣到許某名下為業的當是土地的所有權。然而當事人卻稱“今將前項四至內田租,盡行立契出賣與許名下為業”,也就是說,在當事人看來,其轉讓給許氏為業的對象并不是土地或土地所有權,而是收取該土地田租的權利,并且不是收取當年田租的權利,而是永久收租的權利。嚴格地按照語義來解釋契約的這段文字,可以認為在清人的觀念中,“業”只是指稱收取該土地的田租的權利。嘉慶十五年(1810)的一個賣契則將這種觀念表達得更加清楚: 立斷賣送城租米契約字人李崇忠,今因需錢應用,情將父手遺下租米壹石五斗,兄弟相共,其田坐落洪家窠亭前,內抽出崇忠已分送城租米柒斗五升正,冊載民糧柒升五合,欲行斷賣,請問房親人等,俱各無力承交,次托中人引進到黃凌名下近前斷買,當日經中三面議定時值價銅錢壹拾陸千文正,立契之日,一并交足,分文無欠,自賣定之后,任憑照契管業。(例3)(注:“送城租米”是指由于田主住在城里,佃戶的交租義務不僅包括租米的數量,而且包括將租米送至城里田主手中的勞務。參見楊國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7頁。) 這是一份“斷賣”契,也就是絕賣契。賣主李崇忠與其兄弟共同繼承了其父遺下的一塊土地,每年收租一石五斗,兄弟二人各得一半,現李崇忠將其分得的一半絕賣。既是絕賣,所出賣的應當是土地所有權,但是李崇忠和買主卻明確地認為他們所交易的“業”是“送城租米”,甚至連土地的四至都無需言明,也無需將土地在其兄弟二人之間分割。可見,在清人的觀念中,土地權利的核心并不是對土地作為物或不動產的占有與處分的權利,而是收益的權利。(注:章有義在對清代徽州地主租簿進行分析時也指出:“按照當地通行的習慣,田產的計量大都不按面積,但計租額,以租額多少表示田地多寡。”參見章有義:《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276頁。)理解這一點,對于了解和把握“業”的概念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業”的概念在清代并不必然與土地所有權相關聯,它還可能是指與土地權利有關的所謂“田皮”權,如: 立永遠租契人正白旗漢軍雙成佐領下閑散五士禎同子國齡,因正用,今有祖遺老圈子地壹段叁畝,坐落……四至明白,弓尺開后。同中情愿租與王占元名下永遠為業,凡蓋坊(房)使土、安塋栽樹,由置主至自便,不與去主想干。主明押租東千(錢)叁佰肆拾伍吊正,其千(錢)筆下交足不欠。因押租過種(重),現租當輕,按每年每畝出現租東千(錢)五百文,共計租東錢壹千五百文。按每年拾月拾五日交乞(訖),永不許增租押借奪佃,以(亦)不許勸(欠)租不交。一地二養,子孫世守,日后地隨遺主,佃戶仍舊,恐口無憑,立永遠租契為證。(例4)(注:日本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轉引自孔慶明等編著:《中國民法史》,第594頁。) 這是一份土地出租契約,立契人作為田主,將土地永久出租給王占元,從而形成永佃權。然而契約中亦將買主所獲得的這種永佃權稱之為“業”,可見,在清人的觀念中,“業”并非僅與不動產所有權相關聯。事實上,從這一契約對“業”的概念的使用中仍然可以看到收益權的作用:永佃權作為一種權利,包含著通過占有和使用土地而獲得收益的權利指向,卻并不涉及對土地本身進行處分的意義。順治八年休寧縣許元秀的一個賣契中對“業”的概念的使用,更進一步證實了上述判斷。該契約稱: 廿四都乙圖立賣契人許元秀,今自情愿央中將承父鬮分得辛卯年做過真君會半股并在會家火(伙)、田園、銀兩帳目一切等項,盡行立契出賣與族伯名下為業,當日三面議定,作時值價銀壹兩叁錢整。其銀隨手收足,其會聽從買主管業坐會收租。如有內外人攔占及重復一切不明等事,盡是賣人之(支)當,不涉買人之事。恐后無憑,立此存炤(照)。(例5)(注: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1137—1138頁。) 這一契約的標的是在真君會的“股”。清代遺留下來很多有關會股交易的契約。這里所說的會,當是民間一種祭祖或祭神的組織。從現有的民間契約看,這種會的組織和運作形式大體上是,村民以一定的土地及農具入會構成會產,根據其入會土地及農具的價值確定其在會中所占份額,這種份額被稱為“股”或“腳”;每年在固定的時間以會產的收益置辦祭神儀式,然后將祭神用品按股平分給會員,如果會產的收益在置辦祭神儀式后還有剩余的話,也按股分配。每年的活動由會員輪值,或者是按股輪值。可見,會員憑借其在某一個會中所擁有的“股”或“腳”,不但每年可以獲得固定的收益,而且在會產收益有剩余時其收益還可以相應地有所增加。因此,“股”是以財產權換來的收益權,從這個意義上說,“股”的概念有些類似于現在的“股權”概念。立契人許元秀在真君會中占有半股的份額,上述契約就是許元秀為將這種“股”賣給其族伯而立的。在這一契約中也使用了“業”的概念,立契人稱將“股”出賣與族伯名下為“業”,并且在出賣后“聽從買主管業坐會收租”。顯然,在立契人和買主看來,在真君會的“股”與地權、田骨和田皮之間存在著一種可以稱之為“業”的共同的、一般性的東西,這種一般性當是“業”這一概念的本質。比較一下前面提到的幾個相關契約,不難看到,在清人的眼中,田骨是收取田租的權利;田皮是對土地加以占有和使用以獲得收益的權利;而“股”則是憑借其在會產中所占有的份額獲得收益的權利,收益權是股、地權、田骨、田皮等一系列契約標的的共性所在,被清人表達為“業”的正是作為這種共性的收益權。 下面兩個契約分別是出典房屋和出賣永佃權的例子,在這兩個契約中,立契人都表達了將一種收益權視為“業”的觀念。咸豐十一年(1861),閩南林子溥將其購置的房屋一處典賣給黃姓買主,為此林子溥立契如下: 立典賣契人南門外新巷林子溥,有明買行屋壹座肆落……茲因欠銀別用,托中引就與黃衙上,典賣出佛番銀壹百大員,每員庫平陸錢捌分正。銀即日同中收訖,其行屋聽衙上重新起蓋,管掌招租為業,不敢生端異言……限至十年足,聽溥備契面銀及起蓋銀一齊取贖,不得刁難。(例6)(注:《閩南契約文書綜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7頁。) 這是一起典型的出典契約,林氏將房屋出典給黃姓,約定典期十年,并允許黃姓在典期內于房屋所在地重新蓋房,雙方約定林氏在典期屆滿后以典銀及起蓋銀(即新蓋房屋所花費的款項)贖回房屋,(注:黃氏在該契尾部注有“同治五年四月黃書記稅契司單布字柒百拾柒號”,表明原房主并未將該契所典之房屋贖回,并且已經交納了契稅,從而成為絕賣。) 據此,黃氏便獲得了典權。在清代,典權雖然可以轉讓,但是顯然不同于現代民法中的所有權概念,因為典權人即不能處分典物,甚至也不能隨意改變典物的狀態。(注:該契中雙方約定典主可以重新起蓋房屋,并約定了起蓋用銀的數量,以確定回贖時贖銀數額,當為對一種例外情況的特別約定。)然而,林子溥在契約中卻將此種典權也稱之為“業”,更進一步表明清人之“業”的概念并不專指所有權,而無論這種所有權是指物之所有權還是指不動產所有權。同樣,在使用“當”的概念的契約中,(注: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或有稱典為當亦有典當并用”者,“例如后漢書劉虞傳,有‘虞所賚賞典當胡夷’之說”。參見潘維和:《中國民事法史》,第396—397頁。)因受當而獲得的權利也被稱之為“業”。乾隆三年的一份絕賣園地契中寫道: 立賣契金能五、金學先祖遺園地一片,計四號,坐落土名陳村住基,系良字乙千五百廿四號,計地卅九步;良字乙千五百卅五號,計地廿步;良字乙千五百卅六號,計地十八步八分四厘,良字乙千五百卅七號,計地十四步八分五厘。四號地共計九十貳步二分九厘,共計稅四分六厘三毫四系五忽。先年父叔手將地立契出當與王名下為業,今因急用,自情愿將父名下該業一半,共計地四十六步三分四厘五毫,該稅貳分三厘乙毫七系貳忽五,一并絕賣與王名下為業。(例7)(注: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1233—1234、1314頁。) 這一契約所記載的是金能五與金學先二人的父輩將契中的土地當給了王氏,而現在金能五和金學先又將該出當的土地中的一半絕賣給王氏的事實。契約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使用了“業”的概念:金能五和金學先的父輩將土地當給王氏后,對王氏所獲得的權利稱之為“業”,其表達為“當與王名下為業”;對金能五和金學先的父輩將土地出當后剩下的權利也稱之為“業”,在該契約中要絕賣的正是這一“業”,其表達為“父名下該業”;而絕賣后王氏所獲得的權利也被稱之為“業”,其表達為“一并絕賣與王名下為業”。 另一個契約實例是嘉慶十一年安徽省休寧縣吳惟大的賣佃契: 立杜賣佃契人貳十六都四圖吳惟大,今因急用,自愿央中將承祖遺下佃業乙號,坐落土名馬頸坳,計佃貳畝貳分,計田大小四丘,憑中出賣與貳十七都貳圖朱名下為業……其佃即交買人管業,另發耕種。(例8)(注: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1233—1234、1314頁。) 該契所出賣的標的也是永佃權,與前述例4所不同的是,例4中的賣主擁有對土地的完整的權利,田骨與田皮并未分離,賣主以該契將土地租種權出賣與他人,并且言明“永不許增租押借奪佃”,“一地二養,子孫世守”,從而形成永佃權;而在本例中,賣主對土地并不享有完整的權利,其從祖上繼承下來的僅僅是“佃業”,可見田骨與田皮已經分離,現在賣主將其所享有的“佃業”賣至朱姓“名下為業”,出賣后“其佃即交買人管業”。這一契約表明,清人不但稱佃權為“佃業”,而且這種“佃業”一旦形成,還可以轉讓,是一種獨立的權利。 清代四川自流井(后同貢井合稱自貢)盛產井鹽,其生產方式已經與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差別。在鹽業生產過程中遺留下了大量的民間契約。(注:據有學者稱,僅自貢市檔案館就存有約三千件,參見吳天穎、冉光榮:《四川鹽業契約文書初步研究》,載自貢市檔案館等合編:《自貢鹽業契約檔案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21頁。)與農業地區相比,鹽業生產地區有著自己獨特的習慣用語,例如在農業地區的土地租佃契約中常見“租與某人名下永遠為業”這樣的習慣用語,但在鹽業生產地區的出租契約中常見的卻是“租與某人名下淘辦推煎”,或“租與某人名下淘銼推煎”,而并不多見使用“業”的概念。但是在有關鹽業生產的契約中,也可以看到“業”的概念的三種使用方式,分別如下: 立杜賣地脈井日份文約人王紹寬、王紹酞、王紹三房人等,原祖遺留新擋周家沖泩洪井每年每月水火地脈日份叁拾天,萬順號銼辦見功……情因負債難償,稟明祖母,請憑中證,將存留地脈水火日份壹天零叁時,掃賣與堂叔王培信名下,子孫永遠管業。(例9,同治七年契) 立承佃字約人鄭鳳山,今憑中證佃到王書元子孫五房名下先祖所留熟土一股,地名五家坡,此業分派王緒禮名下。比日五房老少人等當面言明,甘愿出佃與鄭鳳山平地開銼鹽井一眼,更名濟龍井……其有天地二車、一井三基,井基、灶基、車基、柜房、財門、偏廈、牛棚、楻桶、風篾莊(樁)等,任隨客人鄭姓修立,挖石取土一概王姓業內,其有抬鍋運炭、傾渣放鹵、開溝放水、進出筧路、牛馬出入路徑,概無阻當,如有阻當,地主五房承擔,不與客人相染。(例10,同治六年契) 立出絕頂子孫業井份并廊廠牛只家具約人曾義順,情因先年出名,佃得□□獅子山鄭銓康、鄭仕康、鄭紹雍業內復淘子孫業鹽井壹眼,更名源涌井。每月除地脈日份肆天、曾義順占乾日份貳天,不出工本;下余日份貳拾零肆天,派逗工本銼辦。邀得桂磬乾做日份拾陸天,曹德揚做日份貳天,劉榮村做日份貳天,曾義順已下做日份肆天。迄今義順無力煎辦,愿將項下每月做得晝夜水火油井份肆天,每月應占晝夜水火油乾日份貳天,并照日份應占天地二車、筒索、廊廠、牛只、家具、鐵器、貨物等件股份,毫無提留,概行絕頂與桂磬乾名下承頂銼辦推煎。(例11,同治六年契)(注:載自貢市檔案館等合編:《自貢鹽業契約檔案選輯》,第484—485、339、484頁。) 在例9中,立契人將其在鹽井合伙中的份額稱之為“業”,并且將其出賣與王培信。對業的這種表達與例5契有相似之處,但是清代鹽井合伙中的業有著比會股或一般合伙經營中的股更為復雜的內涵,筆者無法將其在本文中展開,擬另文專門討論。例10是承首(注:承首是指清代四川鹽業生產中負責組織合伙組織,并管理生產經營活動的人。)向井基地所有人“佃”(注:清代的民間契約中都將此種關系稱之為“佃”,其實是井基地所有人以井基地入伙的關系。)井基地的契約,該契約稱其項下的土地為王姓家族分派到王緒禮名下的“業”,這與單純的土地交易中稱地權為業也是一致的。例11中則將鹽井合伙本身作為一個整體稱之為“業”,即“子孫業井”。清代四川地區的鹽井合伙分為年限井和子孫井兩種類型,年限井作為一種業是有期限的,而子孫井則是“永遠管業”的,但無論是否有年限,均被稱之為業。 至此,大致可以對清代民間契約中“業”的概念下一個初步的定義:“業”是指能夠給權利人帶來收益的權利,這種權利與物有關,但并不必然表現為對物的權利。在清人的觀念中,權利人對物的關系被包含在“管業”概念中,即通過對物的管理來獲得收益。日本學者寺田浩明也注意到了“業”這一概念在明清時期中國習慣法中的獨特含義,他認為在當時土地法秩序中成為交易對象的并不是具有物理性質的土地本身,而是作為經營和收益對象的抽象的土地,即“業”,而土地交易僅僅是一種經營收益正當性的移轉過程。(注:參見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197—201頁。)
二“業”在清代官方語言中的表達及其含義
上文考察了清代民間契約中有關“業”的幾種表達及其含義,由于這一概念被清代民間契約廣泛地在同一意義上使用,因而可以認為筆者所指出的關于“業”這一概念的含義在清代是一種普遍的、被習慣法所認同的觀念。那么,在官方的語言中對“業”又是如何表達的呢?對此問題我們先看幾個實例。 清代官方語言中對“業”最常見的用法是指地權,例如,在清代開墾荒地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村民借助于當地鄉紳,以紳衿的名義申報開墾的現象,(注: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以紳衿名義申報地權比較容易獲得官方的認可。)申報獲準后由村民開墾,《戶部則例》卷7《田賦二》規定:“(甘肅)有業民田,如初系佃戶開墾,籍紳衿出保報墾,立有不許奪佃團約者,準原佃子孫永遠承耕,業主不得無故換佃。”這一例則所稱“有業民田”,是指所有權歸已經歸私人所有的土地,例則中將地權稱為“業”,而將土地所有權人稱為“業主”。除了在地權的意義上使用業的概念外,在清代的制定法中,也可以看到在非土地所有權意義上使用“業”的概念的實例。《大清律例》卷9《戶律·田宅·典買田宅·條例》中規定:“嗣后民間置買產業,如系典契,務于契內注明‘回贖’字樣,如系賣契,亦于契內注明‘絕賣’、‘永不回贖’字樣。”這一成文律例的用詞非常清楚,即無論是通過典的方式,還是通過買的方式,其所獲得的權利都被稱之為“業”,也就是說,無論是典權還是所有權,都是“業”。可見,清代官方語言中對于地權和典權都稱之為業。 上述兩處對于業的用法當是沒有什么爭議的,然而對清代官方語言中另外一些關于業的用法卻有不同認識需要拓清。順治六年清政府頒布的鼓勵流民墾荒令中稱:“察本地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為業。”(注:《清世祖實錄》卷43,第17頁。)這里使用了“業”的概念,但其含義究竟是指地權還是指佃權卻并不清楚。有學者認為這道墾荒令中的所謂“永準為業”是確認墾荒人對其所開墾的荒田的所有權,但是該學者在同一部著作中討論清代“一田二主”現象時又說:清朝統治者為了將廣大流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上,“實行以‘永佃’或‘永久為業’的獎勵墾荒政策”,而被官府所確認的永佃,為一田二主的出現提供了客觀基礎,(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第90、116頁。)從而又將因墾荒而獲得的權利與永佃權相關聯,如果這樣理解,上述鼓勵流民墾荒令中所稱的業又當是指永佃權;另有學者也認為,“清代通過開墾私有荒地或國有荒地,也可以獲得田面的永佃權”。(注:孔慶明等編著:《中國民法史》,第595頁。)可見,對清代因墾荒而獲得的業權的性質究竟是指地權還是指佃權并未厘清。 筆者認為,上述墾荒令中所稱之“業”當屬永佃權而不是所有權。“無主之地,即給墾戶為業,其有主而自認無力開墾者,定價招墾,給照為業”,(注:《清世祖實錄》卷146,第27頁。)在這里,對于無主之地的開墾和有主之地的開墾都使用了“業”的概念,前者是無主地,開墾者所獲得的權利或許可以理解為地權;而后者是指對于有主的荒地,在田主無力開墾的情況下,可以“定價招墾”,這里所說的“定價招墾”當是招佃,所謂“定價”,當是指定租或押租,而不是確定地價強制轉讓。因此,在后一種情況下,招墾的后果當是開墾者獲得佃權,然而官方語言也稱之為“業”,并且也要求向開墾者發“照”。更進一步看,即使是對于前一種情況中的無主荒地,開墾者所獲得的也未必一定是土地所有權,這一點可以從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一個獲準為例的奏請中得到佐證。劉坤一的奏請主張將蘇州府新陽縣無主荒田,或有主而不開墾的荒地一律作為官田,招集良善客民認領墾種,“取具保結,備價款縣核明,填給印照,準其作為己業”,(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8《田賦八》。)有學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所開墾的荒地還“并聽其轉售過戶”。(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第104、85頁。)請注意該奏請是將無主荒田和有主而不開墾的荒地一律作為官田看待的,而在清代,無主荒地按例歸國家所有,開墾的荒地作為官田,或者分配給王公貴族和旗人耕種或出租,或者交給各級官府租佃給農民耕種,(注:清代有將官田由州縣負責招佃收租的制度,參見孔慶明等編著:《中國民法史》,第590—591頁。)但官田只許租佃、典當,不許出賣。(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第104、85頁。)以此種制度背景看,劉坤一所稱將無主荒田作為官田,便是不可以買賣的,他所說的定價招墾便只能是在定租或押租后,將土地租佃給農民開墾,而“取具保結,備價款縣核明,填給印照,準其作為己業”,則表明農民因開墾荒地而形成的租佃權是永久性的,而在官方文件中,正是此種權利被稱為“業”。咸豐七年為北京程永福租種官地所頒發的執照便是清政府將官田租給農民耕種的一個實例: 禮部為換給執照事:前據催頭王進祿招得佃戶程永福領種 本部北廠官地一塊,共地柒畝,每年應征額租銀叁錢捌分捌厘捌毫,仍照道光初年每銀壹兩折收制錢玖百文舊章,共折收制錢叁百伍拾文。為此,開明段落、四至,給與印照,于每年征租時,按額定銀數合錢交納。如有情愿按畝交銀者,亦聽其便,毋許拖欠。如無本部印照者,即為私種。給照之后,若有盜賣及私行典押者,一經本部查出,典者、受者一并從嚴究辦不貸。須至執照者。(注: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1402—1403頁。) 這一部照實例印證了清代將官田定租后租給農民耕種并發給專門執照的制度,無此執照在官田上耕種即為私種,而即使有執照也不可以轉賣或抵押。如果這種認識是正確的,那么順治六年頒布的鼓勵流民墾荒令中所稱的“開墾耕種,永準為業”也應當具有同樣的含義。可見,在這里,“業”的概念也是指的永佃權,也就是說,即使是對于開墾無主荒地,經官府給照后,開墾者所獲得的、被稱之為“業”的權利也只是永佃權。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不妨改變一下討論的方向:如果把清代官方語言中的“業”看作是僅指地權,便會出現解讀上的困難。順治十四年制定的《督墾荒地勸罰則例》稱:“其貢監生民人有主荒地,仍明本主開墾,如本主不能開墾者,該地方官招民給與印照開墾,永為己業。”(注:《清世祖實錄》卷190,第6頁。)這一則例規定有主荒地如果本主不能開墾,便由地方官招民開墾,并使開墾者“永為己業”。有學者據此認為清代“新開墾的荒田,以利用,即耕種為取得所有權的第一要件,如不利用,即喪失所有權”。(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第90頁。)顯然,持此看法者是把“業”理解為土地所有權的,開墾者獲得土地所有權,原主當然便喪失了土地所有權。但是基于這種理解,利用便不應當僅僅是新開墾荒地取得或喪失所有權的依據,而應當是所有土地取得、保持或喪失所有權的依據,因為如果土地不利用便要喪失所有權的話,那么無論是新開墾的荒地還是老地都應當如此,況且這里所說的荒地并非一定是未開墾過的土地,因為其已經有主,因而可能是原來開墾過,因戰亂等原因而拋荒的土地。然而還沒有可靠的依據說在清代存在著土地不加利用便喪失所有權的制度。事實上,這里“永為己業”僅僅是在永佃權的意義上使用“業”的概念,是說有主荒地經他人開墾后,開墾者享有永佃權,而非土地所有權。可見,將“業”理解為土地所有權來解讀清代的官方文本也是有疑問的,會導致對清代法律制度的誤解。 總之,在清代的官方語言中,“業”可以看作是永佃權、地權、典權等項權利的總稱,在不同的場合下用以指稱不同的權利,因而與民間契約中所表現出來的觀念一樣,清代官方語言中的“業”也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即可以用來表達地權,也可以用來表達永權佃等其他權利。
三“業”在清代民事習慣法中的意義
筆者已經指出,在清代民間契約中,“業”這一概念具有較為廣泛的包容性,所表達的基本內容是以收益權為核心的一種權利,在清代官方語言中也有類似的表達,可見其作為一個基本的權利概念在清代社會中已經獲得廣泛的認同。然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首先是,“業”這一概念在清代民事習慣法中處于何種地位,發揮著何種作用呢? 寺田浩明提出了“管業來歷”的見解,用以解釋“業”這一概念在清代民事習慣法中所發揮的作用。在他看來,清代的土地所有制度不能以所有權或用益物權這一近代的框架來加以類比。實際上,清代的土地被分成小塊通過契約租佃給農戶耕種,從而形成以經營(耕種)收益權為內容的“業主權”,“農地所有就是以小片地塊上的經濟收益為中心的所有,整個土地法秩序或者也可以單純地稱之為私人的土地所有權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寺田已經把“業”看作是清代社會中所特有的所有權形式,所有的對象與其說是“物”,不如說是一種“經營權”,因為成為轉移和持有對象的始終是眼下的經營收益行為。在此基礎上,寺田認為,圍繞土地的交易行為整體上都是以土地的經營收益及其正當性這一理解為基礎而展開的。通過契約而“交易的對象,與其說是完整的無負擔的‘物’(土地)本身,還不如說是在不言而喻地負有稅糧義務的土地上自由進行經營收益(當時稱為‘管業’)的一種地位。所謂‘土地的買賣’,指的是現在對某土地進行‘管業’的人把這一地位出讓給他人,而且今后永遠允許后者對該地進行‘管業’;所謂‘土地的所有’,指的是自己現在享有的‘管業’地位能夠通過前一管業者交付的契據以及正當地取得該地位的前后經過(當時總稱為‘來歷’。具體表現為前一管業者寫下并交付的‘絕賣契’)來向社會表明的狀態。”耕作權、永佃權等,同樣通過“管業與來歷”的結構在佃戶之間轉讓繼受。而一旦佃戶之間形成這種管業來歷的連鎖,人們就把它與原來的土地買賣關系(田主之間形成的另一個管業來歷的連鎖)相并列,或者稱之為“一田二主”,或者表達為“田面、田底”、“皮業、骨業”、“小業、大業”,將其理解為田主與佃戶各自分別進行買賣和所有的兩種對象。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是在同一土地上展開了兩種經營,或者說兩種謀生手段都依托同一土地。“一旦形成這樣的狀態,當時的人們就不再追問對象的內容,而努力把這些‘業’都理解為所有和買賣”。(注:參見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199—201頁。)寺田浩明進一步從“管業”的角度解釋清代土地契約中所表達的“典”和“買”的關系,認為這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于從“活賣”向“絕賣、死賣”逐漸移行的框架的理解,即田主對佃戶的耕作以“絕”的形式賦予正當性時,或者佃戶承佃之后以種種方式使自己的耕作權獲得“絕”的正當性基礎時,就出現了田底田面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佃戶的耕作權的物權基礎離開了與田主的關系,而呈現出前佃可以直接向后佃移轉權利而不受田主干涉的單一正當化過程。(注:參見岸本美緒:《明清契約文書》,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302頁。)寺田認為,“歸根結底這不過是由‘來歷’作為基礎的‘管業’秩序達到一定穩定性時的結果”。(注: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199—201頁。) 寺田浩明上述觀點的新穎之處表現在他從民間契約文本自身所表達的信息中去把握當時社會的權利狀況,把土地交易慣行視為“賦予經營收益行為正當性”的種種不同形態,從而使已經成為我們頭腦中既成觀念的“所有”和“占有”、“買賣”和“租賃”等概念區分不再那么絕對,(注:參見岸本美緒:《明清契約文書》,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302頁。)這顯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注:另一位日本學者草野靖也明確提出了按照當時人們的觀念來構成契約關系各種范疇的主張。他提出“分種”與“租種”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契約范疇,按照當時人們的觀念,分種顯然與土地借貸關系區別開來,是“地主招雇農民來耕種自己所有的土地,并把收獲的一部分作為勞動報酬”的經營方式。參見岸本美緒:《明清契約文書》,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303頁。)然而筆者仍要指出的是,在寺田對于“業”的內容界定中所使用的“經營”概念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詮釋。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中,經營概念具有對物的占有,并為了收益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含義。然而,如果看一下清代社會中存在永佃權的狀態下田主所享有的權利的實際狀況,便可以看到,田主雖然也擁有“業”,從而被稱為“業主”,但是并不享有現代意義上的經營權。由此,寺田將“業”界定為“經營收益的地位”便失去了普遍性。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使是在存在永佃權的情況下,田主也享有收取大租的權利,而為收取地租他需要操心并管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也在經營。但是這種解釋也是在現代的語境中作出的,而在清代社會的語境中并不存與此相對應的概念。因此筆者認為,在清代民間契約所表達的社會觀念中,“業”這一概念的基本含義就是獲得收益的權利,而“管業”則是指對這一權利的行使,即實際獲得收益的行為:對于田主來說,收取大租是其管業行為;對于佃主來說,收取小租是其管業行為,而對于佃戶來說,對土地進行實際的耕種并獲得收獲也是其管業行為。對“業”的概念的此種厘清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對其實際作用作出合理的說明,例如,在出典的情況下,清人認為出典人仍然享有業權,但這種業權顯然已經完全不具有經營的性質,而僅僅表現為一種收回未來收益權的權利。 另一方面,對寺田浩明關于“管業來歷”的觀點也存在進一步推敲的必要。根據寺田的見解,清代“無論國家還是社會之中,都找不到離開事實上的領有關系而證實抽象的權原存在和保護其存在的所謂‘土地所有權制度’。在國家與社會中較清楚地存在著的,只是一種通過契約文書而形成的‘土地買賣制度’。在那里,買賣時由賣主寫下并交給買主的契據本身就是買主唯一的權限證書,發揮著爭取來自社會的一定支持或保護這一功能”。(注: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199—201頁。)因此,土地契約成為表明其業主權的正當性,從而使“管業來歷”得以合法延續的唯一手段。如果這一判斷是正確的,那么在實際發生的土地交易中,賣者所擁有的“前腳”,即其前手寫給他的契約便成為證明其“業”的合法來歷的唯一證據,而向買者交付這一前手契約便成為土地買賣契約成立的必要要件。然而,清代民間契約中所表達的信息卻表明,在土地買賣中,“前腳”的交付并非必要條件,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土地契約中載明賣主因前腳丟失而既無法交付,也無法示明的情況,或者是賣主雖有前契,但是因該契與其他產契連在一起而不能交付的情況。因此,關于“管業來歷”的理論構想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作為一個被社會廣泛認同的概念,“業”所表達的權利內涵是什么呢?或者說,當人們使用“業”這一概念來表達一種權利時,它意味著什么樣的權利呢? 在清代,業作為一種權利,其基本的內涵首先是獲得收益的權利,即憑借對“業”的擁有便可以獲得收益。在前引例1契約中,張萬卿將土地賣給了尤氏為業,尤氏因此而獲得了以此土地“召佃耕種”,從而獲取地租的權利。在清代,當田骨與田皮合一時,地租也是合一的;而一旦田骨與田皮分離,地租便在骨主與皮主之間分割,從而被分為兩個部分:骨主憑借其土地所有權而向皮主收取地租,這種地租被稱為“大租”,而皮主則憑借其田面權向佃戶收取地租,這種地租也稱為“小租”。在例1契中,尤氏買得的土地是田骨權與田面權合一的土地,因而其獲得的當是收取包括大租和小租在內的地租的權利。依照現代民法的觀念,尤氏收取地租的權利來源于他通過購買行為而獲得的土地所有權,這種土地所有權是一種物權,是人對物的關系,而收益權是這種物權的當然組成部分。然而在清人的觀念中,人對物的權利卻并非收益權的基礎,或者說收益權與對物的權利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系。關于這一點,筆者首先要指出的便是前面提到的例2契,在該契約中,立契人認為交易的對象并不是土地,而是地租,或者換句話說,立契人忽略了對土地的物權,而強調了收益的權利,他認為通過契約所讓渡的,是土地的收益權而不是土地本身。其次,筆者還要指出,清代民間有所謂“金皮銀骨”的俗稱,意思是田皮的價值高于田骨的價值,憑借田面權獲得的收益要遠遠高于憑借田骨權而獲得的收益,“以至于皮主從土地所獲得的收益占十之八九,田主卻只得十之一二”。(注: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第117頁。另外,中國臺灣地區清末民初也普遍實行“大租小租制”,基于現代民法物權理論的理解,大租戶應當被視為業主,但在20世紀初日本占領臺灣時期所做的調查中發現,小租戶實際上享有的權利更為強有力,事實上已獲得了業主的地位。參見岸本美緒:《明清契約文書》,載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284、294頁。)一般而言,主要的權利當然應當獲得主要的收益,在現代民法中,物權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當然是主要的權利,而收益權僅僅是物權的一種權能,但是在清代,田面權所獲得的收益卻遠遠超過土地所有權,可見在清人的觀念中,如果不是認為永佃權是一項比土地所有權更為重要的權利的話,便是根本未對物權和用益物權作出區分,從而僅僅是在收益的意義上區分各種權利。再次,從永佃權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看,在設有永佃權的土地上,永佃權人享有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多項權利,并且這種權利可以世代相承,田主不得無故剝奪,而田主卻只剩下了收益權和對田骨的處分權,由于永佃權不可收回,因而其對田骨的處分權實際上也僅僅是對其收益權的轉讓。在清代的土地制度中發展出永佃權這種權利類型,恐怕也是與清人的觀念中重視收益權而輕視對物的權利有關。 筆者認為,業在清代的法律體系中是以能夠帶來收益的財產為對象而設定的權利,其權利客體與那些只能使用而不能帶來收益的財產相對應。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把清代的財產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那些可以構成業權的客體的財產,另一部分則是只能帶來使用效益而不能帶來收益的財產;相應地,財產權利也分為兩部分,即業權和一般財產權,前者的交易需要通過契約的形式進行,而后者則并非必須通過契約進行。契約在業權轉讓的過程中起著確認權利轉移的作用,而在交易之后則起著證明業權歸屬的作用。 當然,正如筆者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契約本身并非業權歸屬的必不可少的證明,因為在清代社會中,對業權的證明是鄉村社會自治的一個重要功能,但是在存在契約的情況下,它往往起著直接證明的作用。如果這樣來劃分清代社會中財產權利的類型,那么,在民間契約中經常出現的所謂田權、骨權、皮權、典權、佃權、永佃權、股權等等,都可以歸入業權的范疇。唯一難以歸類的是貨幣財產。以現代社會的觀念來看,貨幣是可以帶來收益的,事實上,清代社會中民間借貸,甚至高利貸的存在似乎也表明在清人的觀念中貨幣也是可以帶來收益的。和清以前的古代社會一樣,在清代社會中主流的觀念并不認為貨幣是能夠帶來收益的財產,這從當時人們仍然是有了錢以后就要購田置產,或者是有些地主仍然習慣于把錢埋在地下這樣一些現象中可以得到印證。除了少數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以外,貨幣借貸主要被看作是在遇有急用時提供幫助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取得收益的手段。盡管清代民間借貸也是要支付利息的,但在一般村民心目中依靠貸款而獲得利息并非一種可靠的謀生手段。在民間契約中也可以看到所謂“指地借錢”的現象,但這也僅是借貸雙方為錢款有可能得不到歸還而設定的一種救濟手段。當然,筆者也認為清代已經出現了把貨幣看作是能夠帶來收益的財產這一觀念的萌芽,這在土地出典關系中得到明確的體現。出典關系是田主將土地這樣一種能夠帶來收益的“業”交付給典主,以換取對一定貨幣的支配權,并且以土地收益抵沖利息,而又約定在將來某個時候以典價贖回土地。在這里,土地收益與利息相對應并且相互沖抵,這就隱含著將土地這種“業”直接與典價這種貨幣相對應,并且相互對等交付的潛在觀念。顯然,在這一關系中已經包含著貨幣雖然具有與土地不同的存在形態,卻也可以與土地相對應這樣一種觀念。但是,筆者認為,由于田主以土地出典獲得的貨幣通常是用于消費而不是用于投資,因而與其說出典關系在清人的心目中被看作是以土地這種業換得了另外一種業,倒不如說是以土地這種能夠帶來收益的業換得了貨幣這種花了就會少,而根本不會帶來收益的財產更為確切。在清人看來,土地作為一種業,具有比非業的貨幣更大的價值,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盡一切可能要贖回土地,(注:當然,清代人們總是希望贖回土地還有其他的原因,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祖業不可賣,守業是盡孝的一個表現,而出賣土地是有失先輩的體面的,典賣既可照贖,因而可以免蒙出賣祖業的恥辱,因而人們非到萬不得已不愿出賣土地而寧愿選擇出典,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贖回。參見李志敏:《中國古代民法》,第106頁。但是筆者認為,在清代土地交易已經非常普遍的情況下,人們選擇典而不是賣,應當還有其經濟上的原因,即認為作為業的土地比非業的貨幣具有更大的價值,這大概也是為什么典主總是容忍田主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貼不絕的原因所在吧。)因此,筆者更傾向于認為在清代人們是把貨幣歸入非業財產范疇的。清代的民間契約和審判實踐表明,業權主要受民間習慣法的調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成文法的保護;而非業財產權較少發生轉移,其轉移在形式上也主要采取口頭約定的方式,這種情況表明在非業財產權的領域中尚未形成完整的、定型的民間習慣法,因而主要受社會意識和倫理道德的調整。 總之,清代民間契約展示了清人關于權利的觀念和語境,使我們有可能從中把握實際存在于清代的財產權利體系。在這一權利體系中,業權居于核心的地位,它是一種能夠為權利人帶來收益的財產權利,權利人通過“管業”,即對與這種權利有關的物的直接使用、出租等形式來實際獲得收益,而在急需大宗開支時,權利人還可以通過典當而獲得業之半價,或者將其出賣而獲得全部價款,甚至可能以各種形式將業權分割,與他人共享或者部分轉讓。在這樣一種制度框架下,財產被置于統一的權利體系之中。與大陸法系將財產權區分為物權和債權的權利體系相比,中國清代的財產權利體系甚至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其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我們甚至難以將近現代發展起來的知識產權和股權在大陸法系的財產權利體系中合理地定位,它既非物權,也不是債權;而在清代的財產權體系下,知識產權和股權卻可以很方便地歸入業權的范疇,因為它能夠為權利人帶來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