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事司法中的嚴(yán)格法律解釋
黃延廷
關(guān)鍵詞: 清代/司法/嚴(yán)格/解釋
內(nèi)容提要: 在清朝,嚴(yán)格貫徹立法者(皇帝)的意圖是司法的本旨,而且為了嚴(yán)格控制司法官吏的刑罰權(quán)濫用,所以也力求對(duì)法律進(jìn)行嚴(yán)格解釋。其中較為突出的方法有字面解釋、當(dāng)然解釋、擴(kuò)大解釋、體系解釋等。 一般司法理論認(rèn)為,法律解釋是法律適用的前提,沒有法律解釋就沒有法律的適用;欲使法律得到正確的適用,必先對(duì)法律規(guī)定的含義作出正確地闡明,而要正確闡明法律規(guī)定的含義,就必須采取正確、科學(xué)的解釋方法。現(xiàn)代法律為了嚴(yán)格貫徹立法者的意圖,都規(guī)定了對(duì)法律進(jìn)行嚴(yán)格解釋的原則,也就是必須最大可能地按法律條文的字面本義來解釋法律。特別是在刑事法領(lǐng)域,更要嚴(yán)格解釋,防止隨意擴(kuò)大法條的意思,以避免刑罰權(quán)的濫用。對(duì)法律的嚴(yán)格解釋,這是追求司法邏輯性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也是嚴(yán)格依法、適用三段論推理的前提。在中國(guó)傳統(tǒng)刑事司法領(lǐng)域,嚴(yán)格貫徹立法者(皇帝)的意圖也是司法的本旨,所以也力求對(duì)法律進(jìn)行嚴(yán)格解釋。清代亦是如此。 一、對(duì)法律條文詞匯的字面解釋 要準(zhǔn)確把握法條的意思,必先對(duì)組成法條的詞匯的意思嚴(yán)格把握。要對(duì)法條詞匯意思作準(zhǔn)確把握,必須對(duì)法條詞匯作字面解釋。所謂法條詞匯的字面解釋就是指,嚴(yán)格按照這一詞匯的通常含義解釋或者嚴(yán)格按照這一詞匯的特定的法律上的專門的含義進(jìn)行解釋。①這是成文法系司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法律能夠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得到確實(shí)地貫徹的關(guān)鍵所在。中國(guó)古代是典型的、成熟的成文法國(guó)家,故而,這也是清代司法中法官們解釋法律的常用的方法。 先看中國(guó)古代司法嚴(yán)格按照法條詞匯的通常含義來解釋法律。《刑案匯覽》中記載一案:屈全經(jīng)將其女兒屈氏許配給王云之子王杜兒。嘉慶二十三年王杜兒去新疆省哈密打工掙錢,曾寄信來,但人并未回來。道光七年,屈全經(jīng)向縣衙起訴,在“夫逃亡三年不還者,聽經(jīng)官告給執(zhí)照,別行改嫁”條例的基礎(chǔ)上得到官府許可,將屈氏改嫁給王萬(wàn)春,并立即讓他們成了婚。王云不服而上訴,在上級(jí)官?gòu)d審理的結(jié)果,得到“依律,判定以屈氏歸于前夫王杜兒并應(yīng)使之完娶”的判決。但王萬(wàn)春以依夫逃亡律,并已有兒子為由不服,陜西巡撫將之轉(zhuǎn)達(dá)刑部并請(qǐng)指示,刑部解釋道:官給執(zhí)照別行改嫁之例,系專指逃亡不還者而言,如系在外貿(mào)易訪親,卻有定處,雖婚嫁偶致愆期,而恩義豈能遽絕,王杜兒在其伯氈房習(xí)藝,有信寄家,迥非逃亡可比,屈全經(jīng)即欲催娶,不過令王云信囑其子回歸,何止遽行控官。并指示全面支持前府之判斷,屈氏應(yīng)歸于王杜兒。②本案典型的體現(xiàn)了對(duì)法律概念“逃亡”的嚴(yán)格解釋。不知去處、毫無(wú)音信則為逃亡,而王杜兒既有去處又有音信豈為逃亡?既不是逃亡,就不能依“逃亡條”來辦。 再舉清代名吏汪輝祖所斷一案: (乾隆25年,浙江·秀水)縣民許天若正月初五日黃昏醉歸,過鄰婦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以沽飲,虞氏詈罵而散。次日,虞氏控準(zhǔn),未審。至二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值,天若詬其無(wú)恥,還家后復(fù)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繯自盡。孫師受篆,即赴相驗(yàn)。時(shí)松江張圯逢與余分里辦事,虞處居張友所分里內(nèi),張以案須“內(nèi)結(jié)”,令將天若收禁通報(bào)。余以為死非羞憤,可以“外結(jié)”。張大以為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枷通詳。撫軍飭將天若收禁,并先查問議詳。余為之議曰:“但經(jīng)調(diào)戲,本婦羞憤自盡,例應(yīng)擬絞。本無(wú)調(diào)奸之心,不過出語(yǔ)褻狎,本婦一聞穢語(yǔ),即便輕生,例應(yīng)擬流。”夫羞憤之心,歷時(shí)漸減,故曰“但經(jīng)”,曰“即便”,是捐軀之時(shí),即在調(diào)戲褻語(yǔ)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沽飲已閱二十八日,果系羞憤,不應(yīng)延隔許時(shí)。且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鄰相安,幾忘前語(yǔ)。其致死之因,則以虞氏催審,天若又向辱罵,是死于氣憤,非死于羞憤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府司照轉(zhuǎn),撫軍又駁,因照流罪,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夢(mèng)虞氏指名告理,冥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yīng)抵,而虞氏不得請(qǐng)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為疑案也。治刑名者奈何不慎。③ 汪輝祖在此案中對(duì)法條中的詞匯“羞憤”、“即便”、“但經(jīng)”等都作了嚴(yán)格的解釋,“羞憤”絕非氣憤,“即便”、“但經(jīng)”都是馬上的意思,最起碼不能超過當(dāng)日。本案虞氏并非死于“羞憤”,而且也不是“但經(jīng)”褻語(yǔ),“即便”輕生。所以決不能適用“但經(jīng)調(diào)戲,本婦羞憤自盡,例應(yīng)擬絞。本無(wú)調(diào)奸之心,不過出語(yǔ)褻狎,本婦一聞穢語(yǔ),即便輕生,例應(yīng)擬流”本條。只是根據(jù)具體情況作出了“罪刑相應(yīng)”的處罰。④ 此兩案都是通過嚴(yán)格解釋法條中的詞匯的通常含義來嚴(yán)格解釋法律規(guī)范的含義,并與當(dāng)前案件相對(duì)照,結(jié)果是當(dāng)前案件與法條并不相符,結(jié)果排除了這些法條的適用,從而達(dá)到了依照法律判決的效果。依照法律判決就是法律有規(guī)定的就依照法律判決,也就是案件事實(shí)符合法律明文的就依法裁判,按律文的規(guī)定定罪量刑,那么它的另一含義就是如果案件事實(shí)與法律規(guī)定不符,就不得以此一法律規(guī)定判罰。這與現(xiàn)代的罪刑法定原則“法有明文依法處罰,沒有規(guī)定的不處罰”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有一定的差別。古代的依照法律判決、緣法斷罪只講如果案件事實(shí)與某一法條相符,就依法判罰,如果案件事實(shí)與某一法條不符,就不能以此一條文規(guī)定的刑罰處罰(如果還要以不合此一案件事實(shí)的規(guī)定處罰的話,那將會(huì)“情罪不協(xié)”,不公平,這是中國(guó)古代司法的大忌)。僅此而已。如果感覺到還應(yīng)處罰的話,這時(shí)就通過比附、類推、造法等推理技術(shù),⑤得出一個(gè)合適的刑罰,以求實(shí)質(zhì)正義。但這不屬于緣法斷罪、嚴(yán)格依照法律判案的范疇,⑥而屬于中國(guó)古代司法的另一個(gè)方面的問題,即“類推裁斷”的問題。而現(xiàn)代刑法在此時(shí)則是不處罰的,因?yàn)椤胺o(wú)明文規(guī)定不處罰”。 其次,清代法律在很多情況下要嚴(yán)格按照這一詞匯的特定的法律上的專門的含義進(jìn)行解釋。 清代法律規(guī)定,如果丈夫殺死其妻,由于“夫?yàn)槠蘧V”的緣故,丈夫可不抵命。但是在司法實(shí)踐當(dāng)中,有丈夫?yàn)榱吮破绕淦拶u奸等,由于其妻不同意,丈夫殺死了妻子的情況,如果這時(shí)不解釋好條文中“夫妻”的含義,就容易適用法律錯(cuò)誤,導(dǎo)致對(duì)罪犯從輕的處罰。這時(shí)司法官就對(duì)“夫妻”的含義作特定的解釋,排除那些已恩斷義絕的夫妻之間的關(guān)系的適用。強(qiáng)逼妻子賣奸、租賃妻子等等是已失夫妻之義的行為,如果這時(shí)因妻子不從而殺死妻子,就按一般人殺死被害人行為處理,處以死罪。⑦比如,在“熊文杰逼妻自盡”一案中,刑部在判決中論證道:“凡人因奸不從,殺死本婦例因斬決;至本夫抑勒其妻賣奸不從故殺,例因斬候。蓋抑妻賣奸,已失夫婦之義,故照凡人故殺例問擬。”⑧而且為了進(jìn)一步使司法明晰,不致發(fā)生錯(cuò)誤,干脆明確規(guī)定:本夫抑勒其妻賣奸不從,故殺,斬監(jiān)候。 還有師生關(guān)系的情形,本來老師對(duì)學(xué)生的犯罪可減等發(fā)落。但如果老師對(duì)學(xué)生實(shí)行了一些實(shí)在是有虧師道的傷害,則在司法中解釋法律的時(shí)候往往對(duì)師生關(guān)系作特定解釋。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有虧師道傷害,這個(gè)時(shí)候已經(jīng)是老師不像老師了,而法律上規(guī)定的老師可減等處罰中的師生關(guān)系,必須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真正地屬于師生的、達(dá)到一般的師生關(guān)系標(biāo)準(zhǔn)的那種師生關(guān)系,至少不能與師生關(guān)系標(biāo)準(zhǔn)錯(cuò)得太遠(yuǎn)。所以這樣的案件不屬師生之間的傷害,排除減等的法律適用。比如在“儒師引誘學(xué)徒為非”一案中,老師劉廷泰因?yàn)閷?duì)學(xué)生劉恩彤之父劉策先有氣,就通過傷害劉恩彤來達(dá)到報(bào)復(fù)劉策先的目的。他就教劉恩彤以手洩精,結(jié)果劉恩彤養(yǎng)成習(xí)慣不能自拔,致使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因此,在判決中該撫就判道:“劉廷泰因泄私憤,教令學(xué)徒劉思彤以手洩精,欲令疾苦,實(shí)屬有虧師道,應(yīng)以凡科斷。”⑨ 其實(shí)這種按照某一詞匯的特定法律含義來解釋的解釋在漢朝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有了。我們來看董仲舒所斷的“毆父”一案中這種解釋的運(yùn)用。 甲父乙與丙爭(zhēng)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dāng)何論?或曰:毆父也,當(dāng)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jìn)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dāng)坐。⑩ 本案董仲舒對(duì)“毆父”進(jìn)行的解釋,就是典型的按照這一詞匯的特定的法律上的專門的含義進(jìn)行的解釋。“毆父”通常的含義就是只要打了父親、傷了父親就是“毆父”,但是在這里法條上的“毆父”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含義,就是只有嚴(yán)重社會(huì)危害性、嚴(yán)重違背道德的毆打父親的行為才能歸入“毆父”的范疇,沒有社會(huì)危害性、人們并不唾棄的毆打父親的行為不能歸入法律上“毆父”的范圍,正像現(xiàn)代刑法中對(duì)故意殺人罪中的殺人一詞的解釋一樣,并不是所有的殺人行為都是故意殺人罪中之殺人,只有具有嚴(yán)重社會(huì)危害性的殺人行為才是殺人罪中的殺人行為,而像正當(dāng)防衛(wèi)中的殺人行為,特別是在對(duì)嚴(yán)重暴力犯罪正當(dāng)防衛(wèi)中的殺死暴徒的殺人行為,不是犯罪行為,不屬于故意殺人罪中殺人這一概念的應(yīng)有之義。所以董仲舒堅(jiān)決把這一為了救其父親而誤傷其父的毆父行為排除于法律上毆父概念的范疇之外,所謂“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dāng)坐”,就是具有現(xiàn)代解釋意義的按法律詞匯的特定的專門含義進(jìn)行解釋的方法,體現(xiàn)了古人較高的嚴(yán)格司法的水平。所以說古人和今人有好多的相通性,決不可過于擴(kuò)大他們之間的差異性。撇開所謂的“現(xiàn)代法律理論和古代法律理論不同”不談,最重要的一點(diǎn)就是,我們都是人,而且都是中國(guó)人,有著根本相同的思維規(guī)律。 二、對(duì)法律條文的當(dāng)然解釋 當(dāng)然解釋,又稱勿論解釋或自然解釋,是指刑法規(guī)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xiàng),但以形式邏輯或者事物屬性的當(dāng)然道理,將該事項(xiàng)解釋為包括在該規(guī)定的適用范圍之內(nèi)。(11)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舉輕明重”和“舉重明輕”。而“舉輕明重”和“舉重明輕”的解釋方法在古代中國(guó)可謂是源遠(yuǎn)流長(zhǎng)、相當(dāng)成熟、運(yùn)用頻繁。下面就以清代的情況加以說明。 在“郭景夏毆死小功兄”一案中,刑部解釋道:“毆死本宗緦麻尊長(zhǎng)之案,其應(yīng)行留養(yǎng),尚須俟秋審時(shí)辦理。而毆死本宗小功尊長(zhǎng)(較之緦麻尊長(zhǎng),關(guān)系更近一等),自不得隨案聲請(qǐng)留養(yǎng)。”而且又舉出江蘇省張阿悌毆死胞兄張文顯案、山東省姚恒杰毆死大功兄姚恒清一案都作了這樣的解釋,判決不得隨案聲請(qǐng)留養(yǎng)。最后判決道:“此案:郭景夏將郭景魁累毆身死。惟死系本宗小功尊長(zhǎng),本例應(yīng)擬斬監(jiān)候。親老單丁之處,仍應(yīng)照律不準(zhǔn)聲請(qǐng)。”(12)本案“輕重相舉”很簡(jiǎn)單,就是打死遠(yuǎn)親尊長(zhǎng)都不能聲請(qǐng)留養(yǎng)了,那打死近親尊長(zhǎng),根據(jù)事物的當(dāng)然道理,就更不能聲請(qǐng)留養(yǎng)了。需要說明的是,毆死本宗緦麻尊長(zhǎng)不準(zhǔn)聲請(qǐng)留養(yǎng)的規(guī)則雖非法律條文,但是成案中的處理規(guī)則,關(guān)于成案中的規(guī)則,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判例法,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法律淵源,反正都是可以引用的法律根據(jù)、理由。(13)筆者認(rèn)為它應(yīng)像成文法一樣,是重要的法律淵源。故可以它為準(zhǔn)“輕重相明”。此案應(yīng)是“舉輕明重”的情況,下面再舉“舉重明輕”的情形。 奉天司查:隨駕官員之跟役攜帶馬匹器械逃回,……查例載:隨征兵丁在軍營(yíng)潛逃,拿獲擬斬立決。其在軍務(wù)未竣以前投首發(fā)遣,至跟隨之余丁有偷盜馬匹器械潛逃者,亦擬斬立決。如有投首,亦照兵丁投首問擬等語(yǔ)。是隨征余丁逃回,尚得以自行投首分別減等,則隨圍攜帶馬匹逃回之跟役自行投首,亦應(yīng)比擬減等,舉重可以該輕也。今黑龍江將軍咨巴爾達(dá)跟隨伊主浙爾金保隨圍騎馬逃走,旋即赴官投首,咨請(qǐng)部示一案,該司援引聞拿投首減一等例,擬請(qǐng)于絞罪上減等,改發(fā)駐防為奴,詳加查核,似屬允協(xié)。(14) 法有明文,隨征余丁有盜馬或器械逃跑的,斬立決,如投案自首,減一等處理(余丁與兵丁不同,大概屬于給兵丁服務(wù)的人員)。而跟隨皇帝狩獵的官員的仆從在狩獵的過程中騎馬逃跑的,其危害性要比隨征余丁騎馬逃跑的危害性小。隨征余丁逃跑自首能夠減等,當(dāng)然隨圍官員仆從逃跑又自首也能夠減等。須注意的是,清代并非所有的犯罪自首都可按名例律減等處理,嚴(yán)重犯罪的自首是不能減等的,所以才有本案的“舉重明輕”解釋。 我國(guó)古代法律特別是刑法早就在司法實(shí)踐當(dāng)中運(yùn)用了“輕重相舉”的當(dāng)然解釋的解釋方法,應(yīng)該說到唐朝的時(shí)候已經(jīng)相當(dāng)成熟了。《唐律疏議·名例律》正文規(guī)定:“諸斷罪而無(wú)正條,其應(yīng)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yīng)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議》接著以舉例的方式解釋了此條文的意思:應(yīng)“出罪”的,采用“舉重明輕”的辦法,如主人打傷夜間無(wú)故闖入自己家的人,該如何處治,法律沒有規(guī)定,但是可以援引唐律中“夜無(wú)故入人家,主人登時(shí)殺死者,勿論”一條作為根據(jù),既然主人殺死無(wú)故闖入者不構(gòu)成犯罪,那么打傷闖入者更不會(huì)構(gòu)成犯罪。應(yīng)“入罪”的,采用“舉輕明重”的辦法,如殺死期親尊長(zhǎng),該如何治罪,法律也沒有規(guī)定,但法律規(guī)定“謀殺期親尊長(zhǎng)者,斬”,既然謀殺者便要處以斬刑,已殺者更要處斬了。有人可能說此是立法的規(guī)定,實(shí)踐中照著做就是了,不存在司法實(shí)踐中法官解釋、適用法律的問題。但是我們應(yīng)該知道,立法的規(guī)定最初都是來源于司法實(shí)踐當(dāng)中的判例,“法生于例”,“皋陶造獄,法律存”可生動(dòng)地說明這個(gè)現(xiàn)象。也就是說抽象的法律規(guī)范都是對(duì)司法實(shí)踐中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那么也就是說,歸結(jié)到“舉輕明重”、“舉重明輕”此一規(guī)定上,在這樣的正式的法律條文出現(xiàn)以前,在唐代以前的歷史長(zhǎng)河中,司法實(shí)踐中都是在沒有這樣的條文的情況下,遇到此種情況,都是這樣來解釋適用法律的。而到了唐朝,這樣的解釋技術(shù)已經(jīng)爐火純青了,才上升到正式的法律規(guī)定。 唐代這樣的當(dāng)然解釋,是有著非常嚴(yán)格的規(guī)則的,就是被解釋的事項(xiàng)必須與已經(jīng)明確規(guī)定的事項(xiàng)具有同樣的屬性且程度更嚴(yán)重或更輕微,而且,此一事項(xiàng)必須是由已明確規(guī)定的事項(xiàng)發(fā)展而來或者是已明確規(guī)定的事項(xiàng)是由該事項(xiàng)發(fā)展而來。比如,已殺期親尊長(zhǎng)就是由“謀殺期親尊長(zhǎng)”這一明確規(guī)定的事項(xiàng)自然發(fā)展而來的,“打死夜入民宅者”這一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行為就是“打傷夜入民宅者”這一行為的自然發(fā)展。充分體現(xiàn)了古人適用刑罰的慎重、嚴(yán)謹(jǐn)?shù)膽B(tài)度,與西方的概念法學(xué)為維護(hù)人權(quán)而嚴(yán)格解釋法律有著驚人的相像。 唐代法律之所以成熟、經(jīng)典、偉大,是中華法系的代表之作,這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唐以后的朝代也沒有這樣嚴(yán)格要求了,就是現(xiàn)在我們?cè)谧镄谭ǘㄟ@樣的現(xiàn)代理念之下在用這樣的技術(shù)解釋刑法方面與唐人相比也顯得有些遜色。臺(tái)灣學(xué)者通常舉下列例子來說明在司法實(shí)務(wù)界或?qū)W界中“舉輕以明重”的法律解釋方法的運(yùn)用。“修筑馬路,法雖僅記載禁止牛馬通過,但像駱駝之體質(zhì)及重量既較牛馬為大為重,則當(dāng)然亦在禁止之列,法文僅記載禁止以鉤釣魚之捕魚行為,則較以鉤釣魚為甚之投網(wǎng)捕魚之方法,當(dāng)然亦在禁止之列。”(15)法文雖僅禁止陸海空軍軍人搶奪財(cái)物,則更為嚴(yán)重的陸海空軍軍人搶劫財(cái)物的行為,更有理由使用該條文。(16)這些就表明,臺(tái)灣實(shí)務(wù)界和理論界并沒有將“舉輕以明重”的當(dāng)然道理局限在刑法未明確規(guī)定的事項(xiàng)與刑法明確規(guī)定的事項(xiàng)之間具有邏輯發(fā)展關(guān)系的范圍內(nèi),因?yàn)轳橊劦韧ㄟ^馬路并非牛馬通過馬路這樣行為的自然發(fā)展,而搶劫行為也并不一定都是搶奪行為自然發(fā)展而來,罪犯完全可以不經(jīng)搶奪而直接搶劫。這樣無(wú)疑會(huì)導(dǎo)致當(dāng)然解釋的濫用,從而造成對(duì)刑法的恣意解釋,最終破壞對(duì)刑法嚴(yán)格解釋乃至罪刑法定的原則。因而這種方法是危險(xiǎn)的、不可取的。(17) 三、對(duì)法律的擴(kuò)張解釋 即使在現(xiàn)代刑事法律的理論之下,也不能排除對(duì)法律的一定程度的擴(kuò)張解釋。現(xiàn)代的擴(kuò)張解釋是指,對(duì)法條用語(yǔ)通常含義的擴(kuò)張,但此擴(kuò)張仍在該用語(yǔ)可能具有的含義之內(nèi)。(18)在清代的法律之中,這樣的擴(kuò)張解釋也經(jīng)常見到。這樣的擴(kuò)張解釋是在嚴(yán)格解釋之下的擴(kuò)張解釋,排除中國(guó)古代大量存在的為了擴(kuò)大刑罰權(quán)的類推解釋的情形。這種嚴(yán)格解釋的目的是為了嚴(yán)格貫徹統(tǒng)治者或皇帝的意志,而與現(xiàn)在的刑事法律的嚴(yán)格解釋是為了充分的保障人權(quán)有所不同。 比如,在《駁案新編》卷三“本夫奸所獲奸將奸婦殺死奸夫到官不諱·貌應(yīng)瑞”一案中,貌應(yīng)瑞之妻張氏與王幅多次通奸,被貌應(yīng)瑞撞破后受到責(zé)打,仍不思悔改。后王幅買饃送與張氏,在巷道內(nèi)共坐談笑,被貌應(yīng)瑞撞見,張氏被貌應(yīng)瑞毆死。初審據(jù)殺奸處為非奸所而判奸夫、殺者(本夫)各杖一百,徒三年(依律,如系奸所殺死奸婦,本夫?yàn)檎蓉?zé),奸夫?yàn)榻g候)。刑部認(rèn)為:“平日未經(jīng)和奸之人,一男一女面見然一處,亦涉調(diào)戲勾引之嫌,況王幅素系該氏奸夫,今復(fù)同坐說笑,其為戀奸欲續(xù)情事顯然。是同坐既屬戀奸,巷道即屬奸所。律載非奸所一條,非謂行奸必有定所,亦不必兩人正在行奸之時(shí)。巷道之內(nèi),奸夫奸婦同坐一處,不可不謂之奸所。”故此案中本夫貌應(yīng)瑞殺死奸婦張氏,應(yīng)定杖責(zé),而奸夫王幅則定絞監(jiān)候。皇帝批準(zhǔn)了此判決。很清楚,此案中,刑部擴(kuò)張解釋了律文中“奸所”的含義,奸所的字面含義應(yīng)是行奸之所,而戀奸之所當(dāng)屬于奸所可能具有的含義之內(nèi)。張氏與王幅多次通奸,又在巷道戀奸,巷道即屬奸所,司法官依“在奸所殺死奸婦”判決當(dāng)是緣法斷罪。 再如,“鄧沅供殺死奸夫鄧?yán)乡邸币话福嚴(yán)乡叟c鄧沅供之妻鄧程氏通奸,鄧沅供聞知,責(zé)罵其妻,并聲言要捉鄧?yán)嫌滓徊⑺凸佟`嚴(yán)乡酆ε拢s鄧程氏一塊逃跑,鄧沅供糾伙尋找,找到豬市街,發(fā)現(xiàn)二人同坐一處,就將鄧?yán)嫌鬃侥美墸嚴(yán)嫌撞环櫫R,鄧沅供憤激之下將其毆死。刑部就將“奸所”又作了擴(kuò)大解釋,這一次是從奸夫、奸婦同逃之所當(dāng)屬奸所,以及本夫當(dāng)時(shí)的憤激情緒來擴(kuò)大解釋奸所的,當(dāng)然外逃之所也屬戀奸之所。奸逃之所、戀奸之所都屬奸所的可能含義范圍之內(nèi)。正如刑部所論:“至奸夫、奸婦同挈外逃,即外逃之所即與奸所無(wú)疑。在本夫目擊其妻與人外逃較之目擊其妻與人行奸,其憤激難堪之情自無(wú)二致。今鄧沅供瞥見鄧?yán)乡叟c鄧程氏同坐一處,一并挈獲,是拐逃所在即屬獲奸之所,其捕獲捆縛后欲行送究,將鄧?yán)乡酃矚聰溃c奸所獲奸非登時(shí)殺死之例相符。”(19)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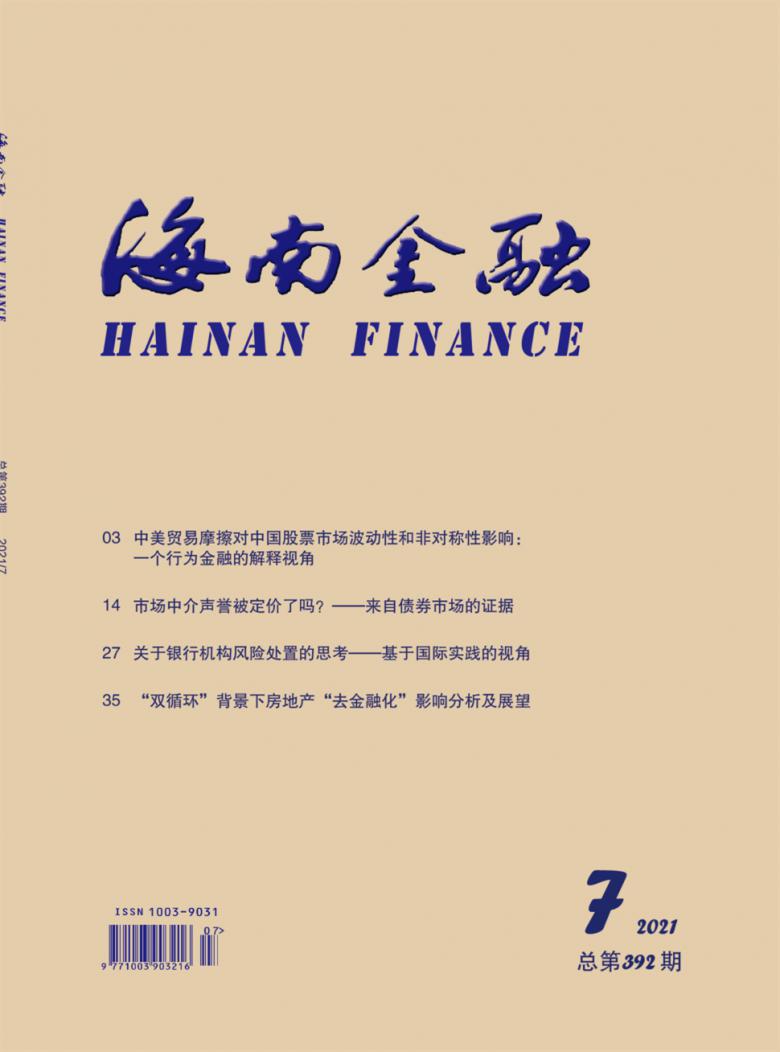
床與液壓.jpg)

能.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