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之分與重情細(xì)故:清代法研究中的法及案件分類問題
里贊
關(guān)鍵詞: 民刑之分/重情/細(xì)故/清代法 內(nèi)容提要: 將清代法以及案件按照現(xiàn)代法劃分民刑的方法進(jìn)行研究或概括雖是法史研究中的固有模式,但對(duì)此研究理路并非沒有再討論的余地。無論從清代成文法的規(guī)定,或是官箴為代表的法律實(shí)踐描述以及基層檔案對(duì)州縣審斷實(shí)踐的記載,似均表明有清法律的案件分類或?qū)彴赋绦虻闹贫仍O(shè)計(jì)是以“重情與細(xì)故(或細(xì)事)”相分而非現(xiàn)代法的民刑劃分。申論此問題對(duì)于如實(shí)再現(xiàn)史實(shí)以盡可能避免法史研究中的“倒放電影”之弊當(dāng)有一定意義。 當(dāng)今中國法學(xué),沿襲了清末以來以西方法為模本研究中國傳統(tǒng)法的范式,形成了在法律體系和案件分類上的看似規(guī)范實(shí)則相距實(shí)情甚遠(yuǎn)的理論表述,如中國古代刑法、中國古代民法、中國古代刑事訴訟法、中國古代民事訴訟法等。①迄今為止,研究中國法律史的作品,大多陷此窠臼。這種在理論思維上的“趨新崇西”和研究方法上的“倒放電影”②,忽視了這樣一個(gè)基本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實(shí),即中國古代社會(huì)及其法律與西方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類型。目前法史學(xué)界對(duì)于包括清代在內(nèi)的中國傳統(tǒng)法律體系以及案件分類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有影響的可大致歸為“套用派”和“古已有之派”(所謂“西方源出于中國”)。 所謂“套用派”,即通過現(xiàn)代的法律術(shù)語和法律體制概括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制度,或以現(xiàn)代的法學(xué)原理解釋以往的法律現(xiàn)象和問題。如將原本一部內(nèi)在有機(jī)的《唐律》或《大清律例》分割為民法、刑法等現(xiàn)代的部門法,將《唐六典》比附為“行政法”,甚至以現(xiàn)代法律體系的理論立場和標(biāo)準(zhǔn)評(píng)價(jià)中國古代成文法的特點(diǎn)為“諸法合體”或“諸法并存”等等③。而“古已有之派”,則通常以暗自承認(rèn)西方或現(xiàn)代標(biāo)準(zhǔn)合理的前提下反以文化自信的姿態(tài)出示,強(qiáng)調(diào)西方或現(xiàn)代的東西在中國古已有之。如認(rèn)為法律之分民、刑非西法獨(dú)有,在中國則古已有之。④另有相當(dāng)一些反對(duì)“中國古代法重刑輕民”論的學(xué)者在申辯中國古代不僅有民法且發(fā)達(dá)時(shí),其所持立場大致多靠此派。 必須肯定地是,所有這些研究無論存在何種可以商榷的余地,就其成果而言在大大豐富了我們對(duì)法律史的認(rèn)識(shí)的基礎(chǔ)上,對(duì)傳統(tǒng)法律研究都不失為有意義的探索和開拓。在這個(gè)前提下,又應(yīng)當(dāng)引為注意的是,按照現(xiàn)有的法律體系對(duì)如清季的法律或案件進(jìn)行六法全書式的劃分,也許方便了我們的“知識(shí)檢索”,但卻是在根據(jù)現(xiàn)在的需要去“使用”歷史事實(shí),難免會(huì)割裂中國傳統(tǒng)法律和文化本應(yīng)有的整體性,用如民、刑的二元?dú)w類也會(huì)忽略掉法律中的某些難以用現(xiàn)代標(biāo)準(zhǔn)歸類的模糊領(lǐng)域,正如李啟成在對(duì)《各級(jí)審判廳判牘》的分類進(jìn)行論述時(shí)談到的,按舊律,分戶婚、田宅、錢債、人命、族制、市厘、盜竊、斗毆、訴訟、贓私、詐偽、奸拐、雜犯、禁煙十四門。若按刑事(確定罪之有無)和民事(確定理之曲直)的分類重新編排,戶婚、田宅、錢債、族制諸門大致可歸入民事范疇,人命、斗毆、盜竊等或可歸入刑事,而訴訟、市厘、雜犯中的案件則很難簡單納入二元標(biāo)準(zhǔn)下的體系,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1] 以滋賀為代表的日本學(xué)者已注意到這個(gè)問題。滋賀在評(píng)價(jià)戴炎輝對(duì)清代淡新檔案進(jìn)行民刑劃分時(shí)就說: 檔案中可以看到,刑事類中將及一半的案件,雖然基本上與某些民事案件類型相同,卻因著眼于其暴力面而被歸入了刑事類,它們的“刑事性”是值得推敲的。對(duì)案件進(jìn)行分類的工作,包括在刑事民事的大類方面和各自的細(xì)目方面,雖然在某些程度上是可能與有意義的,但如果想要在一切細(xì)節(jié)上都分得沒有異議,則相當(dāng)困難。[2] 同樣,對(duì)審斷上的刑事與民事訴訟的區(qū)分,寺田浩明也提出了質(zhì)疑。他承認(rèn),清代司法制度并不存在現(xiàn)代所謂“民事審判程序”和“刑事審判程序”之類程序性質(zhì)上的區(qū)分。[3] 盡管日本學(xué)者意識(shí)到這一問題,但是,在他們的研究中仍不知不覺地回到了他們已然意識(shí)到的、需要克服的思路上。就現(xiàn)有的研究來看,幾乎所有學(xué)者都還是以民刑之分的理論標(biāo)準(zhǔn)作為論述和分析清代法律和州縣審斷問題的基本立論點(diǎn)。 民、刑劃分理論,實(shí)為移植自西法所承襲的六法體系,即將法律按照若干部門進(jìn)行劃分,由此構(gòu)成法律體系。其淵源于羅馬法,確立于近代的歐洲大陸國家,流行于大陸法系⑤,主要特點(diǎn)是將法律區(qū)隔為公法與私法,強(qiáng)調(diào)實(shí)體法和程序法之分,并按照法律的調(diào)整對(duì)象(即法律調(diào)整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及其性質(zhì))和法律的調(diào)整方法來區(qū)分刑、民及其它法律制度。 清代則未有現(xiàn)代體系化的部門法劃分理論,而是以“重情”與“細(xì)故”這兩個(gè)較為模糊的概念來區(qū)分案件種類并設(shè)計(jì)審級(jí)的。⑥按照清律規(guī)定,“州縣自行審理一切戶婚、田土等項(xiàng)”⑦,《清史稿·刑法志》也云:“戶婚、田土及笞杖輕罪由州縣官完結(jié),例稱自理。”[4]即州縣可自行審理戶籍、繼承、婚姻、土地、水利、債務(wù)案件,以及斗毆、輕傷、偷竊等處刑為“笞杖”的案件。這些自理案件州縣即可定讞,因不涉及命盜重情,稱為“細(xì)故”。除此之外,處“徒”刑以上的案件,州縣則只有初審權(quán)而無權(quán)作最后決斷。由于這部分案件通常涉及人命奸盜等重大情節(jié),稱為“重情”。 本文無意對(duì)現(xiàn)代的民、刑劃分和清代“細(xì)故”、“重情”劃分作價(jià)值判斷。事實(shí)上,因劃分標(biāo)準(zhǔn)不清以及對(duì)中間地帶的忽視,民、刑之分在當(dāng)代法學(xué)即已遭詬病,并有同屬西方法律體制的英美法系未有六法之分而依然法律順暢運(yùn)行之例。故倘武斷的以民刑之分描述清代法律及案件分類,甚至給予價(jià)值判斷,⑧并不一定允當(dāng)。而且“重情”與“細(xì)故”之分與民、刑之分本身所涵蓋的案件范圍也不可等同。如前所述,“細(xì)故”中有涉?zhèn)捅I竊等案件,就民刑劃分而言當(dāng)屬刑事而非民事,故而長期以來盛行于法學(xué)界的將“細(xì)故”等同于民,“重情”等同于刑的說法,并由此產(chǎn)生的將清代審斷程序劃分為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論述,都有混淆二者概念而產(chǎn)生關(guān)公斗秦瓊的時(shí)空錯(cuò)亂之虞。 案件和法律體系的劃分,是和其所存在的社會(huì)歷史環(huán)境相關(guān)聯(lián)的。“重情”與“細(xì)故”之分和民、刑之分各有其所存在的文化背景乃至?xí)r代背景。在社會(huì)知識(shí)不斷細(xì)化和專門化的今天,劃分民刑乃至六法,或可適應(yīng)當(dāng)代中國的成文法體制并為法官找法、嚴(yán)格援引法律提供方便;在承襲前朝法律文化的清代社會(huì),以“細(xì)”和“重”為據(jù)將案件概括歸類并給予州縣相當(dāng)程度的自主權(quán),體現(xiàn)的恰恰是清代的法律認(rèn)識(shí)以及法律的存在方式。 據(jù)此,本文未按民事和刑事來劃分案件,也未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來劃分審斷過程。因?yàn)榫科鋵?shí)質(zhì),州縣在處理“重情”和“細(xì)故”兩類案件時(shí),除“重情”需報(bào)上級(jí)定讞外,其審斷過程和州縣所行使的權(quán)力范圍都是一樣的,并不存在兩套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審斷程序。簡言之,州縣以其所享有的事實(shí)上的裁斷全權(quán),結(jié)合個(gè)案的具體情形,以糾紛化解為目的靈活主動(dòng)的運(yùn)用法律、選擇程序,并不因案件之屬民刑否而受影響。 雖然清代州縣審斷中不存在所謂的民刑之分,但并不意味著重情與細(xì)故兩種案件在審斷中沒有制度設(shè)計(jì)上的差別。這種差別在管轄、受理和結(jié)案等環(huán)節(jié)中都有體現(xiàn)。 在管轄問題上,清代法律中州縣的管轄權(quán)是以細(xì)故與重情來確定的。常例而論,清代州縣對(duì)其管轄境內(nèi)所有糾紛俱有管轄權(quán),其中,細(xì)故糾紛即“自理詞訟”,州縣衙門但可自行審結(jié),州縣對(duì)其轄區(qū)內(nèi)的“自理詞訟”有終審判決權(quán)。對(duì)于人命、強(qiáng)盜(搶劫)、邪教、光棍、逃人等嚴(yán)重犯罪案件和其它應(yīng)處徒刑以上的案件,如強(qiáng)奸、拐騙、窩賭、私鹽、衙蠢等,州縣雖無權(quán)作出最終判決,但仍需行使偵查、緝捕、采取強(qiáng)制措施、初審并作出判決(時(shí)稱“看語”或“擬律”,即法律意見)。 清代法律對(duì)“告訴”(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司法程序中的“起訴”)作有時(shí)間上的限制。每年農(nóng)歷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為農(nóng)忙時(shí)期,細(xì)故之案是不準(zhǔn)受理的。此等事件須在八月初一以后,始可聽斷。但命盜案以及謀反、叛逆、貪贓枉法等重情之案仍照常受理。這種在特定時(shí)期不予受理詞訟的制度,亦稱“放告”。按此制度,若在農(nóng)忙期內(nèi)受理細(xì)故之案,則要受督撫指名題參。⑨ 在案件審結(jié)后的處理上,細(xì)故與重情也有不同。細(xì)故之案,即州縣自理之案,應(yīng)逐件登記,每月造冊(cè),申送府道、司、及督撫查考。巡道巡歷州縣所至,即提州縣衙詞訟號(hào)簿,逐一稽查,如有未完之案,未經(jīng)記入號(hào)簿,先責(zé)書吏,并將州縣官揭報(bào)督撫,分別題參。其已結(jié)之案,如巡道認(rèn)為判斷不公,或情節(jié)可疑,須立即提案審查核正。若有吏役訟棍舞弊等情,亦應(yīng)親提究治。[5]重情之案,即罪至徒刑及流刑之案,州縣官審理結(jié)案之后,如有聽斷不公,民人得將冤抑實(shí)情,赴該上司衙門呈訴。上司得提案卷查核改正。命案及盜案,州縣官得報(bào),即行勘驗(yàn),并通詳上司。通詳之后,破獲犯人,取得供詞,應(yīng)將各供詳報(bào)。命盜案審結(jié)后,應(yīng)解府審轉(zhuǎn)。審轉(zhuǎn)官認(rèn)為情節(jié)尚有可疑,或犯人翻供,即派員覆審。至督撫審勘具題。若有應(yīng)專褶具奏者,督撫接到詳文,即提案至省城,率同司道親鞠。⑩罪至死刑之案,須經(jīng)三法司秋審朝審,始可定讞。(11) 雖然細(xì)故與重情在審前和審后均有許多不同的處理規(guī)定,但需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州縣審理過程中,并無重情與細(xì)故的程序性的嚴(yán)格區(qū)分,即沒有如許多學(xué)者所謂“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別。重情案件和細(xì)故案件均由州縣全權(quán)自理,對(duì)于重情案件,清代州縣的初審?fù)瑯邮钦降膶彅啵⑶抑菘h要根據(jù)《大清律例》的條款提出判決意見,即“看語”,亦稱“擬律”,這是州縣針對(duì)重情案件所作書面裁斷。州縣初審?fù)戤叄瑧?yīng)將包括“看語”在內(nèi)的全部案卷報(bào)送上司,所謂“牧令為執(zhí)法之官,用法至枷杖而止,枷杖之外,不得自專。”(12) 州縣對(duì)轄區(qū)內(nèi)重情和細(xì)故均有審斷之責(zé),因此即便是重情案件,也只有州縣衙門不予受理或百姓認(rèn)為審判不公時(shí),才允許申訴于上級(jí)衙門。按清代法律,“軍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應(yīng)先赴州縣衙門具控。如審斷不公,再赴該上司呈明;若再屈抑,方準(zhǔn)來京呈訴。”(13)如果不先到州縣告訴而直接到上級(jí)衙門,就是清律所嚴(yán)令禁止的“越訴”行為。 對(duì)于州縣自理之案,即戶婚、田土、錢債、斗毆、賭博等“細(xì)故”,應(yīng)向事犯地方官衙門告理,若向上司衙門控告者,上司官應(yīng)將原告發(fā)還,聽其在州縣官衙門告理,仍治以越訴之罪。州縣官不受理或?qū)彅嗖还撸孟蚋拦倏馗妫从筛拦俾爺鄽w結(jié)。“重情”業(yè)經(jīng)州縣衙門控理,如有冤抑審斷不公,須于狀內(nèi)將控過州縣衙門及其審過情節(jié)注明,上司官方得受理。若府道官仍不準(zhǔn)理或批斷失當(dāng),方可赴撫按告理。按察司及督撫衙門仍不準(zhǔn)理或判斷失當(dāng),又或未經(jīng)在督撫處控告而所控案情重大,事屬有據(jù)者,方可赴京控訴(即“京控”)。違反上述程序者,均按越訴治罪。 由于清代的州縣衙門并不存在今天地方政府的職能分工和設(shè)置,州縣享有全權(quán),州縣受理案件就不似今天的司法機(jī)關(guān)在制度上的職能分工管轄。州縣受理案件不以民刑之分來決定是否受理,所有案件都?xì)w州縣受理(14)。因此民刑之分在法律上的差別以及訴訟介入的機(jī)構(gòu)分類問題和程序差別問題在清代的州縣并無太大的意義。不僅如此,清代州縣在判斷案件性質(zhì)上有相當(dāng)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這種自由裁量權(quán)既來自于清代在立法上的特點(diǎn),也來自于清代州縣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即州縣得到皇帝的充分授權(quán),以全權(quán)的職責(zé)管理地方的全部政務(wù),而州縣的這種全權(quán)意味著他不僅僅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官,而且扮演著類似現(xiàn)代檢察官、政府官員、甚至立法者的多重角色,實(shí)質(zhì)上州縣就是父母官。父母官的角色決定了州縣在審斷中的全權(quán)和對(duì)糾紛的態(tài)度以及對(duì)案件分類的自由裁量和對(duì)案件處理的自由裁量。無論是案件的分類還是處理方法,州縣所依據(jù)的都是案件本身的輕重而不是現(xiàn)代法律所謂的民刑。因?yàn)閷?duì)地方的政務(wù)而言,所謂的民事案件并不一定于地方治安干系不大,而所謂的刑事案件盡管法律的處刑很重,卻并不必然于地方治安和社會(huì)管理關(guān)系就大。因此,清代州縣對(duì)民間細(xì)故案件也多付諸相當(dāng)?shù)木Α?如州縣在審斷某些重情案件時(shí)并未依律處以刑罰而往往以細(xì)故的方式了結(jié)糾紛,如果以民刑而論,刑事案件以民事方式結(jié)案是不可思議的,但由于重情與細(xì)故的區(qū)分僅在于州縣主觀上對(duì)案件的輕重把握,而非民刑之間的嚴(yán)格區(qū)分,加之州縣在此環(huán)節(jié)上的自由裁量權(quán),故而州縣在案件是按細(xì)故或重情處理的問題上有較大的自主性,便可獲得制度上的解釋。 如,光緒二十三年事涉敬大靜與敬存喜同胞弟兄一案。哥哥敬存喜與已成寡婦的嫡堂嫂敬劉氏通奸。得知?jiǎng)⑹嫌募匏耍创嫦矟撝羷⑹吓P室,執(zhí)持切刀,自行抹喉身死。胞弟敬大靜得知哥哥死訊后具報(bào)至州縣。五月初三州縣訊斷堂諭:“敬存喜既系戀奸滋事,畏罪自抹身死,與人無尤。著當(dāng)堂各結(jié)完案。此判。”(15) 此案所涉“犯奸”歷來被視為重情,《大清律例》“犯奸”條規(guī)定:
①此類論著有李志敏:《中國古代民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葉孝信:《中國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孔慶明等:《中國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朝陽:《中國古代訴訟法》,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7年版;蒲堅(jiān):《中國古代行政立法》,北京大學(xué)2007年版;李交發(fā):《中國訴訟法史》,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張世明:《中國經(jīng)濟(jì)法歷史淵源原論》,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此類論文更不計(jì)其數(shù),故不贅舉。 ②羅志田教授就曾在《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一文中指出對(duì)歷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問題。他認(rèn)為,這樣“倒放電影”雖有助于史家認(rèn)識(shí)往昔,但也有副作用,即無意中可能會(huì)剪輯掉一些看上去與結(jié)局關(guān)系不大的枝節(jié),而且還容易導(dǎo)致以今情測古意,即有意無意中以后起的觀念和價(jià)值尺度去評(píng)說和判斷昔人,結(jié)果往往是得出超越于時(shí)代的判斷和脫離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氐慕Y(jié)論。參見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1999年第4期;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xué)十論》,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259頁。 ③持此論者如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tǒng)與近代轉(zhuǎn)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法律史學(xué)界對(duì)中國傳統(tǒng)法律存在形式原有概括為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后逐漸修正為諸法并存,民刑有分,但無論結(jié)論如何變化,其所依據(jù)的對(duì)中國法律史的認(rèn)識(shí)都是建立在以西方概念“套用”中國史實(shí)的基礎(chǔ)之上的。 ④持此論者如徐朝陽:《中國古代訴訟法》,商務(wù)印書館1927年版。他論述中國所謂刑事訴訟法的歷史時(shí)就論述到:“訴訟之區(qū)別刑事、民事,本各國最早通行之思想,于我國古代蓋有微征……。因《鄭注》有云:訟謂以財(cái)貨相告,刑謂相告以罪名者,可知民事與刑事訴訟,在古代之司法機(jī)關(guān),已有劃然之區(qū)分”。 ⑤大陸法系的六法體系就是由憲法為根本法,民法為支柱,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為基本法律的成文法體系。 ⑥重情與細(xì)故并未形成明文的制度規(guī)范。在《大清律例》中有“重情”和“細(xì)事”概念,在大量的官箴書中,對(duì)重情和細(xì)故的區(qū)分較為常見。本文界定重情和細(xì)故不在于說明清代有著兩類完全不同的法律體系(事實(shí)上二者的區(qū)分往往在州縣的自我把握之中),而是為了與現(xiàn)代民刑之分進(jìn)行比較研究。 ⑦《大清律例》,“告狀不受理”。 ⑧法史學(xué)界多以六法體系的嚴(yán)格劃分作為判斷法律文明的標(biāo)志,由此據(jù)以民刑不分作為抨擊清代法律制度“落后”的論據(jù)。 ⑨《大清律例》,卷三○;《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八一七。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本。 ⑩《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卷七五○,《吏部處分例》,“應(yīng)奏不奏條”。 (11)《大清會(huì)典》,卷五五。 (12)劉衡:《州縣須知一卷》(附居官一卷),宦海指南本。 (13)《大清律例》,“越訴”。 (14)旗人、軍人等特殊管轄的情況除外,參見那思陸:《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 (15)“為計(jì)開敬大靜具報(bào)伊胞兄被敬大友等砍傷身死案內(nèi)人證候訊事”;光緒二十三年,目錄號(hào)13,案卷號(hào)636,南部縣正堂清全宗檔案,四川省南充市檔案館。 (16)薛允升著、黃靜嘉校編:《讀例存疑重刊本》(五),臺(tái)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88頁。據(jù)薛允升注:此條例為“前明舊例”。 (17)里贊:《晚清州縣訴訟中的審斷問題:側(cè)重南部縣的實(shí)踐》,四川大學(xué)2007屆博士論文,“斷不依律部分”。
學(xué)報(bào).jpg)
電技術(shù).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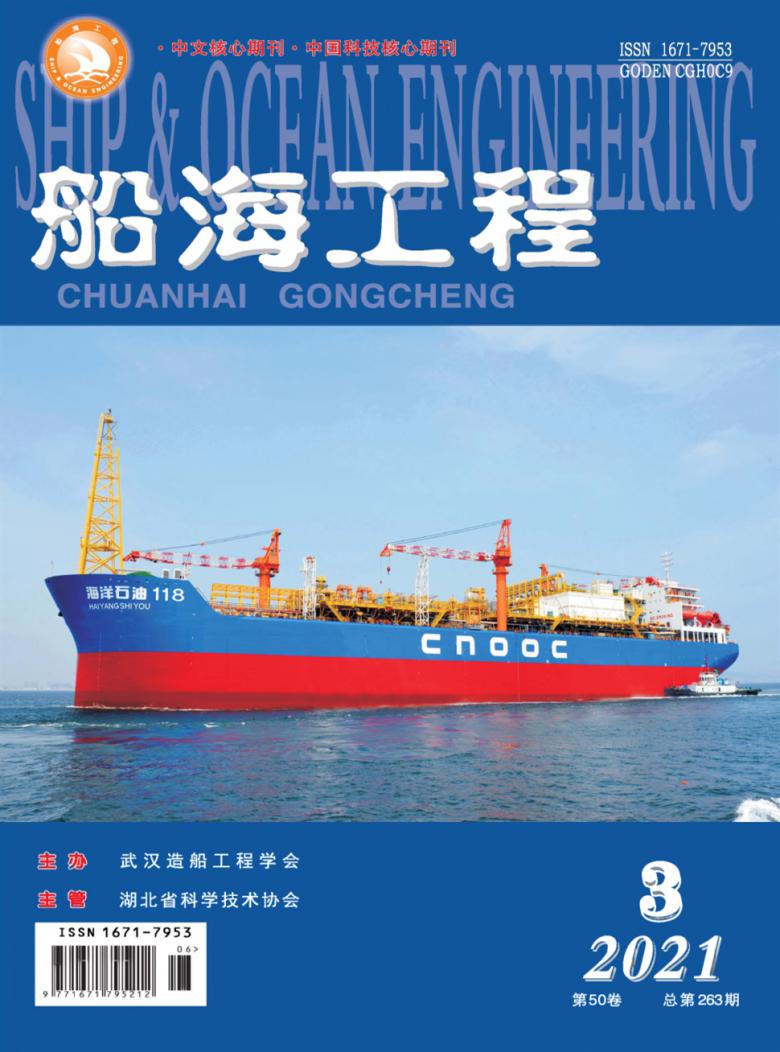
學(xué)影像學(xué).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