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事訴訟中的身份等級與賦役制度:以道光涇縣李氏主仆官司為中心
李甜
近年來學(xué)界對于民間文獻(xiàn)的發(fā)掘可謂不遺余力,徽州文書、巴縣檔案、淡新檔案、黃巖訴訟檔案等一批基層資料的相繼出版給中國法制史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線索,有利于揭示傳統(tǒng)社會的訴訟機(jī)制和法律關(guān)系之演變。其中以皖南佃仆制研究為典型,自1990年代以降逐漸突破了單一的土地關(guān)系視角,從法律身份、家庭關(guān)系、民間糾紛等角度出發(fā),展現(xiàn)紛繁復(fù)雜的歷史內(nèi)涵。不過,傳統(tǒng)研究偏重于法律史和制度史的狀況雖有所改觀,但結(jié)合社會史和法制史的研究仍有待于深入發(fā)掘和細(xì)化分析。由于案情差異所導(dǎo)致的文本存量不同,學(xué)者往往注意刑事案件等熱點(diǎn),對“田土細(xì)故”之類的民事訴訟關(guān)注得不夠。然而,這些平淡的文獻(xiàn)也會蘊(yùn)含獨(dú)特的價值,尤其當(dāng)法律關(guān)系與身份等級相互纏繞時,更有著特殊的意義。 雍正開豁世仆令的頒布,是清代社會身份等級變遷的重要節(jié)點(diǎn)。國家政策的松動,將身份等級推上改革前臺,在此起彼伏的主仆訴訟案中,各利益群體的斗爭趨于白熱化,身份流動出現(xiàn)新的情形。傳統(tǒng)研究大都傾向于關(guān)注國家政策在地方社會的實(shí)施,相對而言容易忽略地方社會和地方政府的主體性。實(shí)際上,除建立法律制度的歷史連貫性之外,有必要將具體事件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予以考察,以更細(xì)膩的個案來思考以下議題,諸如:作為裁判的地方政府,對民間習(xí)慣的認(rèn)可程度,審判時是否有自身的意圖;身份重塑的過程與方式因時而異,其中的區(qū)域、時代差異如何演變。筆者在前期研究中利用新發(fā)掘的安徽寧國府鄉(xiāng)土文獻(xiàn),勾勒出“寧國世仆”這一賤民群體的歷史脈絡(luò)及其生活實(shí)態(tài),初步分析雍正開豁令頒布以來寧國世仆的出戶歷程,并將寧國世仆與徽州伴當(dāng)作了比較。本文從地方文獻(xiàn)與宮藏檔案出發(fā),結(jié)合社會史和法制史的分析視角,以寧國府涇縣南容李氏主仆訴訟案為討論對象,揭示該案對理解清代官方審理機(jī)制和傳統(tǒng)社會身份制度變遷的普遍意義。 一、道光涇縣南容李氏主仆訴訟案始末 道光十七年(1837年)末的臘月十八日,黃山余脈下的涇縣永定都一圖十甲生員李廷棟與李和中等幾位有功名的南容李氏族人署名遞交訴狀,將居住在永定都荀村坑的李蘭生等人告上縣衙。據(jù)說其祖李春輝購買的世仆李珠寶,在雍正六年(1728年)志欲出戶,被安徽巡撫批駁“已受豢養(yǎng)之仆例不出戶”,立有歸戶甘結(jié)文書。被告李蘭生一族系李珠寶后裔,當(dāng)年保舉李蘭生捐納九品職銜,又花重金賄賂十二都二圖一甲戶首李大位,將該族九十三戶在永寧都八甲的糧稅改撥,試圖出戶,強(qiáng)烈要求官府予以處置。 1.一審階段(道光十七年十二月至十八年四月) 訴狀遞交五天后的二十三日,涇縣知縣正式受理,命令茹麻巡檢司調(diào)查。巡檢司林坤于春節(jié)休假后傳訊兩造人等,被告拒不到場。原告稱發(fā)現(xiàn)轉(zhuǎn)投行為后,“鳴鄉(xiāng)黨公正論處”,但被告和受賄戶首避不出面,地方鄉(xiāng)約、宗族無法調(diào)解。此外,林坤于道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收到監(jiān)生潘報頌等人稟文,以鄉(xiāng)鄰身份證明被告李蘭生等是李氏世仆,現(xiàn)尚在服役。三月初三日,林坤將稟文轉(zhuǎn)呈知縣,在報告中認(rèn)為此案事關(guān)重大,涉及控告世仆冒捐一事。 知縣于三月初九日出具傳票,勒令原被雙方、戶首、中證等人赴縣接受質(zhì)訊。各方接到傳訊后皆有反應(yīng),其中以中證潘報頌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最大。他表示與原告“曾未謀面”,前份呈文乃系“盜名稟覆”。并進(jìn)一步指出,其族監(jiān)生潘百祥和周邊的吳、翟等大姓,都與被告結(jié)為姻親。差相同時,被告也呈文稱,始祖李祿和是涇縣十二都頃田李洧源的元孫,明代萬歷間“掛居”永定都荀村坑,與頃田李氏同宗共譜,有自置田宅、墳山和宗譜,附有頃田李含長和姻親們的甘結(jié)為證。同時指責(zé)原告借口修祠勒索白銀,未得逞而懷恨在心,將世仆之名張冠李戴以陷害,并盜名捏造稟文誆騙官方。 被告使用“掛居”而非“定居”,引起原告的警惕,隨即于四月初八日稟文,詳細(xì)介紹被告與永寧都的關(guān)系,希望調(diào)查永寧都納稅科冊。知縣于四月十三日再次出具差票,以措辭嚴(yán)厲的口氣要求差役協(xié)同約保提拘被告和中證。四月下旬開審,原告稱被告私買頃田李含長的宗譜,冒稱李祿和支派,把戶糧撥歸十二都一甲輸差。被告的口供則完全不同,稱祖上原住永定都,因永寧都買有產(chǎn)業(yè)而“輪充鄉(xiāng)約當(dāng)差”,查知祖籍在十二都而撥歸輸差,這得到其姻親們的佐證。不過李含長卻顯得底氣不足:“因年代久遠(yuǎn),并不曉得。” 對比原被雙方和中證的口供可知,導(dǎo)火索是被告改撥糧稅并冒稱頃田李氏支派,由于納稅科冊無法核對,宗譜成為本案的關(guān)鍵證據(jù)。知縣查閱后發(fā)現(xiàn),李祿和乃絕支,乾、嘉間兩次修譜都沒有記載,是為冒認(rèn)無疑。不過,他認(rèn)為雍正控案甘結(jié)不能作為世仆證據(jù),何況與被告聯(lián)姻的均為大族。從納稅平衡角度來說,永寧都八甲戶口不多,若允許被告撥入十二都,則差務(wù)難以支撐,斷令被告撥回輸差。該判決對原告有利,挫敗了被告的意圖。 2.二審階段(道光十八年五月至十九年十一月) 受賄戶首稱,被告錢糧冊已經(jīng)辦齊并造冊,懇求寬限到九月份。原告害怕他們翻供反悔,建議暫扣被告李蘭生的宗譜和監(jiān)照,待撥歸原甲后發(fā)還。這為李蘭生的纏訟埋下伏筆,案情隨即進(jìn)入第二階段。 五月十八日,李蘭生先后赴寧國府和安徽布政使上控,認(rèn)為南容李氏嘉慶間并未修譜,知縣斷案并無實(shí)據(jù),并舉報縣差嚇詐之事。道光十九年,李蘭生將稟文略加刪改后投給安徽巡撫,終于獲得有利的批示:七月初四日批文稱,李蘭生質(zhì)疑宗’譜的證據(jù)不足,書差嚇詐亦是危言聳聽,但“李蘭生等因何必欲撥入十二都,其中有何規(guī)避”值得注意,要求屬下查明。 寧國知府正式受理此案,下文要求涇縣令匯報審理情況,并查明永寧都各甲差役和被告轉(zhuǎn)撥之因。在被告轉(zhuǎn)撥糧稅時,同甲徐成章一族也在轉(zhuǎn)撥,八甲即將淪為空甲,這引起了永寧都其他九個甲的恐慌,上控要求將被告“押歸原都”應(yīng)役。對于這橫出一招,李蘭生、徐成章兩族聯(lián)手“出貼費(fèi)用”,雙方達(dá)成的補(bǔ)償協(xié)議于十一月十三日遞給官府。知府訊問時,被告終于吐露實(shí)情,轉(zhuǎn)撥糧稅“實(shí)系規(guī)避仆戶之名”。知府隨即認(rèn)定被告的良民身份,但禁止冒稱南容李氏,同時批駁了原告的要求。從賦役和情理的角度考慮,被告久經(jīng)遷居永定都,不便隔都應(yīng)差納糧,且為免除仆戶名目,斷令將田產(chǎn)改撥永定都。順利銷案。
二、法律運(yùn)作過程中的訴訟與承審 1.訴訟雙方的策略及其差異 原告最初占據(jù)主動權(quán),向官府出示雍正間的控案文約,及時稟報清明掃墓受世仆抵制之事,爭取到官方的同情。并且抓住被告“不敢直稱世居永寧,而詭稱掛居永定”的表達(dá)漏洞,占據(jù)道德高地指責(zé)被告為逃避勞役而不認(rèn)嫡祖。然而,原告?zhèn)卧旆A文讓被告抓到口實(shí),一定程度上削弱其信度,且沒有否認(rèn)被告“勒索生銀百兩”的指控。最糟糕的在于并未掌握賣身服役文契,無法證明被告一定屬于本族世仆。被告也坦言:“李和中們也沒指說監(jiān)生們?yōu)樗易嫔掀腿撕笠岬氖隆!笨梢姡诮?jīng)濟(jì)上早已獨(dú)立。 被告的訴訟反應(yīng)慢了一拍,但反擊力度較大。其一是請潘報頌呈文澄清,以示原告之欺瞞官長;其二劃清與世仆李珠寶的界限,認(rèn)為“因姓與生同,遂指鹿為馬”;其三指責(zé)原告動機(jī)險惡,“舊藉七李修祠為題,勒索生銀百兩”,敲詐未遂而上控。與此同時動用了大量人際關(guān)系,姻親翟端本、潘百祥、吳世堯、吳汝器、王繼成、查元慶等紛紛呈送甘結(jié),他們都是“列宮庠”、“有宦業(yè)”、“授職銜”的士紳,其中潘氏甚至與河道總督潘錫恩同宗。這對官方判斷起到的引導(dǎo)作用,涇縣令稱:“查卑縣潘、吳、翟、王、查各姓,均系大族,既與聯(lián)姻,自無身家不清之事。”安徽巡撫也說:“爾等果與大族聯(lián)姻,自非身家不清。” 被告不服知縣判決,向?qū)巼暝V未果,轉(zhuǎn)而上控至安徽布政使,杜撰出“蠹差章錦、章文升、朱宣、趙林等公然嚇詐生錢”之事。后來在供詞中承認(rèn):“監(jiān)生們情急,就添砌差役嚇詐的話,希圖聳準(zhǔn),作詞到藩憲衙門呈控……監(jiān)生們上控詞內(nèi)所稱差役串啉勒詐的話,實(shí)是圖準(zhǔn)添砌的。”其目的即在于引起官方重視,其中可能有訟師參與謀劃。名吏汪輝祖有“無慌不成狀”之說,寺田浩明曾專門探討此現(xiàn)象,訴訟當(dāng)事人經(jīng)常將輕微糾紛捏稱為重大案情,以期引起承審官員的重視。滋賀秀三也認(rèn)為官方對民間詞訟的制度設(shè)計上本身具有缺陷,為“纏訟”提供了客觀條件。當(dāng)然,這也為消解民怨提供回旋的余地,某種意義上體現(xiàn)民眾的權(quán)利意識。 考慮到傳統(tǒng)社會中人際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偽造鄰右和中證供詞的門檻甚低,在本案審理時僅僅當(dāng)作輔助性證據(jù),斷案的主要依據(jù)是宗譜和賦役。原告上訴時偽造供詞的手段,一定程度上顯示其訴訟水平之低級。與之相對的是,被告動員了大量的人脈,似乎還邀訟師參與其中,顯得有張有弛,應(yīng)該對祖先的訴訟遺產(chǎn)作過總結(jié)。



學(xué)報.jpg)
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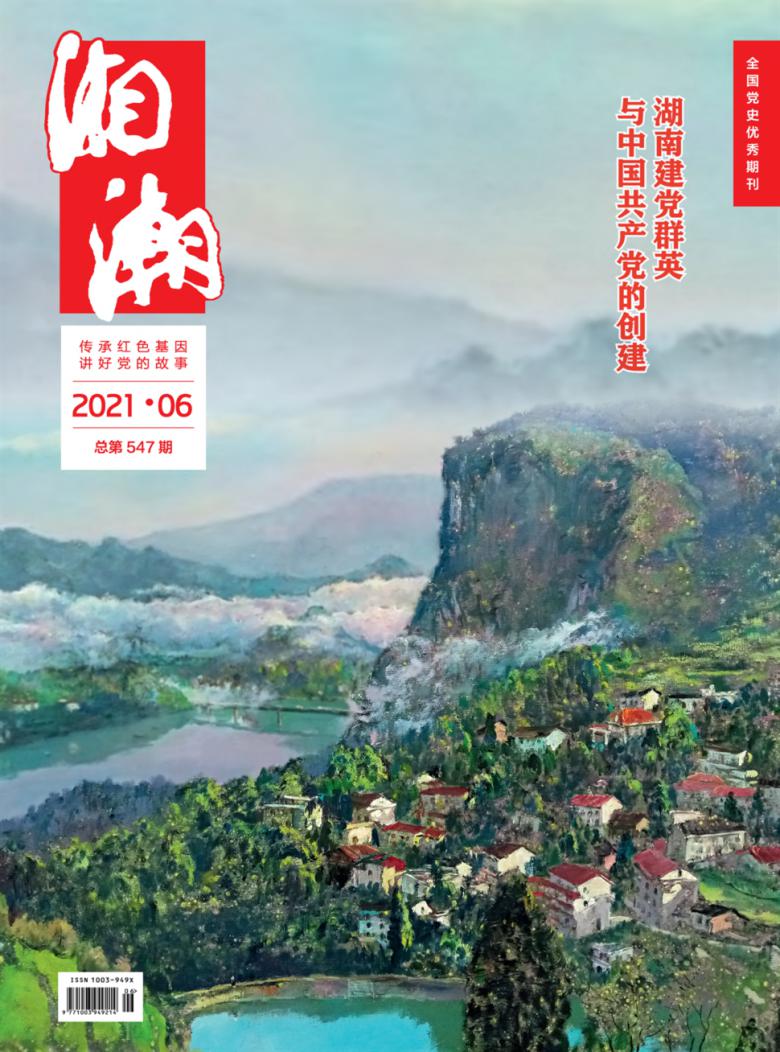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