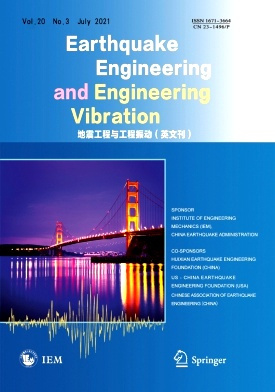宋代戶絕立嗣與遺囑繼承
李錫厚
根據中國古代的父權制度,通常情況下,只有男子有繼承權,女子則被排除在繼承之外,因此,只要是戶下沒有兒孫,即謂“戶絕”。在宋代,已絕之家通過立嗣和遺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處置遺產。遺囑權利“是私有權最終的體現”[1]。隨著私有制的發展,個人對財產任意處置的權利正在不斷擴大。但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立嗣與繼承也如同田宅買賣一樣,要受強大的宗族關系制約[2]。
為已絕之家確立繼承人,直接關系到遺產繼承,為避免由此引發爭端,宋代法律明確規定了立嗣的主體,“在法:立嗣合從祖父母、父母之命,若一家盡絕,則從親族尊長之意”[3]。同為立嗣,由于主體不同,性質也迥然不同。“如生前未嘗養,夫妻俱亡,而近親與之立議者,即名繼絕;若夫妻雖亡,祖父母、父母見在而養孫,或夫亡妻在而養子,終不入繼絕之色”[4]。繼絕又稱為“命繼”;祖父母、父母見在而養孫,或夫亡妻在而養子,均不為“繼絕”,而稱為“立繼”。在立嗣問題上,如夫亡妻在,立嗣決定權歸妻,夫妻俱亡時,立嗣權才輪到祖父母、父母;只有當一家盡絕的情況下,才由近親尊長為之立嗣。這一順序,實際上是根據絕家遺產繼承順序確定的:無子則妻為第一繼承人,其次是父母、祖父母,再次才是近親。“竊詳法意,謂夫妻俱亡,由祖父母、父母立孫,無祖父母、父母,由近親奠長命繼。若夫亡妻在,自從其妻,雖祖父母、父母亦焉得而遣之,而況於近親尊長,如叔伯兄者乎?所以如此者無他,在法:諸分財產,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無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財產,妻之財產也。立子而付之財產,妻宜得而與之,豈近親他人所得而可否之乎?”[5]夫亡妻在,妻承夫分,在這種特定情況下,法律承認妻有繼承權。
妻在夫亡之后取得財產權,其具體體現就是她有決定立嗣的權利。立嗣,首先應當選擇“同宗昭穆相當為子孫”,但也可以收養異姓三歲以下小兒為親子。法律規定:“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為子孫,此法也。諸以子孫與人,若遺棄,雖異姓三歲以下收養,即從其姓,聽收養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亦法也。既曰無子孫者,養同宗為子孫,是非同宗不當立矣。而又一條曰雖異姓,聽收養,依親子法者,何也?國家不重於絕人之義也。如必曰養同宗,而不開立異姓之門,則同宗或無子孫少立,或雖有而不堪承嗣,或堪承嗣,而養子之家與所生父母不咸,非彼不愿,則此不欲,雖強之,無恩義.則為之奈何?是以又開此門,許立異姓耳。”“在法:無子孫,養同宗昭穆相當者,其生前所養,須小於所養父之年齒,此隆興敕也。敕令所看詳,則為母所養者,年齒亦合小於所養之母。”[6]寡妻可以收養同宗昭穆相當者為子,而且年齒應小于所養之母。這樣,她就可以立幼子,從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掌管財產。為此,她還可以不立本宗而收養異姓三歲以下小兒。這些規定,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寡妻不至于很快喪失財產權,實際上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絕家死后遺產不會立即被他人侵吞。
關于收養異姓子,唐代有嚴格限制,《唐律疏議》卷十二《戶婚律》:“即養異姓男者,徒一年;與者笞五十。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聽收養,即從其姓。”[7]“疏議”曰:“其小兒年三歲以下,本生父母遺棄,若不聽收養,即性命將絕,故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很明顯,在唐代,法律原則上是禁止收養異姓的;允許收養三歲以下棄兒,并不是從收養者的需要出發,而完全是為被收養者考慮,與宋代慮及戶絕養子者完全不同。
宋代對于立異姓為后者,一般情況下,即使并非遺棄,也不究治,甚至對即成事實予以認可。“邢林、邢柟為親兄弟,邢林無子,邢柟雖有二子,不愿立為林後,乃於兄死之日,即奉其母吳氏、嫂周氏命,立祖母蔡氏之侄為林嗣,今日邢堅是也。夫養蔡之子,為邢之後,固非法意,但當時既出於堅之祖母吳氏及其母周氏之本心,邢柟又親命之,是自違法而立之,非堅之罪也。使邢柟宗族有知義者,以為非法,力爭於邢柟方立之時,則可;今欲轉移於既立八年之後,則不可。力爭於吳氏、周氏未死之時,則可;今欲遣逐於吳氏、周氏方死之後,則不可。”[8]
法律之所以要嚴格區分“立繼”與“命繼”,是因為二者繼承分額各不相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戶婚門·命繼與立繼不同》載:
撿照淳熙指揮內臣僚奏請,謂案祖宗之法:立繼者謂夫亡而妻在,其絕則其立也 當從其妻;命繼者謂夫妻俱亡,則其命也當惟近親尊長。立繼者與子承父分法同,當 盡舉其產以與之;命繼者於諸無在室、歸宗諸女,止得家財三分之一。又準戶令:諸 已絕之家立繼絕子孫謂近親尊長命繼者,於絕家財產者,若止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戶 四分之一給之,若又有歸宗諸女,給五分之一。止有歸宗諸女,依戶絕法給外,即以 其余減半給之,余沒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戶三分為率,以二分與出嫁諸女均 給,馀一分役官。
“命繼”者只能獲得所繼之人的部分遺產,立繼者卻不限多少,只要死者留有遺囑,皆聽承受。這是“遺囑舊法”即《嘉祐遺囑法》明確規定的。后來“獻利之臣”混淆命繼與立繼的區別,剝奪立繼子孫應得的財產份額,是違背《嘉祐遺囑法》的。《長編》卷三八三元祐元年七月丁丑載: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以天下之可哀者莫如老而無子孫之托,故王者仁于其所 求而厚于其所施,此遺囑舊法所以財產無多少之限,皆聽其與也。或同宗之戚,或異 姓之親,為其能篤情義于孤老,所以財產無多少之限,皆聽其受也,因而有取所不忍 焉。然其后獻利之臣不原此意而立為限法,人情莫不傷之。不滿三百貫文始容全給,不滿一千貫給三百貫,一千貫以上給三分之一而已。國家以四海之大、九州之富,顧豈取乎此?徒立法者累朝廷之仁爾。伏望圣慈,特令復《嘉祐遺囑法》以慰天下孤老者之心,以勸天下養孤老者之意而厚民風焉。如開納乞先次施行。”從之。
這就是說,自元祐元年(1086)七月以后,恢復執行《嘉祐遺囑法》,戶絕之家為養孤老于生前所立繼承人,根據遺囑應當依法獲得其全部財產。至于命繼者的繼承問題,也有很大爭議,有人甚至主張命繼完全不能繼承所繼之家的財產,“(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江南東路提刑司言:本司見有人戶陳訴,戶絕立繼之子不合給所繼之家財產。本司看詳戶絕之家依法既許命繼,卻使所繼之人并不得所生所養之家財產,情實可矜。欲乞將已絕命繼之人于所繼之家財產視出嫁女等法量許分給。戶部看詳,欲依本司所申,如系已絕之家,有依條合行立繼之人,其財產依戶絕出嫁女法三分給一至三千貫止,余依見行條法。從之”[9]。
有“恩養子孫承代”或立下遺囑由近親繼承,皆不能謂為“戶絕”,“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絶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絶戸,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余勿干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10]
由于戶絕財產可以部分沒官,因此,官府對絕家立嗣問題多實行干預。“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父褒故太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后齊有子而褒絶,請復本宗,禮官以請許之。紹圣元年尚書省言,元祐南郊赦文,戶絶之家近親不為立繼者,官為施行。今戸絶家許近親尊長命繼巳有著令,即不當官為施行。”[11]“官為施行”即官為立繼。不過這種作法與近親尊長命繼的規定必然發生沖突,所以,紹圣四年(1097)十二月乙酉又“詔元祐赦文,戶絶之家官為立繼指揮勿行”[12]。官府對立嗣的干預,除了“官為施行”之外,還通過戶籍制度實施干預。收養或命繼,都要脫離原來的戶籍,附于所繼之家的戶籍,稱為“除附”。
唐宋時期,戶絕財產可以遺囑處分。法律明確規定:“唐制凡身喪戶絶者,所有奴婢、部曲、貲財、店宅,并令近親代營葬事及功徳外,余并還女,無女均屬近親,官為檢校。亡人在日有遺囑處分明白者,不用此律。”[13]這說明遺囑是被法律承認的,可以按照死者于生前所立遺囑處分遺產。法律的有關規定只是在死者生前無遺囑的情況下,才可以執行。
唐宋時代財產繼承,如有子數人,采取諸子均分制,不及出嫁女。南宋寧宗嘉定間,“呂文定、呂文先兄弟兩人,父母服闋,已行均分”[14]。這說明,宋代在財產繼承問題上,嫡長子已無特權可言。據《宋刑統》所引唐朝《戶令》:“諸應分田宅者及財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寡妻妾無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壹子之分。”[15]
宋制則明確限定,在室女只能獲得全部財產的1/2,較唐制“戶絕財產,營葬事及功徳外,余并還女”的規定,在室女所得減少一半。而且在處分戶絕財產的實際過程中,官吏還往往不擇手段地進一步侵吞死者女兒的利益。曾士殊有女曾二姑,“其曾士殊一分家業,照條合以一半給曾二姑。今僉廳及推官所擬,乃止給三分之一,殊未合法”[16]。
寡妻妾無男者承夫分,她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完全享有其夫的財產權;“若夫兄弟皆亡,同壹子之分”,是說如果她丈夫的弟兄都已亡故,但財產仍未分析,不論各支有子若干,則諸子均分,在這種情況下,她只能取得“壹子之分”。也就是說,她只能與諸侄均分,而不是“承夫分”了,只能繼承其夫應得的部分財產權。南宋孝宗時袁采論及諸子均分說:“有諸父俱亡作諸子均分而無兄弟者分后獨昌、多兄弟者分后浸微者;有多兄弟之人不愿作諸子均分而兄弟各自昌盛,勝于獨據全分者;有以兄弟累眾而己累獨少,力求分析而分后浸微,反不若累眾之人昌盛如故者。”[17]這里所說的“多兄弟”和“無兄弟”者,是指第三代的情況。因此,按照寡婦“同壹子之分”的規定,她享有的已不再是其夫的權利,而是如其有一子應享的權利。
權利與義務一致,諸子均分,在均分財產的同時,對賦稅負擔也實行均分,因此“均分”受到官府的關注和支持。《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戶婚門·繆漸三戶訴祖產業》載:
繆昭生三子,長曰漸,次曰煥,幼曰洪。繆昭既死,而以長子漸立戶,是繆漸即 繆昭之都戶。今繆漸兄弟俱亡,其子孫析而為七,各有戶名,而祖繆漸猶未倒除,逐 年官物互相推托,虧陷已多。保長具申,追到供對,各已招伏,認將繆漸稅錢均作三 分,人戶送納,已得其直。內一分繆友皋,狀訴祖戶稅錢雖均為三,祖戶田業各自占 據,未曾分析,既是分稅,亦合均田。今勒令繆友皋供出繆漸戶田產,并有號段,倘 果是實,豈有不行均分之理。
這說明均稅與“均田”是緊密相聯系的,均分產業是均攤賦稅的基礎。
“諸子均分”就是當時通行的遺產繼承制度,但不及諸女,依照宋朝法律,“已嫁承分無明條,未嫁均給有定法,諸分財產,未娶者與聘財,姑妹妹有室及歸宗者給嫁資,未及嫁者則別給財產,不得過嫁資之數”[18]。但如果該戶下全無兒孫而只有諸女,即為“戶絕”,在這種情況下,女兒則可以獲得父母遺產較多分額,甚至可以依據遺囑獲得全部,法律有對女兒更有利的規定:“諸戶絕財產盡給在堂諸女,歸宗者減半。”[19]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七月“詳定戶絕條貫”又進一步明確規定了戶絕之人財產的處分辦法:
審刑院言:詳定戶絕條貫,今后戶絕之家,如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將資財、莊 宅物色除殯葬、營齋外,三分與一分;如無出嫁女,即給與出嫁親姑、姊妹、侄一 分,余二分;若亡人在日親屬及入舍婿、義男、隨母男等自來同居營業佃蒔,至戶絕 人身亡及三年已上者,二分店宅、財物、莊田并給為主。如無出嫁姑、姊妹、侄,并 全與同居之人。若同居未及三年及戶絕之人孑然無同居者,并納官,莊田依令文均與 近親,如無近親,即均與從來佃蒔或分種之人,承稅為主。若亡人遺囑主證驗分明, 依遺囑施行。從之。[20]
依照這一規定,戶絕財產除殯葬及營齋外,應分成三分:其中一份歸女兒,如無出嫁女,則將這一分給與出嫁親姑、姊妹、侄。余下的二分給與同居者,包括入舍婿、義男、隨母男等,條件是同居時間必須達三年以上。如果無出嫁女,甚至連出嫁姑、姊妹、侄也沒有,那么上述同居者就可以獲得全部遺產。如無同居者,則莊田均給近親;如無近親,則均與佃種之人。但是“若亡人遺囑主證驗分明,依遺囑施行”,這也就是說,戶絕之人有充分權力自由處分其遺產,他完全可以不受上述分配比例的限制,既可以多給甚至全給出嫁女,也可以少給甚至不給。這說明,身為戶絕的財產擁有者,有充分權利通過遺囑處分自己的財產。“父母產業,父母支撥,為人子者,孰得而違之”[21]。如果戶絕之人依遺囑處分其財產,其繼承人是無權干預的。
哲宗元祐元年(1086)七月二十二日,臣僚上言:“遺囑舊法財產無多少之限,請復嘉祐敕,財產別無有分骨肉,系本宗,不以有服及異姓有服親,并聽遺囑,以勸天下養孤老之意,從之。”[22]這說明,嘉祐間(1056-1063)一段時間內,曾規定戶絕財產不限多少,都可以遺囑處分。戶絕立繼者,必須經遺囑才能繼承所繼之人的財產。“陽夢龍繼八二秀,祖命也,陽攀鱗繼八五秀,父之命與祖母之命也,亦既歷年多矣,親書遺囑,經官給據,班班可考,質之房長,并無異詞。”[23]
戶絕之人不僅可以立遺囑將全部財產給與在室女,甚至也可以遺囑給與贅婿。但宋代有關遺囑繼承的法律,仍不夠明確,所以處理有關爭端,往往無定則。《宋會要》六一之六五《食貨·民產雜錄》載: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知涪州趙不倚言:契勘人戶陳訴,戶絕繼養遺囑 所得財產雖各有定制,而所在理斷間或偏于一端,是致詞訟繁劇。且如甲之妻有所出 一女,別無兒男,甲妻既亡,甲再娶,后妻撫養甲之女長成,招進舍贅婿,后來甲患 危為無子遂將應有財產遺囑與贅婿。甲既亡,甲妻卻取甲之的侄為養子,致甲之贅婿 執甲遺囑與手疏與所養子爭論甲之財產。其理斷官司或有斷令所養子承全財產者,或 有斷令贅婿依遺囑管保財產者。
遺囑不僅在戶絕情況下有效,而且即使有法定繼承人——即有子孫繼承的情況下,父祖遺囑對財產繼承也具有一定的效力。“父祖有慮子孫爭訟者,常欲預為遺囑之文而不知風燭不常,因循不決,至于疾病危篤,雖中心尚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死者多矣,況有神識昏亂者乎!”[24]正因為遺囑可以有效地影響繼承,所以遺囑也會有失公正,立遺囑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擾,“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為身后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于悍妻、黠妾,因于后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25]
不僅戶絕之人可以遺囑處分財產,而且有兒孫者也可以立遺囑處分其特權。“士大夫之有任子,此本朝之仁恩至深至渥也。為人祖父者,宜體朝廷之意,均雨露之恩可也。葢鸤鳩之哺子也,旦則自上而下,暮則自下而上,故其均也。今則不然,有所謂父祖遺囑者,亦聴其奏補。且夫奏補自有成法又焉用遺囑乎!愛憎之或偏,則有遺囑;死生之或亂,則有遺囑。故有奪嫡以與庶者,有舍子而立孫者,其至眾也”。[26]
[1] 董家駿:《試論宋代的訴訟法與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關系》,《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 關于田宅買賣受制于宗族關系問題,參閱拙文《宋代私有田宅的親鄰權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9年第1期。
[3]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爭立者不可立》。
[4]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雙立母命之子與同宗之子》。
[5]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雙立母命之子與同宗之子》。
[6]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雙立母命之子與同宗之子》。
[7] 《宋刑統》卷十二《戶婚律》也有相同的規定。
[8]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生前抱養外姓歿後難以搖動》。
[9] 《宋會要》六一之六四《食貨·民產雜錄》。
[10] 《止齋集》卷四四《桂陽軍勸農文》。
[11] 《宋史》卷一二五《禮志》。
[12] 《長編》卷四九三,紹圣四年十二月乙酉。
[13] 《山堂肆考》卷八七載。
[14]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戶婚門·呂文定訴呂賓占據田產》。
[15] 《宋刑統》卷十二。
[16]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戶婚門·侵用已檢校財產論如擅支朝廷封樁物法》。
[17] 《袁氏世范·分業不必計較》。
[18]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立繼有據不為戶絕》。
[19]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立繼有據不為戶絕》。
[20] 《宋會要?食貨》六一之五八《民產雜錄》。
[21]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遺囑與親生女》。
[22] 《宋會要》六一之六一《食貨·民產雜錄》。
[23]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先立已定不當以孽子易之》。
[24] 《袁氏世范·遺囑之文宜預為》。
[25] 《袁氏世范·遺囑公平維后患》。
[26] 《誠齋集》卷六九《論吏部恩澤之敝札子》。
[27]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戶婚門·夫亡而有養子不得謂之戶絕》。
[28] 《宋會要》六一之五八《食貨·民產雜錄》。
[29]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戶婚門·繼母將養老田遺囑與親生女》。
[30]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戶婚門·繼母將養老田遺囑與親生女》。
[31]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戶婚門·從兄盜賣已死弟田業》。
[32]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欺凌孤幼》。
[33]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已有養子不當求立》。
[34]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戶婚門·探鬮立嗣》。
[35]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戶婚門·侄假立叔契昏賴田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