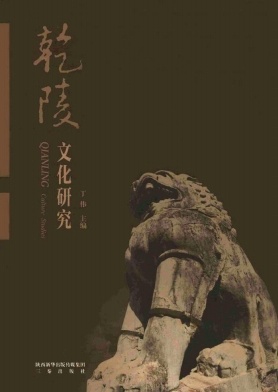宋代伎術官研究
余貴林 張邦煒
宋朝重文輕武,即重用文官,壓抑武將。這恐怕是很難否認的歷史事實。于是,人們產生了這樣一個印象:宋代的知識分子待遇好、地位高。這個印象即使不完全是錯覺,至少也失之于片面。其實,文官與知識分子不能劃等號。當時的知識分子大體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即儒學之士和專門技藝之士。前者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成為享有不少特權的官僚,即文官。作為知識分子,后者無疑比前者更典型,但他們的待遇和地位在宋代卻與前者相差甚遠。長期以來,研究者們對前者論述較多,對后者則缺乏探討。伎術官即是一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專門技藝之士,這里先簡要地介紹一下它的含義、淵源和類型。 “伎術”在古代文獻中又作“技術”或“藝術”。“伎”與“技”同義,都是指才能。而“術”則與“藝”相通,泛指各種各樣的知識、學問和技能,只不過“藝”偏重于社會方面的知識,“術”偏重于自然方面的技能。可見,“伎術”、“藝術”的含義在古代漢語中要比在現代漢語中寬泛。至于伎術官,在宋代則是對“凡執伎以事上者”[1]的統稱,也就是在朝廷任職的專門技藝之士。 天文官、醫官等官職雖然設置甚早,但伎術官之名始于唐代。王溥《唐會要》一書,特地辟有《伎術官》一條。唐代的伎術官供職于秘書省、殿中省、太常寺、左春坊、太仆寺等機構,多半是直接地專門服務于皇室。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十八日,中書省在上疏中說: 和安大夫至醫學,太史令至挈壺正,書藝、圖畫奉御至待詔,為伎術官。[2] 從中可以看出,宋代的伎術官主要包括四類:一醫官,即所謂“和安大夫至醫學”;二天文官,即所謂“太史令至挈壺正;”三書法官、四繪畫官,即所謂“書藝、圖畫奉御至待詔。”《宋史》卷166《職官志六·入內內侍省》稱: 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內侍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伎以事上者皆在焉。 也就是宋代管理伎術官的主要機構是翰林院,其長官為翰林院勾當官,由內侍充任。宋孝宗淳熙年間有此一說:“和安大夫至醫學,春官大夫至挈壺正為伎術官。”[3]只提到醫官、天文官,沒有講到書法官、繪畫官。其原因何在?待考。 本文的重點在于揭示宋代伎術官低下的社會地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利影響。全文分為三篇:上篇對伎術官的地位作縱向考察,證明宋代伎術官的地位明顯低于前代;中篇對宋代伎術官的地位作橫向比較,表明宋代伎術官的地位明顯低于文官武將;下篇介紹宋代伎術官的文化創造活動,說明由于地位低下,因而他們的積極性受到影響,創造性無法發揮。
伎術官的社會地位,總的來說在歷史上經歷了由官高位崇到位卑職賤的變化,但各類伎術官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現分類概述如下。 一、天文官 天文學是我國最為古老的學科之一。天文學的產生同人類社會最初的物質生產緊密相連。《周易·系辭》稱: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 ,“始作八卦”。因此,人們把伏羲氏視為我國天文學的始祖。進入文明時代,特別是在漢武帝采用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理論以后,天文學成為統治階級論證君權神授的理論工具: 占天之法備,則畏天之念興;紀變之書詳,則銷變之政舉。[4] 朝廷設官觀察天文變異,其政治意義遠遠超過經濟意義。“司天之官者,豈輕任哉!”[5]上古時代,天文官由于作用很特殊,因而格外受尊重。此后,天文官的地位經歷了兩次大變化。 第一次是在司馬遷去世前后。唐代學者劉知幾對此曾經加以揭示: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歷象,日月、陰陽管數。司馬遷既沒,后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并以別職來知史務。于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6] 從中可以看出,司馬遷去世以前,天文官與史官合而為一。他們負有依據歷史經驗并按照“上天”旨意,參與政治決策的重要責任,因而位高職崇。司馬遷去世以后,天文官與史官一分為二。中國古代有著“以史為鑒”的傳統,號稱“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 [7]天文官失去了史官之權,因而地位明顯下降。 第二次是在唐宋之際。唐代天文觀察機構比較完善,設有司天監。其建制如下表:[8]
官名 監 少監 丞 主簿 主事 官品 從三品 正四品上 正六品上 正七品上 正八品下 官名 春官正 夏官正 秋官正 冬官正 中官正 副正 官品 正五品上 正六品上 官名 保章正 監候 司歷 官品 從七品上 正八品下 從八品上 官名 靈臺郎 挈壺正 司辰 漏刻博士 官品 正七品下 正八品上 正八品上 從八品下
官名
監
少監
丞
主簿
主事
官品
從三品
正四品上
正六品上
正七品上
正八品下
官名
春官正
夏官正
秋官正
冬官正
中官正
副正
官品
正五品上
正六品上
官名
保章正
監候
司歷
官品
從七品上
正八品下
從八品上
官名
靈臺郎
挈壺正
司辰
漏刻博士
官品
正七品下
正八品上
正八品上
從八品下
可見,唐代司天監的長官雖然不像漢武帝時的太史公那樣位高職顯,但其官品為從三品,同六部尚書(正三品)相差無幾,與御史大夫官品相當,地位仍然相當高。 宋代同唐代一樣,設有司天監(太史局)。除此而外,還設有翰林天文院。宋代天文觀察機構的建制,大致經歷了下面三個階段的變化。 第一階段:從北宋初年到元豐年間。司天監的建制如下表:[9]
官名 監 少監 丞 主簿 官品 從三品 從四品上 正七品上 從七品下 官名 監 少監 五官正 太史令 官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官名
監
少監
丞
主簿
官品
從三品
從四品上
正七品上
從七品下
官名
監
少監
五官正
太史令
官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可見,這一階段天文官建置基本因襲唐制,其官品與唐代相比,也無多大變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實行官制改革,晚唐以來的使職差遣被廣泛運用,促成了官、職、差遣的分離,即所謂“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結果是“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為輕重。”[10]唐代以來的官品到這時,其實際意義已大大減小。 第二階段:元豐官制改革以后。“元豐官制行,罷司天監,立太史局,隸秘書省。”[11]太史局的建制如下表:[12]
官名 太史局令 正 五官正 太史局丞 直長 官品 從七品 正八品 正八品 從八品 從八品
官名
太史局令
正
五官正
太史局丞
直長
官品
從七品
正八品
正八品
從八品
從八品
官名 靈臺郎 保章正 挈壺正 官品 從八品 從九品 正九品
官名
靈臺郎
保章正
挈壺正
官品
從八品
從九品
正九品
這時,“總一局之事”的太史局令,其官品僅為從七品,與太常、國子博士以及監察御史相當。僅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的天文官地位明顯低于唐代。 第三階段:淳熙二年(1175)以后。這年十月,宋孝宗感到天文伎術官官品太低,決定加以調整。他說: 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今太史局官制太輕,自如醫官有大夫數階,太史獨無之,可創大夫階如醫官保安、和安之類,庶幾稍重其事。[13] 春、夏、中、秋、冬五官大夫即是宋孝宗為提高天文官的地位而專門增設,其官品史不見書。但據《慶元條法事類》卷4《職制門》記載,就雜壓而言,五官大夫與醫官和安、成和、成安大夫同屬一等。又據《宋史》卷168《職官志八》記載,醫官和安、成和、成安大夫的官品為從六品。由此可知,五官大夫的官品也不過如此而已。換而言之,這時天文官的官品僅比元祐官品提高一品兩階,仍然比唐代低。 二、醫官 “人之身莫危于病,病之急莫急于藥。” [14]生老病死,人所不免。只要人類存在,就需要醫學,就離不開醫生。中醫科學的來源十分復雜,既有“神農嘗百草”式的科學實踐證明,又有巫覡祭神驅鬼、方士追求長生不老的迷信活動。秦漢魏晉時期,儒生與方士很難區分,儒生往往即是方士,方士常常即是儒生。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單獨為醫學家扁鵲、蒼公立傳,便反映出當時人們對醫生的價值認識以及醫生社會地位之高。 唐代設有太醫署、尚藥局,負責為皇室、貴族、官僚治病。太醫署的建制如下表:[15]
官名 太醫令 太醫丞 醫監 醫正 官品 從七品下 從八品下 從八品下 從九品下 官名 醫博士 助教 官品 正八品上 從九品上 官名 針博士 按摩博士 咒禁博士 官品 正九品上 從九品下 從九品下
官名
太醫令
太醫丞
醫監
醫正
官品
從七品下
從八品下
從八品下
從九品下
官名
醫博士
助教
官品
正八品上
從九品上
官名
針博士
按摩博士
咒禁博士
官品
正九品上
從九品下
從九品下
尚藥局的建制如下表:
官名 奉御 直長 侍御醫 司醫 醫佐 官品 正五品下 正七品上 從六品上 正八品下 正八品下
官名
奉御
直長
侍御醫
司醫
醫佐
官品
正五品下
正七品上
從六品上
正八品下
正八品下
太醫署屬太常寺,其官員的官品不算太高。尚藥局屬殿中省,專掌“天子服御”,與皇帝親近,因而其官品比太醫署官員高兩品四級,與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相當。其地位顯然很高。 宋代設有醫官院,其建制前后變化較多,大體可以劃分為前、后兩期。 前期:政和以前。醫官院設于北宋初年。大約在仁宗時,將有名無實的尚藥局奉御劃歸醫官院。熙寧四年(1071),又將太醫丞并入醫官院。同時,宋神宗把武官東班諸司使副劃為醫官。據《宋史》卷169《職官志九》記載,“其東班翰林以下十九司使、副,雖有見在官及遷轉法,并授技術官。”東班諸司的機構名稱如下表:[16]
皇城翰林 尚食御廚 軍器庫
儀鸞 弓箭庫衣庫 東綾錦院 西綾錦院
東八作 西八作 牛羊香藥庫榷馬
氈毯 鞍庫 酒坊 法酒庫翰林醫官
由于史書對于前期醫官的官品失載,因此無法同唐代進行比較。
后期:政和以后。史稱:“政和既易武階,而醫官亦更定焉。”[17]政和年間改定醫官以后,醫官有十四階。其具體建制如下表:[18]
新官 舊官 官品 和安成和成安大夫軍器庫使從六品 成全大夫軍器庫使正七品 平和大夫西綾錦使正七品 保安大夫榷易使 正七品 翰林良醫翰林醫官使 正七品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 軍器庫副使 從七品 平和郎 西綾錦副使 從七品 保安郎 榷易副使從七品 翰林醫正 翰林醫官副使 從七品
和安大夫從六品,與侍御史相當。其官品雖高于唐代太醫署長官,但是仍低于唐代尚藥局醫官。 上面對于唐、宋兩代天文、醫學伎術官社會地位變遷的考察,僅涉及官品,雖然不盡全面,畢竟可見一斑。馬端臨曾經指出:“自魏以后始有九品之制”,“所以辨高卑之等級。” [19]
三、書法官 書法藝術誕生于東漢魏晉時期,封建王朝設官管理書法藝術的創作和教學則始于隋唐。隋朝在國子寺設書學博士以事書法教導。[20]唐朝是書法藝術發展的黃金時節。唐朝不僅在國子監設書學,而且在科舉考試中以“身、言、書、判”四項標準衡量舉人才干。因此,書法是入仕的必備才藝,它促使所有士人認真學習書法。[21]貞觀元年(627),唐太宗令五品以上命官嗜好書法者,可到弘文館學書,并由著名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教授。[22]唐代社會,由于有較好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條件,促成了書法藝術的大發展。無疑,書法家的社會地位較高,深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敬仰。 宋王朝在許多政府機構中,都配備有書法官,從事抄寫和應奉工作。太平興國年間,宋太宗創設翰林御書院。[23]史稱: 翰林御書院在崇政殿東北橫門外,掌御制御書及供奉筆札、圖籍之事,以內侍三人勾當,御書待詔以同正官充,亦有正官在院祗候者,皆不常置。[24] 宋太宗置院的初衷,是讓這些官員學習和模仿他的字體,替他抄寫詔令,“自是書詔四出,寰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25]這不僅欺騙了百官庶民,而且對他們還能起到見書如見君的威懾作用,有利于政權的鞏固。這種指導思想,使御書院不可能成為促進書法藝術發展的園地。 除御書院外,學士院和御藥院也設有書法官。學士院是替皇帝起草詔令的機構,“國朝初,翰林待詔六人寫書詔。……又有隸書待詔六人,寫簽頭封角。……雍熙四年廢隸書增置翰林待詔十人。”[26]謄寫詔令依然是書法官的職責。御藥院雖是供奉湯藥之所,但“兼受行典禮及貢舉事”,[27]經常向各個部門傳達詔令,[28]需要配備書法官員。建炎四年(1130)六月,宋高宗說御藥院有“書寫崇奉祖宗表詞待詔等八人”。[29]從工作性質看,所有書法官員,不過是皇帝的高級書吏罷了。 翰林待詔等職,本身并無官品可言。周必大說:學士院翰林待詔“與院吏固亦有間,若平居則視之全與吏等。” [30] “與吏等”說明待詔不過是胥吏的代名詞。因此,待詔之名在宋代并不被人看重,甚至成為人們對手工藝人的稱謂。[31]書法官“與吏等”的社會地位,自然無法與唐代書法家相比。這就難怪某些書法官不安心本職工作,要千方百計地換官了。天圣六年(1028),有翰林待詔王明,以“臣元不攻習諸家書體,欲乞比換班行。詔授左班殿直。”[32] 四、繪畫官 繪畫藝術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繪畫藝術因其兼具實用和審美兩大功能而得到發展。宮廷專業畫師大致最早出現在文明社會之初。這是因為宮廷環境需要他們來裝點,宮廷生活需要他們來調劑。 隨著繪畫藝術的發展,宮廷繪畫制度也日趨完善。后蜀在唐代翰林院基礎上,于明德二年(935)首創畫院。接著,南唐中主李璟也設立圖畫院。晚唐五代雖非繪畫藝術的燦爛時代,但社會上形成了學畫的風氣。在當時的中原各地,無論是寺院、民舍,還是高樓大廈、亭臺樓閣,隨處可見繪畫藝術品。正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后蜀和南唐創設畫院,招徠和禮遇畫家。以后蜀為例,畫家黃筌即受到后蜀高祖孟知祥的禮遇,任翰林待詔、權院事,賜紫金魚袋。此后,“士有一技一藝,皆開涉褒賞如筌焉”。[33]明德年間,畫家阮知誨“多寫皇姑帝戚”,更是“渥澤累遷,授翰林待詔、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34]可見,后蜀圖畫院官員地位之高。 宋朝在統一全國后,將俘獲的大批畫家集中到汴京,設立翰林圖畫院。[35]史稱: 圖畫局(或應作“院”)掌以繪事應奉,若塑造則課工為之。有待詔、藝學、祗候、學生。[36] 宋代圖畫院機構之大、人員之多,為中國繪畫史上所僅見。[37] 有人認為:“歷代帝室獎勵畫藝,優遇畫家,無有及宋朝者。”[38]其實,史實并非如此。宋太宗時,有畫院藝學董羽于端拱樓上畫水,“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太宗與宮中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遙見畫壁,驚呼畏哭不敢視,亟令圬墁之……”。[39]皇子一聲啼哭,畫家佳作被毀。宋太宗就是如此“獎勵畫藝”! 與宋太宗不同,宋徽宗置政事于不顧,獎勵書畫之藝。可是,他雖然置身于畫家之林,但并未忘記祖宗遺訓,“不欲以好玩輒假名器”,[40]絕不把高官輕易授予繪畫官。據筆者所見記載,宋徽宗、宋欽宗在位期間以及整個南宋時期,朝廷授予繪畫官的官階最高不過成忠郎而已。如李迪“宣和蒞職畫院,授成忠郎,紹興間復職。” [41]成忠郎是低級武官階,其舊官為左班殿直,正九品。可見,宋代畫院官員的地位較之后蜀,相去十萬八千里! 五、唐宋翰林院的變遷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有宋一代無論天文官、醫學官,還是書法、繪畫官,其社會地位都比前代明顯下降。此外,唐宋翰林院的變遷,同樣可以作證。唐宋時期,翰林院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的變化。 第一階段:唐代前朝。《舊唐書》卷43《職官志二·翰林院》載: 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錬、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 正如宋人所說: 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并處。……唐置翰林,反與釋老伎術雜處”。[42] 也正如清代學者趙翼所說:在唐代前期,“學士亦伎術之一”。[43]唐代前期,不少名臣供職于翰林院,如唐高祖、唐太宗時的溫大雅、魏征、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等,唐高宗時的許敬宗、上官儀等,武則天時的蘇味道、韋承慶等,唐玄宗時的張說、張九齡等。唐代最高統治者雖然“其所重者詞學”,但由于文詞、經學之士與卜醫伎術之流均供職于翰林院,使得整個翰林院包括伎術官的地位都相當高。因此,《新唐書》卷46《百官志一》把翰林院置于相職之后進行介紹。 第二階段:唐代后期。文詞、經學之士與卜醫伎術之流雜處于翰林院的狀況,到開元年間才有所改變: 開元二十六年(738),劉光謙、張垍乃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44] 翰林學士院獨立建院,即開始于這時。值得注意的是,翰林院與翰林學士院并未完全分開。此后,翰林院不僅還有不少文詞、經學之士如李白等,而且仍然設有翰林學士這一官職。史稱: 至德宗(“宗”系衍文)已后,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45] 第三階段:宋代。北宋建立后,翰林院與翰林學士院完全分途。翰林院隸屬入內內侍省,由內侍勾當,是伎術雜流之所在。而學士院則獨立于兩府及臺諫之外,直屬皇帝,是宿學名儒的處所。在宋代,翰林學士“乃將相之儲”,“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46]出現了諸如此類的說法: 人間之官無貴于學士。[47] 詞臣實神仙之職。[48] 在宋代文獻中隨處可見。其地位之高,伎術官實在是望塵莫及。甚至在唐代曾經榮耀無比的翰林院官員一一待詔,到宋代居然成了民間對裱褙工、碾玉工等手工藝人的尊稱。變化之大,簡直猶如天地之別。總之,宋代翰林學士學院與翰林院判若兩途,毫不相干,這既是伎術官社會地位下降的結果,又是其表現。
中篇 宋代伎術官社會地位的橫向比例
在宋代,伎術官自成體系,有別于文官武將。宋朝推行歧視伎術官的政策。宋人指出: 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49] 同文官武將相比,伎術官地位低下。其主要表現可以概述為以下三個方面,即待遇差、升遷難、限制嚴。 一、待遇差 盡人皆知,宋朝優遇士大夫。宋人對此津津樂道: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50] 官員不僅享受俸祿,而且福澤子孫,每逢盛大節日以及官員本人致仕或去世,都可以蔭補子孫親屬入仕為官。可是,伎術官被排斥在士大夫之外,無論俸祿還是恩蔭方面的待遇都明顯低于文官武將。 先就俸祿而言。為官逐利,以權謀私,這是封建官僚入仕的第一需求。宋代官員的俸祿以月俸錢為主。據《宋史》卷171《職官志十一·奉祿制上》記載,天文伎術官的月俸錢為: 司天五官正,十三千。(春、冬絹各五匹,冬綿十五兩。)……司天監丞,五千。(春、冬絹各五匹。)主簿,五千。(春、冬絹各三匹,丞、簿各綿十五匹。)靈臺郎,三千。保章正,三千。(春、冬絹各三匹,惟靈臺郎冬隨不錢三千。) 另據記載,翰林待詔“月俸九千,春、冬給衣”;隸書待詔“月俸止六千”。[51]至于醫官、繪畫官的月俸錢,史書失載。 關于天文伎術官的祿粟,《宋史·職官志十一》稱: 司天監丞,四石。主簿、靈臺郎、保章正,二石。(已上并給米麥。) 宋代官員的俸祿、祿粟數額,前后變化比較頻繁。[52]僅就《宋史·職官志十一》所載作比較,也可見伎術官的待遇明顯低于文官武將。如宰相、樞密使月俸錢三百千,節度使月俸錢四百千,五官正的月俸錢分別為他們月俸錢的23分之1弱、30分之1弱。五官正的待遇,只能同縣令、主簿、縣尉這類幕職州縣官相比較。七千戶以下、五千戶以上縣的縣令月俸錢為十五千,萬戶以上縣的主簿、縣尉月俸錢為十二千。五官正的月俸錢尚且低于前者,僅略高于后者,但在元豐以前,五官正的官品比這些幕職州縣官高得多。 南宋學者章如愚指出: 選人廩給,下者至請錢七千,米麥兩石而已,貧不足養。[53] 選人又稱幕職州縣官,是低級文臣階官和地方官的總稱。大多數伎術官的俸錢和祿粟還不到章如愚所說之數,自然更是“貧不足養”、難以糊口。 宋代官員俸祿種類繁多,除了俸錢、祿粟而外,還有職錢、衣賜、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之給、隨從衣糧、馬匹芻粟、添支、恩賞以及公使錢等等。諸如此類,伎術官或者完全沒有,或者所得甚少。 再就恩蔭來說,所謂恩蔭是朝廷根據官員官職高低,授予他們的子孫或親屬官職的制度。按照宋真宗時的規定,知雜御史以上的高級文官和橫行以上的高級武官,一年蔭補親屬一人為官;帶職員外郎以上的中級文官和諸司副使以上的中級武官,三年可以蔭補親屬一人為官。此外,宋代官僚們還享有南郊大禮節恩蔭、誕圣節恩蔭、致仕恩蔭、遺表恩蔭等特權。宋代恩蔭多而濫,無怪乎清代史家趙翼感嘆: 朝廷惠下之典,未有如宋代之濫者。[54] 可是伎術官在恩蔭方面所享有的待遇,遠遠不如文官武將。嘉祐元年(1056)十一月,宋仁宗在詔令中規定: 伎術官合奏蔭者,止授以伎術官,仍一次而止。[55] 這項規定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伎術官享受恩蔭待遇,必須是“合奏蔭者”,也就是說僅限于高級伎術官。第二,伎術官蔭補親屬“一次而止”,不能像文官武將那樣,多次蔭補。第三,伎術官蔭補親屬只能擔任伎術官,不能改做文官武職。其所以這樣規定,據說有兩個目的,即“不獨使專其業,且以杜入官之濫”。[56]因此,伎術官的子孫們按照規定,至多也只能世世代代地擔任伎術官。如“太史局令吳師顏在京師時已世為日官,及渡江,掌其職者猶二十年”。他死后,其子“澤繼代父任,令(當作“今”)為春官大夫判太史局”。[57] 宋高宗的御醫王繼先在宋代伎術官中是個特例,他曾經飛黃騰達于南宋初年。其原因在于,一則他深受宋高宗信任,宋高宗“以一身委之繼先”;[58]再則他與秦檜關系特殊,秦檜叫其夫人王氏拜他為兄弟,“往來甚密”。[59]因此,王繼先的親屬蔭補官職突破了上述規定,不僅不是“一次而止”,而且在他的親屬當中,蔭補為文官者有之,出任武將者也有之。但是,盡管王繼先炙手可熱,這些違反規定的做法仍然遭到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被譴責為“僥冒補轉”。[60]如紹興年間,宋高宗降旨,把王繼承先的女婿任命為添監浙江稅務。宰相張浚、趙鼎對這項任命事宜很不理解,認為醫官即使治病有效,也只能“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效驗以答其勞。”而給事中王居正則將詔旨封還。宋高宗“玉色頗厲”,王居正依然堅持己見。他指斥王繼先不過是個“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俸祿”的伎術官,并勸告宋高宗:“臣不愿陛下輒起此門。”宋高宗無言可對,只能表示贊同:“卿言是也”。并決定“前降指揮更不施行”。[61]就事論事,王居正直言極諫,膽識可嘉。但他的“技術庸流”之說,卻反映出有宋一代士大夫對整個伎術官的歧視和輕鄙。 除了俸祿、恩蔭而外,服飾對于封建官僚來說,也是一種不能忽視的待遇。它在封建時代是用來區別貴賤,表示等級身份的一項重要標志。宋朝在服飾方面,對士大夫待遇同樣相當優厚,失之于濫。宋人對此曾慨嘆: 嬰孩授命,年才十五者,今遂服緋。而貴近之子,或初年賜緋,年才及冠者,今遂賜紫。朱、紫紛紛,不亦濫乎![62] 相反,宋朝對伎術官服飾限制相當嚴,其主要表現有下面三點。 第一,一般只能服綠。宋代官員公服的顏色,北宋前期因循唐朝舊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元豐元年(1078),宋神宗把官員的服色改為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上服綠,青色則去而不用。元豐改官以后,最高一級伎術官為從六品,才勉強可以服緋。何況朝廷在元豐元年還明確規定: 伎術若公人之人入品者,并聽服綠。[63] 因此,宋代盡管有“伎術官之服,有紫、緋、綠”[64]之說,但絕大多數伎術官只能服綠。這些身穿綠袍的伎術官,在“朱、紫紛紛”的官場中,不免有地位低下、狼狽不堪之感。 第二,一般不能佩魚。魚是一種“以金、銀飾為魚形”的裝飾品,“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官員們身著公服,將魚袋“系于帶而垂于后,以明貴賤。”宋代從雍熙元年(984)開始,“內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魚”。服紫者佩金魚袋;賜紫服者“則給金涂銀”;賜緋服者“亦有特給”。甚至連“京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佩。”[65]但是,伎術官卻沒有這項待遇。大中祥符六年(1013)五月,宋真宗下詔規定: 伎術官見佩魚者,特許仍舊。自今未至升朝官,賜緋、紫者,不賜魚袋。[66] 因此,翰林待詔王文度在天圣二年(1024)請求佩金魚袋,遭到宋仁宗拒絕。宋仁宗的理由是: 先朝不許伎術人輒佩魚,以別士類,不令混淆。[67] 景祐二年(1035),尚藥奉御徐安仁因深受宋仁宗寵信,“特許佩魚”。不過,這只是“特許”,不是通例。在宋代,“服緋、紫者必佩魚,謂之章服。”而伎術官即便是賜緋、紫者亦不能佩魚。按照宋人的說法: 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68] 可見,伎術官地位之低下,簡直不能與士大夫同日而語,只能同胥吏相提并論。 第三,一般只能著屨。伎術官不僅服色、佩飾與高中級文官武將不同,而且穿的鞋子也與他們有別。其區別在于四飾。即絇、繶、純、綦。按照宋徽宗在位時期的規定: 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上減去一繶,并稱履,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繶、純,并稱屨。[69] 也就是說,伎術官穿的鞋子只能有絇、綦二飾,不能四飾齊備;只能叫做屨,不能稱為履。盡管在政和、淳熙年間曾經分別為醫官、天文官增設大夫階,但伎術官大夫階并不等于文武官大夫階,他們同樣只能著屨,不能享受與文武官大夫階相等的待遇。 二、升遷難 傳統制度是一種頗為嚴密的等級制度。等級制度就像一架梯子,等待著每一個為物欲驅使的人去攀登。誰爬得高,誰受益就大。宋朝為文官武將,特別是文官提供了一架可以比較順利地向上爬的梯子。宋真宗以后形成的升遷制度大致是: 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 所謂磨勘,即是經過考察,升遷本官階。制度雖然如此,但實際上往往“不問勞逸,賢不肖并進。”[70]磨勘考課失去考課的意義,官僚僅憑年勞升遷,但是,伎術官卻不能沿著這架梯子往上爬。至道二年(996)正月,宋太宗“申嚴”歧視伎術官的政策,宣布: (伎術官)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勛階,不得擬常參官。[71] 天圣元年(1017)八月,宋真宗規定: 今后司天監及諸色伎術官雖系京朝官,并不得磨勘。[72] 至于各類伎術官的升遷辦法,朝廷另有規定。 關于司天監官的升遷制度,南宋人王栐說: 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正、靈臺郎、直長、局丞至冬官正,僅五遷爾。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醫官則太優,欲增其等級。慶歷五年六月乙卯朔,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73] 洪適也說: 太史局遷轉資格,自局令至直長共九階,并系十年無過犯,方許下磨勘。[74] 從上面兩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以下三點。第一,慶歷五年(1045)以前,天文官“五年一轉”,其升遷速度與武臣相等,比文臣遲緩,可是士大夫們認為這項規定“太優”。第二,慶歷五年以后,宋仁宗把大多數天文官的升遷時間更改為“十年一遷官”。這無疑是對伎術官更加歧視的表現。第三,在設置五官大夫以前,南宋天文官共有九階,也就是說,一個天文官從最低一階爬到最高一階,至少要90年。90年,何等漫長的歲月,天文官只能望“階”興嘆,嘆息生命太短。 醫官的升遷制度,類似天文官。其基本原則有兩條。第一,一般是十年一遷。宋仁宗在天圣六年(1028)七月明確規定: 自今后醫學、祗候、醫人如補授十年有過犯一度者,并不在補轉之限。[75] 第二,通常在本院內升遷,慶歷二年(1042)五月,宋仁宗在一道詔令中說: 翰林醫官有勞者,止遷本院官,勿得換右職及兼差遣。[76] 所謂右職,即是武官。 宋代的醫官升遷制度在宋神宗將東班諸司使副作為醫官官階之后,有所變動。他為此在熙寧八年(1075)六月下詔: 詔翰林醫官使、副使并五年一磨勘。醫官副使以上,舊無磨勘法,副使遇相恩即改正使。至是立法,以資遷東班諸司使、副使,仍舊兼醫官使、副使,其副使遷至軍器副使,乃遷醫官使。[77] 現將這道詔令的主要內容,列表述如下: 差遣(醫官院職) 敘資(醫官階) 醫官使 ←── 諸司正使 ↑ ↑ 醫官使醫官使 ↑↖↑ 醫官副使—―—→ 軍器庫副使
這道詔令粗讀起來,似乎是把十年一遷改為五年一遷,醫官的升遷速度從而加快。略加推敲,其實不然。由于在醫官副使到正使之間增加了若干官階,因而升遷速度更加遲緩。 至于書法、繪畫藝術官的升遷制度,與天文、醫學伎術官有所不同,其不同之處主要在于下面兩點。 第一,元豐官制改革以前,大多兼任文武官(即同正官)。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所立《中岳中天崇圣帝碑》,由“翰林待詔、朝奉大夫、守國太府少卿同正、輕車都尉白憲奉敕書并撰額。”[78]白憲所擔任的朝奉大夫是散階,太府少卿是空官即同正官,輕車都尉是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所謂的官職在北宋前朝并沒有任何實權,沒有多大實際意義。元豐官制改革,以階易官,廢除加、兼、勛、檢校官。此后,書法、繪畫官員自然也就不再兼任同正官。政和更改官制后,他們則兼任低級武官。 第二,面臨著一個“出職”問題。如宋真宗、宋仁宗在詔令中都曾經涉及到書法官員的出職。天圣元年(1017)十月,宋真宗詔稱: 御書院翰林待詔、書藝、祗候等入仕十年以上無私犯者與出職。[79] 天圣六年(1028)十月,宋仁宗詔稱: 御書院待詔出職者,自今不得為文資。[80] 宋高宗在紹興十六年(1140)十一月,對書法官的出職作了比較具體的規定: 書學祗候滿十五年補承信郎,書藝學滿一十年補保義郎,直長充書待詔滿五年補成忠郎。[81] 承信郎、保義郎、成忠郎都是低級武官階。這里應當指出,所謂出職是為了酬勞執役多年的胥吏,特許他們入仕為官。書法、繪畫官居然也還面臨著一個出職問題,[82]這恰恰表明他們名義上是官員,實際上是胥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