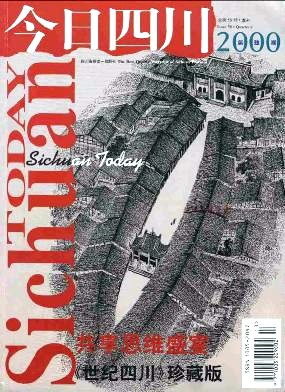略論宋代城市消費
吳曉亮
【內(nèi)容提要】自中唐至宋代,城市消費與市場的關系,表現(xiàn)出更多的積極因素。在宋代,經(jīng)由市場的個人消費是當時城市消費的主流。由于城市消費經(jīng)由市場,所以大眾化消費必然促進古代社會不同階層社會地位的變動。市場的日用品消費量擴大,是促進城鄉(xiāng)連接、相互推動、彼此作用、向前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關 鍵 詞】宋代/城市消費/政治性城市/消費性城市
一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今人用“政治性城市”或“消費性城市”來評價中國古代的城市,而且常常帶有貶義,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結(jié)論或失之于簡單,或失之于籠統(tǒng)。如果我們以中唐及宋為界,就會發(fā)現(xiàn)古代的城市消費(注:城市消費本應包括生產(chǎn)消費和個人消費,但是,因篇幅所限,本文論及的主要是城市的個人消費。)在此前后有所不同。同樣是消費,但可以說已開始發(fā)生了一定量的質(zhì)變。
在中國古代社會,由于城市形成途徑的不同和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差異,城市消費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特點。中國古代城市自誕生以來,都城作為一個政權的統(tǒng)治中心所在地,其他城市大多是不同級別的地方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其政治職能的發(fā)揮十分充分,經(jīng)濟服從于政治十分明顯。這在城市消費方面表現(xiàn)尤其如此。從城市消費方面看,城市中居住的工商業(yè)者、文化人、小市民等要全部或部分依靠市場才能生存,這一點長此不變。但是,由于古代城市是不同級別的行政中心所在地,所以,城市中有相當部分的居民就是達官顯貴、城居地主、軍人及其家屬。因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受整個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水平的限制,那些居住在城市的顯貴們主要依靠俸祿和賞賜來滿足他們的日常需要,這些人與市場的聯(lián)系極少。這樣,在城市消費中形成兩種不同的個人消費:一種是經(jīng)由市場才能完成個人的消費;一種是不需要市場,只須依靠國家俸祿和賞賜就可以進行個人的消費。因為前者更能促進社會生產(chǎn)和流通,所以,前者較后者進步。
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政治、經(jīng)濟、文化都可稱之為輝煌的歷史時期,也是城市發(fā)展的第一個極盛時期。此間,城市的各種職能,特別是經(jīng)濟職能的發(fā)展十分迅速。其中,經(jīng)由市場的消費同市場的活躍相呼應,成為那一時期城市消費的一大特色。但在漢代以后,城市的發(fā)展受到獨尊儒術、重農(nóng)抑商等國策的影響,經(jīng)濟上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國家對鹽、鐵、酒等盈利較高的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與銷售實行專營;對商人實行了“算緡”、“告緡”,不得衣絲、不得乘馬等打擊政策,由此,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盛極一時的商業(yè)及商人階層受到沉重的打擊。隨著豪商富賈地位的跌落,皇族、宮室、官貴等上層獨占鰲頭,成為城市中最顯赫的居民,權勢不斷滲入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與城市消費較密切的,可以從這些人的生活來源來分析。僅從“一千石”、“二千石”等實物俸祿的量詞作官名的代稱來看,可知這些人的個人消費主要靠實物俸祿和賞賜才得以最終完成。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唐代前期。以唐長安為例,這個一直令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宏偉的、規(guī)整如棋盤的建筑典范,除了宮城和皇城占地9.4平方公里、約占全城總面積的九分之一外,108坊就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區(qū),它占據(jù)了全城的大部。這說明唐長安城市居民數(shù)量前所未有。但是,如此規(guī)模的城市,其商業(yè)區(qū)——東市和西市卻只各占兩坊之地,四圍皆有墻。而且,兩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注:宋敏求:《長安志》卷2。 )這說明兩市之內(nèi)的交換有著嚴格的時空限制。由這樣一種交換水平可以斷定,唐代長安的城市消費狀況與漢代相較,除了量的增長外,沒有質(zhì)的變化。所以唐人有詩一方面贊嘆“長安大道橫九天”的浩蕩之勢;另一方面,又感慨長安城是“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唐都城尚且如此,地方城市可見一斑。
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至唐代中期以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夜市及浸街占道現(xiàn)象頻頻出現(xiàn),史不絕書,坊市制度開始崩潰。這時,唐代的城市消費必然隨之有不同的表現(xiàn),較有代表性的事例,即“宮市”。“宮市”利用政治權勢對平民百姓掠奪的事實在白居易筆下的《賣炭翁》里有著極其生動的描寫。我們暫且不論宮廷依權仗勢盤剝百姓的事實,而僅就宮廷需要市場、走進市場這一點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商品經(jīng)濟的滲透力。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社會產(chǎn)品的豐富、社會需求的增大和社會欲望的膨脹,使得那些高居于金字塔尖之上的階層向市場低下那曾經(jīng)是不可一世的頭。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部分人開始進入市場和廣大的農(nóng)民階層卷入市場一樣,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因為,這從政治上表明了長期以來政治權勢牢不可破與等級森嚴壁壘的松動,顯示了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端倪;從經(jīng)濟上則表明市場的擴大。盡管它是那樣的微不足道,但應當給予一定的重視和肯定。就城市消費講,自唐代“宮市”等現(xiàn)象出現(xiàn)后,更說明宮廷、官貴等上層社會與市場聯(lián)系的程度加深。這些人的個人消費就逐漸由原來那種單由國家貢賦滋養(yǎng)、無需市場或極少需要市場的消費轉(zhuǎn)變成為逐漸依靠市場或說經(jīng)由市場進行的消費。
二
在中國古代城市發(fā)展史上,宋代的城市發(fā)展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國內(nèi)外學術界多有論述認為宋代發(fā)生了城市革命,那么,城市消費如何?個人消費作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是否如是說呢?
入宋以后,城市制度最大的變化就是坊市制的徹底崩潰。它是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結(jié)果,同時,又反作用于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坊市制徹底崩潰對城市居民生活的直接影響,就是使得人們的生活越來越隨意、越來越自由。在宋代,有關城市生活的記載很多,較著名的如《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詳細記載了兩宋都城的社會生活;《夷堅志》又以怪異小說的形式反映了宋代城鎮(zhèn)居民生活的不同層面;加之大量的宋人筆記等,皆向后人展示了宋人豐富的城市生活。根據(jù)這些史料看,宋代的城市消費與前代有一個最大的差別,就在于個人消費的行為有很多是在經(jīng)由市場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之后才最終完成的。可以說,宋代城市的個人消費較前代發(fā)生了一定量的質(zhì)變。
(1)衣食住行與市場的關系
衣食住行是個人消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內(nèi)容。就飲食方面看,茶坊酒肆在城市中普遍存在就是城市消費經(jīng)由市場的明證之一。據(jù)《東京夢華錄》載,茶坊酒肆已經(jīng)遍布開封城的大街小巷,飲食業(yè)生意興隆。僅開封城內(nèi)“正店”(大酒店)就有“七十二戶”。這類大酒店往往“繡旌相招,掩翳天日”。顯然,能出入此類酒店的絕非等閑之輩,定是有經(jīng)濟實力的人。而“腳店”(小酒肆)“不能遍數(shù)”,這些小酒肆,“賣貴細下酒”,這肯定是中下階層的飲酒去處。(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卷3。)在宋人飲食文化中,飲茶的習俗也占據(jù)著重要地位。飲茶場所也有茶樓、茶肆之分,不同身份的人自有取舍。除了固定的飲茶場所“茶坊”外,還有“車擔設浮鋪”,許人“點茶湯“,大大方便了游觀之人。(注:吳自牧:《夢梁錄》卷16。)茶坊酒肆的盛景我們還可以從張擇端的長卷風俗畫《清明上河圖》中獲得形象的認識。在衣著方面,宋人的服飾隨著經(jīng)濟的變化而變化。宋朝初年,尚“崇尚節(jié)儉,金銀為服用者鮮”,所以,“金銀之價甚賤”。到真宗年間,金銀之價飛漲,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究其原因,當時“服用浸侈”,以金銀裝飾衣物之風盛行,“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就是原因之一。于是,屢有詔令頒行,“非命婦不得以金為首飾”、“自中宮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為飾”等等。盡管至仁宗即位,“申嚴其禁”,但是,仍然“有未至焉”。(注:王:《燕翼詒謀錄》卷2。)到了徽宗時, 就有“奢蕩極靡”(注:《宋史·輿服志》。)的記載。這樣的服飾消費風尚,正是基于繁榮的市場之上。在開封,交易金銀彩帛、買賣衣物和花環(huán)領抹之所很多,而且交易的時間也很靈活,甚者有“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卷3。)的行為。可以看出,服飾業(yè)的市場既有高檔的也有一般的,完全可以滿足不同的消費層。就居住而言,城市市民的住宅、店鋪鱗次櫛比。在城市里,由于流動人口較多,所以客房、塌房店鋪的房屋租賃業(yè)較發(fā)達。在開封,客店很多,如保康門瓦子往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于此安泊”。(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卷3。)在臨安,就有“慈元殿及富豪內(nèi)侍等人家起造塌房數(shù)十所,為屋數(shù)千間。專以假賃與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貨物并動具等物”。(注:吳自牧:《夢梁錄》卷19。)就行的消費看,古人大多依靠車、船、馬、轎等人力作為代步的工具。在開封,凡遇紅白喜事游玩等活動,檐子、車子、船等交通工具的租賃“自有假賃所在”,而且“皆有定價”。百姓“尋常出街干事,稍似路遠倦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在宣政年間,在池苑內(nèi)就有“假賃大小船子,許士庶游賞,其價有差”。(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7、卷4。)《塵史》卷下亦曰“京師賃驢,涂之人相逢,無非驢也”。以上史料證明,宋代城市的衣食住行與市場的關系極其密切。
(2)個人的貨幣擁有量及使用程度與市場的關系
貨幣的擁有量及使用程度是經(jīng)由市場的個人消費的必要前提。這種消費量的大小,除了看社會經(jīng)濟的進一步發(fā)展,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物質(zhì)基礎外,還要看人們所擁有的貨幣量的多少及進入這種消費層的變化。中國古代官員俸祿的變化就可以佐證這一階層對市場的需求與參與,使我們窺見“政治性城市”的一點變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官員俸祿一直實行既有實物也有貨幣的分配制度,其實物與現(xiàn)錢的比例各代不一。一般情況下,社會經(jīng)濟尤其是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較快、水平較高的情況下,官員俸祿中現(xiàn)錢的比例會有增長;否則,則反之。據(jù)王《燕翼詒謀錄》卷2載:宋朝初年“士大夫俸入甚微,簿、 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細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可知,宋建國之初,即使是朝廷的命官,也只是處于溫飽甚至在貧困線上,這是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不高的表現(xiàn)。然而,至真宗年間,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物質(zhì)資料豐厚,人們的生活追求奢華已成為時尚。為了滿足消費的多種需要,人們進入市場,致使金銀之價騰踴的記載不少。正是這一時期社會上貨幣的需求及使用量有較大增長,所以,景德三年、四年,先后對赤、畿知縣等官員的俸祿進行了調(diào)整。俸祿調(diào)整的主要內(nèi)容一個是較大幅度地提高了官員俸祿實物及現(xiàn)錢的數(shù)額,另一個就是增大了現(xiàn)錢的比例。景德四年有詔曰“自今文武,宜月請折支,并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由此“惠均覃四海矣”。據(jù)此分析可以得出幾點看法:官員俸祿數(shù)額的調(diào)整必定建立在社會經(jīng)濟有較好發(fā)展的基礎之上;現(xiàn)錢比例的增大必定是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所致由貨幣的使用率提高而引發(fā);這一調(diào)整,必然加深龐大的官員階層卷入市場的程度。由于官員俸祿中現(xiàn)錢比例的增大,他們進入市場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增強。他們或許是為了經(jīng)營(官員經(jīng)商的記載史不絕書)、或許是為了消費(就像我們前面所引述的那樣),對市場必然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又由于他們也是當時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群體,用階級觀點分析,他們屬統(tǒng)治集團;但用社會學的觀點看,他們是社會的管理人員。他們與其他成員一樣,都有存在的社會價值,所以,他們的消費、特別是經(jīng)由市場的消費對社會的影響并不都是消極的。
(3)精神消費與市場的關系
經(jīng)由市場的精神消費較物質(zhì)消費屬更高層次,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較物質(zhì)消費更能反映出人們的生活質(zhì)量與風格。宋代城市的個人消費除了物質(zhì)生活消費已經(jīng)有許多要經(jīng)由市場而完成外,還有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也是如此。后一種消費屬更高層次。因為只有在人們的溫飽問題,亦即生存的基本條件滿足后,精神文化方面的滿足才可能列入日常生活之中。對精神文化需求水平的提高必定建立在物質(zhì)水平提高的基礎之上,只有在民眾的錢囊里有了余錢,他們才可能經(jīng)由市場獲得精神文化方面的滿足。兩宋時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內(nèi)容除了陽春白雪類的詩詞書畫等,又增添了許多下里巴人的內(nèi)容。確切地說,主要是城市市民娛樂方面的。從《東京夢華錄》、《夢梁錄》、《都城紀勝》等文獻里對勾欄瓦肆的記載看,內(nèi)容非常豐富:有小唱、嘌唱、般雜劇、傀儡、講史、小說、影戲、散樂、諸宮調(diào)、商謎、雜班、弄蟲蟻、合聲、說諢話、叫果子以及教坊的鈞容直等等。如此豐富的內(nèi)容使得娛樂的人“不以風雨寒暑”,皆要前往,致使“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終日居此,不覺抵暮”;有的惟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熱鬧非凡。勾欄瓦肆的數(shù)量很多,規(guī)模不小:在開封潘樓酒店附近的一個瓦子,“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一個被名之為“象棚”的規(guī)模最大,“可容數(shù)千人”。(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卷5。)在臨安可數(shù)的“瓦舍”也有17處。盡管這些地方被吳自牧視為是“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注:吳自牧:《夢梁錄》卷19。)但是,正是這種娛樂形式符合大眾口味,繼而才有了大眾的參與性行為;而大眾的參與加深,又反作用于娛樂活動本身。這都是當時俗文化興盛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
(4)城市商品和娛樂場所的豐富以及優(yōu)質(zhì)服務與市場的關系
城市居民擁有貨幣,是經(jīng)由市場消費的必要前提;城市擁有品種多樣的商品、各式各樣的娛樂場所以及優(yōu)質(zhì)的服務是擴大消費范圍、增加消費頻率、延長消費時間的又一前提。我們可以從宋代服務業(yè)之興盛發(fā)達來理解為什么宋代的城市消費會如此興盛、如此大眾化。比如飲食業(yè),其服務周到、價格合理已惠及不同的社會層。 在《東京夢華錄》卷4中載,北宋的筵會假賃是“椅卓陳設、器皿合盤、酒擔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賃。”“欲就園館亭榭寺院游賞命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其收費大體公允,“不敢過越取錢”。對小客戶“雖百十分,廳館整肅,主人只出錢而已,不用費力”。消費如此便當合理舒適何樂而不為呢?其他凡是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如“雇覓人力、干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3。)其分類之細, 幾乎可以服務和滿足于城市的各行各業(yè)乃至官府衙門的需求,各式服務已經(jīng)形成一定規(guī)模,居民生活因此而更加方便。(注:吳自牧:《夢梁錄》卷19。)基于當時的社會條件,這里的行老已具有“牙人”的職能。他與上下的關系一定是金錢的關系。顯然,宋人的城市消費已經(jīng)達到個人愿意出資以求便當、快捷、舒適的程度。 三
根據(jù)上述資料可以看到,宋代都城的城市消費不同于前代。由于都城以下各級城市的政治性及消費性城市的消極面影響會依次遞減,加之篇幅有限,不再擴展論述。總之,宋代的城市消費具有以下積極影響:
(1)經(jīng)由市場的個人消費成為城市消費的一大特色, 在一直被認為是“政治性城市”、“消費性城市”的兩宋都城里,在它們作為政治中心這一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其城市消費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生了變化。城市的個人消費行為與市場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它不僅涉及到人們生存的最基本消費,而且涉及到在物質(zhì)消費之上的精神消費。它較前代那種不需要市場、不經(jīng)由市場的消費大大地進了一步。同時,它對社會生產(chǎn)與交換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在宋代資料里,就有這樣一些記載:為了滿足城市居民龐大的飲食消費量,米面雞鴨魚肉菜蔬水果等源源不斷地運入兩宋的京城,而且交換活躍。在開封,每日“有生魚數(shù)千擔”運入;那些“殺豬羊作坊,每人擔豬羊上市,動即百數(shù)”;糧食“用太平車或騾馬馱之,從城外守門入城貨賣”,每日自五更始,“至天明不覺”。(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4、卷3。)在臨安,每日大米的消耗量很大,僅“細民所食”,“城內(nèi)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鋪家”。于是,米鋪也很多。僅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米市三四十家”。由于米在臨安成為一大商品,所以當它從產(chǎn)地運輸至銷售地后,就從下貨處至店鋪的過程中形成一種較規(guī)范的營運形式:“叉袋自有賃戶、肩馱腳夫亦有甲頭管理、船只各有受載舟戶,雖米市搬運混雜,皆無爭差。故鋪家不勞余力而米徑自到鋪矣”(注:吳自牧:《夢梁錄》卷16。)。這樣的消費水平,特別是和市場發(fā)生關系的消費,對社會生產(chǎn)與交換的促進作用顯而易見。可以肯定地說,宋代養(yǎng)殖、種植等專業(yè)戶的生產(chǎn)與經(jīng)營的發(fā)展,就與城市這種經(jīng)由市場的消費密切相關。
(2)經(jīng)由市場的消費是大眾性消費或說是全民的城市消費, 它可以促進并加速社會不同階層社會地位的變動。本文所指的大眾是一個廣義的詞,它泛指不同的社會階層而非僅只指被統(tǒng)治階層。在上述所引證的宋代城市生活的資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宋代人們經(jīng)由市場的各種消費活動形成了不同的檔次,它適合于各個階層。無論是物質(zhì)消費還是在其之上的精神消費都是如此。這種大眾性的、經(jīng)由市場的消費行為使得人人都必須支付一定的貨幣,才能滿足自己的消費愿望。盡管其消費活動有著高檔和中低檔、高價和普通價的差別,但僅就必須付錢一點而言,就包含了人人平等的因素。它反映出在商品經(jīng)濟的浸蝕下,政治權勢的基礎再度松動和普通民眾社會地位的上升。
(3)經(jīng)由市場的消費品中日用消費品量大大超越了前代, 它進一步體現(xiàn)了城鄉(xiāng)關系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發(fā)展。盡管文獻中仍然有金銀珠寶等奢侈品的交換與消費的記載,但是,吃穿用等消費品的交換與消費無論在其數(shù)量上還是在其消費規(guī)模和水平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古代中國社會,對經(jīng)由市場的日用品的消費應當給予一些更積極的評價。這一點以往做得不夠。因為生活日用品的生產(chǎn)、交換與消費最密切地聯(lián)系著廣大民眾,而且最能體現(xiàn)古代的城鄉(xiāng)關系是一種農(nóng)村支持城市,城市又激勵著農(nóng)村的關系。數(shù)千年來,中國社會就是在這種相互作用中發(fā)展前進的。
通過對宋代城市消費特點的認識,筆者認為學術界應當對中國古代的“消費性城市”做深入、細致、具體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識中國古代城市的歷史地位,從而借古喻今,對當今中國城市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凡是經(jīng)由市場而完成的消費、凡是經(jīng)由市場而形成的大眾性消費以及日用品消費都應當給予積極的評價。



展研究.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