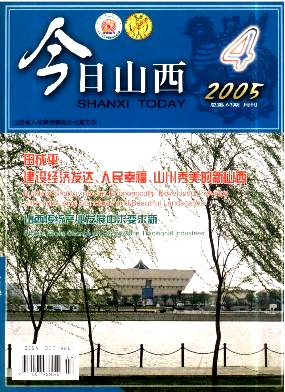試論宋代“全民經商”及經商群體構成變化的歷史價值
吳曉亮
宋朝繼唐末五代將中國古代商品經濟推向又一個高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當時市場最活躍的地方,呈現出一種皇室日益靠近和走進市場、官僚吏員迷戀市場、禁軍士卒被迫走進市場、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以及中小商人活躍于市場的情況。由于經商群體源自不同的職業和人群,成為經商群體的新的組成部分。其經商勢頭兇猛,可謂“全民經商”的大潮不可阻擋。
由此,我們能否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除了有通常人們理解的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發展外,除了我們可以看到和理解的工商業者的活動之外,其他社會群體的經商活動是否有其合理和積極的一面呢?對于社會下層人士諸如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以及中小商人在市場上的活動,學術界多持肯定的態度。但對那些屬于上流社會的群體,特別是那些屬于國家管理層的人員進入市場,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他們憑借特權。投機取巧,欺壓百姓以及敗壞朝綱的一面。但是,這部分人作為社會的一個群體,參與市場活動似乎有著主客觀的原因,亦即有其必然性和客觀合理性。本文對此試作一些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一、宋代“全民經商”態勢的形成
通過歷史文獻的記載和今人的研究,宋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已經為人們熟知。只是,在紛繁的商品流通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宋代行商坐賈活躍于城鄉社會,市場向王朝的各個角落盡情地滲透,宋代社會經濟呈現出勃勃生機。同時,我們也發現,有另外一些人群,也在不知疲乏地奔走各地,追逐著市場利益的最大化,展現出宋代市場的另一個側面。
士卒本是為國家效力,行保家衛國之事的群體;綱船本是運輸國家物貨,連接中央和地方經濟命脈的工具,但兩宋士卒、綱船等參與經商的記載很多。早在太祖開寶三年間(970年),成都府“押綱使臣并隨船人兵多冒帶物貨、私鹽及影庇販鬻,所過不輸稅算”。后有詔令有司“自今四川等處水陸綱運,每綱具官物數目給引付主吏,沿路驗認,如有引外之物,悉沒官”①。盡管宋代對綱船私貨曾經有征稅的記載,但是“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即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是當時的主流,所以,一方面綱卒以及綱船的經商行為確實使社會
__________
①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42之1,中華書局,1957年。
“物貨流通”①,但另一方面,伴隨物貨流通也發生諸多問題,如太宗雍熙四年(987年),“聞西路所發系官竹木,緣路至京,多是押綱使臣、綱官、團頭、水手通同偷賣竹木,交納數少即妄稱遺失”②。仁宗年間,綱船“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③。徽宗年間,在江、湖等比較發達的地方,仍有“裝糧重船,多是在路買賣,違程住滯”④。“諸路合發上供錢糧、金銀、匹帛、雜物等綱,在路多是妄作緣故,住岸販賣百端”。地方有司也為自身利益而縱容這些行為,“不行催趕”⑤。這些損公利私、賄賂官員的例子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當時綱船和綱卒經商逐利已經發展到膽大妄為的地步。在南宋初年,押綱人“往往沿路移易綱物,于所至州縣收買出產物貨,節次變賣以規利息”,至有一二年不到目的地者⑥。殿司諸統領將官公開“養兵營運,浸壞軍政”⑦。南宋淳熙年間,諸軍將佐不僅于屯駐之處私自興販營運,而且經營邸店、質庫等贏利性產業⑧。由此可見,北宋較活躍的是綱卒以及綱船,南宋則多是駐軍的軍官。軍人的經商活動日益活躍,其經營的商業領域也在不斷拓展。
僧侶道士本是宗教人士,清凈無為、淡泊名利應是其本分,寺院道觀自然也應當是清凈之地,是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但是,在前代寺院經濟主要立足于有司賜予土地和免除徭役賦稅等優惠政策的基礎上,宋朝的宮觀寺院以及宗教人士另辟蹊徑,從事營運,追財逐利者日眾。僅以北宋東京那個有著“萬姓交易”大相國寺為例,除了熙熙攘攘的世俗之人參與交換外,有“王道人”自制的“蜜煎”出售;有“諸寺師姑”制作的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帽子、冠子等出售。寺內“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也要以金錢論價,“雖三五百分,莫不咄咄而辯”⑨。顯然,這樣一種贏利場面實在是與佛祖出世時的初衷、道教清凈無為的宗旨格格不入。
官吏本是國家的管理人員,行治理國家之政事,但宋朝上下官員經商的事例史不絕書。如宋朝初年,王溥為相,其父王祚曾經“頻領牧守”,因其“能殖貨”,故“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⑩。應當說,宋朝承襲五代以來官吏經商的現象已經引起統治集團的高度重視,并設法阻止以免敗壞朝綱。史曰:“五代藩鎮多遣親吏往諸道回圖販易,所過皆免其算。……國初,大功臣數十人,猶襲舊風,太祖患之,未能止絕。于是詔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傳出入,赍輕貨,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諸處回圖,與民爭利,有不如詔者,州縣長吏以名奏聞。”⑾同時,朝廷還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以行政貶職等措施打擊官員販易規利者,如開寶年間太子洗馬周仁俊,因“坐知瓊州日販易規利”故貶官懲之⑿。但是,官吏經商圖利的勢
_____________
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5《國用考三.漕運》,中華書局,1986年。
②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42之2,中華書局,1957年。
③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5《國用考三.漕運》,中華書局,1986年。
④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43之11,中華書局,1957年。
⑤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2之46,中華書局,1957年。
⑥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44之6,中華書局,1957年。
⑦ 脫脫等撰《宋史》卷194《兵志八》紹興十三年條,中華書局,1977年。
⑧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刑法2之122,中華書局,1957年。
⑨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卷之3,中華書局,1982年,第88—89頁。
⑩ 脫脫等撰《宋史.列傳第八.王溥》,中華書局,1977年。
⑾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中華書局標點本。
⑿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中華書局標占本。
頭有增無減。太宗年間,范晞“嘗為興元少尹,居京兆,殖貨鉅萬”①。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因“以公錢貿易規利”,且“遣部吏強市民羊及買妾”,因而“坐奪三任”②。仁宗朝孫沔,先后為通判、知州、轉運使等官,“所在皆著能跡”。但他在杭州時“嘗從蕭山民鄭吳市紗”,在并州又“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③。又如贓官任守忠,憑借其侍奉過真宗,所以獲俸祿賞賜頗多。但其資性貪婪,“聚斂之心”不滅,其“竊盜官物,受納貨賂”,以致“金帛珍玩溢于私家”,即便在被司馬光等人彈劾并放逐后,雖然“只于街市鬻販規利”,但仍然是東京富戶, “宅第產業甲于京師”④。這些都是十足的大官商。由于官吏經商和巧取豪奪對社會發展有負面影響,真宗年間曾加大法治的力度,明令京官、朝官以及州縣官無論是在任還是赴任都“不得將行貨物興販”,“如違,并科違敕之罪”。不久又補充曰:今后“官員使臣赴任不得興販行貨于本任貨賣及在任買物”,不僅禁賣物而且禁買物⑤。幾年后,又令“近臣除居第外,毋得于京師廣置物業”⑥。盡管三令五申,但到仁宗皇祐年間“江淮兩浙荊湖南北等路,守官者多求不急差遣,乘官船往來商販私物”的狀況依舊。北宋末徽宗朝,仍然有“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眾”⑦的記載。南宋后期,官員非法經營鹽、木、米等物貨受到懲處的例子很多⑧。這些都表明,官吏經商十分猖獗,其勢已到了難以遏制的程度,這簡直就是一幅從上至下的百官營利圖。
在宋代,宮廷與市場的聯系更加密切。與唐朝“宮市”走進“市場”不同的是,宋朝將“市場”置于宮廷內,即雜買務和雜賣場的設置;皇室及其相關的人員更多地進入市場。
宋朝初年,“京師有雜買務和雜賣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景祐年間又詔曰“須庫物有闕,乃聽市于雜買務”。這就是說只有在府庫物貨不足時,方能到雜買務購買。但僅在幾年以后。仁宗就對設置雜買務的結果倍感憂慮:“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百姓。”但是,雜買務一方面“非所急物一切收市”,另一方面則“累歲不償錢”,以致“擾人甚也”。于是,仁宗“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下令“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⑨。值得重視的是,雜買務原是主掌購買宮禁所需之物,即“凡宮禁官物所需以時供納”的場所;但是,一旦到了“非所急物一切收市”的地步,這就不得不讓人思索其背后的社會原因。另外,宋代還設有雜賣務,它主掌宮中用不完的物品,“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⑩。從雜買務和雜賣務的設置及其變化可知,宮廷與市場的聯系在逐步加深,宮廷對市場的需求隨社會的發展有增無減。
盡管朝廷一再三令五申“凡禁中須庫物非有闕者,毋得下雜買務市之”⑾,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府庫原有的物資早巳不能滿足宮廷及皇族成員的需要。如真宗年間,御廚所需的
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脫脫等撰《宋史.列傳第八.范質》,中華書局,1977年。
②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7,中華書局標點本。
③ 脫脫等撰《宋史.列傳第四十七。孫沔》,中華書局,1977年。
④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2,中華書局標點本。
⑤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17之19,中華書局,1957年。
⑥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7,中華書局標點本。
⑦ 馬端臨《文獻通考.征榷考一》,中華書局,1986年。
⑧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70之29、70之52、7l之21、73之37、73之61,中華書局,1957年。
⑨ 馬端臨《文獻通考.市糴考一》,中華書局,1986年。
⑩ 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十四》,中華書局,1986年。
⑾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6,中華書局標點本。
羊就要靠陜西市場的供給。所以,時人有“御廚歲費羊數萬口,市于陜西”①的記載。真宗年間,駙馬的家僮“自外州市炭人京城,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以取利,復市于雜買務”②。毋庸細言,一個家僮若沒有皇親這樣雄厚社會背景和經濟實力的支持是無法完成這些活動的。不僅如此,宋朝的宦官較唐朝似乎發展了一步,史載“中人奉使江、淮,多乘官船載私物營利,州縣不敢檢察”③。這些“中人”已經比唐朝的“宮市”走得更遠,從為宮廷掠奪市場發展到自己走進市場,經商贏利。這說明,當社會發展變化不斷刺激著這些皇室成員、其消費和斂財欲望在不斷增長時,市場實際成為宮廷及成員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述史料顯示,由于那些本衣食國家、與市場聯系有限的士卒、宗教人士、官吏、皇室成員等人的積極介入,使宋代從事市場交換活動的人群變得復雜起來了,真可謂為“全民經商”。即宋朝的“經商群體”不再指單一的專職商人。而且,“全民經商”中的“民”不再是狹義的下層民眾或被統治階級,而是包含了相當的上層社會的人群或說統治集團的成員。這樣,宋朝所謂“全民經商”就帶有特殊的含義。而且,因“全民經商”勢頭愈演愈烈,難以阻擋,又成為宋朝商品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一大特點。
二、宋代經商群體構成及其特點
在宋代商品經濟的熱流中,行商坐賈追逐利潤,市場極其活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從上述史料中不難發現,宋朝職業商人以外的社會群體已經紛紛從事經商活動,對市場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專職商人以外的社會群體從事經商活動是唐末五代以來就出現的社會現象,但皆未如宋代那樣普遍和深入、那樣勢不可擋。由于一些原從事其他職業但兼營商業的士卒、僧侶道士、官吏、皇室成員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人員直接而頻繁地參與市場交換,他們也就當然地成為宋代經商群體的不同組成部分。他們雖分屬于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社會等級,從事不同的職業,但卻有一些共同點:
第一,他們都是衣食國家或享受國家優惠政策的群體。
先看宋朝將士。由于宋朝行募兵制,故由國家維持著龐大的常備軍開支。一般說來,一旦有人應招加入兵籍,不僅本人衣食有助,且可以養活家小。有資料說宋朝初期,那些在京禁軍及其家屬“衣食縣官日久”,他們大多“生長京師,姻親聯布,安居樂業”④。不過,在宋朝養兵政策下衣食完全有靠的士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北宋繁盛的仁宗時期,就已有“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給”的情況⑤。南宋初年,那些統兵將官也因“別無供給職田”,出現“日贍不足”的生活危機⑥。盡管如此,兩宋的官兵無論其所處地區的差別,無論其軍種是禁兵還是廂兵,無論其軍階的高低,都有正式俸祿,包含有料錢、月糧、春東衣等名目,還有其他的補助⑦。除去人為盤剝的因素,兩宋軍人總體上是一個享受軍俸、衣食有助的群體。
________________
①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3,中華書局標點本。
②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2,中華書局標點本。
③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0,中華書局標點本。
④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53《兵考五》中華書局,1986年。
⑤ 脫脫等撰《宋史》卷194《兵制八》仁宗康定元年條,中華書局,1977年。
⑥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53《兵考五》,中華書局,1986年。
⑦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軍俸》,中華書局,1983年,第215—235頁。
其次看官僚吏員。宋沿襲前朝制度,官吏皆有俸祿。略有區別的是,宋在建國之初,為了確保封建王朝統治的穩定,曾一度實行“視官制祿,所以養賢官”的政策①。盡管當代學者研究或認為宋代官員的俸祿很高,生活無憂②;或認為人不敷出,生存不易③;或認為收支基本平衡④,意見并不統一,但無論怎樣,宋朝官員是享受國家俸祿的群體沒有疑問。
再看皇室成員。在中國歷朝歷代,這都是一個經濟上寄生性最強的群體。如果說軍人和官員由于薪俸含實物與銅錢,需要到市場購置日常生活所需物品,那皇室成員由于長期以來其生活資料幾乎全部來源于各地對中央的貢奉,所以他們與市場的聯系最為稀疏。這是一個享受國家最優待遇、衣食無憂的群體。
最后看寺觀及其成員。由于佛教、道教在中國社會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歷朝歷代對它們皆實行各種優惠政策,不僅專門撥付維持其生計的土地,還予之減免各種稅收的待遇。在國家和善男信女的扶持下,寺院和道觀除了是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外,還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僧侶道士們也因此是享受國家和社會奉養的群體。
第二,他們從事不同的職業,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但都兼事經商活動。
歷朝歷代的軍人,禁衛京師,戍守邊地,保家為國,維護政權的穩定就是他們的職責。但因軍人有軍階的差別,所以也就有軍人地位的差異。在上述各群體中,下層士兵的地位最低。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多數士卒無權無勢,既無政治地位也無經濟實力,在軍俸不能保障其生活的基本條件時,營運牟利成為其生存的重要手段。這一群體與市場的關系十分密切。如前文提到的綱卒,其營運經商的路線隨著綱舟所到而向東西南北延伸;其在此地賤買又到彼地貴賣;其銷售的物貨無所不有。還有資料證明,營運販賣不僅是在籍士卒補貼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他們解除兵籍以后的生活支柱。比如在宋神宗年間曾經整頓軍制,裁汰兵籍冗員,允許年“五十以上愿為民者聽之”。對那些解除兵籍和職事的在京禁軍士卒,“聽其自便在京師居止”。據載當時“免為民者甚眾”,乃至“冗兵由此大省”⑤。由此可知當時裁汰為民的士兵不在少數。至于當時究竟有多少士卒留居城市我們不得而知,但那些解除兵籍并留居城市的人員,其謀生的主要途徑大多是參與市場活動應當不差。《夷堅志》載:“京師修內司兵士闞喜,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賣果實自給。”⑥可以說,在城市消費群體龐大、消費需求增加的社會條件下,如闞喜這樣充當小商小販等服務性行業以自足的人肯定占有相當比重。對那些社會地位稍高的軍官們來說,除了軍俸的不足外,也受當時社會形勢的影響。在利益的驅動下越來越離不開市場。軍官們的經商活動已如前所述,此不贅言。
僧侶道士這一宗教群體,常常因為各個歷史時期國家以及皇室貴族信仰的認同而身份特殊,可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唐宋社會轉型在宗教方面就表現為由出世向人世的變化,以及經濟上由倚重耕織結合的自給自足走向市場經營,此前僅以土地作為財富標志的狀況發生變化。前文所引開封大相國寺內道士、師姑和僧侶們的行為就是生動的寫照。而在寺院手工業經濟里,天下聞名的“寺綾”也已從自我消費走向了市場⑦。
_______________
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征榷考六》,中華書局,1986年。
② 邵紅霞:《宋代官僚的俸祿與國家財政》,《江海學刊》,1993年第6期。
③ 何中禮:《宋代官吏的俸祿》,《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④ 張全明:《簡論北宋官員的俸祿制度及其特點》,1998年宋史年會參會論文。
⑤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53《兵考五》,中華書局,1986年。
⑥ 洪邁《夷堅志》乙志卷11《米張家》,中華書局,1981年,第275頁。
⑦ 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6頁。
官吏自產生之日就承擔起管理一個國家或政權方方面面事務的職責,屬管理階層。宋朝由于官和吏的差別、官階的高低、差遣職任的不同,官吏的社會地位高低有別。一般說來,品官地位高而吏的地位低,官階越高地位就越高,掌管實際職事的差遣官的地位又高于有官階而無職事的官等。但正如前文所引,這一群體中各級官吏亦官亦商的現象十分普遍,正如史料記載的那樣“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眾”①。
皇室成員在帝王至尊無上的光環籠罩下,處于社會金字塔的頂尖部位,地位顯赫。他們與市場之間那種若隱若現的聯系,在唐中后期隨著宮市的出現變得逐漸明朗起來。宋朝雜買務和雜賣務的設置、皇室成員以及中人直接經商贏利都說明市場較前代更進一步滲透到宮廷的生活中。
第三,他們的經商活動大都違背傳統道德,且為國法所不容。
由于軍人、官吏衣食國家,各有公干,為國家和社會盡心效力是他們的本分。僧侶道士各自尊奉的宗教教義本身也以淡泊名利,慈悲為懷,與世無爭為基點。但是,兼事營運首先以贏利為目的,違背了傳統的“君子不言利”的道德規范。在追逐錢財利益熏心的同時,也必然伴隨著欺詐、以強凌弱、大魚吃小魚等不良動機和行為。有宋一代,兼事經商一方面被視為與民爭利之事,另一方面更因為由此浸壞軍政和敗壞吏治,最終將危及王朝的統治,所以也為國法所不容。可事實上,一方面朝廷屢下政令,禁止官吏赍輕貨邀厚利②、禁止官員置物業③等,但另一方面官吏、軍人因為經商贏利而受到懲處的記載不斷:
如宋太祖乾德元年,“海陵、鹽城兩監屯田副使張藹除籍為民,……坐令人赍輕貨往江南兩浙販易”④。開寶八年,太子洗馬周仁俊被貶為縣令,“坐知瓊州日販易規利故也”⑤。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樞密直學士邊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強市民羊,……坐奪三任”⑥。宋仁宗嘉枯六年,“蕭固追三官,勒停廣南西路轉運使”,“坐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揮人兩浙商販私物”⑦。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龍神衛舊廂都指揮使、興寧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特降一官,以前任江東副總管日私販貨物”⑧。孝宗乾道四年,“詔湖北轉運判官王次張放罷,以言者論其積貨營私故也”⑨。寧宗慶元元年,“淮東提舉陳損之、運判趙師筭并放罷。知揚州錢之望特降直徽猷閣。以臣僚言損之盜官鹽販往江上,得錢買貨人蜀。師筭往上江買木,結籐就真州出賣,侵奪商賈之利。之望將備邊椿積之錢糴米,博賣營運”⑩。寧宗開禧三年,“主管殿前司公事郭呆放罷。以臣僚言其*[外門內音]庸貪黷,專務營私”⑾。如此種種,不勝枚舉。官吏和軍人濫用職權,利用公務之便倒賣官物、挪用公款、強買強賣、假公濟私等非法行徑可謂猖獗到了極點。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征榷考一》,中華書局,1986年。
②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中華書局標點本。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17之19—20、食貨50之3,中華書局,1957年。
③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7,中華書局標點本。
④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中華書局標點本。
⑤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中華書局標點本。
⑥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7,中華書局標點本。
⑦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4,中華書局標點本。
⑧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70之29,中華書局,1957年。
⑨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71之21,中華書局,1957年。
⑩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73之61,中華書局,1957年。
⑾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73之37,中華書局,1957年。
上述資料表明,這些衣食國家或享受國家優惠政策的群體,無論從政治地位或經濟生活上原與追逐利潤的商人不一樣。但是這一群體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早已忘卻自身的身份、職責和地位,根本無視國家的法律和傳統道德。他們為利益的驅動紛紛擠進市場。與此前不同的是,無論他們原來的身份如何,無論是否存在以權壓人的情況,他們一旦走進市場,市場自身的規則就要求他們必須改變原來的身份,只作為市場中的買方或賣方。他們不可以憑借權力白拿白占他人的東西,必須依照市場的規則與他人進行大致公平的交易。在市場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里,他們的行為基本上與職業商人相同,由此使得宋朝經商群體的構成不僅有職業商人,而且有相當數量的非職業商人。 三、宋代“全民經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宋朝經商群體構成的復雜化是歷史發展所使然。兩宋繼唐末五代后,一直處于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轉型時期。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諸多變化,比如土地制度從原來以均田制為代表的國有制為主,發展到宋朝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得土地私有制迅速發展;農民起義從過去的反暴政轉向求均平;思想文化方面從過去的遵從道德規范轉向追求自我心性的張揚等等,這些都顯示出一種反傳統的特征。本文所說的“全民經商”及經商群體變化。實際也是一種反傳統的現象,且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全民經商”態勢的形成,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市場猶如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著宋代不同的社會階層。這是不以個人意志或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宋朝社會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市場的磁力迫使不同的社會階層對其做出相應的回應。當時代潮流不可阻擋時,順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不僅只是工商業者的責任,而是全社會的責任。
工商業者對市場有本能的反應,從事商品生產與交換是他們的本職,作為市場的主要群體,他們肯定會不失時機地抓住機遇。不過,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本身的局限以及自漢武帝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重農抑商”傳統觀念的影響,商人階層受到社會的歧視,大多仍屬于社會的下層。而且在實際的市場交換中,個體商人的活動常常受政府的局限,或說必須在政府的規范下進行。以宋代行會為例,說明私商活動和作用的局限。然而,宋朝社會的發展以市場發展為表征之一。時常需要更多的物品和更多的經營者。于是,在物質利益和金錢的驅動下,宋朝那些原本不應卷入市場的人群已經為市場的魅力所動,他們以不同的經營方式融人商品大潮:皇室雖然在需求增大和利益的驅動下走進市場,但往往憑借其優越的社會地位而無視市場規則,偷稅漏稅,巧取豪奪;官吏憑借在國家機構任職或辦理國家事務之便而從事經商活動,利用權力假公濟私;軍隊下級官吏和士卒經商則多為生活所迫,但許多也是在利用執行公務的情況下贏利;宗教人士無視教規教義,與世俗社會一樣追逐金錢。顯然,為更加廣泛的社會群體所構成的經商群體,無一例外地以追逐市場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在此,我們暫且忽略這些政治上或經濟上皆享有國家和社會優惠待遇的群體無視國家法令、違背傳統道德的一面,充分認識他們參與市場活動的意義在于其走進市場的那一刻。即當各界人士在市場里充當“商人”的角色時,商人“這個革命的要素”就必然承擔起打破地域封閉、物貨不通、城鄉各自為陣的自然經濟狀態的任務,和生產者一道起到推動社會發展進程的作用。特別是宋王朝的商品經濟雖然有明顯發展,但從事個體工商業者的力量還遠沒有發展到可以在不長的時限內扭轉時局或改變傳統勢力的地步。在時代需要更多商人的形勢下,非職業經商群體的行為就有極大的合理性并能發揮出特定的作用。
其次,宋朝經商群體各組成部分由于各自生存環境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在市場的交換層次,同時也預示了他們進入市場后的發展勢頭。
宋代軍人雖然衣食國家,但大多處于社會的下層,沒有政治特權,更談不上經濟實力。生活上,他們常有“日贍不足”之患,只得靠經常的營運、販賣所獲利潤來維持和補充生活。他們的經商活動一旦被禁止,其生活就會受到威脅。為了生存,他們與市場的接觸較上等社會的人要頻繁得多。顯然,這是一個為了生存走進市場的群體。應當說,他們對市場的依賴同普通市民一樣,參與市場是生活所使然。為生存而進入市場,本身就有天然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由于他們社會地位卑微,經濟能力有限,只可能從事細碎而規模不大的交易。
__________________
①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冊,《宋代寺院所經營之工商業》,(臺灣)新亞研究所。
僧侶道士從事營運的行為與宗教日益世俗化密切相關。比如宋代以前寺院經濟立足于土地,土地就代表財富。而隨社會經濟的發展,寺院經濟也轉向寺院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財富的基礎“除了土地以外,工商業也是其中的主要份子”①。其實,這樣的變化是整個世俗社會經濟的必經歷程。宗教雖然在精神世界高于世俗,但在現實生活中從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脫離世俗。宗教的世俗化必然包含其經濟生活的世俗化,所以宋朝凡界的市場生活會在宗教生活中再現。由于這一群體為數不多、工商業活動有限,所以其對市場的影響不大。
皇族處于社會的上層,或為追求利潤的心理所驅使,或為保持住以往生活的最優越狀態而進入市場。這個政治和經濟上享有特權的群體,參與市場活動的意義不能僅從其是否遵從市場規則、是否還有強權成分的方面看,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們走出宮墻的那一刻,以及他們對市場的需求和認可。由于這一群體享有極尊貴的地位并擁有豐厚的物質財富,一旦走進市場就易使經營形成規模且能加速商品流通的過程。
官吏是社會的管理層,在宋朝非職業經商群體中也是最有政治和經濟實力的群體。他們在經商營利過程中的違紀違法無疑影響了王朝的政治清明,但其經商營利的動機和事實較其他群體更有意思。在我看來,在宋朝那樣的社會環境下,官員的經商贏利行為也許不能簡單評價或僅僅持批判態度。之所以這樣說,是我將這個群體視為領導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較之皇室成員不同的是,他們是國家政權機構的管理者而不是政權的寄生者。他們生活在一個與外界社會或說與廣大市民更為接近的圈子里,常常可以根據社會或大眾的需要充當國家政策的調整、制定和執行者。由于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有較強的、對社會的認知能力。所以,當社會處于轉型的時候,這個群體因其所處的社會地位,可以最先感受到社會的變化、時代的需要和最新的信息。他們和商人一樣,可以最先或說最敏銳地感受到商品經濟那種不可阻擋的力量。但他們與商人不同,常常具有較商人優越的政治地位。一旦具備經濟條件,他們的經商贏利活動較商人有更大的影響力。盡管官吏經商中有許多不規范的操作,不符合市場的原則,但其權力使其商業活動在較短的時間內所能達到的廣度和深度是商人無法與之相比的。試想,在一個“重農抑商”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里,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里,如果不是官員,難道還有什么社會力量比之更有社會地位且更貼近社會呢?前面的資料也表明一點,這一群體介入市場后,和商人一樣奔走于各地,參與各種交換、置辦各種產業,宋代的市場也因此而活躍。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第三,“全民經商”態勢的發展不僅對當時社會的市場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那些原來衣食國家的、社會地位優越的群體參與經商行列,更說明社會進步意識不斷沖撞著舊傳統中落后而頑固的堡壘,具有進步意義,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會更快地向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尊崇“重農抑商”、“學而優則仕”、“天下惟有讀書高”等觀念,它們對社會影響之深入,不僅使得個人的觀念如此,即使是國家選拔管理人才和制定政策都未能擺脫其束縛。由此,上層社會群體以及國家就成為這些傳統落后觀念的最頑固的捍衛者。客觀地說,對商人和交換活動的蔑視在一定程度上是制約和影響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社會的發展進步是離不開商人的活動的。當宋朝上層社會直接進入市場、目標直指市場的最大利益時,市場交換已經超越了其他群體那種僅為求生存而被迫走進市場的水平,在持定時期下(持別是市場發展不成熟的情況下),作為統治集團的成員,官員經商的行為從客觀上和思想上都是對過去蔑視商人營利的傳統觀念的挑戰,是對自漢武帝以來一直占據中國社會主導地位的“重農抑商”傳統的反叛。而且,由于這一群體具有政治地位,且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一群體的行為對社會的影響力可以超越其他群體。從另一個側面看,當市場擁抱社會的時候,利用權力來獲取貨幣也許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原始資本積累的一種形式。而官員對金錢的崇拜實際上也是對中國古代等級社會、對“天下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等傳統的否定。拜金主義是不能提倡的。但在封建等級森嚴的古代社會,這一群體通過對市場的認識和參與,實際承認了金錢面前人人平等這個最基本的市場原則,他們已經進入一個自我否定的階段。如果我們將所有這些現象放到中國歷史的長時段中考察,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就更加清晰了。它確實表現出古代社會進步的程度。
第四,宋朝國家政策不斷調整變化,一方面表現出政權也處于對新形勢的適應階段,另一方面國家政策的調整在客觀上鼓勵了“全民經商”態勢的發展。
在唐宋社會處于重要轉型期的形勢下,不僅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市場有各種反應,朝廷也是如此。面對唐末五代及人宋以來各階層開始經商的社會趨勢,無論宋統治集團愿意與否,在朝廷不斷懲治官員違法營利行為的同時,實際上對一些難以解決或制止的問題也采取了默認的態度。
宋朝廷不僅依然行使中國歷朝歷代對高官、寺院等免稅優惠的政策,而且還進一步擴大了免稅的范圍,恩及普通階層。其中與“全民經商”相關的、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對綱運攬載貨物販運的免稅。史料記載:“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貨物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①當然,朝廷對綱船經商的認可是有條件的,即“但不妨公,一切不問”,而且必須做到“官物至京無侵損爾”②。這是宋朝廷對唐末五代以來綱卒經商事實的認可,無疑會鼓勵宋朝綱卒的經商行為。在仁宗時期,有司奏請“糧綱舟卒隨行有少貨物經歷州縣,悉收稅算,望與蠲免”,獲準③。也正是因為這樣,仁宗朝發運使的權力日益膨脹。他們總攬六路上供糧物事宜,因“文移坌并、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在
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5《國用考三.漕運》,中華書局,1986年。
②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5,淳化五年二月條,中華書局標點本。
③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17之15,中華書局,1957年。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8,嘉祐三年十一月條,中華書局標點本。
這里,宋朝的政策無疑對綱卒經商泛濫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由于國家政策的許可和優待,且使綱卒上下皆有利可圖,那些不辭辛勞的挽舟之士卒愿為區區利益,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①。
由于綱卒經商帶有集體操作、上下聯手的特點,所以也帶有官吏經商的性質。全漢昇先生曾經對官吏私營商業歸納為幾點:以公錢作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舟販運;利用公家的勞力;藉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逃稅,并由此認為,官吏私營商業的影響皆是不利的,即官吏暴富;政府損失;商民受害②。全先生的總結切中官吏私營商業的弊端。即便如此,這在宋朝社會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對綱卒經商并得以免稅這樣的事情,官員們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弊,即“緣路雖失商稅”,但“京師坐獲富庶”。國家吃了虧。但個人及地區富裕了。當然,在綱船免稅等政策實施的同時,也受到其他官員的抨擊。同樣是仁宗朝,嘉祐五年又采取“汴綱不得復人江”,“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等限制綱船攬載貨物營運的措施,但結果確是不僅使京師“失商販之利”,而且“汴綱工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③……
上述資料說明,面對社會規范和社會需要的沖突,特別是對日益活躍的市場,宋朝廷的政策處于調試階段。同時,上述例子還提出一個令人思考的問題是,即面對無法阻擋的市場沖擊,國家的一紙禁令究竟有多大的效用?“堵”還是“疏”,何者更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呢?當然,從穩定政權統治的方面看,官員經商是吏治敗壞的表現。它在摧毀傳統不良觀念和行為舉止的同時也破壞了良好的道德規范。在參與市場的同時因其違背公平競爭等市場原則,因而又有其不利于社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一面。從理論上講,社會應當對此具有快速反應,即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套法規法制限制以致最終杜絕官吏經商,保證社會的良性循環,但是,這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社會歷程。迄今為止,如何杜絕官吏經商并保證市場正常發展的問題仍然是困擾中國的社會問題。
綜而述之,宋代“全面經商”態勢的形成及經商群體構成的復雜化確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唐宋社會轉型期,當長期受到貶斥的職業商人還未形成一個強大的、足以推動社會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社會力量時,社會的發展急需更多的商人。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非職業的經商群體實際起到補充的作用;同時也豐富了市場并推動了市場的發展。在歷史的長時段中,那些上層的非職業經商群體進入市場,更顯出他們對自我的否定,以及對以往重農抑商等落后傳統的挑戰和反叛。這些,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所以,應當給予客觀和積極的評價。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5《國用考三.漕運》,中華書局,1986年。
②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冊,《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臺灣)新亞研究所。
③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5《國用考三.漕運》,中華書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