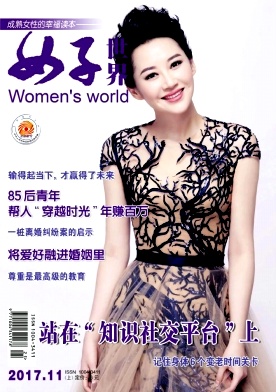宋代地主制經濟的特權性
姜錫東
地主制經濟的核心,是地主階級。探討地主制經濟,重點應放在地主階級及其租佃者、雇傭者上面。
宋代的地主階級,若按占田多少可分為大、中、小三個階層,若按政治身份可分為官僚地主、庶民地主①兩個階層。兩宋時期(960—1279),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官僚地主。這是因為,在宋代的各種土地所有制中,占優勢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對此,筆者在《試論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文中已有論證和說明。②所以,宋代地主制經濟的核心問題,便是官僚地主及其經營活動。
對宋代對主階級和地主制經濟、以及由此決定的宋代經濟的特點,例如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租佃制、租賃制的盛行和干人階層的出現為標志;土地所有權轉移的頻繁;工商業的相對發達等,史學界已做了不少研究論述,比較重視。但對宋代地主制經濟尤其是官僚地主經濟活動的特權性,探討的不多。
宋代地主制經濟(主要是官僚地主經濟活動)的特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依靠政治權勢獲取田地
在封建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宋代的士大夫們,更是把土地視為“衣食之源”③和“致富”之源④,千方百計地獲取土地。“宦游而歸,鮮不買田。”⑤武將們也不甘落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楊存中等高級將領都有大量土地。如果文官武將們獲取土地的方式都是通過買賣,并且是平買平賣,那是無可指責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馬端臨總結秦漢至兩宋土地兼并的情況時說:“田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貲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⑥漆俠先生指出:“宋代土地兼并也主要的是這兩種方式:所謂‘貴者’,是憑借政治特權占有大片田產;所謂‘富者’,是憑借雄厚的貨幣力量購置大批良田。當然,這兩者還可以結合起來,成為再一個方式。”⑦憑借政治特權占田得地的人主要是官僚地主。其手段和途徑,大致有如下三種。
______________
① 庶民地主,亦可稱為民庶地主。現在看來,稱庶民地主更好一些。
② 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三期。后收入漆俠先生主編的《宋史研究論叢》第三輯,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③ 《隆子集》卷7,《韓億傳》。
④ 葉夢得:《石林治生要略》。
⑤ 袁燮:《絮齋卷》卷16,《叔父承議郎通判常德府行狀》。
⑥ 馬瑞臨:《文獻通考》卷l。
⑦ 漆俠:《宋代經濟史》上冊第24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國經濟通史·宋代經濟卷》(上)第278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一)恃勢霸占
倚仗權勢霸占民田,是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最惡劣的一種手段。在四川嘉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①“(呂)惠卿之舅臨簿鄭膺,始寄居秀州華亭縣,以惠卿之故,一路監司如王庭老之輩皆卑下之,而招弄權勢,不復可數,至奪鹽亭戶百姓之地以為田。”②天章閣待制、提舉洪州玉隆萬壽宮曾考蘊,在池州“干擾州縣,侵奪民田”。③宋徽宗時的“六賊”之一朱勔,“田產跨連郡縣,歲收租課十余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為用,莫敢誰何。”④朱勔掠奪的對象,已不限于普通百姓。宋高宗時,王歷“寓居撫州,恃秦檜之勢,凌奪百姓田宅,甚于盜寇,江西人苦之。”⑤這僅僅是被公開揭露出來的幾個事例,是冰山之一角,未被公開揭露出來的會更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僚地主們,還把魔爪伸向國有土地。“贍士公田,多為形勢之戶侵占請佃,逐年課利人于私家,以致士子常患饔廩不給。”⑥宋孝宗乾道元年三月,“戶部言:浙西所管營田官莊,共一百五十九萬余畝,內有未承佃六十七萬余畝。緣上件田產,皆系肥饒,多是州縣公吏與形勢之家通同管占,不行輸納租課。”⑦朱熹說:“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海、涂溪、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官戶、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⑧這類事例和史料還有不少,恕不畢舉。上述事例已足以暴露出官僚地主寡廉鮮恥、霸田占地的丑惡嘴臉。官僚地主們不用花錢就可以占田得地,靠的是手中的權勢。
(二)仗勢強買
霸占行為畢竟有失身分,過于露骨、丑惡,極易引起民憤,士大夫們也想找塊遮羞布,也想打起“買”的旗號。然而,他們的購買行為,卻經常變成仗勢強買。種放曾以隱逸不仕而名聞朝野,后來卻暴露出奸橫不法的本來面目:“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瓷橫。”⑨宋神宗時,呂升卿兄弟曾“居喪潤州,嘗令嘩亭知縣張若濟置買土田。若濟遂因此貸部民朱庠、衛公佐、吳延亮、盧及遠、押司錄事王利用等錢四千余貫,強買民田。”⑩據劉安世揭露:章惇用他兒子的名義,將蘇州昆山縣“朱迎等不愿出賣田產,逼脅逐人須令供下愿賣文狀,并從賤價強買人己。”⑾南宋時,關于官員“強買民田”的記載也不少。⑿他們究竟怎樣強迫,如何逼脅,陸游之子陸子通的作法可謂一個典型事例:他“以福賢鄉圍田六千余畝獻時相史衛王。王以十千一畝酬之。子通追田主索田契,約以一千一畝。民眾相率投詞相府。訴既不行,子通會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廬。眾遂群起抵拒,殺傷數十人……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灌以尿糞,逼寫獻契,而一金不酬。”⒀他們不僅強買民田,也“強買官田”。⒁上述事實反映出,宋代官僚地主在兼并土地時,仗勢強買的情況是很嚴重的。由于他們披上買賣的外衣,比前述的恃勢霸占行為更有欺騙性,因而更不易被公諸于世。強買的本質在于賤價、壓價,而“賤價強買”與恃勢霸占只有一步之遙,陸子通的所作所為便是如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95,《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志銘》。
② 《長編》卷269,熙宋8年10月庚寅。
③ 《宋會要輯稿》職官邱之38。
④ 胡舜陟:《胡少帥總集》卷1,《再劾朱勔》。⑤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4,紹興23年3月癸丑。
⑥ 《宋會要輯稿》食貨5之26。
⑦ 《宋會要輯稿》食貨61之29。
⑧ 《晦庵集》卷99,《約束侵占田業榜》。
⑨ 《宋史》卷457,《種放傳》。
⑩ 魏泰:《東軒筆錄》卷5。
⑾ 劉安世:《盡言集》卷5,《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⑿ 參見《宋會要輯稿》職官70之23,29等記載。
⒀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
⒁ 《宋會要輯稿》職官72之17。
(三)利用權勢計取巧奪
據朱或記載:“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錢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①乘別人困難之機而兼并其田產的官員不止蘇掖這一個。如宋高宗時的同知樞密院事同麟之,“貸錢與強知文者,乘其急而索其數倍之息,得田四百畝。”②南宋后期,吳縣農民嚴七七“有田七畝,盡典在李奉使邊”,因“欠租”,不得不“將上項典業作賣契折還。”③宋代很多庶民地主和自耕農,由于難以承受差役、夫役和各種苛捐雜稅的沉重負擔,不得不將自家田產低價出賣或投獻于官僚地主。早在乾興元年就有“上封者”說:“人戶懼,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若不禁止,則天下田疇半為形勢所占有。”④這種趨勢,不幸被他言中,確實愈演愈烈。紹興元年權戶部侍郎柳約說:“比來有司漫不加省,占仕籍者統名官戶。凡有科敷,例各減免,悉與編戶不同。由于權幸相高,廣占隴畝。”⑤淳祐六年,謝方叔說:“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曰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⑥一般民戶為逃避苛重的賦役而把田產轉移給官僚地主,呈日益加劇之勢。有的是民戶主動投獻,有的是官僚地主逼迫,有的則是官僚地主設計謀取。例如在仁壽縣,“洪氏嘗為里胥,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為若稅,免若役’。鄰喜,劃其稅歸之,名于公上。逾二十年,且偽為券,茶染紙類遠年者以訟。”⑦他們利用此類手段兼并的對象,主要是普通民戶,但達官貴人也以此兼并低小官吏之地。如宋高宗時,石邦哲為向宰相湯思退謀求差遣,“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非,命翥(湯的女婿)取元金而還其田。”湯思退實際上卻掌握田契不還,給石邦哲除授福建參議官。石邦哲是“田與金皆不可得”。⑧宋朝政府有禁止官戶承佃官田的規定。但官戶卻采取“詭名”(以代理人出面)的計策繞過禁令,承佃官田,并且拒不交租,長期占據。宋孝宗時,“臣僚言:在法:品官之家不得請佃官產。蓋防權勢請托也。今乃多用詭名冒占,有數十年不輸顆粒者。逮至許人劃佃,則又計囑州縣,不肯離業。”⑨說明這種情況是比較嚴重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朱彧:《萍洲可談》卷3。
②《系年要錄》卷191,紹興31年7月己丑。
③黃震:《黃氏日抄》卷70,《由縣乞放寄收入狀》。
④《宋會要輯稿》食貨63之169。
⑤《宋會要輯稿》食貨6之1。
⑥《宋史》卷173,《食貨志》。
⑦《李覯集》卷30,《江公墓碑銘》。
⑧《系年要錄》卷187,紹興30年2月丙午。⑨《宋會要輯稿》食貨6l之30至3l。
上述三種土地兼并的做法,基本上是宋朝法令所不許的,也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但作為統治階級的當權派,作為一個特權階層,這些法令和譴責,對他們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當然也不可否認,官僚地主內部在地位、權勢、財力、素質等方面是參差不齊的,并非鐵板一塊,有不少官僚是以合理合法的形式獲取土地。總的來看,宋代官僚政治的演變趨勢是曰益腐敗,清廉官吏較少,貪官污吏較多,采用卑鄙惡劣的違法手段兼并土地者比例更大一些。同時還應該看到,采用霸占、強買、計取手段兼并土地者,不可能僅僅局限于官僚地主,其他階層尤其是那些豪橫惡霸之家也不乏此類行徑。但官僚畢竟是官僚,官僚地主擁有其他階級階層所沒有的特殊權勢,采用惡劣而低廉的手段大肆兼并土地的便利條件更勝一籌。所以,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說:“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①顯而易見,權勢在宋代地主階級土地兼并中的特殊作用,實在不可低估。 二、依靠政治權勢減免賦役,逃稅抗稅
兩宋時期,富貴者田產多而稅役輕、貧窮者田產少而稅役重的現象,一直嚴重存在,難以革除。這種極不合理的社會弊病,主要是由官僚地主造成的。
早在宋太祖建隆四年的詔書中就提到“見任文武職官及州縣勢要人戶隱漏不供(賦、稅)”問題。②開寶四年閬州通判路沖上奏說:“當州稅租,多違日限。蓋本州曹吏,倚以形勢,遷延不納,亦有一戶庇三戶者。”③宋太宗在淳化四年嘆息說:“今州縣城郭之內,則兼并之家侵削貧民;田畝之間,則豪猾之吏隱漏租賦,虛上逃帳,此甚弊事。”④太祖、太宗兩朝是宋代懲治貪官污吏最嚴厲、政治狀況比較好的時期,官僚地主們抗稅逃稅即已如此嚴重,以后的情形更是變本加厲、日益猖獗了。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說:“然人言:天下稅賦不均。豪富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地薄而稅重。”⑤據《治平會計錄》的說法,當時中央所統計的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傾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⑥由此反映出,在此之前的抗稅漏稅之弊已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而其主兇,則是官僚地主。宋徽宗宣和元年十二月的一道詔書中說:“豪右形勢之家類蠲賦役而移于下戶。”⑦偽齊官員揭露北宋末期的社會弊端時說:“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略稅畝,至有人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于貿易,儲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于賣妻鬻子、死徙而后已。官司攤逃戶賦時,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⑧南宋時,此弊不僅沒有絲毫好轉,反而更加劇烈,相習成風。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的赦文中說:“訪聞州縣催理稅賦,多因形勢官戶胥吏之家不輸納,或典買之際并不推割,產去稅存,無從催理。”⑨南宋中后期,王柏當時的惡劣現象說:“今州縣大家,以不納常賦為雄。”⑩“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為能,相習成風。”⑾上述官僚地主的逃稅抗稅行為,是違法亂紀的。也有一些權貴的免稅,是皇帝批準的。前述王蒙正“特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⑿宋高宗賜田給大將李顯忠六十三頃,“依薛安靖例,放免十料租稅。”⒀宋度宗咸淳十年,侍御史孫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上奏中說:“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
______________
①《宋史》卷173,《食貨志》
②《宋會要輯稿》食貨70之2。
③《宋會要輯稿》食貨70之3。
④《長編》卷34,淳化4年2月戊子。⑤《宋會要輯稿》食貨63之165。
⑥《文獻通考》卷4,并參見《宋史》卷173。
⑦《宋會要輯稿》食貨4之14。
⑧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82。《系年要錄》卷65。
⑨ 《宋會要輯稿》食貨9之29。
⑩ 王柏:《魯齋集》卷17,《答季嚴州》。
⑾ 王柏:《魯齋集》卷5,《送曹西淑序》。
⑿ 《長編》卷11l,明道元年1月己丑。
⒀ 《宋會要輯稿》食貨61之49。
蠲二稅。”①總的看來,宋代皇帝批準減免賦稅的官僚地主戶數和次數并不多,但每家占田數量卻不少,影響很壞。宋代官僚地主減免賦稅以違法手段為主。
至于正稅之外的各種苛捐雜稅和攤派,官僚地主也竭力逃避,把這些沉重負擔轉嫁到其他民戶頭上。屬于攤派性質的“科配”,在宋神宗至宋高宗時期,曾允許部分官戶在一定范圍內減免。但據紹興元年十二月權戶部侍郎柳約說:“比來有司漫不加省,占仕籍者,統名官戶。凡有科敷,例各減免,悉與編戶不同。”②紹興十七年有臣僚指出:“今日官戶,不可勝計。而又富商大業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幸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須者,比比皆是。”可知,至少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官僚地主合法或違法減免科配問題是比較普遍的。
宋朝長期實行“市糴”(和糴)政策,由政府出錢財購買糧草。但具體實施過程中的情況很復雜,有時不付款或低價而強制征取,成為一項似稅非稅的負擔。除個別例子外,按宋朝規定,“官戶及權勢之家并與乎民一等科納。”④可謂士庶無別。但實際情形又如何呢?南宋時,陳謙“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訴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并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⑤說明某些官僚地主是享有免市糴特權的。另外,宋代的“和預民綢織”(和買)制度演變成一種賦稅后,有的官員家庭也拖延不交。如宋寧宗時,臨安府仁和縣“有韓尚書戶所敷和買,連歲送納,多是不足。蓋其家韓杖者,見任本府通判,輕視屬縣,敢為拖延。縣乃申杖,杖大怒,輒追縣吏及里正囚系決罰,備劇慘毒。”⑥。
熙寧四年普遍改革職役制度,改差役為募役。原應服役之人,按等出錢免役;原不應服役之人,也必須出錢,稱“助役錢”。役錢實際成為又一種賦稅。但是,官戶比鄉村上戶享有減半的特權。后來。該項特權有時縮小,有時取消。但到宋孝宗乾道二年,戶部侍郎李若川、曾懷上奏說:“官戶比之編民,免差役,其所納役錢又復減半,委是太優。”建議“令官戶與編民一等輸納,更不減半。”⑦得到批準。宋寧宗開禧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臣僚言:臣聞賦稅均平,則通行無弊。后除者眾,則名始告病。夫天下所謂占田最多者,近屬勛戚之外,寺觀而已。和買、役錢,與夫諸色雜科之類,皆因畝頭物力起敷。近屬勛戚,或有所挾。而寺觀亦間出于一時之橫恩,乃以特旨而蠲免。今近屬勛戚之家既免之矣,旁及姻親,詭名隱寄,并緣為奸,亦從而脫減。……”⑧這些所謂的“近屬勛戚”,地位高,田地多,反而“以特旨而蠲免”,并且趁機庇護他們的姻親也逃避役錢等。
宋代的職役(差役),被普遍視為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按宋朝政府的規定,官戶也在一定范圍內免差役:“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侄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為官戶;身亡,子孫并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及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⑨就是說,即使是官僚地主的上層——品官之家,也不是可以一概免差役,也有田地數量和身份高低之類的嚴格限制。然而,法令規定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實際情況,二者之間相距甚遠。乾興元年十二月“上封者言”中就曾提到:“且以三千戶之邑五等分算,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約千戶。官員、形勢、衙前將吏不帝一二百戶,并免差遣。”⑩觀全文可知,此處的差遣,就是指差役而言。差役轉嫁到貧窮的中下戶頭上,負擔不均。所以王安石變法時改用募役法,情況大有好轉。但南宋時,故態依然。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大理評事趙善養說:“官戶田多,差役并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小貧下之民。”⑾淳祐六年謝方叔又說:“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前引)。在這種情況下,宋朝實行了“限田”政策,只準許官員在田畝數額限制之內免差役,限外不免。但利欲薰心、奸詐不法的官員們總是殫思竭慮地突破限制,“雖申嚴限田之法,而所立官品有崇卑,所限田畝亦有多寡。品官田多,往往假名寄產,卒逃出限之數。”⑿結果,出現“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數過者極少”⒀的局面。宋代官戶的免役特權,一是來自政府的允準,是合法的。二是來自私下謀取,是違法的。不論合法還是違法,其實都來源于他們的特殊身份。 三、倚仗特殊身份,突破禁令,違法經營工商業
中國古代有土、農、工、商之區分。官僚士大夫們主要從事行政管理事務,不應再去親自經營私家工商業。宋朝政府并未完全禁止官吏經營私家工商業,而是做出很多限制。宋太祖乾德四年五月曾下詔,命令官員“自今其勿復令部曲主掌事務,及于部內貿易,與民爭利。違者論如律。”⒁這是禁止官員在自己管轄范圍內(部內)擅自經商,此后基本沒有改變。宋太宗至道元年三月又下詔禁止“文武官僚敢遣親信于化外販鬻。”⒂不許官員委托代理人擅赴海外貿易。宋真宗咸平四年“詔京朝幕職官、州縣官,今后在任及赴任、得替,不得將行貨物色興販。”⒃就是說,官員不僅在任職期間,即使在赴任、離任的過程中,也不許擅自經商。宋代官府收購糧草,有時稱作“人中”。宋太宗端拱二年九月下令,允許“客旅”向京城開封的官倉出賣糧食,“所有食祿之家并形勢人,并不得人中斛斗,及與人請求折納。”⒄但向其它地點出售糧草并未禁止。熙宋九年二月規定:“自今應官員及子弟并舉人,非見有熙河路本貫,輒至彼中納糴請官物者,徒二年。”⒅宋仁宗天圣七年時,曾嚴厲禁止官員“將職田、月俸及粗弱糧草假立他人姓名中納入官。”⒆宋徽宗時又下詔,對官吏們“緣糴事循私意,公受請托……詭名借本,停塌人宮……;強糴攪拌,低估贏略,計會中納……抑勒軍兵,賤買交旁……詐作客人中官,及在任者冒法入納”等活動,予以嚴厲禁止。⒇宋真宗時下詔規定:“兩
_____________
① 《宋史》卷174,《食貨志》。
②③ 《宋會要輯稿》食貨6之l至2。
④ 《系年要錄》卷173,紹興26年7月癸丑。
⑤ 《葉適集·水心文集》卷25,《朝請大夫提舉江洲太平興國宮陳公墓志銘》。
⑥ 《宋會要輯稿》職官47之72。
⑦ 《宋會要輯稿》食貨65之96;《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5。
⑧ 《宋會要輯稿》食貨70之104。
⑨ 《宋史》卷178,《食貨志》。
⑩ 《宋會要輯稿》食貨63之168至169。
⑾ 《宋會要輯稿》食貨6之2。
⑿ 《宋會要輯稿》食貨6之5。
⒀ 《系年要錄》卷51,紹興元年1月丁巳。
⒁ 《長編》卷7,乾德4年5月乙丑。
⒂ 《宋會要輯稿》職官44元2至3。
⒃ 《宋會要輯稿》食貨17之19至20。
⒄ 《宋會要輯稿》食貨52之3。
⒅ 《長編》卷273,熙寧9年2月辛卯。
⒆ 《宋會要輯稿》食貨39之15。
⒇ 《宋會要輯稿》食貨40之8。
京、諸路場務、津渡、坑冶等,不得令仕宦之家該蔭贖人主掌。”①到南宋孝宗乾道二年開禁。宋徽宗政和二年曾規定:“自今已后,諸在外見任官,如私置機軸,公然織造匹帛者,并科徒二年。”②估計在此之前還是允許的。同時,宋朝還有大量規定,如不許擅自挪用公款,不許私自役使部下、士卒從事工商活動,不許制造、出賣假冒偽濫商品,不許短斤少兩,不許強買強賣,不許私造私販禁榷專賣品,不許逃稅抗稅等,對官吏私家工商業經營活動都是有效的,都是他們應該遵守的。然而,實際情況與上述禁令大相徑庭。
(一)“部內”經營工商業.趁赴任、離任之機經商
宋太祖開寶六年,盧多遜向太祖揭發宰相趙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③宰相統管全國,當然也包括京城,況且趙普本人就在開封辦公,他經商顯屬違禁。此時與乾德四年禁止官員“于部內貿易、與民爭利”的規定,才相距數年。數年后,即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的一道詔令中描述當時的情形說:“(中外臣僚)雖在縉紳之間,猶競錐刀之末。乃至奉使郡國,守鎮藩方,罔守不貪之言,親與細民爭利。”④后來,官吏經商之風日益盛行,部內經商之事就更是屢見不鮮了。宋真宗時,兩浙轉運使姚鉉“鬻銀多取直。托湖、婺、睦三州長吏市縑帛,不輸征算。”⑤宋仁宗時,孫沔曾擔任提舉兩浙刑獄,“在杭州,嘗從肅山民鄭昊市紗。”任并州知州時,“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⑥當時的樞密使夏竦,“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巨萬,自奉尤侈。”⑦宋哲宗元符二年閏九月,權殿中會侍御史左膚揭露說:“(呂)嘉問先任發運使,就除知青州日,未赴任間,先令客司(安彥)般載本家米往新任出糶。”⑧“臣僚言:伏睹令州官及本縣官不許托縣鎮寨官買物。訪聞貪吏違法,禁托買而不禁自買。故州官行屬縣,縣官經鎮寨,多出頭引收買匹帛絲綿等物。”⑨南宋時,新任知房州廖視“到郡之初,多令私仆販運紗布。”⑩官至宰相的沈該,“頃在蜀部,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為本也”⑾南宋武將們在轄區內經營工商業也是很普遍的。
(二)私造私販
宋朝禁榷專賣制度,比前代有所擴大。諸如鹽、酒、茶、舶來品等,在大部分時間都屬于禁榷專賣物品,不許私造私販。但文官武將們卻違犯禁令,私造私販。
宋徽時的一道詔書中說:“比年以來,稍復縱馳,破制玩法,恃帥權每次高勢而為邪……率來為釀,不可以數計,科配軍民,侵奪官酤,公私交害。”⑿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八月有臣僚說:“今權豪恃勢競為私酤,開創酒庫肆,布在諸處……造曲用麥動以數萬斛計。”⒀洪擬也曾指出:“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其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
________________
①《宋會要輯稿》刑法2之11。
②《宋會要輯稿》刑法2之59。
③《長編》卷14,開寶6年6月丁未。
④《宋大詔令集》卷198,《禁約中外臣僚不得因乘傳出入赍經貨邀厚利詔》。
⑤《宋會要輯稿》職官64元20至21。
⑥《宋史》卷288,《孫沔傳》。
⑦《宋史》卷283,(夏竦傳)。
⑧《長編》卷516、卷517。
⑨《宋會要輯稿》刑法2之69。
⑩《宋會要輯稿》職官75之6。
⑾《系年要錄》卷182。
⑿《宋會要輯稿》職官45之9至10。
⒀《宋會要輯稿》食官20之22。
問,是行法只及孤弱也。”①如果官吏敢于過問,也不會有好結果,甚至招來殺身之禍。如周極“知秀州日,自帶私家,坐船于本州酤賣私酒,為州酒務轄下人所捕。極忿怒其人,誣以行劫,繃拷有至死者。”②從中可以看到,從北宋到南宋,文官武將們倚仗權勢,蔑視法禁,私釀私賣已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宋代官員販運私鹽,也屢屢見諸文獻記載。宋仁宗時,淮南轉運使張可久曾“販私鹽萬余斤在部中。”③南宋時,“二廣州縣自來寄居待缺官、有蔭子弟、攝官、舉人、形勢之家,判狀買鹽,夾帶私販。”④宋代官員違禁私販的商品并不局限于食鹽。早在北宋仁宗時,蔡襄即曾指出:“仕宦之人……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⑤
(三)擅自利用官府人力、資金、物資為自家經營工商業
宋太宗時,官至京東轉運使的和峴,“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⑥宋真宗時,發運使李浦“私役兵健,為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官船販鬻材木,規取息利。”⑦宋仁宗時,“中人奉使江淮,多乘官船載私物營利,州縣不敢檢察。”⑧河北轉運使王沿“嘗假官舟販鹽。”⑨蘇洵說:官吏經商時,“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⑩蕭固知桂州時,“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揮人兩浙商販私物。”⑾呂溱在真定,“委信小吏,至假官曲釀酒,又使人詣旁郡貿易私利。”⑿南宋時,此風有增無減。趙伯東“守雷州,多破官錢,收買商貨,航海以歸。”⒀最典型的例子是唐仲友。據朱熹揭露:唐仲友在家鄉婺州開設彩帛鋪和書坊等。唐在臺州擔任知州時,其次子結婚,“凡供帳幞帟染破紫綾羅絹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并是會物庫陸侃支公使庫錢,往仲友私家婺州所開彩帛鋪高價買到暗花羅并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數百斤,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遂拘系染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其余所染到真紅紫物帛,并發歸婺州本家彩帛鋪貨賣。……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并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擷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彩帛鋪充染帛用。”⒁武將們比文官也毫不遜色。有關記載很多,恕不贅舉。
(四)強買強賣
官吏有權有勢,具有強買強賣的條件。宋太宗時,辰州知州董繼業“私販鹽賦于民,斤為布一匹,鹽止十二兩,而布必度以四十尺,民甚苦之。”⒂宋高宗的醫官王繼先“籠公私之利,凡客人有重貨,則強買之。⒃宋孝宗時,“知鄂州趙善括……強令拍戶沽買私酒,白納利錢。”⒄臺州知州唐仲友“在鄉開張魚鲞鋪。去年有客人販到鲞鮭一船,凡數百篰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宋史》卷381,《洪擬傳》。
② 《宋會要輯稿》職官72之25。
③ 《長編》卷151,慶歷4年8月戊申。
④ 《宋會要輯稿》食貨28之17。
⑤ 蔡襄:《蔡忠惠公集》卷18,《廢貪贓》。
⑥ 《宋史》卷439,職官64之24。
⑦ 《宋會要輯稿》職官64之24。
⑧ 《長編》卷100,天圣元年5月辛巳。
⑨ 《宋史》卷439,職官64之32。
⑩ 蘇洵:《嘉祐集》卷5,《用法》
⑾ 《長編》卷194,嘉祐6年7月己亥。
⑿ 《宋大詔令集》卷205,《呂溱落職分司制》。
⒀ 《宋會要輯稿》職官74之45。
⒁ 《晦庵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狀》。
⒂ 《長編》卷18,太平興國2年3月乙亥。
⒃ 《三朝北盟會編》卷230。
⒄ 《宋會要輯稿》職官72之25。
不容本州人戶貨買,并自低價販般歸本家出賣,并差本州兵級般運。其他海味,悉皆稱是,至今逐時販運不絕。”①宋寧宗嘉定五年二月,“臣僚言:今之任于廣者,凡有出產,皆賤價收之而歸舟滿載。南方地廣民稀,民無蓋藏,所藉土產以為卒歲之備。今為官吏強買,商旅為之憚行。”②由此看來,官吏強買強賣并不是個別現象。
(五)逃稅抗稅
宋代官員經商時的逃稅抗稅行為,是比較嚴重的。北宋初期,“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間,聯臣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③宋真宗時,兩浙轉運使姚弦經商時也“不輸征算。”(前引)。宋仁宗時,李清臣評論當時的官員:“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托郡邑,商算盈縮,秤較毫厘,匿關市之征。”④)蘇洵亦曾指出:“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⑤“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⑥說明北宋前中期官員經商不納稅是相當普遍的。后來的情況未好轉,到南宋時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王繼先經商,“稅物浩瀚,則令監官放免之。”⑦趙彥滿“載鹽六巨艘,越采石徑過,津吏方欲誰何,彥滿即以竹槍戮傷軍人,幾死。”⑧長江沿線商稅務的商稅,因官吏們的逃稅抗稅行為而受到嚴重沖擊。“今沿江場務所至蕭條,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推原其由,皆士大夫之貪黷者為之。巨艘西下,舳艫相銜,稇載客貨,安然如山。問之,則無非士大夫之舟也。……曲為覆護免稅。”⑨他們既能為自己或親信經商免稅,又能庇護其他商人免稅,是依靠其特殊身份。
_______________
①《晦庵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狀》。
②《宋會要輯稿》刑法2之136。
③《宋史》卷257,《王仁贍傳》。《長編》卷2l。
④《宋文鑒》卷106。李清臣《議官》。
⑤蘇洵:《嘉祐集》卷5、卷11。
⑥蘇洵:《嘉祐集》卷5、卷11。
⑦《三朝北盟會編》卷230。
⑧徐鹿卿:《清正存稿》卷1。
⑨《宋會要輯稿》食貨18之25。
宋代官僚地主在上述農業和工商業方面的一系列經營活動及其具體做法,突出地表現出官僚地主經濟的特權性。誠然,其他階級或階層并非沒有上述作法,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但他們缺乏職權,都不如官僚地主那樣典型、那樣突出。此其一。其二,官僚地主經濟的特權性,反映了宋代地主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換言之,宋代的地主制經濟具有典型的特權性。因為,兩宋320年中,占優勢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唯有官僚地主經濟,才能代表宋代地主經濟的基本特點。
這種特權性,產生出兩大危害性。一是民貧。即廣大農民階級的貧困。不言而喻,宋代農民階級的貧困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如各種戰亂、商人和高利貸者的盤剝、龐大的軍費財政開支等。地主階級上述帶有嚴重特權性的經營活動和做法,則是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農民自愿出賣土地,一般來說可以得到比較公平合理的價錢。而官僚地主的恃勢霸占行為,則意味著農民分文難收。強買往往意味著壓價,吃虧的仍是農民。計取巧奪也意味著農民是在極不情愿的條件下失去土地。官僚地主擁有很多土地,卻利用權勢拼命逃避賦役。他們逃避的賦役,轉移到庶民地主和廣大農民身上。農民難以承受沉重的賦役負擔,有的自殺、自殘,有的背井離鄉,有的把田產投獻或出賣給官僚地主,有的喪失發展生產的積極性。這方面的事例和記載為數甚多,在此僅舉三條。宋真宗說:“然人言天下稅賦不均,豪富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地薄而稅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①乾興元年十二月“上封者言:……才得歸農,即復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閑休。所以人戶懼,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差役)。”②三司使韓絳說:“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同等見存之戶。”③所以,此消彼長,官僚地主越多、特權越大,農民的處境就越艱難。二是國窮。宋代長期存在財政拮據問題。財政困難的成因,與冗兵、冗官問題密不可分。軍費占財政支出的七成到八成,是首要的原因。而冗官和官僚地主經濟的特權性,實為深層次的根本原因。《宋史·食貨志》在談到北宋前中期的墾田數時寫道:“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余頃。由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而開寶之數幾倍于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敘《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就是說,宋代的實際墾田數與宋朝政府所掌握并從中征收到賦租之數很不一致,隱田漏稅之弊極為嚴重。墾田的增加,往往并不意味著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甚至出現不增反減的怪相。如“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余頃,而歲人九谷乃減七十一萬八千余石”。④隱田漏稅者包括社會各階級階層,而以官僚地主階層為罪魁禍首。前引事例和記錄,已足以看清宋代官僚地主瘋狂的逃稅、抗稅行為及其普遍性和嚴重性。眾所周知,宋代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水平獲得顯著發展,超邁前代,卻沒有出現民富國裕景象,倒形成民貧國窮局面,那么,財富都到哪里去了?北宋末年,李光透露了天機:“天下財賦盡歸權倖之家。”⑤李光此論,未免夸張,但卻確切地揭示了宋代大部分財富歸于官僚地主階層的真象。
最后必須指出,特權性決不是宋代地主制經濟所獨有的,是中國封建社會始終存在的。戰國秦漢時期,地主階級一是由奴隸主貴族轉化而來,二是在二十等爵制度下由軍功、權貴、官吏成長起來的富有者。漢代的征辟、察舉制度,既是地主階級特權的一種表現,又是其特權的一種助長劑。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世族門閥地主占據主導地位,其特權性更是極為顯著的。隋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以安史之亂為界,前期仍是世族門閥地主占優勢地位,后期則是軍閥地主和庶民地主的天下,軍閥地主的影響更勝一籌。元代統治集團,由蒙古族為核心的少數民族權貴、軍功地主和官僚地主組成,其特權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明代,由王公貴族,文武官吏組成的縉紳地主,其特權性亦很突出。清代,縉紳地主依然存在,但其比重和特權性已大不如前,明顯削弱,庶民地主和小農經濟才獲得顯著發展。費維愷教授曾指出:“自宋以來,中國的財富、政治權力、社會地位皆為官紳階級所壟斷,而其家庭皆為擁有若干資財的地主”。⑥此言顯然失于片面化、絕對化,但看到了官紳階層的政治與經濟相結合的特權性則是值得重視的。實際上,從戰國秦漢到兩宋,也大致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官紳階層及其特權性,對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很值得我們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們探討地主制經濟,也不可忽略這個問題。
______________
① 《宋會要輯稿》食貨1之18。
② 《宋會要輯稿》食貨l之20。
③ 《宋史》卷177。以《文獻通考》卷12校。
④ 《宋史》卷174,《食貨志》。
⑤ 李光:《莊簡集》卷8,《論制國用札子》。
⑥ (美)費維愷:《宋代以來的中國政府與中國經濟》。載《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