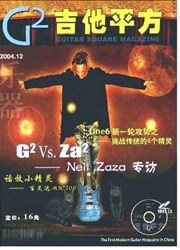試論宋代的“江湖社會”
虬髯客
1989年3月我在澳洲應Phd.Mable Lee的邀請,曾有機會在悉尼大學一個中國問題系列論壇上作了一次講演,題目是《中國古典小說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重點就是從關羽何以為“義神”,談到“義”在中國倫理中具有多重組合功能,如“仁義”、“忠義”、“信義”、“情義”、“孝義”、“節義”、“恩義”、“義勇”等等。而組合功能的取得,應當與使用頻率與社會范圍成正比。古今學者討論“義”或者“正義”的論說亦伙矣,但多由典籍引論,概念推衍,鮮見從社會文化角度立論者。這里僅就宋代江湖社會的形成,與“義”使用概念和空間的延展試為申說,并求教正。
傳統的“五倫”中,唯有“義”是社會交往的準則。故此處所述“江湖空間”特指社會空間,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變遷形成的公共空間。“江湖”一語自武俠小說標立“現代”以來,已濫用斯極。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閱竟有80萬5千條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俠小說及其電子衍生物的內容。目前論及“江湖”社會的專著論文雖然很多,但大都帶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貶斥詭異莫測。所據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說法。
我以為必須為“江湖社會”尋找一個原點,一個價值中立的定義。還原到宋代,“江湖” 一語至少也有三種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須對“江湖”一語略為辨析,才能設論于後。
宋人雖然重視回歸家族,敦親睦鄰,但是社會演進、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變化,勢必帶來社會空間之擴大,也造成個人出入家族內外的靈活余地。人流物轉既然自中唐已經大興,宋代更是勢如離弦之箭,欲罷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長了流動趨勢。“江湖”社會的空間,亦應運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宗族”社會和公共空間呈現出雙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著這樣的社會現實,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結拜兄弟”之間出現了一個相當寬松的公共空間,這樣的互相補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為現實。鄧子琴言:
“嘗考宗法時代與門閥時代皆為有形之社會組織,蓋此兩時代均有血族及經濟關系,以為聯系之資。至于士氣時代,在經濟為各個獨立,互相等夷;在血族為人盡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舉取士,茍士之有聰明才能者,咸能自奮一有所表焉。故此時代欲研社會風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氣節風格為重。”[1]
“在經濟為各個獨立,互相等夷”的現象,即是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平等關系結合體,尤其表現在宋代的城市形態上。蓋緣城市作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會發展的天然指標,既集聚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播之大成,又對周邊乃至全國起著示范功能和反饋作用,在以農耕文化和宗法氏族為主的中國,這種作用尤為突出。試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語的是莊子,他的著名比喻是:
“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咰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2]
即用本義,但又把當時江河湖海遼闊的自然地貌賦予廣闊、流動的內涵。在《外篇》的《天運》、《至樂》、《山木》等文中也有類似表述。尤其是當時的江南的河湖縱橫,汪洋恣肆,尤成專語,如《淮南子·主術訓》:“湯、武,圣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記·三王世家》述漢武帝封廣陵王劉胥的策文中說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之類。
由此引申的意義,則是與“魏闕”、“廟堂”對舉,含有“隱居”、“退處”的意思,這也首見于《莊子》。《外篇·讓王》中說: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于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可知“隱巖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為于布衣之士”。後人反復吟詠這個對舉,或者兩者對立,如《舊唐書》本傳述李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白居易“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術,不樂趨競,久游江湖。”《新唐書·文學傳》“天寶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以至黃庭堅《寄黃幾復》詩“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之類;或者兩者兼容,最為人傳誦的即是范仲淹《岳陽樓記》之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江湖”之第三義則出于《史記·貨殖列傳》敘范蠡事: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而《史記·三王世家》傳漢武帝封齊王劉閎、廣陵王劉胥的策文,曾言“齊地多變詐,不習于禮義”,“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則知范蠡變名易姓之所在,本不習于禮義,而擅魚鹽礦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注意力集中于抓商機,而不必看上司臉色。
宋人周淙撰《乾道臨安志》卷第二言:
“吳地,古揚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魚稻富饒,不憂饑餒,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吳郡余杭,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商賈并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國史·地理志·總敘》:兩浙路以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進取,善于圖利。” [3]
此處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與治賈善生,鬼神淫祀。雖引前人之說,亦為時人自道。可知漕運及水上貿易大興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淵源。“江湖”究指何所,眾口紛紜,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國自周以來‘以農立國’,‘以農為本’,長期還以井田制為社會理想范式,并以此為中心設計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來。‘離土離鄉’意味著逸出傳統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動隱秘,生計無常的特性,又使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壞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難管理的一類階層。從農本社會的觀念出發,這些離土離鄉,游蹤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為業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張,所為可疑,坑蒙拐騙之輩。常言道:‘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其此之謂也。這類角色恰合莊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構成傳統中國社會豐富的人物譜系。”[4]
從概念貫通的意義上說,本文所論“江湖”亦包容以上三義。因為第一是兩宋主要取賦東南,故兩京端賴舟楫交通,屬于“浮在水面上”的繁華都市;第二是朝臣賦閑,或者文士轉徙調動,每嘆不得其志用,都是以“江湖”自況,正顯示著他們此刻的平民立場(限于篇幅,本文從略);第三是航運交通貿易及其延伸到都市中的商業、服務業、娛樂業,構成了兩宋“民間社會”的新基礎,這正是本文論述的重點。惟這些內容非數部專著不能容納,所以須用化繁為簡的方式,梳理出一個能夠令人信服的角度。本文擬標舉唐宋之際的漕運—城市水系—商業布局變遷為線索,以此貫通“江湖”一語的本義、引申義、轉借義和隱喻義,進而論及宋代社會的公共空間及其信仰。
有同事曾以“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間”為題先有論列,理或然實不盡然。[5]本文僅及“江湖”之中立意義,不予辨論,姑執一端可也。
[1] 《中國風俗史》(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175。
[2]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3]《叢書集成初編》本,頁20。按《乾道臨安志》十五卷早為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錄,且明言撰者為“府帥周淙
彥廣”。今存三卷,為最早之南宋方志。
[4] 《顯性和隱性:金庸筆下的兩個社會》,載《‘1998臺北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5] 參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及李慎之序《發現另一個中國》。學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日人桑原騭藏《歷史上所見南北中國》[1]釋文中引用的史料,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國漕運史。大致而言,中國歷代京師一向依靠漕運供給,起初端賴秦漢時代的關中水利建設,供給長安用度,而中唐以後關中水利淤塞,中央財賦愈來愈須仰仗東南。故水路運輸的通暢狀況,直接決定著都城的設置和續後命運。歐陽修《新唐書》感慨于此,故特別夸贊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堅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市睢陽區)力戰之功: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而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以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2]
張巡等力戰保全的江淮,其實就是趙宋王朝起家的本錢。據《太平御覽·水經》,汴河之開鑿緣于“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浪宕渠,即汴渠”的傳說。後隋煬帝下江都,“更令開導名通濟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東引入泗,達于淮,至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御河。”這樣就形成了全國漕運的骨干網,“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公私漕運商旅軸轤連接。”自從關中“八水繞長安”的景觀不復再現,黃河漕運一度成為遷都洛陽的主要原因。隨著五代黃河改道,朱梁被迫再次東遷至黃河與運河的交叉地汴梁,以就食淮南。宋代的前三個君主都有過在長安重建京師的宏愿,宋真宗還借祀汾陰、封西岳的名義親往考察,但終因漕運問題不能解決,永遠放棄了追摹漢唐的雄心。元明清以北京為都城,也是在南北大運河貫通以後才能實現。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也說:“宋以後的運河中心時代,中國社會沿運河線移動,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由各種其它社會情勢在彼此相關、互為因果的情況下,所形成的近世社會的特性。大運河的機能是交通運輸,所謂運河時代就是商業時代。”[3]可謂一語中的。
話說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和顯德四年(957年)先後頒布過兩個著名的詔令,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預先規劃出大批空閑之地,“其標識內,候宮中劈畫,定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以網羅天下客商,建成商業都會,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招商引資,官民共建”;[4]第二是疏浚汴河,顯德四年四月“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梁。”。五年三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5]“汴口既浚,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斛賈,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周景)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為都會之壯。世宗許之。”[6]今語謂之“預留城市發展空地”,實際上主要作了沿河街市。北宋還特別設立了“汴河堤岸司”和“京師修完所”,作為河道運輸和市政管理的常設機構,推動這項政策的持續進展。
以今日視線觀之,周世宗的諭令不啻都市“重商主義”宣言,倘非如此,宋代經濟就不可能出現黃仁宇所謂“前現代化”問題。論者咸以為這從根本改變了中國都市的發展格局,梁思成對此特別推重,認為“顯德二年增修汴河兩詔,富于市政設計觀念,極堪注目。”而柴榮“實為帝王建都之具有遠大目光者,其所注意之點……皆近代都市設計之主要問題,其街道有定闊兩邊五步內種樹掘井、修蓋涼棚,皆為近代之方法。”[7]
宋代以東京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異常繁榮,論者多言其坊里制度的演變。其實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繼續執行後周的中央集權制度和“強干弱枝”方略。趙匡胤不僅“杯酒釋兵權”,大力削弱地方武力,而且實施了一系列制度,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勢力膨脹的任何可能性。《宋史》說:
“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強干弱枝之勢,故于兵食為重。”[8]
宋朝分置“禁軍”、“廂兵”、“鄉兵”和“藩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者,皆收補禁兵,聚之京師,以備宿衛”,為天子自將之軍,而且主要職責是衛戍京師,[9]當然也由中央實行財政大包干。《水滸傳》曾言林沖為“八十萬禁軍教頭”,初讀者每惑“禁軍”數量何其多也,其實并非虛言。宋太宗視察汴河決口處時曾說“東京兵甲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至道元年(995年)參知政事張洎奏議汴河重要時,亦稱開封之繁盛:“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并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于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10]
集結重兵的同時,宋廷又建立起一個空前龐大的中央集權制官僚政府,并頒詔“令自今諸州歲收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也就是說為了加強中央財政控制,天下的供賦物資都要不憚煩難,先運至京師汴梁,然後再“回綱轉輸外州”。[11]因此繼續後周工程,建成了以開封為中心、以汴河為樞紐,進而連接西北與東南江河之水運綱,河北、陜西、河東三路局部地區之可通水運者,亦有相應設施,并注意水陸聯運之利,以向開封漕運糧食。汴京漕運盛時,諸州歲造運船三千多艘,歲運糧食六百萬石。四方特產珍異,紛至沓來。京師經濟之繁盛,文化之發達,與水上交通之便利關系至為密切,這無疑構成了北宋都市繁榮的堅實基礎。如此龐大的漕運體系,造成了人流物轉的空前繁盛,足以造成一個廣闊的“江湖”空間。後世隱性社會由“漕幫”而起,絕非偶然。[12]
范鎮《東齋記事·補遺》說:
“錢俶進寶犀帶,太祖顧謂曰:‘朕有三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上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可見趙匡胤對于經營汴梁運河的得意。“工商外至,絡繹無窮”的確為汴梁帶來了巨大的商機,首先是邸店住宿、貨物存放問題。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言,負責浚汴的北周大將周景理解柴榮意圖,首先“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于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尚存。”[13]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九也明說周景威起樓有假公濟私之嫌,“實所以規利也”。[14] 不僅如此,還有以供房出租,私人獲利者。“景德中(998~1007年)有司言京師民僦官舍,居人獲利多而輸官少,乞增所輸,許奪賃。若人重遷,必自增其數。上曰:豈不太刻耶?先帝屢常止絕,其申戒之。” 蔡襄曾有《乞罷晏殊宰相奏》言:
“臣竊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為宰相,首尾數年,不合奇謀異略,以了國事,唯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聞於道路。”[15]
可見京師的大官僚也參與了這種“射利”的勾當。正是這種優惠政策,使汴梁迅速繁華起來。同時都市的市集和最繁華的商業區域,也作為漕運向都市內部的延伸而沿河散布,徹底打破了坊里制度的封閉格局,深刻影響了汴梁城市續後的演進。沿汴設市的好處,是在商業之外還連帶加工業的繁榮。比如飲茶已是北宋普遍習俗,尤其末茶為百姓日需,《宋史·食貨志下六》云: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堤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并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圣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余緡。四年,于長葛等處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輔郡榷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創月進。”
僅此一端,即知漕河兩岸加工業之發達,以及榷稅利于國用之便。《東軒筆錄》還描述了另一個細節: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荊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澀,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于是以腳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眾。京師有諺語曰:‘昔有磨磨漿水,今見碓搗冬凌。’”
可知汴河漕運作為都市的支持供應體系,已經到了須臾不可脫離的程度。隨著的人員幅集,城市擴大,原先在外城的十三間房、大相國寺和州橋一帶,反而成為汴京中心最繁華的地帶。[16]這樣汴河不但成為漕運向都市水系的延伸,而且成為都市交通運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是北宋城市建設的又一項重大突破,并且是從根本上改變了坊里制的商業布局,造成汴梁異常繁華的又一直接原因。討論汴京突破坊里制度的中外論文很多,但大都是從城市制度的改變立論,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發生這種改變的經濟因素。《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情景所以沿汴河展開,不僅是繪畫構圖的需要,更反映著汴梁城市商業格局水陸并行的生動現實。[17]
[1] 載《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中華書局1992年出版。
[2] 《新唐書·忠義·張巡許遠傳》評贊。
[3] 同上,170-171頁。
[4] 《五代會要》卷二六《城郭》。《冊府元龜》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亦有記載,文字稍有不同。
[5] 《資治通鑒》卷二九三,二九四。
[6] 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
[7] 梁思成《中國建筑史》(高等院校內部交流講義,轉自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頁275頁注釋⑤)。
[8] 《宋史·食貨志·漕運》。
[9] 《宋史·兵志一》:“禁兵者……皆以守京師,備征伐。”陳師道《上曾樞密書》:“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宋文鑒》卷一百一十九)以此觀之,開封為首都的選擇,忽略了‘四戰之地’的戰略劣勢,正是宋代重商主義建國方略的產物。
[10] 《宋史·志·河渠三》。
[11] 《宋史·食貨志上·漕運》:“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緣為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于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是官僚體制運轉不靈,故轉輸者須以官船挾帶私貨規利的證據。
[12] 李世瑜、呂宗力、欒保群為提倡“社會歷史學(Social History)”,曾編選了一套《民間秘密結社與宗教》叢書(河北人
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輯入20世紀30-40年代著作多種。其中關于青幫的起源說法不一,孫悅民《家理寶鑒》以為起于安徽安慶,後訛為“安清幫”;朱琳《洪門志》以為源于乾隆時“漕運不靖,糧運不行”;生可《青紅幫黑幕》言青幫源于乾隆時“運糧船只屢遭寇劫”;陳國屏《清門考源》則以為是由康熙年間“漕河各岸夫役結合一團體曰糧米幫”轉化而來;李子峰《海底》說哥老會起于同治間湘勇撤營,在湘水襲劫兩廣總督李某之弟的財務百余船。而以天津社科院李世瑜之《青幫早期組織考略》最為明晰。(載《會黨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286-303頁。)這些說法大都基于民間秘密會社“不立文字”的口頭傳說,但都不約而同地歸結到漕運問題。我以為固然淵源有自,但都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宋代以來中國龐大的漕運,僅僅依賴官僚體制,是不能滿足其貢賦以外民間商貿千差萬別需要的,必然會產生相應的非政治性支持體系和協調機制,以及由此而至的更大公共社會空間。
[13] 如何處理“十三間樓”規模“逾制”的問題,是周世宗推行“重商主義”的一個證明。這處所在後來成為“大東京地區”的
中心。《宋會要·輿服、臣庶服》規定“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臨街市之處,毋得為四鋪作、鬧斗八”,對臨街鋪面房的
建筑規制實行了特別優惠的政策。楊寬對此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參該書283-284頁。
[14] 曾鞏《隆平集》卷三。
[15] 《全宋文》第23冊,672頁。
[16] 參《東京夢華錄》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州橋夜市”、“大內前州橋東街巷”、“相國寺內萬姓交易”諸條,此凡談汴京繁華者例皆引之,故不贅。
[17] 研究《清明上河圖》與汴梁城市面貌的專著有多種,楊寬綜合其說,以為“先描繪東水門外虹橋以東的田園景色,有些是墻
身很矮的草屋,有些是以草屋和瓦屋相結合而構成的一組房屋。接著描繪的是汴河上的‘市橋’及其周圍的街市。再進一步又
描繪到城門口街市以及十字街頭街市的情景。其中還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繪了這一段汴河的航運。”“畫中的市橋……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東水門外七里的虹橋,這是可信的。”(參該書316-317頁) 中國古代都市建設規劃本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說法。《考工記·三禮圖》還繪有周王城的示意圖。[1][1]城市水源除了飲用之外,另一個重要功能便是防御,甃池以為險,即孟子所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俗稱“護城河”。第三個用途才是帝王苑囿的鋪排點綴。從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附圖看來,把漕運水系引入城市作商業交通之需,恐怕始于亟需就食淮米的中唐洛陽。洛陽郭城由洛水中分,而北、南、西三個主要市場,則分別臨近漕渠、運渠和通濟渠。竊以為中國古代城市格局的突破,正是由此開始的。而真正的變革則來自漕運的起點揚州。
中唐揚州所以能夠異軍突起,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商業都會,完全得益于它居于漕運骨干水系的黃金位置。唐人張祜《月明橋》“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李紳《宿揚州》“夜橋燈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斗牛。今日市朝風俗變,不須開口問迷樓。”都是從水陸商道交會的景觀,來描摹揚州的商業繁華。當時的漕運水系也深入到了都市內部的交易場所,并且留下了後人艷羨的繁榮神話:“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2][2]
曾經盛極一時的揚州,或許正是柴榮改建汴梁的“粉本”。理由有四:
一是柴榮的兩項詔令,都與征南唐事相踵接。親征揚州正橫亙在他兩道詔令的中間。據《資治通鑒》,他下令擴城的第二天,就詔求《開邊策》,王樸上書即言先攻南唐的戰略。在進攻的準備階段,他已經盤算過投入產出的效益,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上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于標外。上曰:‘近廣京城,于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
第二是柴榮很注意保護揚州,顯德三年親征揚州時,先“诇知揚州無備”,才“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又于顯德五年兩次“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馀,筑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3][3]著名的“浚汴口”詔令,正是在揚州發出的。顯德六年二月,又“命王樸如河陰按行河堤,立斗門于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如果不是他此年病逝,漕運工程和揚州建設不知還會有多大的動靜。
第三,柴榮根底上就是個精明的商人,他的重商思想或者與其曾經身為估客的經歷有關。《舊五代史·世宗紀》言郭威嘗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資用獲濟。”陶岳《五代史補》則言:“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司馬光也說他“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于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
第四是柴榮早有快速“致太平”的設想,陶岳《五代史補》: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樸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余六個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數也,蓋樸婉而言之。”
三個“十年”之說,也符合他銳意進取的一貫作為。套用今日之“深圳模式”一語,那么依賴水利漕運之便,迅速實現商業化大都會的“揚州模式”,當能予後人以啟示,這應該是周世宗革除舊制,創立新規的動力。于是才會出現新型的“汴梁模式”,即以京師為中心,以商業經濟帶動政治、軍事、文化一體發展的新型大都市。[4][4]
--------------------------------------------------------------------------------
[1][1]《考工記》。參劉敦楨《中國建筑史》第二版,36頁。
[2][2] 陶宗儀《說郛》引《殷蕓小說》“有客相從,各言其志:或愿為揚州刺史,或愿多資財,或愿騎鶴飛開。其一人曰:“腰纏
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欲兼三者。”咸淳《古尊宿語錄》卷四十七《東林頌》:“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騎鶴下揚州。”拙文《李晟與「關公斬蚩尤」傳說》(待發表)曾略論及中唐以來樂府詩題“估客樂”吟詠內容的變化及有關揚州的繁華傳說,說明新興的商業城市和漕運貿易的關系非常密切。權德輿(759-818)為憲宗朝名相,以立朝端正而在貞元、元和間稱“縉紳羽儀”,但在揚州感官卻受到極大刺激,吟詩從“廣陵實佳麗,隋季此為京。八方稱輻輳,五達如砥平”的繁華,描繪到“交馳流水轂,迥按浮云甍。青樓旭日映,綠野春風晴。噴玉光照地,顰蛾價傾城。燈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飄搖翠竹薄,掩映紅襦明。蘭麝遠不散,管弦閑自清”的綺麗,最後竟然發出了“且申今日歡,莫務身後名。肯學諸儒輩,書窗誤一生” 的感慨。(《全唐詩》卷十二)。可見“揚州模式”對京城大員的沖擊。以今證古,誰曰不然?
[3][3] 《宋史·范質傳》:“世宗初征淮南,駐壽、濠,銳意攻取,且議行幸揚州。質以師老,與王溥泣諫乃止。”可見柴榮對于揚州興趣之濃。北宋揚州有所恢復,但已成為汴梁的附庸。沈括曾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揚州之下。舟車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七。’”(《輿地紀勝》卷三十七)南宋時由于地處宋金前線,又受到李全破壞,遂不復舊觀。故《容齋隨筆》卷九《揚州之盛》感慨說:唐末以後“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為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毀于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可知揚州在五代時期亦有再生恢復能力。元代疏通南北大運河,揚州又再現繁榮,優勢俱在漕運。值得強調的是擴汴城是令趙匡胤跑馬圈地,征揚州亦是趙奮勇爭先。作為柴榮的親信權臣,也許他更多了解柴榮的權謀機變和治國方略,所以能把建汴方針堅持下去。[4][4] 1853年6月10日,馬克思在一篇給《紐約每日論壇報》(6月25日3804號發表)寫的時評《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提出了了一個遠非深思熟慮的觀點:“在亞洲,從很古的時候起一般來說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愿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145-146頁)以現代常識而言,這段話的論據和論證都經不起檢驗。比如東方政府制度相當繁雜,遠非三個只負“掠奪”之責的部門;比如撒哈拉到青藏高原不是同一氣候地質季風帶,形成沙漠的原因也不同;比如東方的文明發展程度并不“太低”,尤其是和農耕時代的“西方”相比,等等。百余年后德裔美籍學者卡爾·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摭拾此說,加以引申發揮,在所著《東方專制主義——對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中斷言“東方專制主義”源自“水文化”,在90年代初中國史學界引起興趣、應合和討論。(參李祖德、陳啟能著《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近年韓國宋榮培博士有《儒家思想、儒家式的社會結構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ongrujia.htm)中對上述說法進行了全面質疑。,但中國的水資源及其管理體制不僅要考慮到“全流域治理”的管理需要,即中央集權和“大一統”,亦應包含續後的“內陸及海運漕運支持體制”,即中國社會的商業化規模及進程。這是一個相關而內容更加龐雜的專門問題。前輩學者如史念海《中國的運河》,許輝《唐宋運河論述》、何榮昌《唐宋運河與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朱瑞熙的《大運河和唐宋帝國的統一》等專著專論亦對運河漕運與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關系論述詳瞻,自可參考。略帶一筆,以示關注。 汴京商業網如何沿城市水系演變發展,鑒于資料不夠完備,是一個微妙而難以證實的問題,而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相關法令記述入手的思路頗可稱道。其中元豐年間有好幾條材料涉及到開封的街市問題,例如元豐二年(1079年)由修完京城所申請批準租官地與民創屋而為“面市”,明確官地民商的分利原則;入京商貨先運至泗州,“官置場堆垛”再用官船運達京師,私船不許入汴,實行官船壟斷;元豐八年(1085年)頒詔令修完京城所管屬的“萬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豬羊圈、東西面市、牛圈、垛麻場、肉行、西塌場俱罷。”停止若干官辦商業機構;御史黃洚上奏請求罷免新興行市地稅,談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許人斷賃”的問題,明確沿汴空地允許租賃;廢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錢”(既免除行役的錢),并把汴河提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和歲收課利,撥給戶部左曹掌管征收。中書省決定“除代還免行錢外,余充本曹年計”,據稱受惠的各行商人多達6400多行,免除總額4萬3千多緡,目的是減少中間環節,惠商利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變“地稅”為“國稅”。[1]這些措施的本意無論是獎勵還是抑制民商,都反映出利用沿汴閑置官地謀利的思路。宋神宗逝于元豐八年三月,隨即高太后用司馬光盡變王安石新法,考慮到上述事件橫亙在新舊兩“黨”政策交替的關鍵時刻,圍繞汴河兩岸的法令變化就更有意味了。
南宋都城臨安地處水鄉澤國,本是古越“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之舊地,東南財賦輸入京師愈加方便,漕運則直接連接閩廣海外,也更加發達。故宋室南遷之後承襲“商業立市”的“祖宗家法”,很快就從連年戰禍中恢復發展起來,繁華程度甚至超越汴梁。[2]臨水建市的特點也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來,今觀宋人記載的臨安各市多設在橋頭,就因為橋頭正是水陸交會之處,最易滿足運輸和交易的雙重方便。在城市空地和橋頭上做買賣的習俗一直延續到今天,如果資金規模達不到相當程度,即便城市管理部門緝拿追捕,有意驅街頭集市之“行商”變為賃屋經商的“坐賈”,成效也是有限的。[3]
又如平江府是南宋第二大都市,白居易詩言“霅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蘇州)太繁雄。惟有錢塘郡(今杭州),閑忙正適中。”“曾贊錢塘兼茂苑,今來未敢苦夸張。”可知中唐蘇州也依仗水運之便,略勝錢塘而追摹揚州。五代時地方藩鎮孫儒曾攻陷蘇州造成破壞,更大災難是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人入平江,縱兵焚掠”,“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廩庫積聚。縱火延燒,煙焰見二百里,凡五晝夜”,士民“遷避不及遭殺者十之六七……死者甚眾,一城殆空”。但由今存南宋碑刻《平江圖》(紹定二年,1229年)看,重建之蘇州城市井然有序,注明名稱的橋梁就有304座,規劃亦展示出重商特色:“交通方面的特點是安排了水道和陸道兩套系統,除了街道外,城墻各有河一道,城內的河道又有干線和彌補的分渠。大部分分渠采取東西方向,構成與街道相輔助的交通網,使住宅、商店和作坊都是前街後河。”[4]分渠就像毛細血管分布到城市的每一單元。故黃仁宇以為: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車橋梁較之20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并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後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後32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Quinsai)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贊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于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里市廛櫛經,而且鄉間里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5]
如果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發現宋代新興城市大多是沿江河湖海和漕運干線分布的。這和宋代管理制度的沿革頗有關系,趙匡胤分全國行政區為十三道,設置諸道轉運使以總財賦;趙匡義又分全國為十五路,并強化職責,“經濟掛帥”,以邊防、盜賊、刑訟、金谷、按廉之任,悉皆委于轉運使。隨著經濟區域性功能的發展演變,真宗時再分為十八路,神宗時二十三路,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增加到二十四路。所設衙門轉運司亦稱“漕司”,此即見出漕運職司之重。行政區域細化的目的,主要是為增加對于中央的貢賦,但也反映出處于漕運水系交叉處的商品集散地,已經作為城市中心地位也在不斷提升的事實。[6]此亦專門性課題,南宋方志多詳載地方經濟管理官吏的數量及分布狀況,幸望研究者注意。
[1] 分別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五八、三五九、三六八。
[2] 這種風習延續到元大都的城市規劃,最重要的表征是郭守敬設計北京的水系,使什剎海既是漕運終點,又是元大都最大的集
市和娛樂場所。明朝重申“重本抑末”的國策,建都時亦遵從《周禮》“政治掛帥”,城市水系設計和整體規劃布局因此作過調和處理。清承明制,內城復由八旗分駐,則又形成新的典制。
[3] 日人斯波義雄《宋代商業史研究》(1968年出版)和《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1988年出版)向為宋史研究者重視。筆者草完此節之後才讀到《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頗有“先得我心”的欣喜,且論述重點恰好彌補了本文所略,如臨安的商業布局特點,請參該書“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一節。他的“400年周期說”筆者也深有同感。
[4] 劉敦楨《中國建筑師》第六章第三節。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圖181-182頁,文183頁。
[5]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之《賈似道買公田》。
[6] 王鞏《聞見近錄》:“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設,必招‘河市樂人’者,由此也。”可知“河市”興盛緣由概貌。案王鞏為王旦之孫,書法家,蘇軾友人,曾因烏臺詩案“除名勒停,全州編管”。 宋代的社會性質是一個聚訟已久的問題。中國史學界一般都認為屬于“封建社會”,而國外學者則有以為是“近代社會”的發端者。[1]因為兩種說法不在同一理論坐標體系上,因而沒有發生正面的爭論和碰撞。但是將中國傳統社會一律視為馬克思“五階段論”中的“封建社會”的說法已經受到了挑戰,這也許提醒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歷史的分期和不同時代社會性質的問題。本文稱宋代為“重商主義”,就是在爭論明晰之前一個替代性的說法。
司馬遷就是一個重商主義者,他在《貨殖列傳》縷述先秦西漢的“牟利沖動”以後,總結道: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恰好也是以“水”為喻,用“水之趨下”,來表征後世市場經濟論者以“看不見的手”改變社會的巨大能量的。[2]邵雍總結宋朝建國有五件事是“唐虞而下所未及者”,首先標舉的就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3]把不干擾商業當作和平換代的第一指標。而兩宋漕運的繁榮,正是窺知當時市場經濟的主要指標之一。
隨著漕運網絡的浸潤,首先是都市通衢內河網交錯,接著是水路或水陸交會點出現新興的商業市鎮,再次是沿岸圩墟市集依次鋪排,那些“與時逐而不責于人”的商販估客亦如水之流轉,晝夜不休,穿梭其間,無孔不入。就像血脈運行于周身,必定會灌注于四肢百骸。他們既已逸出農本社會和家族宗親,故需自成體系。傳統官僚體制除了征稅及官司以外,亦難以介入。商業從來不會是孤立的個人行為,任何一筆遠程交易的背后,必然都有一個供應和消納體系給予支持,中外古今亦然。這是一個日漸增長的社會空間,就成為傳統體制管理最為薄弱甚至空白所在,所以能生長出新的價值觀念、信仰系統、社交需求、禮儀形式和“自組織”(autopoietic organization)、“自治性組織”(self-management),或“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宋代城市中的各種組織,包括“行”、“肆”、“會”、“團”等,意義功能都和農村大不相同。日人加藤繁對唐宋商業組織曾有深入研究,故不具論。[4]明清時期盛行的以地域或者行業形式建立起來的“會館制度”,即是宋代類似社團的某種延續。新興民間組織除了商業型社團外,還包括娛樂型、互濟型、軍事型、宗教型和文人結社型等多種形態,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有所羅列,可以參看。[5]政治型的秘密社團,應當是這一連串組織中最後才出現的。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指出:“北宋十萬戶以上的州、府,宋神宋元豐年間為四十多個,宋徽宗崇寧年間為五十多個,而唐代僅有十多個。”但我據《宋史·地理志》統計,北宋五萬戶以上的府州軍達到122個,十萬戶以上的53個,超過50萬人以上的9個,其中太原124萬,潭州96萬,吉州95萬,贛州70萬,還有成都、漢州、洪州、大名、京兆。[6]奇怪的是連《東京夢華錄》極力描摹的汴梁,和柳永“參差十萬人家”形容的杭州都還未達到這個程度,以今方古,可以想象流動人口在繁榮中心都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宋代航運技術的不斷發展,也證實著這方面的巨大需求。商業貿易性海運的發展,促使宋人在使用指南針和海圖之外,船匠也不斷創新。中國的遠洋巨型海船已有四層艙室和水密隔艙。且造船數量龐大,每年造船3000艘,運糧船竟多達6000余艘。制造了樓船、斗艦、走軻、河鶻、蒙沖、槳船等,船型多達數百種,標志著中國的造船技術趨于鼎盛時期。乾道五年(1169年)水軍編制官馮湛打造的多槳船長8.3丈,闊2丈,用槳42支,屬于綜合型的新式槳船。淳熙六年(1179年)馬定遠在江西造馬船100只,這是一種戰渡兩用船。平時作渡船,戰時作戰船,體現了船舶設計思想的靈活性。嘉泰三年(1203年)池州秦世輔創造鐵壁鏵觜海鶻戰船,能載150人,是一種特別堅固、具有沖角的新型戰船。都科匠高宣造的車船能載千余人,船長36丈,寬4.1丈。[7]
世有所謂“李約瑟難題”,此即制度答案之其一乎?
[1] 參內藤湖南(1966-1934)《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其中從貨幣供應的情況分析了唐宋的時代差別,結論是“總而言之,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第一冊,中華書局1992年版,18頁。)法人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著《中國社會史(Le Moude Chinois)》(Armand Colin,Paris, 1990.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譯本),則逕對宋代冠以“新社會”、“商業帝國”等名目,并稱宋為“一個流動性更大的社會”,因此“人們可以理解一些新型關系的發展:重新集聚和結社的傾向與自我隔離的威脅同樣大,故互助行為更顯得必要了。”“這種互助的必要性不會與文人階級大家族的鞏固風馬牛不相及,這些家族以其組成、道德準則和倫理形成了宋代的新鮮事物之一。”(275-276頁)這些與本文相關的重要論點,都是在以歐洲中世紀作為參照系得出的。
[2]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曾指出,人們盤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5—27頁) 形象地表述出動機與效果在經濟活動中的錯位,或者說純經濟動機會引出非經濟性的社會效果,這也正是柴榮和汴梁城故事的主題。
[3]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第十八,196頁。
[4]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唐宋時代的市》、《論唐宋時代的經濟組織》等,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5] 《中國的社與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惜其未分證唐宋轉型對民間社會的影響。
[6] 《宋史·地理志》每地之下多列崇寧時戶口及人數,大約是行政區劃變更的原因,夔州路、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用的是元豐
戶數,而福建路僅列戶數沒有注明年代。以上四路均未標列人數。戶數和人數的比例也極不均衡,如開封府“崇寧戶二十六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平均每戶1.7人;而太原府“崇寧戶一十五萬五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八。”平均竟達每戶8人,是一疑焉。差別因素可以考慮的有兵制、家庭結構和流動人口等。又元豐、崇寧都是厲行“新政”的時期,則按戶征稅問題恐亦原因之一。
[7] 參鄭學檬《技術進步:兩宋航運業發展的動力》。《廈門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 中唐開始的社會轉型,主要的制度標志之一就是宰相理財。洪邁言:
“唐自貞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于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大府卿及兩京司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于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骎骎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異由衛尉卿鹽鐵使,并命為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豫以度支,魏扶、魏墓、崔慎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 [1]
北宋沿襲了這個制度,可知開國即實行“經濟掛帥”,亦有淵源。遺憾的是,千年以後,中國才再次意識到政府首腦之首要職責就是理財。宋代官吏經商智術可道者甚多,《涑水紀聞》談到著名的岳陽樓時,就稱贊它的建造沒有動用公款,也不糜費民財,純粹是“贊助”修成的: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于民,但片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案典籍。樓成,極壯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2]
《宋稗類鈔》卷之三“才干”曾總結數事言: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馬溫公幼年之擊甕,亦皆于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只,限一日辦。從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只,糊以清江紙,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于后圃造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檐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于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眾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值,負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3]
以辛棄疾上馬擊賊,下馬賦詞之全才,猶能在毫不擾民的情況下,以極小的代價,幾天之內經營起賞月之樓,也許是受到滕子京的啟發。可見宋代官吏于公事俗務之干練,迥非腐儒之作為。
[1] 《容齋續筆》卷十四《用計臣為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303頁。
[2] 《涑水紀聞》卷十,196頁。此頁下條即言滕貶岳州的原因即是公私不明:“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數,為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鞠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職,徙至岳州。”當時涇州處在西夏前線,權財比岳州大得多。這樁案件還牽動了范仲淹、歐陽修為他辯護。所以修岳陽樓,他仍以不守會計制度聞,“一好遮百丑”,順帶洗刷了貪賄污名,復因范仲淹一賦而名動天下。
[3] 《宋稗類鈔》,226-227頁。
今之論者議論“江湖社會”者缺乏中立的價值基準,例有三大誤區:
第一是每用“江湖”等同游離于近世法治社會之外的“黑社會”概念,直截套接古代社會成長過程中的公共空間。古代“江湖”社會處在未經法治規范的階段,自不能與公共法制大體完善的近世社會相提并論。宋代以“冗員”著稱于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集權”和“經濟掛帥”兩項既定方針,導致了政府管理重點的偏移,監管范圍和部門增多,經濟官吏數量異常龐大。[1]盡管如此,由于經濟新興領域多,經濟體量不斷增大,傳統管理體制仍然照管不過來,難以避免產生自組織現象。[2]
第二是每好以政治性質的“秘密會黨”,取代非官非私的公共空間。民國初自中山先生談及洪門淵源,認為是反滿復明的民族主義組織,復以武俠小說文學描述與懵恫學者論述交相扇熾,一時甚囂塵上。民間組織的發展最終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但是不一定創始于政治訴求,尤其一開始就用秘密結社的形式訴諸暴力。我曾提出古代隱性社會最大的民間組織是商幫,可以參看。[3]
第三是每以“江湖”為“流氓(游民)”麕集地帶,而非商業性公共社會。論者每以“寄生性”、“依附性”等蔑稱談論宋明筆記中的城市“閑人”,且以《名公書判清明集》之類結訟文獻為據,條分縷析當時“惡棍”如何包攬詞訟,如何欺壓良善等情事。殊不知這可能源于對傳統話語的誤讀,或者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據《夢梁錄》卷十九分釋,“閑人”即昔日豪門清客幫閑、“閑漢”即今之旅游業,“專精陪侍涉富貴子弟郎君,游宴執役,甘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干。”“涉兒”則是服務中介業,“廝波”亦為特色服務業。出于制度原因兩宋都城實有旅游服務需求,《西湖老人繁勝錄》言:
“遇補年:天下待補進士都到京赴試。各鄉奇巧土物都擔戴來京都貨賣,買物回程,都城萬物皆可為信。混補年:諸路士人比之尋常十倍、有十萬人納卷、則三貢院駐著諸多。士子權借仙林寺、明慶寺、千頃寺、凈住寺、昭慶寺、報恩觀、元真觀。太學、武學、國子監、皆為貢院、分經入試。每士到京、須帶一仆。十萬人試,則有十萬人仆,計二十萬人。都在都州北權歇,蓋欲入試近之故也,可見都城之大。”
如大體屬實,則僅此一項制度,對京城服務業的需求即可知曉。國家統一考試的制度延續至今,每年高考及入學時考生及送考親屬一時猬集之壯觀場面,以及圍繞“考試經濟”與旅館飯店之“經濟增長點”的評論,以今度古,不中不遠。宋人“江湖”派詩集中多侈詠如“江湖偉觀”等臨安勝景,即此之類,亦當時“考試”延伸到“旅游業”之一的證明。[4]曾有對這些都市服務業頗多輕視責難,以致“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之類的鄙諺,若從農本經濟立論可以理解。但今之論者仍舊沿襲這些觀念就未免冬烘了。城市“閑人”與文化勃興的關系,已有“休閑經濟學”論述,不侈論。[5]
至于《名公書判清明集》之類結文書判牘,所引都是指控用詞,依據中國傳統“有罪推定”的法理,被指控者例先被謚以“惡名”,後人對被告情況缺乏了解,只能據官方一面之詞加以推論。也是一種可以理解的 “誤讀”。倘若對被指控者多些了解,就會發現真相或非如此。
試舉一證以供類推:朱熹與唐仲友的互劾案本為南宋著名“道學”訟案,復因“二拍”演為擬話本小說《硬勘案大儒爭閑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而名聞天下。而朱熹奏章就指控過唐“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如果不知道唐仲友的生平史實,不也類同《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方閻羅”、金千二和鐘炎之類“市井無賴”了嗎?其實戲曲《四進士》就展示過訟師宋士杰“構訟”的措辭技巧,這也是傳統社會法律古老的文字游戲。[6]有的學人連京劇中的常識也不具備,故易無視古人,倉促立論,令人遺憾。另一例證,則是鄧廣銘年輕時曾寫作有關陳亮的三篇論文,分別是《陳龍川獄事考》、《朱唐交忤中的陳同甫》和《辯陳龍川之不得令終》[7],以葉適等友人證言對陳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以及“死于非命”的宋人種種傳說進行了辨證。設問當初陷陳于獄,必致死罪的判詞狀文,又該作何措詞,以何鋪張?運用法律文書典籍固然必要,信用過實也有瑕疵。
受到郭毅生《論新興市民等級在太平天國革命中的作用》一文啟發,羅爾綱在《〈水滸傳〉與天地會》一文結末曾說,天地會的創立“和當時中國南方城市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城市平民勢力的發展,也有著內在的聯系。關于這方面,還有待于同志們進行深入的研究。”[8]雖然還格于“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說”,但畢竟從更為廣泛的背景下提出了同一問題,可惜至今未能受到充分重視。
目前雖然還不能對宋代的商業的規模,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作出準確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突破了傳統的經濟結構和制度框架,呈現出與前後朝代大不相同的社會特點。在為宋代“江湖”社會正名之後,我們就容易理解當時的商業中心主義開拓出多么大的公共空間,這正是公共道德和新型人際交往需要拓展的領域。“義”之為“誼”,正在此處。《水滸傳》借以建立的隱性社會及“梁山泊英雄大聚義”,也是立足于這樣的社會基礎,亦為繼宋而至的元代社會洶涌澎湃的關羽崇拜熱潮預設了條件,另文再表。
(原載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藉研究所張其凡、范立舟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1] 參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費》條。中謂“王禹偁言,臣藉濟州,先時只有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自後團練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見《禹偁傳》)楊億疏言:員外加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余員,郎中亦百數”。按《容齋隨筆》卷七:“趙韓王佐藝祖,監方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強,置轉運、通判使掌錢谷以奪其富,參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于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于殿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為,至于今是賴。”說明置官首先出于中央集權的需要;二是重商政策導致財政管理官吏增加,例如數量最多的“員外郎”之置,《宋史·職官二》:“戶部,掌天下戶口、稅賦之籍,榷酒、工作、衣儲之事,以供邦國之用。副使:以員外郎以上歷三路轉運及六路發運使充。判官:以朝官以上曾歷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充。三部副使各一人,通簽逐部之事。舊以員外郎以上充。”三是順應商業空間擴大而加置的監酒榷稅之類行政管理人員。宋代冗官之多還有其它原因,但經濟管理官吏的增設亦為重要因素,導致宋代官制自有特色,不可一筆抹殺。
[2] “自組織”是基于現代“耗散結構“、“系統論”和“協同學”移植于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觀念。自組織系統的一個重要性質是,必須不斷重新制定目標,必須不斷適應新的環境。協同學創始人德人哈肯曾類比說:“在無生命自然界中,例如在水的液相或固相中,各個分子相互間有一定方式的排列關系,而這種關系又轉而決定水或冰的宏觀狀態。人類社會成員的行為方式在不同的政府形式中也是不同的。”(《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P168)美國E.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認為:“細胞、器官、生物體,以及生物體組成的群體和社會都是自創生系統;它們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復自己,并且自己復制自己或自己生產自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P45)“雖然個人的行為舉止部分受到有意設立的規章制度的指導,但最終形成的秩序卻是自然而然的,更象是一個有機體,而不象是一個組織。”(同上,P91)
[3] 參拙文《顯性和隱性:金庸筆下的兩重社會》。
[4] 四庫本《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江湖偉觀”條:“在葛嶺壽星寺,外江內湖,一覽在目。淳佑十年趙安撫重創廣廈,危欄顯敞虛曠,旁又為兩亭,可登山椒。”類似今日之標志性旅游觀賞景點。
[5] 為了拉動內需,刺激“假日消費”,于光遠等主編有《休閑研究譯叢》五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關心“城市閑人”論題者可以參看。
[6]《四進士》一名《節義廉明》。焦菊隱曾贊譽該劇像個“九連環”,情節復雜曲折,結構嚴謹合理。略述明嘉靖間新科四進士毛朋、田倫、顧讀、劉題四人共約赴任後不得違法瀆職,以報海瑞薦舉。後田倫之姐謀產殺人,復又轉賣妯娌素貞。素貞鳴冤,正遇毛朋私訪,乃狀紙,囑其控告。素貞遇難為被革書吏宋士杰所救,認為義女并代告狀。田倫遣人送書賄賂顧讀,差役夜寓宋店,宋偷窺其信文。顧讀徇情反禁素貞。後毛朋接狀,宋士杰作證,田、顧、劉均以違法失職問罪。田氏死刑,素貞雪冤。這也是文士“結義”變質之近代版本,可發一嘆。
[7] 均載《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8] 羅文載《會黨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1-18頁。郭文載《歷史研究》雜志195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