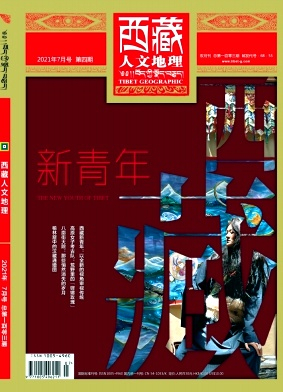宋代鄉役人數變化考述
刁 培 俊
內容提要:大致以王安石變法為分界點,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宋朝政府在鄉村中增加了大量協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管理者——以吏民身份在官府服徭役的鄉役人,即鄉役人的數量有了明顯增長.倘若以唐宋對比,這一增長更加明顯。這是宋代也是中國古代鄉村社會中的一大變化。它反映出在國家財政困窘和基層社會混亂的巨大壓力下,兩宋出現了國家權力向鄉村社會延伸的傾向,由此,也可以顯現出唐宋之際社會和經濟領域發生的一些變革。
關鍵詞:宋代 王安石變法 鄉役人數 增長 唐宋社會變革
宋朝的職役制度(徭役之一),按民戶服役地點的不同,分為州、縣和鄉役,在鄉村服役者即為鄉役人。南宋陳耆卿修撰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門》設“鄉役人”條,孫應時等所撰《琴川志》卷六也有“鄉役”的記載,說明這一名稱已為時人接受。兩宋期間,不但鄉役名目有所變化,而且有從輪差到雇募,再到差募并用、名募實差的充役方式的變化,鄉役人數成倍增長則是其中又一較為顯著的變化。中外學界對于宋朝職役制度已多有研究①,但是,對鄉役人數的變化及其相關問題卻鮮有探討,故作此考述,以補其缺。
————————————————
① 聶崇岐、孫毓棠、黃繁光、王曾瑜、漆俠、雷家宏等學者的相關研究,請參見刁培俊《當代中國學者關于宋朝職役制度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原載臺灣《漢學研究通訊》總第87期(2003年8月),增訂后轉載于中國宋史研究會主辦《宋史研究通訊》2004年第1期。另外,美國學者Brian E.Mcknichl(馬伯良)著有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Aina(《中國南宋鄉村職役》,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版),日本學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戶長、耆長》(載《東洋學報》第34號,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縣職役和胥吏的發展》(《宋代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年版),《宋代鄉村制的變遷過程》(《唐宋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版),佐竹靖彥《宋代鄉村制度的形成過程》(《東洋史研究》25之3,1966年),柳田節子《宋元鄉村制的研究》(創文社1986年版)等也多有研究。
一
兩宋鄉役制度前后變化很大。《宋史·食貨志·役法上》載:宋初,循唐五代舊制,在鄉村中設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設耆長、壯丁“逐捕盜賊”,都是輪流差派(即所謂之差役)鄉村民戶中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戶承擔。開寶七年(公元974年),詔令“廢鄉,分為管,置戶長主納賦,耆長主盜賊詞訟”①。此外,三年一次攢造戶等簿,也由耆長、戶長和鄉書手共同承擔。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四月,詔令廢除里正衙前,里正也隨之廢除。宋神宗朝,王安石變法改革,先后推出募役法(或稱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等。保甲法之設,最初意在部分恢復府兵制,減省養兵費用,增強軍隊候補者的戰斗力,并藉以加強地方社會的治安管理②。然而,熙豐后期卻逐漸與鄉役法混同為一了。這主要表現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以大小保長或催稅甲頭取代戶長等負責催納賦稅。自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甲頭等也就相應地轉化為鄉役人。兩宋鄉役之制,雖然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時期,就大多數地區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來的戶長、耆長等(鄉書手則于元豐前后上升為縣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長、承帖人及催稅甲頭承擔鄉役之責。雖此后又有元祐改制、紹述之變等反復,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時期,各地多以后者為主。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還有所謂“兼差”之制③。
趙宋王朝給鄉役人所設定的社會角色是“民”,是“庶人在官者”,是國家用來“役出于民”、以民治民的吏民④,其身份并非是“官”。在貴官賤吏的宋朝,鄉役人并非由中央直接任命,其社會地位很低,除王安石變法時外,一般情況下,官方也不支付任何報酬,他們沒有固定的辦公衙門,更沒有國家權力象征的官府印信,所以不能構成一級政權。對于廣大應役的鄉村主戶中的上戶而言,尚有充役為吏的某些好處,而對于鄉村中下等主戶甚至部分客戶而言,卻往往成為自家一項沉重的負擔。⑤但是,宋代鄉役人卻又是介于國家和鄉村社會之間、官與民之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社會群體。他們處于國家權力的“神經末梢”,在填補縣政和鄉治之間“權力空隙”的諸多方面,起著極為關鍵的中介性樞紐作用。國家政令,大凡須由州縣政府轉交于鄉役人,方能最終落實于鄉間;而民生民瘼,也大都經由他們上達于州縣乃至朝廷。國家對于廣土眾民的控制、鄉村社會秩序的維護,尤其是政府斂于民間的各種財賦,也端賴于他們的運作和努力,國家機器方得以正常有效地運轉。
————————————————
① 徐松:《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職官四八之二五,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下同)。
② 《宋會要》兵二之五;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華書局點校本;脫脫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③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門》,中華書局1990年“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轉對論役法札子》,《四部叢刊初編》本。勾勒上述役法變化的已有研究如黃繁光先生《宋代民戶的職役負擔》(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承蒙黃教授慨贈大作,謹此致謝),先師漆俠先生《宋代經濟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有關“兼差制”則參前揭Brian E.Mcknigh所著之第四章。
④ 《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五·役法上》,第4299、4295頁。
⑤ 參見王曾瑜先生《宋朝的吏戶》,載《新史學》第四卷第一期,1993年3月;并其《宋朝階級結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309頁,第333—346頁。
二
北宋前期的里正、戶長、鄉書手和耆長、壯丁等鄉役的設置,現存史料幾乎沒有具體人數設置的記載。但是,依據當時設置名目和士大夫的一些議論,可知這一時期大致的設員情況。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七月,范仲淹在一道奏疏中反映河中府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馀戶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于鄉村差到”①。所謂“鄉村差到”,應指鄉役人。按上述數字,河西縣主戶中平均每4—5戶就輪差鄉役一人,但其中并不包括鄉村客戶在內,這與后來保甲法中“通主、客[戶]為之”②所算出的比例是有差距的。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十一月時,李覯云:“今夫大鄉或二、三千戶,小者亦數百戶。與其使耆、壯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鄉千百戶出力?”③其中的鄉役人數并不確切。同樣,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文彥博有“比近三兩鄉合差一里正”④的建議;熙寧年間,司馬光曾說“向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⑤,均未提及其他鄉役。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在上奏中說,先前“五等之有差役,一鄉不過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⑥。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知靖江府胡舜陟說:“……若祖宗時,于人戶第一、第二等差耆長,第四、第五等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二人而已。今保甲于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⑦只說此前一鄉之中有差役二人,是未將戶長等負責稅收的役人計算在內,但這則資料同樣反映出這一史實,即熙豐以前鄉役人數是比較少的。根據以上文獻中僅存的吉光片羽,大致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即熙豐前,鄉村中一鄉⑧的鄉役人員大致在10人左右。
——————————————
①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譜》,《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載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例”,第5297頁。需要強調的是,擔任保正長者須是主戶。
③ 李覯:《直講李先生集》卷二八《寄上孫安撫書》,《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 文彥博:《潞公文集》卷一七《奏理(里)正衙前事》,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
⑤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三八《衙前札子》,《四部叢刊初編》本。
⑥ 《長編》卷三二四,元豐五年三月乙酉。
⑦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七并六五之八二(靖江,一作靜江,誤);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六與前引《宋會要》的記載相同,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下同)。
⑧ 按宋初以來,職役制度沿襲唐五代舊制,王安石變法初期,仍然設置一都管轄范圍為500戶,與唐一鄉之制相當。因此前并無相關變化的記載,故此處暫按一鄉500戶計。日本學者河上光一也推測,這時鄉役的推行是以100戶左右為單元的,合于唐朝一里百戶之制,參見其《宋初的里正、戶長、耆長》一文,載于《東洋學報》第34號,1952年。
宋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的保甲法規定,以鄉村中相鄰近的每10戶為一小保,設小保長一人;以50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一人;以500戶為一都保,設都副保正二人。不久,又改為以每5戶為一小保,設小保長一人;以25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一人;以250戶為一都保,設都副保正二人①。到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時,已有保甲法混同于鄉役法的記載②。另據“元豐本制”云:“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保]長。今若常輪二太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③朝廷的詔令和現存南宋地方志中所載的有關規定,也與上述熙寧八年之制大體相同,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還有一些細微的變化④。
現存南宋時期的史料,則反映出熙豐之后鄉役人數增加的情況。如前揭紹興五年時胡舜陟就說,自從章惇、蔡京等將經過他們改造的募役法推行于東南地區,“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五十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正、一保副,號為一都”。這樣一來,“今保甲于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不若耆長、壯丁之法為寬”⑤。而在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時,知常州鄭作肅說:“一都之內,當執役者,都副保正凡二人,大保長凡十人,小保長凡五十人。”⑥據上所述,“以一都計之,則廢農業者六十人”⑦,反映出鄉役人數的增長變化情況。換言之,這些史料與熙寧八年的制度規定是一致的。南宋人舒璘以徽州歙縣為例,論說南宋役法弊病云:該“縣三十七都,每都稅[長]二人,則一稅不過七十四人,轉而
——————————
① 《宋會要》兵二之五;《長編》卷二一八,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卷二四八,熙寧六年十一月戊午。而揆諸中國傳統社會之實情,在血緣和地緣關系緊密交織、聚族而居和親善友鄰的鄉土社會中,以5戶為一單位,設置小保長催稅一事,能否真正貫徹到實際之中,或者說,小保長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符合制度制定者的治理理念,通過現存史料還很難加以說明。關于南宋保甲制的編制,可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論差役利害狀》(《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點校本,第866—867頁)、《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一○一載乾道九年十二月詳定一司敕令所修立法條等。
② 《長編》卷二六三,熙寧八年閏四月乙巳條載:“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其并耆長罷之。以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鄉村每主戶十至三十輪保丁一充甲頭,主催租稅、常平、免役錢,一稅一替……凡盜賊、斗毆、煙火、橋道等事,責都副保正、大保長管勾。都副保正視舊耆長,大保長視舊壯丁法。未有保甲處,編排畢準此。”
③ 《宋史》卷一七八《食貨上六·役法下》,第4329頁。
④ 如《宋會要》食貨一四之四七至四八并六五之一○一載紹興五年四月十六日朝廷敕旨云:“于‘大保’字下添‘通’字,‘選保’字下刪去‘長’字。及紹興九年四月四日敕旨,于‘都保’字下添‘通’字,‘選’字下改‘大’字為‘都’字,‘保’字下刪去‘長’字。自此差役極便。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明……故有是命。”類似更改,似都無害于熙寧八年之制的宏旨。
⑤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七;六五之八二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六,紹興五年十二月丙午記事。而據《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二一載淳熙元年三月五日臣僚言“諸路州縣,一都之內,保正凡二,而保長凡八。”同前六六之二六載紹熙二年八月十七日太常少卿張叔椿言:“夫有鄉則有都,有都則有保。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稅用保長二人。二年之間,為稅長者四十人。保正副之數少則上中戶為之而有余,保長之數多則中下戶為之而不足。州縣之間,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長,不理役次,固有朝辭保長之役,而暮受保正之帖者,而上中戶俱受其困矣……”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二一《轉對論役法札子》引紹圣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似有身為保正副而兼任同都保內大小保長者,則一都之中,鄉役總數為50人,如此,則一都役人比熙寧之制少12人。近見楊宇勛先生《取民與養民:南宋的財政收支與官民互動》(臺北,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集刊之31,2003年6月版,第267頁注釋)亦有相似的疑問。兩宋是否皆然,當再詳考。
⑥ 《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六,紹興五年十二月丙午記事。
⑦ 《宋會要》食貨一四之一九。
為十,則一稅將差三百七十人……是向也一稅之內,以七十四家而受此禍;而今也以三百七十家而受此禍”①,同樣反映出鄉役人數的成倍增長。
現存明朝天一閣方志中還有三則相關史料,茲摘錄于下。
唐制: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據唐華亭一縣,統鄉十三,則里正六十五人也。宋制:熙寧以前……熙寧以后,曰保正曰保長,據《嘉熙便民省札》,華亭諸鄉苗稅舊例,差保長三百人有奇。②
宋分鄉、吏二役,舊以人戶等第差充……鄉役:舊有里正、戶長、鄉書手、壯丁,分主賦稅及煙火盜賊。中間罷里正,募耆長。熙寧行保甲法,令五家為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保長,都有都保正副,專一逐捕盜賊等公事。而耆長、戶長專督賦稅。其后,耆、戶長亦廢,保正副遂兼其役。本縣二十里,為都三十有四,保正副六十八人。嘉定間,簿林榘創義役,每都為十甲,大保長十一人,共三百四十人。小保長每甲五人,共一千七百人。鄉書手十八人。③
役法之弊久矣……淳熙六年春……縣十四鄉三十五都,保正凡五十四人,而當役之家實四百三十五,視力高下,出田有差……④
今按:依上所載,宋時華亭縣單保長一役就差有三百多人,比之唐朝差里正65人,已多出5倍。惠安縣有34都,差保正副68人,正好與宋制每都設保正副二人相符;而嘉定后的鄉役人數,大小保長數即達2040人,也反映出其間鄉役人數的增長。至于淳安縣的記載,其35都中當役者達435人,依熙寧之制,應是指保正副和大保長而言。下面,我們再根據成書于南宋淳熙九年的《淳熙三山志》⑤卷一四《版籍類》做成下表,來考察其中的變化情況。
__________
① 舒璘:《舒文靖集》卷下《論保長》,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一《溧陽縣均賦役記》載陸子遇所記宋寧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時,建康府溧陽縣自從推行義役后,溧陽縣“而贏役戶凡得保正三百六十有七,保長二千八百八十有七”。
② 《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戶口》,(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本,第268頁。
③ 《嘉靖惠安縣志》卷七《職役》,(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初編)上海書店1965年影印本。
④ 《嘉靖淳安縣志》卷一四載錄[宋]胡一之《義役記》,(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初編)上海書店1965年影印本。
⑤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華書局1990年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上面兩個表格中的數字統計,未必完備,但仍可反映出以下問題:
其一,在表1中,熙寧元年時,鄉書手還是鄉役之一,到元豐和紹圣之后,則因已上升為縣役而不再列出(修撰于南宋嘉定時期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門》中則明確將其劃為縣役人)。表2中北宋后期和南宋時期所出現的鄉書手,或是福建路所推行的兼差制。
其二,根據表2中福州地區有關年份的民戶總數,我們對淳熙年間鄉役人數在民戶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做一大致測算。據《淳熙三山志》卷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福州民戶總數為321284,而該州所轄諸縣鄉役人數,據現存史料的統計為16486人,所占比例為21.3%。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福州,每5戶左右就有一人充當鄉役。這與每5戶設一小保長的熙寧之制是相符的。
其三,表1中顯示,福州一地元祐元年的鄉役人數為2187人,而到紹圣元年則上升至10429人,比前者多出8242人,后者約為前者的5倍。表2中顯示:連江縣淳熙年間有鄉役1919人,熙寧年間為213人,淳熙比熙寧多出1706人,后為前的8.8倍。長溪縣中,淳熙年間鄉役人數為5440人,比熙寧年間多出5197人,后者為前者的19.7倍。寧德、羅源等縣也有大致相當的比照。另,福建路個別地區的個別年份也有差派甲頭催稅的情況,但在表2中并沒有顯示。而倘若再依各地每20—30戶(一般應接近30戶)設立一催稅甲頭計算,以一都250戶計,每都應有8名左右的催稅甲頭,若非兼差,基層鄉村負責稅收者則又有增多①。
_________
① 據《宋會要》食貨六六之七三并六五之七七載紹興元年九月十二日臣僚言:“……大保長催科,每一都不過四家……今甲頭每一都一料無慮三十家……”可知。另汪應辰《文定集》卷五《論罷戶長改差甲頭疏》載,潼川府中江縣差甲頭862人,懷安軍金堂縣差甲頭700人。又據真德秀言,福建路浦城縣七十二都,每年差144名保長催督夏秋二稅,見《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九《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四部叢刊初編》本。關于一都催稅者僅有大保長四人,朱熹曾說:“……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但他又同時又有“……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之說,均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論差役利害狀》,據《朱熹集》第s66—867頁。這和前揭《宋會要》均與熙寧之制不符,尚需詳考。
其四,分析表2中的數字,我們發現,各縣并未嚴格按照熙寧之制設置鄉役人員,而只是與制度大體符合而已。如,就連江縣淳熙年間的鄉役而言,保正副為60人,則大保長應為300人,小保長應為1520人,而史料的實際記載卻是大保長302人,小保長則實為1520人;再以長溪縣為例,元祐年間的鄉役人數是263人,而淳熙年間缺少大保長的記載,卻同時兼差有耆長、壯丁和鄉書手。再如,古田縣淳熙年間設有81名保正副,那么,按規定,則大保長的人數應是405人,小保長的人數應有2025人,而實際史料的記載,大保長只設398人,小保長只設1874人;再看永福縣的情況,淳熙年間,該縣設73名保正副,那么,按規定,其大保長、小保長設置的人數應該分別是365人和1825人,而實際史料的記載卻分別是316人和1030人。其中的差距是比較大的。閩清、寧德、羅源等縣的情況也大致相當。總之,從中既可以發現前后鄉役人數的增加,也可發現其中的人數設定并非十分嚴格。這或許既與中國傳統社會構成中,國家對于地方的控制,越到基層,管理機制的控制力就越顯松弛的特點有關,似也與王安石等在制訂保甲法之初,就有因地制宜的規定有關①,即各地可以因民戶多少以及“其風俗利害,各有不同去處”②等因素,而確定都保、大小保的具體設定。
通過上面的兩個表格,還可以發現,宋神宗熙豐以后,福建路等地鄉役人數大幅度增長的史實。這相對于北宋初期而言,增長數量確實是比較大的。雖然現存史料僅江浙、福建等地的記載較為詳備,其他地區的相關史料卻相對缺乏,但是,參照熙寧八年的朝廷詔令,南宋時期朝廷的屢次詔敕以及各地官員的反映,大致可以說,北宋熙豐后、整個南宋時期比熙豐之前鄉役人數的增加,應是一個不爭的史實。
____________
① 《長編》卷二四八,熙寧六年十一月戊午條載朝廷準司農寺奏請:“……但及二百戶以上,并為一都保,其正、長人數且令依舊。即戶不及二百者,各隨近便,并隸別保。諸路依此。”并《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五》,第4300頁。
② 《宋會要》食貨六五之八二,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廣東轉運常平司據知平江府長洲(一作常州,誤)縣丞呂希常陳請。據史料記載,各地還出現了如下現象:如《宋會要》兵二之二○載元豐四年正月判尚書兵部蒲宗孟言:“開封……十大保為一都保,保外別立副都保正各一人,及二小保以上亦立大保長一人,五小保以上亦立都保正一人,不及者,就近附別保。隔絕不可附者,二小保亦置大保長一人,四保亦置保正一人。”又《宋會要》食貨六五之八八載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十日權知復州章燾言:“湖北、京西州縣有戶口稀少去處,其都分名額悉無改并,每遇都副保正闕,官司依舊隨都選差,則是頻并。欲乞今后每一都人戶若不及五大保處,即合并接鄰近都分人戶通行選差都保正一人……候人戶各及一都之數日,仍舊選差。”得到朝廷的允許。又,《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九○載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四日,朝廷也批準了處州遂昌縣丞黃揩的奏請“……兼契勘州縣差募保正副,依法系以十大保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材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緣州縣鄉村內上戶稀少,地理窄狹,并有不及一都人戶去處,致差役頻并。今看詳,欲下諸路常平司行下所部州縣,委當職官將都保比近地里窄狹,人煙稀少并不及十大保去處并為一都差選,仍不得將隔都及三都并為一保,如內有都分人煙繁盛,山川隔遠,更不須撥并。其并過都分,從本司保明供申……”再如《宋會要》食貨六五之一○一載乾道九年十二月時,詳定一司敕令所修立下條云“……諸村疃五家相比為一小保,選保內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內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通選都保內有行止、財勇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余及三保者亦置大保長一人,及五大保者置都保正一人。若不及,即小保附大保,大保附都保”;以及宋金邊界地區因民戶稀少而合并都保等等相關記載。另,在狹都戶貧處,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論差役利害狀》還有以下的議論:“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并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據《朱嘉集》,第866—867頁。
上溯隋唐,我們再看有宋之前鄉村管理體制中設員的情況。隋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二月,隋高祖的詔制云:“五百家為鄉,正一人;百家為里,長一人。”①杜佑《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載:“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人大村,不須別置村正……”②則反映出中唐以前鄉村管理體制的狀況。與宋朝并存二百多年的金朝(公元1015—1234年),也大致沿襲上述隋唐兩朝的鄉村之制。其500戶中所設管理人數,一鄉五里在6人左右;村正的設置,似乎只在少于10戶的村落才能設置一人,而具體人數設置卻難以確定,但考慮到平原與山區的區別,以及古代人口較少,并且為了合力耕作和共御盜賊,一般在平原聚族而居的村落,人戶稍多,則村正人數較少;偏僻山區、湖泊的居民,則多散居各地,一鄉所設,應該稍多。中唐以后,鄉里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唐后期的鄉村管理體制中,則在原有設置的基礎上又出現了“書手”等役名,五代時期則又出現了“耆長”、“三大戶”等。這時,鄉村管理人員較此前大致已有所增加③。上述似乎可以表明,鄉村管理人員是逐漸增加的:北宋前期,鄉村社會中還沒有大量增加管理人手,直到熙豐之后,才出現了大量增加的現象。由唐朝初期500戶中僅設10人左右(唐后期設置數量上的變化情況,現存文獻并無更為明晰的記載),到宋神宗朝以后,每500戶中多達120人左右,鄉役人數增加了數倍之多,這一變化是極其顯著的。
三
由唐人宋,特別是在宋神宗朝以后,鄉村社會中何以出現鄉役人數大幅增長這一現象,其中是否蘊涵有唐宋之際社會變革、國家權力極欲滲透到基層社會,以強化政府對鄉村的治理等史實④,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等,又可以申述并印證哪些史實,尚有待進一步探索。下面,謹從唐宋社會經濟變革的角度,稍加探索。
唐中葉以來,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較快,隨著兩稅法的實行,改變了過去鄉村賦稅征收的體制,與此同時,民戶有了更多流動的自由,且逐漸為社會所接受。因事設職是行政管理體制中慣常的道理。為了適應社會和經濟領域的變化,勢必要求鄉村社會管理體制的適時應變。
____________
① 魏征:《隋書》卷二《高祖紀》,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32頁。
② 杜佑:《通典》卷三《食貨三》,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62—63頁。依同書第68頁王永興先生所做校勘記云“其村居如滿十家者求人大村,疑‘如’下脫‘不’字。這一推斷,頗有道理。
③ 李錦繡先生從地方財政的角度,探討了唐朝后期州縣鄉村胥吏的增加及其作用,見其《唐代財政史稿》下卷第一編第六章第三節《里胥典正與地方財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06頁。
④ 最近,黃寬重先生《唐宋基層武力與基層社會的轉變——以弓手為中心的觀察》(《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拙文《宋代鄉村精英與社會控制》(《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2期)對此進行了討論。拙作淺陋,純屬初步涉及。其中諸色鄉役、縣役的社會效用較之縣尉、巡檢等,似乎更能反映出唐宋時期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滲透的努力,但尚有待進一步詳加探討;黃先生的大作則跨越唐宋,視域廣闊,挖掘甚深。
第一,魏晉南北朝以降,迄于隋唐,門閥士族開始走人城市,他們在鄉間的統治力量逐漸減弱,原來在宗主督護制下,士家大族強有力控制鄉村民眾的現象不復存在①,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權力對鄉村的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所以,中唐五代和宋初,國家控制力難以抵達鄉間,更缺乏支配每一個社會細胞的能力,似乎可以說是鄉村發展史上的一個無序化時代。入宋后,統治者勢必要采取措施,以彌補前此“權力空隙”,加強國家對鄉間的控制。鄉役人數的增加,以及宗族重新出現等,都是宋政府為順應這一歷史發展趨勢所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唐以后,“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②,或說“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③的新稅制的出現,即由“稅丁”到“稅產”的變化,對國家基層管理方式影響很大。我們知道,相比而言,“稅丁”的方式簡單而易行,履產而稅,這就需要鄉村稅收人員在履定稅額時,既要走遍所轄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邊邊角角,勘驗田畝多少、貧腴成色,又要到農戶家中逐一檢察各種各樣的家產,以便最后計算鄉戶的資產總數,評定戶等,征稅派役。自中唐人宋后,鄉村賦役攤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鄉村主戶的戶等、按家業錢和稅錢等劃分鄉村主戶戶等的財產標準。這四種方式往往重疊,又派生出多種攤派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④鄉村稅收人員的工作日趨復雜化了,工作量也大大地增加了。這樣一來,就需要增加人手,以便及時有效地完成上述各項事務⑤。這是中唐以降尤其是宋代,鄉役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三,按“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⑥的規定,改變了過去人口相對固定的戶籍制度,鄉村民戶對于地主的人身依賴漸趨淡化,有了一定的流動自由。在租佃關系占主導地位的宋代,佃戶還擁有了一定程度的起移權,流動性也相對增大⑦。民戶的自由流動,和災荒、戰亂等因素導致的民戶流移,不但使社會治安
_______________
① 參見韓昇先生《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劉昫:《舊唐書》卷——八《楊炎傳》;同書卷四八《食貨志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421、2093頁。
③ 陸贄:《唐陸宜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 《唐陸宜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囤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已大致反映出兩稅法之后計算民戶資產、評定戶等的繁難。類似論說,宋人尤多。梁太濟先生對此有精詳研究,參其《宋代家業錢的估算內容及其演變》,載《宋遼金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91年版,今據氏著《兩宋階級關系的若干問題》,河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另參閱王曾瑜先生《宋朝劃分鄉村五等戶的財產標準》,載《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并《宋朝鄉村賦役攤派方式的多樣化》,載《晉陽學刊》1987年第1期。
⑤ 本處參考了王棣先生《從鄉司地位變化看宋代鄉村管理體制的轉變》(載《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代鄉里兩級制度質疑》(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兩文中的部分研究。
⑥ 《舊唐書》卷——八《楊炎傳》,第3421頁。
⑦ 參見先師漆俠先生《王安石變法》(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頁。朱瑞熙先生《宋代社會研究》,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38—43頁。陳明光先生《唐朝兩稅預算形式與封建人身依附關系》,見氏著《漢唐財政史論》,岳麓書社2003年版。
問題日益突出,而且也進一步給評定鄉村民戶的戶等、征收賦稅等帶來了難度。由于宋代田產、戶等以及其他家產的變動是極其頻繁的,有限的人手難以勝任評定戶等、征派賦役等繁難的工作,所以,在基層社會管理中,不但要增加鄉村社會治安人員,而且也往往差派他們承擔催稅的任務。第四,鄉役人數的變化,也是與宋朝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等,尤其是與財政收支狀況密切相關的。自宋仁宗朝以來,三冗三費和積貧積弱、邊境等問題就日益突出出來,此后,趙宋朝廷就陷入了財政上人不敷出的窘局。疆域大為縮減的南宋更是如此,國家財政也更顯窘迫,地方州縣財政同樣日益匱乏①。既然國家允許土地私有,并確定根據產業的多少繳納賦稅,那么,具有這樣或那樣背景的形勢戶官戶、豪強民戶就會想方設法隱瞞田產,貧窮不能自存的民戶則只能蔽身于形勢戶,詭名挾戶(隱戶)、詭名寄產、詭名挾佃等現象也就隨之出現,并成為宋朝一大社會痼瘤②。總而言之,對于趙宋王朝來說,其所要求于鄉役人者,最主要的有兩點:第一,及時、足額完成稅收任務,以保證國家財政的正常運行;第二,保證基層社會秩序的安定。為了應對上述各種壓力和社會變動,就需要向鄉村民戶征收盡可能多的賦稅,以保證國家財政的運轉。國家賦稅本已沉重,而這些官無俸給的地方吏役還會對民戶有更多的侵剝,這就導致鄉村民戶負擔的增重。剝削量的增加,無疑又會引起民眾各種方式的反抗,一些鋌而走險者就時不時地對地方政府構成威脅。隨著財政稅收和鄉村治安管理問題的突出,如何避免中唐五代以來基層社會失控等問題,并進一步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從稅收和治安兩個方面,加派替政府管理廣土眾民的鄉役人員,也就成為宋神宗和王安石們治理國家的要務了,有關鄉役問題自然也就引起了此后宋朝君臣更多的關注。順應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于是,在這一時期,鄉役人數也就發生了數量上的較大增長。宋代鄉役人數的增長,其社會作用固應重視,然社會影響也不容忽視。另外,這一增長從某些方面也顯現出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延伸的趨勢,但是,考諸于兩宋社會之史實,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說,這一趨向并非宋王朝政治制度的治理理念所在,而是從保證國家財政和政權穩定的角度,所轉化出的一種統治意向。③
——————————————————
① 參見前揭《王安石變法》(增訂本),第18—27頁。并黃繁光先生《宋代民戶的職役負擔》第三章,第257—268頁;汪圣鐸先生《兩宋財政史》第一編諸章,中華書局1995年版;包偉民先生《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第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95頁。兩宋差役、募役之爭,以及鄉役人并無官方支付的報酬,而淪為“職役”,都是和國家財政狀況密切相關的。這也是兩宋期間役法中有“名募實差”現象及其一再更革的原因所在。
② 參閱王曾瑜先生《宋朝的詭名挾戶》,載《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4—5期。
③ 習作先后承蒙王曾瑜、李治安、汪圣鐸、黃寬重諸先生惠賜教益,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