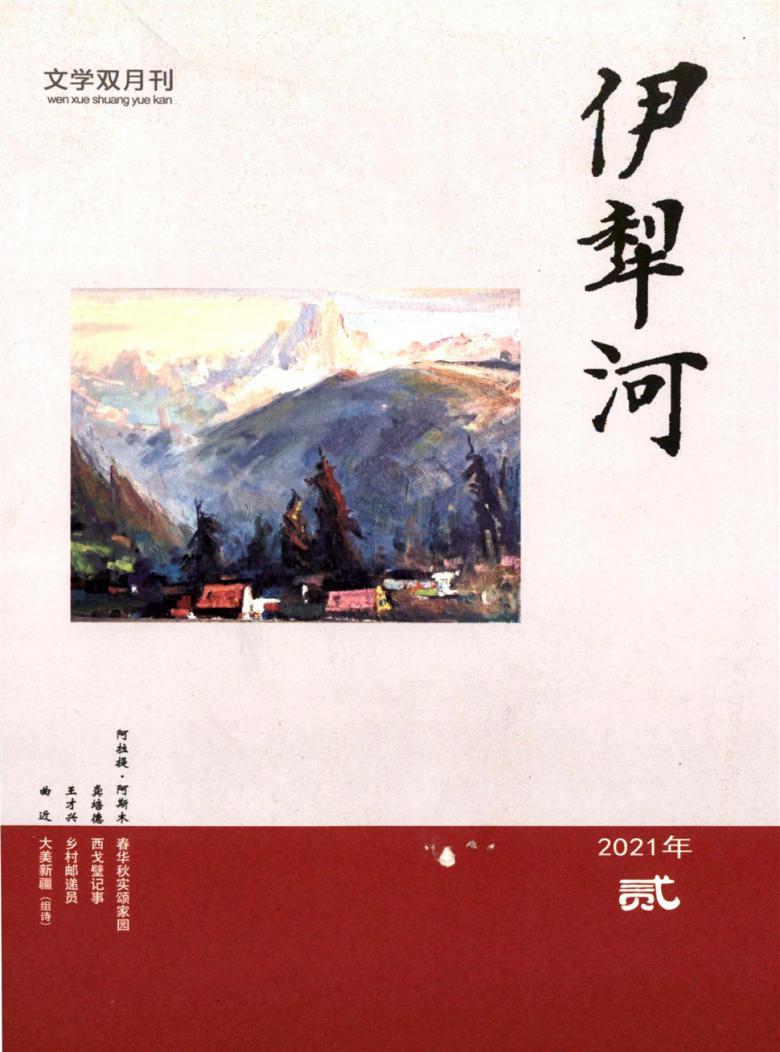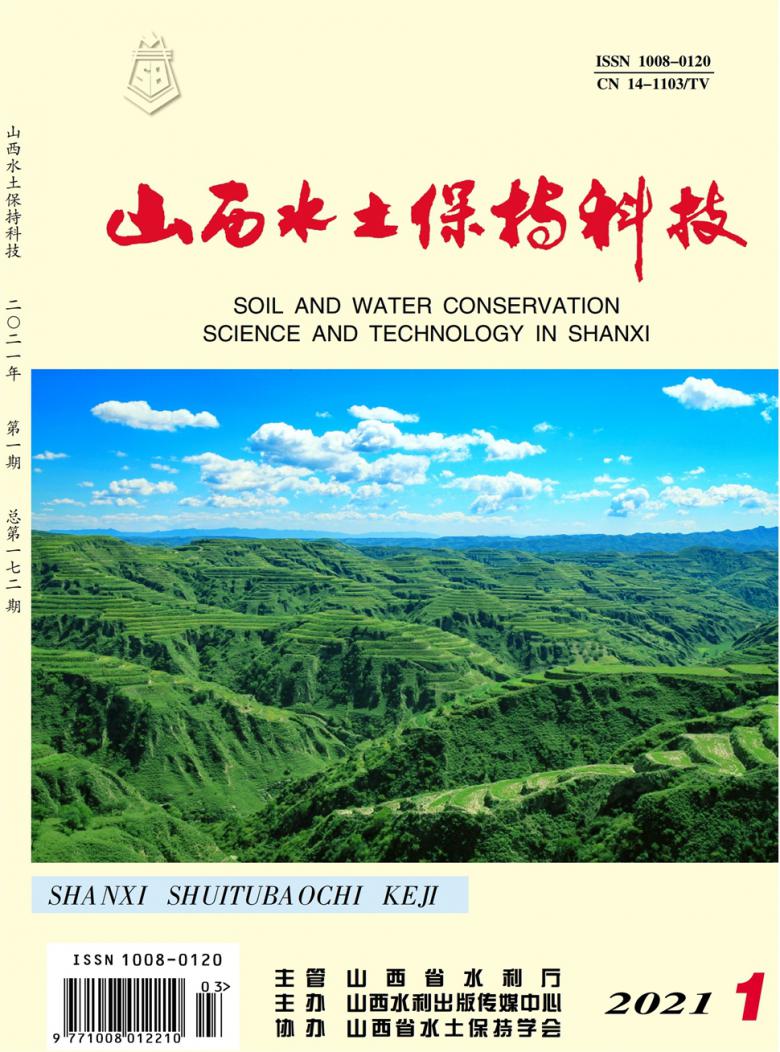宋代兩浙路的市鎮與農村市場
陳國燦
【內容提要】在宋代兩浙地區,隨著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躍和草市、鎮的大量興起,農村市場快速發育和成長,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兩級市場網絡,并與發達的城市市場結合,進而形成了區域性多層次的等級市場體系。但宋代兩浙路農村市場的發展又是有限的,各地區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性。
【英文摘要】The during Song Dynasty,with the aris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towns in Liangzhe area,market grew up rapidly in the countryside,andthe system of market network appeared.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market towns was limited and they were different level according to thearea.
【關 鍵 詞】宋代/兩浙路/市鎮/農村市場Song Dynasty/Liangzhe(兩浙)/Market Towns/Rural Market
【正 文】
商業性市鎮在鄉村和城郊地帶的廣泛興起和發展,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在兩浙路(其范圍約當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蘇南部),各種市鎮的大量涌現和快速發展,有力地推動了農村市場的發育和成長,引發了農村社會的一系列變革,導致了局部地區鄉村都市化現象的出現。下面,本文從市鎮的角度出發,試就宋代兩浙路農村市場的發展形態及其局限作一探討。
一、草市的廣泛興起和農村初級市場的形成
宋代的市鎮總體上可分為草市和鎮兩種。其中,草市多為小規模的鄉村集市和商業點,承擔著農村初級市場的功能;鎮是規模相對較大的經濟中心地,起著農村中心市場的作用。
草市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現。在兩浙地區,早在六朝時期,就興起了不少草市,如吳興郡(治今湖州)的陸市(又稱新市)[1]、會稽郡(治今紹興)的臨浦市[2]等。但直到宋初,草市的數量仍相當有限,且大多只是相鄰村落之間互通有無的一種交易場所。從北宋中期起,隨著兩浙社會經濟的繁榮,商業活動由城市深入到鄉村,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的生產規模和流通范圍不斷擴大。如太湖流域的蘇、湖、秀、常等州,是全國最著名的糧食產地和輸出地之一,民間廣泛流傳有“蘇湖熟,天下足”[3]、“蘇常熟,天下足”[4]之類的諺語;婺州的紡織業十分發達,“號稱衣被天下”;[5]位于浙西山區的睦州(嚴州),“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6]是重要的山貨輸出地。這種活躍的商品生產和流通,給兩浙農村傳統的自然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廣大農民越來越多地卷入到市場活動之中。在此基礎上,各種草市大量涌現。據畢仲衍《中書備對》記載,到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兩浙路共有坊場河渡1238處,[7]其中相當部分即屬于草市。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征榷考》云:“坊場,即墟市也,商稅、酒稅皆出焉。”假設在兩浙路的坊場河渡中,一半為河渡,且一地數坊場(即一處草市同時設有酒坊和稅務)的重復率為1/3,則草市的數量仍達200多個。宋室南渡后,兩浙路的草市數量又有大幅度的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僅目前尚有史可考的就有500多處,[8](p450-477)實際數量肯定還要多。即便以500處計算,其分布密度就已經相當高了。從地域密度看,兩浙路約122622平方公里,[9]平均245平方公里即有1處;從人口密度看,南宋時期兩浙路戶口的最高記錄是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的2898782戶,[10](卷83玉牒初草)平均近5800戶即有1處。特別是在浙西太湖平原和浙東沿海地帶,分布尤為密集。如到南宋中期,太湖周邊的平江(蘇州)、嘉興(秀州)、湖州等地,共有草市200多處。
與此同時,草市的形態也發生顯著變化,其突出表現是:第一,商業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功能日益增強。早在北宋中期,兩浙路草市的商業就已相當活躍。以前文提到的熙寧九年坊場河渡的情況為例,雖然兩浙路的坊場數量在全國23路中居第12位,但年稅收總額卻僅次于成都符路而高居第2位,可見其個體商業發展水平較其他地區要高得多。特別是那些興起于大中城市周圍和農村交通線上的草市,商業尤為發達。如熙寧十年(1077年),杭州的龍山市、柏坎市,越州的龍山市,常州的岑村市,秀州的金山市、廣陽市,溫州的路橋市等,年商稅額都在1000貫以上,幾與一般縣城相當;蘇州的昆山市和杭州的浙江市更是分別高達7448貫和26446貫,與部分州級城市相當。[11](16之7至9)到南宋時期,兩浙各地的草市商業更是空前興盛,不僅像浙江、龍山之類的城郊草市,“商賈駢集,物貨輻萃”,“車馳轂擊,無間晝夜”,[12](卷21橋道,引馮楫中興永安橋記)而且那些遠離都市乃至地處山區的草市也十分活躍。如紹興府城西北50里的禹會橋市,“橋邊多酒樓”;[13](卷77舟中醉題)臺州天臺縣山區的折山市,“折山山下簇人煙,一似吳兒笑語喧”。[14]第二,市場活動突破狹隘的地域限制,對外聯系不斷增強。北宋時,兩浙路不少草市的對外商貿往來就已相當活躍,如處于崇山峻嶺之中的嚴州淳安縣云程市,“其水陸達杭、越、衢、建,凡舟車日夜之所奔走”。[15]迨至南宋,這種現象更為普遍。如平江府的許多草市與浙東、閩、廣等地都有密切的商貿關系。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有臣僚上奏說:“黃姚稅場系二廣、福建、溫、臺、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輻輳之地,南擅澉浦、華亭、青龍、江灣牙客之利,北兼顧逕、雙浜、王家橋、南大場、三槎浦、沙涇、掘浦、肖逕、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稅,每月南貨商稅動以萬計。”[11](18之29)這里所說的黃姚、江灣、顧逕等草市,即分屬于平江府嘉定、常熟、昆山等縣。第三,專業性市場的大量出現。如南宋時期,紹興府山陰縣的梅市和項里市,是著名的楊梅和茨實市場,詩人陸游曾以“明珠百舸載茨實,火齊千擔裝楊梅”[13](卷44戲詠鄉里食物示鄰曲)等詩句來贊嘆這兩個草市的興盛;秀州華亭縣的下砂市、海鹽縣的鮑郎市、明州鄞縣的大嵩市等則是著名的鹽業草市,年產鹽量均在萬石以上;嘉興府(秀州)崇德縣的濮院市(又名永樂市),是頗具規模的紡織業草市,“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云集”。[16]
隨著草市的廣泛興起和發展,到南宋中期,在兩浙路的不少地區逐漸形成了密集的農村集市網絡。以紹興府境內的鑒湖流域為例,在東西約100余里、南北不到50里的區域內,分布著30多處草市,它們以紹興府城為中心,呈放射狀向四周擴展。其中,有的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常設市,如城西6里的西跨湖橋市,樓臺參差,商船會集;[13](卷55泊舟湖橋酒樓下)城西11里的湖桑堰市,“居民頗繁”;[13](卷68行飯至湖上)城東60里的東關市,市街寬闊。[17](卷4堰)有的則是村頭路邊的墟市,如城東北40里的小江市,“數家茅屋小江頭”;[13](卷67小江)城西南12里的亭山市,“一汀蘋露漁村晚,十里荷花野店秋”。[13](卷17秋夜泊舟亭山下)在市時上,有早市、晝市、夜市之分。如城西南9里的三山東市,夜市十分活躍,“誰令屠沽居里中,鼓聲終夜聒老翁”。[13](卷64夜聞堤東賣酒鼓聲嘩甚)在市場形式上,除了一般性的鄉村集市外,還有不少專業市場,如前文提到的梅市和項里市就是頗為典型的例子。曾長期游歷鑒湖流域的著名詩人陸游,在其《劍南詩稿》的不少詩篇中經常提到諸如茶市、魚市、菱市、筍市、花市、樵市、果市之類的專業草市。顯然,在鑒湖流域,隨著草市網絡的形成,不僅將市場活動引入到各個鄉村,而且使得原本處于孤立、分散狀態的農村小規模商品交易活動互相結合起來,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農村初級市場體系。
二、鎮級經濟中心地的發展與農村中心市場的成長
鎮的設置始于南北朝時期。但在宋代以前,它一直是封建政權用以加強對各地人民控制的軍事據點,而非農村經濟發展的產物。北宋建立后,鎮的性質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逐漸向農村經濟中心地演變。在兩浙地區,大體到北宋中期,鎮作為農村經濟中心地的意義已基本確立。以熙寧十年(1077年)的商稅為例,在全路共86.8萬余貫的總稅額中,屬于草市鎮的有近14萬貫,占總額的16.13%。其中秀州、杭州的草市、鎮稅額,在所屬州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更是分別高達30%和29.38%。[11](16之7至9)而在各州草市、鎮稅額中,鎮的稅額又占了大部分。這表明,鎮級中心地已成為各地工商稅收的重要來源。就鎮的數量而言,根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到宋神宗元豐(1078-1085)初年,全路共有75個。進入南宋以后,又有進一步增加。如杭州由12個增至15個,嘉興(秀州)由4個增至6個,明州由3個增至7個,處州由3個增至6個,衢州由2個增至4個。[8](P450-477)估計到南宋中后期,全路已有鎮100個以上。
兩浙各地鎮的數量雖較草市要少得多,但其在農村市場體系中所起的作用卻是大多數草市所無法比擬的。這可從四個方面來看:第一,鎮的人口規模比草市大。它們一般都有數百戶固定的居民,有的甚至達到上千戶乃至數千戶。如南宋中后期,臨安府仁和縣的臨平鎮有“約千余家”;[18]嘉興府海鹽縣的澉浦鎮有“約五千余戶”;[19]慶元府(明州)奉化縣的鮚埼鎮,“生齒厥多,煙火相望”,環鎮居民數千家;[20]湖州烏程縣的烏墩鎮和德清縣的新市鎮,“其井邑之盛,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21]而草市的居民一般多只有數十家乃至數家而已。第二,鎮在社會形態上已具有不少城市化的特征。如南宋時,海鹽縣澉浦鎮所轄南北5里,東西12里,面積約60平方里。在鎮中心,有街道、坊巷,有商業區、居民區和行政區,以及各種市政設施。其居民已不再屬于鄉村戶籍,而是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戶系統,他們的社會生活也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城市化特點。[19]其它如平江府的福山,嘉興府的青龍、上海、烏青、魏塘,湖州的新市,常州的湖濮,臨安府的臨平、江漲橋,紹興府的西興、漁浦、曹娥,慶元府的鮚埼,臺州的章安,溫州的白沙等鎮,也都與澉浦鎮的情況相似。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鎮已是初步成形的經濟都市。第三,鎮的工商業發展迅猛。以商稅為例,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兩浙路年商稅額1000貫以上的草市鎮稅場共31處,其中25處屬于鎮級稅場。[11](16之7至9)進入南宋以后,許多鎮的商稅額進一步呈現快速增長之勢。如常州的青城、萬歲、張渚、湖濮四鎮,年商稅額由熙寧十年的5241貫增至咸淳(1265-1274)初年的23839貫,增長3.5倍多;[22]臨安府的江漲橋、北郭二鎮,由2805貫增至咸淳初年的145908貫,增長達51倍多;[12](卷59貢賦)紹興府的曹娥、三界、漁浦三鎮,由9083貫增至嘉泰(1201-1204)初年的12749貫,增長40.36%;[17](卷5課利)特別是臨安府的北郭、江漲橋,嘉興府的烏青、澉浦、魏塘,慶元府的鮚埼等一批巨鎮,年商稅額都在3萬貫以上,超過了同期許多縣級城市。第四,鎮的市場專業化水平高。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到南宋時,兩浙各地鎮市逐漸呈現出專業化的特征。如臨安府的北郭、江漲橋是典型的環城商業鎮;嘉興府的魏塘、婺州的孝順是典型的農業鎮;溫州的白沙是典型的林業鎮;嘉興府的澉浦、青龍和臺州的章安是著名的港口鎮;臺州的杜瀆、于浦,慶元的岱山,紹興府的錢清、西興、曹娥,嘉興府的廣陳等是重要的鹽業鎮;湖州的南潯是絲織業鎮;紹興府的楓橋、三界是造紙業鎮;湖州和嘉興府的烏青、四安,平江府的平望,鎮江府的呂城,常州的奔牛,紹興府的漁浦,衢州的孔步是典型的交通型商品轉運鎮;平江府的許浦、福山、梅李是消費型鎮。這種市場專業化特征的出現,標志著鎮的市場形態日趨成熟,市場分工日趨精細。
從鎮的地理分布狀況,或許能更清楚地看出其在農村市場和城鄉市場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以紹興、慶元、臺州為例,紹興府各縣鎮的分布狀況是(括號內為距所在縣城里程數,下同):三界鎮(東南120),東城鎮(東60),曹娥鎮(東南72),錢清鎮(西北50),蛟井鎮(西南15),南安鎮(西50),楓橋鎮(東北50),西興鎮(西12),漁浦鎮(南35),五夫鎮(北30),纂風鎮(西北70)。[17](卷12八縣)慶元府各鎮的分布情況是:小溪鎮(南40),公塘鎮(西北30),鮚埼鎮(南20),澥浦鎮(西北60),岱山鎮(海中)。[23](卷13-20)臺州各鎮的分布情況是:大田鎮(東30),章安鎮(東南120),杜瀆鎮(東180),于浦鎮(東南60),路橋鎮(東南30),嶠嶺鎮(南120),港頭鎮(東南15),縣渚鎮(南70)。[24]從中可以看出,絕大部分鎮都分布于距州縣城二三十里以遠的地區。這表明,鎮和縣級城市有著各自的市場輻射空間,前者屬遠離城市的鄉村地帶的中心市場,后者屬于城市初級市場。兩者的互相結合,便構成了所在地區城鄉市場體系的基礎。可見鎮既是農村中心市場,也是聯結城市市場和農村市場的主要紐帶。而且,作為新興的經濟中心地,鎮市有著諸多縣級城市所沒有的有利條件,如較少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接近各種農村商品的產地,有著充裕的廉價勞動力等等。因此,到南宋時期,隨著農村經濟的繁榮和城鄉商品流通的活躍,不少鎮的市場發展水平平不僅趕上、甚至超過了所在縣城。 三、農村市場發展的局限性
在探討宋代兩浙路農村市場發展的同時,也應看到,這種發展又是有限的。一方面,兩浙路農村市場發展的基礎并非專業化的商品生產,而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簡單化商品流通,故從根本上講,仍只是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前文曾指出,促成草市、鎮在兩浙路廣泛興起的一個直接動力是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躍,而導致商品流通異常活躍的因素,除了農村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各級城市的興盛外,還有各地區地理特征的巨大差異所造成的自然性生產分工以及政府賦稅征收的貨幣化傾向。就地理狀況而言,兩浙路北部是較為廣闊的太湖平原,東部是濱海小平原和丘陵,西部和南部則是廣袤的山區和內陸盆地。與這種地理格局相對應,各地區農村的生產狀況和物產構成也有很大差異。以糧食為例,地處太湖平原的蘇、湖、秀、常等州府,因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深厚的歷史基礎,到宋代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糧食產地和輸出地。史稱:“兩浙之地,湖、蘇、秀三州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25]而兩浙路其它地區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耕地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常常需要從蘇、湖等地輸入大批糧食。如南宋時,嚴州“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搬販斗斛為命”;[10](卷11建德縣賑糴本末)紹興府“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豐如浙西米斛之多”;[26]明州“小民卒仰米浙西,浙西歉則上下皇皇”。[23](卷16敘產)溫州、臺州、衢州、處州等地的情況也大致相似。顯然,糧食之所以成為兩浙農村市場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是與各地自然地理條件的差異密不可分的。也正因為如此,雖然市場上糧食的流通量很大,但其基礎主要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而不是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宋末元初學者方回在談到嘉興府魏塘鎮的糧食流通情況時說:“佃戶攜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醯、漿粉、麩曲、椒姜、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準之。整日得米數十石,每一百石,舟運至杭、至秀、至南潯、至姑蘇糶錢,復買物歸售。”[27]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情況。就賦稅制度而言,在宋代的各種賦稅中,貨幣稅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時期,更是如此。時人曾感嘆地說:“今民之輸官與其所以自養者,悉以錢為重,折帛以錢,茶鹽以錢,芻豆以錢……酒醋之賣于官,非錢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錢不行;坊場河渡之買撲,門關務庫之商稅,無一不以錢得之。”[11](66之15)兩浙路一直是賦稅最為繁重的地區之一,其貨幣稅的征收額也相當龐大。如宋寧宗嘉泰元年(1201年),紹興府所屬各縣僅貨幣形式的各種雜稅就高達100萬貫。[17](卷5賦稅、課利)為了完納賦稅,廣大農民不得不將更多的產品投放市場,不少人“雖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賦稅,須別作營生”。[26]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村市場的畸型繁榮。
另一方面,兩浙路農村市場的發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從草市、鎮的數量和分布密度來看,浙西的蘇州、鎮江、湖州、秀州、杭州和浙東的紹興、明州、臺州等地,其草市、鎮數量占了全路總數的90%以上;而浙西的嚴州和浙東的處州等地,數量較少。特別是地處山區的嚴州,在整個宋代幾乎沒有涌現較具規模的市鎮。從草市、鎮的發展形態來看,浙西地區(除嚴州外)的市鎮無論在規模還是在市場發展水平上,都走在浙東各地前面。如在市鎮人口方面,南宋時浙西各地相繼涌現了一批居民在千戶以上的大型市鎮,如臨安府的臨平,湖州的烏墩鎮和新市鎮,秀州的澉浦鎮、青龍鎮、上海鎮,平江府的昆山鎮,常州的湖濮鎮等;而浙東沿海只有明州的鮚埼鎮等少數市鎮達到如此規模;地處浙東內陸的婺州等地,則始終沒有巨鎮出現。在市鎮的工商業發展水平上,北宋熙寧十年,年商稅額在千貫以上的市鎮,浙西除嚴州外共有22處;浙東只有7處。草市、鎮稅額在所在州府總稅額中所占的比重,秀州為30%,杭州為29.4%,潤州為16%,蘇州為15.8%,常州為15.4%,湖州為12.4%,均在10%以上;浙東除越州和溫州分別為18.2%和14.8%外,其它各州均不到10%。特別是婺、衢、處三州,平均只有2.7%。[11](16之7至9)南宋中后期,臨安府的浙江、北郭、龍山、江漲橋和嘉興的澉浦、魏塘、烏青等市鎮,年商稅額都在3萬貫以上,湖州的四安、常州的湖濮、嘉興府的青龍、平江府的黃姚和顧逕等市鎮,也都在萬貫以上;而浙東即便是那些大型市鎮,年商稅額一般也只有數千貫。如宋寧宗嘉泰(1201-1204)初年,紹興府所屬的錢清、曹娥、三界、蛟井、楓橋、漁浦、新林諸市鎮的年商稅額分別為1945、6285、1544、1743、3090、2673和1139貫,[17](卷5課利)無一超過萬貫。事實上,不僅浙西與浙東之間、東部沿海和西南部內陸之間,在市鎮和農村市場的發展水平上存在明顯差距,而且在各州府內部,也同樣存在著不平衡現象。如南宋中后期,慶元府鄞縣共有市鎮42處,占了全府市鎮總數的近1/3,而象山縣僅有5處,只及鄞縣的1/8弱。這種地域格局的不平衡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兩浙農村市場在總體上尚未達到成熟的形態。
[1]嘉泰吳興志(卷18事物雜志)[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2]寶慶會稽續志(卷3市)[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3]范成大.吳郡志(卷50雜志)[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4]陸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閘記)[M].四庫全書本.
[5]劉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狀)[M].四庫全書本.
[6]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42)[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7]永樂大典(殘本,卷7507常平倉)[M].
[8]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9]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64.
[10]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庫全書本.
[11]宋會要輯稿(食貨)[M].中華書局影印本.
[12]咸淳臨安志[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13]陸游.劍南詩稿[M].四庫全書本.
[14]袁甫.蒙齋集(卷20憩折山市)[M].四庫全書本.
[15]方逢辰.蛟峰集(卷5芳潤堂記)[M].四庫全書本.
[16]光緒桐鄉縣志(卷1疆域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17]嘉泰會稽志[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18]方回.桐江集(卷13過臨平)[M].四庫全書本.
[19]常棠.紹定澉水志(卷1地理門)[M].臺灣大化書局影印本.
[20]吳潛.許國公奏議(卷3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彌盜賊)[M].四庫全書本.
[21]薛季宣.浪語集(卷18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M].四庫全書本.
[22]咸淳毗陵志(卷24賦稅)[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23]寶慶四明志[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24]嘉定赤城志[M].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25]王炎.雙溪集(卷11上趙丞相書)[M].四庫全書本.
[26]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狀)[M].四庫全書本.
[27]魏了翁.古今考(卷18附方回續考)[M].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