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
王廣慧 張世偉
【摘要】依據(jù)吉林省的微觀數(shù)據(jù),本文對進城務(wù)工人員和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進行了統(tǒng)計性描述,并應(yīng)用微觀經(jīng)濟計量模型分析了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研究結(jié)果表明,一方面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的流動有顯著的、積極的作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wù)工的概率越大;另一方面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的收入也有積極作用,但進城務(wù)工人員和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的教育收益并不相同,前者高于后者。
【關(guān)鍵詞】教育;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收入
Abstract: Based on micro data from Jilin in 2005, we build micro econometrical models to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and earnings by comparing their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is remarkable and positive. The higher inpidual’s education level i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his migration is on condition that others are same; moreover,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earnings is positive, but the schooling returns of migration and rural resident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Key words: education; rural labor; earnings; mobility 一、引 言 根據(jù)人力資本理論,教育與培訓(xùn)、遷移以及尋找新的工作是勞動者所承擔(dān)的人力資本投資的三種類型。經(jīng)典人力資本理論已經(jīng)證實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相關(guān)性,而且通常認為受過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平均收入。而遷移行為和尋找新的工作則是通過提高既定的知識技能(這些知識技能是從教育和培訓(xùn)中獲得的)在勞動力市場上所能夠獲得的價格來增加某人人力資本價值的活動。但遷移是具有選擇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從事的活動。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年輕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高一些。國外一些學(xué)者在這一方面給出了相應(yīng)的經(jīng)驗證據(jù)。例如L. Long [1]曾指出在美國的同一年齡群體中,一個人是否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測遷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2]對印度尼西亞不同年齡、性別和教育的農(nóng)村勞動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學(xué)以上教育的年輕人具有較高的流動傾向;L. Lanzona[3]對菲律賓的數(shù)據(jù)分析表明,個體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動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教育不僅僅是影響個體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響另外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遷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 [4]把教育稱作是人力資本理論“內(nèi)核”中的“內(nèi)核”。 在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農(nóng)村勞動力的遷移行為尤為突出。我國作為一個農(nóng)業(yè)大國,農(nóng)村人口基數(shù)巨大,農(nóng)業(yè)勞動力嚴重過剩,農(nóng)村失業(yè)和不充分就業(yè)人口大量存在,因此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開始向城市轉(zhuǎn)移。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這個行為確實給勞動者及其家庭帶來了相應(yīng)的回報。李實[5]通過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的收入分配效應(yīng)的分析結(jié)果表明農(nóng)村勞動力的流動確實提高了外出打工戶家庭的收入水平。但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關(guān)心的是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胡士華[6]利用2000-2002年數(shù)據(jù)檢驗了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概率的影響,但并沒有指明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關(guān)系。另外雖然侯風(fēng)云[7]和趙力濤[8]等國內(nèi)學(xué)者分析了人力資本對外出勞動力收入的影響,但卻沒有分析其流動的成因。與現(xiàn)有的文獻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又分析了教育對進城務(wù)工人員和農(nóng)村務(wù)工人員的收入的影響。 本文第二部分對進城務(wù)工人員和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的統(tǒng)計特征進行了描述,并給出了各教育-年齡組勞動力流動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邏輯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產(chǎn)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給出了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前后教育對其收入的影響效果。另外,我們在構(gòu)建人力資本模型時,特別地將勞動者的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因素也考慮進來,以盡量減少教育收益的估計偏差。 綜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研究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傾向及其收入的影響,提供一個更為直觀地理解我國勞動力市場行為的實證依據(jù)。 二、農(nóng)村勞動力統(tǒng)計特征描述與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觀數(shù)據(jù)集來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其調(diào)查對象覆蓋了吉林省各個城市和農(nóng)村的現(xiàn)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夠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該數(shù)據(jù)集提供了戶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員人口和經(jīng)濟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別、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戶口性質(zhì)、婚姻狀況、工作單位類型等。在選擇樣本的時候首先需要明確一個事實——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著性別歧視 ,為了盡可能消除這種影響,我們將農(nóng)村15歲以上的男性作為基本樣本集。由于農(nóng)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獲得,因此我們將其年收入換算為月收入。最終樣本總量為15305,進城務(wù)工樣本數(shù)為1118,占總樣本的7.3%。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3.06歲(最小年齡為15歲,最大年齡為31歲),可見我們研究的是農(nóng)村中年輕一代的勞動力流動狀況和教育收益。 對于進城務(wù)工人員,主要包括兩類流動人口:一類是在城市中定居的農(nóng)村勞動力,另一類是暫時到城市打工的人。我們通常稱后者為“候鳥式”流動,當他們賺到一些錢或者家里需要他們時,他們可能會返回農(nóng)村。 由表1可以發(fā)現(xiàn),進城務(wù)工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66年,而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359年,即具有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輕人在流動過程中似乎占有優(yōu)勢。這與少數(shù)發(fā)達國家農(nóng)村向城市遷移的大多數(shù)研究結(jié)果一致[9]。 表1 進城務(wù)工人員和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的統(tǒng)計特征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除了預(yù)期的收入差異外,個人的教育、年齡、婚姻狀況也是決定流動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對流動者預(yù)期收益的影響尤為顯著。已有的國外相關(guān)文獻也表明年輕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更高一些 。為了檢驗這一結(jié)論是否也適用于我國,本文運用二元邏輯模型對其進行了分析。 由于我們不能觀察到預(yù)期的收入差距,而只能觀察到某個人是否外出務(wù)工,因此觀察到外出務(wù)工行為時,定義Mobility=1,表示流動后的預(yù)期收入差距大于零。邏輯模型的一般形式如(1)式所示: (1) 其中X表示勞動力的個人和家庭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齡、婚姻狀況、父母的收入情況和父母的教育程度。 由表4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對勞動力流動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層次的教育水平對外出務(wù)工的影響差異較大,并且這種差異具有隨著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遞增的趨勢。其中高等教育對外出影響最大,而小學(xué)教育的影響并不顯著。Spence[11]曾對這種現(xiàn)象進行了解釋,即教育程度為雇主提供了勞動者能力的信號,因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流動者更容易被雇傭;另外教育提高了勞動者適應(yīng)城市環(huán)境的能力。具有較高教育的流動者相應(yīng)地具有較高的生產(chǎn)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資水平。而且如果個體的教育水平太低,則其流動后的預(yù)期收入并沒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獻資料指出在我國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輕人有著較高的流動傾向 。 表4 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決策的Logit模型估計結(jié)果
工作單位類型不同,個體收入也有顯著的差別。對于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來說,由于大部分個體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樣本的92.4%),所以只有這個因素對個體收入有影響,而其他工作單位類型對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對于進城務(wù)工人員來說,在集體企業(yè)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為國有企業(yè)、私營企業(yè)、個體工商戶,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數(shù)關(guān)于勞動力市場的文獻表明正規(guī)部門的收入會較高,正規(guī)部門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規(guī)模企業(yè)[11]。可是本文并沒有得到這樣的估計結(jié)果,這是因為在國有企業(yè)上班的個體,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體力勞動,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業(yè),20%的人在建筑業(yè),31.2%的人在運輸業(yè))。 回歸中使用6個因素解釋了進城務(wù)工人員收入變化的39.8%。這意味著進城務(wù)工人員收入中教育、經(jīng)驗、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門等因素可以在較大程度上解釋收入的變化。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的收入與這些因素的相關(guān)性稍微弱一些,收入變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歸系數(shù)解釋。 五、結(jié)論 本文運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觀數(shù)據(jù),針對教育對農(nóng)村勞動力收入以及流動可能性的影響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和計量檢驗。得出以下結(jié)論: (一)具有相似年齡和教育背景的進城務(wù)工人員和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相比,當我們控制年齡變量時,無論是進城務(wù)工人員還是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其收入都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當我們同時控制年齡和教育變量時,進城務(wù)工人員的收入均高于相應(yīng)的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與各個教育——年齡組之間的流動傾向存在著正的、弱相關(guān)關(guān)系。因此影響我國勞動力流動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wù)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專學(xué)歷的農(nóng)村勞動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學(xué)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概率沒有顯著影響。 (三)教育是影響農(nóng)村勞動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對進城務(wù)工人員的收入影響高于其對農(nóng)村務(wù)農(nóng)人員收入的影響;而且在同一個群體中,個體收入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單調(diào)遞增,但是這種增加并不是線性的;此外,教育對個體收入的影響存在“閾值”效應(yīng),即個體所受的教育必須累計到一定程度才能對收入產(chǎn)生影響。對吉林省而言,“閾值”是初中教育。 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教育不僅是影響個人收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響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農(nóng)村勞動力素質(zhì)低下的現(xiàn)狀既制約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的規(guī)模和速度,也制約農(nóng)村勞動力專業(yè)層次的提高[14]。因此,若要持續(xù)增加農(nóng)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農(nóng)村勞動力外出就業(yè)能力,首先應(yīng)該提升農(nóng)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我國推行的九年義務(wù)教育對提高農(nóng)村勞動力素質(zhì)和增加農(nóng)村收入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由于樣本數(shù)據(jù)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只分析了學(xué)校教育的作用,而沒有考慮職業(yè)培訓(xùn)的影響。現(xiàn)有的文獻資料已經(jīng)證實了進行專業(yè)技能培訓(xùn)對于增加農(nóng)民收入有重要的影響 ,但是培訓(xùn)對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如何,是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管研究.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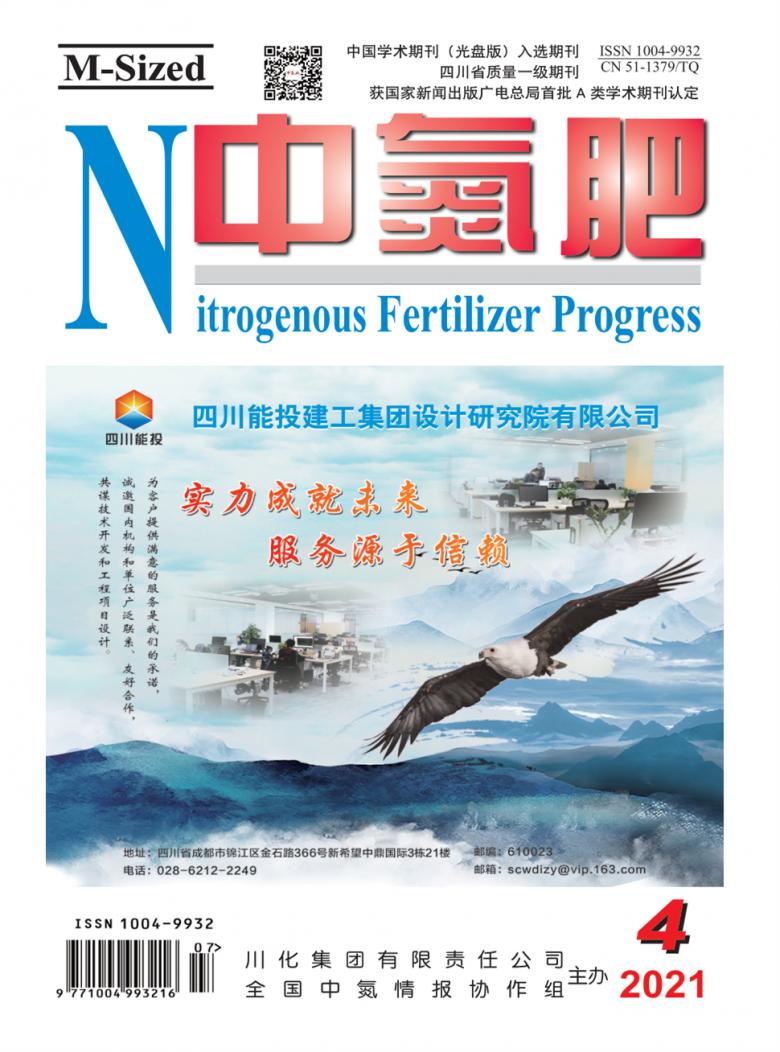
院學(xué)報.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