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說理散文之源:歷史記言文
陳桐生
文學(xué)史家在寫先秦散文史的時候,一般要將先秦散文劃分為先秦歷史散文和先秦諸子散文兩大塊:講先秦歷史散文,重在分析甲骨文、金文、《尚書》、《春秋》、《國語》、《左傳》、《戰(zhàn)國策》等作品在敘事、寫人以及語言藝術(shù)方面的演進(jìn);講先秦諸子說理散文,則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論語》、《老子》、《墨子》為第一階段,《孟子》、《莊子》為第二階段,《荀子》、《韓非子》為第三階段。對先秦散文史作出如此劃分,雖然條理井然易懂好記,但卻未必符合歷史真實情形。文獻(xiàn)表明,中國說理散文并不是從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論語》才開始起步,在商周春秋時期《尚書》、《國語》等歷史記言散文之中,就已有大量的說理文章,這些記言散文是戰(zhàn)國諸子說理散文的先驅(qū),只不過這些說理散文有一個外在的敘事框架,這個敘事框架有很大的迷惑性,導(dǎo)致人們長期以來將這些說理文章當(dāng)做敘事散文作品來讀。我們現(xiàn)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撥開歷史迷霧,根據(jù)文獻(xiàn)來探討中國早期社會說理散文的發(fā)展情形,理清先秦說理散文發(fā)展的源流脈絡(luò),還先秦散文史的本來面目。
一、中國早期社會人類思維的發(fā)展特點
理論家認(rèn)為,從古猿到現(xiàn)代人,人類思維發(fā)展史經(jīng)歷了原始的形象思維、抽象思維到辯證思維三種思維發(fā)展形態(tài)。原始形象思維依賴于對事物表象的感知,它的特點是原邏輯的、主客觀互滲的、感性的,帶有很大的幻想和想象因素,西方的神話、史詩以及某些史前的巖畫藝術(shù)等,都是原始形象思維的藝術(shù)產(chǎn)物。抽象思維又稱邏輯思維,它是人類思維的一種高級形式。其特點是以抽象的概念、判斷和推理作為思維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綜合、比較、抽象、概括和具體化作為思維的基本過程,以揭示事物的本質(zhì)特征和規(guī)律性聯(lián)系。西方人的抽象思維起步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致力于形式邏輯的研究。辯證思維是遵循唯物辯證法的規(guī)律進(jìn)行思維,就是從事物的聯(lián)系、對立及對立面的轉(zhuǎn)化之中去進(jìn)行分析、判斷和推理。
遺憾的是,這個人類思維發(fā)展三段論在中國商周文獻(xiàn)中得不到印證。商周文獻(xiàn)表明,當(dāng)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既不是典型的原始形象思維,也不是純粹的抽象思維,更不是人們所大力推崇的辯證思維,但其中又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原始形象思維、抽象思維甚至辯證思維的因素。商周人的思維方式是帶有原始思維色彩的經(jīng)驗思維,其基本特征是注重歷史經(jīng)驗、天人合一、主客滲透。當(dāng)時統(tǒng)治階層習(xí)慣于從歷史和現(xiàn)實的帝王政治中總結(jié)治國安民的經(jīng)驗,表現(xiàn)出相當(dāng)清醒的理性精神,已經(jīng)能夠從事簡單的分析和綜合,也有一些樸素的抽象和概括,從這個意義看,中華民族是一個思維早熟的民族。但是商周人的經(jīng)驗并非完全來源于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他們經(jīng)驗中的很多內(nèi)容來自于信仰的虛幻的世界——原始宗教神學(xué),他們真誠地信仰天人感應(yīng),相信天命神意是王朝執(zhí)政的最終依據(jù),認(rèn)為上帝時刻在關(guān)注和主宰著人間,會通過種種祥瑞災(zāi)異現(xiàn)象向人間顯示自己的意志,他們也相信自己的祖先死后升天為神,陪伴在上帝身邊,給上帝意志施加種種影響,而人間則可以通過祭祀、修甚至巫術(shù)等手段來改變天命神意。這是一種既崇尚歷史與現(xiàn)實經(jīng)驗又執(zhí)著地堅持原始宗教信仰的東方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一直貫穿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終。據(jù)說法國社會學(xué)家列維一布留爾看到《史記》的法文譯本,對其中的天人感應(yīng)內(nèi)容大為震驚,這促使他致力于研究原始思維的特征,由此寫下《原始思維》這部學(xué)術(shù)名著。
由于思維早熟,所以翻開中國歷史文獻(xiàn)的第一頁,人們所看到的就是一個相當(dāng)老練、成熟、重視經(jīng)驗的理性民族。中國似乎沒有經(jīng)歷西方那種充滿童稚的人類少兒年代,中國上古人們沒有多少浪漫的感性的幻想,在長期的與社會和大自然敵人的搏斗中,他們過早地培養(yǎng)了清醒的經(jīng)驗理性。中國上古作家沒有給后人留下多少作為原始形象思維載體的神話、史詩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展示王權(quán)神圣威嚴(yán)、充滿訓(xùn)誡意味、總結(jié)帝王政治經(jīng)驗的歷史記言散文。中國上古作家并不是等到充分地發(fā)展了記敘、描寫等感性能力之后才去寫作說理散文,實際情形恰恰相反,中國上古散文中的說理內(nèi)容要遠(yuǎn)遠(yuǎn)多于記敘、描寫的成分,說理散文的較早起步是中國上古散文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點。
二、《尚書》中的說理散文
虞夏時代至今尚無考古依據(jù),研究中國上古散文要從商周講起。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幾種商周散文。甲骨文刻于龜甲獸骨,金文則是銘鑄在青銅器之上,由于受到書寫工具的限制,所以甲骨文和金文都不能代表商周散文的發(fā)展水平,代表商周散文水平的是《尚書》。
商周時代學(xué)在王官,政學(xué)合一,社會尚未分蘗出專門從事文化學(xué)術(shù)事業(yè)的思想家和文學(xué)家,執(zhí)政的商王、周王、卿士、諸侯就是當(dāng)時文化學(xué)術(shù)創(chuàng)造的主體,現(xiàn)實政治主題也就是當(dāng)時的文化學(xué)術(shù)主題,商王、周王、卿士、諸侯們出思想,史官負(fù)責(zé)記載,他們就是當(dāng)時的文化人。史官記錄的演講詞被后人稱之為“上古之書”亦即《尚書》。這些“上古之書”既是當(dāng)時的“中央紅頭文件”,也是當(dāng)時的宗教學(xué)、哲學(xué)、政治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軍事學(xué)、法學(xué)作品,同時也是中國最早的說理散文。
《尚書》有虞、夏、商、周四個部分,從典誥誓命文體形成的角度看,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商書》。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表明,商代不但有成熟的文字,而且散文也開始發(fā)軔,《尚書》的典誥文體應(yīng)該在商代就已經(jīng)形成。《尚書·多士》載周公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說明周初人們還可以讀到不少商代傳世典籍。一種文體在形成之后,就有它相對的穩(wěn)定性,并對后人產(chǎn)生一種示范作用。《虞書》、《夏書》就是后代史官仿照《商書》典誥文體而追記,《周書》的典誥誓命也是模仿《商書》寫成的。《尚書》中最早的文章是《堯典》,故事大約發(fā)生在公元前22世紀(jì),最晚的是《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前后歷時1500多年,而《尚書》文體風(fēng)貌幾乎處于凝固狀態(tài),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誓”這一文體為例,《尚書》中收入了《甘誓》、《湯誓》、《牧誓》、《費(fèi)誓》、《秦誓》5篇文章,《甘誓》是公元前21世紀(jì)夏啟討伐有扈氏的誓詞,《湯誓》作于公元前16世紀(jì),《牧誓》作于公元前11世紀(jì),《費(fèi)誓》寫作時間稍后于《牧誓》,《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5篇誓詞相隔近1400多年,而文體風(fēng)貌若出一人之手,這又是什么原因?qū)е碌?再拿《周書·秦誓》與《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所載秦穆公悔過之語相比,可以發(fā)現(xiàn)兩篇秦穆公悔過之辭相差甚遠(yuǎn)。為什么記載同一事件,不同典籍的文辭風(fēng)貌懸殊如此之大?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虞書》、《夏書》、《周書》都是模仿《商書》典誥文體。再從空間來看,虞、夏、商、周的活動地域大約在今天的山西、河南、陜西一帶,彼此方言差異應(yīng)該很大,但在《尚書》中卻看不到明顯的語言差異,這可能是不同時代的作者們都有意識地以《商書》典誥語言為典范。所以,研究《尚書》中的說理散文,《商書》是一 個關(guān)鍵。《周書》繼承了《商書》的典誥文體,在說理方面較《商書》有所進(jìn)展,但從總體上說,《周書》對散文的貢獻(xiàn)沒有《商書》大。據(jù)說《尚書》最初有三千篇之多,在經(jīng)過無數(shù)次歷史劫難之后,《尚書》留下可信的文章只有28篇,大量原始文獻(xiàn)的亡佚,使我們已經(jīng)無法看到《尚書》的原貌,我們今天所能做的只是窺一斑而見全豹的工作。在《尚書》28篇文章中,《堯典》、《禹貢》、《金滕》、《顧命》4篇側(cè)重敘事,《文侯之命》為周平王表彰晉文侯勤王功績的嘉獎命令,其余24篇文章都有或多或少的說理內(nèi)容,對后代說理散文有程度不同的影響。
代表商代說理散文水平的是《商書·盤庚》。漢代伏生本《尚書》將《盤庚》歸為一篇,而今本《盤庚》則分上、中、下三篇,記載盤庚對邦伯、師長、百執(zhí)事等各級執(zhí)政官員的訓(xùn)詞。《書序》說:“盤庚五遷,將治毫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左傳·哀公十一年》征引《盤庚》之語,稱為《盤庚之誥》,可見《盤庚》與《大誥》等篇章同為誥體。商朝舊都奄地由于受到水患的威脅而不宜居住,為了商民族長期的生存與發(fā)展,盤庚決定將首都由奄遷殷。如此大規(guī)模的遷徙給廣大臣民帶來諸多不便,臣民因此怨聲載道。盤庚的三篇訓(xùn)詞就是為統(tǒng)一思想認(rèn)識、平息民怨而發(fā)。《盤庚》雖然文字古奧屈聱牙,但其文章脈理仍然可以尋繹。三篇訓(xùn)詞之中,以上篇說理最為充分。盤庚首先對阻礙遷都的百官指出,遷都是繼承和復(fù)興先王大業(yè)的需要,也是占卜所顯示的天命神意。接著,他嚴(yán)厲地批評百官傲慢放縱,貪圖安逸,不把他這位天子放在眼里,不向民眾宣布善言德音,而是用虛浮之言蠱惑民心。他說,他對百官的心理言行洞若觀火,如果官員們不思悔改繼續(xù)為惡,那么將會禍及自身,因為他手中操縱著他們的生殺大權(quán)。只有除去自私之心,施德于民,才會得到善報。盤庚還捧出先王與官員祖宗的亡靈,說他的先王與百官祖先曾經(jīng)勞逸共享,而今百官祖先的靈位還在商朝祖廟之中配享先王,百官的幸福與災(zāi)禍都取決于祖宗神的旨意。他告誡百官“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最后,盤庚發(fā)出嚴(yán)厲警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在中篇,盤庚開始的語氣稍微和緩,他說歷代商王都是根據(jù)天時民利而遷徙,而今遷都也是為了民眾的利益,百官不應(yīng)該自鞠自苦,起穢自臭。他回顧了先王與百官祖先同甘共苦的往事,說他們?nèi)绻磳w都,祖先神就會降下災(zāi)禍。結(jié)尾處盤庚再次露出兇狠的面目:“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下篇是盤庚一個撫慰性的談話,他說遷都是為了拯救民眾,復(fù)興成湯之大業(yè)。他表示要像先王一樣,任用舊家的人,他勉勵百官率民謀生,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家園。閱讀這三篇訓(xùn)詞,感覺到盤庚并不像后代儒家筆下圣王那樣以德感人,那樣和藹可親,相反,他是用天命神意來嚇人,用王權(quán)來壓人,用刑罰來唬人。盤庚也有動之以情的地方,只是以情感人之處很少,更多的是對現(xiàn)實利害的剖析,是對阻礙遷都官員們的威嚇,其中透發(fā)出宗教神學(xué)和王權(quán)的力量,數(shù)千年之下仍能強(qiáng)烈感受到文章的威懾力。或許,這才是真實的盤庚,這才是上古圣王的真面目。盤庚用來說服百官遷都的論據(jù),主要是天命神意和現(xiàn)實生存需求,他還列舉了古代著名史官遲任“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的名言。在表現(xiàn)手法上,盤庚在演講中運(yùn)用了許多淺顯、形象的比喻,諸如“若顛木之有由蘗”,“予若觀火”,“若網(wǎng)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nóng)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或射之有志”,“若乘舟,汝弗濟(jì),臭厥載”等等,這說明盤庚已經(jīng)刻意講究說理技巧,以便臣民們從內(nèi)心接受他的遷都主張。
《周書·洪范》是《尚書》中概括水平最高、最有邏輯條理性的文章,堪稱西周初年說理散文的典范。文章開頭有兩句敘事文字,用來交代背景。在滅商的第二年,周武王拜訪殷朝遺老箕子,向他咨詢治國安邦的方略,箕子向周武王講述了上天賜給夏禹治理天下的“洪范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nóng)用八政,次四日協(xié)用五紀(jì),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義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征,次九日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從結(jié)構(gòu)上看,這一節(jié)文字是全文的大綱,以下分為九段,逐層闡述“洪范九疇”的具體內(nèi)容。《洪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文章高度精練,沒有旁逸側(cè)出、節(jié)外生枝的內(nèi)容。如果借用后人的“經(jīng)”“傳”概念分析《洪范》,那么開頭一段文字為“經(jīng)”,以下解釋的九段為“傳”。在商周之際就出現(xiàn)如此有條有理、綱目清晰的文章,簡直是一個散文奇跡。如果刪除開頭那兩句敘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完全成熟的說理散文。“洪范九疇”是運(yùn)用抽象、概括、歸納、綜合的思維方法總結(jié)出來的,九條治國大法廣泛涉及民生日用要素、儀態(tài)思維、職官、歷法、統(tǒng)治方法、理想人格、占卜原則、物候征兆和人生禍福各方面,雖然“洪范九疇”彼此之間沒有內(nèi)在聯(lián)系,但是將帝王政治經(jīng)驗作出如此精辟的概括,這已經(jīng)是非常難得的了,特別是將民生日用要素歸納為“五行”,堪稱中國古人對生活現(xiàn)象進(jìn)行概括的杰作。通體用韻是《洪范》文章一大特色,上古用韻文章如《易經(jīng)》、民諺、格言等等,都是經(jīng)過長期錘煉而成,這從側(cè)面證明《洪范》九疇不是一時所為,而是夏商思想政治家在長期觀察、總結(jié)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文字。
如果說《洪范》的最大優(yōu)點在于綱舉目張,那么《無逸》的明顯長處就是主題高度集中。《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yè)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可見這是西周老一輩開國政治家對周王朝事業(yè)繼承人殷切囑托之作。“無逸”篇名取自“君子所其無逸”,不知為何時何人所取,它完全能夠概括文章的主題。文章按意思可劃為三層:首層揭示無逸主題,提出君子要“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就是說要了解最下層小民謀生的艱難。第二層是對無逸主題的拓展延伸,周公通過回顧殷代興亡和文王辛勤治國,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無逸的重要性。在殷朝歷史上,中宗、高宗、祖甲等幾個有為的君主都是以敬畏之心治國安邦,他們施惠于民,深知小民謀生之艱難,不敢荒廢政事,不敢欺侮鰥寡,因而能夠享國日久。此后殷商嗣王一生下來就只知道貪圖享樂,不知稼穡之艱難,最終一個個福淺壽夭。對周民族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xiàn)的太王、王季也能夠貶抑自己,敬畏天命。特別是周文王,堪稱勵精圖治、勤政愛民的典范,他穿著粗衣開墾山野,以和氣仁慈、善良謙恭的態(tài)度對待民眾:“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善行終得好報,他享國達(dá)五十年之久。最后一層回應(yīng)開頭,周公殷勤告誡成王和其后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正確地對待小民的怨恨情緒,做到以歷史為鑒。文章在語重心長的叮嚀中結(jié)束,充滿了無限期望的意味。這篇文章的論據(jù)完全來源于歷史,周公不是像《西伯勘黎》中殷紂王那樣抱著“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觀念,他沒有教導(dǎo)年輕的成王完全依賴天命神意,沒有完全從宗教神學(xué)中尋求周王朝統(tǒng)治依據(jù),而是教成王目光向下,放下尊貴身段,體察民生民情,了解小民謀生的艱辛,從歷史成敗中汲取政治經(jīng)驗,這體現(xiàn)了西周初年統(tǒng)治集團(tuán)思想意識的轉(zhuǎn)變。文章觀點集中,論據(jù)充分,三個部分環(huán)環(huán)相扣,使主題得到步步深化。
《盤庚》、《洪范》、《無逸》分別代表商周說理散文的藝術(shù)成就。《尚書》中還有一批說理散文,其藝術(shù)成就容或不及上述三篇文章,但在確立文章意脈方面仍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高宗肜日》載祖已訓(xùn)導(dǎo)商王,說明上天是按照“義”來“監(jiān)下民”,不要因為事件而產(chǎn)生心理恐慌。文章雖然短小,但每句都有強(qiáng)烈的針對性,讀者不難感受到語句中內(nèi)涵的力度。《大誥》載周公以成王名義為東征而告諭天下,文章以“大寶龜”所顯示的天命神意來鼓舞民心,統(tǒng)一王朝內(nèi)部對東征的分歧意見。周公東征是西周初年決定周王朝生死存亡的一次重大戰(zhàn)役,由于希望得到“多邦”和“御事”對東征大業(yè)的支持,周公在發(fā)表文誥時動之以情,文章寫得聲情并茂。《康誥》、《酒誥》、《梓材》載周公以攝政王名義訓(xùn)誡衛(wèi)國始封君康叔之辭,三篇文章各有側(cè)重:《康誥》告訴康叔,執(zhí)政之要在于明德慎罰,任賢愛民;《酒誥》要求康叔在衛(wèi)國嚴(yán)厲戒酒,文章歷舉從成湯到帝乙戒酒勤政與殷紂王酗酒亂德的正反面歷史經(jīng)驗,說明戒酒的必要性;《梓材》以梓人治材為喻,說明為政之道在于明德;幾篇文章基本上都能做到主旨突出。《召誥》為建筑洛邑新都而作,文章載召公告誡成王,從夏商的歷史教訓(xùn)談到周王朝的現(xiàn)實隱憂,最后落腳到居安思危,敬德保民,給人以清晰的層次感。《多士》載周公對遷殷遺民的訓(xùn)詞,先說周之代殷猶如殷之代夏,都是出于天命;然后說遷殷民于洛邑是天意所歸,不任殷人官職也是天命;最后說周人將對殷民采取比較寬松的管理政策,殷民應(yīng)該安居樂業(yè),服從新朝統(tǒng)治。全文據(jù)天命立論,逐層揭示文章意旨。《多方》是《多士》的姊妹篇,記載周公代表成王訓(xùn)誡殷人和各國諸侯,文章說理方法與《多士》頗為近似,大意是說夏商周政權(quán)的嬗遞都是由天命決定,因此殷人和各國諸侯必須服從周朝的管理。《君爽》載周公告召公之語,與《大誥》、《多士》、《多方》等篇章宣揚(yáng)天命不同,本篇說“不敢寧于上帝命”,“天不可信”,強(qiáng)調(diào)輔臣的重要性,提出周召二人戮力同心,共同擔(dān)負(fù)起文武的未竟事業(yè),輔佐成王永保周朝江山。因為周公是對自家人說話,所以本篇不僅在思想上說了真心話,而且在語氣上比較和緩,娓娓道來,辭不迫切而意已獨(dú)至。《立政》載周公歸政成王之語,重點闡述設(shè)官用人之道,文章總結(jié)了夏商周三代設(shè)官用人的經(jīng)驗教訓(xùn),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用人主張和官職建制系統(tǒng)。以勿用人為一篇之骨,文章前后一以貫之。《呂刑》載周穆王對呂侯發(fā)表刑法文誥,系統(tǒng)地闡述了周朝的刑律條文和斷案的方法原則,強(qiáng)調(diào)慎罰思想。這些文章在說理散文寫作方面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
《尚書》中有一些對話體文章。如《皋陶謨》記載了皋陶與禹、舜與禹、舜與夔及皋陶的三段對話,皋陶和禹互相告誡要以德治國,修身安民,舜和禹則探討君臣職責(zé),并與夔、皋陶討論丹朱之過和禹之功。其他如《洛誥》記載周公與成王圍繞營建洛邑、還政成王等問題展開的幾輪對話,《微子》載微子與父師、少師的問答,《西伯戡黎》載祖伊勸諫殷紂王。這些文章都是每人各說一段,看不出孰為賓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主客問答格局,談話主題也時常發(fā)生轉(zhuǎn)換,像《洛誥》還存在時間、地點的變易問題,文章主旨究竟是作洛、祭祀、記功還是周公請退抑或是成王命周公后,頗不易判定。這些對話文章有記敘有議論,不是《尚書》中典型的說理文章,距離論說文的要求很遠(yuǎn)。但是,它們卻是中國最早的對話體散文,為春秋戰(zhàn)國說理散文開啟了一種有意義的形式,戰(zhàn)國諸子不少文章采用對話體,如記載孔孟言論的文章就大多采用對話體形式。
《甘誓》、《湯誓》、《牧誓》、《費(fèi)誓》、《秦誓》5篇文章是特殊的文體——誓詞。由于要指陳敵方罪狀,申述征討理由,鼓舞大軍士氣,所以誓詞也要說理,而且文章理由要充分,只不過要求文鋒特別犀利。這種聲討性質(zhì)的說理文字是此后檄移散文的先驅(qū),對戰(zhàn)國諸子的批駁辯難文章也有一定影響。 經(jīng)過篳路藍(lán)縷的艱辛開拓,《尚書》初步積累了一些說理散文的寫作經(jīng)驗。從《尚書》我們看到,商周時期的王侯卿士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較高的理性思維水平和說理能力,而負(fù)責(zé)記載的史官們也能夠圍繞一個主題,成功地組織材料進(jìn)行論證,他們的文章已經(jīng)初步具備說理文章所必須擁有的論點、論據(jù)、論證三要素,這為中國說理散文的寫作開了一個好頭。在敘事的框架之下記載說理內(nèi)容,是《尚書》說理散文的主要形式,這是史官忠實地記載執(zhí)政者談話的結(jié)果。此后《國語》記言散文大都以這種形式出現(xiàn),戰(zhàn)國諸子的某些作品也還在采用這種形式。《尚書》的對話文章雖然稚嫩,但由于戰(zhàn)國諸子散文大都是宗師應(yīng)對弟子及時人,所以《尚書》對話體形式在他們手中得到長足的發(fā)展。王侯卿士發(fā)表演講,史官們記錄王侯卿士的演講詞——《尚書》這種散文著述模式從商周一直延續(xù)到戰(zhàn)國,在相當(dāng)長的歷史時期之內(nèi),一篇文章往往是由思想發(fā)表者與文字記錄者合作完成的。在指出《尚書》記言文藝術(shù)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尚書》記言文畢竟處于中國說理散文的起步階段,像《洪范》、《無逸》這樣有邏輯性的文章畢竟是屈指可數(shù)的,《尚書》中不少文章內(nèi)容橫生枝蔓,它的古奧艱澀的典誥體語言也影響思想的表達(dá)。
三、《國語》說理散文的幾大進(jìn)展
繼承并發(fā)展《尚書》說理散文成就的是《國語》。《國語》之“語”,是西周春秋時期一種記載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君臣治國之語的文體。《國語·楚語上》載楚大夫申叔時論太子教育:“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wù)用明德于民也。”楚國宮廷用來教育太子的《語》,是一部記載先王德治言論的典籍。《國語·鄭語》所引《訓(xùn)語》,大概與申叔時所說的《語》性質(zhì)相近。不僅楚國、鄭國有《語》,周王室和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和他國史官所作的《語》。《語》之前冠以國名,就成為某國之《語》,諸如《魯語》、《齊語》、《晉語》、《吳語》、《楚語》等等。各國之《語》最初可能以單篇形式保存在宮廷檔案室,作為史官向君主獻(xiàn)書的原始資料,或作為朝廷教育貴族弟子的教材。西周春秋時期有朝聘赴告制度,各國的“語”借此機(jī)會得到交流。戰(zhàn)國初年某國史官把他手頭上所掌握的各國之《語》按國別編為一書,遂成今本《國語》。《國語》選編范圍,包括西周、東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等諸侯國,西周春秋時期重要諸侯國衛(wèi)、燕、宋、陳、蔡、秦這些國的“語”都沒有入選,這可能是編者手頭資料缺乏的緣故。《國語》內(nèi)容廣泛涉及 “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dāng)?shù)”,編者選編的宗旨是為王侯治國“道訓(xùn)典,獻(xiàn)善敗”。
任何一種文體在確立之后,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fā)生演變。《國語》這一“語”體在發(fā)展過程中也有變異。周王朝在政治上是天下共主,記載周室君臣治國言論的《周語》(特別是《周語上》載西周史官所作的“語”)標(biāo)志著“語”體的確立。《周語》“語”體的典范形式是,文章前后有簡短的介紹前因后果的敘事文字,中間主體部分記載君臣治國之語。魯國由于擁有與周王室共同的政治文化資源——天子禮樂,因此《魯語》與《周語》親緣關(guān)系最近,與《周語》同為“語”體的正宗。《鄭語》雖冠鄭國之名,但在文風(fēng)上與周、魯屬于同一系統(tǒng)。這是因為鄭桓公向史伯咨詢時尚在擔(dān)任西周王朝的司徒,其時鄭國尚未立國,而與鄭桓公對話的史伯則是周王室的史官,對話的地點是在西周都城。清人姚鼐在《辨(鄭語>》一文中說:“《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姚氏的懷疑不無道理。南楚在西周尚為落后蠻夷邦國,進(jìn)入春秋之后迅速崛起,為了適應(yīng)政治、軍事的迅猛發(fā)展,這個南方大國有意識地吸取周魯?shù)亩Y義文化以壯大自己,所以《楚語》在形式文風(fēng)上也向《周語》、《魯語》靠攏。與上述幾國之“語”相比,《齊語》、《晉語》、《吳語》、《越語》呈現(xiàn)出兩大明顯變化:一是立論標(biāo)準(zhǔn)由禮義道德一變而為權(quán)謀智慧,如《齊語》、《晉語》所記載的齊桓、晉文君臣治國之語,都與周、魯所持的禮義標(biāo)準(zhǔn)有很大的差距,這正好印證了《韓非子·五蠢》所說的“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二是敘事成分增多,若將《晉語》、《吳語》、《越語》這些文章稱之為“事語”,可能會更加貼切一些。敘事筆墨的增多,淡化了《國語》以記言為主的文體色彩,當(dāng)然也就削弱了說理散文的成就。如果我們借用《詩經(jīng)》學(xué)中的風(fēng)雅正變概念,那么《周語》、《魯語》、《鄭語》、《楚語》可以作為《國語》的“正語”,而《齊語》、《晉語》、《吳語》、《越語》則是《國語》中的“變語”。
《國語》與《尚書》有一些共同之處:它們都是重點記載周王朝和各諸侯國君臣治國之語,著述方式也是由史官記載執(zhí)政君臣所發(fā)表的言論,《國語》記言文在形式上也有很多地方因襲《尚書》,諸如在敘事框架內(nèi)記載說理內(nèi)容,不少文章采用對話體形式,等等。但《國語》與《尚書》也有明顯不同之處,其中最大的不同點體現(xiàn)在文章性質(zhì)之上:《尚書》文章是國家對外發(fā)表的正規(guī)文誥,相當(dāng)于今天中央和地方政府頒發(fā)的公文,而《國語》則是史官隨時記錄的君臣治國言論,記錄簡冊歸入王室或諸侯國檔案,用于日后史官向君主獻(xiàn)書或各國之間赴告時交流,略似于今天黨政高層人士才能看到的內(nèi)部參考資料。文章性質(zhì)的不同決定了它們屑于不同的語言文化系統(tǒng):《尚書》是出于殷商官方公文語言系統(tǒng),屬于官方雅文化,這是商周時期的“雅言”;《國語》則屬于西周春秋時期的民眾口語系統(tǒng),屬于大眾俗文化。這樣說是有充分依據(jù)的。證據(jù)之一是,《尚書·呂刑》是周穆王發(fā)表的刑罰文誥,《國語·周語上》所載“祭公諫穆王征犬戎”也是周穆王時期的文章,但兩篇文章的語言風(fēng)格差異及其難易差別是任何讀者都能體會到的。證據(jù)之二是,《尚書·文侯之命》是東周初年周平王時期的文章,在《國語·周語上》中可以找到同時期的文章,這就是寫于周幽王二年的“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周將亡”,該文僅比《文侯之命》早9年,可是兩篇文章語言差異甚大。證據(jù)之三是,《尚書·秦誓》載秦穆公誓詞,《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載秦穆公悔過之詞,兩者同為一事,但語言風(fēng)格相距甚遠(yuǎn)。《尚書》與《國語》的記事時間,在從周穆王到秦穆公這一段是重合的,像“祭公諫穆王征犬戎”、“邵公諫厲王弭謗”這一類文章,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都與《尚書》中的《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相近,按說也可以收入《尚書》,但事實上《國語》這一時段的文章并沒有被收入《尚書》,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國語》中這些文章不是正式對外發(fā)表的公文,它們是史官用當(dāng)時口語記錄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wèi)靈公》)語言就是作者手中的“利器”,語言的運(yùn)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章的寫作,要求一個作者用已經(jīng)僵化的前代官方公文語言進(jìn)行寫作,其難度可想而知,而《尚書·周書》作者恰恰就是刻意地用商代典誥語言寫作。由于《尚書》典誥公文語言古奧晦澀,脫離生活,落后于時代,不便于表達(dá)思想,遠(yuǎn)不及《國語》作者運(yùn)用當(dāng)時民眾口語表達(dá)思想得心應(yīng)手,所以《國語》作者在語言上占領(lǐng)了一個制高點。從《尚書》中看不到說理散文的進(jìn)展,而將《尚書》與《國語》加以比較,就能清楚地看到說理散文在西周春秋時期的進(jìn)步。
首先,《國語》說理散文的主題比《尚書》更為鮮明集中,在邏輯結(jié)構(gòu)上較《尚書》更為緊湊嚴(yán)謹(jǐn)。《尚書》中雖然有《洪范》、《無逸》這樣主題集中、層次井然的文章,但畢竟是少數(shù),不少說理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內(nèi)容旁逸側(cè)出的問題。這種情形到《國語》有了明顯的改變。《國語》大多數(shù)說理散文都是先提出核心論點,再圍繞主題逐層展開論述,一席言論往往就是一篇主題突出、結(jié)構(gòu)緊湊的說理散文。《國語》立論方法常常是開門見山,核心觀點往往在第一句。如《國語·周語上》第一篇文章載“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觀兵”作為一篇說辭的靈魂,然后從五個方面圍繞這一中心觀點展開論證。祭公首先征引《詩經(jīng)·周頌·時邁》“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的詩句,說明西周在革故鼎新、天下大定之后就止戈藏矢、偃武修文。第二層是以史實為論據(jù),說先王的治民方法是正德厚性,阜其財求,教之禮法。第三層進(jìn)一步歷舉從后稷到武王修德保民的事跡,說他們都是“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而不是炫耀武力。第四層闡述先王五服制度,說明先王都是致力于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只有在修文德失敗之后才去修刑征討。最后指出犬戎并無失職之處,穆王征討觀兵之舉是錯誤的。全篇文字都緊扣“耀德不觀兵”的主題,沒有節(jié)外生枝的內(nèi)容,堪稱一篇觀點鮮明、主題集中、結(jié)構(gòu)謹(jǐn)嚴(yán)的小型論文。《周語上》載“邵公諫厲王弭謗”,也是一篇主題鮮明的好文章。邵公首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為民者宣之使言”的中心思想,然后從正面具體討論廣開言的途徑言和方法,主張讓社會各階層人士都對王朝政治提出批評和建議,指出這樣做可以調(diào)動人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帶來衣食財用。邵公指出,人民對王朝政治的批評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應(yīng)該嚴(yán)肅對待。最后以“若雍其口,其與能幾何”的反面設(shè)問收柬全文,對開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觀點予以照應(yīng)。一篇言論,始終扣住讓人民說話這一主題。又如《周語上》載“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開頭提出“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的觀點,然后分三層展開討論:先指出利是百物所生天地所載,天下民眾都要獲取利益以維持生存,君主應(yīng)該“導(dǎo)利而布之”,而不應(yīng)該專利以觸犯眾怒;繼而征引《周頌·思文》和《大雅·文王》,說明先王如何布利;最后指出專利必然導(dǎo)致失敗。文章緊緊圍繞中心論點進(jìn)行論證。其他如《周語上》“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周將亡”、“仲山父諫宣王料民”、《周語中》“單襄公論陳必亡”等等,都是主題鮮明、條理分明的文章。這表明《國語》記言文在說理論證方面較《尚書》確有長足的進(jìn)步。
第二,《國語》為對話體說理散文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尚書》雖有人物對話體但未形成固定格式,說理散文中的主客問答形式格局是在《國語》中初步形成的。問者為賓,答者為主,而文章重點則落在對答之上,許多重要思想觀點都是通過解答提問而得以表達(dá)。如《鄭語》載史伯對鄭桓公,這是西周末年一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文字。鄭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六個問題:“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南方不可乎?”“謝西之九州,何如?”“周其弊乎?”“若周衰,其孰興?”“姜、贏其孰興?”針對上述問題,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他從天道賞善罰惡角度立論,縱論天人古今,對未來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齊、晉、秦、楚的崛起大勢作出預(yù)測。《國語》中的對話形式不僅是客觀的敘事,而且具有推進(jìn)文章步步深入的結(jié)構(gòu)意義,即通過問句將論題層層引向深入。如《齊語》載齊桓公問管仲:“成民之事若何?”“處士、農(nóng)、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安國若何?”……這一系列的問語不僅區(qū)分結(jié)構(gòu)層次,而且將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統(tǒng)全面地闡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張。《越語下》載“范蠡進(jìn)諫勾踐持盈定傾節(jié)事”一文,也是范蠡在應(yīng)對越王勾踐過程中發(fā)表重要思想。特別是《越語下》“范蠡勸勾踐無蚤圖吳”、“范蠡謂人事至而天應(yīng)未至”、“范蠡謂先為之征其事不成”、“范蠡謂人事與天地相參乃可以成功”、“越興師伐吳而弗與戰(zhàn)”5篇對話文章蟬聯(lián)而下,這5篇文章各自獨(dú)立成篇,合起來又可以成為一個藝術(shù)整體,完整地反映了在滅吳過程中范蠡戰(zhàn)略思想的發(fā)展演變,體現(xiàn)了作者和編者的藝術(shù)匠心。經(jīng)過《國語》作者的努力,對話體文章成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說理散文的一種重要形式,春秋戰(zhàn)國之際孔門七十子后學(xué)記載孔子應(yīng)對弟子及時人言論,多采用對話體形式,這些文章保存在《論語》和大小戴《禮記》之中。戰(zhàn)國時期仍有一些諸子使用對話體,如著名的《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就是運(yùn)用對話體的典范之作。
第三,《國語》說理文章的論據(jù)較《尚書》有重大變化。論據(jù)是論說文的基石,說理文章有沒有說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者所使用的論據(jù)。《多士》說唯殷先人有冊有典,但《尚書》文章征引冊典的情況并不多見。《尚書》文章的論據(jù),主要取材于宗教神學(xué)、歷史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社會現(xiàn)象,偶爾也有征引前人名言的情形,如《盤庚上》引用遲任關(guān)于“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的名言。殷商人尊天事神,而西周初年周人也深信自己得到天命,因此《尚書》中不少涉及王朝執(zhí)政依據(jù)的文誥都從天命神意立論,像《盤庚》、《大誥》、《多士》、《多方》等文章論據(jù)都有濃厚的宗教神學(xué)色彩,這些文章在當(dāng)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說服力,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宗教神學(xué)地位的削弱,文章的說理力量就顯得不夠了。《國語》文章的論據(jù)雖然也有一些宗教內(nèi)容,但并不常見。與《尚書》相比,《國語》說理散文出現(xiàn)了一些新論據(jù)。一是多取材于《詩》、《書》及其他文獻(xiàn)古籍,大約從西周中葉開始,《詩》、《書》就成為人們在言論中經(jīng)常引用的經(jīng)典,他們認(rèn)為《詩》、《書》是“義之府”,就是說《詩》、《書》是一個思想庫,要從中尋求理論依據(jù)。《國語》說理文章引《詩》最多,達(dá)33次,許多文章的理論基礎(chǔ)就建立在《詩》意之上,如《周語中》載“富辰諫襄王以狄伐鄭”,主要思想依據(jù)就是富辰稱之為“周文公之詩”的《詩經(jīng)·小雅·棠棣》“兄弟于墻,外御其侮”。其次是征引《尚書》,引《書》共10次(含逸書)。如《周語上》“內(nèi)史過論晉惠公必?zé)o后”,一席言論就分別征引了《夏書》、《湯誓》和《盤庚》。《詩》、《書》之外,《國語》言論征引的文獻(xiàn)古籍還有《周易》、《夏令》、《周制》、《秩官》、《禮志》、《訓(xùn)語》、《春秋》、《世》、《札》、《樂》、《令》、《故志》、《訓(xùn)典》等等。二是大量地引用古今名言,諸如“古人有言”、“先民有言”、“先王之教”、“先王之令”“人有言”、民諺、商銘、童謠、輿人之誦、“西方之書”、“瞽史之紀(jì)”、“衛(wèi)武公之箴”等等,這些名言凝聚了豐富的歷史、社會、自然、人生的經(jīng)驗,給文章增添了說服力。三是多引此前的典章制度。從表面上看,《國語》所引的典章制度頗似《尚書》所稱的歷史經(jīng)驗,其實它們還是有不小的區(qū)別。《尚書》文章所引的歷史經(jīng)驗多為先人故事,沒有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而《國語》所說的歷史經(jīng)驗則多為先王典章制度。如《周語上》載“虢文公諫宣王千畝”,虢文公就是詳細(xì)地闡述先王籍田制度,作為勸諫周宣王籍田的理由。《魯語下》載“公父文伯之母論勞逸”,也是歷舉前代圣王勞民而用的制度。《國語·周語上》載樊穆仲語云:“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xùn)而咨于故實。”其中的故事,就是指典章制度而言,這種重視遺訓(xùn)故實的風(fēng)氣給文章帶來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yùn)。四是從歷史人生中提煉出來的政治道理。如《楚語上》載“蔡聲子論楚材晉用”,蔡聲子就是從王孫啟、析公、雍子、申公巫臣等人叛楚行為中總結(jié)出楚材晉用的深刻教訓(xùn)。《國語》論據(jù)的變化,顯示出西周春秋人們理性精神的發(fā)展和說理能力的增強(qiáng)。
第四,《國語》某些記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較《尚書》有所提高。能否從個別現(xiàn)象中提煉出一般原理,這是判斷人類抽象思維能力提高的一個標(biāo)準(zhǔn),也是衡量說理散文進(jìn)展的一個尺度。《洪范》是《尚書》中抽象概括水平最高的一篇,其中“五行”、“五事”、“八政”、“五紀(jì)”、“皇極”、“三德”、“庶征”等概念,都濃縮了豐富的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現(xiàn)象。但像《洪范》這樣高度概括的文章在《尚書》中找不出第二篇,《尚書》中大多數(shù)文章都處于敘述直觀經(jīng)驗、就事論事的水平。《國語》某些文章已呈現(xiàn)出由敘述直觀經(jīng)驗向抽象概括過渡的傾向。如《周語上》載伯陽父論三川地震:“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于是有地震。”伯陽父沒有將地震歸于天帝旨意,而是從復(fù)雜的宇宙現(xiàn)象中抽象出陰陽這兩種原始的物質(zhì)和力量,用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來解釋地震發(fā)生的原因。《鄭語》載史伯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史伯此論是由周幽王遠(yuǎn)君子親小人現(xiàn)象而發(fā),他超越了經(jīng)驗層次,從對立統(tǒng)一的哲理高度來討論朝廷用人問題。《越語下》載范蠡諫勾踐:“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jié)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jié)事者與地。”“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節(jié)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范蠡所說的持盈、定傾、節(jié)事,實際上就是后來 孟子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就是說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時要充分地尊重客觀條件,范蠡就是根據(jù)這一思想制定滅吳的斗爭策略。即使是討論鑄幣問題,單穆公也從中概括出在不同情況下實施“母權(quán)子”“子權(quán)母”(《周語下》)政策的金融理論。對說理散文而言,抽象思維水平的提高與概括能力的進(jìn)步,可以增加文章的理論含量,拓展說理散文的思想深度。
第五,《國語》繼《尚書》之后進(jìn)一步豐富了說理散文的表現(xiàn)手法。《尚書》在說理過程中已經(jīng)能夠嫻熟地運(yùn)用比喻、設(shè)問等手法,只是表現(xiàn)手法還不夠豐富。《國語》所載西周人物發(fā)表言論,于比喻之外又多了引經(jīng)據(jù)典。春秋說理散文表現(xiàn)手法持續(xù)發(fā)展。層層遞進(jìn)是作者們常用的手法,如《周語上》載“內(nèi)史過論晉文公必霸”:“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jié)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jié)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倫,節(jié)度不攜。”前一層是后一層的前提,后一層是前一層思想的演進(jìn),幾層意思環(huán)環(huán)相扣,層層推進(jìn)。這種手法多為戰(zhàn)國諸子散文沿用。排比是春秋散文又一常用的手法,如《周語下》載“單襄公論晉周將得晉國”,一連用了11個“言……必及……”句式,以說明晉周懂得禮文。又如《楚語上》載申叔時論太子之教,在講到文獻(xiàn)教育時接連用了9個“教之……”句式,論及道德教育時又一口氣用了12個“明……以……之”排比句,最后說:“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后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jié)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jiān)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fā)之,德音以揚(yáng)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多重排比句的大量運(yùn)用,為言論增添了藝術(shù)感染力。同篇載蔡聲子為椒舉游說楚國令尹子木,蔡聲子沒有從正面為椒舉求情,而是從側(cè)面歷舉楚材晉用現(xiàn)象,以此警醒楚人不要再做策士所常用。春秋散文時有幽默諷刺之筆,如《晉語九》載董叔娶范宣子之妹為妻,叔向加以勸阻,董叔說“欲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狀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將董叔綁在庭院槐樹上,正好叔向從旁邊路過,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說:“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幽默之中包含著諷刺意味。
最后,《國語》中出現(xiàn)了一些篇幅短小的人物言論,它們比《尚書·西伯戡黎》、《高宗肜日》更接近后來的語錄體散文,堪稱《論語》、《禮記》之《緇衣》、《表記》、《坊記》、《中庸》等語錄體文章的先驅(qū)。例如: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
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
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垌蛹,水
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日贛羊。”——《魯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
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
下有章。”——《魯語下》
文公學(xué)讀書于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
咫,聞則多矣為淵驅(qū)魚的蠢事。這種側(cè)面微諷的手法為后來戰(zhàn)國
。”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
愈也?”——《晉語四》
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
為難,其易也將至焉。”——《晉語四》
趙簡子曰:“魯孟獻(xiàn)子有斗臣五人,我無一,
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茍欲之,也待交
摔可也。”——《晉語九》
上述三條《晉語》材料中,有兩條與晉文公有關(guān),這說明早在春秋中葉,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近似語錄體的散文。這些小文章言短意長,意味雋永,充滿機(jī)鋒與智慧。孔子師徒言論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關(guān)注的熱點,《魯語下》論載了5條有關(guān)孔子博物的材料,另有一條子夏評論公父文伯之母的言論。上文論列的兩條《魯語下》材料,如果將其放進(jìn)《論語》之中,在形式上已經(jīng)達(dá)到幾可亂真的水平。
當(dāng)然《國語》記言文也有不及《尚書》的地方。從《周語上》“內(nèi)史過論晉惠公必?zé)o后”,征引《湯誓》和《盤庚》來看,至少在春秋中葉,《尚書》文章就有了篇名。而《國語》的文章都是以一條一條的原始史料的面目出現(xiàn),給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韓非子·五》)的感覺。
《左傳》也記錄了春秋時期歷史人物的長篇言論,其中尤以行人辭令美妙絕倫,但是一則《國語》是《左傳》材料來源之一,《國語》某些言論被《左傳》采入書中并加以加工改寫,而從說理散文角度看,《左傳》這些加工過的人物言論反而不及《國語》那樣主題集中;二則《左傳》重在記事,敘述文字遠(yuǎn)較《國語》為多,歷史人物言論多淹沒在敘述過程之中;三則《左傳》成書于戰(zhàn)國前期,可能與孔門七十子后學(xué)同時,因此很難說《左傳》記言文對七十子后學(xué)散文寫作會有什么影響。所以,探討中國說理散文的源頭,僅看《尚書》、《國語》中的記言散文就可以達(dá)到“觀止”的水平。雖然這些歷史記言文還有一個外在的敘事框架,距離標(biāo)準(zhǔn)的論說文尚有一些差距,但剝開敘事的外衣,其中的人物言論主體部分卻是實實在在的說理文章,中國的說理散文就是從這些歷史記言文發(fā)展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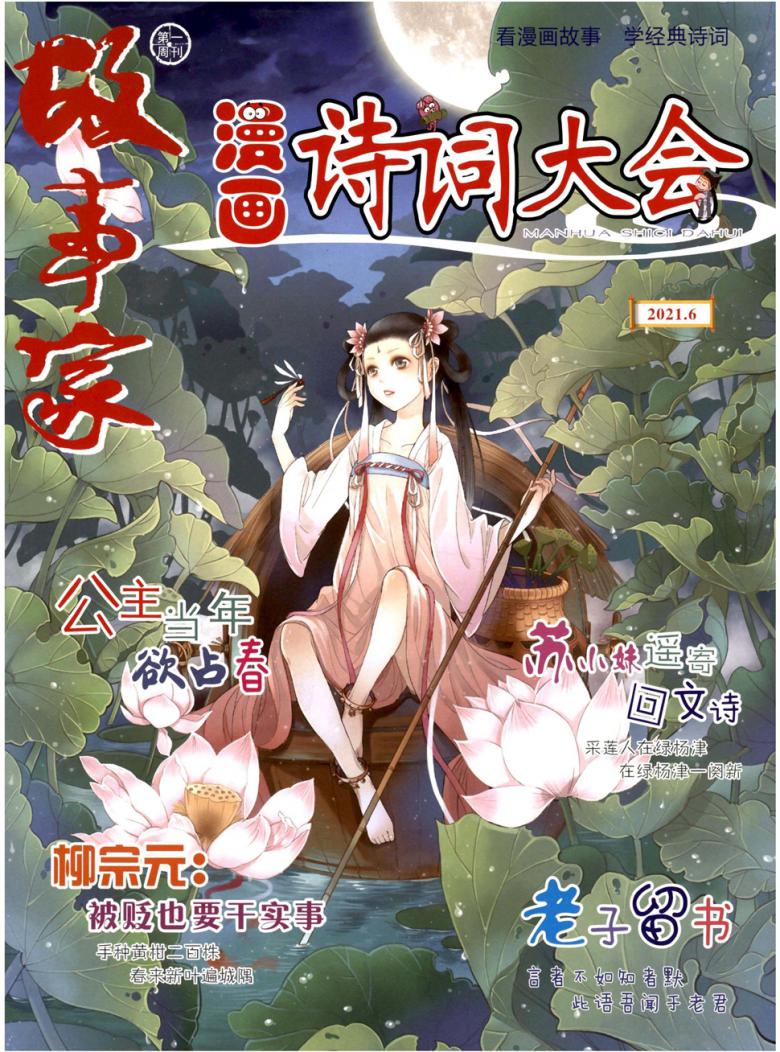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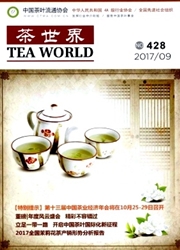
院學(xué)報.jpg)
燃機(jī)與車輛技術(shù).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