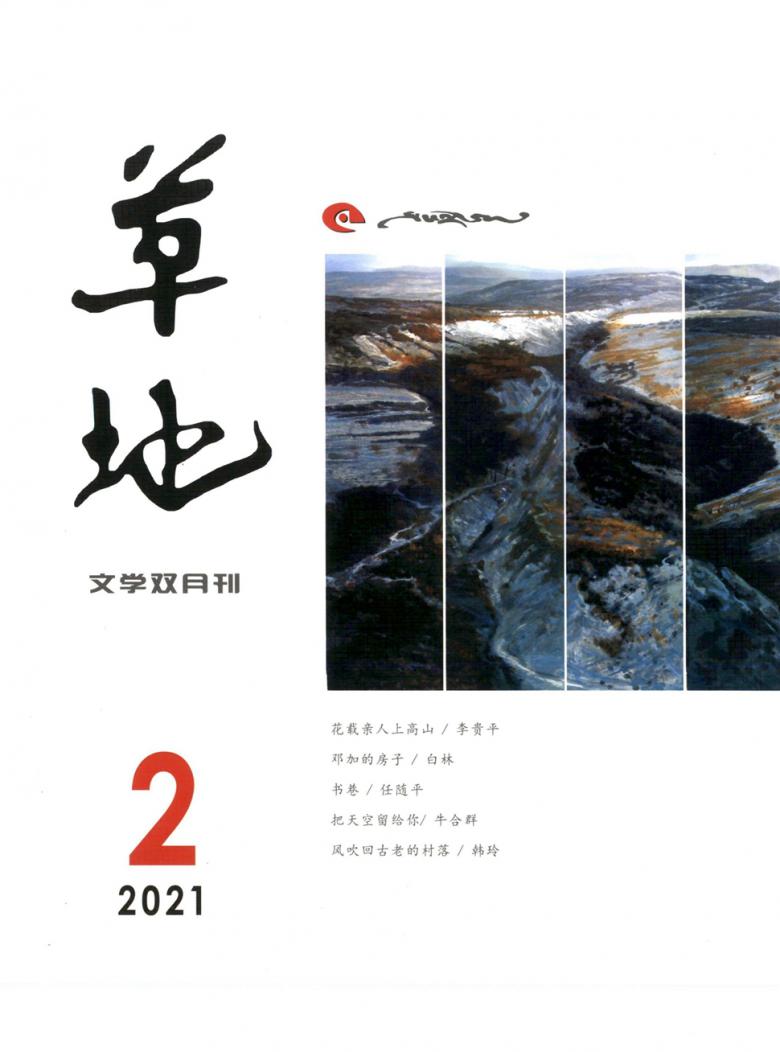從出土文獻看七十子后學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
陳桐生
【內容提要】 本文將七十子后學著述的《論語》、大小戴《禮記》、《孝經》、《儀禮》、郭店簡及上博簡中儒家文獻等作品稱之為“七十子后學散文”。七十子在年輩上有“先進”“后進”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別。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學散文處于上承史官記言散文、下啟諸子說理散文的樞紐地位。
【關鍵詞】 七十子后學散文 先秦歷史散文 先秦諸子散文
《郭店楚墓竹簡》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在世紀之交相繼面世,為先秦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資料。郭店簡和上博簡第一冊中都有《緇衣》,這是《禮記》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簡第二冊中的《民之父母》,內容與《禮記·孔子閑居》大體相同;第四冊中的《內禮》,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內容相近。上博簡中還有一批在內容和形式上與大小戴《禮記》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冊中的《魯邦大旱》、第四冊中的《相邦之道》,都與大小戴《禮記》中那些記載孔子應對弟子及時人的文章相近。特別是上博簡中出現了以孔門弟子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冊中的《子羔》、第三冊中的《中(仲)弓》。雖然這些出土竹書的數量與大小戴《禮記》現有文章相比,還只占較小的比例,但它們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李零指出,郭店簡“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東西,或‘七十子’時期的東西”。“在數量更大,現在還沒有公布的上博楚簡中,我們也發現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中的人物,如顏回、仲弓、子路、子貢、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們的名字題篇。它們是‘七十子’的東西,這點更明顯。”他說:“這是我們的福氣。” (《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這些文獻的出土對某些學術定論——諸如認為大小戴《禮記》作于秦漢時代——提出了挑戰,它們表明,像大小戴《禮記》之類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戰國之際七十子后學之手。新的資料引發我們提出“七十子后學散文研究”論題。
一 “七十子后學散文”釋名
“七十子后學散文”這個概念能否成立?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為此前只有“七十二子”、“七十七子”、“七十子”之說 ① ,而從來沒有“七十子后學散文”的概念。如果“七十子后學散文”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也就沒有研究的必要。“名者,實之賓也。” (《莊子·逍遙游》) 要論證“七十子后學散文”概念能否成立,關鍵是看有沒有七十子后學散文這一史實。漢代文獻記載了一些七十子后學著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以為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景十三王傳》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類載《記》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也。”又載《王史氏》二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學者。”這些《記》都是解說《禮經》之作,傳世的大小戴《禮記》就是選自這些《記》。《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錄《曾子》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子思》二十三篇。《郭店楚墓竹簡》中的《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被專家斷為子思學派之作。上博簡中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學文章,如《性情論》、《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昔者君老》、《中弓》、《內禮》、《相邦之道》等等。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論語》的“記”、“輯”、“纂”都與七十子后學有關。據《禮記·雜記下》載,孺悲從孔子而書《士喪禮》,以此推測,《儀禮》是孔子所述七十子所記。《孔子家語》、《孔叢子》中可能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學文章。據此,“七十子后學散文”是指七十子后學著述的以《論語》、大小戴《禮記》、《孝經》、《儀禮》以及郭店簡、上博簡中儒家文獻為代表的文章。有如此豐富的文獻作為依據,“七十子后學散文”概念就不是出于個人的杜撰,它完全能夠成立。
“七十子后學散文”的外延很難確定,因為戰國文章往往不是一次寫定,它是由宗師口述,弟子作筆錄,然后在傳習過程中不斷地被后學增刪,這個增刪的過程可能長達兩三百年,大小戴《禮記》中有些文章的最后寫定可能已到秦漢時代。因此,“七十子后學”既指七十子本人,也包括七十子弟子及其向下延伸數輩的戰國秦漢之際所有儒家后學。但“七十子后學散文”的主體,則是由孔子口述而為七十子筆錄以及由七十子口授而為他們弟子筆錄的文章,說理散文的創新主要是由這兩代人完成的。此后雖然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學之作,但這些文章的藝術創新價值已經不大。如果不考慮儒家后學增刪的因素,僅以文章開題者為標準,那么我們可為七十子后學散文設定一個大致的下限——子思及其弟子作品,所以戰國中后期孟、荀等文章是排除在七十子后學散文之外的。那么,對大小戴《禮記》、郭店簡、上博簡中的某一篇儒家文章,怎樣才能知道它是由七十子及其后學開題,抑或由戰國中后期乃至秦漢儒生所作呢?這就要從思想內容、典章制度、文風、體裁形式等各個方面進行艱苦細致的考證。七十子后學文章雖然不斷地被后人增刪,在學術觀點、篇章順序以及文字上較初稿會有不同程度的改動,但基本文風應該保持了初稿的原貌。對此,竹簡本、帛書本、王弼本三種《老子》,郭店簡、上博簡和今本三種《緇衣》,上博簡《民之父母》與今本《禮記·孔子閑居》,郭店簡和帛書兩種《五行》,郭店簡《性自命出》和上博簡《性情論》等,都可以作為有力的證據。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擁有一批珍貴的出土竹簡,像上博簡《子羔》、《中弓》等竹書應出于子羔、仲弓之手,《魯邦大旱》也應該是出于七十子的記載。這些文章基本保留了春秋戰國之際的文章風貌。結合傳世古籍與出土文獻,完全可以得出科學的結論。
并非所有七十子后學文獻都有文學研究價值,像《儀禮》和大小戴《禮記》中那些專載禮儀制度的文章,文字枯澀艱深,內容淡乎寡味,基本上沒有文學意味,至多只能作為先秦諸子散文研究的背景資料 ② 。具有文學研究價值的主要是以下幾類:
1.片斷語錄體:《論語》中的語錄部分,《禮記》之《坊記》、《表記》、《中庸》、《緇衣》。郭店簡中幾篇《語叢》也可歸入這一類。
2.問答記事體:《論語》中的記事問答部分,上博簡《子羔》、《中弓》、《魯邦大旱》、《民之父母》、《相邦之道》,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禮記》之《檀弓上》、《檀弓下》、《曾子問》、《禮運》、《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儒行》、《孝經》,《大戴禮記》之《主言》、《哀公問五義》、《禮察》、《衛將軍文子》、《五帝德》、《子張問入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閑》。
3.專題論文:此類文章又可分四種情形:(1)《大戴禮記》之《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禮記》之《大學》。這些文章大都是曾參的講學記錄,它們是最早的專題論文。(2)《禮記》之《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大傳》。這些文章都是典型的《儀禮》傳記。(3)《學記》,《樂記》,《大戴禮記·禮三本》。這些文章討論教育、音樂和禮義,可以視為廣義上的禮學傳記。(4)郭店簡《五行》、《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性自命出》、《六德》、《尊德義》,上博簡《從政》甲乙篇。這一組文章都是近年出土竹書。
上述文章除《論語》外,此前大都不在文學史家的學術視野之內。其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此前人們將大小戴《禮記》等文章斷為秦漢之作,二是以為這些禮學文章屬于典章制度,不在文學研究之列。這兩大認識障礙,前一個已被掃除;至于第二個誤解,只要將我們將上述論列的文章與《孟子》、《荀子》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它們在內容和形式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既然《孟子》、《荀子》可以作為文學史研究對象,為什么七十子后學文章就不能呢?
二 “先進”與“后進”,“述”與“作”
孔子三十四歲開門授徒,七十二歲去世,從教三十八年(《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年十七,魯國貴族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從孔子學禮。如果孔子從教生涯從此時算起,則有五十五年教齡),他的弟子年齡跨度很大。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七十子之中年齡最大的是子路,小孔子九歲;年齡最小的是公孫龍,小孔子五十三歲,最大與最小之間相差四十四歲。而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孔門弟子中年齡最大的是秦商,小孔子四歲;年齡最小的與《史記》所載相同,兩者之間相差四十九歲。這個年齡差距足足跨越了兩代人,事實上孔門弟子中有些人——諸如曾點與曾參、顏由與顏回——就是父子關系。《論語·先進》載孔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清人劉逢祿在《論語述何》中認為,“先進”與“后進”指的是弟子及孔門之次第。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中進一步指出,孔門弟子有前輩與后輩之分,像子路、冉有、宰我、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都是孔門弟子中的前輩,他們多問學于孔子去魯之前;而子游、子夏、子張、曾參、樊遲、漆雕開、澹臺滅明,則是孔門弟子中的后輩,他們多從游于孔子返魯之后。而前輩與后輩的風氣大不相同:“由、求、予、賜,志在從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學;前輩則致力于事功,后輩則精研于禮樂。……大抵先進渾厚,后進則有棱角;先進樸實,后進則務聲華;先進極之為具體而微,后進則別立宗派;先進之淡于仕進者,蘊而為德行;后進之不博文學者,矯而為瑋奇。” (《先秦諸子系年》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1—82頁) 為什么同出孔門,“先進”與“后進”的風氣竟有如此大的變化?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春秋戰國之際,伴隨著宗教、政治、文化、風氣和社會心理的巨變,士風逐漸由實趨華,尤其是魏文侯所開創的尊士養士之風,直接引導著社會心理和士風的深刻轉變,士林階層競相向社會展示自己的創造個性,以吸引社會的注意力。如果將春秋戰國之交的社會變革比做一個門檻,那么“先進”尚處于這個門檻之內,他們更多地接受春秋士風的影響,所謂樸實深厚、志在從政、蘊為德行等等,無不深深地打上了春秋士風的烙印,可以說“先進”是春秋士風的殿軍;“后進”則處于這個門檻之外,他們重視文學,精研禮樂,務求聲華,別立宗派,是戰國士風的開啟者。
“先進”長篇文章可以辨識的有:宰予一篇:《大戴禮記·五帝德》;子貢一篇:《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仲弓一篇:上博簡《中弓》;子羔一篇:上博簡《子羔》(本文采用郭沫若《十批判書》的研究方法:凡文中涉及到某一孔門弟子的,就視該文為某弟子的作品)。“先進”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子路、冉有、閔子騫、冉伯牛、原憲、公西華、曾點都沒有長篇文章傳世,尤其是孔子最得意的高足顏回,竟無一篇獨立的長篇文章留下來。“先進”是中國第一批私學弟子,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最大功績,就是模仿史官記言記事,首開記述其師言行之風——這一風氣直接影響到“后進”和戰國諸子百家。孔子本人述而不作,他僅在口頭發表言論,弟子將老師言行載于簡帛。“先進”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這一模仿不亞于一場文學革命,因為那支筆伴隨著官學下移而從史官轉移到諸子手上,這是從先秦歷史散文向先秦諸子說理散文嬗變的樞機所在。如果說孔子開門辦學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標志著史官文化向士文化的嬗變,那么七十子記述孔子言行就意味著散文寫作在作家、內容、形式各方面都在產生深刻的變革。《論語·衛靈公》載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這條語錄是孔門弟子記述其師言論的一個縮影,只不過子張屬于“后進”,而記錄孔子言行肇端于“先進”。七十子記錄孔子言論,這種情形與蘇格拉底在雅典市中心廣場與游人討論哲學、弟子柏拉圖將其思想載于《對話錄》一樣,東西方的哲人在大體相同的時間,以相同的形式從事學術活動,這是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由記載孔子言行,而派生出孔門另一個“弟子規”,這就是七十子應該在孔子名義下發表學術見解。《禮記·檀弓上》載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往吊,子夏哭訴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批評子夏說:“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孔穎達疏:“云‘疑女于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辨彗聰睿,絕異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 (《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頁) 子夏居西河教授時“不稱其師,自為談說”,以至于西河之民誤認為子夏的道德修養達到了孔子的水平,這被曾子指為子夏的一大罪過。這表明,七十子在著述時要“稱其師”,而不能“自為談說”。“稱其師”就是“述”,“述”包含記述和闡述兩層涵義,前者是指記載孔子言行,后者則指以老師的名義對某些重要觀點進行解釋和發揮。所以,七十子筆下的“子曰”,有時是記載孔子的真言論,有時則是七十子借乃師名義表達思想觀點。只是由于弟子以孔子名義發表見解,這給后人辨析先秦文獻中哪些是孔子真言論、哪些是孔子后學思想帶來了難度。“先進”具有極高的從政熱情,他們渴望從孔子那里學會從政之道,對傳說中的“五帝”“三王”充滿向往之情,這一點可從宰予、子羔、仲弓之文見出。“先進”文章大都是“述”,在記事問答框架之下安排說理內容,與《尚書》、《國語》記言文形式相近,這是戰國諸子散文的最早形態。
“后進”的著述熱情要遠遠高出于“先進”,僅曾子這一系可辨識的文章就有十四篇:《禮記》之《曾子問》、《大學》,《大戴禮記》之《主言》、《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孝經》。此外有子夏一篇:《禮記·孔子閑居》(上博簡《民之父母》與此內容略同);子張一篇:《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子游一篇:《禮記·禮運》。“后進”中的宓子賤與漆雕開都有專著傳到漢代,可惜均已亡佚。大小戴《禮記》和上博簡中有十幾篇專記孔子答魯哀公問的文章,孔子應對魯哀公,應在哀公十一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84—前479年)之間,即在孔子返魯之后去世之前,此時孔子的身份是前朝元老,處于既不復求仕但又不能忘情政治的心態,而在思想學術上則臻于老更成境界,愛作理論思考的魯哀公因此經常向孔子請益,而此時孔子的應對更具學術含量,這樣高水平的學術談話,自然是弟子們爭相記錄的內容,而記錄者是“后進”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檀弓》上下篇涉及到的人物頗多,其中時間最晚的是曾參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以此推測,這兩篇文章的素材是七十子提供,編者似是曾參一系弟子。為什么“后進”中文章最多的并不是以文學著稱的子游、子夏而是曾參?曾參并不在孔門“十哲”之內,他何以成為七十子中最大的作家?須知“十哲”只是孔子或時人在某一時期對孔門高足的評價,其時曾參尚未嶄露頭角。《論語·先進》有“參也魯”之說,“魯”意為遲鈍,這表明曾參反應慢,在孔門一開始并不出眾。他成功的奧秘在于情商高,壽命長,弟子多且能,所以最終他超軼游、夏而成為七十子中的巨擘。與“先進”相比,“后進”著述呈現出一些新的動向,他們的文章從形式上看都是“述”孔子之言,似乎與“先進”文章沒有什么區別,其實不然。他們嘗試在孔子名義之下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如《禮運》記載孔子對子游講述“大同”和“小康”,前者的特點是“天下為公”,而后者的特點是“天下為家”。文中的“孔子”尊“大同”而貶“小康”,這一情感態度與《論語》中矢志“從周”的孔子相距甚大,可以說是把《論語》中孔子畢生追求的價值都貶低了,難道孔子傾注一生心血為之奮斗的目標全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嗎?我個人的看法,《禮運》可能是子游氏之儒借孔子之名來發表自己的社會理想,即寓“作”于“述”,用莊子的話說,就是“重言”。曾參創新傾向更為明顯,他的十四篇文章分為兩種情形:《禮記·曾子問》、《大戴禮記·主言》、《孝經》三篇是以問學孔子的形式出現;另外十一篇則是曾參自己的演講,這些文章間或偶爾提及孔子,如《曾子天圓》中有“參嘗聞之夫子曰”的字眼,但從總體上說都是以“曾子曰”形式發表見解。這些文章的記錄者當為曾子門生,門人之稱述曾子,就像曾參稱述孔子一樣。極有意味的是,曾參曾經指責子夏不稱其師,他自己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其中的原因是在曾參弟子身上,弟子們客觀地記下曾參的演講詞,結果就成了曾參的獨立作品。“作”的出現可能還與孔子師徒講學形式變化有關:從《論語》和其他七十子文獻來看,孔子的教學方式,一是隨機應答弟子問,這相當于今天的個別輔導,二是有意識地組織小范圍座談(即所謂“侍坐”),那種以一個“孔子曰”領起一篇大演講詞的情況尚未發現。而曾子之“作”則是以一個“曾子曰”領起全文,這表明曾參是在向全體弟子發表專題演講,是“大班授課”,這樣師徒對話的機會就少了,記錄稿就是一篇獨立的演講詞。如果說“稱其師”是“述”,那么不稱其師就是“作”。曾參是“述”與“作”兼而有之,而“作”多于“述”,他是七十子中第一個可考的“作”者。從說理散文寫作角度看,“作”的意義比“述”要大得多,因為“作”不僅拋棄了對史官記言的形式依傍,而且要擺脫“稱其師”的形式束縛,獨立地發表自己的思想見解,體現在文章上就是去掉了敘事框架,剩下的完全是說理內容,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專題說理論文,它是諸子說理散文走向獨立發展的最為關鍵的一步。
無論是七十子的“述”還是“作”,似乎一切都是雁過無痕出于無意,其實不然。第一個執筆記述孔子言行的弟子,就是一位具有原始創新精神的作家;第一個改變孔子教學方式的弟子,更是一位勇于開拓的先行者。就是在他們手中,先秦散文完成了意義深遠的巨變。沒有人發薪金,沒有人付稿費,甚至連著作權都沒有,他們所憑的是一種真誠的信仰。七十子從“述”到“作”,歷時不過三四十年,這就是一往無前、銳意創新的七十子!
“先進”與“后進”的文章都有一個共同主題——闡述禮學。七十子后學散文被后人視為禮學傳記,郭店簡、上博簡中的儒家文獻,如能傳到漢代,或有可能收入大小戴《禮記》之中。為什么七十子后學散文都是禮學文獻?這是因為,如何對待周禮,是從平王東遷到戰國初年這幾百年間意識形態的焦點。孔子代表了那個時代一部分人對西周禮制秩序社會的強烈懷舊情緒,他一生的政治目標就是恢復周禮。七十子所繼承的就是孔子畢生為之奮斗的禮學事業 ③ ,他們以空前的緊迫感和巨大的熱情從事禮學著述,記載禮儀,闡述禮義,借此深入探討宗教、哲學、倫理、政治、教育、藝術乃至歷法等一系列問題,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學說 ④,就是在他們手中,先秦禮學完成了由重視禮儀到崇尚禮義的重大轉變。他們的著作為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奠定了堅實的根基。
三 七十子后學散文的文學成就
在討論七十子后學散文文學成就之前,首先要確立一個評價尺度。這是因為,此前對先秦諸子散文的評價標準有些混亂:有人以形象化作為評價標準,這樣他們就較多地關注諸子散文中的取象譬喻和人物事件的描寫;有人則以文章的情感氣勢作為批評尺度;也有的人是兩者兼而有之。本文認為,說理,是諸子散文質的規定性,所以不能拿形象是否生動之類的記敘文尺度評價諸子散文,否則,最優秀的諸子散文中的藝術形象也無法與最差的歷史散文相比。評價先秦諸子散文的尺度,就是這些文章所體現的情感氣勢之美,這種情感氣勢一方面來自于戰國士文化所激發的作者人格力量和情感意志,另一方面則是通過論證過程中的嚴密邏輯安排和各種表現手法的成功運用而產生出來的。對于七十子后學這些早期說理文章,我們還應該更多地關注論說文逐步成型的過程。
讓我們從片斷語錄體、問答記事體和專題論文幾類,討論七十子后學散文的文學成就。
《論語》和《禮記》中的孔子片斷語錄,是孔門弟子從記錄的諸多孔子言論中精選出來的。此前論者或以為先秦說理散文是從零開始,《論語》的片斷語錄正代表了說理散文剛起步時的幼稚形態,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們從《尚書》、《國語》、《左傳》的記言文看到,早在七十子之前,人們就已經具備了相當高的理性思維水平和書面表達能力。《論語》語錄體制的短小,絕不意味著當時說理散文只能達到這樣的水平,而是語錄編纂者刻意從原始記述材料中節選出來的。對此,上博簡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論語·子路》載:“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這一章語錄在剛剛面世的上博簡《中弓》中有所體現,分別見于第一簡:“季桓子使仲弓為宰,仲弓以告孔子,孔子曰:‘季氏……’”第七簡:“……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赦過與罪。”第九簡:“‘……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雖有賢才,弗知舉也。敢問舉賢才……’”第十簡:“‘……如之何?’仲尼曰:‘夫賢才不可弇也。舉爾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赦過與罪,則民可要?’”雖然兩者在文字和孔子稱謂上存在某些差異,但主要內容是相同的。以此推測,《論語》“仲弓為季氏宰章”與《中弓》所記應為同一件事,前者是仲弓一系的弟子從當年仲弓原始筆錄材料中節取的。七十子后學之所以要節選孔子語錄,可能是受到此前社會上流傳的哲人格言、警句、民諺的啟示。從《國語》、《左傳》可以看到,春秋時期政治文化界習慣于征引仲虺、史佚、周任等古代哲人的格言警句,作為說辭的論據和行為的準則。如《國語·周語上》載晉大夫叔向引史佚之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左傳·襄公三十年》載子皮引《仲虺之志》:“亂者取之,亡者侮之。”這些格言警句于片言只語之中,凝聚了豐富的政治、軍事、歷史、社會、人生經驗,有些甚至蘊含了深刻的哲理,給后人以無窮的警示和啟迪。七十子認為孔子的智慧可以與上古哲人媲美甚至超軼古人,所以他們才將筆錄的孔子言論進行提煉和節選。經過七十子選擇提煉后的《論語》片斷語錄,言約意豐,高度凝煉,于深沉含蓄之中見出雋永的意味,透發出一種理趣美,體現出口述者的深刻睿智和執著信念。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而》)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罕》) 等等,片語之中凝聚著豐富的人生經驗,耐人久久地涵詠,不少語錄可以作為格言來讀。特別是語氣詞的運用,疏宕有致,讀之回腸蕩氣。某些語錄通過如詩如畫般的意境,傳達出某種深刻的哲理,如“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罕》) 。《禮記》之《坊記》、《表記》、《中庸》、《緇衣》四篇據說是輯自子思之手,這些語錄的篇幅較《論語》要長一些,感性成分大為減少,精警程度不及《論語》,編輯者子思雖曾親聆乃祖音旨,但這畢竟是幼年的事情,他所收集的都是經過儒家后學輾轉相傳的孔子語錄。郭店簡三篇《語叢》沒有“子曰”字眼,可能是孔子某幾位后學的學術短札。《論語》、《禮記》、《語叢》片斷語錄的文學價值,不在于它們代表了說理文起步時期的風貌——它們其實并不能真實反映春秋戰國之交說理文的水平,而在于它們確立了中國哲理散文的一種體裁——語錄體,從戰國的《孟子》到漢代的《法言》,從隋代的《文中子》到宋代的《朱子語類》,再到明代的《傳習錄》,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都樂于采用先哲曾經運用過的凝煉含蓄、睿智圓通的語錄體形式。推而廣之,中國古代汗牛充棟的詩話、詞話、賦話,在形式上也未必沒有受到《論語》、《禮記》語錄體的影響。
七十子后學散文中問答記事體的最大藝術價值,就在于它們體現了先秦歷史散文與諸子散文之間的密切聯系,展示了先秦歷史散文向諸子散文嬗變的軌跡。它告訴人們,諸子說理散文并非從零開始,而是從先秦歷史記言散文轉變而來的。理解此類文章的關鍵,在于了解七十子對史官記言的模仿。在七十子之前,史官記載了很多王侯卿士大夫的治國言論,它們被保存在《尚書》和《國語》之中。這些記言文的常見結構是在敘事框架之下記載人物言論,大學中文系講堂上必講的《國語·周語上》“邵公諫弭謗”一文,就是此類記言文結構的典型代表。如果將這些文章的敘事框架去掉,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篇說理文。從《尚書》、《國語》可以看出,早在商周時代,人們就表現了相當高的說理才能。如《尚書·洪范》載殷朝遺老箕子向武王陳述“洪范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極,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先綜括全文大意,以下各段具體論述九疇內容,這種結構方式對七十子后學闡發師說具有啟示意義。又如《國語·周語上》載祭公諫穆王征犬戎,開頭提出“先王耀德不耀兵”的大綱,以下諫辭全從這七個字生發開去:先征引《詩經·周頌·時邁》,說明先王治民重在修德厚性;繼而歷述后稷、不、武王等周民族先王修文德安民的事例,微諷周穆王無端征伐犬戎不合先王舊章;最后說犬戎按時向周王朝履行荒服納貢之責,并無失職之處,周穆王此舉實在師出無名。全篇諫辭一氣呵成,環環相扣,層層生發,既觀點鮮明又有理有據,層次井然,極有文法。有些文章是以君臣對答形式出現的,如《尚書》之《西伯戡黎》、《微子》、《洛誥》等篇就有簡單的人物對話。《國語》中記載人物對話尤多,像《周語上》“內史過論神”,《齊語》“管仲對桓公以霸術”、“管仲教桓公親鄰國”、“管仲教桓公足甲兵”,《鄭語》“史伯為桓公論興衰”,《楚語下》“觀射父論祀牲”等,都是以君臣問答形式結構全篇,問者多為君主,而對答者為卿士大夫,重點落在答語之上。尤其是《國語·魯語下》所載“孔丘論大骨”、“孔子論楛矢”、“孔丘非難季康子以田賦”幾篇,與《論語》、大小戴《禮記》以及上博簡《魯邦大旱》等記載孔子答時人問的文章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孔子師徒雖然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但孔子曾經擔任魯國大夫,卸職后仍自稱“從大夫之后” (《論語·憲問》) ,孔門不少弟子也都在各諸侯國或大夫門下出任宰臣等要職 ⑤ ,孔子師徒都以從政作為人生第一目標,因此孔門之下官場作派很濃。史官是“君舉必書” (《漢書·藝文志》) ,七十子就來一個“師舉必書”。當然,七十子在繼承中有新變:史官記言文大都是針對現實政治問題,一事一議,而從七十子開始,務虛性的學術探討增多了,學理意味增強了。
問答記事體兼有記事、說理因素而以說理為主。從說理文發展角度看,記事描寫的感性因素越少,論述邏輯性越強,文章價值就越高。因此像《論語·鄉黨》對孔子形象的素描,像《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章”等,雖然將人物事件寫得具體可感,但對推動說理文寫作意義不大。《禮記·檀弓》上下篇記載了幾十個禮學故事,這是七十子后學以具體事例宣傳禮學的嘗試,它對寓言文體的產生可能有直接的啟示,尤其是對戰國后期韓非子《說林》上下、內外《儲說》、《喻老》、《解老》諸文影響甚深,但對說理文的發展同樣沒有多少借鑒價值。問答記事體的一些文章是多主題的漫談。如上博簡《子羔》有十四支殘簡,一至八簡討論堯、舜禪讓,孔子告訴子羔,上古時代“善與善相受”(第一簡),“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第六簡);九至十四簡主題變為“三王者之乍(作)”。又如上博簡《中弓》現存二十八支簡,主題變換了三次:一至十簡是孔子回答仲弓“為政何先”問題,孔子提出“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赦過與罪”的為政四綱領;十一至十九簡是孔子解答仲弓關于如何“導民興德”問題,其核心觀點是“刑政不緩,德教不倦”;后九支簡內容是孔子告訴仲弓如何與季桓子相處,關鍵在于“以忠與敬”。《禮記》之《曾子問》、《哀公問》以及被稱為“孔子三朝記”的七篇文章,文中的論題也經常轉換。說理文應該主題集中,像這種多主題的漫談,還不能說是上乘的說理文。《禮記》之《孔子閑居》在統一主題方面有所進展,文章以子夏問“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提出論題,而以孔子回答“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總領全篇,接下去分別討論“五至”、“三無”、“五起”和“三無私”,層層遞進,極有章法。《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以論士開題,然后逐一論述“庸人”、“士”、“賢人”、“君子”和“圣人”,文脈清楚,而論士主題一以貫之。文中雖然還有賓主問答的敘事框架,但這些問答的敘事功能已經弱化,它是通過提問而將論述引向深入。同類文章還有《禮記》之《禮運》、《經解》、《仲尼燕居》、《儒行》,《孝經》,《大戴禮記》之《主言》、《五帝德》、《子張問入官》等等,出現篇名是問答記事體的又一進展。上博簡《子羔》第六簡背書有“子羔”,《中弓》第十六簡背書有“中弓”,整理者認為這兩個字就是文章篇題。這種命名方式雖然不能點出文章宗旨,只有標識意義,相當于今天的代碼,但它畢竟是給文章設立篇名的開始,標志著說理文的新進展。有些文章在表現手法上積極創新,如《禮記·儒行》載孔子縱論儒行,“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容貌有如此者”,“其備豫有如此者”,“其近人有如此者”,“其特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其自立有如此者”,“其仕有如此者”,“其憂思有如此者”,“其寬裕有如此者”,“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其任舉有如此者”,“其獨立特行有如此者”,“其規為有如此者”,“其交友有如此者”,“其尊讓有如此者”,一共十六個“其……有如此者”排比而下,壯浪縱恣,氣勢浩然,開后來戰國策士鋪張揚厲之風,只不過此類文章在七十子后學散文中尚不多見。從總體上看,這些問答記事散文還脫離不了史官記言文的格局,它們還處于由歷史記言文向典范的諸子說理散文過渡的形態 ⑥ 。從說理散文角度來看,七十子后學的專題論文意義最大,因為這些文章不再有敘述、描寫的因素,而純粹是說理文字。在前文列舉的七十子后學四類專題論文中,郭店簡中的儒家文獻被專家視為子思學派之作,寫作時代可能偏晚,而《樂記》受到后學增益的可能性較大,成書年代一直存在爭議,具有研究價值的是前兩類文章。《大戴禮記》收錄的曾參一系十一篇文章,可以視為七十子后學之“作”的代表。以《曾子本孝》為例,文章一開頭就揭示中心論點:“忠者,其孝之本與!”以下從五個層次來進行論證:首先要全身遠禍,既要遠離自然的禍患,又要避免人事的是非;其次要居于平安容易之地,不以危險行為謀求非望之福;再次是以內斂的方式與人相處,無論是在父母生前身后,都要以恭敬態度待人;第四是要求卿大夫、士、庶人各個階層都要履行自己的倫理義務;最后要求孝子應該從父母的生、死、祭三個方面來實踐“敬”的倫理。全文以“忠”開篇,以“敬”作結,層層鋪開,首尾呼應,已是一篇比較完整的專題論文。《禮記·大學》開頭以極有邏輯性的語言概括了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一段文字,被宋儒概括為三綱領八條目。作者論述的方法是,先設定一個邏輯起點,由此生發,從小到大,由淺入深,前一項是后一項的必要條件,后一項是前一項的邏輯提升。以下幾段,重點論證誠意、正心、齊家、治國,最后說明仁義道德是治國的根本。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將第一章定為孔子所論的經,而以下幾章為曾子所述的傳。此說是否屬實,還可以討論,但《大學》第一章確實是全文的論綱,它的藝術結構明顯受到《尚書·洪范》的影響,而在邏輯嚴謹方面超過了《洪范》。我們可以說,中國典型的專題說理散文,是在曾參時代出現的。
《禮記》中專釋禮儀意義的論文共有七篇,它們應該是七十子后學為宣傳禮學而專門寫作的。這些文章是按照“總——分——總”的思路結構全文,前有概述,后有呼應,中間層層展開,義脈文理俱可圈點。以《冠義》為例,全文分為四層:首論冠禮之大義就在于它是成人之禮的開始;次論冠禮各項細則所包含的意義:“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三論舉行冠禮意味著成人要肩負起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的倫理責任;最后呼應前文,并從成人而升華到“治人”高度,由此深化了“冠義”的主題。其他幾篇文章大體上都能圍繞一個禮義主題展開論述,說理充分,結構嚴謹,已是規范的說理散文。
一部先秦散文的發展史,從歷史散文到諸子散文,就如同一條長河,其間雖有曲折,有改道變遷,但卻從來沒有中斷過。先秦歷史散文與先秦諸子散文決不是互不關聯的兩大河流,它們屬于同一水系,在內脈上是互相打通的。七十子后學散文是先秦散文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是一個轉折點,它處于上承歷史記言散文、下啟諸子百家說理文的樞紐地位。事實表明,先秦諸子說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第二代后學手中就已基本成型,此后諸子百家散文只不過是在篇幅、風格、技巧、手法、邏輯結構上有所發展而已。因此,不僅對此前關于先秦諸子散文三段論發展模式(《論語》、《老子》、《墨子》為第一階段,《孟子》、《莊子》為第二階段,《荀子》、《韓非子》代表第三階段)應該重新審視,而且對《尚書》、《國語》的藝術成就也要進行再認識,要充分關注《尚書》、《國語》記言文的說理成就,因為這些記言文積累了豐富的說理經驗,它們是七十子后學散文和諸子說理散文的先驅。由于七十子后學散文尚處于先秦散文發展的歷史轉折點上,他們所寫的差不多都是禮學文章,而他們所生活的春秋戰國之交尚未進入激情燃燒的歲月,這些因素使七十子后學散文顯得有些沉悶枯燥,在情感氣勢上無法與戰國中后期散文相比。這是時代所造成的局限。
本文的結論是:第一,郭店簡、上博簡出土文獻表明,大小戴《禮記》、《孝經》等大部分禮學文章作于春秋戰國之際七十子后學之手,而不是寫于秦漢,“七十子后學散文”概念完全能夠成立。第二,七十子中的“先進”仿照史官記言記事傳統,首開記述孔子言行之風,由此實現了從先秦歷史記言散文向諸子說理散文的過渡。先秦諸子說理散文并非從零開始,此前史官的歷史記言文是它的直接源頭。第三,七十子中的“后進”突破了言必“稱其師”的慣例和對史官記言的形式依傍,以個人名義獨立地發表學術見解,這些文章已經具備了說理文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專題說理論文,說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弟子手中就已基本成熟。第四,七十子后學散文牽一發而動全身,它涉及先秦歷史散文、先秦諸子散文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因此對此前關于先秦散文的整個知識體系要予以重新審視。
注 釋
①《論語》中出現孔門弟子姓名的有二十七人。《史記》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儒林列傳》分別有七十二子、七十七子、七十子三種提法。《孔子家語》中有《七十二弟子解》,但正文卻載七十七人。《文翁弟子圖》載七十二人。《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蓋受教者七十有余人。”《呂氏春秋·遇合》說孔子“達徒七十人”。《韓非子·五蠹》說孔門“服役者七十人”。《淮南子·要略》:“孔子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漢書·藝文志》:“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本文采用班固七十子后學的說法。
②這一類文章有:《禮記》之《曲禮上》、《曲禮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少儀》、《雜記上》、《雜記下》(含《大戴禮記·諸侯釁廟》)、《喪大記》、《祭法》、《祭統》、《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大戴禮記·投壺》相同)。《大戴禮記》之《夏小正》、《保傅》、《武王踐阼》、《帝系》、《盛德》、《明堂》、《諸侯遷廟》、《朝事》、《公符》、《本命》、《易本命》。《文王官人》記載歷史舊聞,上博簡《昔者君老》記載太子朝見彌留父君的行為規范,《內禮》記載男女居室禮儀,大體上也可歸入這一類。《孔叢子》、《孔子家語》真偽并存,暫不討論。《大戴禮記·勸學》與《荀子·勸學》相同,可能是秦漢儒生取自《荀子》,故不予討論。
③先秦禮學可以分為禮儀與禮義兩個層次,而禮儀、禮義均有廣狹之分:狹義的禮儀專指冠、婚、喪、祭、聘、燕、射、飲、相見等行為規范,廣義的禮儀則包括封建、職官、祿田、賦稅、田租、軍制、軍賦、學制、刑法、宗法制度等等;狹義的禮義專指禮儀所包含的倫理政治意義,廣義的禮義則涵蓋政、教、德、法各個方面,相當于封建時代整個上層建筑。懂得這一點,就可以明白七十子后學散文何以內容如此廣泛。
④七十子后學對孔子學說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曾子學派發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形成了由孝及忠、從倫理到政治的思路,對漢代和整個封建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二是子游學派闡發了孔子“大同”的社會理想,給后代志士仁人以強烈的感召;三是以漆雕開、宓子賤為代表的弟子深入研究人性,經由孔子之孫子思的發展,形成一股強大的人性論思潮,此派一方面直接啟發了孟子的性善論和仁政學說,另一方面在藝術上則導致了儒家對藝術抒情本質的發現,從而接觸到中國藝術理論的核心問題;四是仲弓學派注重禮樂刑政,此派思想經過荀子的發揮而深刻地影響了秦漢政治;五是以商瞿、孺悲為代表的弟子從事傳經事業,影響了漢代和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學術。
⑤如子路曾為季氏宰、蒲大夫、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子羔為費宰、費 宰、孟孫氏成邑宰、衛之士師、武城宰,子貢為信陽令,子夏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閔子騫為費宰,宓子賤為單父宰,冉求為季氏宰,仲弓為季氏宰,宰我為臨淄大夫,原思為孔子家宰。
⑥七十子記述宗師言行的風氣為此后諸子百家所繼承,諸如《墨子》中的《三辯》、《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商君書》中的《更法》,《吳子》中的《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藝文類聚》卷二〇載《尹文子》逸文“尹文子見齊宣王”條,《荀子》之《議兵》,《韓非子》之《問辯》、《問田》、《定法》,都是記錄言論行事之作。至于“大賢擬圣而作”(趙岐《孟子題辭》)的《孟子》,所收錄的都是孟子言論行事。《荀子》中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雜錄堯舜及孔門佚事,大約也可歸入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