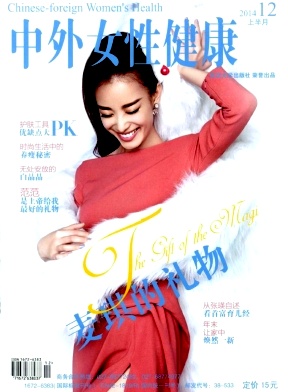論劉勰的“論”體散文觀
林春虹
【內容提要】 “論”體,古代散文的一種重要文體,在劉勰的文體專章中被置于筆體的第二位,他的系統敘述在古代十分難得。他遵循文體論篇章的一貫方法,對論體文進行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等工作,論述十分到位。同時,劉勰關于論體文散文觀的最高理想已經不同于為政教服務的傳統散文觀,而是轉向以體現個體生命價值作為立足點。當然,他也堅守宗經原則,對論體文的社會功能并不忽視。 【關鍵詞】 “論”;體;劉勰
“論”體,古代散文的一種重要文體,對于喜歡隨感悟而信手成文的古人來說,要把握好無疑是一個比較嚴肅的難題。劉勰作為中世紀一個承前啟后又空前絕后的文論家,對于論體文的認識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將論體放置于筆體的第二位進行詳細探討,可見此體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重。古代較有系統地專門研究這一文體的人并不多見,這使得劉勰對論體的敘述更顯得重要,今天的學者專門注意到劉勰這些見解的也不多,所以本文嘗試著來談談劉勰的論體散文觀。 一 劉勰說:“圣哲彝訓日經,述經敘理日論”。經是圣人所作,而“論”帶上了孔子所說的“述而不作,,的意味。他還指出,《論語》是第一部以論為題的著作(這里認同范文瀾對“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的理解),于是,無意中孔子對論體的產生就做出了或直接或間接的貢獻,這突出了論體的獨特意義,同時也說明了劉勰視論體為僅次于史傳體的第二大無韻文體的潛在深意。古來學者對劉勰在此首舉《論語》頗有微詞:從宋朝晁公武到明朝楊慎到清朝紀昀等等這些大學問家都很奇怪劉勰為什么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同時舉出經書中有“論”字的例子。其實他們都忽略了劉勰是從“體”的視角來說這句話的。經書有“論”字但不以論為題,因為經書是一切文體的根本依據,經就是道的載體,不能用也不必用某一“體”來分解經。經無“論”字僅僅為了說明論體是從經書中分流出來而已,正如劉勰所說“論”這一體是“《易》統其首”,《易》經無所謂哪一體,但卻分流出“論、說、辭、序”等各種體。經與論體的關系就是“原始以表末”的關系,劉勰指出了“論”的“述經”性質,實際上是突出了論體的重要地位,其他“體”如“詔、策、章、奏”等都是從實際功用層面來定位的,而論體卻直接從意義屬性的層面來定位,因此它可以與其他體如“議說”、“傳注”、“贊評”等相交叉。 論體與經書固然是密切相聯的,然而劉勰認為《論語》對論體具有開創之功是否恰當呢?蔣祖怡先生在其《文心雕龍論叢·文心雕龍內容述評》中說: 《論語》之“論”,是“論纂”之“論”,不是“議論”之“論”或“辯論”之“論”。其實,論說之體,并不始于《論語》,而且《論語》中大半是記言記事,不純粹是議論。劉氏因為“尊圣宗經”,把《論語》作為論說文的始祖,這種說法顯然是很勉強的。 劉勰真的是因為尊崇孔子在經學上的地位而勉強抬出《論語》為論說文裝點門面嗎?筆者以為劉勰的用意并非如此簡單。《論語》雖是一部語錄體著作,但字里行間無不滲透著深刻的哲理,表面上看它不是論的形式,但實際上卻具有論的本質屬性。蔣先生將“論”與“倫”的意思完全用現代語義來理解,這就忽略了古漢語中“論”與“倫”不只是文字假借層面的字形之通,而且具有語源學層面的字義相通處。先來看看“論語”這個詞。一般地,人們對這個題名的理解都依據《漢書·藝文志》的這段話: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其中“論”與“倫”(指有秩序、有條理)相通,“論纂”就是有條理地編纂的意思。劉勰說“述經敘理日論”,而“論纂”成文的體例完全符合“述經”的精神,所以說《論語》作為論體的定位也完全符合劉勰的認識。在漢魏時期的學術史上,《論語》往往被稱作“經傳”且地位突出,劉勰在下文說到論體的多個條流時也指出“釋經,則與傳注參體”,那么,《論語》通過論纂體例直接反映出來的“傳經”性質一點也不違背劉勰對論體的看法。當然,因它與孔子相關,劉勰沒有理由不重視,但并不能因此懷疑它的本來性質。在先秦諸子爭論的年代,儒家是最早最有系統的一家,而儒家的創立與《論語》的成書是相輔相成的,那么將《論語》當作論體之始也就順理成章。 上面從成書體例角度講了《論語》的“論”體特征,而如果繼續探討“論”與“倫”的深層語義相通處,更能發覺劉勰以《論語》為論體之首的良苦用意。“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圣意不墜”,“倫”是秩序、條理,而秩序與條理的獲得要通過“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即“論”來實現,這就是說人類語言的條理是一切秩序的依據,“論”的最終目的即是“倫”,所以二者在語源上屬于同一體系,隱含了深刻的同一性。以近義詞轉注是劉勰一貫樂于采用的傳統訓詁方法,他將“論”與“倫理”的“倫”相聯系,一下子把握住了這一文體的本質意義。既然論體文就是為了探討倫理,而倫理之道本與天地之道相通,那么論體文不就自然而然指向“道”了嗎?通過對“論”的這一番“釋名以章義”,再結合前面所說經與論的關系,劉勰“原道”、“宗經”的文章理念得到了圓滿的言說。 二 原道、宗經是論體文的本質屬性,這是論體文與其他文體的共同點,而論體文的特有屬性即劉勰所說的體“要”則是“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簡言之為“述經敘理”。從劉勰“選文以定篇”的情況看,論體文主要存在兩大分流系統:一是注經(或稱“傳經”)系統,一是敘理(今人稱“說理”)系統。劉勰對述經的重要方式——注經——敘說不多,僅舉了毛公訓詩、安國傳書、鄭玄釋禮、王弼解易四個例子作為典型范式,強調這一體的體貌特征為“要約明暢”,但他在《序志》中說:“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可知劉勰對這種體式是十分重視的。 “注經”就是注釋疏解經書,劉勰說:“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認為注經的方式雖然散亂,但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論述,當然屬于論體。清代學者紀昀對此則有異議,說“訓詁依文敷義,究與論不同科,此段可刪。”這樣說是不恰當的。古人注經并非只在做一些文字訓詁的表面功夫,而是帶著強烈的思想觀念來對待經典,否則就不會出現秦延君十萬字注《堯典》、朱普三十萬言解《尚書》的現象了。注經雖不能妄自“六經注我”,但通常都有鮮明的論辯傾向與學術統派意識。可以說,古代經學史實際上就是各個不同注經派系爭相辯駁、師法傳承的歷史,更何況,以經學史為核心的古代學術史更喜歡微言大義的注解體式,對于邏輯嚴密的長篇大論反而多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