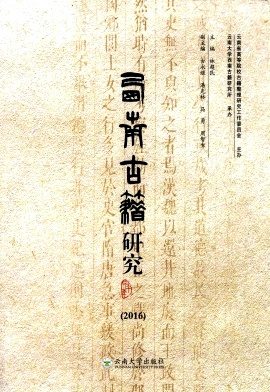從孫悟空的形象塑造看《西游記》對悲劇和喜劇的超越
趙紅娟
《西游記》作者吳承恩繼承了魏晉志怪小說擅長寫鬼怪和唐傳奇小說的傳奇筆法的民族傳統,并將兩者融為一體,形成了藝術形象神、獸、人三結合的藝術特征。這一藝術特征在孫悟空身上得到了最完美、最出色的表現。神的本領、人的思想感情、獸的外形和動作特征在孫悟空形象塑造上結合得如此完美,以致這一形象與傳統的悲劇形象或喜劇形象相比有著獨創性的意義。在神、獸、人三位一體的結構中,神是中介,它與人、獸構成兩極。具體地說,由神的本領和人的思想感情構成了悟空作為悲劇英雄的一極;由神的本領和獸的外形及其滑稽動作構成了悟空作為喜劇英雄的一極。前者是內在的、本質的;后者是外在的、形式的。但我們一般往往僅注意到后者,對前者則大都忽略,其實《西游記》是超越了悲劇和喜劇模式來塑造孫悟空形象的。
一、“神人”結合建構了悲劇性的孫悟空 《西游記》中孫悟空作為悲劇英雄的形象是通過“神──人”結構來建構的。哭是從神到人的紐帶,是神式英雄人性的最生動體現。持有一萬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又有著七十二般變化的孫悟空自然是一個英雄,一個神式的英雄。然而就是這么一個神式的英雄,在一本100回的《西游記》中,卻哭了25次,比書中其他任何人物都哭得厲害。 取經之前,孫悟空有兩次哭:第一次是第一回中與群猴喜宴之間,因慮及無常而墮淚;第二次是第二回中,師父菩提因他炫耀本領于眾人,逐他歸鄉,他滿眼墮淚。對這兩次哭,我們不必深究,畢竟這時的悟空還涉世未深。但有一點不能否認,孫悟空一開始就會哭,《西游記》作者一開始就寫了他人性的一面。西天取經路上,悟空一路行來,其哭更是接連不斷;在海浪翻滾、潮聲濤濤、一望無際的大海之上,一朵云花托著的是身形瘦小、凄凄慘慘腮邊淚墜的齊天大圣;“噙淚叩頭辭長老,含悲留意囑沙僧”的是當年暢快淋漓鬧天宮的齊天大圣;“回顧仙山兩淚垂,對山凄慘更傷悲”的是齊天大圣;平頂山遭逢魔障,屈身于須彌山根之下,嘆“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為名高名喪人”,珠淚如雨的是齊天大圣;壓龍洞二門外,仵著臉,脫脫哭將起來的是齊天大圣;想起取經苦惱,只為受辱于人,淚出痛腸,放聲大哭的是齊天大圣;被火云洞圣嬰大王劈臉一口煙燎得眼花雀亂,忍不住淚落如雨,投身于澗水,險幾喪身,復又活轉,止不住淚滴腮邊的是當年攪亂蟠桃盛會的齊天大圣;敗于獨角兕大王,赤手空拳來坐于金山后,撲棱棱兩眼滴淚的是“官封齊天意未寧”的大圣;在小雷音,與妖魔一戰,跳在九霄,舍了性命,按下祥光,落于東山頂,咬牙恨怪物,滴淚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聲的是齊天大圣;孤單一人立于西山坡上,悵望悲啼的是齊天大圣;被黃花觀道士所追趕,力軟筋麻,渾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淚,失聲叫苦的是齊天大圣;“愧上天宮,羞臨海藏!怕問菩薩之原由,愁見如來之玉像”,對功曹滴淚是齊天大圣;遇著燒紙錢婦人點頭嗟嘆“正是流淚眼逢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的是齊天大圣;獅駝嶺獅駝洞困于魔瓶,擔心弄作個殘疾之人,忍不住吊淚的是齊天大圣;靈山山上,跪地捶胸的是當年大鬧天宮的齊天大圣;陷空山上,不見唐僧只見半截兒韁繩,止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大哭的是齊天大圣;隱霧山妖魔一個分瓣梅花計劈心里撈了唐僧,大叫“天天天”,止不住腮邊淚滴的是齊天大圣。 一個曾暢快淋漓鬧龍宮、鬧冥府、鬧天宮、攪亂蟠桃盛會,十萬天兵無敵手的英雄,卻幾次三番,屢陷困境,以至黯然淚下,甚至放聲痛哭,豈不撼人心魄,讓人感其凄涼茫然?然而諸如此類的哭,由于大家一開始便把孫悟空作為一個喜劇英雄來接受,所以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作為一個英雄,非到真心痛處,決不會哭。歷來的英雄,有愁只是借酒消愁,其出真言是在酒后。悟空的哭是英雄人物史上的一個例外。因為悟空作為一個僧人,不可能老是醉酒消愁,而這哭正是代了醉酒,深深道出了其憂愁悲憤的心境。 細讀書中哭的情節,我們不難發現,哭的實質是好“名”。在孫悟空一生的戰斗過程中,他宣揚追求的只是“名”:使一切妖邪聞大圣之名而驚魂喪魄;要保持對諸天神祗的威懾,使普天神將看見他,一個個彎背躬身。要“名”,可以說是孫悟空形象的心理脈搏。 孫悟空雖名封齊天,而在他人安排的取經路上卻三番五次遭受到自己無法解決的魔障。西天取經的目的是為了求得正果,要求得正果的強烈意識和獲取正果中遭受的挫折形成了矛盾沖突,這種沖突為悟空這個具有人性的神性英雄的哭提供了可能性。哭時憶起所歷艱辛,感受現時凄涼,語層深處念念不忘的是:他被壓前轟轟烈烈的鬧天宮和所封的“齊天大圣”之名。本以為出了五行山能再顯一番身手,卻只是贖罪似的虛假釋放。現實與愿望的強烈反差導致了悟空的哭。在取經過程中,悟空幾次深思,十分明了導致自己不幸的原因。 《西游記》三十三回,悟空的哭言:“這正是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為名高名喪人。”《西游記》四十一回,悟空哭言:“一心指望成正果,今日安知痛受傷!”《西游記》七十五回,悟空哭言:“想是我昔日名高,故有今朝之難。”這些都是哭時真言。如果當初他不嫌弼馬溫官職小,不去計較有無赴蟠桃會資格,他怎會落入如來手掌?以至金箍加頂,派往西天取經,歷盡艱辛,幾喪性命,悲到深處,又怎能不放聲大哭?《西游記》九十九回,師徒四人遭了第八十一難后,孫悟空的一番言語,更是流露了這種心態,帶有很大的總結性:“行者氣呼呼地道:‘師父,你不知就里,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耳。……’三藏、八戒、沙僧方才醒悟,各謝不盡。”為有“名”高,必遭此大難: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水濕真經。之所以悟空先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一路行來,悟空苦思的正是這個問題。 好“名”是人的社會性的集中體現。孫悟空的好“名”為何帶有一種悲劇色彩呢?這是因為悟空的好“名”超過了他的能力。雅斯貝爾斯說:“每當意識超越了能力,悲劇便會發生,特別是對主要欲念的意識超過了滿足它的能力的時候,……悲劇可以說是產生在意識超越了能力的空虛地帶。在那里,人們可以體驗到自己已是毫無能力取得成功,并經受著由此而來的痛苦。”孫悟空一心求“名”,“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但他對“名”的強烈意識卻超過了他要名的能力。為什么這樣說呢? 首先這是孫悟空要的“名”決定的。他所宣揚、追求的“名”是威懾諸天神衹,使一切妖邪驚魂喪膽的天真無邪的救世英雄的共名。孫悟空雖然漂洋過海學了一身本領,然而他身為一個下界仙石所生的無名之輩,在天上有玉帝諸神的統治、地下有閻王老子握命的環境里,是找不到施展才能的天地的。于是他在求名的道路上便連遭冷遇,受盡挫折。弼馬溫之辱,齊天大圣之有名無實,所有的這一切都讓他羞惱萬分。自以為身懷絕技而心高志遠,一心想建大功,于是有了一場轟轟烈烈、暢快淋漓的鬧天宮,最后的結果是被如來壓在五行山腳下。這一壓就是五百年,這五百年可是饑餐鐵丸,渴飲銅汁的五百年。石匣中的大圣;頭上堆苔蘚,耳中生薜蘿,鬢邊少發多青草,頷下無須有綠莎。眉間土,鼻凹泥,十分狼狽,指頭粗,手掌厚,塵垢余多。悟空這么一個愛自由的精靈被折磨成這副非神、非人、非獸的鬼相,不能不說是悲劇,悟空在天庭的悲劇。這中間深深透出了《百年孤獨》似的魔幻凄涼感。在人間亦如此,很少有妖邪買他“齊天大圣”的帳。他們很難把面前的這么個“身軀鄙猥、面容羸瘦、不滿四尺”的孫悟空與傳聞中的齊天大圣掛起鉤來。在一陣激戰后,他們也往往能用自己的寶貝勝過這一齊天大圣。悟空不得不經受著由此而來的莫大痛苦,而哭便成了這前前后后一切悲憤心情的發泄方式。
二、“神獸”結合建構了喜劇性的孫悟空 評論家對《西游記》文本中喜劇性、幽默性的分析已十分深刻,孫悟空是一個喜劇英雄也已成為定論。撇開文本的角度,筆者主要從審美心理學、接受美學角度來探討孫悟空形象的喜劇性也就是通過對“神獸”這一藝術結構的分析,回答“孫悟空既是一個悲劇人物,讀者何以把他僅作為一個喜劇英雄來接受”這個問題。 從讀者接受這一角度看,悟空之所以被認為是喜劇英雄,似有以下三種原因: 第一,從一般接受心理看,凡審美對象為形貌丑陋者,即使他們的行為動作是悲劇的,而其效果則可能是喜劇的。從《西游記》的文本效果看,悟空形象的藝術接受也未能逃脫上述接受心理。即是說,由“神獸”結構而產生的丑陋形象和滑稽動作沖淡、掩蓋了人們對孫悟空悲劇形象的認識。一個面目丑陋猙獰的人,無論正義感多強,其悲劇效果總比外形英俊瀟灑、兒女情長的人物遜色,我們的同情往往在后者。 在我國古典悲劇中,有時主要的悲劇人物也可賦予喜劇性格。悲劇《嬌紅記》中以生扮的申純,當他和王嬌的愛情在封建倫理的重壓下,尚處在撲朔迷離,摸不透對方底細的時候,突然聽到王嬌約他晚上幽會,他欣喜若狂。在王嬌走后,他一個人留在臺上如癡如呆地自言自語,連說帶唱,恨不得太陽早點下山:“天,我央及你,我與你唱喏。怎生不動?我與你下跪,又不動。我與你下拜也不動。呸!潑毛團鰾膠粘住你哩。紅紅潑潑更瞳瞳,夕陽西沉早在東,其今朝偏戀著生根結蒂在當中?說什么‘人有善愿,天必從之’?我如今唱喏,你也不動,拜你,你也不動;敢待罵哩!”通過這些插科打諢的喜劇表現,把申純書呆子氣的至誠種,活靈活現地表現了出來,真實呈現了他此時復雜的心情。然而未來的結局卻證明:“天”并未恩賜他人生應得的起碼善愿,強大的封建勢力不僅吞噬了他們的愛情,而且奪走了他們的生命,這還有什么天良?!這是一種以喜寫悲,更見其悲的手法,有很深的悲劇效果。 然而在《西游記》里同樣是以喜寫悲,為什么沒有如此的藝術效果呢?《西游記》第三十四回,孫悟空騙巴山虎、倚海龍說出壓龍洞老母住處后,取出鐵棒,走上前,著腳后一刮,然后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卻拖著腳,藏在路旁深草科里。隨即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成了巴山虎,自身卻變個倚海龍,假裝做兩個小妖,徑往壓龍洞請老奶奶。這一系列動作和外形的神獸式變化,有著強烈的喜劇色彩。但從圣變為小妖,緊接著的便是要向老怪嗑頭。這對“為人做了一場好漢,止拜了三人”的悟空來說,簡直是莫大的污辱。他結果被迫承受了這污辱,便是悲劇。難怪當他意識到要拜倒在老怪腳下時,站在門外,仵著臉脫脫地哭將了起來。這哭應說是有著撼人心魄力量的,很有悲劇色彩,然而歷來的讀者和評論家們對此并未引起足夠重視。 我們把申純和孫悟空的動作和外形作個比較,不難發現造成這種接受差異的原因。申純是以生扮演的才子,他年輕、漂亮又多情;他的動作是極富人情味的人的動作,因而他的心靈非常容易與接受者的心靈發生共鳴。而孫悟空則是一個面目丑陋,動作滑稽的老猿,不容易與我們人的心靈溝通,他的悲劇也就不易引起我們心靈的震撼。如果孫悟空以一個人的面目出現,且賦予他英俊瀟灑的外表,只是偶爾現形為猴子。那他一定是一個十分動人的人物。問題在于,這樣的人物,不能象猴那樣完美自如地融入《西游記》中。以猴的面目出現,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第二,悟空由“神──獸”結構而產生的丑陋外形和滑稽動作本身,給讀者的印象是丑的,其效果只能令人發笑,而不會發現其他。鬧劇是喜劇最簡單的形式。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當滑稽只限于外在行為和表面丑態之時,這就叫做鬧劇。”在最初,鬧劇常常表現為對某些動物的夸張、歪曲的摹仿,人類把某些動物作為被征服對象加以調笑,以扭曲、夸張、笨拙的化妝、形態和動作來貶抑動物,肯定人的力量,顯示出人與獸對比中人的優越性。 《西游記》中孫悟空的丑陋外形和滑稽動作給讀者的印象是鬧劇式的。文中描寫孫悟空咨牙俫嘴、兩股通紅,腰系一條虎皮裙,活脫脫是個雷公。猴子式的厲聲高叫,跳來竄去,眼珠的流轉,都給讀者以丑的印象,引發讀者的只是一陣陣笑聲。從孫悟空鉆腹這一事件來看:由于猴子外形的輕巧,作者不免賦予他善變各類小蟲的特征,使他能非常容易地鉆入妖魔腹中,大鬧一番“肚宮”,疼得妖魔哇哇亂叫,滿地打滾。由悟空這一外形變化和技術本領所產生的這類丑式畫面,可謂非常逗人發笑。把孫悟空作為猴子看,當然只能令人發笑別無其他。但若把他作為一個人來看,他憑本事無法制服妖魔,使不得不使用這小人之計。是多么可悲。因為孫悟空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好漢,是不能受辱于人的。這樣做豈不壞了他一生所追求的“名”?更何況就是憑這,他還不一定能救出師父前往西天取經。 第三個原因在于讀者的心理定勢。大部分讀者在沒接觸作品《西游記》前,就或多或少接受了戲劇舞臺、電視屏幕、連環畫上孫悟空的形象。而由于受傳統評論模式的影響,廠來的編者、導演、繪畫者都是把孫悟空作為一個喜劇形象來設計制作的。他們把孫悟空獸的動作和外形加以強烈的歪曲、夸張和摹仿,不時逗發觀眾陣陣輕松愉快的笑聲。正是受了戲劇、電視劇和連環畫的熏陶,人們對孫悟空這一形象所抱有的喜劇心理可謂根深蒂固。抱有這種心理來讀《西游記》作品本身,當然是不能正確理解作者對孫悟空的獨特塑造。 《西游記》對孫悟空形象作出如此塑造,其實正表現出它塑造人物形象之高妙。其高妙之處就在于,它超越了悲劇和喜劇的創作模式。《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是一個超越了悲劇和喜劇的藝術形象。可惜的是,長期以來,讀者未能悟解《西游記》這種創作特色,結果把孫悟空僅作喜劇英雄來接受。在我看來,要對孫悟空作出全面而系統的認識,必須遵循《西游記》超越悲劇和喜劇的創作思路和創作特點。只有這樣,才不辜負《西游記》作者苦心孤意慘淡經營出來的孫悟空這個神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