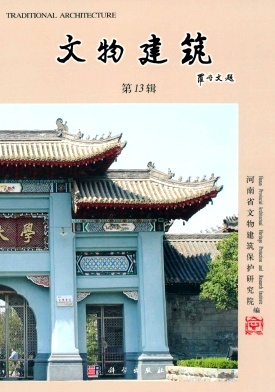悲歌一曲水國吟——《紅樓夢》水意象探幽
俞曉紅
一
水,是《紅樓夢》中蘊涵豐富、在在而有的意象。大觀園里,由曲徑通幽處穿過石洞,便見“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下;往北數步.可俯視“清溪瀉雪”;它流向瀟湘館,盤旋竹下而出,行經花溆,“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迂”,度沁芳閘而后穿墻出園。這一脈清澄潔靜的園中小溪,名之曰“沁芳泉”。在這汩汩流動的泉水之外,“水”意象還往往借助一些特殊的形態來呈現:它有時是梨花上的輕“露”,有時是石徑上的薄“霜”;有時化為寒“雨”,淋漓在竹梢、芭蕉葉上和林黛玉寂寞的秋窗外;或凝成冷“雪”,飄舞在半空、梅花枝頭以及眾女兒歡樂的詩篇中;有時,它又聚作“淚”水,無休止地從林黛玉的眼中心底流出,無風仍脈脈,不雨亦瀟瀟,成為大觀園中一道特殊的人文景觀,而有別于泉、雨、霜之類的自然意象。
與大觀園現實性“水”意象相對應,作者還設置了神話層面上的“水”景觀:西方“靈河”岸邊的三生石畔,絳珠仙草因有神瑛侍者每日的“甘露”灌溉,得以久延歲月,修成女體,遂以蜜青果為食,“灌愁海水”為飲;太虛幻境里,有綠樹“清溪”,情天“情海”,警幻仙姑用以款待濁玉的,是名為“千紅一窟”的仙“茗”和“萬艷同杯”的美“酒”。其茗乃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烹成,其酒則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麟“髓”鳳“乳”釀就。如曰清溪、寒雨、冷雪、薄霜、輕露乃是實體性“水”意象的話,那么靈河、愁海、情海則是虛擬性“水”意象。作者既賦予“水”以韻味獨存的幽深寄寓,又賦予它以風姿各異的外在形態,通篇文字自然是“水”象聯翩,“水”意盎然。
二
“水”在《紅樓夢》中,不僅僅是溪流河海、霜雪雨露這樣一些自然意象,也不僅僅是盈盈珠淚這一人文意象。在曹雪芹筆下,“水”還是“女兒”的象征。這位性靈殊異于眾、詩人氣質濃郁的小說家遷想妙得,讓他的男性主人公賈寶玉向蕓蕓讀者訴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將“女兒”比作“水”,自然也可以說,“水”是“女兒”的象征,“女兒是水”與“水是女兒”便構成微妙的等式。故而,“水”在“女兒是水作的骨肉”這句名言里,就成了一個比喻性的新意象。
女兒是“水”,因為女兒擁有如水般“自然的風流態度”。芍藥裀中,史湘云酣眠初醒,慢啟“秋波”;壽怡紅時,芳官打扮異常,愈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青;高談闊論時的尤三姐也是一雙“秋水”眼。古詩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是以眼波之晶亮多情比喻水波之清澄流溢,水是實象而眼波為喻象;眼如秋水,則眼波為實象而秋水是喻象。風神靈秀的林黛玉,眉是“罥煙眉”,淡如青煙,彎似曲流;目是“含情目”,晶亮似水,柔媚如波;“淚光點點”,仿佛是那溪邊水痕斑斑,又好像是花上晨露滴滴;“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的描述性意象,則不僅蘊含著林黛玉有如芙蓉般傍水而生、承露而活的生命況味,也傳達了她如水波般柔曲輕盈、搖曳生姿的體態風韻。曹雪芹以水喻女兒之眼之淚之體態,是在傳統喻象的基礎上拓展了其聯想內涵。女兒肌膚的柔軟、線條的婉曲、氣質的清純、目光的晶亮,和“水”有太多的相似之處,說“女兒是水”,實在是樸素不過真切不過的比擬了。(今人詠唱“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與“女兒是水”的名言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為大觀園諸少女的一個審美參照,太虛境中的警幻仙子更是美到極致:她的腰肢纖細柔美,行止輕盈飄忽,仿佛回風舞“雪”;她的姿容清純美好,氣質高貴嫻雅,可當“冰”清玉潤;她素若春梅綻“雪”,潔若秋菊被“霜”,靜若松生空谷,艷若霞映“澄塘”,文若龍游“曲沼”,神若月射“寒江”。警幻仙子之美,是水的清澄晶瑩、光燦流動之美,冰霜雨雪意象的高潔冷凝充盈其身,女兒美的集合體警幻仙子豈不恰是“水作的骨肉”?!
仿佛是警幻仙子美的印證,人間女兒的詠白海棠詩,也紛紛用到了“水”的變體意象。探春之“雪為肌骨易銷魂”,寶釵之“冰雪招來露砌魂”,黛玉之“碾冰為土玉為盆”,湘云之“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魂”,詩句中“冰”、“雪”、“露”、“雨”俱以詠白海棠花的潔白柔美。然而詠花亦詠人,眾女兒借物喻情,無一不是“清潔自勵”(脂評)。花如冰如雪,而人又如花,則人、花、水三位一體,構成一新的復合意象。水之清潔靈動與花之潔白芬芳,便無聲地轉化為人的內在氣質和精神內涵。在詩中,冰、雪、霜、露是水,而且是含香沁芳的水;在詩外,眾女兒清潔的品格如水,芬芳的性靈如水,超凡脫俗的精神風貌如水,豐逸靈動的才思文筆如水(“才思泉涌”、“才情橫溢”原本就透射著“水”意象),擁有諸端美好意象底蘊的大觀園女兒,又焉能不是“水作的骨肉”?!
在借助比喻性的水意象“冰雪霜露”來表達“女兒是水”的意涵之外,曹雪芹還精心營構了一個實體性的水意象。大觀園中那道清流妙名“沁芳”,聯又云“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可謂道盡了水流的美質:岸邊花繁柳郁,水面落紅片片,水因柳色而染綠,又因花香而沁芳;它有三篙之深而仍清純澄碧,是一脈之形而更顯其蜿蜒曲折。泉水意象因此而彌漫一派清靈芬芳、柔婉明媚的氛圍,構成那“真無一些塵土”的無比潔凈之境。太虛幻境也因有“綠樹清溪”而成“飛塵不到”的仙家凈土,以與凡界遙相呼應。在賈寶玉心目中,“女兒”無一不鐘神毓秀,得日月山川之精華,是“清凈潔白”、令人一見便清爽的“人上之人”。從“女兒”的整體意義上看,這群清凈潔白的女兒,居于少塵絕埃的大觀園里,恰似潔凈清澈的沁芳泉水。流紅沁芳的脈流,是全體“女兒”的化身。落紅陣陣、水流潺潺之際,它已由實體性意象升華為象征性意象。
或以林黛玉曾阻止寶玉拋花于水,詩又有“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之句,而認為園中泉水并不潔凈。這其實是一種誤讀。黛玉明明說:“你看這里的水干凈,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塌了。”水在大觀園中總是干凈而芬芳的,它出了園子便會污濁,這恰好隱寓大觀園眾女兒的清凈潔白。賈寶玉天性喜聚不喜散,渴望與所有姐妹終身廝守,一有分離便深感痛苦。這里面實隱含著“女兒三變”的思想:女兒未嫁是顆無價寶珠,出嫁便光色頓失,成了死珠,往后便成了魚眼珠了。因為女子一嫁了人便沾染了男人氣息,而不復純潔芬芳。迎春將嫁,并要陪四個丫頭過去,寶玉得知,跌足自嘆道:“從今后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在園中是“清凈潔白”的女兒,出了園子便不再是“清潔人”,這正和沁芳泉在園內是凈泉、出園便成污淖的景況一樣;寶玉對女兒們的感覺,是審美的而不是現實的,是性靈化的而不是世俗化的。對所有“女兒”(包括他的姐妹在內)的“水”性,他從整體上一概予以尊重、傾慕、細心呵護,就像當年神瑛侍者悉心灌溉絳珠仙草一樣,賈寶玉虔誠地呵護著一群晶瑩澄澈、芬芳靈秀的“水”女兒,并從心底期望她們永遠如此。
沁芳泉是女兒泉,自然意象與人文意象相映互輝、整合為一之后,“女兒是水”的命題便衍申出更多的蘊涵。——不僅女兒的姿容體態、性情品格之美幻化為水意象,而且女兒的青春與生命、柔情與愁緒,都融入了那一灣鮮活潔凈、深柔婉轉的泉水之中。第23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在描述了落花浮水、飄飄蕩蕩的景象后,集中筆墨來指明水之象征意蘊。《牡丹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唱詞隔墻傳來,原不經意的林黛玉竟然聽得“心動神搖”、“如癡如醉”,站立不住,坐在石上細嚼其中滋味,及聯想到古人詩詞中“水流花謝兩無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等,加上剛剛讀過的《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湊聚在一起,“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癡,眼中落淚”。崔鶯鶯、杜麗娘青春與個性意識的覺醒,濃聚在“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和“花落水流紅”這警醒芳心的妙詞艷曲里,啟迪了林黛玉對生命的憬悟、對自身命運的沉思,故而心痛神癡、潸然淚下。作者對落花滿泉的描寫與構思,顯然是從《西廂》、《牡丹》的花水意象中申衍而來。“花落水流紅”固是前人事,也是眼前景、心中情。飄花沁芳的水流意象,其韻味醇美如是、濃厚如是,一如柔情似水的少女本身。
三
傳統詩文中的水意象,往往含有情絲萬縷、愁思不絕的象征意蘊。“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無端一夜空階雨,滴破思鄉萬里心”,人們以“水”來寄托其相思愁苦之情,多取流水之波動深柔、迢迢不斷和雨水之連綿淋漓、凄寒抑郁。柳永的《雨霖鈴》詞,流水與雨水俱在,酸淚與苦酒共存,仿佛是一篇水淚吟。“淚”訴離情,“酒”澆離愁,多情深恨波涌于心,恰如千里煙“波”;驟“雨”則既是實景意象,亦是象征意象,“蘭舟”與“楊柳岸”則是“水”的潛意象。愛如水,愁如水,風情如水,抒情主人公宛在“水”中央。
大觀園女兒的最優秀者林黛玉,便也是這么一枝宛在水中央、淚水淋漓的水芙蓉。在她的精神生活中,淚水仿佛是她情感宣泄的最主要的方式。初入賈府時“淚光點點”,當夜便因寶玉摔玉而流淚不止,平日又總愛在瀟湘館內臨風灑淚,對月傷懷,自然界的風風雨雨、落花飛絮,他人的歡聲笑語、眼色行止,無一不是引動她“淚自不干”的誘因。愁緒滿懷無釋處時,她哭出了一篇凄絕艷絕的《葬花辭》;題帕三絕句,無異于三首詠淚詩.“秋閨怨女拭啼痕”——因何而啼?又有何怨?在痛感自己身世飄零、青春易逝之外,自然含有對愛情的痛苦期待及前景茫然的悲戚。林黛玉生魂名曰“絳珠”,此二字乃是她一生“血淚”凝就。眼中流出的淚是水,心底流出的淚是血,血總是濃于水的。“絳珠”是對林黛玉將生命與靈魂全交付與愛情的精當概括。“絳珠之淚至死不干,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怨與不怨是一對矛盾,怨因情愛無著、前途無望;不怨因求仁得仁、愛得其所。作為少女詩人的林黛玉,詩是她將滿懷愁緒怨情訴諸自我、自憐于幽閨的形式;而當這位詩家以淚美人、水芙蓉的姿質風韻楚楚動人地搖曳于大觀園清新靈秀的世界里時,淚便成為她柔情深愛的視覺化傾訴了。在轉瞬即逝的人生之旅上,她一邊行吟一邊灑淚,歌聲伴著淚痕,血淚又化作歌吟,而長歌原可當哭呵!在那個沒有性靈、無視情愛的漠漠塵世里,瀟湘妃子的淚流與大觀園中那一脈泉流愈加顯得清亮晶瑩,纏綿悲慨.作者在情節展開之先設計的三生石畔的澆灌神話,是為這淋漓淚水所作的先驗性解釋。神瑛侍者用以澆灌絳珠草的,是象征清純愛意的甘露,絳珠草心承神受的同時,郁結了一股纏綿不盡之意,思欲下凡“還淚”。那條靈河無疑是靈界淚河,它清亮無塵,“纏綿不盡”,成為絳珠仙子凡界還淚的源泉。大觀園中的脈脈泉流有如靈河在凡界的投影,無聲地映現著瀟湘妃子的點點淚痕。甘露與河水創造了凡界的生命,又源源不斷地給予這生命終生所需的情愛淚水;反過來,這生命又每每以性靈的淚泉沖蕩頑石,滌其塵去其泥,使之煥然而為玉。“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一向是為離恨而揮落的,然而,“絳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脂評)珍惜其石,必痛惜石上塵垢,于是淚作清泉“石”上流,“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至死不干,萬苦不怨。林黛玉因而成了淚小姐、水女兒。
也正因此,作者才設計她通體晶瑩透亮的“水”質“水”韻。諸少女中,唯有林黛玉是自揚州逆水而上,舟行來京的;結社取號,也唯獨“瀟湘妃子”之名血痕斑斑、情愛離離,“水”象四溢。而極具象征意味的花名設計更是“水”意淋漓:“除了她,別人不配作芙蓉。”林黛玉傍水而生,依露而活,恰似一枝風露清愁的水中蓮花。西方人對蓮花意象有如下的理解:“實際的蓮花具有兩種特別激發了東方人想象力的特征——它樸素純潔的美和它神秘的水中誕生”。①這兩個特征與林黛玉的美質妙合無痕。“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宛如林黛玉風神氣韻的寫照。在這位清純靈秀的少女身上,人們仿佛看到了那位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灼若芙蓉出淥波”的“水”仙洛妃的影子。
循此以觀,我們也才會明白,為什么“雨”的意象以瀟湘館內為多。雨不僅以自然意象的身份韻和著林黛玉凄寒孤寂的心緒,雨還是上天對超凡拔俗的人間靈魂傾訴情愛、盎現性靈之舉的一種感應。人間泣聲細細、淚雨漣漣,上天便寒風習習、冷雨瀟瀟。雨水像是上天的眼淚,當上天俯視那作踐女性、泯滅真情的世界,發現還有血淚成河的凄艷之情存在時,禁不住潸然淚下。于是瀟湘館內便常常春雨凄凄,秋霖脈脈,窗外天之淚,窗內人之淚,天與人默相應和,“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瀟湘館內為何植有千百竿翠竹?那是為了印證林黛玉的斑斑血淚。瀟湘館后院內又為何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因為梨花帶雨的意象宛似黛玉珠淚盈盈,而雨滴芭蕉的聲音更助黛玉悲情戚戚。第45回寫黛玉“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雨聲”這一聽覺意象與“滴淚”這一視覺意象的組合,透射出黛玉心底哀怨無極、天與同泣的意蘊。
賈寶玉所唱之“紅豆曲”云:“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后,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里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相思血淚凝成紅豆,“紅豆”適與“絳珠”等量齊觀,黃昏雨聲里愁思難絕,流不斷的悠悠綠水原本由新愁舊愁幻化而成。今人贊譽“你是眼淚的化身,你是多愁的別名”,恰極當極。
在林黛玉的“雨”、“淚”意象之外,作者也為釵、探、湘、妙營構了水意象的其他特殊形態。如果說林黛玉的水世界是淚漣漣、雨瀟瀟、泉流潺湲的話,那么薛寶釵水意象的設計,則多為晶瑩冷凝的“冰”、“雪”、“霜”、“露”等。“薛”諧“雪”,判詞與曲辭俱直言“雪里埋”、“晶瑩雪”。那著名的冷香丸調制過程中所用的“四樣水”,是雨水日的“雨水”、白露日的“露水”、霜降日的“霜”和小雪日的“雪”;寶玉詩有“出浴太真冰作影”作喻,寶釵亦有“冰雪招來露砌魂”自比。冰雪霜露的本質是水,其外在特征是晶瑩透亮、冷凝輕寒。它象征薛寶釵也和眾女兒一般,品格高潔晶亮,契合“女兒是水”的命題,此其一。其二,它有異于溶溶漾漾的流水,也不同于拋珠滾玉般的淚水,“淚”與“泉”是動態的水意象,鮮活而纏綿;冰霜雪露多為固態化的水,呈靜態。這自然象征著薛寶釵內心世界無淚寡愛的情感冷藏狀態。因而她偶或有香汗淋漓,卻絕少淚雨淋漓。與此相仿佛,大觀園中那位美麗的青年女尼妙玉,平日所喝的水是舊年“蠲的雨水”和收的梅花上的“雪”。說是“雨水”,必定自空中接來,而且還將這雨水密閉封存使之澄清,一個“蠲”字立顯此水之“潔”;是“雪”而來自梅花,自然愈加潔凈,且亦“沁芳”(此“花上水”意象與園中“水上花”意象恰成對照)。妙玉行止如此與眾迥異,其求“潔”程度遠逾黛玉,其抑情程度也甚于寶釵,故云其“太高”、“過潔”。然而物極必反,雨再潔落地不潔,雪再白入泥即污,豈不正是“風塵骯臟違心愿”?妙玉終陷淖泥中,欲潔而何曾能潔?與妙玉相比,寶釵之雪之霜,于最終孤守空閨之時,寂寞余生之中仍保持其形其質,既潔且冷,“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為此亦當。
“水”的另一種特殊形態是“云雨”。《周易·小畜》云:“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在《高唐賦》中,那位愿薦枕席的巫山神女“旦為朝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都有云雨相伴而行。“云”與“雨”相連,始終有男女歡愛的特定內涵。大觀園女兒中,與此意象翕翕關涉的,是史湘云。“湘江水逝楚云飛”不獨巧妙嵌入了“湘云”之名而已。十二釵正冊之四,畫著“幾縷飛云,一灣逝水”,十二支曲子之六說“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云”與“水”的意蘊是十分顯明的。“湘江水逝”、“一灣逝水”、“水涸湘江”三重意象相同,一謂史湘云之情感性靈如流水般波動深柔,而非是止水之靜穆、雪霜之冷凝;二喻湘云如湘水女神般擁有一段情愛;三則象征湘云青春已逝,情愛失所。“楚云飛”、“飛云”、“云散高唐”的意象喻指更為明確:夫妻歡愛不永,幸福轉眼消逝。有“云”而無“雨”,并不影響其寓意。瀟湘館中的“雨”意跡近“淚雨”之“雨”,空有情愛期待而實踐無望。此處之“云”象卻是“云雨”之“云”。《高唐賦》中“朝云”始出時,“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云無處所。”水云作雨,風止雨霽而云飛水逝,歡愛成空,唯留寒塘鶴影而已。
探春形象所關涉的水意象,則又與眾不同。很有一點英武之氣的三姑娘既無黛玉式的纏綿哀愁,也非寶釵式的冷凝淡漠,而傾向于闊朗爽俊、神采飛揚。她亦有哭,哭得剛烈;她亦有愁,愁與人異。骨肉分離的遠嫁之悲,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悲慨,這在小說中化作“江水”的意象呈現出來。“一帆風雨路三千”之“路”,是“水”路,是煙波浩淼的大江和無邊無際的大海。十二釵正冊上畫著“一片大海,一只大船”,以一弱女子而只身獨行三千里,更兼風雨飄搖,能不“掩面涕泣”嗎?“清明涕送江邊望”,江上一去,正是“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的意境。當是時,“自生自滅”的現實憤慨與家園破敗、“子孫離散”的悲涼預感交織而成的深悲厚哀,恰似那一江春水連綿不絕向東涌流而去。“江水”在此也便成為一象征性意象。
四
在遠古神話里,女媧既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又化育萬物,摶土造人。在這有關我們祖先起源問題的原始意象里,泥水混合而為人,無論男女,泥性與水性共存且渾然一體。《紅樓夢》的作者卻從女媧造人的傳說中得到啟迪,并由此衍申出開拓性的新意象。他將女媧造人的材料“泥”和“水”判然分離,將“水”賦予了女性,而把“泥”留給了男子,并對各自的特質作了規定:泥,不過是人世間的渣滓濁沫,濁臭逼人;水,卻是日月山川精華靈秀之所生,令人清爽。作者將人世間“極清靜極尊貴”的美質給了女性,并對她們作了深情的贊美和歌詠。這真是“女媧煉石已荒唐,更向荒唐演大荒”!然而這一“大荒”之“演”,卻有如那一向視女性為卑為下的男權世界里發聾振聵的一聲吶喊,喚醒了人們對女性價值的重新思考。
“女兒是水”的命題,又與春秋時《管子》中關于人與水關系的闡述有部分暗合之處:“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是以水……凝蹇而為人。”②人由水凝蹇而成,與“女兒是水作的骨肉”本質相通;而曹雪芹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提出“女兒”是水,男子非水的說法。這不僅是將《管子》中的哲學命題文學化了,而且還將“水”的專利權歸于女性;且更將“水”的靈秀清明聚集于“女兒”之最優秀者林黛玉的形象中,這又如同是對《管子》中“水集于玉”思想所作的進一步的文學化表達。由“人,水也”申發為“人上之人——女兒是水”,到突出“水集于玉”,作者對傳統水觀的承襲與拓展之脈絡清晰可見。
《管子》又說:“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③水是萬物的本源,是自然與生命的創造者,這與西方原型批評理論中有關水意象的解釋不無相通之處:“水這個原型性象征,其普遍性來自于它的復合的特征:水既是潔凈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維持者。因此水既象征著純凈又象征著新生命。”④據說圣子基督本人就是通過在約旦河的洗禮,從水中和精神上再生和復活。水是潔凈的,可以使人再生,這雙重意蘊與林黛玉形象的隱寓意義何等相似:她既是“潔凈”女兒之最,又承甘露而生;而后者在盎現水是她生命本原這一意義之外,無疑還含有愛情使她從精神上再生的特殊意味。這恰好表明,水意象的象征性是人類普遍性的經驗和感受,是集體無意識的一種。按照榮格的說法,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種形象,“每一個意象中都凝聚著一些人類心理和人類命運的因素,滲透著我們祖先歷史中大致按照同樣的方式無數次重復產生的歡樂與悲傷的殘留物。”⑤水意象中所凝聚的“潔凈”與“新生”因素,正是這樣的一些“殘留物”,它跨越了時空的拘限,潛伏和蟄動于東西方人共同的“水”觀念中;而曹雪芹匠心獨運的結果,是讓作品中“水”原型的出發點上升到了一個較高的起點。這個起點既是文學的,也是哲學的,當然更是歷史的和傳統的。
倘若細加品賞“水”意象在中國思想文化園林中的潺潺流動,我們可以發現它除了潔凈與再生之外的許多意蘊。老子以水為“上善”,水是“善利萬物而不爭”⑥、曲則全、柔勝剛的典型;荀子以水為民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水能覆舟”;⑦孔子從水流悟出“逝者如斯,不舍晝夜”;⑧有人從水中見到了“性”:“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淬,動之則流而濁。”⑨有人從水中體味到“德”:“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⑩“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的洞庭湖水,喚起的是“欲渡無舟楫”的失意;“奔流到海不復回”的黃河水,“江水流春去欲盡”的春江潮,意味著時光與年華;“迢迢不斷如春水”的,是離愁;“流到瓜州古渡頭”的,是相思;秦少游眼中,柔情是水;李清照心里,閑愁是水……人們對水的認識與表現,漸漸從哲理走向審美,而水之諸端象征意蘊,又匯聚著人們對水的自然意態風韻的感受與領悟,作為一種普遍經驗而得到歷史、社會的認同。《紅樓夢》中的水意象,自然也融入了各種審美化的“水”意、“水”象。
思想家的水觀,是哲理性的,文學家的水觀,是審美性的,而倫理家們的水觀,則又是道德性的。幾千年男權統治的社會里,“女人禍水”是頑固強韌的官方意識,歷代王朝中,幾乎每一個亡國之君的背后,都站立著一位禍水紅顏,國破家亡、朝綱頹毀的歷史責任往往不是由“明君賢臣”來承擔,而多半歸罪于一個個“水性”女子。即便是民眾文化心理,也普遍存在“水性楊花”的觀念。中國政治化的歷史中,只見偽道德的猙獰,而完全不見真性情的脈流。然而,到了《紅樓夢》的作者,卻將這道德傳統作了一個顛覆。作者正式宣告,女兒是水作的骨肉,是清明靈秀、清凈潔白的人上之人,而男人才恰恰是渣滓濁沫!這在以男權統治為中心的世界里,該是怎樣一聲驚世駭俗的吶喊!女兒是水,是潔凈,是生命萬物之源。無論她為泉為河,為云為雨,為冰為雪,為霜為露,她的本質是水,晶瑩透亮,清爽潔凈。在大觀園這個女兒國里,一脈清流應和著上天的汩汩靈河,草上露,梅上雪,竹上雨,面上淚,構成一個聲色并作、風光秀異的水的世界,水的王國。“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一部《紅樓夢》,是一篇“水國吟”,一卷“真真國女兒詩”!靈河是淚河,沁芳泉是女兒泉,靈魂與性情兩條清流上下輝映,虛實相襯,滌蕩著蒙塵數千年的道德傳統,以復活其本真面貌。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不過是曹雪芹借助其主人公之口向歷史所作的宣言。凡一提到這句“寶玉名言”,便以為男主人公好色好淫、邪魔淫鬼者,不特誣寶玉,更誣雪芹矣!
作者曾自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自云“荒唐”,又何必慨嘆無人解“其中味”?可見,將一篇“女兒頌”、“水國吟”說成“荒唐言”,不過是作者在調侃讀者。作者以癡情歷十年之苦辛而成此書,字字是血,行行是淚,何“荒唐”之有!對荒唐歷史的反動,是真切。倘若歷史以偽真實的姿態來看這真實,真實自然也就是荒唐。作者以一把辛酸淚傾訴其癡,則“淚”水漣漣、“血”痕斑斑的,又豈止是淚小姐、水女兒?說“女兒是水”的作者亦當水性豐盈!林黛玉以終生的淚水沖滌“濁玉”之塵垢,去其泥性,成其玉性,則此玉此石亦當水意盎然、晶瑩發亮;那精心琢玉、深情吟水、灑淚瀝血的曹雪芹又焉能不有水之光、玉之輝?“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作者之情之恨遠甚紅袖,若以水作比,也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了!
警幻仙姑有歌曰:“春夢隨云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閑愁。”這又是一個悖論。既告誡眾兒女“何必覓閑愁”,又何必慨嘆“誰解其中味”?又何必淚何必癡、何必荒唐何必辛酸?花落水流云飛,原可緬懷悲悼;而名之以“夢”,仿佛夢醒情冷,一切皆空,可又不能不灑淚泣血于字里行間,任它點點與斑斑。可見云空未必空。為千紅一哭,與萬艷同悲:有此悲天憫人之博大襟懷,才可能在昨夜朱樓夢醒時,酣然飽滿地悲歌今宵水國吟。
注 釋:
①④ P、E、威爾賴特《原型性的象征》,葉舒憲編《神話——原型批評》230、228頁。
②③ 《管子·水地篇》。
⑤ C.G.榮格《論分析心理學與詩的關系》,《神話——原型批評》101頁。
⑥ 《老子·第八章》。
⑦ 《荀子·宥坐》。
⑧ 《論語·子罕》。
⑨ 《全晉文》卷49《傅子》。
⑩ 《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