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人口
西部地區(qū)貧困人口問題的非經(jīng)濟(jì)因素分析與政策分析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全國貧困發(fā)生率降低到了3%以下。然而距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所測算,如果按照低收入現(xiàn)行標(biāo)準(zhǔn),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目前還有8517萬人口屬于貧困人口,若按照聯(lián)合國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fèi)不低于購買力平價美元(約折合2,5元人民幣,即人均年收入約900元)的國際貧困標(biāo)準(zhǔn)測算,中國貧困人口就增加到1億人,超過農(nóng)村總?cè)丝诘?0%。而這些貧困人口絕大多數(shù)生活在西部地區(qū)。世界銀行(2000-2001年度報告)指出:貧困不僅意味著低收入、低消費(fèi),而且意味著缺少受教育的機(jī)會,營養(yǎng)不良,健康狀況差,沒有發(fā)言權(quán)和恐懼等。本文貧困人口主要從經(jīng)濟(jì)層面加以圈定,主要囊括西部地區(qū)貧弱農(nóng)牧民、農(nóng)民工、城市無業(yè)、低保等人群。一、西部地區(qū)貧困人口問題的非經(jīng)濟(jì)因素影響西部地區(qū)貧困人口問題的非經(jīng)濟(jì)因素非常復(fù)雜,其主要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收入差距過大,引發(fā)西部地區(qū)貧困人口心理失衡首先,東西部地區(qū)收入差距較大。西部地區(qū)大部分處于環(huán)境脆弱的石山區(qū)、高原區(qū)、偏遠(yuǎn)荒漠區(qū)或冰川區(qū),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寧夏回族
現(xiàn)階段中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分析
(四)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安全網(wǎng)存在漏洞。市場經(jīng)濟(jì)條件下,市場競爭和優(yōu)勝劣汰是永恒的法則,社會保障是其正常運(yùn)行的安全網(wǎng)和穩(wěn)定器,它關(guān)系到勞動者的切身利益,是調(diào)節(jié)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但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還難以起到穩(wěn)定和調(diào)節(jié)作用。 (五)貧困人口的素質(zhì)低下、勞動能力差。城市貧困人口的文化技術(shù)素質(zhì)偏低、年齡偏大。當(dāng)前,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況比較嚴(yán)重,新生勞動力充裕,文化技能要求相對較高,形成了35歲以上的勞動力再就業(yè)較為困難的局面。 四、城市貧困人口未來發(fā)展趨勢 (一)城市新貧困的人口結(jié)構(gòu)特征將更突出 過去的城市貧困者主要集中于無勞動能力、無收入來源、無法定撫養(yǎng)人的社會救濟(jì)對象,人口學(xué)特征還不太突出。但未來的發(fā)展可能使貧困越來越集中在一些特定性別年齡結(jié)構(gòu)的人群中,導(dǎo)致貧困現(xiàn)象的結(jié)構(gòu)化。其中影響最大的可能有老人群體、部分單親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以及弱勢女性,這將帶來更多的社會矛盾。 (二)時間分布上更具集中性 我國城市貧困問題凸顯于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以來的近20年時間。1978年前,由于鐵飯碗和城鄉(xiāng)割據(jù)的二元體制的雙層保障,城市幾乎是不存在貧困的。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向深層次發(fā)
農(nóng)村貧困人口的醫(yī)療保障問題研究
[摘要]農(nóng)村醫(y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保障農(nóng)民健康,促進(jìn)新農(nóng)村建設(shè),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現(xiàn)行的“新農(nóng)合”制度和亟待完善的農(nóng)村醫(yī)療救助制度不同程度存在不利于解決貧困人口“看病難”問題的缺陷。本文以JP村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為依據(jù),分析了缺陷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完善該制度的政策方面的建議。[關(guān)鍵詞]貧困戶農(nóng)村新型合作醫(yī)療農(nóng)村醫(yī)療救助制度一、 調(diào)查背景介紹湖北省SY市JP村位于湖北省西北山區(qū),群山環(huán)繞,距離市區(qū)近26公里,占地面積7200畝,其中可耕地面積495畝。全村常駐人口1137人,共386戶村民,其中29戶貧困戶。JP村的主要產(chǎn)業(yè)是蔬菜種植業(yè),建成了全市多家大型超市的蔬菜供應(yīng)基地。全村只有1所醫(yī)療衛(wèi)生室,大病患者4人。2008年全村貧困戶的社會救助金額共16000元,其中醫(yī)療救助6000元,生活救助8000元,自然災(zāi)害救助2000元。調(diào)查顯示,全村新合作醫(yī)療參合率達(dá)100%,每年村民個人繳費(fèi)20元,上級政府為參加新農(nóng)合的農(nóng)民人均補(bǔ)助80元,因而人均總籌資額為100元。新農(nóng)合起付線100元,封頂線30000元,新農(nóng)合規(guī)定鄉(xiāng)鎮(zhèn)衛(wèi)生院報銷比例為
城市貧困人口的特征及其經(jīng)濟(jì)生活狀況
摘要:對哈爾濱市和沈陽市城市貧困人口的抽樣調(diào)查表明:我國的城市貧困人口已出現(xiàn)了女性化和青少年化的傾向,尤其是老年單身女性更易陷入貧困;貧困人口的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居多,但與一般市民的受教育程度無顯著差異;下崗、失業(yè)和無業(yè)人員占77%。貧困家庭的戶均就業(yè)人數(shù)不及普通家庭的一半。貧困家庭大都收不抵支,51.1%的城市貧困家庭都有負(fù)債,平均負(fù)債額為14763元,看病、孩子上學(xué)是大額支出和負(fù)債的最主要原因。住房面積與一般市民差距不是太大,但房屋質(zhì)量普遍不太好。分析發(fā)現(xiàn),用恩格爾系數(shù)測量我國城市家庭的貧困程度出現(xiàn)了失效的問題。根據(jù)調(diào)查結(jié)果推算,未來一段時期內(nèi)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數(shù)量還會進(jìn)一步增加。關(guān)鍵詞:城市;貧困人口;分布特征;經(jīng)濟(jì)生活狀況;恩格爾系數(shù)貧困是人類社會出現(xiàn)階級分化以來一直伴生著的社會問題。近些年來,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我國城市貧困問題日益嚴(yán)重。據(jù)《2005年民政事業(yè)統(tǒng)計發(fā)展報告》公布,截至2005年底。全國低保對象已達(dá)2234.2萬人,如果加上應(yīng)保未保人員,實際數(shù)字應(yīng)該更大一些。若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必將影響黨的十六大確立的在21世紀(jì)全面
我國城鄉(xiāng)貧困人口醫(yī)療保障研究
根據(jù)官方公布的數(shù)字,截止2005年9月底,中國城市共有貧困人口2186萬人;[1] 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nóng)村共有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2] 以及近6000萬低收入人口。城鄉(xiāng)貧困人口在構(gòu)成、致貧原因等方面并不相同。在城市,下崗、失業(yè)、困難企業(yè)職工,以及上述人員的家屬構(gòu)成了貧困人口的主體,經(jīng)濟(jì)和社會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是導(dǎo)致這部分人陷入貧困的主要原因;在農(nóng)村,自然條件因素和個性因素同時對貧困起作用。上述城鄉(xiāng)貧困人口的差別與城鄉(xiāng)二元社會結(jié)構(gòu)不無關(guān)系,與這一社會結(jié)構(gòu)同樣關(guān)系密切的還有城市和農(nóng)村各自獨(dú)立的社會制度,醫(yī)療保障制度也不例外。 一、城鄉(xiāng)貧困人口的衛(wèi)生服務(wù)利用和醫(yī)療保障覆蓋 1. 衛(wèi)生服務(wù)利用之比較 2003年全國第三次衛(wèi)生服務(wù)調(diào)查的數(shù)據(jù)顯示[3] 了城市不同收入居民的健康和衛(wèi)生服務(wù)利用情況。按照收入五等分法劃分,從最低收入的1/5家庭到最高收入的1/5家庭(從左到右),兩周患病率呈上升趨勢,但是差別并不明顯(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該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來源是“居民自我報告”,如果考慮到收入不同的被調(diào)查者對患病的主觀判斷因素在內(nèi),結(jié)果可能略有不同);然而,從因病臥床率的數(shù)據(jù)來看,收入最低的1/5家
淺論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
[摘要]對一個問題是不是社會問題的界定,不僅要把它放在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中考察,而且也要借用一個公認(rèn)的準(zhǔn)則來分析它。文章基于當(dāng)前我國社會處于轉(zhuǎn)型期這一背景,并結(jié)合公認(rèn)的分析社會問題的四要素,即問題對個人或社會的損害、對某些權(quán)力集團(tuán)標(biāo)準(zhǔn)的觸犯、持續(xù)性和過多的解決方案,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進(jìn)行了分析。[關(guān)鍵詞]轉(zhuǎn)型期;城市貧困人口;社會問題貧困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是一個貧困人口自身必須面對的個人問題?盡管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認(rèn)為,對于貧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會系統(tǒng)背景中進(jìn)行,而不是僅僅關(guān)注貧困人口這一亞文化群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貧困是一個經(jīng)濟(jì)匱乏的現(xiàn)實,但貧困的持續(xù)以及在其持續(xù)的過程中引發(fā)并連帶的其他相關(guān)問題(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貧困人口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并不足以減少所有與貧困相關(guān)的問題。當(dāng)前,我國社會正處于轉(zhuǎn)型期這一宏觀背景中,對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理解離不開這一背景。何謂“轉(zhuǎn)型期”?在我國社會學(xué)學(xué)者的論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體制轉(zhuǎn)型,即從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向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轉(zhuǎn)變。二是指社會結(jié)構(gòu)變動,持這一觀點的學(xué)者認(rèn)為,社會轉(zhuǎn)
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透析與建議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x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成為全社會發(fā)展的主流。然而,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中貧困人口與日俱增,貧富差距日益擴(kuò)大,因此,城市貧困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極大關(guān)注。本文從城市貧民的生活現(xiàn)狀和特點著手,其致貧原因,得出我國的城市貧困問題是轉(zhuǎn)型時期出現(xiàn)的暫時現(xiàn)象,隨著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絕對的城市貧困最終將消失。[關(guān)鍵詞] 社會轉(zhuǎn)型 貧困 城市貧困社會保障自化成為全球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主流方向后,相伴隨而來的貧困問題成為人類社 會的一大隱患。世界銀行在《1990年世界發(fā)展報告》中對“貧困”是這樣描述的:貧困是指缺乏達(dá)到最低生活水準(zhǔn)的能力,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絕對貧困。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在《人類發(fā)展報告1997》中給貧困下的定義是:貧困是指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huán)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即人文貧困。人文貧困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政府有義務(wù)為人們提供更好條件,以消除貧困;另一方面它更注重貧困的“質(zhì)量”,即貧困可以是國民普遍幸福條件下部分人生活改善相對滯后——相對貧困。[1]2001年亞洲發(fā)展銀行的
城市貧困人口的群體認(rèn)同與社會融合
摘 要:本文側(cè)重從心理與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貧困問題。通過調(diào)查分析認(rèn)為,由于城市貧困人口大多認(rèn)同貧困群體,從而在心理上拉開了與非貧困群體的距離,出現(xiàn)了與社會分離的趨勢,這不利于社會融合。城市貧困人口認(rèn)同貧困群體會形成貧困群體文化,將更不利于他們的社會融合。因此,城市反貧困行動不僅要有助于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而且還要有助于他們的社會融合。關(guān)鍵詞:城市貧困人口;貧困群體;認(rèn)同;社會融合城市貧困人口是一個處于劣勢地位的少數(shù)人群體,它的出現(xiàn)是我國社會變遷的結(jié)果。20世紀(jì)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向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轉(zhuǎn)變,大量的國有、集體企業(yè)職工下崗失業(yè),致使城市貧困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貧困群體處于較低的社會地位上,尤其在當(dāng)今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越來越遠(yuǎn)離主流社會,因此,他們必然面臨著群體認(rèn)同與社會融合的問題。認(rèn)同概念及城市貧困人口的群體認(rèn)同問題認(rèn)同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認(rèn)為,認(rèn)同就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①這一解釋已經(jīng)表明,個人與他人或社會保持一致的過程,
中國城市貧困人口分析
◎數(shù)字透露的城鎮(zhèn)貧困從三個角度看生活狀態(tài):城鎮(zhèn)貧困人群收入低且不穩(wěn)定,用于食品消費(fèi)的支出比例較大,營養(yǎng)水平較低,穿戴和日用品簡陋,住房條件差。困難職工反映最怕的是過"三關(guān)":生病關(guān),子女輟學(xué)關(guān),年節(jié)關(guān);他們最發(fā)愁的是無力承受日益加重的醫(yī)療、教育、住房方面的開支。從收入狀況、財產(chǎn)狀況和消費(fèi)狀況三個角度,大體上可以看出我國城鎮(zhèn)貧困群體基本生活狀態(tài):收入狀況。國家統(tǒng)計局對城鎮(zhèn)17000戶居民家庭的抽樣調(diào)查顯示,2000年,占調(diào)查戶數(shù)5%的貧困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25元,不及城鎮(zhèn)居民6280元平均收入的36.9%,與10%的高收入戶相比(人均收入為13311元),則相差5.7倍。我國由基尼系數(shù)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呈現(xiàn)出一種迅速上升的勢頭,城鎮(zhèn)居民基尼系數(shù)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0年的0.32。財產(chǎn)狀況。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顯示,到1999年6月底,城市居民戶均金融資產(chǎn)已達(dá)52895元,與1984年城市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開始時戶均金融資產(chǎn)1338元相比,增長了38.5倍。但居民金融資產(chǎn)的分布呈不均勻狀態(tài)。20%最低收入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chǎn)的1.5%,戶均為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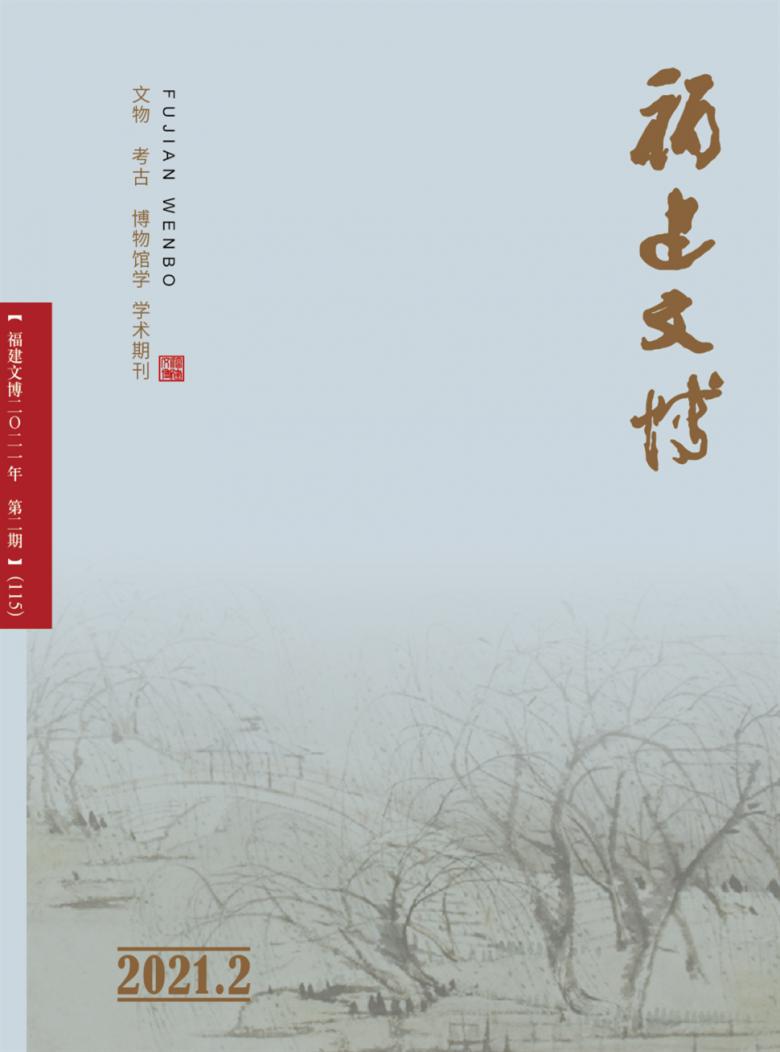
害.jpg)
學(xué)報.jpg)
.jpg)
構(gòu)與行政.jpg)
代鄉(xiāng)鎮(zhèn).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