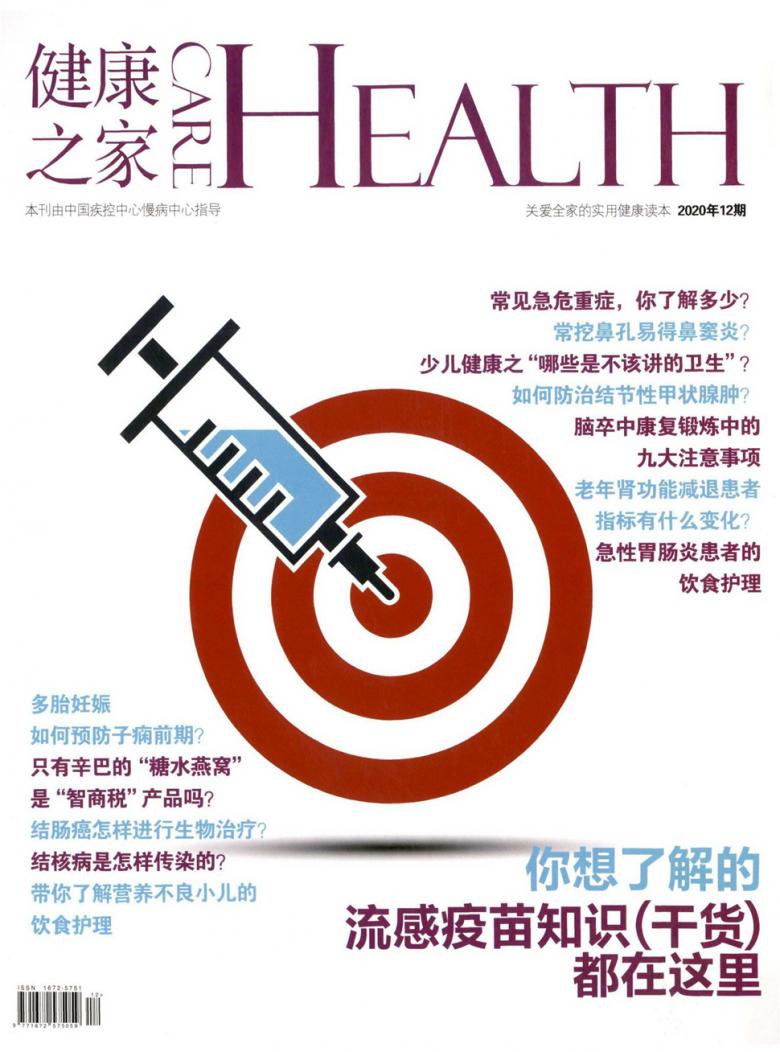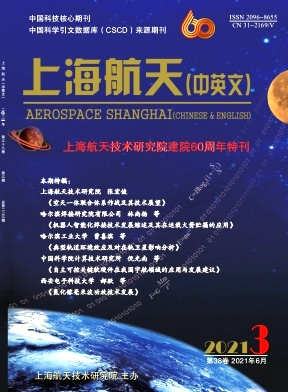制度、模式化與“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
張宇 謝勇旗
摘 要:職業教育的“特色”可以視作用來規范其利益相關者行為的制度總和,它表現為各種利益相關者行為的模式化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的人才規格、教學組織與管理體制。中國在近、現代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并沒有形成職業教育的特色,解放后引進的“蘇聯模式”雖然具有特色,卻不專屬于中國。市場經濟環境下,特色的形成主要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一經形成也就必然可以稱為“中國特色”。
關鍵詞:職業教育;特色;制度;模式化;利益相關者
關于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道路,也就是究竟應當發展什么樣的職業教育以及如何發展的問題,溫家寶總理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5年11月7日)給出了一個官方認可的結論。這篇題為《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的講話指出:“凡是成功的模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與本國實際緊密結合,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在實踐中探索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發展路子。”所謂“中國特色”,當然并不排除國際比較中的經驗借鑒,而這一提法卻已旗幟鮮明地否定了今后照搬別國職業教育模式的發展道路。
為什么不能照搬呢?為什么我們的職業教育不能像引進技術裝備一樣,繼續向發達國家看齊,大搞“拿來主義”?簡單地說:國情使然。按照大家通常的理解,現時中國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特殊國情就是“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落后”,即由于存在著過多需要提高素質的城鄉人口和過于落后的文化技術水平,那些建立在先進生產力基礎之上的職業教育模式會在國內“水土不服”。但是,生產力并不是這里所要談論的“國情”的唯一要素,否則便難以說明當今工業發達的國家之間職業教育的顯著差異。在筆者看來,若想對國情有一個更為全面的把握,至少還應該考慮一些制約職業教育發展的復雜的社會關系,或者可稱之為制度因素。
一、制度視野下的“特色”解析
“制度”一詞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語境下有著不同的特定含義,諸如“社會結構”、“政治體系”、“辦事規程”,等等,單是考察以制度分析見長的制度主義思想流派,其間眾多的經濟學家就曾提出過各種各樣的解釋。我們的論述能夠采用目前影響頗大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定義,那么制度就是與具體選擇集和行為集有關的規范體系,如馬爾科姆·盧瑟福(M.Rutherford)所言:“它詳細規定具體環境中的行為,它要么自我實施,要么由外部權威來實施。”在現實世界中,個人或組織的任何理性行為都不是憑空做出的,總是離不開一定的規范體系,他們或者因為正式規則(成文與不成文的法律以及一般與個別的契約)的約束,或者無需法規的限定,依據從未被人有意識設計過的非正式的約束即會采取某種自覺的行為。
就職業教育的發展而言,各方面的力量都會對此發生影響,不過,這中間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應是職業教育直接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職業學校、學生、企業,以及政府專門的教育管理機構都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包含在內。對于特定的某個國家,面臨著各不相同的具體環境,職業教育的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專業人才的培養與使用部門若是能夠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行為預期,我們即可認為該國的職業教育具備了不會輕易改變的特色。此處引出的“特色”,實則便是用來規范利益相關者行為的制度總和,而表現為各方行為的模式化(或稱為規律性)。這是一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模式化,就像“模式”一詞所揭示的含義,它提供了一種范例,其中包括一國的職業教育需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人才規格),如何保證教育與生產實踐的緊密結合(教學組織),又將由誰來進行管理(管理體制),筆者將這些看作特色最基本的外在反映。
當前職教界人士大都認可德國和日本的職業教育,原因就在于大家所看到的兩國有關方面對職業教育采取高度模式化的行為及其人才規格、教學組織與管理體制的嚴格規范。德國的“雙元制”培訓與日本的企業內教育作為兩個突出的典型,盡管它們的實施細則并非一成不變,規模形勢也時有漲落,各自的職業教育特色卻能夠隨著生產力的進步長期保持下來。
不僅是德國和日本,另其他國家的職業教育同樣稱得上特色鮮明,例如我們熟悉的原蘇聯。雖然它的中等專業學校與技工學校確有專業劃分過細、專業面過窄的問題,但它卻能依靠實習基地和工廠辦學解決教學與生產實踐的結合,又能憑借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保證制度的實施。現在的研究人員盡可以對我國“學蘇”的后果大加褒貶,然而有一點必須指出:近代以來,中國的職教工作者一直在大量地吸收、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職業教育的學制也是“先抄日本的,后抄美國的”,可為何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形成了公認的“蘇聯模式”,此前數十年間卻沒有形成“日本模式”或者“美國模式”?
二、歷史的回顧——中國近、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啟示
一部近現代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向著先進國家不斷學習、模仿的歷史。如果說最初伴隨“洋務運動”興起的實業學堂還多少帶有些應急的性質,那么“癸卯學制”(1903年)的頒布即標志著政府開始有意識地移植資本主義國家的職業教育制度。自此以后,無論是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還是國民黨執政時期,推動職業教育改革的人物往往受到國外職業教育實踐的影響。當時的專家學者也在致力于廣泛的國際比較,據統計,僅從1917年11月至1925年11月,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教育與職業》雜志上刊載的介紹外國職業教育的文章多達116篇,涉及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蘇聯、日本等所有職業教育發達的國家。盡管不乏外域的新潮理論和成功樣板,舊中國的職業教育卻沒有因此而與上述任何一國變得趨同,特別是其它國家種種解決教學“實用”問題的有效方法,如那時的“廠訓制”、“教場制”等,在中國始終無法得到推廣。于是,“辛亥革命后,學界批判實業教育,其核心內容是說實業教育脫離實際。而到20世紀30年代初,學界總結轟轟烈烈的職業教育事業所以很快衰落的內部原因,主要是學非所用,分析失敗的客觀條件,主要是缺乏實習和實訓場所”。
為什么職業教育到了中國總是不夠實用?黃炎培先生歸因于“農校無實驗田,工校無工廠”。有鑒于此,他在上海創辦中華職業學校(1918年)時,便根據科目設立各種實習工場,如鐵3232場、木工場,琺瑯工場等,聘請富有經驗的中外技師擔任教員,一時成績斐然。可是好景不長,這一民國時代職業學校的佼佼者后來仍然嚴重虧損,到1921年就被迫將其下設的工場停辦或者出賃。
以上事實說明,“只從職業學校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有界,職業界努力地溝通與聯絡。我們此刻不妨設想一下:當年的中華職業學校如果不是自辦工場,它能否依靠當地的企業或小型作坊(其時木工和鐵工正是學校所在地的重要職業)解決教育與生產實踐的結合?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依照制度分析提供的思路,在民國初年,想要進行產學合作,將會面臨著既無法律規定,也無先例的不利情形,此時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及行為的結果是難以預期的。而要通過自身的努力消除不確定性,例如校方同那些合適的企業、作坊分別談判,就各自的權利、義務、執行與保障方案達成詳細的契約,則需要耗費大量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也譯作“交易費用”),以至于達成契約的情形只能作為個案,通常學校寧愿自行創辦工場,否則,就沒有實習場所。由于我國缺乏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行業組織的徒工培訓傳統,又不像同期(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日本那樣,以廠辦學校為主的企業內教育占絕對優勢,加之,職業學校大多力量薄弱,一旦獨立設置,普遍地脫離實際的問題立即凸顯出來。
由此可見,制約中國職業教育向外學習、模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是落后的生產技術與動蕩的社會秩序,而且能夠“拿來”別國的現成模式也確實需要一定的條件。
三、“蘇聯模式”的形成與制度移植的條件
就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職業教育幾乎一下子便呈現出了新的面貌:培養技術員的中專和培養工人的技校成為基本的教學機構,前者建起了校內外的生產實習(實踐)基地,后者則力圖作到“既是學校,又是工廠”,實現生產和教育的統一。從制度的角度來看,最根本的變化當然不是新建了這兩類學校,而是蘇聯職業教育的一系列范例被全盤引入進來,人們稱之為“蘇聯模式”并不過分,因為無論人才規格、教學組織,還是管理體制,所有這些原先都是蘇聯獨有的,與中國以往的情況迥然不同。
“蘇聯模式”的職業教育所以能在我國迅速生根,直接的原因莫過于政府的大力推動。中國自近代以來,中央集權不斷遭到破壞,政令不能統一,各地自行其是,縱使出臺了《職業學校法》(1932年)、《修正職業學校規程》(1935年)等法律規定,實踐中也難以得到貫徹。而到了1949年,我國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通過社會資源的公有化,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局面:新建的工廠與學校的產權屬于國家,學生將來也是“國家的人”;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政府事實上成了教育等各項事業唯一的利益相關者,專業人才的培養部門與使用部門的正式交往全都處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協調之下,服從“全能政府”的內部組織。這樣一來,“照搬”的過程就是我們的職業教育管理人員向蘇聯同志學習如何下發相關政策指令的過程,市場經濟慣用的節約交易成本的立法協調手段此時也顯得多余了。
形成“蘇聯模式”是否意味著我國的職業教育一時之間就有了“特色”?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只不過它還不能被稱為“中國特色”。因為,這種“照搬”來的特色并非中國專有,而是蘇聯以及學習蘇聯職業教育經驗的秘會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相對于西方國家的特色,它表現為政府行為的模式化,且只有政府才是職業教育真正的利益相關者。需要說明的是,能夠照搬的只是學制、政令等正式的規則,而非正式的約束,如整個社會(包括政府決策者在內)對技術工藝的價值判斷,對某種身份、職業和教育的認識偏好等則是不可移植的,它們仍然在正式規則沒有“定義”的地方發揮著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正式規則產生效果的前提是與非正式約束相容,否則就會出現“緊張”,中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職業教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與蘇聯相似,也正取決于移植來的正式規則的作用范圍及其與非正式約束可能的偏離程度。
四、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展望
如今,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還有后來的職業高中已經統一命名為“職業技術學校”(2002年),行業、企業也紛紛將原有的教育部門剝離出去,“蘇聯模式”的痕跡逐漸消退,“中國特色”正在為職教界人士越來越多地提及。《中國教育報》上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堅持政府主導、加強統籌管理的職業教育”。這當然還是從政府的視點出發得出的結論。若是考慮到經濟改革帶來的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化趨勢,即職業學校與企業的產權不再完全屬于國家,受教育者也有了更多的入學與就業的選擇,我們的立論就不應僅僅局限于政府的行為,不應僅僅圍繞著幾項工作重點或重點工程進行闡述,而必須更多地著眼于職業教育如何才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
正像許多專家所言,目前中國職業教育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以正規學校教育為主的職業教育,其教學內容、實訓設備水平以及專業教師的技能素質經常滯后于生產實踐的要求,這和民國時期的情況有些許相似之處,究其原因,也仍然是缺乏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制度安排。根據以往幾十年形成的思路,我們固然可以呼吁政府加緊設計一套切實可行的校企合作模式,并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向企業推廣下去,可這畢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依筆者所見,今后政府的功能應當體現在有目的地引導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如果是要促進企業接收學生與教師參加生產實踐,那么采用立法、行政、財政等調節手段的宗旨就是為了方便職業學校與企業的交往;同時,政府可以為相關的制度,特別是正式規則提供有效的實施機制,這便需要加強職業教育管理中的執法監督。
至于“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究竟會以什么樣的面目出現,這里并不打算預先列出幾條應然的特征,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特色”的形成主要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非刻意設計、制造的結果。我們只能說:產業結構的變化,而不是某種“先進”的教育理念將會決定職業教育的人才規格;企業的用人規模與人力資本專用性的需要將會影響職業教育的教學組織;而職業教育自身或許將不再是專門的教育管理機構獨有的領地,勞動就業部門、行業經濟部門、企業組織等將會越來越多地參與職業教育的決策和管理。這樣的“特色”一經形成也就必然要被稱為“中國特色”。它不是一定要在方方面面與眾不同,而是由于國情的特殊性,用來規范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行為的制度(即使僅限于人們看得到的正式規劃)總不會和其它國家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