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教育中的平民思維
劉長海
摘要:精英思維與平民思維是我國道德領(lǐng)域的兩種不同思維方式,學(xué)校道德教育長期以來奉行的是精英思維,在教育目的和教育過程中強調(diào)個體的社會責(zé)任;強調(diào)個人的生存和幸福的平民思維在教育中受到壓抑,但在社會生活中較普遍地存在并發(fā)揮作用。在道德教育研究和道德教育走向平民化、生活化的過程中,道德領(lǐng)域的平民思維必將在道德教育中獲得應(yīng)有地位。平民思維的引入對德育變革有其啟示意義,但德育變革不應(yīng)一味迷信平民思維,而應(yīng)理性選擇,合理利用。關(guān)鍵詞:道德教育 平民思維 精英思維 傳統(tǒng)
一、我國道德領(lǐng)域的精英思維與平民思維
“平民”與“精英”是一組相對的范疇,“平民”指“普通的人”,“精英”指“出類拔萃的人”[i]。在特定社會中,平民與精英因其出身、職業(yè)、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而處于不同階層,并且由于兩個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所擁有的活動能力、所面對的實際問題等的不同,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逐漸形成相互區(qū)別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生活理想及生活方式;在道德領(lǐng)域,這種區(qū)別集中體現(xiàn)在精英階層、平民階層逐步確立適合本階層的道德體系和道德教育方式。
中國傳統(tǒng)社會長期存在著精英與平民的對立。在傳統(tǒng)社會中,擁有穩(wěn)固經(jīng)濟(jì)和政治地位的士大夫以及經(jīng)濟(jì)有一定保障、有望通過薦舉、科舉進(jìn)入政權(quán)的士子是社會中的精英,他們活躍于政治舞臺,享受經(jīng)濟(jì)、生活中的各種優(yōu)待,對國家的內(nèi)政外交享有發(fā)表意見、參與決策的權(quán)利,對社會事務(wù)的處理有著較大的支配能力。處于社會底層、直接從事農(nóng)業(yè)和手工生產(chǎn)、沒有穩(wěn)定經(jīng)濟(jì)收入的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以及一大批小私有者是社會中的平民,他們沒有參與政治的權(quán)利,在經(jīng)濟(jì)和生活中受到各方面的盤剝,對社會事務(wù)的處理中處于被支配的無能、無力地位。士大夫和平民在經(jīng)濟(j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懸殊,決定了他們所面對的實際問題以及對問題的思考和處理方式有很大差別。在道德領(lǐng)域,士大夫階層與平民階層對于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的思考遵循著不同的路徑,由此產(chǎn)生精英道德與平民道德的對立以及精英道德教育與平民道德教育的對立。
中國社會的精英道德是士大夫在思考和處理自我與社會、自我與他人關(guān)系過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則、規(guī)范與準(zhǔn)則的集合體;它們清晰、系統(tǒng)而集中地體現(xiàn)在儒家經(jīng)典、士大夫文稿之中,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凝聚著精英階層的精神,彰顯著士大夫的風(fēng)范。平民道德則是平民百姓在思考和處理自我與社會、自我與他人關(guān)系過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則、規(guī)范和準(zhǔn)則的集合體;由于平民群體結(jié)構(gòu)成分的復(fù)雜性以及平民群體教育水平的限制,平民道德廣泛地散布在民間俗諺、民間儀式和大眾文化作品之中,而沒有較為系統(tǒng)與全面的總結(jié)。
平民道德與精英道德在內(nèi)容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就其整體特征而言,兩者的最大區(qū)別在于精英道德強調(diào)社會責(zé)任,注重人的社會角色與使命;平民道德強調(diào)自我保全,注重個人的得失與幸福。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qū)嬅裆兄钋械年P(guān)懷,將平治國家和天下視為自己的使命,有“任重而道遠(yuǎn)”以及“今日之世,舍我其誰”的使命自覺,以致“進(jìn)亦憂,退亦憂”——“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而憂其君”。精英道德的基本內(nèi)容均與精英的社會責(zé)任感緊密相聯(lián):他們嚴(yán)于律己,率先垂范,在家庭、鄉(xiāng)村、朝廷努力盡到自己的義務(wù),成為道德模范,期望他人信從、模仿,從而達(dá)至理想社會。精英道德體系中的理想人格——君子、圣賢,都是恪盡社會責(zé)任的典范;精英道德體系的具體條規(guī),則是清晰厘定士大夫各方面社會責(zé)任的準(zhǔn)繩。平民百姓則將思考的焦點集中于自身,為柴米油鹽和錢財而忙碌;國家大事,在他們看來,是有權(quán)者的份內(nèi)事,他們自己沒有精力顧及,而且沒有能力和機(jī)會參與。“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平民的思維中很少有社會責(zé)任存在,即使偶爾有人說出“責(zé)任”字眼或做出“責(zé)任”行為,也會被視為異端而遭受譏笑。平民道德基本上與社會責(zé)任無關(guān),純粹是平民的生存技巧的集合,因而,其內(nèi)容與精英道德有著極大區(qū)別:精英道德主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zé)”,平民道德主張“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精英道德主張“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民道德注重“朋友多了路好走”。并且,平民道德是因時、因地制宜的,沒有固定的規(guī)范,允許個人依據(jù)具體情境中的得失利害來選擇行動方式,此時講“和氣生財”,彼時講“人善被人欺”;這一點,與精英道德的嚴(yán)整、明確有著極大的區(qū)別。
平民與精英的不同思維還尤其明顯地體現(xiàn)在對子弟的道德教養(yǎng)方面,即平民道德教育與精英道德教育的不同。精英道德教育以士大夫的家庭教育與學(xué)校教育為基本途徑,以傳播強調(diào)社會責(zé)任的精英道德為己任,以培養(yǎng)嚴(yán)于律己、心憂天下的君子為目標(biāo)。在教育過程中,教育者通過禮儀訓(xùn)導(dǎo)、課堂說理等方式,引導(dǎo)學(xué)習(xí)者遵守既有的道德規(guī)范,認(rèn)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人格標(biāo)準(zhǔn)和“平治天下”的社會理想。教學(xué)過程是以社會需要為基本出發(fā)點的,教育者引導(dǎo)學(xué)習(xí)者主動從家族、國家和天下的需要出發(fā)思考自己的使命,依據(jù)即將擔(dān)負(fù)“平治天下”重任的君子的標(biāo)準(zhǔn)嚴(yán)格要求自己。精英道德教育的過程其實就是教導(dǎo)個體“克己以復(fù)禮”的過程,個體必須革除各方面的個人興趣、愿望、追求,使自己的思想與行為全面地皈依精英道德。這種自我克制的過程是痛苦的,要求個體有明確的意志,通過讀書、實踐、自省、慎獨等方式,不斷完善自我德性,以致如孔子所說“七十(才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此外,傳統(tǒng)家庭、學(xué)校也確立了種種以儒家倫理為依據(jù)的行為準(zhǔn)則、儀式和懲罰措施,要求學(xué)習(xí)者嚴(yán)格遵守,對違背規(guī)章的學(xué)習(xí)者進(jìn)行相應(yīng)懲罰。
平民道德教育以平民的家庭教育為基本途徑,而承載各種人生理念的大眾文化在很多方面支持著家庭中的平民道德教育。平民道德并沒有固定的規(guī)范,以致大量平民并沒有“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意識;平民道德教育其實就是長輩通過家庭生活的身體力行、口耳相傳,將自己所掌握、認(rèn)同的為人處世技巧、原則傳授給下一輩的過程。這種教導(dǎo),基本上是在生活過程中進(jìn)行的,而且由父母傳授的人生規(guī)范往往能夠幫助年輕人在具體場合獲得表揚、獎賞和物質(zhì)收益、避免批評、懲罰和物質(zhì)乃至性命的損失,因此能夠被年輕人很愉快地接受、遵行。戲劇、評書等大眾文化作品對平民生活進(jìn)行了抽象與概括,較直觀地呈現(xiàn)了一些較為復(fù)雜的道德準(zhǔn)則,如不要以貌取人、不要因一時貧賤而得罪人——父母可以借助這些例子,引導(dǎo)子女更好地明白事理。
強調(diào)個體的社會責(zé)任、將人生的最高價值看作平治天下,這種儒家道德理想在千百年的學(xué)校教育、社會教化中一以貫之。精英道德教育的長期推行,強化了廣大社會成員的社會本位思維,使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克己復(fù)禮的理念得到了普遍認(rèn)可;精英道德教育也強化了精英的歷史使命感,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堪稱人格表率的君子、賢臣、名儒,他們的鞠躬盡瘁、舍生取義,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客觀而言,由于我國傳統(tǒng)社會中并沒有世襲的貴族,社會成員的身份、地位、財富都是不確定的,因而,我國傳統(tǒng)社會中穩(wěn)定地居于精英階層并且在思想上具有牢固的精英意識的人,并不是很多。盡管承載精英道德的儒家經(jīng)典廣為誦讀,但多數(shù)人讀經(jīng)有強烈的功利目的,真正認(rèn)同、遵守儒家道德的人也只是官僚、士大夫、地主中的少數(shù)。廣大民眾(包括一大批受過系統(tǒng)儒家教育、擁有豐厚財產(chǎn)、享受國家俸祿的士大夫)出于溫飽、富裕、升遷等個人私利的考慮,選擇信從平民道德的一些較為低俗、淺陋的條目。于是,在中國社會的道德領(lǐng)域就出現(xiàn)了舉世罕見的、普遍的道德標(biāo)榜現(xiàn)象,即社會成員在公開講話、承諾時滿口仁義道德,而在真正行動時卻唯利是圖、見利忘義,道德話語成為缺德行為的“遮羞布”。透過歷代史書及《儒林外史》等文學(xué)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鋪天蓋地的精英道德話語遮蓋之下,平民道德大行其道,在事實上支配著絕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
二、我國學(xué)校道德教育的精英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德育的平民化取向
(一)我國學(xué)校道德教育的精英傳統(tǒng)及其演進(jìn)歷程
教育傳統(tǒng)是教育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并積淀下來的教育觀念、制度、內(nèi)容和方法[ii],在學(xué)校道德教育方面,我國的基本傳統(tǒng)是精英主義的,這種傳統(tǒng)一方面來自幾千年的儒家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來自近代先進(jìn)知識分子主持的學(xué)校、解放區(qū)學(xué)校的精英立場。
在封建社會,儒家思想得到君權(quán)的器重,在學(xué)校教育中長期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進(jìn)入近代社會,精英道德思維仍然在社會中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并且由于外國侵略力量在軍事、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威脅,仁人志士更加注重在社會和學(xué)校中宣傳精英道德,喚起青年和廣大民眾的社會責(zé)任感,以期鑄成萬眾一心的鋼鐵長城。精英道德教育是學(xué)校德育的主導(dǎo)形態(tài),它造就了大批學(xué)子的民族責(zé)任心——恰如《畢業(yè)歌》所唱的,“同學(xué)們,大家起來,擔(dān)負(fù)起天下的興亡”。當(dāng)然,此時的中國社會堪稱亂世,一些軍政要人、商業(yè)人士大發(fā)國難財,但他們?nèi)匀徊煌远Y義廉恥自我標(biāo)榜;更有一大批青年和各界人士在個人利益和民族需要、安逸享受與奮發(fā)有為之間徘徊,或沉淪或與舊生活(平民道德主導(dǎo)的生活)決裂。
在解放區(qū),共產(chǎn)黨注重對軍隊和群眾的思想教育,努力凝聚力量。新中國得以成立,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大公無私的精英道德對軍隊、民眾的教化與鼓舞是密不可分的。為了應(yīng)對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問題,黨和政府更是努力在全社會范圍內(nèi)提倡以服務(wù)、奉獻(xiàn)、犧牲為核心的無產(chǎn)階級道德體系。盡管這種道德在具體內(nèi)容上與傳統(tǒng)社會中的儒家精英道德有極大不同,但兩者都堅持社會本位立場,可以視為精英道德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具體存在方式。
在傳統(tǒng)德育與近現(xiàn)代德育的綜合影響之下,當(dāng)代學(xué)校道德教育是一種精英取向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目標(biāo)是引導(dǎo)學(xué)生樹立責(zé)任意識、集體意識、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和祖國需要、舍小家顧大家的覺悟,引導(dǎo)學(xué)生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wù)中去;道德教育的內(nèi)容高、大、全、美,包括了從個人修養(yǎng)、家庭美德、職業(yè)道德、社會公德在內(nèi)的各方面內(nèi)容,要求學(xué)生認(rèn)真遵守,尤其強調(diào)個體在工作中任勞任怨、無私奉獻(xiàn);道德教育的方法主要采取社會本位的說理,強調(diào)個人對社會、對他人的責(zé)任,依據(jù)社會需要、榜樣事跡來引發(fā)學(xué)生的道德追求——“同學(xué)們,我們是祖國的希望,我們該怎樣承擔(dān)建設(shè)祖國的重任呢?”“雷鋒叔叔從小幫助身邊的小朋友,讓我們一起向他學(xué)習(xí),好嗎?”這種教學(xué)時刻將個人與集體、社會、國家、他人連在一起,提醒個體為集體、他人、社會做好事,而很少引導(dǎo)學(xué)生考慮自己,客觀上壓制了學(xué)生的個人需求和個人利益。
在教育改革的前期,學(xué)校的道德教育定位有所調(diào)整,主要是依據(jù)普遍性與先進(jìn)性相結(jié)合的原則,降低對學(xué)生的普遍道德要求,逐步做到綜合考慮個人利益與集體需要。而道德教育的說理方式基本上沒有改變,教師仍然習(xí)慣于依據(jù)社會需要引導(dǎo)學(xué)生的道德思考。
(二)當(dāng)前德育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平民化取向及其影響
隨著經(jīng)濟(jì)、政治改革的深入,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領(lǐng)域逐漸走出政治化、精英化的一統(tǒng)格局,各種新鮮視角不斷引入并引起思想界或大或小的震動,其中,與后現(xiàn)代主義緊密相聯(lián)的平民化視角是一種重要的力量。平民化研究的基本特點就是跳出傳統(tǒng)精英主義的視野,從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邏輯入手,發(fā)現(xiàn)社會生活的真實狀況,呈現(xiàn)問題,并嘗試依據(jù)平民邏輯解決問題。
平民化取向在當(dāng)代倫理學(xué)研究和道德教育研究中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倫理學(xué)方面,研究者討論道德的本質(zhì)與功能,提出將道德的本質(zhì)看作人生智慧的總結(jié),將道德的根本功能看作主體性功能,認(rèn)為道德對行為的規(guī)范其實是對個體人生的促進(jìn)和發(fā)展。在道德教育研究中,世紀(jì)之交的德育研究者逐漸由批判德育目標(biāo)的“高大全美”過渡到主張德育為生活服務(wù),具體來講,包括:(1)在德育目標(biāo)方面,主張德育應(yīng)該為人的生活服務(wù),應(yīng)該促進(jìn)人過上“好生活”,使其享受人生的幸福[iii];(2)在德育內(nèi)容方面,反對既有道德規(guī)范力求全面、高大的取向,而是主張依據(jù)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對個體道德的最低要求(底線倫理)以及個體生活的自然需要,確定符合人的幸福生活需要的道德教育內(nèi)容體系;(3)在德育方法方面,主張德育基于生活、在生活中進(jìn)行,通過豐富個體的生活經(jīng)驗,依據(jù)個體成敗得失的經(jīng)驗、感受來引導(dǎo)學(xué)生思考自我與他人、自我與社會的關(guān)系,選擇、確定自己所要遵行的道德。
以生活德育為代表的眾多當(dāng)代德育研究論著都體現(xiàn)了強烈的平民化取向,這種取向一方面得到了一線教師的情感認(rèn)同,另一方面也在德育課程中得到了較全面的體現(xiàn)。教師對平民化德育主張的認(rèn)同主要是由于平民化使道德教育不再是板起面孔說教,而是對學(xué)生有了較切近的意義;平民化可以使師生在教學(xué)過程中思想自由,而不必一味地高呼口號。在新一輪的德育課程改革中,生活化、平民化的主張得到了較全面的貫徹。小學(xué)德育課程的核心目標(biāo)就是使兒童“健康安全地生活、愉快積極地生活、負(fù)責(zé)任有愛心地生活、動腦筋有創(chuàng)意地生活”,兒童的生活、幸福、成長在文本中成為德育關(guān)注的中心。在教學(xué)中,教師依據(jù)文本要求,也必須更多地采取依據(jù)兒童生活體驗的方式,引導(dǎo)兒童思考生活中的道理、人際交往中的學(xué)問,提升學(xué)生的人生智慧與生活質(zhì)量,幫助學(xué)生過上“好生活”。
在德育研究與道德教育走向平民化、生活化的過程中,長期壓抑平民思維的各種制度力量、心理力量發(fā)生松動,家長、學(xué)生、教師頭腦中所形成的各種基于個人生活、福利的思想逐漸有了較多的表達(dá)機(jī)會和表達(dá)自由,并且,由于德育課教學(xué)所選用的主題多半來自日常生活,平民思維中的一些既成論點很自然地會受學(xué)生、教師想到并提起。程紅艷曾引述一個例子:教師教導(dǎo)學(xué)生說:“你們在學(xué)校里應(yīng)該相互關(guān)心、謙讓,不應(yīng)該動手打人。”學(xué)生回答教師說:“我爸爸說,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不能太老實,誰要動手,我就必須還擊。”[iv]在現(xiàn)實的校園中,這樣的例子可能很多。面對學(xué)生的對質(zhì),在精英取向的德育中,教師會采取講大道理(關(guān)于人與人互愛、人對社會的責(zé)任等基于精英思維的理論)的方式來強制學(xué)生服從;而在生活取向、平民取向的德育中,教師是否會變得束手無策呢?
三、在道德教育中引入平民思維的合理性與其限度
當(dāng)代德育研究中德育生活化、道德要求“從天空回到地面”的表達(dá)不斷沖擊著精英德育的尊嚴(yán),也不斷地擴(kuò)展著平民思維在道德教育領(lǐng)域的活動空間。如何看待道德教育中的平民思維呢?是否有必要將平民思維正式引入道德教育,甚至以平民思維取代道德教育中的精英思維呢?筆者認(rèn)為,我們有必要對平民思維引入道德教育的合理性進(jìn)行分析,以明確平民思維進(jìn)入道德教育的限度。
(一)在道德教育中引入平民思維的合理性分析
綜合而言,將平民思維引入道德教育,是有其學(xué)理依據(jù)和現(xiàn)實價值的。
就道德本質(zhì)而言,平民思維有助于人們?nèi)胬斫獾赖潞偷赖陆逃W鳛檎{(diào)節(jié)人與人、人與社會關(guān)系的原則與規(guī)范,道德是人類社會生活經(jīng)驗的總結(jié),是有助于人生成功與幸福的、對個體社會活動的合理規(guī)范。各種道德規(guī)范的根源都來自社會生活,人們應(yīng)該基于生活經(jīng)驗來理解其實質(zhì),而不應(yīng)盲目信從。尤其在社會轉(zhuǎn)型期,社會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條件發(fā)生根本性變化,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所依附的物質(zhì)條件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而人們的道德思維卻可能遵循傳統(tǒng),維護(hù)一些并不具有合理性的道德規(guī)則;從生活經(jīng)驗出發(fā)反思道德、組織道德教育,可以促使人們反思各種道德規(guī)范的物質(zhì)基礎(chǔ),從而將那些與現(xiàn)代社會不相適應(yīng)的道德規(guī)范剔除或揚棄,讓部分道德規(guī)范的內(nèi)涵進(jìn)行與時俱進(jìn)的闡發(fā);引導(dǎo)年輕一代在生活經(jīng)驗基礎(chǔ)上理解道德規(guī)范,更能發(fā)揮道德對人生的服務(wù)功能,并且提高道德教育的親和力與有效性。
就個體道德發(fā)展規(guī)律而言,平民思維符合個體道德發(fā)展初級階段的規(guī)律,因而適合于低年級的道德教育。美國著名道德心理學(xué)家柯爾伯格經(jīng)過長期研究提出個體道德認(rèn)知發(fā)展的階段理論,將個體道德認(rèn)知發(fā)展分析為三個階段六個水平,依次為:前世俗水平,包括懲罰與服從取向階段和工具性的相對主義取向階段;世俗水平,包括人際協(xié)調(diào)取向階段和維護(hù)權(quán)威或秩序的道德取向階段;后世俗水平,包括社會契約的取向階段和普遍的道德原則取向階段。在個體道德認(rèn)知發(fā)展的低級階段,個人對善惡、是非的判斷是依據(jù)自己的利益、行為后果對自己的利害關(guān)系而得出的;只有在個體道德認(rèn)知發(fā)展進(jìn)入高級階段之后,個體道德判斷才轉(zhuǎn)而以社會秩序、契約和普遍原則為依據(jù)。由此可知,低年級的道德教育應(yīng)該依據(jù)個體道德認(rèn)知發(fā)展的特點,訴諸個體生活經(jīng)驗,而不應(yīng)一味提出高尚道德強調(diào)學(xué)生遵守,否則就會導(dǎo)致學(xué)生的盲從或者對道德教育的逆反。
就社會轉(zhuǎn)型期道德體系重建與德育實效性提高而言,平民思維的引入有著現(xiàn)實必要性。我國封建社會的主流道德體系,是建立在宗法君主制基礎(chǔ)之上的、一味強調(diào)個體對群體的忠誠與犧牲的精英道德體系,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主流道德體系沿襲了精英主義傳統(tǒng),以集體需要、人民利益為核心,要求個人利益服從祖國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這種精英道德是精美的、高尚的,但卻一方面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中國社會普通成員的生活實際,成為對個體德性的“無限拔高”,無助于調(diào)動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精神;另一方面不能正確界定個人利益、權(quán)利與義務(wù),容易導(dǎo)致官僚在集體與道德的名義下對個人權(quán)益的不當(dāng)侵害。當(dāng)代中國的社會轉(zhuǎn)型一方面要求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而對個人利益(尤其是勞動收益)的尊重,有助于調(diào)動個體的積極性與創(chuàng)新意識;另一方面要求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關(guān)系,建設(shè)民主社會,這也要求走出強調(diào)自我犧牲的精英思維,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建構(gòu)新型道德。就學(xué)校道德教育而言,學(xué)校德育存在著較為普遍的實效性低下的問題,這一問題與德育目標(biāo)和內(nèi)容方面的“高大全美”有關(guān),也與德育過程和方法方面片面強調(diào)集體和社會需要,而不引導(dǎo)學(xué)生思考人生、反思生活經(jīng)驗有關(guān)。平民思維的引入,一方面可以引導(dǎo)成人(包括道德理論界)反思、厘定當(dāng)代中國的合理道德體系;另一方面可以引導(dǎo)教育者反思德育內(nèi)容與方法,確定合乎時代要求的德育目標(biāo),選擇更具親和力和實際效應(yīng)的德育方法。此外,將平民思維引入道德教育,能夠使長期以來受到壓抑和忽視的中國本土民間智慧得到發(fā)掘,更全面地發(fā)揚中國德育傳統(tǒng),建立當(dāng)代德育的民族根基。
(二)在道德教育中引入平民思維的限度
平民思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并不具有獨立指導(dǎo)道德教育的合法性;學(xué)校道德教育的開展,不應(yīng)從一個極端轉(zhuǎn)入另一個極端,將個體生活經(jīng)驗、生活需要與民間生活智慧作為道德教育的唯一基礎(chǔ),對現(xiàn)存的平民生活智慧全盤繼承,是不可取的。
就道德本質(zhì)而言,道德并非個體生活經(jīng)驗的總結(jié)。盡管道德是人類社會生活經(jīng)驗的總結(jié),這種經(jīng)驗總結(jié)不是建立在某一個人的生活經(jīng)驗基礎(chǔ)之上的,而是對特定時期特定社會中復(fù)雜社會生活的概括,由此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道德準(zhǔn)則和規(guī)范并不與具體個人的生活經(jīng)驗相符合,而個人依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可以得出與普遍認(rèn)可的道德規(guī)范相背離甚至對立的結(jié)論(如社會倡導(dǎo)友愛,而富家子弟則可以歧視勞工并且不會受到任何報復(fù))。一味強調(diào)從個體生活經(jīng)驗出發(fā)引導(dǎo)學(xué)生的道德思維,學(xué)生可以得出背離道德的人生信條。
就個體道德發(fā)展而言,個體德性并不以日常生活、成敗得失為其限度。人的需要,既有低級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也有高級的尊重需要、自我實現(xiàn)需要;人性既有其受制于物質(zhì)條件的一方面,也有超越于物質(zhì)世界之上、追求終極的光輝面。將崇高、無私作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對人性的拔高,是不恰當(dāng)?shù)模粚⒌赖吕斫鉃槔娴牟┺摹€體的道德引導(dǎo)限定于遵守公德和底線倫理,則是對人性的貶抑,是使人回到動物的水平,更是不利于人生的豐富與幸福的。尤其在現(xiàn)代社會,個體生活的物質(zhì)水平越來越高,個人的精神追求越趨豐富,關(guān)心、分享、志愿服務(wù)等正在成為公民充實生活、完善人生的選擇,道德教育應(yīng)該發(fā)揮引導(dǎo)人性發(fā)展的功能,而不應(yīng)專注于基礎(chǔ)道德的普及,對人性的美好視而不見。
綜上所述,平民思維并不能獨立指導(dǎo)學(xué)校道德教育的開展。如何發(fā)揮平民思維對學(xué)校道德教育的積極推動作用,而減少其誤導(dǎo)德育的消極作用呢?筆者認(rèn)為,我們應(yīng)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綜合精英思維與平民思維,依據(jù)公民與民主社會關(guān)系的視角,合理厘定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責(zé)任內(nèi)涵,逐步確立民主時代的道德體系。精英思維無視個人利益,平民思維的基本啟示是尊重個人需要與利益,但平民思維僅僅關(guān)注“我”的收益,而不考慮普遍適用的規(guī)則。在民主社會中,任何個人都沒有理由犧牲自我,而每一個人都對社會的發(fā)展承擔(dān)責(zé)任,理論家應(yīng)該從公平、正義出發(fā),對其中的責(zé)任關(guān)系進(jìn)行界定,對個體道德過高或過低的期望都是不正確的。
其二,啟發(fā)、引導(dǎo)學(xué)生的生活反思,由低到高地培養(yǎng)學(xué)生的道德品質(zhì)。任何道德規(guī)范都應(yīng)該能經(jīng)得住生活的考驗(當(dāng)然,并不是個人的某一具體成敗經(jīng)驗)和理性的審視,而個體對經(jīng)過自己考驗和反思的道德體系才會真正認(rèn)同、堅持,因而,道德教育不應(yīng)片面地對個人提出行為要求,而應(yīng)啟發(fā)學(xué)生結(jié)合生活事例思考,形成自己的道德觀念。并且,個體道德發(fā)展的初級階段應(yīng)該以個體生活經(jīng)驗為基礎(chǔ),教師應(yīng)該充分利用學(xué)校資源,為良好學(xué)校生活創(chuàng)造條件,幫助學(xué)生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礎(chǔ),繼而在個體道德成長的更高階段,引導(dǎo)學(xué)生基于理性,在生活中承擔(dān)更多的責(zé)任。
其三,適當(dāng)引入反映平民思維的、較具親和力的概念、話語,但對既有平民智慧應(yīng)批判性地繼承并且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幸福”、“好生活”等概念出自民間,能夠拉近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距離,使受教育者不再將道德教育視為異己,因而對于道德教育改革有其積極意義。但另一方面,既有平民智慧、民間話語是在傳統(tǒng)條件下民眾生活的總結(jié),對當(dāng)代社會發(fā)展而言并不一定適合,如“好生活”在普通民眾心目中是有錢、有權(quán)、平靜的生活,“幸福”的秘訣是“百忍成善”、“退一步海闊天空”;道德教育在適當(dāng)借助平民思維時,必須對傳統(tǒng)平民智慧的含義進(jìn)行詳細(xì)考查,選擇其適于現(xiàn)代社會的含義進(jìn)行闡發(fā),并且,要引導(dǎo)學(xué)生反思日常話語的合理性與局限,依據(jù)當(dāng)代社會需要對日常話語進(jìn)行詮釋,以真正發(fā)揮其對于學(xué)生道德成長的正面價值。
--------------------------------------------------------------------------------
注釋:
[i] 中國社科院.現(xiàn)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
[ii] 褚宏啟.教育現(xiàn)代化的路徑.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0.41.
[iii] 鄭航.和諧社會的“好生活”與道德理性的生長.華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06(2):27-33.
[iv] 程紅艷.教師的道德沖突.教育研究與實驗,2006(3):1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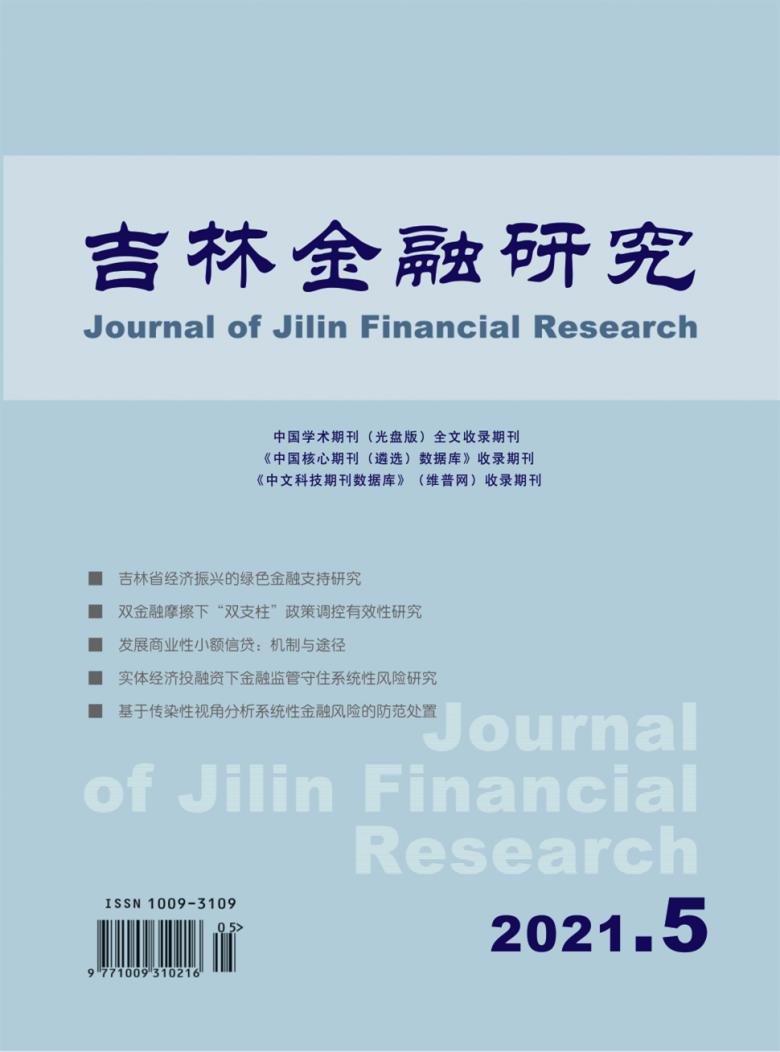


代經(jīng)濟(jì)研究.jpg)
學(xué)報.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