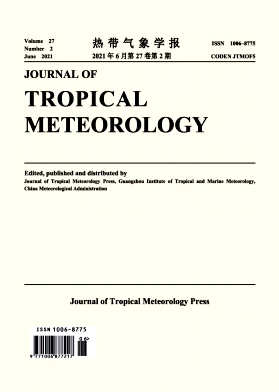中西歷史進程差異的地理基礎
許平中
摘 要: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動力不是技術突破而是市場興起。西歐產品差異大,水路運費低,商品交換有利可圖,吸引人們發展商品市場。中國東西方向產品差異小,南北方向陸路運費高,商品交換無利可圖,農民的“合理選擇”是調整產品結構以滿足需求,自給自足導致社會長期停滯。
關鍵詞 : 無差異;陸路;市場;停滯
現代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都是經濟人在特定客觀環境下“合理選擇”的結果。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這種客觀環境主要就是自然地理環境。早在18世紀前期,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就認識到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更是非常重視“歷史的地理基礎”。普列漢諾夫在其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地理環境對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筆者受這些思想的啟發,多年來力圖探明近代西歐興起和中國落伍的地理根源。本文就是探討的成果。
一
傳統觀點認為,技術突破是西歐興起的原動力。技術突破促進了生產 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分工,加速了市場形成,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興起。
這一觀點沒有解釋:技術突破是偶然出現的,還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為什么中世紀后期西歐出現了那么多技術突破,而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兩千多年中,生產技術卻幾乎沒有出現任何重大突破?如果具有某種必然性,那么這種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 ·諾思(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等人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闡明了技術創新的原理和西歐興起原因。
人類歷史上的許多發明創造具有偶然性。例如,魯班發明鋸子的故事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這一發明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偶然性的發明和創新能否對社會發展起重要作用,取決于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例如,南歐人很早就發明了利用水力和風力的技術,但這些技術在南歐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到10至11世紀時,西歐采用了這些技術,制(建)造了水力碾磨機、羊毛漂洗機和風力磨房,大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為什么這些技術在南歐未起到多大作用而在西歐起到了重大作用呢?答案是南歐不存在而西歐存在對它們的市場需求,因為利用這些技術建造相應的設備需要大量資金,只有在生產大量產品的情況下才經濟合算,而大量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但南歐缺乏大量銷售產品的市場。如果沒有廣闊的市場需求,西歐也不會采用這些技術。可見,偶然性的發明創造能否對社會發展起重大作用,取決于市場對它們的“需求”程度。
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到西歐以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卻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馬克思語)。人們過去一直對四大發明在中國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感到迷惑不解,現在看來,它們之所以在中國未起到多大作用,完全是由于在中國采用這些技術的人得不到什么利益,社會幾乎不存在對它們的“需求”;同樣,它們之所以對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起到了重大作用,則是因為當時的歐洲社會對它們存在著巨大的市場需求,采用這些技術能夠使人獲得具體利益。
根據成本收益原理分析,歷史上偶然性的發明創造之所以出現不少,是由于這些發明創造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與偶然性的發明創造不同,按照特定目標進行研制而取得的技術成果,往往需要花費很高代價,是否有人愿意承擔這樣的代價,就要看這一研制是否有利可圖。我們以人類發明計時鐘的過程為例作一說明。
隨著海洋運輸的發展,急需確定輪船在海洋中的經度和緯度。人們早就知道測定北極星的頂垂線或太陽在中天的垂線都可以求得緯度,于是關鍵問題就歸結為如何測定經度。15世紀葡萄牙的亨利親王召集一批數學家研究測定經度的方法,最后又歸結到需要一臺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鐘。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為發明計時鐘懸賞1000金克朗,荷蘭把賞金提高到10萬弗羅林,而英國最后懸賞的賞金依天文鐘的精確度定為1萬至4萬鎊不等。直到18世紀,英國的哈里森為此耗費了半生精力最后獲得了這筆賞金。如果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急病死亡,計時鐘也一定會被其他人發明出來,因為只要巨額懸賞存在,總會有一些人耗費時間和經歷去從事研制工作。發明計時鐘對社會的利益是巨大的,但如果沒有各國政府懸賞,發明者從中得到的收益遠遠低于他所付出的代價,便不會有人為了社會的利益而破費個人財產去進行研制。懸賞是刺激人們努力發明創造的有效途徑。不過,政府懸賞的只能是重大而緊迫的項目,每個項目都靠政府懸賞是不現實的。為了對發明創新給予經常的刺激,英國最早創立了保護知識產權的專利制度。而在發明者利益得不到保護的社會中,人們受“白搭車”利益的刺激,對于那些容易被人仿制因而個人預期收益顯然低于預期成本的項目,就都想等待別人發明出來之后去進行仿制,于是社會只可能出現一些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簡單的或偶然性的發明創造。在偶然性的發明創造都已經出現并被人們利用以后,生產技術就會限于停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生產技術的長期停滯,就是這一原理造成的。
不過,當西歐技術突破出現時,專利制度還沒有形成。因此,西歐生產技術的突破,并不是專利制度刺激的結果。那么,西歐的技術突破是如何出現的呢?
9世紀初,當封建主義和莊園制度在西歐形成時,莊園之間還有很多空地未加以利用,許多邊遠地區尚未開墾。當人口增長達到飽和以后,就會溢出到一些尚未開墾的地區。新老地區自然條件和人地比例有較大差異,導致產品存在較大差異,產品差異引起交換的需要,結果在地理位置適中處,逐步形成了定期集市,以后又發展成永久性市場。市場逐漸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規則、組織和制度,例如委托制使得商人可以利用外地同行做遠距離生意;合伙制可以使小商人參加大批量物品的貿易;保險公司分散了遠距離貿易的風險;銀行存貸制度使借款人能夠利用他人的資金完成生產和經營活動;匯票制度則降低了攜帶資金的風險,并且創造了新的流通手段……這些制度和組織都方便了交易過程,降低了交易費用,增加了盈利機會。盈利又吸引更遠的地區和更多的商人加入到市場活動中來。市場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范圍越大效率也越高。市場盈利使擴大生產規模有利可圖。靠近市場的地區信息靈通,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生產,逐步形成了專業化的生產中心。那時西歐主要的制造品是羊毛織品,其制造過程可以分解為許多細小的工序,精細的分工使人們只需要重復簡單的操作,“將人們天生的發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難題上”(諾思語),為生產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可能。 西歐一系列的技術突破,就是這樣出現的。
過去,人們一直以為技術突破是西歐生產擴大、市場興起和社會進步的初始原因。諾思通過研究西歐興起的過程證明,技術突破是生產規模擴大引起的勞動分工的結果。從經濟人“理性選擇原理”來看,技術突破是人們利用市場擴張所帶來的盈利機會的結果。因此,西歐經濟興起的基礎不是技術突破而是市場興起。
我們根據諾思闡明的原理可以知道,近代以來西歐和中國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差異,歸根到底是市場發展狀況的差異造成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和西歐市場發展的狀況為什么出現重大差異呢?下面我們討論市場發展的有關原理。
二
按照諾思的看法,西歐市場興起的原動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長。不過,人口增長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為什么只在西歐引起了市場興起呢?這就需要探討市場發展的基本條件。
過去,歷史教科書過分強調剩余產品是商品交換的前提條件。有人就此認為,良好的自然條件使西歐生產了較多的剩余產品,是西歐商品市場發展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因為再優越的自然條件,其最大的環境人口容量也是有限的。人口的自然增長引起勞動收益遞減,導致剩余勞動越來越少,當人口飽和時剩余勞動就減少為零,那時就根本談不到對商品市場的刺激作用了。因此,即使生產技術不變,剩余勞動的多少也不僅取決于自然條件,還與當時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單從自然條件上說,文明古國所在的大河流域比西歐更為優越,單位土地產出量高,早就生產了較多的剩余產品,但它們的商品市場卻沒有發展起來。因此,光用剩余產品的多少來解釋西歐的興起不能令人信服。
在人類歷史上,剩余產品大致起到了以下三種作用:第一,通過交換轉化成其它商品,從而刺激市場的發展。中世紀后期的西歐就是這樣。第二,直接被統治者集中起來,建造宏大的工程或者進行對外戰爭。金字塔、萬里長城 、大運河以及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隋煬帝侵略高麗戰爭等,都是剩余產品的轉化形式或者以剩余產品為基礎。第三,按照馬爾薩斯論證過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會堅定不移地增長)轉化為人口。歷史上漢、唐、明、清四大王朝前期大幅度的人口增長,就是剩余產品轉化而來的。剩余產品究竟能夠起到何種作用,主要取決于它們本身的特點。例如白薯等塊根類作物和瓜果、蔬菜都容易腐爛,不便于運輸和保存,這就難以被統治者集中利用,也不容易刺激商品交換的發展。這樣的剩余產品,只能轉化為人口。
歷史上中國的剩余產品主要是糧食和布匹,它們都容易集中利用和遠途運輸,所以歷代統治者利用它們建造了不少宏大的工程,也組織過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規模巨大的戰爭。下面我們分析中國的剩余產品為什么沒有刺激商品市場的發展。
人們相互交換的主要是用途不同的產品。剩余產品要成為交換的對象,從而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那么在一個較大的地域內,產品必須具有多樣性,或者說,在這一地域的不同地點,產品必須具有差異性。
產品的差異性首先由氣候條件決定。地球東西方向的自轉使得世界各地氣候呈東西方向帶狀分布,南北方向氣候差異較大。西歐氣候除了這種帶狀差異外,還受北大西洋暖流和常年盛行的西風影響,降水量從西到東逐漸減少,年溫差自西向東逐漸增大,東西方向上產品差異也較大。 例如大不列顛這一南北狹長的海島,面積比中國的河南省大不了多少,但在島上東西不大的寬度內,西部降雨多日照少,東南部降水少日照多,結果西部發展了畜牧業,而東部則發展了糧食種植業。
西歐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早在10至11世紀就促使人們開始了活躍的內部貿易,先是地區內和地區間的貿易,逐漸擴展為國家之間的貿易。英國和西班牙的羊毛、法國和波羅的海流域的糧食、北歐的木材、北海與波羅的海的魚類、法國的葡萄酒,都集中到尼德蘭的大市場上進行交換,促進了交換手段和方法的發展,也促進了各地區的生產逐漸走向專業化,最終都促進了經濟增長。
有人會問:中國幅員960萬平方公里,經、緯跨度都有四、五千公里,地形和氣候復雜多樣,自然產品幾乎無所不有,但為什么沒有形成范圍廣闊的市場呢?
在全中國范圍內討論,自然產品當然會有很大差異,例如地處熱帶的廣東和接近寒帶的黑龍江,自然產品就很少會有相同。但是考慮到實際情況,古代條件下黑龍江和廣東不可能實現產品交換,因為它們相距太遠,運輸費用太高,沒有人去進行交換。這就引導我們考慮不同地區之間的運輸費用問題。
三
運輸費用問題不但未受到歷史學家的重視,甚至也沒有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但是不考慮運輸費用,就不可能認識西歐興起和中國落伍的原因。
商品的運輸費用可以分解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克服空間距離和沿途自然條件的障礙而花費的代價,我們把它稱為“純粹運輸費用”;另一部分是人為原因增加的負擔,包括:(1)為對付旅途中盜匪搶劫而支出的武裝保衛費用;(2)實際發生的搶劫造成的損失;(3)沿途關卡的收稅和勒索。這些費用可以稱為“附加運輸費用”。這些運輸費用的高低都與道路的性質有關。
在陸地上成批運送貨物,既要有適于通行的路面,又要有結實的運載工具(車輛),還需要較大的運輸動力。因此,陸路運輸的“純粹運輸費用”很高。陸路所經過的荒野上常有盜賊攔路搶劫,商人們必須有武裝護送。陸路經過的村莊常有領主或莊主設卡收費。因此,陸路運輸的“附加費用”也很高。
利用河道運輸,水體本身就能夠承載舟船,不需要專門修筑道路,水上運輸對運載 工具的牢固性要求也較低,并且所需動力也比陸地小得多。因此,河道運輸的純粹運輸費用很低。
河道運輸所需的附加運輸費用比較復雜。在河上搶劫需要專門的作案工具,不象陸地搶劫那樣方便(經濟學術語就是“進入門檻高”),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搶劫的頻繁性;但是另一方面,商人在遇到搶劫時也無法繞道躲避,這又增加了河道運輸的風險,所以不好確定河道運輸時人為風險比陸地大還是小。但是,河道上很便于設卡收稅。14世紀時,法國羅亞耳河上有關卡74處,加隆納河上有70處,征稅名目繁多,例如1300年時萊茵河上的通過稅有35種以上。因此,河道運輸時附加運輸費用很高。不過,盡管承擔了大量的附加運輸費用,河道運輸仍然有很大的收益。如果不是低廉的純粹運輸費用彌補了高額的附加運輸費用的話,沿途關卡沉重的勒索,恐怕早就扼殺了西歐遠距離的河道運輸。
在海洋上運輸貨物,航路可以適當選擇,純粹運輸費用比河道運輸更為低廉。在廣闊的海洋無法設卡收稅,海盜也不易隱藏,而商人遇到搶劫時回旋余地卻較大(當然并不是毫無危險,近些年甚至出現了配備現代設備的海盜集團),所以,海上運輸的附加運輸費用也不高。
商品的運輸費用還取決于商品本身的特點。金銀、珠寶等貴重物品體積和重量都很小,單位價值所攤的純粹運輸費用很低,它們最適合遠途運輸。但是也正因為貴重,它們對劫匪的吸引力也很大,專門運輸這樣的貴重物品,光是武裝保衛費用就承擔不起,所以歷史上恐怕從來就沒有過專門運輸貴重物品的車輛和船只,它們對市場的擴大也沒有起到過多少刺激作用。
香料、瓷器、象牙(以及現代的毒品)等有特殊用途的商品,最初生產成本低而最終消費價格高,它們能夠承受遠距離的運輸費用。歷史上跨大洲、越大洋交易的都是這樣的特殊商品。但是由于最終售價很高,往往成為消費不起的“奢侈品”,因而社會需求量小,對市場的刺激作用也有限。
促進了商品市場發展,從而帶動整個經濟發展起來的,是農、林、牧、漁等基本物品(糧食、木材、牲畜、魚類)(低值笨重貨物)的貿易。不過大多數地區都生產基本物品,而相鄰地域的產品又大都類似,沒有交換的必要。只有當相距較遠時,基本產品才可能有較大差異。但又由于基本產品都具有低值笨重的特點,它們又承受不了較遠距離的運輸費用。因此,低值笨重貨物的交易,只能夠在一些條件很特殊的地區發展起來。
中世紀初期,西歐具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農產品的生產成本較低,因而剩余產品較多。在不大的范圍內,西歐基本產品差異較大。這兩個因素首先刺激了地區市場的興起。大西洋暖濕氣流使得西歐的降水豐富而且均勻,那里河流密布并且流量穩定,一年四季都 適于通航。古代缺乏陸上道路和機械動力,陸路運費大致超過水路運費30倍。同樣的商品差價,水路可以運到比陸路遠30倍的地方銷售,水路市場比陸路市西歐的輻射半徑可以大30倍,覆蓋面積就比陸路市場大900倍。廣泛的水路運輸促進了西歐低值笨重貨物貿易的發展,遠在工業革命前就形成了輻射幾百公里的國際大市場。
可見,小范圍內產品差異大,大范圍內運輸條件好,是西歐發展商品市場十分有利的條件。
四
在了解西歐市場興起的基本條件以后,讀者也許已經意識到中國商品市場長期難以發展的原因了。與西歐相比,中國的自然地理條件幾乎正好相反,簡單地說就是產品差異小,運輸費用高。
(1)東西方向上氣候條件相同,產品無差異。
我們以中國文明本部(黃河流域)為例予以說明。中國文明本部屬于暖溫帶的半濕潤地區,一月份的零度等溫線,七月份的28度等溫線,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線(即中國地理上重要的氣候分界線秦嶺——淮河),大致是這一地區的南界;而一月份零下6度等溫線,七月份24度等溫線,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大致在這一地區的北界。如果我們從該地區最西端陜甘交界處一直走到最東端的山東半島,所到之處,土壤和氣候條件幾乎都是相同的,這就使得農作物的品種大致相同,因而沒有交換必要。當然,從更廣闊的范圍看,中國南北方向上氣候和產品差異較大,例如北部旱地產粟,南部水田產稻,不同產品有交換必要。但是,這些有交換必要的產品被運輸條件所制約,因為
(2)缺乏適于通航的河流。
中國文明本部降水的季節性導致河流的季節性變化,夏秋漲水時往往溢出泛濫成災,冬春則幾乎干涸斷流,河床變化大,無法建立固定碼頭,不能發展水運生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自然河流均為東西走向,在河流的上下游地區,自然產品基本相同,不需要進行交換,利用水路沒有意義;雖說南北方向上產品有差異,但卻沒有通航河流,而陸路運費本來就高,又正好被東西方向的河流所阻隔,南北方向的陸路交通比東西方向更為困難。歷史上隋煬帝下那么大功夫開鑿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就是為了解決南北方向的運輸問題。 那么,依靠陸路運輸能不能形成輻射范圍廣闊的市場呢?
一個身強力壯的農民,肩挑背扛最多能把四、五十公斤的農產品運到10公里外,交換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后再于當天返回他所居住的村莊。手推獨輪車較為省力,但一天也不能往返更遠的距離。由農民自產自銷形成的陸路市場,輻射半徑不超過10公里,覆蓋面積不超過400平方公里。按平原地區每平方公里50人(歷史上華北平原大致的人口密度)計算,市場輻射范圍內的總人口不到20000人。假定從事手工業的人口占十分之一,并且都居住在中心城鎮,那么城鎮最多有2000人。我們把一個中心城鎮和它輻射范圍內的鄉村,看作一個經濟系統(模型)。由陸路運輸形成的經濟系統,最大就具有這樣的規模。一個只有區區20000人的經濟系統,如果不與其他系統交往,自身很難有什么發展。
可惜的是,在中國文明本部的黃河流域,直至清末民初,專門從事手工業的集鎮還沒有形成。實際形成的集鎮,其人口主要還是從事農業,集鎮的輻射范圍還遠沒有我們設想的模型大。筆者所在的縣全部位于平原地帶,面積約800平方公里, 民國時集鎮的輻射半徑大都不到5公里,農戶常年男耕女織, 不同村莊之間很少交往。直至現在,全縣還可以區分出五個不同的方言區,方言區之間卻并無山河阻隔。
東西方向上產品的無差異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兩千多年來制約中國商品經濟不 能夠發展的根本原因。在古代的中國,任何兩地基本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都補償不了運輸費用,從事基本物品的交換無利可圖,所以就沒有人去致力于基本物品的交易。因此,古代中國不可能形成大范圍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場(唐代長安、宋代汴梁等繁華都市,并不是經濟原因形成的大市場。我們在《東京夢華錄》中可以看到,汴梁的繁華完全是由于大量酒樓、茶肆、果鋪、妓院、藥房、珠寶店等等為宮廷官僚服務的消費行業造成的。中國歷史上那些繁華的城市,與我們此處研究的由基本物品貿易形成的市場沒有關系)。
過去,學者門往往把中國維持小農結構和商業不發達歸咎于統治階級的“重農抑商”政策,這一認識是比較膚淺的,實際上正好顛倒了其中的因果關系,因為不是“政策”產生了相應的經濟結構,而是經濟結構使統治者選擇了相應的政策。
人們自從定居以來,大致有三種方式可以獲得產品:一是自己生產,二是與人交換,三是偷來搶來。作為群體,農民當然不能依賴偷盜或搶劫,這就只有生產或者交換得到。但在中國,用交換方法得到產品,比直接生產它們花費的代價更高,農民的“理性選擇”就是自己需要什么就調整產品結構直接生產什么,于是社會就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
在中國,也許只有經銷鹽、鐵、茶、酒等特殊物品有利可圖。但從戰國時起,國家就逐漸壟斷了鹽、鐵(后來又增添了茶、酒)的經營,私自制造或販賣要受到嚴厲制裁。由于基本物品的交易無利可圖,所以商販的主要門道就是行奸弄巧或者販賣違禁物品,這樣,商業在社會生活中就起不到什么積極作用,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提倡以農為本,采取重農抑商政策。這種政策當然會對市場發展更為不利。不過,在我們看來,由于地理條件限制,即使 沒有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的商品市場也不可能自發發展起來,社會長期陷于停滯是必然的。由于資本主義興起完全依賴于市場的發展,所以,封閉的中國也不可能自發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西歐和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差異,歸根到底是由于地理條件的差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