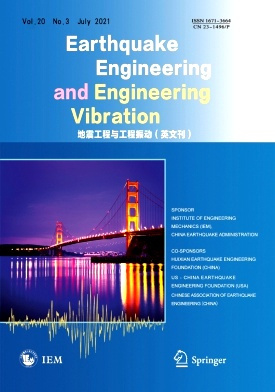揭示史前中國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
薛翔驥
摘要:《山海經》是史前人文、地理、氣候、歷史的唯一科學記錄,具有很高的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通過對《山海經》的研究,可以科學有效地揭開因史前人類用神化的記敘手法記敘歷史所形成的神秘面紗,清晰地看到史前中國在第四紀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期這一階段的基本面貌。
Abstract:《The record of the mountain and sea 》be unique science record of prehistoric humanities、geography、weather、history, have the very high science credibility and the result matches degree of history, pass by《The record of the mountain and sea 》 of research, Can expose China availably by science prehistoric mysterious.
關鍵詞:《山海經》;史前,全新世;昆侖丘,河套;海侵;人文地理
Key words:《The record of the mountain and sea 》;Prehistoric, Holocene;The mountain of KunLun, River set;sea invade;Human geography
一、《山海經》的科學信度與效度
1.1、《山海經》簡述:
經過十余年不懈研究,我以為《山海經》的山經部分應該是史前炎黃各氏族的口頭傳說,以及帝嚳后期(包括唐堯、虞舜、夏禹時期)對各地山川的考察記錄。
從《山海經》山經部分清晰地勾畫出西山、中山和北山的情形,而南山、東山的情形甚為虛妄、模糊的情形看,山經應當是炎黃氏族群對自己發祥、居住地域的一部地理和人文情況記錄,其形成年代恐怕要遠于夏禹治水時期。
夏禹治水時期(前2150年左右),海侵現象早已結束,但東山經記敘的依然是海水漫漫的情形,這說明,山經主體部分的形成,應在夏禹治水以前。
東山、南山二經的記敘內容相對模糊,一則說明山經的形成,與當時的東夷氏族、南方氏族,沒有緊密關系,二則說明,夏禹的治水工作,多在西山、中山、北山三經所記敘的地域。
山經中,惟有西山、中山二經記敘了神靈(即氏族首領的神化形象),而西山、中山所涵蓋的地域,正是炎帝氏族群和黃帝氏族群發祥、居住的地域。這說明山經主體的形成,應該在前4500年~前3800年的炎黃時期。
因此,《山海經》的山經部分,應在夏禹治水以前,由炎黃各氏族完成內容,最后由夏禹前后的人們完成書籍。而《山海經》的海經部分,我以為它是夏以后的人們,總結各地的古史傳說,在不同的年代完成。
根據海經所記敘的內容看,海外四經最早出現,其后是大荒四經,再后是海內四經,最后是海內經。
我同意王紅旗先生的觀點[1],根據海經所記敘內容的歷史時序,判斷海經各經的成書年代。
海外四經記敘的內容,截止于商代,因此,海外四經的成書,應在商代以前的某個時期。
海外四經記載的地域,大致在秦嶺、兩湖平原、江淮以南,河套、大青山以北,六盤山、賀蘭山以西,泰山、淮渦流域以東。
大荒四經記敘的內容,截止于周代,因此,大荒四經的成書,應在周代以前的某個時期。
大荒四經所記載的地域范圍,與海外四經大體相當。
海內四經的完成,應在春秋戰國時期,此時正是百家爭鳴的文化時期,對歷史文化的追溯,應是這一時期的文化潮流,而海內四經的內容,恰恰具有這樣的文化傾向。
海內,意即天下所有地域,因此,海內四經記載的范疇,涵蓋海外四經、大荒四經,似乎是對山經、海外四經、大荒四經的補充、說明。
因文字載體的保存問題(如布帛損壞或竹簡脫落),海內四經錯位、遺漏很多,造成了劉向父子修訂《山海經》時,不得不在海內四經后,附加了海內經。
海內經雜亂而涵蓋,似乎是對《山海經》海經部分(尤其是海內四經)做補充,而補充者又不太明晰此前成書的海經部分的準確信息,因此導致內容一沒有文字意義的上下延續和承接,二沒有地理方位和描述順序,與此前成書的海經部分,形成內容表達上的許多差異。鑒于此,它應當是西漢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及其兒子劉歆)校經傳,修訂《山海經》時,將因文字載體的保存問題而從海經部分(尤其是海內四經)脫漏下的那些文字,因無法考據原文在何處,而簡單地匯總成一篇,附加在海內四經后面的。
1.2、《山海經》的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
依據《山海經》對中國史前人文地理進行考證,必須確證《山海經》的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
一般以為,《山海經》是史前人類的口頭傳說,歷經千百年的歲月,在歷史時期完成著述,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不高,甚至沒有科學研究價值。
而我經過十余年研究,將最新考古(包括地理、氣候、人類文化)成果,與《山海經》相關記載對比,發現,《山海經》的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相當高(尤其是山經部分和海外四經、大荒四經部分)。以下就是無可辯駁的例證。
例1:
最新的歷史地理研究指出[2],冰川和冰緣遺跡的研究都證明,中國境內歷次冰期都沒有出現過大冰蓋,即使是在青藏高原上,也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大冰蓋。這是季風環流形勢下,冬季雖低溫卻干旱,夏季雖多雨卻高溫,都不利于冰雪積累之故。最后冰期結束后,與全球趨勢相應,中國境內氣溫回升,降水增多,至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時期達到最高峰,稱為仰韶暖期;其后,溫度在波動過程中降低,至公元1500—1850年期間達到最低點,成為世界性的“小冰期”;19世紀末以來,氣溫又略有升高。[3]如采取大理冰期年平均溫0℃線通過大連附近,此線向西延伸時將在北京以北接近密云(年平均溫10.9℃)的位置上通過,并沿西山、太行山麓而下,跨越漳河,然后折向潞沁高原。從30年代以來,太行山前以及北京西、北郊,關于冰川遺跡的報道日益增多,泥礫及帶擦痕礫石是主要內容。不論對成因最后作怎樣的解釋,實際物質的存在是客觀的,因而將京西北、太行山麓確定為冰期永凍土帶邊緣,是合理的。
對此,《山海經》的山經部分,只在西次四經的申首山、北次一經的小咸山、北次二經的狂山、姑灌山、北次三經的空桑山,有“冬夏有雪”的記錄,這說明,山經部分的形成時期,恰是仰韶暖期,本來就沒有形成大冰蓋的中國,唯在華北和西北的極少數地點,尚有一些冰期冰雪覆蓋的“痕跡”,而其記錄的“冬夏有雪”的地點位置,也符合中國北方冰期永凍土帶的地理緯度。
例2:
最新的歷史地理研究指出[2],內蒙古高原邊緣的半干旱地區內,從東北向西南,自大興安嶺西麓至鄂爾多斯,是另一條湖泊萎縮帶,殘存的許多湖泊,周圍都存在多層湖岸遺跡。其中岱海的最高湖水面高出現代湖面約30米,達來諾爾約高出69米。值得重視的是從這些高湖岸遺跡中取得的C年齡數據,與青藏高原上相應高湖岸取得的數據極為接近。
對此,《山海經》(尤其是西山、北山經部分)予以了準確的描述,記錄了河套地區的稷澤、泑澤、北方(直至大興安嶺西麓)的大澤、印澤、泰澤等一系列晚更新世、全新世的大型湖泊。
例3:
最新的歷史地理研究指出[4],自晚更新世冰期結束以后,海面發生世界性的迅速回升,但至距今8000年左右上升速度減低,以后的起伏幅度就比較小了。影響全新世海面升降的因素是復雜的,在我國特別要考慮到最新構造運動所起的作用,但就總的進退趨勢來說,與全新世氣溫變化過程是同步的。我國境內,遼南平原海侵達到盤山地區,渤海灣西岸達到寶坻、天津、文安、滄縣、海興地區,萊州灣西岸達到廣饒地區,蘇北達到里下河地區,蘇南浙北達到太湖、杭嘉湖、寧紹地區,以南在靈江口、甌江口、閩江口、九龍江口、韓江口、珠江口及海南島等地也都有海侵記錄。沉積物測年分析表明,海侵在距今5000—6000年時達到最高海面,高海面的高程高出現代海面3—4米;以后,總趨勢為海面緩慢下降,在下降過程中發生過距今4700-4000年、3800—3000年和2500—1100年等幾次小波動,出現高程1—2米的高海面,每次高海面都留下了貝殼堤之類的遺跡。這一波動過程與氣溫波動相符,但海侵所及的最大范圍和型式卻往往受構造變動的影響,最大的海侵在華北平原、蘇北平原及長江三角洲得以深入內地達二三百公里,正由于這些地區屬于構造沉降帶。
對此,《山海經》的東山經部分,予以了準確的描述,東次二~四經,描述的正是以上海侵的情景。
例4:
最新的歷史地理研究指出[4],最后冰期結束以后,全球處在氣溫升高的階段,北半球森林帶北移,山地樹線升高,冰蓋融化,海面迅速上升,約在距今5000—6000年左右,達到溫度高峰,正當我國仰韶文化時期,因而稱為“仰韶溫暖期”,估計華北地區年平均溫度高于現代2—3℃,冬季1月平均溫度高于現代3—5℃。當時竹類大面積分布在黃河流域,西安半坡遺址的動物遺骸中有食竹筍、竹根為生的竹鼠;山東歷城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炭化竹節;河南淅川下王岡遺址發現大量竹炭灰等,都是證明。而現代大面積竹類的生長范圍不超過長江流域。
對此,《山海經》的山經部分(無論是西山經,還是北山、東山、中山經),都有竹和漆樹、楠木的描述。
例5:
當代人類考古研究不爭的共識[5][6][7],自鄂爾多斯(河套地區)高原向南直到川西北、青東北的河、渭流域,是仰韶文化發生發展的主要地區,而代表仰韶文化早期的中國史前人類,正是由涇水以北的黃帝軒轅氏和渭水流域至豫西北的魁隗神農氏這兩大族群構成。
《山海經》的山經部分,對此予以了準確的描述。整個山經部分,只有西次三經和中山經記錄有神靈,而山經記載的這兩個地域,恰恰對應著考古學上的黃帝軒轅氏和魁隗神農氏在仰韶文化初期的生活地域。
證實《山海經》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的例證還有很多,限于論文篇幅,這里不再綴述。
因此結論:《山海經》關于史前(主要是全新世)的人文地理記載,除去歷史時期因文字載體錯亂(主要是竹簡脫落)造成的少量內容錯亂因素,如果經過科學縝密的勘誤,應該對當今的中國史前研究,具有很高的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
二、本文研究方法
2.1、以山定水,以水定山
《山海經》記錄的某些山水,當代可以確指,如下表
《山海經》記載的山、水當代確指的山、水
西次一經、太華山陜西華山
西次一經、嶓冢山陜西寧強嶓冢山
西次一經、天帝山甘肅天水麥積山
西次二經、皇人山、中皇山、西皇山青海湟水中下游
西次三經、泑澤黃河前套
西次三經、稷澤黃河后套
西次三經、三危山甘肅敦煌三危山
西次四經、白于山陜北白于山
西次四經、鳥鼠山甘肅渭源鳥鼠山
北次二經、王屋山山西垣曲王屋山
北次三經、燕山冀北、燕山
利用當代確指的《山海經》記錄的山、水,依據《山海經》記敘的山水間的方位、地脈關系,可以定位《山海經》時代地理的準確信息。
例如:
根據太華山、嶓冢山、天帝山、渭水的定位[8][9],可以通過方位、距離的計算推導,推算出西海應是川西若爾蓋濕地,以及所有西次一經所記載的山、水的大致地理位置。
根據涇水、河水、白于山、鳥鼠山的定位,也可以推算出崦嵫山即今日青海西傾山,以及所有西次四經所記載的山、水的大致地理位置。
2.2、連環舉證
利用相關記載的地理方位,對某地點的地理方位進行邏輯推演,再利用當代地圖,進行圖上推算,然后,再與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比照。
例如,對顓頊出生地若水的推斷:
海內經記載“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根據這三節記載,青水在華山附近,黑水在都廣野(成都平原)附近。[8][9]再根據地圖推算,則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的若水,必然是嘉陵江無疑。
然后,再根據人文地理的考古成果[10] [11],顓頊后裔白馬氏(即夏禹父系鯀氏)生活地域在川西岷江流域的茂汶盆地,推出結論:若水就是今日的嘉陵江上游地區。
2.3、相互舉證
根據《山海經》各部分記載的地域邏輯關系,進行邏輯推演。
例如,對西次三經中昆侖丘、河源的推斷:
根據北次各經對泑澤、稷澤的地理方位記載,與西次三經記載的泑澤、稷澤地理方位對比,可知泑澤、稷澤應在黃河河套地區。而西次三經記載的河水所潛的泑澤,正與河套地區的歷史地理情形符合。據此可推知,西次三經所記載的各山,就圍繞泑澤所在的河套地區,依次排列。
再根據北次一經對敦薨山的記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次三經所記載的昆侖丘,并不是現在青海地區的昆侖山,而是靠近今日呂梁山脈北段、河套前套,位于鄂爾多斯高原的一座山。
三、史前中國地理概貌
依據上述研究方法,結合當代人文考古、史前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參考了王紅旗先生對西次三經昆侖丘的定位,本文認為,《山海經》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學信度和歷史效度的史前(這里指晚更新世——全新世早期)中國人文地理著作,通過對《山海經》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認知史前中國北方(包括中原)地區人文地理。
下面,給出十幾年研究的部分結論,主要是一些史前中國人文地理的關鍵點和焦點,供中國史前學研究借鑒。
3.1、山經
北山經所記載的地域是:西河(黃河從內蒙土默川到陜西風陵渡段)以東,陰山山脈以南,南河(黃河從陜西風陵渡到河南濮陽段)以北,東河(黃河從河南濮陽到天津東南古黃河口段)以西。
西山經所記載的地域是:西北到新疆與甘肅交界的天山末端、羅布泊,西到青海的湟水上游,西南到青海的西傾山,東到西河,北到內蒙狼山,南到陜西米倉山、四川若爾蓋。
中山經所記載的地域是:西到四川的岷山,南到湖南的洞庭湖地區,北接秦嶺、南河,東到江淮。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地域不包括四川盆地和洞庭湖以東的長江南岸地區。
《山海經》的山經部分,北山經記載地理方位最準確,西山經除西次三經外,記載的地理方位也很準確,中山經的山序與地理方位的順序雜亂,且將原來的中次一經已丟失,而將原屬北次二經的部分山編成中次一經。
經過長期的研究,我發現:
問題一:《山海經》山經部分所記載東山經,地理方位基本準確,但情形卻是七千年前海侵年代的景象,而且各山的距離、方位記載多屬主觀直覺,而非實測結果;
問題二:《山海經》山經部分所記載南山經,地理方位記載很虛,似乎這一部分的記載內容,很大部分是通過間接方式獲得,沒有經過核實,因此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問題三:《山海經》山經部分,只有西次三經和中山經記載有神靈。
問題四:西次三經所記載的各山,起點在陜西境內白于山東南靠近山西處,沿西河、北河(黃河前套、后套間的河段)一直過賀蘭山、祁連山,到達新疆境內的天山末端、羅布泊地區,其方位記載很虛,而神靈記載卻很實,且西次三經脫離西山經的地理方位排序,明顯與西次一、二、四經分離,似乎是山經作者的一種有意識的撰寫行為,隱含著某種現實寓意。
3.1.1西山經
西次一經:錢來山在陜西潼關附近,太華山就是華山,符禺山在陜西羅敷附近,羭次山在陜西高塘附近,時山在陜西葛牌附近,大時山在陜西太白山,嶓冢山即陜西寧強嶓冢山,天帝山應是甘肅麥積山,皋涂山在甘肅理川附近,騩山在川西若爾蓋附近。
研究西次一經發現:西山經所謂赤水,就是黃河從青海積石山到寧夏銀川段,盼水即甘肅洮河,西海即川西若爾蓋濕地。
西次二經:鈐山在陜西韓城附近,泰冒山在陜西合陽附近,數歷山在陜西銅川附近,龍首山在甘肅彭陽,鳥危山在甘肅會寧附近,皇人山、中皇山、西皇山在青海境內的湟水岸邊,萊山即青海的托來山。
研究西次二經發現:西山經所謂赤水,就是黃河從青海積石山到寧夏銀川段,鳥危水就是甘肅祖歷河,楚水就是陜西石川河。
西次四經:陰山應在陜西黃龍到韓城間,鳥山在陜西黃龍附近,上申山在陜西南泥灣,號山在陜西羊馬河附近,孟山在陜西新城堡附近,白于山即陜西白于山,邽山應為甘肅華家嶺附近,鳥鼠山就是甘肅渭源鳥鼠山,崦嵫山就是青海西傾山。
研究西次四經發現:西山經所謂洋水,似指甘肅葫蘆河。
西次三經:崇吾山應在陜西佳縣附近,不周山應在內蒙準噶爾旗到山西平朔間,泑澤在內蒙黃河前套(土默川盆地),鐘山、槐江山應在內蒙烏拉特前旗地區,昆侖丘應在陜西鄂爾多斯高原西南方,羸母山似是寧夏賀蘭山,玉山似在甘肅冷龍嶺或烏鞘嶺,長留山似在甘肅龍首山或合黎山,三危山就是甘肅敦煌三危山,泑山應為甘肅馬鬃山,翼望山應在新疆羅布泊地區。
研究西次三經發現:西次三經脫離西山經的地理方位排序,越過二經到四經間的正常排序規定的地理方位,直接放在了四經以北以西地域,明顯與西次一、二、四經分離。三經所記載地域的各山,不論是方向還是距離,都是模糊不清,若按一、二、四經的方向和距離概念,依據三經所給的方向和距離來排列三經各山,則不周山已經接近陜西鄂爾多斯高原西北方,峚山和鐘山的位置就無論如何也排不到前套和后套,即使我們能將峚山和鐘山的位置排到前套和后套,其以后的槐江山、昆侖丘也將遠離赤水(黃河從青海積石山到寧夏銀川段)以東的陜西鄂爾多斯高原,進入內蒙狼山以西的阿拉善高原,這顯然不符合現代考古研究考證的史前中國西部(尤其是西北方向)各氏族生活地域的實際情形。
因此,可以肯定,《山海經》的山經部分,是有意把西次三經從西山經中單獨列出,以示三經與一、二、四經的不同,以示三經所載內容的神秘與崇高。
從現有的史前地理研究成果看,在地球最近一次冰河期的最冷期(2.2萬~1.3萬年)以外的時期,陜西鄂爾多斯高原到內蒙的河套地區,曾經是個水草豐美、氣候宜人的地方,這里曾經有3萬5千年左右的河套文化(也稱鄂爾多斯文化),是中國北方晚期智人最早出現的地方。
從現有中華史前人類研究的階段成果看,黃帝軒轅氏族群就發祥于涇水上游,在進入渭水流域前,主要游獵生活在涇水以北到河套間的陜西鄂爾多斯高原。
因此,西次三經這樣與西次一、二、四經不同,也說明了《山海經》山經部分的創作者,與天黿軒轅氏族群有著一定的淵源,可以推斷,他(或她)要么是與天黿軒轅氏族群有著親密關系的人,要么就是天黿軒轅氏族群的族裔。
他有意把西次三經從西山經中單獨列出,以示三經與一、二、四經的不同,他有意把西次三經所記載的地理方位和實際地理方位情況造成差異,以顯示西次三經所載地域的神秘與崇高。
他這樣做,恰恰表達了這樣的一組信息:從涇河以北到河套間,曾經是天黿軒轅氏族群發祥、生活過的一個地域。這里眾多的氏族部落(鐘山的燭龍、鼓,槐江山的英招,軒轅黃帝的定居地(圣城)昆侖丘,天黿軒轅氏族群的親族陸吾,羸母山的長乘),都曾經拜伏在天黿軒轅氏族群周圍。從賀蘭山向西的各氏族(玉山的西王母,三危山的三青鳥),也曾與天黿軒轅氏族群發生過親密的關系。
3.2、海外四經
海外四經記載的地域,大致在秦嶺、兩湖平原、江淮以南,河套、大青山以北,六盤山、賀蘭山以西,泰山、淮渦流域以東。
海外南經:結匈國應在岷山附近,比翼鳥應在大巴山西段,畢方鳥應在秦嶺東段,讙頭國應在武當山地區,三苗國在兩湖平原附近,昆侖虛在大別山,壽華之野在大別山東麓靠近長江的地方,狄山就是東山經里的岳山,在淮北與淮南間。南方祝融,指祝融八姓,在江漢地區、江淮地區。
海外西經:滅蒙鳥在白龍江上游,大樂之野在洮河上游,常羊之山在秦嶺西段,丈夫國在涇水上游以西,巫咸國在六盤山地區,軒轅國在銀川附近的鄂爾多斯高原,諸夭之野在銀川盆地,白民國在賀蘭山以西,西方蓐收,指少昊氏族群東遷后,留在祁連山以西地區的一個分支。
海外北經:鐘山應是狼山,相柳應在鄂爾多斯高原東北,夸父北飲大澤,應在河套地區,務隅之山應在大青山南麓,北方禺強,在今山東半島、遼東半島間的渤海沿岸。
海外東經:嗟丘,在蘇南或安徽南部,青丘國,在安徽懷遠附近,湯谷、扶桑在山東沂、沭流域。東方勾芒,少昊氏族群在華東地區的一個分支。
3.3、大荒四經
大荒四經所記載的地域范圍,與海外四經大體相當。
除了比海外四經記敘得多而詳細,大荒四經還有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大量描述帝俊的文字,尤其是大荒東經。似乎描述帝俊的余興未盡,兼及帝顓頊的文字也相對較多。這是否說明:大荒四經的作者和帝俊、帝顓頊有著特殊的感情?
古史傳說中,帝顓頊將天帝權位傳給帝俊,帝俊為黃帝增孫,顓頊為黃帝兒子昌意的孫子,因此,顓頊與帝俊的權力承接,因這種親緣關系而成立。
按大荒東經,帝俊似乎出自東方(即東夷地區),而黃帝軒轅氏族群主要在西北和中原,東方只有認軒轅黃帝為父、改羸姓為姬姓的少昊青陽氏和海隅民族禺號,難道帝俊就是青陽氏的后代帝嚳?
如果這樣,大荒四經展示的,就是大汶口文化向各地的龍山文化演進時期的人文地理。
3.4、海內四經
海內四經的完成,應在春秋戰國時期,此時正是百家爭鳴的文化時期,對歷史文化的追溯,應是這一時期的文化潮流,而海內四經的內容,恰恰具有這樣的文化傾向。
海內,意即天下所有地域,因此,海內四經記載的范疇,涵蓋海外四經、大荒四經,似乎是對山經、海外四經、大荒四經的補充、說明。
因文字載體的保存問題(如布帛損壞或竹簡脫落),海內四經錯位、遺漏很多,造成了劉向父子修訂《山海經》時,不得不在海內四經后,附加了海內經。
因此,研究借鑒海內四經尤其是海內經的內容資料,必須首先研究參照山經、海外經、大荒經的內容。
1、王紅旗.經典圖讀山海經[M].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08第一版
2、張蘭生.中國環境演變研究的進展[J].地理科學,第10卷,第3期,1990年
3、張蘭生.中國晚更新世最后冰期氣候復原[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0第1期
4、張蘭生.中國自然地理環境的形成、演變與地域分異[C]
5、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M].三聯書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122頁
6、許順湛.陜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啟示[J].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7、孫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J].考古學報,1998年第4期
8、地圖科學研究所.中國地形(立體地圖)[Z].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01第一版
9、中國分省地圖冊[Z].中國地圖出版社,2005
10、陳衛東,王天佑.淺議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文化[J].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11、張強祿.白龍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的初步研究[J]. 考古,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