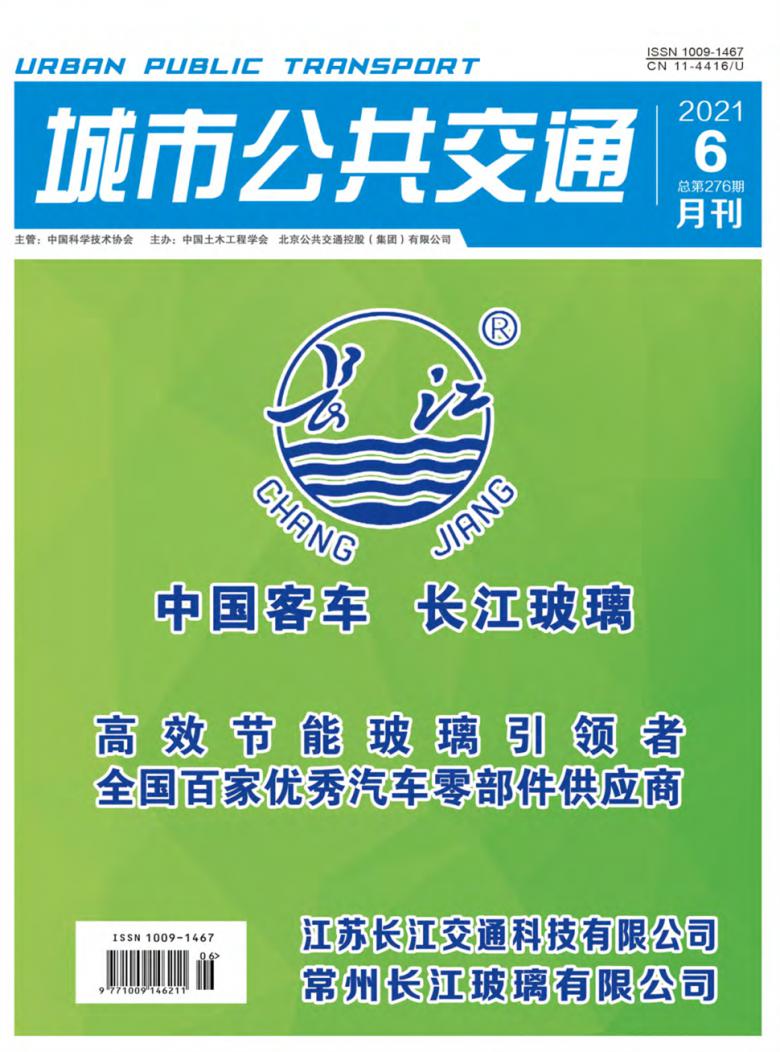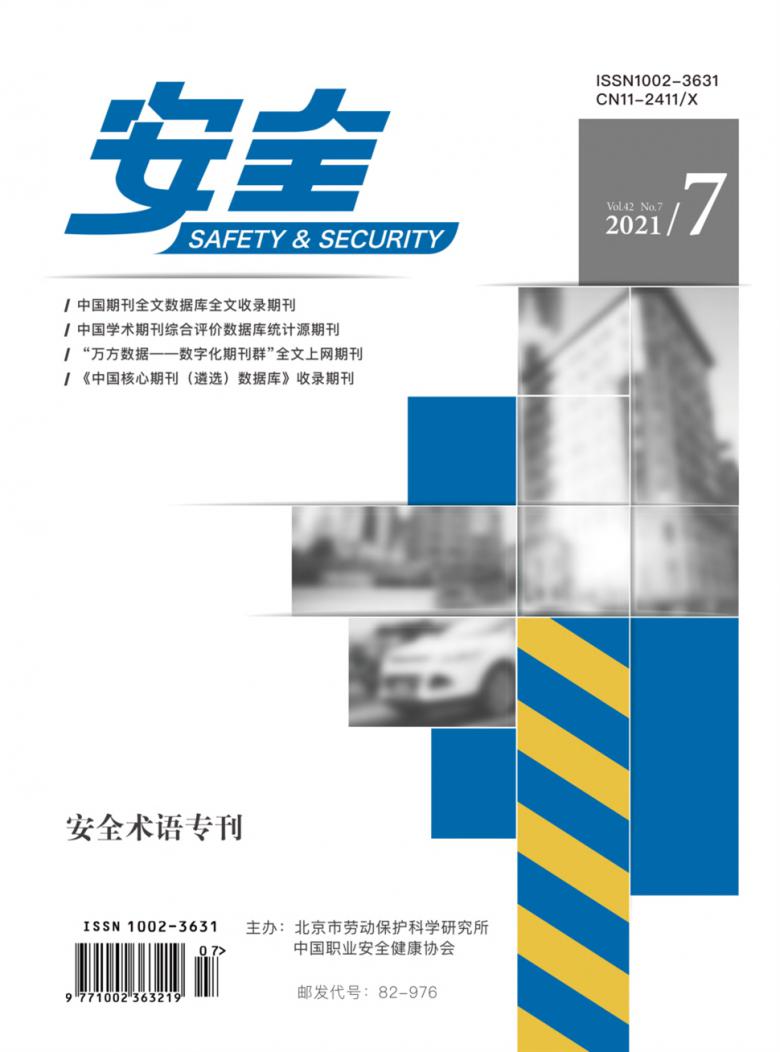雇主團體與勞資關系——近代工商同業公會與勞資糾紛的處理
佚名
【作者簡介】魏文享,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歷史學博士。(湖北武漢430079)
【內容提要】近代工商同業公會與工會都是勞資分立的產物,二者在組建之后均加強了各自階級的組織整合,也使勞資關系更具有階級政治的特點。不過,工商同業公會作為行業性的雇主組織,并非如一般所認為的與工人及其工會處于完全對立的位置,在政府的勞資處理機制、勞資合作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摘 要 題】社會·經濟
【關 鍵 詞】雇主團體/勞資關系/同業公會
【正 文】
近代之勞資關系一直為政治史研究的中心議題,早期在“階級斗爭”的視野之下,主要關注的是勞資矛盾及政黨領導下的勞工運動。在此類研究之中,對于資本家、資產階級的政黨、政府、團體剝削壓制工人階級的行為給予了足夠的抨擊。在抨擊的對象之中,既包括資產階級性的商會組織,也包括國民黨管制下的工會。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近代中國政黨、政府、工人、資本家之間的復雜關系有了更為客觀的認識,既研究其矛盾和沖突,也關注其協調與合作。在雇主團體方面,已有較多學者分析了商會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有學者關注到“資產階級”性的商會在解決勞資糾紛方面的作用。不過,對于行業性的工商同業公會在近代勞資糾紛處理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還缺乏全面認識,尚有探討的必要(注: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奇生:《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20世紀30年代一例勞資糾紛的個案分析》,《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徐思彥:《20世紀20年代勞資糾紛問題初探》,《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朱英、馬敏、彭南生、鄭成林、魏文享等合著:《近代同業公會與當代中國的行業協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日]小浜正子:《南京國民政府の民眾掌握——上海の工會と工商同業公會》,《人間文化研究年報》(日本ず茶の水女子大學),1991年第14號;[美]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劉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彭南生:《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馬軍:《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業同業公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魏文享:《近代工商同業公會的政治參與》,《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
本文以檔案和報刊資料為基礎,試圖從同業公會之興起及其在勞資關系處理過程中的作為,來分析作為雇主團體的同業公會與階級政治的復雜關系。本文在分析的過程葉,試圖將同業公會、職業工會及政府同步納入研究視野,以三方互動的格局來演示同業公會在勞資沖突及勞資協調機制中的復合角色。
一、勞資分立與勞資團體之興起
近代工商同業公會作為新興的行業組織,其產生的途徑有二:其一由傳統的行業性會館、公所轉變而來,其二為新興行業自主組建。不論何種方式,其興建之因大體相似,包括有行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整治行業經營秩序、抵制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等多種因素。所謂行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際上不僅包括生產方式的革新,也包括生產關系的變革,勞資關系之變化當然蘊含其中。新興行業之同業公會大多由企業主自主組建,雇工已明顯被排除在外,勞資分立之勢已現(注:參見魏文享:《近代工商同業公會的社會功能分析——以上海、蘇州為例(1918-1937)》,章開沅主編:《近代史學刊》2001年第1輯。另有相關論著參見魏文享:《近代工商同業公會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如要探明勞資分立與同業公會興起的內在關系,還需分析傳統的會館、公所在晚清民初之蛻變、分化。
明清之際全國的都市邑集大都設有各類會館、公所。據彭澤益統計,自1655年到1911年間,漢口、蘇州、上海、北京、重慶、長沙和杭州等地區有工商會館、公所共約598個,其中手工行業占49.5%,商業行幫占50.5%(注: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下),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907-908、985-991頁。)。此類行業性的會館、公所多由小作坊主或業主集合組建,各店的伙計、學徒在其中難有話語權。不過,在大多店鋪之中,店主與伙計、學徒均一同工作,彼此境遇相差并不為遠。伙計、學徒依各業行規,在達到一定期限之后也可以自主開業,但須借助于會館、公所方能繼續其職業生涯。可以說,在會館、公所之行業管理體制下,業主與伙計、學徒有著共同的利益。此外,在會館、公所之中,店主與店主、學徒與學徒、店主與學徒之間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血緣、地緣和鄉緣關系,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緩和相互之間的對立情緒。此種業緣之外的情感聯系不僅存在于會館、公所之內,也存在于會館、公所之外,并使中國各地之行業經營者帶有相當明顯的地域特色,形成頗具規模的商幫(注:關于商幫的研究請參見:張海鵬等:《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陶水木:《浙江商幫與上海經濟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美國學者裴宜理在《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一書中對地緣關系于職業工會整合之影響有所分析。)。再加上伙計、學徒人數有限,亦極為分散,因此或與業主群體有工薪、待遇等方面的沖突,也難以真正擴大。因此,得益于傳統會館、公所的“復合結構”,業主與伙計、學徒尚可共存于一會之內。
晚清民初,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規范行業經營秩序、抵御外資入侵的需要,在政府法令的規范下,大量會館、公所改組為同業公會。據虞和平先生統計,上海、蘇州、漢口和北京的行會在1840年之前成立的只占1912年后實存總數的28.7%;1840-1903年間成立的行會數則占到總數的48.7%。但到1904年后伴隨著商會及新型行業組織同業公會的大量建立,行會的增長量已大為減少(注: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在傳統行會基礎上分轉合并而來的工商同業公會占絕大多數,而完全新成立的同業公會由于新興行業的有限所占份額并不大。據1930年統計,上海市“總計改組合并及新組織之同業公會數目共得一百七十個,分析之,計改組者一百四十個,合并者由五十八個合并成二十三個,新組織者七個。”(注:《商業月報》第10卷第7號,1930年。)在會館、公所向同業公會轉化的過程中,雇主與工人間的階級分野也逐漸明晰起來。雇主從勞動生產中分離出來,為了擴大再生產,不少行業以契約形式招募工人。近代工業“一變從來的形式,向之師傅為一業之首領者,今而變為工作之經理矣,向之以伙計與徒弟為工作人者,今則變為自由締結契約之勞動者矣”(注:王清彬等:《中國勞動年鑒》第一次,第二編,“勞動組織”,第4頁。),這正為勞資分化在行業組織內部的體現。
在工商同業公會自主發展階段,同業公會雖然實際上與會館、公所一樣也是業主的集合體,不過,對于雇工仍然沒有明確予以排除。1918年,北京政府頒布的《工商同業公會規則》規定,工商同業公會之發起,須由同業中3人以上資望素孚者發起,同一區域內之工商同業者設立公會,以一會為限。在《工商同業公會規則施行辦法》中,要求將同業者工商號及經理人姓名表冊送交官署審核。該規則對于手工勞動及設場屋以集客之營業排除在外,對于原有之會館、公所均得照舊辦理。因此,該規則雖確定了工商同業公會及會館、公所之合法地位,但對于其成員僅以同業為限,對于會員并未明加限定。1927年11月,與南京國民政府同時對峙之北京北洋政府頒布了《工藝同業公會規則》,規定“凡屬機械及手工之工廠、作坊、局所等,操同一職業者,得呈請設立工藝同業公會”(注: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下),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907-908、985-991頁。)。據此規定,工廠之普通工人、技工或師傅均可成立工藝同業公會。不過,這一規則最終未得實施。在北京政府時期,雖然工商同業公會有關法規未將工人排除在外,但也只是在形式上維持了會館、公所時期的組織架構,并不意味著工人在同業公會之內的權利有所擴大。如果結合此一時期職業工會的發展情況來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實際上的勞資分立及勞資團體分別發展的趨勢已不可避免。
在傳統會館、公所向同業公會的轉化過程中,業主與師傅依然對同業公會保持著控制權,而職業工人要求另組職業工會的情況則不斷增多。不論是在新興行業或者傳統行業,隨著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的數量和規模的擴張,工人的數量和集中程度也大為增長。在近代結社意識的影響下,不少行業的工人聯合起來另組工會或新的公所。在蘇州,成立于道光二年的云錦公所,原本為蘇州絲織業共同的行會組織。至同治年間“重建”的云錦公所,已由蘇州絲織業的全行業組織向紗緞莊“帳房”的同業組織演變,其后,“機匠一幫設立霞章公所”,攬織機戶和機匠開始從云錦公所中分化出來。據《重修霞章公所碑記》記載:“霞章公所者,吳縣絲織產業工會之基礎也。始創于民國紀元前二年”,亦可明其性質(注:蘇州市檔案館等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頁。)。在有些地區,因雇主與雇工之組織并存,分稱為“東家行”、“西家行”。如佛山大材大料行中東家組織稱廣善堂,西家稱敬業堂;佛山漆盒行中東家稱同志堂,西家稱彩聯堂;佛山朱砂年紅染紙行中,東家稱同志堂,西家稱至寶祖社。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工人運動趨于高漲,職業工會之成立不斷增多。1920年5月,《新青年》雜志曾對各地勞動狀況進行過調查,其中關于上海、南京兩市的雇工行會記載較詳細,現將有關情況列表如下:
上海、南京兩地行會中分化出來的雇工組織狀況表 地區 行業 工人人數 行會名稱 備注
成衣業 47000 軒轅公所 工人與店家共同的組織
理發業 不詳 羅祖公所 每年逢羅祖生日全行業都要停業一天
醬業 2000 醬業伙友聯誼會 成立一個月,被資方分化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