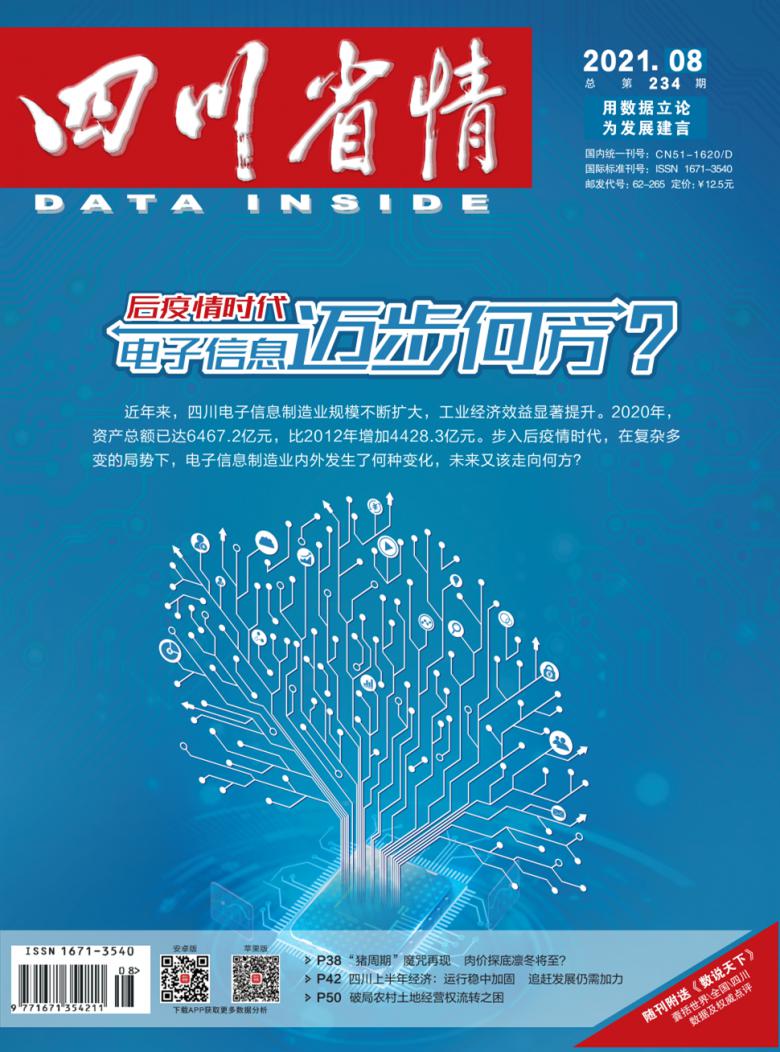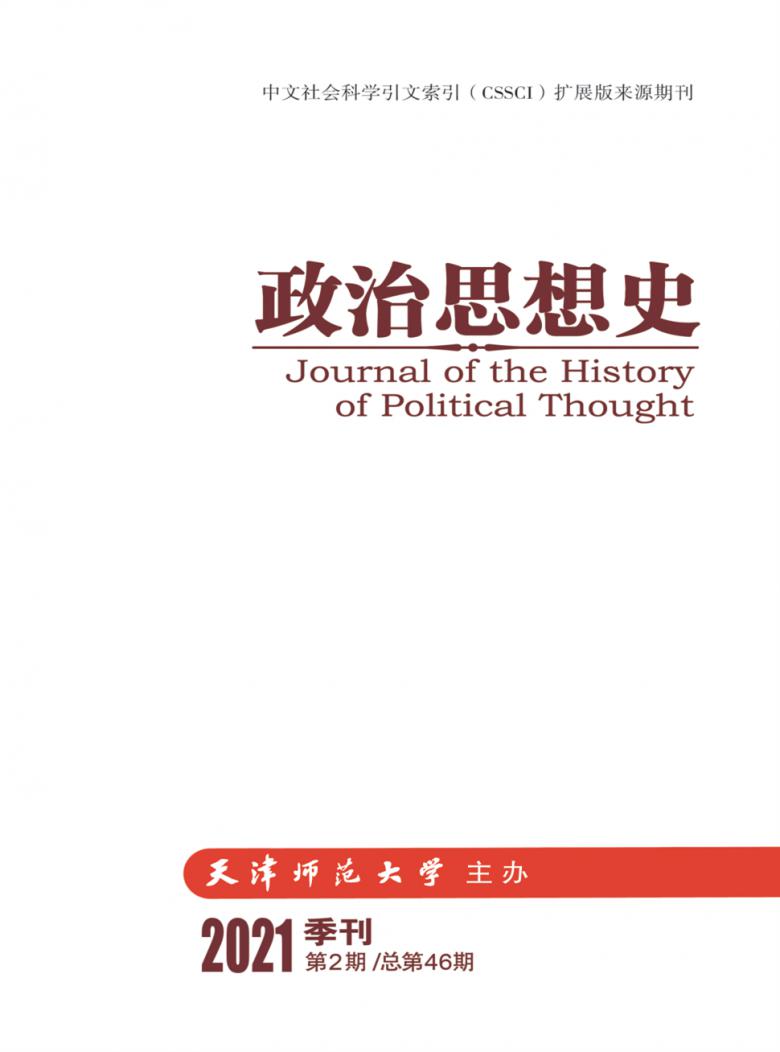先秦秦漢以太原為中心的交通線路
薛瑞澤
太原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從先秦以來即是北部邊境的戰(zhàn)略重鎮(zhèn)。為了充分發(fā)揮太原的戰(zhàn)略優(yōu)勢,先秦秦漢政府對以太原為中心的交通線路關注有加,相繼開辟了不同方向的交通線路,形成了供給便利的交通運輸線,為北方地區(qū)的社會安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先秦交通線路開辟的概況 以太原為中心交通線路的開辟始于先秦時期。《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其勢力“北逐葷粥,合符釜山”。《集解》引《地理志》言“葷粥,居于北蠻”。黃帝部族的勢力已經(jīng)達到今山西省、陜西省北部地區(qū),太原一帶當有道路可通。大禹治水時曾經(jīng)到過太原一帶,《尚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師古曰:“太原即今之晉陽是也。岳陽在太原西南。”因而有“禹鑿龍門,通大夏”之說,[1]《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史記》卷二《夏本紀》:“禹于是遂即天子位。”《集解》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從平陽到安邑、晉陽之間都有往來的線路,說明遠古時期的先人們即對以太原為中心交通線路的重視。吳起曾經(jīng)對魏武侯說:“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2]《正義》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說明夏朝的勢力已遠達晉陽西北一帶。 殷商時期,太原附近道路的開辟沒有更為明確的記載,但從相關史料可以推知,因為對北方少數(shù)部族的戰(zhàn)爭,商王朝的軍隊曾經(jīng)抵達過太原。《易經(jīng)•下經(jīng)》:“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漢書》卷二十七《五行志中之下》:“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序》:“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鬼方活動于今晉北一帶,為了抵御鬼方對中原地區(qū)的騷擾,商王朝的軍隊曾經(jīng)達到山西的中北部地區(qū)。 西周建立后,即開始對太原一帶進行控制。《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載,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張守節(jié)認為“在晉州平陽縣”。到其子燮改為晉,稱晉侯,遷往晉陽。《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筑也。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墻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也。”[3]《史記》卷四《周本紀》載,周厲王暴虐政治,引起國人暴動,“厲王出奔于彘”。《集解》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正義》《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后改彘曰永安。從鄗奔晉也。”說明從西周都城鎬京至彘(今山西省霍縣)有道路相通。上述史實說明太原在西周初年已經(jīng)與鎬京建立了交通往來的關系。 春秋時期全國道路的形勢更為發(fā)達。以洛邑為中心全國性道路網(wǎng)的建立,將北方地區(qū)重要交通樞紐的晉國晉陽納入其交通序列中來,晉陽的對外交通開始繁榮起來。《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載,齊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平定晉國內(nèi)亂以后,與諸侯盟會,曾經(jīng)說:“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正義》:“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意即齊國的軍隊已經(jīng)達到晉陽一帶,究其實齊桓公的軍隊只到達晉國高粱(今山西省平陽縣西南),但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當時已經(jīng)有了從齊國到達晉陽的線路。《春秋》載,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羊傳》與《谷梁傳》均作“大原”。“大原,晉陽縣”。晉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趙簡子(趙鞅)要求邯鄲大夫午歸還他送給的衛(wèi)人五百家,并打算“吾將置之晉陽”。因邯鄲午食言,乃囚之晉陽。是年十月,范、中行氏聯(lián)合討伐趙簡子,趙簡子逃奔晉陽,晉定公率人包圍晉陽。十一月,范、中行氏被打敗,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4]這段史料雖然反映的是春秋末年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階級斗爭的史實,但由之可知,從晉陽到邯鄲和絳(今山西省曲沃縣西南)之間都有了交通線路。是后,晉陽成為趙國的軍事堡壘。晉出公死后,知伯掌握晉國大權(quán),“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5]以上事實說明從太原到邯鄲和齊國都有了往來的線路。 從晉陽南行可以直達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市)。從洛邑過黃河,有一地名曰陽樊,周襄王十二年(公元前640年),王子帶發(fā)動叛亂,周襄王求救于晉,時晉文公剛剛周游列國后急于取得威望,聽從了謀臣趙衰的建議,“三月甲辰,晉乃發(fā)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nèi)陽樊之地”。[6]《集解》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史記》卷四《周本紀》《正義》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樊、溫、原、攢茅之田也。”從晉陽可以直接發(fā)兵洛邑,說明其間的道路是暢通的。《左傳•閔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東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縣東南。說明有從晉陽到皋落的道路。從皋落到絳,然后沿汾河河谷經(jīng)昆都(今山西省臨汾市)、彘、中都、祁、魏榆直達晉陽。[7]晉人在這一線路上活動的史料史書中時有披露。如《左傳•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是晉國城邑。《左傳•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zhí)諸中都。” 戰(zhàn)國時期以太原為中心交通線路的開辟與統(tǒng)一戰(zhàn)爭有著密切的關系,并且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伐取趙中都、西陽”。《正義》引《括地志》云:“中都故縣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陽即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東十里。《地理志》云西都、中陽屬西河郡。”此云“伐取趙中都西陽”,說明從晉南沿汾水可以直達晉陽。趙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288年),“秦取梗陽”。《集解》: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xiāng)。與杜預所據(jù)小別也。”秦國的軍事力量已經(jīng)深入到了晉陽一帶,其線路的暢通當屬必然。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司馬梗北定太原”。秦莊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初置太原郡”。[8]至此,晉陽入秦國版圖。隨后又攻取了魏榆、狼孟等地。秦始皇即王位,“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秦王政八年,“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雖然嫪毐不居于封國,但太原與咸陽便利的交通是他得以收取賦稅的重要保障。秦始皇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狼孟在太原北。十九年,“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9]說明秦始皇是沿著汾河河谷,然后渡過黃河回到咸陽的。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分天下三十六郡,其中有太原郡。在瑯邪臺石刻中有“六合之內(nèi),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說明秦朝的面積之大。漢代賈捐之曾說秦朝“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10]說明太原一帶是秦朝北部邊境的軍事重鎮(zhèn)。 秦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中太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從常山可直達太原,戰(zhàn)略地位非常重要。陳勝派武臣與張耳、陳余進攻河北,渡黃河以后,武臣自立為趙王,分三路攻城掠地,其中李良進攻常山,李良占領常山后,“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11]石邑在常山境內(nèi),應劭曰:“井陘山在南。”師古曰:“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這是從常山進入太原的必經(jīng)之地。漢三年,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控制了井陘,即可“以令于趙,脅燕定齊”,韓信就是這樣做的。[12]廣武君李左車對成安君陳余談及井陘的形勢時說:“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然而成安君不聽,結(jié)果趙被韓信打敗。[13] 綜觀戰(zhàn)國時期以太原為中心的交通線路的開始稠密起來。從洛陽渡過黃河,經(jīng)野王(今河南省沁陽市)達上黨郡(今山西省長子縣),經(jīng)屯留、銅醍至祁再到魏榆,達太原郡。這是南線。《戰(zhàn)國策》卷十七《楚策四》載汗明對春申君說:“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馬拉鹽車上太行,說明沿太行山的南北道路已經(jīng)開辟。向東經(jīng)魏榆、馬首可通燕國。這是東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