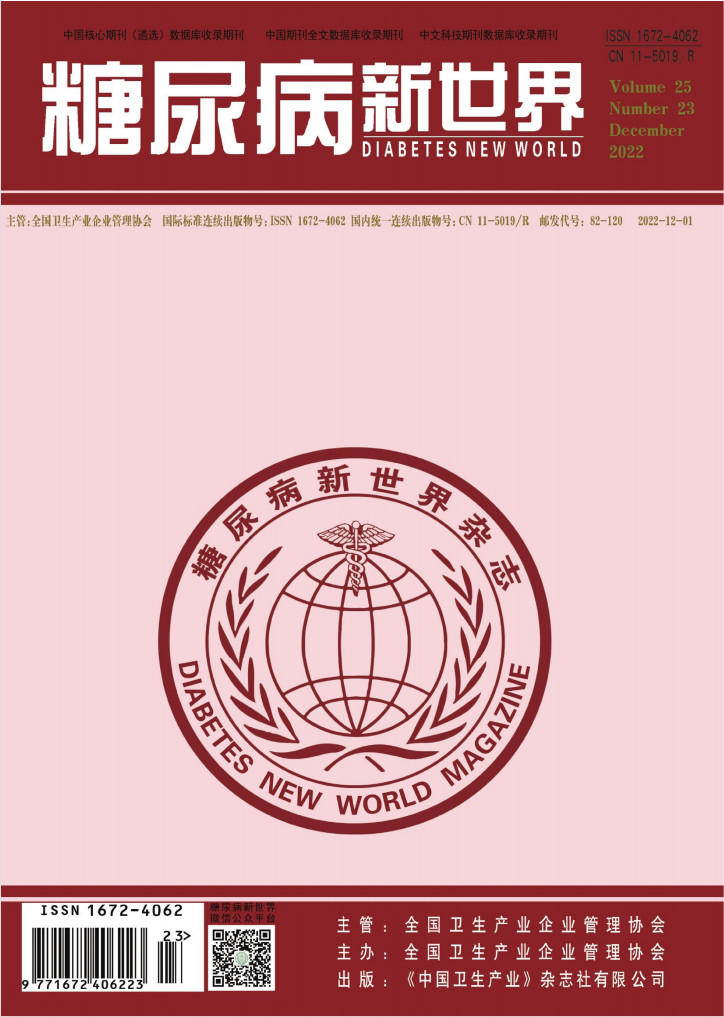淺析我國刑事檢察制度概述
王宏
論文摘要 檢察制度是現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全與否事關一國司法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國的檢察制度移植于西方國家,肇始于清末法律改革,在歷史長河中的發展無疑是短暫的。本文通過研究檢察權的涵義,檢察制度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具有的相應功能對我國的檢察制度進行了系統的介紹。
論文關鍵詞 檢察權 檢察制度 起源與發展
一、刑事檢察權的涵義
刑事檢察權是檢察制度貫徹落實的前提,直接關系到檢察改革的大局,因此,研究刑事檢察制度首先要明確刑事檢察權。檢察權在刑事領域是指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刑事案件的公訴權,國家司法機關適用法律的情況進行監督的權力。總而言之,檢察權是追訴犯罪和糾正錯誤適用法律的一項獨立的國家權力。 我國憲法從法律事實的角度明確規定了檢察權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相關的基本法也對檢察權進行了闡述。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檢察權無外乎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刑事公訴權。檢察機關對刑事案件的偵查結果進行審查后決定是否提起公訴以及是否進一步派員出庭。二是職務犯罪偵查權。為有效維護國家權力行使的廉潔性和正當性,國家公職人員的職位犯罪由檢察機關進行偵查,具體偵查對象的范圍包括了刑法分則第八章的貪污賄賂犯罪,第九章的瀆職犯罪,第四章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虐待被監管人、報復陷害、破壞選舉等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犯罪,以及由省級以上的人民檢察院決定立案偵查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三是刑事訴訟監督權。監督的權力是檢察機關活動的主線。
二、刑事檢察制度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古代一直延續行政監察兼理司法監察的傳統,因此始終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檢察制度,在清朝末年面臨著政治統治危機,此時的封建政權迫于壓力進行修律改制,在各級審判庭內附設同級的檢察庭作為各級檢察機關,負責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監督審判和監視判決執行。在中國的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審判權與檢察權的分離。這一司法制度的構建影響深遠,后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臺灣地區對這一檢察制度進行了繼承與發展。隨著人民革命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的檢察制度不斷完善,檢察機關的職權包括了刑事案件的預審、提起公訴和出庭支持公訴。1949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頒布,有中國特色的檢察制度基本正式成形,1950年9月4號,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于建立檢察機構問題的指示》。這一黨內文件對檢察機關的性質給予了明確規定“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同時也彰顯了黨對檢察制度的高度重視。1951年普遍建立各縣檢察署。1954年,中國第一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了檢察權配置的一些基本原則和程序,配置了一般監督權、偵查、審判以及監所勞動監督權,改檢察署為檢察院,正式脫離行政機構,形成“一府兩院”格局,是檢察制度完善的一項重大改革。但是在接下來的十年的文化革命期間,檢察制度形成虛設,甚至取消了檢察機構,冤假錯案成堆,中國的檢察制度面臨著巨大的挑戰。1978年至1988年是我國檢察制度的恢復重建階段,這一時期主要從檢察機關的屬性、基本職權、機構體系等宏觀層面進行探索。197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頒布,揭開了我國檢察制度嶄新的一頁,再次明確了檢察機關的性質是法律監督機關,并在此基礎上取消了檢察院的一般監督權,深入明確了檢察機關實行雙重領導體制。1983年9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決定》,至此,有中國特色的檢察權配置基本定格。這一時期有關檢察制度的法律規定不但過于粗獷,司法實踐中操作價值不大,而且檢察制度的發展帶有明顯的依賴性特征,缺乏內在的積極的自主性發展主要是依賴憲法、組織法等基本立法的引導。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檢察權的完善發展步入了快車道。尤其是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對檢察制度的規定進行了重大的調整,加強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范圍、手段和程序,調整了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范圍以及突出對職務犯罪的監督,廢除了免于起訴制度建立了酌定不起訴制度,強化了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控訴職能等。 我國的檢察制度的誕生是舶來品,不是土生土長的,百年來進行了三次重要的法律移植,清末對職權主義特征的大陸法系檢察制度的移植—新中國對前蘇聯一般的監督模式的照搬—90年代對當事人主義的英美法系檢察制度的借鑒,我國現行的檢察制度兼具了三大法系的特征,具有獨特的混淆的性格。這種移植如果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與時代背景也不會長久發展,不斷完善,因此這一制度的移植本身包含了對中國傳統的尊重,對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認識,因此我們可以明確,中國的檢察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法律監督模式也是同我國的國體和政體相配套的。
三、刑事檢察制度的功能
(一)追訴犯罪的功能 刑事案件的公訴權是檢察機關的立命之本,檢察制度的研究偏離了檢察機關這個基本的角色定位,現代法治國家的檢察機關只可能是有其名而無其實。檢察機關追究刑事犯罪的公訴權具體是指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或者涉及有關爭議事項的被告人或者被告提交法院審判并作出裁決的一種訴訟職權,主要包括了決定、提起公訴權、支持公訴權、不起訴決定權或者起訴裁量權。檢察機關刑事公訴權的行使的價值可以體現在以下的四個方面:一是公訴職責處于同犯罪較量的第一線,對有犯罪事實并且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絕不姑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應有的懲罰,成為社會不良現象的凈化器。二是檢察機關公訴權的行使體現了被害人伸張正義的心聲,幫助被害人舉證、控告,甚至出庭,有效的保護了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三是檢察機關在行使公訴權,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的同時,張揚正義,懲罰邪惡的同時本身更具有了一種威懾力量,人們在在進行違法行為的同時必須要考慮到檢察機關的司法權威,公訴權的行使可以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再現了社會秩序保護神的形象。四是檢察機關的公訴處于訴訟監督的前沿陣地,承擔著對刑事訴訟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的職責,不但是偵查程序的審查把關者,又是審判程序的啟動者和訴訟程序的糾錯匡正者,最終達到使我國的法律正確的執行準確的適用的目的。 (二)職務犯罪的偵查職能 職務犯罪偵查權已經成為檢察機關一項普遍的職權,反腐倡廉、懲貪肅貪已成為檢察機關的重任,并且已經得到了聯合國有關的文件的肯定。我國的刑事訴訟法順應國際潮流結合本國的實際,將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我國的檢察權是一項獨立的國家權力,與行政權、審判權互相獨立相互并存,檢察機關可以通過職位犯罪偵查權的行使,制約監督另外兩項與之并存相互獨立的行政權和審判權,從而通過法律監督有效的促進合理執法與公正司法。實踐證明賦予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來作為監督法律正確適用的堅強后盾效果明顯,意義重大。行政執法者的權利具有不斷膨脹的天然屬性,如果不加約束,權力的嚴重濫用將造成比普通犯罪行為更加惡劣的影響,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樣,司法者追逐利益天性使司法不公的成為可能,司法不但無法給當事人期待的公正判決無法給予滿意的答卷,而且司法與法律的權威也將遭受到嚴重的踐踏。檢察機關將職務犯罪作為工作的重點,不斷并且有力的對貪污受賄、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和政治腐敗進行揭露,及時提交審判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清除了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害群之馬,掃除了吏治腐敗,維護了權力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國家法治的尊嚴。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行使從一個側面實現了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防止了權力的不當運行,從大局的角度維護了人們的根本利益。 (三)檢察制度實現了對行政權和審判權的制約 公安機關嚴重的行政化色彩形象極易造成權力的過度膨脹,檢察機關對警察偵查的成果進行驗收,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通過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引導偵查等對公安等偵查機關形成制約引導,公安機關的執法行為使其更加趨于合法,不但實現了對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而且擺脫了人們對警察國家恐懼的夢魘。法院作為正義的化身,在審判時由于無法擺脫傳統思想的影響,“寧缺勿縱”“重實體輕程序”的行為普遍存在,在法院審判前、審判中,審判之后都有檢察機關的身影,檢察機關進行了全方位、全程的監督。例如為了制約審判權,防止法官司法專橫,刑事訴訟中的“不告不理原則”便是很好的例證。在重大的刑事案件中,法院審判的前提受到檢察機關的制約,沒有檢察機關的起訴,法院是不能發動審判權的,不但如此,法院在其后的審判活動中不得就未經檢察機關起訴的對象和事項進行擴大式的審判,可以檢察機關通過提起公訴、支持公訴等對法院審判權的啟動和審判的內容都構成了約束。檢察機關介入法院的審判活動更多的體現了對程序正義的維護,最終的實體判決在程序正義的大傘保護下更容易被當事人和社會大眾信服。檢察制度的存在不但實現了對國家相關權力的制約而且無形中強化了對人權的尊重與保護,并且進一步促進了法律的正確統一的實施。 (四)司法救濟功能 國家權力針對權利具有天然支配與控制的屬性,無論怎樣被束縛,都有不當行使的可能。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不被權力隨意的踐踏,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來自公權力的侵害時有處伸冤,就需要設立相應的救濟渠道。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處于相對的弱勢一方,例如可能面臨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可能受到不公正的裁判待遇;刑事被害人可能無法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尤其是當自身的訴權與檢察機關的公訴權發生沖突的時候,被害人可能因為司法的不公正遭受到二次侵害。刑事訴訟的當事人無論是哪一方,當面對強大的權力的時候顯得都是那么渺小,此時權利隨時可能受到強大的權力的侵犯,為此,檢察制度為權利受到侵害的救濟敞開了大門,當事人可以借助于檢察機關進行檢舉、控告、申訴,請求檢察機關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對司法人員在職務行使中的違法行為采取懲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