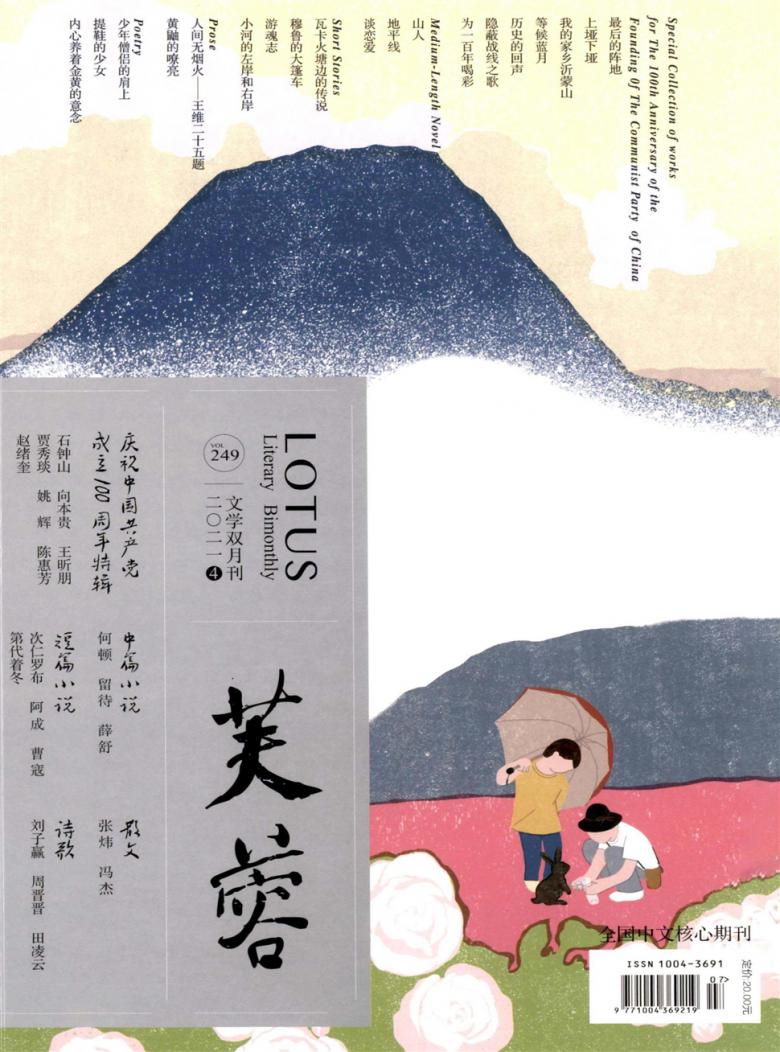儒家思想與中國民主
佚名
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儒家思想妨礙了中國在20世紀實現民主轉型。進入21世紀后,仍然有一部分“特殊國情”論者認為,在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民主制度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基于文化相對主義與文化決定論的邏輯,中國今后仍然不適合實行民主。這些觀點除了有其他邏輯和事實方面的問題外,還有一個錯誤的理論前提,即對于儒家思想本身的歪曲與誤解。
一、 儒學:民間輿論興起的產物
學術大家對于原始儒家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對于孔子時代的儒學已經不是“官學”而是一種“私學”,則沒有什么疑義。
春秋戰國是民間勢力逐漸興起的時代。殷周宗法貴族社會的兩大支柱——國野制與世卿制趨于瓦解,國人與野人、君子與小人的界限日漸消失,禮樂制度下移,公子公孫對卿大夫的世襲被打破,通過“學而優則仕”的途徑,士和庶人可以晉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門下由賢人七十、弟子三千組成的儒家團體,正是新興的“游士”階層的最初代表。
正是儒家與其他學術團體和流派之間的“百家爭鳴”,造成了華夏文化區域內一種跨國界的公共輿論。這種公共輿論一方面導致華夏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產生,一方面擴大了政治參與,使“君子”不再是一種身分限制,而成為一種政治抱負、一種人生典范,有心從政的人可以通過求學問禮,為邁入仕途創造條件。
由于儒學產生的社會背景,儒家思想中具有一些原始的民主意識,也就不足為奇了。經孔子整理的經典中有這樣的論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惟天時求民主”,人主只有能“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書經·多士》)孟子和荀子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社會契約論思想。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君的原意是群,君的職能是維護群的利益,殘害仁義的紂王只是獨夫民賊而已,沒有資格再被視為君。他又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盡心下》)“天與”是“人歸”的結果。(《萬章上》)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制篇》)君王也是一種職分,“治國有道,人主有職”。(《王霸篇》)君王不盡職守,不行仁義,就會被取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王制篇》)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后人常從“君為臣綱”方面理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語叢三》中則說:“友,君臣之道也。”君不以友道待臣,臣就有理由不臣,當時的公共輿論、庶民力量以及臣僚群體對君王的制衡程度,我們現在可能還不充分了解。
二、 儒家道統:專制皇權的制衡力量
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澤東也說,“百代皆行秦政制”,自秦始皇以來,專制主義便是中國政治的一大特色。以往,人們常常把專制主義與“封建社會”和“孔孟之道”聯系在一起。現在,中國歷史學界已經基本上達成共識,把西歐封建社會套用在中世紀中國是錯誤的,專制主義與封建主義原本是兩種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而專制主義與孔孟之道的關系,尚待進一步的澄清。
首先,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的儒學,已經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諸如“君臣友道”之類的觀念已經從元典中消失了蹤跡。其次,儒學也并非專制主義的主要思想資源。李慎之認為,法家在締造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過程中,其作用決不亞于儒家。儒家的作用不過是替法家冷酷無情的專制主義為之“節文”,為之“緣飾”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一直有“儒表法里”或“陽儒陰法”的說法。漢武帝的玄孫宣帝就曾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所謂霸道與王道雜用,說的就是法家與儒家并用,歷代最高統治者對于這一點都是心領神會的。明朝開國之君朱元璋,就因為看到孟子書中有對帝王不敬的話而勃然大怒,想要把他永遠革出孔廟。毛澤東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晚年又開展揚法批儒的運動,無非是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尋找一個中國歷史上的根據,但是他明確指出法家在中國專制主義傳統中的地位,看到大反傳統的五四先賢所沒有看到的東西,在學術上倒是頗有貢獻的。1最后,即使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學對于皇權專制主義也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漢代儒學通過神秘主義的路徑,竭力把儒學準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應”、“災異之變”的方式,來節制皇帝的行為。董仲舒說:“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氣蓄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漢書·董仲舒傳》)人君的“貌、言、視、聽、思”五種行動如有不當,就會引起五行的變化和四季的失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智》)公羊學和讖緯之書用“天”來警示和恐嚇人君,對肆無忌憚的皇權多少有一點威懾性。
韓愈、二程和朱熹等人開創的宋明理學或稱道學,演繹出一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原道》,《昌黎先生集》卷十一),以后又經韓愈、朱熹傳之后世的儒家“道統”。道統首先是思想學術的統系和精粹,認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所表達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諦,把“道統”從“政統”、“皇統”中獨立出來甚至凌駕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來拒絕和匡正當朝執權柄者的悖謬之言和隨意之政。道統也體現為古來賢君良臣面臨各種情形時的行為舉止,構成一種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貴為天子,也必須從小學習和終生遵循。
一方面用“天命”來恐嚇“人君”,一方面用“道統”來干預“政統”,儒學和儒士對于皇權專制主義構成一種事實上的制衡力量。如果從權力制衡的角度來理解民主憲政,就不好說儒學思想純粹是專制主義的工具。
三、 儒家思想資源:近代民主萌芽的培養基
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無疑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但是“新文化運動”的源頭在哪里,則是有爭議的。以往,人們更看重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幾乎成了陳獨秀、胡適等《新青年》同人發起的思想運動的專用名詞。近來則有了“戊戌新文化運動”的說法。2張灝更明確指出,在從傳統到現代中國文化的轉變中,19世紀90年代中葉至20世紀最初10年里發生的思想變化應被看成是一個比五四時代更為重要的分水嶺。3把“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提前到世紀之交,有助于正確理解儒家思想與中國民主的關系。
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產生主要是受舶來“西學”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資源發掘自傳統的“中學”。康有為從公羊學平滑過渡到君主立憲思想,梁啟超則從黃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清代學術概論》中寫道:“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從黃宗羲的《原君》、《原法》向前邁出一步,譚嗣同便能夠在《仁學》中暢論:“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梁啟超則在《古議院考》中稱:《禮記》中講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里說的“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議院的思想基礎。“《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諸大夫,上議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國人,下議院也;”就是議院的制度雛形。4從清末新政到民國建立,儒學傳統并沒有對國人接受民主思想構成障礙,而且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接受并闡發了族性概念。盡管他的族性分析不無精彩之處,但從總體上說并非一種科學理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在戊戌變法失敗后的感慨之論,而且帶有某種自我解脫的意味。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首先應當從統治集團的保守性及其內部矛盾中找尋,其次應當檢討改革陣營自身素質的缺陷以及戰略策略上的失誤,由于種種因素,梁啟超不方便或不愿意在這些方面展開討論,歸罪于國人族性上的的劣根性,就成為一種理論上的強烈誘惑。
在梁啟超以族性理論為政治改良路線辯護時,陳獨秀等作為革命的鼓吹者,顯然對之不屑一顧。然而,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奪取時,失敗的前革命黨人便追隨進而超越政治改良主義者,成為以批判傳統文化為特色的國民性理論的信奉者。1917年初,《新青年》發表署名光升的文章《中國的國民性及其弱點》,把國民性界定為“種性”、“國性”和“宗教性”的集合體。此時,這種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文化理論已經被西方主流學界拋棄,但在中國卻被作為外來新理論倍加尊崇。上述文章的結論是:中國何以不發達,“則以吾國民性固有絕大之數弱點在焉”。5陳獨秀據此提出了“倫理革命”的呼吁,他斷言:“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6按照這種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國民性”,中國人就沒有資格實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礙,不是從政治實踐上著手逐步的解決,而是在倫理思想上尋求根本的解決,這是五四時代的一個思想誤區。陳獨秀雖然對“德先生”推崇備至,但并沒有對民主思想進行深入的研究,也沒有下大氣力推動民主運動的開展,他的注意力很快便轉移到了新的思想潮流方面。
羅志田指出:20世紀中國人有一種“新的崇拜”。北大教授陳百年在1923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時“現在的人以為外國來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變就成了‘凡是外國的都是好的’。”趨新大勢與尊西傾向的結合是非常明顯的。7由于趨新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是要學“最新最好”的西方,陳獨秀、毛澤東便從“拿英美作榜樣”轉向“走俄國人的路”;世紀末的青年學子則迷上了“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因此,20世紀中國民主化的曲折與失敗,與其說是由于中國人的過于保守以及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不如說是中國人的過于趨新以及世界時髦思潮造成的負面作用。
四、 儒教文明:民主價值觀的見證與提升
當前,我們正處在從人類多文明向多元一體世界文明的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作為世界歷史上的一大文明,以中華文明為核心,并輻射到東北亞和東南亞,中外學者也常常稱之為儒教文明。
關于儒教文明,學者們進行了許多深入的比較研究,提出過著名的“李約瑟問題”和“韋伯問題”。這兩大問題作為歷史課題來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按照人類學的路徑演繹出文化本質主義的結論,則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固然,中國在技術長期領先世界的情況下沒有實現現代科學的突破,但是,一旦中國文化嫁接上科學基因,儒教文明中教育優先的傳統基因便會發揮良性作用,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在美國的表現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同樣,在歷史上確實是新教倫理而不是儒教倫理催化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降生,但是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儒教文明與資本主義不能相得益彰,由于日本和東亞“小龍”、“小虎”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功,李光耀、杜維明等人圍繞這個話題有過許多精彩的論述。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再提出儒教文明與民主不相容的命題已經不合時宜。
日本文明是儒教文明圈的亞文明之一,從明治維新便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二戰后融入自由民主國家的陣營,90年代又開始從“一黨獨大”體制向“政黨輪替”體制演變。近十幾年來,韓國、臺灣等更接近儒教文明中心的地區也相繼實現了向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新加坡、香港則正在從足夠自由而缺乏民主的政體向更加民主的政體過渡。隨著一波波民主化浪潮的沖擊,在儒教文明中心地帶——中國大陸最終實現民主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通常所說的民主價值觀是自由主義、鄉土主義、憲法愛國主義、世界主義等多種價值的復合體,包括了個人層次上的人權思想,社區與地方層次上的自治思想,國家層次上的憲政民主思想以及全球全人類層次上的博愛思想,等等。這些思想的大部分生長點都可以從儒學傳統中發掘出來。如果有所欠缺,還可以到中國傳統思想的其他組成部分中尋根,譬如最近就有論者倡言“楊墨兼用”。8楊朱是先秦最著名的個人主義者,墨翟是與孔門弟子同時代的兼愛主義者,孔孟之道所偏重的則是家與國這兩個中間層次的倫理。把孔孟與楊墨來一個創造性的綜合,就可以讓民主價值觀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扎下更深更廣的根基。歷史上的儒家士大夫曾以寬容的心態面對佛教東來;當代中國知識精英也會以開明的態度看待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在炎黃子孫中的傳播。事實上,基督教會在日本、韓國和臺灣都擁有相當大的勢力,而且它們已經在民主化進程中展現了自己的作用。通過適量攙入基督教價值觀,改良中國政治文化的土壤板結,這是一個可供考慮的選擇。如果中國堅持宗教自由的憲法原則,就應當允許基督教價值觀、世俗民主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平等競爭,讓它們各得其所并進而相互融合。
梁啟超曾經說過: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因為人類全體才是“自我”的極量。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強便了,要叫自己國家有功于人類全體。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就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的文明。9在政治領域,西方文明的長處是“善政”、“良制”,儒教文明的長處是“善治”、“良吏”。18、19世紀,西方人從中國吸取了文官考試制度,使自己的政治體系得到了大大的提升。20、21世紀,中國人堅持不懈、百折不撓地向西方國家學習民主法治,一旦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相信會把“善政”與“善治”更好地結合起來,開創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
五、 結論:儒家思想不是中國民主的障礙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不是中國實現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礙,如果去蕪存菁,揚棄得當,它還可以成為民主價值觀的思想資源之一。思考中國民主的前途問題,與其把關注焦點投向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不如更多地考慮世界趨勢、集團利益以及人們的種種現實考量的影響。
在對中國民主化的目標、途徑、動力和障礙進行展望與預測時,文化分析遠不如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得實用。事實上,傳統文化批判與國民性理論在中國已經被統治集團用來為極權專制辯護。梁啟超、陳獨秀、魯迅等人引進國民性理論的用意顯然是要暴露、批判和改造國民的“劣根性”,但結果適得其反。沒有引進這種理論時,國民黨政治家還是民主主義的信奉者,引進這種理論后,執政的國民黨政客們卻更加振振有辭地打出了訓政、黨治的旗幟。在“先知先覺”們的“一黨專政”下,“后知后覺”的國民永遠也無法在民主實踐中學會民主,因而也永遠無法改變自己的“劣根性”。同樣的道理,80年代的中國知識精英曾以“曲線救國”的方式,用文化批判來虛擬和代替政治批判,未曾想到的是,這種文化批判到90年代卻成為政治保守主義最心愛的兵器。國民性理論作為一種工具,既可以為激進主義服務,也可以為保守主義效力。就目前而言,它主要是在為后者效力,一方面是由于權勢者的偏愛,一方面是理論自身的本質主義和文化決定論的邏輯使然。20世紀中國知識精英之所以屢屢選擇從文化批判和文化改造入手來推動中國社會政治改革,其原因與19世紀德國知識分子喜歡談論文化如出一轍,即埃利亞斯所說“市民階層的獨特命運——政治上長期的軟弱無力”,“知識分子這個階層遠遠地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他們不是在政治的范疇里,而首先是膽怯地在民族的范疇里思考。”10
真正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思想因素,并不是“三綱六紀”之類的儒家傳統觀念,而是各階層人士的一系列現實考量。現在統治階層的成員畏懼民主變革后的政治清算,實業界人士擔心民主化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憂慮蘇聯解體后的混亂局面在中國重演。有志于推動民主化事業的中國人,不僅要從古今中外的進步思想傳統中吸取養分,尤其要重視總結當代民主實踐的經驗教訓,解答人們的種種現實疑慮,妥善處理社會各階層間的關系,在各種力量的對抗與均衡中把握住民主轉型的契機。
1 李慎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載“思想的境界”網站。
2 《戊戌新文化運動述略》,載龔書鐸:《中國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116—123頁。
3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18頁。
4 轉引自李喜所等:《梁啟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3、97頁。
5 張寶明等主編:《回眸<新青年> 社會思想卷》,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373-378頁。
6 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載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79頁;《通信》,載《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442頁。
7 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沖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載“世紀中國”網站,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60-61輯。
8 馬悲鳴:《楊墨兼用》、《再說“楊墨兼用”》,載“多維新聞網”網站。
9 《飲冰室合集》,7,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專集之二十三,35頁。
10 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I:西方國家世俗上層行為的變化》,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