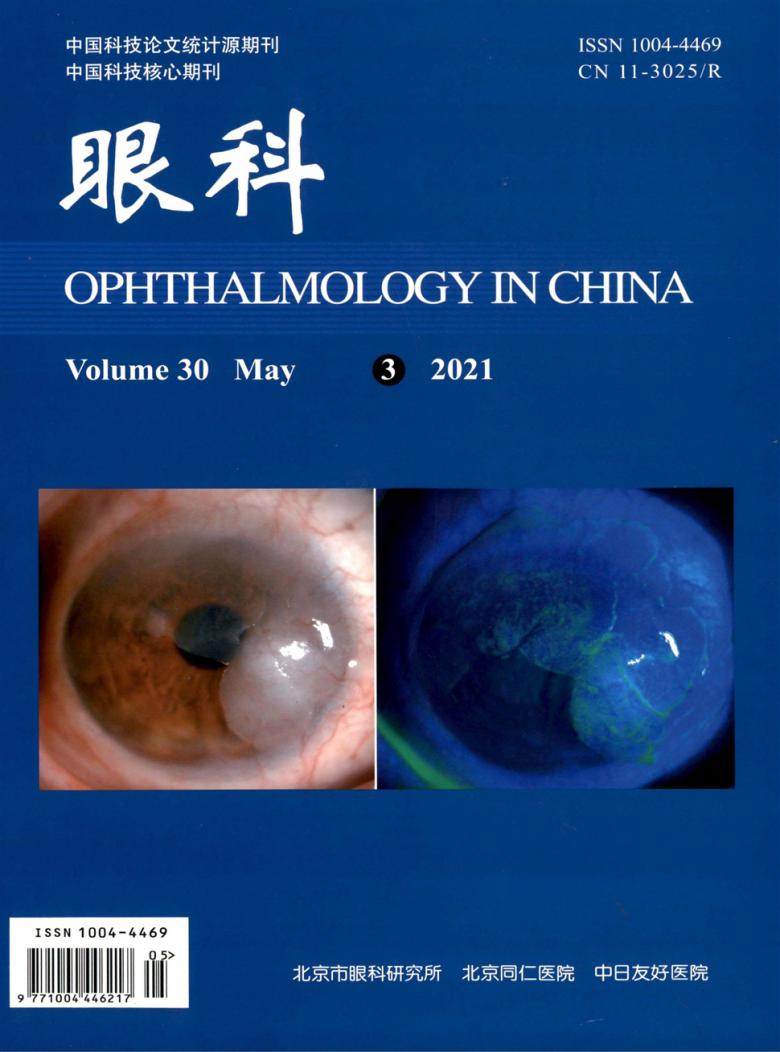日常生活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沖突——以中國近代公園為中心的考察(之一)
陳蘊茜
【內容提要】公園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勢力引入中國的,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休閑娛樂空間,伴隨著殖民主義的滲透而成為政治空間。在初期因禁止華人入園而引發公園運動,形成了中國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深刻民族集體記憶,而且公園中的殖民主義紀念建筑進一步刺激著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因為如此,中國人自己在建造公園時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強調教育功能,從公園名稱、空間布局和建筑到公園功能都體現出民族主義精神。公園問題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沖突的發展軌跡。 【摘 要 題】社會·經濟
【關 鍵 詞】近代公園/殖民主義/集體記憶/民族主義
【正 文】 日常生活史是目前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主題,因為它與普通大眾的歷史關系密切,而大眾是社會發展的重要主導力量,所以,關注大眾生活史的研究更能從深隱層面揭示政治勢力的實際影響。西方殖民勢力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遠不止于傳統近代史研究所關注的主權、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它已經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因為,“殖民主義體系的運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軍事侵略造成的征服與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穩定的宰制,必須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種仰賴情結。這個仰賴情結,包括了經濟、技術的仰賴和文化的仰賴,亦即所謂經濟和文化的附庸。”[1](p.364)殖民主義在日常生活層面的影響對于大眾而言更實際、更真切,也更容易形成切實的體驗與反彈,從而建構起全民族的歷史記憶,對于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隨著公共空間研究成為近十年來的新熱點,近代公園問題也逐步引起學者的關注。史明正的《從御花園到大眾公園:20世紀初期北京城區空間的變遷》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園開放與公共空間的拓展》較早開始研究公園與城市空間及公共空間發展的問題,以后陸續有學者撰文論述廣州、成都公園的興起和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以及公園里的社會沖突。(注:參見Mingzhen Shi,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Vol. 24, №3, 1998;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園開放與公共空間的拓展》,《學術月刊》1998年第8期;陳晶晶:《近代廣州城市活動的公共場所——公園》,《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0年第3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間與城市社會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園為例》,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城市史研究》第19輯,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李德英:《公園里的社會沖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園為例》,《史林》2003年第1期。)研究者將過去學界所忽略的公園這一“場所”與公共空間聯系起來,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史中現代性研究的深化。 實際上,公園不僅僅與公共空間有關,它還與人們日常生活、觀念心態聯系緊密,它曾經是殖民主義向中國滲透的重要象征與渠道,對中國人的民族情感產生過強大的沖擊并形成深刻的民族集體記憶,因而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要問題,但在這方面僅有《淺析中國近代租界花園——以津、滬兩地為例》一文對租界花園的格局及園林小品進行了簡要分析,(注:參見楊樂等:《淺析中國近代租界花園——以津、滬兩地為例》,《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近代租界公園不準華人入內而引發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曾引起學界熱烈討論,但學者們主要圍繞外灘公園門口污辱中國人的木牌是否真實存在而展開,(注:參見薛理勇:《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世紀》1994年第2期;馬福龍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的來龍去脈》,《上海黨史與黨建》1994年第3期;張銓:《關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史林》1994年第4期;《中國人民被污辱的史實不得抹煞曲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的史實綜錄》,《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6期。)對于其作為民族集體記憶的意義卻未能予以充分關注。因此,本文將全面考察近代西式公園的引入與華人公園的發展,透視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撞擊及中國民族國家通過公園建設在日常生活層面的民族主義建構。
一、租界公園的殖民主義空間復制
鴉片戰爭以后,外國殖民勢力陸續在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廈門等地建立租界、居留地、租借地及附屬地,并將西方市政建設及生活方式引入中國,公園就是其中的代表。工業化后,英法等國為緩解工業化大生產給人們帶來的精神壓力,開始通過建造城市公園等綠色景觀系統來解決城市環境問題。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公園是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后的產物,最早出現于租界,而后影響至華界。目前學界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公園是由英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開放的外灘公園,當時稱“公家花園”。[2](p.473)[3](p.249)又據閔杰考證,自1903年留日學生在《浙江潮》上介紹日本公園后,次年,《大公報》在報道南京建公園時就全部用“公園”一詞。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資,各地漸興修建公園之風,“公園”一詞逐步取代“公家花園”而成為專用名詞。(注:參見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頁。) 上海是近代中國公園的發源地,大量外僑隨著殖民勢力的侵入而移居上海,建立起繁華的十里洋場,正如時人《租界》詩所云:“北鄰一片辟蒿萊,百萬金錢海漾來。盡把山丘作華屋,明明蜃市幻樓臺。”[4](p.52)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外國花園”進入上海人的生活空間。英國人最早建立的外灘公園位于“英界虹口大橋沿江一帶”,每天“西人摯眷攜童游賞”。[5](p.5)繼外灘公園之后,外國人在滬所建公園逐漸增至10多個。(注:據《上海研究資料》(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485頁),吳馨、姚文楠修纂:《民國上海縣志》卷二《政治下·名跡》,屠詩聘主編:《上海市大觀》(中國圖書雜志公司1948年版)整理。)1860年,天津辟為通商口岸,先后有9個國家在天津設立租界,面積達1500多公頃。1880—1938年,英、法、日、德、意、俄等租界共修建了10座具有各國象征與文化特色的公園。(注:參見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五《食宿游覽》,天津文明書局1911年版,第7頁;崔世昌:《租界里的公園》,《天津租界談往》,《天津文史資料選輯》1997年第3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天津通志·城鄉建設志》,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541頁。)關于公園統計資料保存完整的還有青島,青島在歷史上曾為德國人占領,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人又從德國人手中奪得青島,因此,青島盡管城市不大,但近代西式公園數目較多,據《膠澳志》統計達15個之多。[6]上海、天津與青島三地的近代公園見下表(未標注具體修建年代者,待考): 表1上海、天津、青島近代公園一覽 上海公園 天津公園 青島公園 外灘公園(1868)、昆山花園(1895)、虹口 海大道花園(1880)、維多利亞公園 旭公園、若鶴公園、新町公園、深山公園、 公園(1905)、法國公園(1908)、德國公園、 (1887)、德國公園(1895)、皇后公園、俄國 千葉公園、官邸公園、天后公園、司令部 匯山公園(1911)、兆豐公園(1914)司德蘭 花園(1900年后)、大和公園(1906)、法國 前公園、曙濱公園、萬年町園、治德町園、 園(1918)、新康花園、寶昌公園(1920)、膠 公園(1917)、意國花園(1924)、久布利公 山東町園、大村町園、青島神社、松板公 州公園(1935)、貝當公園(1935) 園(1937) 園
外國勢力侵華后力圖將其引以為傲的公園等所謂“文明”的藝術文化及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國,因此,只要有外國移民定居之處便會有近代公園出現。俄國人、日本人先后在東北的大連、哈爾濱、沈陽等地建立起大批公園,如大連的西公園、北公園、電氣公園,旅順的植物園、動物園,哈爾濱的公立公園、極樂村,丹東的鎮江山公園。(注:參見蕭山、喻守真等編:《全國都會商埠旅行指南》上卷,中華書局1926年版,第124頁;大連市中山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山區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李元奇:《大連舊影》,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頁照片及說明:《旅順口區志》編纂委員會:《旅順口區志》,大連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頁;哈爾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哈爾濱市志·外事對外經濟貿易旅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頁; 丹東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印:《丹東市志》(第二冊),1996年版,第135—136頁。)南滿鐵道會社在其鐵路附屬地如沈陽、遼陽、鐵嶺、長春各地,建立各種市政設施,“上下水道、公園、市場、學校、醫院、墓地”等一應俱全。[7](p178)此外,外國人還在漢口等地建有各類公園。 著名社會學家福柯對空間特別關注,指出“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8](pp.13—14)殖民主義勢力正是通過空間向中國滲透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專家亨利·列斐伏爾進一步指出:“空間一向是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鑄造,但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9](p.62)公園作為一種人造的空間同樣體現歷史與自然元素的模塑,折射出西方工業化后人們尋求新型娛樂休閑空間形式的特性。但由于近代公園是隨殖民主義進入中國的,因此,其獨特的空間建構與中國傳統園林有著本質區別,體現出中西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差異與沖突。 西式公園的重要屬性之一是公共性、公眾性與休閑性,因而一般占地面積較大,在空間布局上強調視野開闊、舒適明朗,普遍以草地、綠樹、花卉、噴泉及西式涼亭為主要景觀,迥異于狹小、精巧的中國官家或私家園林。最早的上海“公家花園……細草如茵,落花成陣。芊綿蔥翠,一望無垠”,[10](p.133)且“遍地栽花,隨處設座”,“中央為噴水池及音樂亭”,而法國公園“園址甚廣,境頗幽靜”。[11]天津最早的法租界海大道花園“地廣百數十畝,路徑曲折,遍植花木,小橋流水,綠柳濃蔭”。[12](pp.538—539)這些特征是與西方工業化后空間的發展及人們在被制約后尋求放松、休閑等需求相聯系的,所以,一般公園內還建有球場、運動場、游泳池、動物園,天津皇后公園就建有游泳池和兒童運動場,大和公園亦設兒童運動場并飼養小動物。其次,公園布局都帶有其設計建造者本國的造園風格,如天津意國公園呈圓形,總體布局為規則式,中心建羅馬式涼亭,園內有噴水池及花壇,花繁樹茂。法國公園同樣為圓形,空間布局則為典型的法國規則式,小區由同心圓與輻射狀道路分割,設四座園門。園中心建西式八角石亭,亭四周草坪環抱,南端豎和平女神銅像一尊,右手持劍,劍尖向下,左手握鞘。而大和公園則是典型的日本園林風格。[12](p.540)日本在長春建的西公園從總體格局到建筑式樣均為日本風格,園內供游人坐賞湖景的涼亭就是日本式方亭。[13]當然,也有極個別的外人所建公園具有中國園林風格,如上海“麗虹園在佘山路,洋商利得利建。亭臺樓閣,悉仿中國古制”,[11]但絕大多數公園均按其本國風格建造。不僅如此,有的公園甚至在植物種植上也體現出象征意義。最初均從殖民母國引進花草,如最早的公家花園的“奇花異卉,大都來自歐洲。紫姹紅嫣,名色各異。不特目所未見,耳所未聞”。[10](p.133)日本更為典型,將其國花——櫻花移植到中國的公園。青島旭公園(后改為第一公園)有一條通往紀念日本陣亡士兵“忠魂碑”的路,兩側遍栽櫻花,因此,櫻花成為該公園的主要植物,也成為該公園的象征,當時的青島人稱其為櫻花公園。[14]丹東鎮江山公園也栽種著從日本奈良吉野山寄來的櫻花樹木1000株。[15](p.136)這樣的空間布局與植物種植顯然是要將其母國的公園移植過來,并復制其母國文化以達到空間的殖民主義化。 在公園的空間構成中,除布局與植物外,建筑也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構成公園空間的核心。福柯曾說,“空間位置,特別是建筑設計,在一定歷史時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變成了為達成經濟—政治目標所使用的空間布署問題’。”[16](p.30)殖民者在公園中建造代表其文化意象和殖民侵略象征的建筑物,更直接地傳達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即透過這一空間炫耀其武力、種族及文明的優越感。這在最初上海的租界公園中就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而到后期日本的做法更令中國人發指。1880年英國人在外灘蘇州路及外擺渡橋入口處建立紀念碑,紀念導致中國被迫與英國簽訂《中英煙臺條約》的英人馬加禮(今譯馬嘉理),該碑于1907年移入外灘公園。[1](p.376)[17](p.146)天津英國公園內則建戈登堂。[18](p.257)日本在中國所建公園內修建紀念碑最多,以炫耀其戰功。1906年,為紀念鎮壓義和團而戰亡的日本官兵,日本人在天津大和公園內豎立“北清事變忠魂碑”,后增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及明治天皇之靈位,門口有日兵守衛,日人過此均虔誠敬禮,中國人則不許靠近。日本人還在春秋兩季到神社祭祀,日本在津軍政要人均參加儀式,極為隆重,神社成為日本推行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18](p.7)[19](p.258)[20]實際上,日本每占領一地均建神社、納骨堂等建筑物,如大連東公園內建有“表忠碑”,紀念日俄戰爭在海城陣亡者,“每屆四月十日,日人舉行招魂大祭于此”。青島太平山會前公園內也有日人修建的納骨堂,奉祀青島戰役中的日本士兵遺骨。[21](p.125)日本人又在丹東鎮江山公園內建“忠魂碑”、神社、八幡宮等,為日本侵略者歌功頌德。[15](p.135)到抗戰時期,日本的做法進一步升級。1940年,日本在長春西公園入口處,豎立一座象征日本“皇軍南進”的武人銅像——日俄戰爭中立有顯赫功勛的兒玉源太郎大將銅像。兒玉頭戴法式圓柱軍帽,身著日俄戰爭時軍服,腰佩長刀,肩披斗篷,騎馬向南,并舉手側臉向東(園林正門方向)致禮。這座銅像把日本軍國主義者傲慢與蠻橫的神態表現得淋漓盡致,西公園也由此更名為兒玉公園。[13]抗戰時期,日本人不僅在公園建立侵略者紀念物,有的甚至將整個公園改建為神社,并要求中國人表示敬意。據人們回憶,日本人在攻入廣東佛山后一度進駐中山公園,并在園內修建一座“靖國神社”,供奉侵華日軍的亡靈;[21]廣州永漢公園則“被日本侵略者改建為供祭侵華日軍亡靈的‘神社’,在里面設有‘神亭’、‘神龕’等,人人走過都要低頭‘致敬’”。[23]這些建筑物顯然在傳達殖民主義信息,中國人對此深有感觸,“帝國主義者掠人之地猶建大兵頭花園,立其掠奪者之銅像以自豪”,[24]這使中國人感到恥辱與憤慨。 構成公園空間的“歷史因素”,最突出體現在同一建筑物上所表達的政治內涵不斷改變。1897年11月,德國侵占青島后,為紀念其殖民主義政策的勝利而在一個小游園內建立“勝利紀念塔”。塔為六面體形,正面銅片上刻著占領青島的德國軍隊首領肖像,其他幾片則鐫刻著占領年月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從德國人手中奪取青島,遂揭去紀念塔上的銅片,保留原塔未動,作為日本戰勝德國的紀念塔。1922年,中國贖回青島,原塔仍保留未動,只是在塔的正面鑲了一塊銅片,上書“膠澳商埠督辦熊炳琦接收青島紀念”,作為中國接收紀念塔。1937年冬,日本再占青島,此塔再度更名為“東亞勝利紀念塔”。[25]這一小游園充分反映了殖民主義者在青島統治的歷史。 公園空間的構成除園內空間布置與建筑外,公園門口的布置與近旁的建筑物同樣對于人們的影響甚大。1896年德國炮艦伊爾底斯號在暴風雨中沉沒于山東海面,死難者77人。上海德僑得怡和洋行資助,在外灘公園旁建立紀念碑。[2](p.377)另外,外灘公園對面矗立著紀念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陣亡的5名英國士兵的紅石紀念碑,碑身為英國運來的花崗巖十字架,上刻“英領署地上十字紀念碑”。[2](p.376)這些建筑物在空間上已經與外灘公園渾然一體,在視覺與精神上共同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 殖民主義在公園中的滲透不僅表現在空間上,同時也表現在時間上,即把特定的日期作為公園開放日,或在公園中舉行殖民者的紀念日儀式。如天津維多利亞花園,又名“英國花園”,是英租界的第一個公園,是工部局專門為慶祝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誕辰而投資修建的,其正式開放日就定于英皇誕辰50周年的1887年6月21日,[20]以此來宣揚維多利亞時代的殖民主義精神。無獨有偶,在滬日本人則于每年4月29日“天長節”(天皇生日)舉行慶祝儀式,如1932年的這一天,日人在虹口公園舉行盛大的“祝捷”閱兵典禮,由日軍司令部至公園,沿途警戒,園內“高搭彩牌,小旗招展”,全體日軍及日僑齊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后因朝鮮革命黨志士在觀禮臺下所埋炸彈爆炸而中止。[26] 筆者認為建筑界學者所提出的“空間殖民主義”概念對于理解近代中國的租界公園極有參考價值。所謂空間殖民主義實際上是對過去殖民主義概念只注重軍事、主權、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補充,強調空間為列強從事其侵略提供了廣泛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基礎。因此,空間殖民主義是殖民主義者奴役和剝削他國政策的一種延續和文化表現,其媒介則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空間環境。空間殖民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在他人之鄉,按自己的生活習性、文化偏愛去構造一個為自己所喜聞樂見的空間環境,以殖民空間移植來滿足并宣揚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表現自己的文化優越感,無視他人、他鄉的社會及生態環境,從視覺到物質感受上嘲弄地方文化,奴化他國民眾的心身。(注:參見吳家驊:《論“空間殖民主義”》,《建筑學報》1995年第1期。)就空間本身而言,其所傳輸的象征意義與文化、政治內涵對于人們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涵化作用,而紀念性空間更具教育功能。因此,近代殖民勢力進入中國后,以空間作為權力意志表征,完全按照他們的審美情趣、欣賞習慣對各地進行市政規劃,建立起一座座帶有其文化藝術風格的公園,不僅將一整套殖民主義空間復制移入中國,滲透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精神上奴化、戕害中國人。公園作為空間殖民主義與文化殖民主義的產物,比政治、經濟殖民主義更具隱蔽性,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及觀念心態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
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集體記憶
租界公園不僅成為殖民主義空間的物化載體,而且因華人不能入園問題而成為歧視華人的象征符號,構成對華人精神的嚴重戕害,使中國人對殖民主義空間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彈心理與深刻的民族集體記憶。 這一情境在上海最為典型,上海最早的公家花園開始并未公開禁止華人入園,只是授令巡捕,禁止下層華人入內,由于“門禁甚嚴,故華人鮮有問津者”,[10](p.133)但不到五年,英人即以華人不守規則為由禁止華人入內。后工部局明確告示的公家花園《游覽須知》規定:“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小孩之車,須遵路旁而行;毋許拆毀鳥巢,損壞花木;小孩尤宜加意管束;樂亭欄桿內,游人不得擅入;華人無西人同行,不得入內。”[27]《申報》曾刊登外灘公園照片,標題為《不準華人入內之上海公園》。[28]法租界的顧家宅公園(即法國公園)于1909年6月落成,“當時該公園章程,第一條第一項便明白規定,不許中國人入內,但是照顧外國小孩的阿媽,加套口罩為條件。”[29] 殖民者的做法引起中國人的強烈抗議,上海要求公園對華人開放的呼聲一直不斷。早在1878年《申報》就刊登《請弛園禁》,認為“該花園創建之時,皆動用工部局所捐之銀。是銀也,固中西人所積日累月而簽聚者也,今乃禁華人而不令一游乎?”[30]此后,華人繼續據理力爭,1885年11月,租界著名華商陳詠南、吳虹玉、唐廷樞等8人聯名致函工部局,再度要求準許華人入園游觀。此舉立即得到華人輿論的積極響應,《申報》予以支持,并批評工部局的禁例,指出公園“造之者西人,捐款則大半出自華人”,而且名稱是“公家花園”,就應該“以見其大公無私之意”,然而,實際上“仍系私家。西人得以入園中游目騁懷,往來不禁,雖日本人、高麗人亦皆以公諸同好,聽其嬉游,而獨于華人則嚴其厲禁……此事似于公家兩字顯有矛盾”。而且,“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計之,華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幾何?則是此園而例以西法,華人斷不至被阻。且彼日本之人其捐尤少于西人,高麗之人則竟一無所捐,而何以顛倒若斯乎?”[31]但工部局對于華人的要求仍然置之不理。1889年,唐茂枝、吳虹玉等又呈道憲向英國領事交涉,結果,工部局允發給執照,執照不收費,但每張只能用一星期,且為數甚少,因此,問題仍然存在。 由于園小人多,1890年工部局又決定另建一公園。所選蘇州河浜的漲灘,上海道聲明“屬中國官地,不能由外人任意處置”,工部局遂決定“對中外一律公開”,定名為“新公園”,次年改名“華人公園”,但新花園占地面積小,各項設施亦遠遜于公家花園,“布置殊草草”。[2](p.474)[11]另據《上海閑話》載,“公園建筑,遠不逮西公園”。[32](p.18)雖然華人有了專門的公園,但僅一個公園無法滿足廣大市民生活的需要,由此,為爭取所有公園對華人開放的努力一直進行著,甚至被稱作“公園運動”。[33] 1926年夏,上海“天時奇熱,為十年來所罕見,時疫猖獗,死亡相繼,而滬地空氣不佳,游散無地,亦為重要原因”,因此,華人急切盼望公園對其開放,但工部局仍然只“允以黃浦灘草地開放于華人”,其他公園一律不開放。[34]《申報》在1926年8月18日詳細記述了華人游公園納涼時被西人巡捕迫令退出之事,[35]引起華人普遍不滿。經過華人努力,工部局公園委員會中有3名委員由總商會推選華人出任,于是,華人紛紛要求委員會“力爭華人入園免去憑證”,[36]公園委員會亦主張“中外市民應平等享受”。[37]但是,這個公園運動后來又有所消退。所以,1927年,鄭振鐸呼吁:“在去年,我們曾有一度熱烈的表示,而至今卻又銷聲匿影了。難道是因為冬天到了,公園用不到了,所以又沉寂下去了么?不,不,我們要熱烈地持久地舉行著‘公園運動’!”因為“主人翁是被放逐出自己的公園之外了!……難道我們竟袖手地聽憑那些最少數的客民們緊握了我們的咽喉而要將我們窒息死了么?不,不,我們要求呼吸權!我們要求生存權!”而且“‘公園運動’表面上看來,也許比之最根本的辦法,‘收回租界’,是不重要些。然而區區公園運動而尚不能成功,則還談什么收回租界!”[33]公園問題已不僅僅是華人的地位問題,也是中國近代租界問題、華人生存與國家主權的問題。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928年納稅外人年會通過《公園開放案》。同年6月1日,外灘、虹口、兆豐3公園對華人開放,同時開始售票制度:年券售價1元,零券每次銅元10枚。華人公園仍舊無條件開放,[38][39]但是,法國公園等仍然禁止華人入內。 上海關于公園問題的爭議最為激烈,公園儼然成為殖民主義的象征物,提到公園必然聯想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已經成為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對于中國人而言透心徹骨。關于外灘公園門前是否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直至幾年前學術界仍在爭論不休。著名學者熊月之等認為,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由公家花園《游覽須知》的規定衍生出來的。[40](p.578)美國學者也著文討論,指出外灘公園門前沒有這樣的木牌。[41]爭論這一牌子是否存在對于追求歷史真實性的學者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為什么會形成如此深刻的歷史記憶,而且擴展為全民族的集體記憶?因為公園的確是不準華人進入,工部局的檔案及公家花園《游覽須知》上都曾有過華人不得入內、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的規定,而且華人為了爭取同等的入園權利奮斗了半個世紀。可以想見,中國人不可能再將公園視為簡單的游覽空間場所,它完全成為西方列強進行殖民主義滲透的空間,是文化殖民主義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最鮮明的象征。于是,近代中國人對于公園有著難以言表的隱痛,許多人在著作、文章、通信中都談到公園問題。早在1907年,李維清在《上海鄉土志》中就寫道:“公花園……東西各國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國之民、洋人豢養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獨禁華人入內,是彼之蔑視華人,且奴隸犬馬之不若矣。喧賓奪主,實堪浩嘆!可知當今之世,惟有強權足恃而已。我儕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恥耶!”[42]對殖民主義的反彈情緒躍然紙上。郭沫若在1923年憤然寫道:“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43]同年,蔡和森發表《被外國帝國主義宰割八十年的上海》,再度質詢“上海未開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點不是華人的?但是既開埠以后,租界以內,最初是不準華人居住的,而‘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標揭,至今還懸掛在外國公園的門上!”[44]對于直接提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的文章更多,廖沫沙曾撰文《中國人與狗》,談到在公園門口“那時讀書的中國人看見了,真是‘人生識字憂患始’,免不了感到侮辱,憤慨萬分”。[45]因此,中國人對于上海公園均印象深刻,“上海的公園對于我的印象是不好的,那里邊所有的人物,我都不歡喜;特別多的是洋太太,洋太太的孩子,領洋孩子的江北娘姨。好一點的地方和好一點的時間,全被他們占有了”。[46](p.367)有的人雖多次游覽租界公園,但都是“紅著臉去”的。[47]曹聚仁雖然有朋友邀請同游法國公園,但他卻斷然拒絕,“一則我是一直穿布長衫,犯不著去‘丟臉’;二則,我們那時‘反帝’的狂熱,使我不愿低頭。直到公園開放了,我才進入那里”。[48](p.216)所以,華人去租界公園游玩的并不多,正如1929年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的沈從文所記述的:“到公園去,全是小洋囡囡的天下,白發黃毛。”[49](p.72)也許相當多的華人沒有用文本書寫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卻用實際行動表達著自己的思想。 租界公園給予中國人的印象就是一個殖民主義禁區與象征,華人不能入公園這一事實真正讓中國人認識到殖民主義政策的切實存在,華人將這一情緒升華至對殖民主義的認識。著名文人陳西瑩對上海的記憶是這樣的:“上海完全是外國人的上海,不久中國就會不知不覺地變成外國人的中國。……十年來添許許多多美麗的花園和舒服的別墅,里面住的又都是黃頭發、藍眼睛的人。……總而言之,他們西洋人是貴族,中國人是他們的奴隸;他們西洋人是享樂者,中國人是供給他們的生產者。”[50](p.94)方志敏在其所著《可愛的中國》一書中寫道,“‘華人與狗不準進園’……這幾個字射入我的眼中時,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這是我感覺著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在中國的上海地方讓他們造公園來,反而禁止華人入園,反而將華人與狗并列。這樣無理的侮辱華人,豈是所謂‘文明國’的人們所應做出來的嗎?華人在這世界上還有立足的余地嗎?還能生存嗎?”[51](p.8)此外,孫中山等政治家、文人都曾在文章中提到這一情結。(注:參見孫中山:《在神戶歡迎會的演說》(1924年4月24日),《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還有的文人因公園問題而上升至對整個上海精神與文化的批判,“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52](p.47)一般文人則用竹枝詞的形式表達著這一歷史記憶:“公園設備固然新,不許華人去問津。世界有何公理在,何稱奪主是喧賓”;“英人游憩有家園,不許華人闖入門。綠樹蔭中工設座,洋婆間跳挈兒孫”;“狗與華人禁令苛,公園感想舊山河。而今各處都開放,又見倭兵列隊過”。[53](pp.496—497)“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僅是中國人處處受奴役受欺凌的一個縮影,殖民主義奴役下的中國人只能是奴隸。著名詩人蔣光慈在《哀中國》中感嘆道:“法國花園不是中國人的土地么?可是不準穿中服的人們游逛。哎喲,中國人是奴隸啊!……我的悲哀的中國啊!你幾時才跳出這黑暗之深淵?”[54](pp.69—70)可見,這一深刻的記憶逐漸由個人的憤恨而上升為對國家與民族的憂患。 在上海以外的其他租界、租借地及附屬地的西式公園也禁止華人入內。日本人內藤湖南1899年訪問天津紫竹林租界公園時曾看到,“不能進入此園者有二,一為華人,另一為狗”。[55](p.81)天津英國公園至1930年仍規定“華人非與洋人相識者不得入之”。[18](pp.257—258)更有甚者,武漢華人若入簡易公園游玩將遭拘罰。據曾做過巡捕的李紹依回憶,漢口英租界捕房依據《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附則》履行職責,其中第20條規定:“華人擅入江邊草坪(坪內設有靠椅,從江漢關達界限路,接通俄、法、德、日租界,有似簡易公園,專為洋人散步游覽之區,華人不得越雷池一步)者,拘罰。”[56]從當時的竹枝詞中也可見到漢口民間話語中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記憶,“鴻溝界限任安排,劃出華洋兩便街。莫向雷池輕越步,須防巡捕捉官差”。[57](p.198)有的公園雖然沒有禁止華人入園,但在公園內專門劃定華人游覽區,如天津義國(意大利)公園“東有中國兒童之游戲場及避雨亭,西有西童游戲場及小花亭”,[18](pp.257—258)華人同樣不能越雷池一步。不僅公園的規則嚴重歧視華人,而且有的游覽場所內,華人還要受到侮辱。如日本滿鐵會社在奉天(今沈陽)建的附屬地公園,園內綠樹成蔭,但“華人至其地者,多受日人侮弄,故有識者多不踐足其間”。[21](p.76) 中國人到公園要受到如此多的精神傷害,自然而然會產生強烈的反彈心理與對殖民主義的深刻記憶,當關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言說進入知識精英所主導的公共話語時,遂構成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而且這種記憶會轉化為民族主義意識,正如著名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所言,“只要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歷史事實滲透進入了這種記憶,就會被轉譯成一種教義、一種觀念,或一個符號,并獲得一種意義,成為社會觀念系統中的一個要素。”[57](p.312)歷史證明,公園問題所形成的社會記憶已經轉化為民族主義情緒與實踐,如1925年五卅運動時,上海東吳大學法科學生就在停課宣言中將公園問題與民族主義運動聯系起來,“上海公共租界華人納稅據金額十之九,而工部局董事反不得參加;公園及其他娛樂場所,華人不能入內”,[58]因而,中國人感到生活在殖民主義空間時無處不受壓迫,“直接伏處在洋人勢力之下,往往在一個極普通的去處,可以使你感覺到一種不安”,但也因此讓人們感到“國,是不可不愛的”。[59](p.28)毛澤東甚至將公園問題納入民族戰爭領域來探討:“上海有所謂‘外國火腿’,就是外國人踢了一腳,算作給一個‘火腿’。到上海的人,還看見過有的公園有‘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民族戰爭就反對這些東西。外國民族壓迫中國民族是不行的,我們要獨立。”[60](pp.155—156)關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憤恨不是少數人的感受,而是全民族共同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已經上升為中華民族強烈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精神,這是公園問題上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撞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