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與超越: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的發(fā)展邏輯
王中汝
[摘要] 民主政治的價(jià)值取向,從古代到近代經(jīng)歷了從“揚(yáng)善”到“懲惡”的]化。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借鑒了古典民主重視人民、自由主義民主重視法治與權(quán)力制衡的民主精華,摒棄了古典民主忽視權(quán)力制衡、自由主義民主忽視人的發(fā)展的缺陷,以人的全面發(fā)展為核心價(jià)值取向,重視法治、權(quán)力制衡的政治功能,重視執(zhí)政黨在民主建設(shè)中的巨大作用。遵循這樣的邏輯,以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不斷發(fā)展、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的需要為坐標(biāo),穩(wěn)妥漸進(jìn)地發(fā)展下去,必將創(chuàng)造一種嶄新的民主模式。
[關(guān)鍵詞] 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繼承;超越;發(fā)展邏輯 一、以人的全面發(fā)展為核心價(jià)值取向 民主政治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滿了爭(zhēng)議。把古雅典民主推向顛峰的伯里克利聲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制度,是因?yàn)闄?quán)力不是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全體人民的手中。”[1]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是民主的反對(duì)者,前者認(rèn)為民主制是僅次于僭主制這個(gè)“城邦的最后的禍害”[2],因?yàn)樗安患訁^(qū)別地把一種平等給予一切人”,人們被“容許有廣泛的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行動(dòng),最終導(dǎo)致道德墮落;[3]后者認(rèn)為民主制只為窮人謀利益,違背了“公民的共同利益”,不是“正確的政體”。[4]盡管如此,古典民主的精華卻不容人們忽視,它主張人民主權(quán)(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和積極的公共參與,認(rèn)為公民參與能夠最大限度地培養(yǎng)“公民美德”,甚至走到極端,“每個(gè)忽視參與公共事務(wù)的雅典人都應(yīng)該受到全體公民的懲罰”。[5] 古雅典民主的這種“揚(yáng)善”功能,在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民主那里消失了。洛克、孟德斯鳩等思想家,基于人性自私的理論假設(shè),把民主政治的核心價(jià)值放在防范權(quán)力專斷即“懲惡”上。盡管也有思想家主張民主的“揚(yáng)善”功能,如盧梭強(qiáng)調(diào)人民主權(quán)及公民對(duì)于公共領(lǐng)域的責(zé)任和義務(wù),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認(rèn)為民主政治是人類理性與道德實(shí)現(xiàn)“最高的和諧的”發(fā)展的主要機(jī)制,但這些思想始終沒有成為自由主義民主的主流。進(jìn)入20世紀(jì),民主政治更]變?yōu)橥ㄟ^競(jìng)爭(zhēng)性選舉遴選領(lǐng)袖的制度化機(jī)制。例如,約瑟夫·熊彼特等人的“精英民主”理論認(rèn)為,大多數(shù)選民既是消極的,也缺乏很高的政治水平,其唯一的作用就是參與競(jìng)爭(zhēng)性選舉。輕視公民參與,不承認(rèn)參與在提升公民素質(zhì)上的巨大作用,充分反映了自由主義民主的階級(jí)本性。自由主義者以自由而不是民主為首要價(jià)值,認(rèn)為民主本質(zhì)上意味著“烏合之眾”的統(tǒng)治或“多數(shù)暴政”,是對(duì)個(gè)人自由的潛在威脅。但自由主義者又不能不要民主,他們需要借助大眾的力量反對(duì)封建政治專制。由于這個(gè)原因,民主被框在私有制和原子式個(gè)人自由的狹小籠子里,成為只見競(jìng)爭(zhēng)性選舉而忽視公民素質(zhì)提升的自由主義民主。“民主的理想和方法變成了現(xiàn)行民主制度的理想和方法。既然甄別不同民主理論的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是其‘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程度,那么,那些背離當(dāng)前民主實(shí)踐,或者與這種實(shí)踐不十分和諧的模式,就可能被錯(cuò)誤地看作是在經(jīng)驗(yàn)上不精確的、‘不現(xiàn)實(shí)的’和不可取的模式”[6],從而成為“限制了那些尋求其他合理政治模式”的政治“壟斷行為”[7]。 對(duì)于自由主義民主或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馬克思主義的評(píng)價(jià)很客觀。馬克思、恩格斯稱贊“資產(chǎn)階級(jí)在歷史上曾經(jīng)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無情地?cái)財(cái)嗔税讶藗兪`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8],消除了等級(jí)特權(quán)和封建割據(jù)。列寧也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邁進(jìn)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步”[9]。自由主義民主的局限性,主要是其自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即一方面主張政治平等,另一方面主張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無視由此造成的極大的經(jīng)濟(jì)不平等,從而使得人的解放只停留在政治層面。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列寧批評(píng)“資本主義社會(huì)里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shù)人享受的民主”[10]。晚近以來,部分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的主流政治學(xué)家也開始正視這個(gè)問題。達(dá)爾指出,在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積累無限經(jīng)濟(jì)資源的自由”[11]所形成的“資源的不平等造成了公民中嚴(yán)重的政治不平等”,致使“民主的道德基礎(chǔ),即公民之間的政治平等遭到嚴(yán)重的破壞”,“民主政治制度同非民主的經(jīng)濟(jì)制度的關(guān)系在整個(gè)20世紀(jì)中對(duì)民主的目標(biāo)和實(shí)踐提出了嚴(yán)厲而持久的挑戰(zhàn)”[12]。實(shí)際上,達(dá)爾所說的這種“嚴(yán)厲而持久的挑戰(zhàn)”,從自由主義即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制度確立那一刻就開始了。那就是社會(huì)主義民主理想與制度實(shí)踐的出現(xiàn)。 社會(huì)主義民主,就其性質(zhì)和享有主體來說,是全體人民共同建設(shè)、共同享有、當(dāng)家作主的民主,也是工人階級(jí)政黨領(lǐng)導(dǎo)、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管理和監(jiān)督的民主政治制度。社會(huì)主義民主是對(duì)自由主義民主的揚(yáng)棄,它批判地繼承了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中具有普遍價(jià)值的內(nèi)容,特別是人民主權(quán)思想,揚(yáng)棄了自由主義民主的狹隘性,不僅重視個(gè)人的民主權(quán)利,更重視以工人階級(jí)為主體的勞動(dòng)階級(jí)的民主權(quán)利,認(rèn)為只有在經(jīng)濟(jì)解放和社會(huì)解放中才能充分實(shí)現(xiàn)人類解放。社會(huì)主義民主并不否定資產(chǎn)階級(jí)政治革命的歷史意義,但認(rèn)為這是不夠的,必須在這個(gè)基礎(chǔ)上進(jìn)行經(jīng)濟(jì)革命和社會(huì)革命,把民主原則從政治領(lǐng)域貫徹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領(lǐng)域,在保持形式民主的同時(shí)獲得實(shí)質(zhì)民主,使每個(gè)社會(huì)成員都可以平等、自由、自主地參加社會(huì)公共事務(wù)的管理。社會(huì)主義民主的第一次偉大實(shí)踐,發(fā)生在俄國。列寧非常重視發(fā)展社會(huì)主義民主,認(rèn)為“勝利了的社會(huì)主義如果不實(shí)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13],強(qiáng)調(diào)要“徹底發(fā)展民主,找出徹底發(fā)展的種種形式,用實(shí)踐來檢驗(yàn)這些形式等等”[14]。由于列寧過早逝世,后來的蘇聯(lián)直到共產(chǎn)黨失去政權(quán)、國家解體,都沒有很好地解決民主問題。從蘇聯(lián)到東歐國家,也包括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中國的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實(shí)踐,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沒有商品經(jīng)濟(jì)的充分發(fā)展,就沒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權(quán)等觀念產(chǎn)生,也不可能建立起民主政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的脈絡(luò)也逐漸清晰起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huì)主義,就沒有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15],從20世紀(jì)80年代到現(xiàn)在始終是中國政治建設(shè)的指導(dǎo)理念,黨的十七大更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huì)主義的生命。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本質(zhì)上是人民當(dāng)家作主。在民主的哲學(xué)前提上,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不同于自由主義民主建立在人性“惡”的假設(shè)以及個(gè)人主義基礎(chǔ)之上,而是以承認(rèn)合理個(gè)人利益的集體主義為基石。在民主的目的上,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不同于自由主義民主只重視防范權(quán)力專斷,而以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為自己的最高命題。在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中萌芽,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制度,以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作為自己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保障,而不同于自由主義民主把“非民主的經(jīng)濟(jì)制度”即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作為自己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在制度保障上,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以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度、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自己的基本骨架,在這個(gè)基礎(chǔ)上發(fā)展各個(gè)層次、各種形式的民主及民主機(jī)制,確保人民當(dāng)家作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jiān)督、民主管理在多個(gè)方面得到實(shí)現(xiàn),不同于只重視“權(quán)力競(jìng)爭(zhēng)”而忽視人民參與的自由主義民主。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的最大特點(diǎn),在于它的基本價(jià)值取向是促進(jì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并以此使自己區(qū)別于歷史上各種民主制度,包括蘇聯(lián)模式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條件下高度集權(quán)的“民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汲取了為自由主義民主所摒棄的古典民主精華,繼承了自由主義民主的政治平等主張,通過揚(yáng)棄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和按資分配,有效克服了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中政治平等與經(jīng)濟(jì)不平等之間的矛盾,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新型民主政治模式。 二、從人治逐步走向法治 實(shí)行法治,是當(dāng)代民主政治的一大特征,也是自由主義民主對(duì)人類政治發(fā)展的重要貢獻(xiàn)。法治要求政府、政黨、公民和各種社會(huì)行為主體的一切活動(dòng)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jù),不允許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quán)存在。作為一種治國方略,法治是與那種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個(gè)人說了算的“人治”相對(duì)立的。法治與法制不同,前者所要求的“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礎(chǔ)上的“良法”,要求法律本身即最高權(quán)威;后者指的是靜態(tài)的法律制度,而不管其性質(zhì)如何。法治必然包括法制,而法制卻不一定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只存在于民主政治之中,法制可以存在于任何社會(huì),甚至存在于封建專制政治中。 1978年以前,“人治”是中國政治的基本特點(diǎn),權(quán)力過分集中于個(gè)人。毛澤東認(rèn)為,“……不能靠法律治多數(shù)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的各種規(guī)章制度,大多數(shù)、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huì),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劉少奇也曾經(jīng)提出:“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shí)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兩位開國元?jiǎng)椎恼f法,實(shí)際上反映了當(dāng)時(shí)大多數(shù)人的認(rèn)識(shí)——不能正確認(rèn)識(shí)法律的重要性,更不理解法治的真諦。基于對(duì)歷史教訓(xùn)的反思,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提出民主必須法律化、制度化的政治建設(shè)任務(wù),1982年憲法也規(guī)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jī)關(guān)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huì)團(tuán)體、各企業(yè)事業(yè)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dòng)準(zhǔn)則,并且負(fù)有維護(hù)憲法尊嚴(yán)、保證憲法實(shí)施的職責(zé)。”這里的各政黨,當(dāng)然也包括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chǎn)黨。社會(huì)主義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執(zhí)政黨也不能凌駕于憲法之上,這已經(jīng)接近了法治的真諦。20世紀(jì)90年代后,中國共產(chǎn)黨對(duì)法治的認(rèn)識(shí)逐漸深化。1996年2月初,江澤民指出:“加強(qiáng)社會(huì)主義法制建設(shè),依法治國,是鄧小平同志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huì)事務(wù)的重要方針。”[16]3月,“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制國家”被寫入《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九五”計(jì)劃和2010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綱要》。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江澤民對(duì)依法治國作了更系統(tǒng)的表述:“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wù),管理國家經(jīng)濟(jì)文化事業(yè),管理社會(huì)事務(wù),保證國家各項(xiàng)工作都依法進(jìn)行,逐步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lǐng)導(dǎo)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lǐng)導(dǎo)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7]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huì)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治國家”寫進(jìn)了憲法,從根本大法的高度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和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目標(biāo)。2002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紀(jì)念憲法施行20周年大會(huì)上的講話中再次強(qiáng)調(diào),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jī)關(guān)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huì)團(tuán)體、各企業(yè)事業(yè)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dòng)準(zhǔn)則,并負(fù)有維護(hù)憲法尊嚴(yán)、保證憲法實(shí)施的職責(zé)。 從“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卻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shè)進(jìn)程中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治國家,需要防范并克服兩種相互聯(lián)系的片面傾向,即法治虛無主義和法治浪漫主義。法治虛無主義過于重視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道德的作用、人的義務(wù)履行,忽視法律的功能與邊界、人的權(quán)利保障。法治浪漫主義則認(rèn)為法治無所不能,超越時(shí)空,忽視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法治的特殊性、中國法治進(jìn)程的漸進(jìn)性以及法治自身的局限性。[18]中國具有數(shù)千年的以法“治民”的“人治”歷史,卻缺乏以法“治官”、“治權(quán)”的法治傳統(tǒng)。在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歷史進(jìn)程中,一定要準(zhǔn)確把握復(fù)雜的國情,逐漸削弱人治的消極影響,增強(qiáng)法治約束權(quán)力、規(guī)范社會(huì)行為的作用。可以說,中國法治的實(shí)現(xiàn)程度,取決于中國共產(chǎn)黨推進(jìn)法治的政治意志,更取決于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程度與社會(huì)的成熟程度、自主程度。 三、從高度集權(quán)走向適度分權(quán) “一切有權(quán)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quán)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jīng)驗(yàn)。有權(quán)力的人們使用權(quán)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從事物的性質(zhì)來說,要防止濫用權(quán)力,就必須以權(quán)力約束權(quán)力。”[19]防范權(quán)力專斷與肆虐,是自由主義民主的精髓所在,但這并不妨礙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對(duì)于權(quán)力制衡的需要。“斯大林嚴(yán)重破壞社會(huì)主義法制,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他雖然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但是,由于沒有在實(shí)際上解決領(lǐng)導(dǎo)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dǎo)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gè)教訓(xùn)是極其深刻的。”[20]斯大林破壞法制“這樣的事件”為什么在西方發(fā)達(dá)國家不可能發(fā)生?因?yàn)檫@些國家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已經(jīng)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約機(jī)制,具體表現(xiàn)為“三權(quán)分立”的權(quán)力運(yùn)行模式。

代電影技術(shù).jpg)
踐.jpg)
學(xué)分子生物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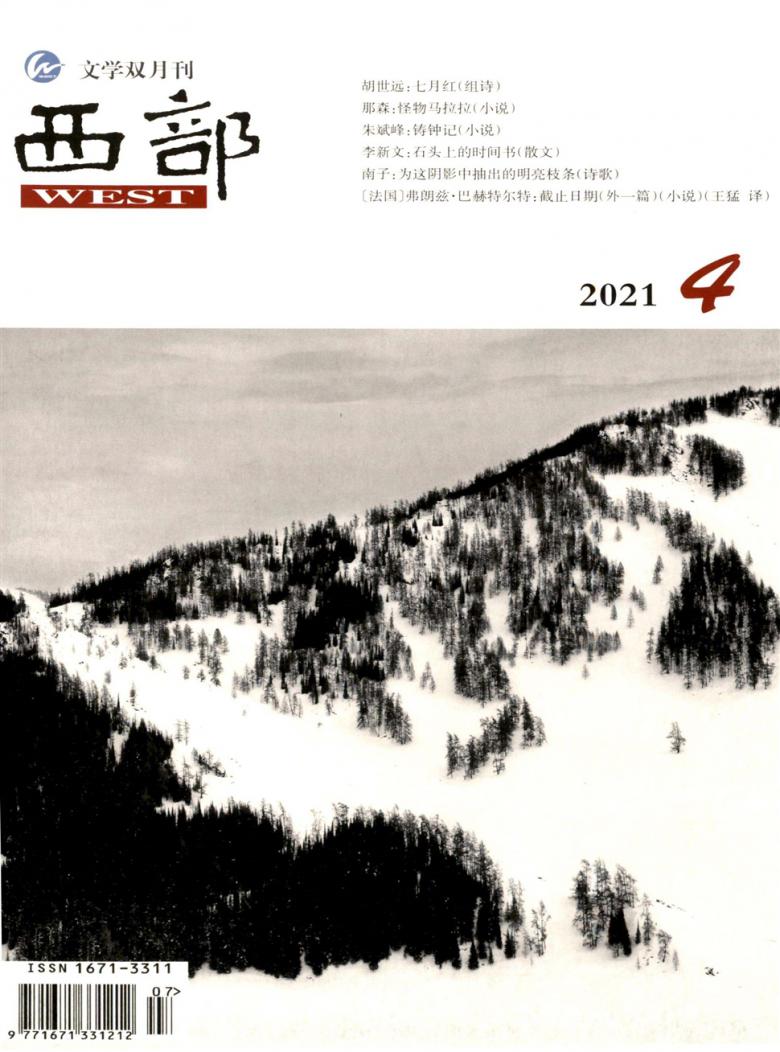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