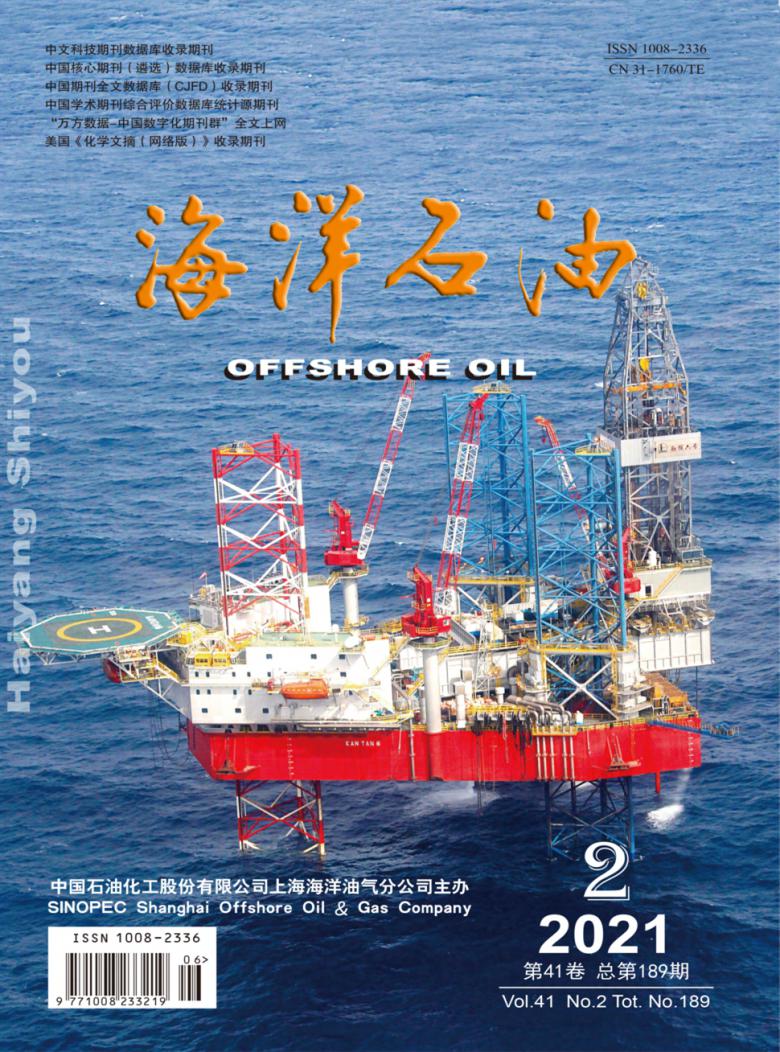“中國農村派”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上)
雷頤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長期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作為在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指導理論。這一理論體系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的理論”,另一方面是有關革命成功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社會如何建設的理論。由于后一方面在奪取政權之前對中國共產黨只是一種尚不具實踐意義的理論設想,所以當時內容最豐富、最富創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論吸引力和征服力的還是它的第一個方面,即作為一種“革命的理論”。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這“三座大山”作為革命對像,是以它對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闡釋和界定為基礎的。無疑,這種闡釋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當然有多種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與一大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且受過良好現代社會學訓練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對中國農村所作的深入細致的社會調查和研究分不開的。事實上,正是他們(后來被稱為“中國農村派”)在30年代以現代社會學的“科學”語言和方法,以大量詳細的調查數據,公開論證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的努力成果,實際上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和基礎。但是,對此卻一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認識。因此,本文擬對1928━1935年間“中國農村派”有關中國農村、中國社會的理論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視,并試圖由此對他們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一恰當的歷史定位,藉此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商榷之資和引玉之磚。
一
“中國農村派”是在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刻,中國理論界(包括馬克思主義派與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派)必須重新認識、界定中國社會性質,并為此幾次激烈論戰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當2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之時,便爆發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首次論戰。1920年11月張東蓀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的時評【1】,認為中國的救國之道唯在開發實業,“而不是歐美現成的甚么社會主義、甚么國家主義、甚么無政府主義多數派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當在另一個地方。”正這篇短短的時評,觸發了關于社會主義、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首次論戰。
張文發表后,陳望道、李達、陳獨秀、蔡和森等馬克思主義者立即對此進行反駁,他們認為張東蓀以“發展實業”來反對各種主義其實質是以發展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而張東蓀、梁啟超又發表了多篇文章詳論自己的觀點。大體說來,張、梁一方認為中國目前根本談不上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更無從言及社會主義。所以希望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行以階級調和、勞資合作為特色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而這,自然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同意的,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與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雖有所不同,但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能夠走社會主義之路。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尚極簡陋,遠談不上一種“社會學”的方法。如陳獨秀這樣“論證”:“請問中國無勞動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車船,是何人做出來的?先生所辦的報,是何人排印出來的?”【2】蔡和森則斷定“全國人民除極少數的軍閥、財閥、資本家以外,其余不是無產階級,就是小中階級,而小中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的候補者。”【3】可以看出,他們的論斷還只限于一般性論述,只是套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論斷,根本沒有以各種統計數字為基礎的實證性分析說明,自然缺乏理論的說服力。對中共來說,中國社會性質是什么仍是一個沒有解決但卻無法回避的理論問題。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對此卻無明確、統一的看法。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較為發達,所以國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資本主義社會,要待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之后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有的則認為中國資產階級直接間接都是帝國主義的買辦,均屬革命對象。1927年4月國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敗。那么,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失誤還是一種理論指導的錯誤?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性質是什么?中國的社會性質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實踐”把理論推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一文中寫道:“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是一個舊問題同是時又是一個新問題,因為這一問題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生長以前擺在我們面前,但在理論上從未獲得正確的解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或已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革命?這一根本問題將決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戰術與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對“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釋:“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資產階級的方式占優勢(土地可以買賣),地主對于農民的剝削關系是封建的方式占優勢(如農產物交租和勞役制的殘余),所以中國農村經濟關系是一種半封建制度。”【5】對此,已被免除總書記職務的陳獨秀,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概括地說,他認為商業資本的發展、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他的這一觀點,在《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統的闡發【6】。這種觀點亦成為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第二次論戰中“托派”的主要論點。
面對這些論點,中共理論家必須作出回答,這就開始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二次論戰。李立三撰寫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這一長文,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論證“現在社會組織的經濟基礎是建筑在城市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鄉村封建生產方法上,而封建的剝削關系,仍然是占優勢。所以上層的政治組織毫無疑問的是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即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聯盟。”而陳獨秀等“否認封建勢力的存在,就是不愿農民的革命的反動理論的根據。”【7】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對“半封建”的解釋與共產國際對這一概念的解釋已略有不同,即中國社會既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又有封建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資產階級的方式占優勢”而“剝削關系是封建的方式占優勢”。后來,中國共產黨對“半封建”的解釋也大體如此。1929年1月,李達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書中開始運用一些統計資料,力圖論證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便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年11月,共產黨在上海創辦了《新思潮》雜志,并于翌年4月出版了“中國經濟研究專號”,發表了多篇共產黨理論家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之一是不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開始注重以各種數據和材料作為分析的基礎,論證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了反駁中共的理論觀點,“托陳派”也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其中以嚴靈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盡管他們二人的論點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擊,但其基本觀點卻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國主義的擴張“不但不保持封建勢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他們并引用了更多的數據來論證此時“中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是有蒸蒸日上之勢”。二,他們根據大量海關統計數字、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增加及民族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認為“我們很可以肯定的結論道: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三,他們認為商品化的發展和農機的使用,使“中國農村經濟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經濟而是處于商品經濟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來自給自足的封建性的生產,便日益崩潰,以至到微不足稱的殘余地位”。【8】如果說前此陳獨秀的著作尚屬一種抽象的泛論,僅提出了一般性的論點,那么任、嚴的著述則引用了大量的數據以為陳的論據。
這樣,中共理論家必須對這些數字與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釋,因而提出“死的數目字與活的解釋”這一問題。他們認為“托陳派”只是玩弄數字游戲,把“個別”當“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實質。如他們認為海關冊上外貿數字表明農產品出口的增加恰說明是“農村破產,生產力降低的結果,而不是資本主義農莊發展,即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進口的主要是工業品,恰恰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對土地的高度集中,他們也認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來用農機雇傭農民,而是仍將其分成小塊租給農民,仍是封建剝削關系。【9】根據同樣的數據,雙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與第一次論戰相比,這次論戰表明中國的理論界在這短短的幾年間無疑有了非常明顯的進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概念開始具有較確切的函意,并開始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由于中國農村的社會狀況極其復雜,而這次戰對決定中國社會性質的農村的論述卻依然籠統,也就是說對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這一極為宏大的理論概念依然缺乏詳細、充份的論證,因此整體的理論建構尚無法完成。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和論戰。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論證和確立,而這一理論工作主要是由“中國農村派”完成的。
二
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但長期以來卻未得到理論界和社會科學界應有的重視,甚至中共中央此時也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尤其注重“無產階級較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對農村的實際和理論的調查研究亦不能說充分。【10】但是,有一批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家幾年來卻一直作著雖不引人注意、但卻深入細致的中國農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而被稱為“中國農村派”。30年代中期關于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使他們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廣泛的注意,而他們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斷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意義則更為深遠。
在他們的工作中,曾在美、德兩國留學的陳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陳氏于1915年赴美留學,于1921年以論文《茶葉出口與中國內地商業的發展》獲波莫納大學(Pomona College)碩士學位,畢業后又到哈佛大學進修訪問。不久又到德國柏林大學東歐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員,并于192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即應蔡元培之邀回國在北大任教。這些經歷,使他對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有著頗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間,他因李大釗影響而信仰馬克思主義,并于1926年經李大釗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的介紹加入第三國際。1927年春,他來到莫斯科第三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任研究員,開始了對中國農民運動和農村問題的研究。在此間,他與國際的中國農村問題專家馬季亞爾(L。Madjar)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發生爭論。馬氏認為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而“我認為,中國農業基本上是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性質。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國農村的具體情況,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實例來駁倒馬季亞爾”,“因而決心返回祖國后,一定要對中國的社會作一番全面的調查研究。”【11】
陳翰笙回國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副所長,實際主持所務,開展了廣泛細致、現代社會學方法的中國農村社會調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錢俊瑞、張錫昌、張稼夫、孫冶方、姜君辰、薛暮橋、秦柳方等多人參加調查工作。后來,其中不少成為中共極有影響的經濟理論工作者。從1929年開始,他們先后在江蘇無錫、河北保定、廣東嶺南、廣西、河南、陜西等地選點進行詳細的調查。同時,他們又組織力量去營口、大連、長春、齊齊哈爾等地調查東北難民問題。為了了解國際資本對中國農村的具體影響,他們對與國際資本聯系較為密切的煙農狀況還作了專門調查。他們的調查結果出版了《畝的差異》《難民的東北流亡》《黑龍江流域的農民和地主》《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系》《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之發軔》《東北的難民與土地問題》等許多專題論文或論著。許多調查報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因其資料翔實而被納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農復會的調查系列。而陳翰笙于1933年發表的英文著作《現今中國的土地問題》(不久即譯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廣東農村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都獲得了極高的聲譽,前者被太平洋國際學會認為是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權威之作。陳氏的指導思想是:“一切生產關系的總和,造成社會的基礎結構,這是真正社會學的研究的出發點,而在中國,大部分的生產關系是屬于農村的。”“農村諸問題的中心在哪里呢?它們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與利用,以及其它的農業生產手段上:從這些問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農村生產關系,因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意識。”對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農村調查,他批評說:“它們都自封于社會現象的一種表列,不會企圖去了解社會結構的本身。大多數的調查側重于生產力而忽視了生產關系。它們無非表現調查人的觀察之膚淺和方法之誤用罷了。”【12】而這也就是他們調查研究的理論指導。
例如,無錫農村經濟調查團成員有45人,在調查前學習了《資本論》的有關章節,并重點研究了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力求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說明農村生產關系,社會性質,并依此理論設計調查方案。他們用階級關系、地位來對農戶進行分類,即將農戶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用此取代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分類法,即將農戶分為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或分為小農戶、較大農家、大農家、更大農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個月中,調查團對無錫縣22個自然村的1204戶農家進行了逐戶詳細調查。同時還對附近55個村莊的概況和8個農村市鎮的工商業作了調查,以對調查對像與周圍環境和背景的關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對保定清苑農村進行調查,由于清苑各鄉地勢水利差異大而村戶田權尚無較大分化,所以“調查團按農作水利將全縣分為4個區。每區選擇最普通村莊作分村經濟、村戶經濟、城鎮分業和農戶,抽樣4種調查。第一種注重分配,第二種注重生產,第三種注重交換,第四種注重消費。”共在6個農村市場、78個村莊和11個村的1773個農戶進行了詳細調查。1933年11月--1934年5月他們又對嶺南農村作了詳細調查,首先對中山等16個縣作了全面系統調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對番禺縣10個代表村1209戶農家作了具體調查研究。同時又對廣東省另50個縣的335個村作了通訊調查。【13】這些調查活動其對象典型,組織安排科學,調查手段和技術靈活多樣,因地置宜,是歷史唯物主義、現代社會學與中國農村社會實際結合得較為成功的一次社會實踐。這三個地方的自然條件、社會環境、土地關系及雇傭關系都非常不同,但陳翰笙以大量的調查和精心的設計向人們說明盡管有此種種不同,但農村問題的實質無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關系問題。中國的土地問題之所以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問題,并不僅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貸所能解釋的。實際上,土地問題所反映出的復雜的社會經濟政治關系,即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才是問題的所在。通過對不同地區的“農村經濟”的調查研究,說明的卻是有關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政治關系的普遍性質,這確是陳翰笙的過人之處,也是他與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區別之所在。【14】
稍后,在陳翰笙等創辦的《中國農村》月刊上,陸續發表了一些“怎樣做農村調查?”“農村經濟的調查和統計”等有關調查統計方法的文章,引導人們從這樣的角度和目的來作農村調查:“我們的調查,首先要研究帝國主義怎樣侵略中國農村,妨礙農業生產的發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分配,地主豪紳的各種榨取方式,以及他們同帝國主義和都市資本之間的聯系。第三要研究各類農民的經濟地位,他們的生產方式和農村勞動大眾所受到的各種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種復興政策的意義和效果,暴露各種改良主義的本質,并替農村勞動大眾指示一條正確的出路。”強調“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確的社會意義”,“在我們把一大堆的調查材料著手統計之前,首先就要考慮到分類問題”。在按量和按社會性質這兩種分類法中,又強調按社會性質、“根據著土地關系和雇傭關系”將農民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這五個階層,“這是最科學的分類方法”。由此出發,調查設計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況,租佃關系,雇傭關系,借貸關系,田賦、稅捐、攤派、勒索、勞役,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同鄉公所的關系,帝國主義、買辦資本同地主豪紳間的聯系,帝國主義、買辦資本怎樣操縱農產品價格或用其他方式剝削農民。在這種理論構架和方法的引導下,結論是很明顯的【15】。
所以有人說:“現階段的中國農村研究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算具備了微弱的基礎。這種研究有別于前階段的農村研究者三:第一,它的出發點是農村生產關系的徹底改造;而后者乃從舊秩序的持續和局部改良出發。第二,現階段研究的對象是農村社會的生產關系,而前階段則著重于生產力的技術分析(并非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形態)。第三,現階段的研究方法,是從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適應和矛盾的過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質與歸趨;而前此的研究則把事物的片段,孤立起來,僅僅從事于靜止的觀察。”【16】
另外,中共黨員、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李平心(李于1927年參加共產黨,1932年參加“社會科學家聯盟”1936年參加陳翰笙發起成立的“中國農村研究會”)在1932年6月寫就的《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方法論》一文,已用相當成熟的“辯證法”語言提綱攜領地結合中國實際闡明了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他對矛盾是事物的發展運動的動因、矛盾的對立統一、互相轉化、普遍聯系、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量變質變規律等方面的論述尤為深刻。但遺憾的是,該文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建設的意義后來遠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承認。限于篇幅,本文僅能概述其要點:他認為形式邏輯與形而上學的機械“均勢論”都不能正確了解認識中國農村,“形式邏輯不承認事物的矛盾性之存在,完全建筑于陳死的、凝固的、空虛的概念之上”,“只能認識事物的靜態”,“不能從事物的矛盾中,在流動發展中,與事物的聯系和互動中去把握實際,即是不能捉住諸事物的過程與動態以及它們內部對立性的統一和相互轉變”。依此觀點推論,“則帝國主義商品之流入農村,只有促成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化”,而“不能指出帝國主義假手于中國的封建軍閥和豪紳買辦剝削農民的事實”;“只能看見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與地主勢力的分立,而不知道它們往往是勾結起來剝削和壓迫農民的。”若是“機械地、抽象地把握到事物的類似,由此而構成一種沒有內容的概念”。例如在分析農村中的社會階級關系時,便會“將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雇農等一概歸納而為同一范疇,而對于他們之間的差別性無條件地抹煞了”,終將導致對階級關系和剝削關系的抹煞。而且,“機械的均勢論不了解對立的統一法則,即是不了解事物運動的基礎在于它本身一切聯系中所包含的諸矛盾性與對立的相互轉變,……”;“抹煞質與量的差異性,企圖將一切高級的復雜的運動還原為單純的機械運動,否認高級形態的事物之特殊性”,“把個別的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暫時的相對的均衡普遍化、絕對化,而由此來確立事物存在之一般的基礎。”所以說“唯物辯證法是最正確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其第一個規律“就是事物的矛盾性之發展與轉變”,“因此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注意這些矛盾的關系之發生與轉化。要考察各種矛盾的實質與內容是什么,要追溯各種矛盾之史的發展與轉變。”所以不能孤立地從土地買賣、高利貸的發達等來斷定中國農村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而應看到這些因素在中國社會現實中反而轉化為封建性剝削。另外,既要看到中國與世界聯系(殖民地)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特殊性,“我們必須認識這種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這種辯證法的統一”。因此應該看到世界資本主義農業危機對中國農村的影響,但又不能認為中國農村是資本主義性質進而用資本主義農業經濟危機的理論解釋中國農村的深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