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困境與出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民主法治之間
吳容 張放
論文關(guān)鍵詞: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文化精神民主法治
論文摘要: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式、社會控制模式以及價值系統(tǒng),不僅強調(diào)國家通過法律來控制社會,而且也強調(diào)國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為西方文明產(chǎn)物的法治有著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礎(chǔ),體現(xiàn)出人權(quán)、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不具備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入手,探討了我國法治進程中應(yīng)正視和思考的幾個問題。
一、困境: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推進民主法治的消極作用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冬的政治和經(jīng)濟。本文在使用文化這個概念時,僅指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發(fā)展中所內(nèi)化而成的一套價值觀念和評判標準,并表現(xiàn)為一種普遍、持續(xù)和較為穩(wěn)定的思維與行為的方式。簡言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共同具有的觀念與標準.即觀念文化。
作為近代西方文明產(chǎn)物的法治,體現(xiàn)出了人權(quán)、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基礎(chǔ)上,秉承儒家“內(nèi)圣外王”的指導(dǎo)思想,經(jīng)封建君主專制的固化長期沉淀而成的。契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是“德治”或“人治”,這便成了在中國推行法治之艱難的社會心理因素。
(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基于血緣紐帶的宗法倫理導(dǎo)致了權(quán)力絕對化
宗法倫理是原始社會父系家長制公社成員之間的親族血緣關(guān)系和社會政治關(guān)系密切交融的產(chǎn)物,其直接表現(xiàn)為等級制和禮教。根據(jù)宗法制原理,與國君血緣最近的、輩分最近的在政治上地位最高,相反則政治地位低。而禮教則把宗法人倫等級制度以文化的形式正式固定下來,成為維護等級制度的精神工具。“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基于血緣紐帶的宗法倫理,只承認人倫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存在,而否認個人可以獨立于這種關(guān)系之外享有的民主權(quán)利,整個社會就分成尹命令和服從兩個等級。個人毫無權(quán)利可言,沒有公平、正義,只有絕對的服從,權(quán)力由此而絕對化了。
宗法倫理形成的文化,導(dǎo)致人們在進行行為選擇時,總是首先考慮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會不會使當權(quán)者的利益受損,而不管是否符合正義或是法律。對上級的絕對服從.反過來必然導(dǎo)致對普通民眾權(quán)利和法律規(guī)則的視而不見。權(quán)力的絕對化還會導(dǎo)致對權(quán)力的絕對崇拜。權(quán)力本位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人的個體主體意識喪失,權(quán)利意識、平等觀念匾乏,不能形成追求正義、公平、權(quán)利、自由的行為模式。
(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義致使對法律權(quán)威的信仰難以樹立
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shè)。它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法律權(quán)威信仰是民主法治社會人們普遍守法的情感基礎(chǔ)。在西方文明中,這一信仰己憑借宗教對上帝權(quán)威的信仰而內(nèi)化為每個成員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對上帝的忠實信仰,法律權(quán)威淵源的合法性得到鞏固。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由于古往今來強烈的法律工具主義性質(zhì)和意識,使得人們難以產(chǎn)生神圣的法律情感,而法律情感恰恰是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礎(chǔ)。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作為人文精神載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宗法倫理”,而非“宗教倫理”,它的目的是為了純粹的實用,因政治而生,又被專制政權(quán)所利用,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本身缺乏對公平、正義與公正的追求。法律只是一種統(tǒng)治手段,不體現(xiàn)公平和正義,人們也只是敬畏法律而非信仰法律,法律權(quán)威的神圣性并不存在,因而社會心理中也就難以樹立對法律權(quán)威的信仰了。
(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強調(diào)國家本位主義,忽視個人權(quán)利自由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使人們長期意識不到對社會的獨立性,不能從社會中分離出來。專制政治的目的是為專制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和統(tǒng)治者利益的實現(xiàn)服務(wù),強調(diào)整體為本位,把整體看做起點、核心和目的,整體利益高于一切;個體沒有任何地位,個體不是作為個體而是作為整體的部分而存在。絕對整體主義的道德要求個人無條件服從整體,為整體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要求個體完全融于整體之中。個人不得有個性和人格,更談不上獨立、權(quán)利、價值和尊嚴。
從文化發(fā)生學的角度看,人類建立個性主體觀念走過了兩個歷程:一是人類擺脫對自然的依賴,二是擺脫對社會(家庭、組織)的依賴。后者在中國至今尚未完成,而且其進程也是緩慢的。強調(diào)國家利益,要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注重團結(jié),這本是中華民蘇的美德,但是如果這種妥協(xié)沒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為社會主體的個性。而尊重人的權(quán)利、自由和個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今天國家本位主義的法律傳統(tǒng)雖然在制度層面上已經(jīng)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著人們的思想,這直接導(dǎo)致了現(xiàn)今我國公民對權(quán)利的不尊重,維權(quán)意識的淡薄。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號下。中華民族的人民習慣了順從、忍讓.無形中導(dǎo)致了對法律的輕視、遠離和不信任,因此他們難以真正地以納稅人的身份理直氣壯的監(jiān)督政府行為,理所當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權(quán)利,不卑不亢與政府對話。
二、關(guān)于文化的兩對范疇:民主與法治論題下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確實對推進民主法治產(chǎn)生了消極影響和一定程度的阻礙。但如何才能突破困境,找到由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通向民主法治的出路呢?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兩對范疇:一是文化的道德層面與法律層面;一是學術(shù)思潮與社會心理。
道德層面和法律層面是文化的兩個基本層次。道德層面的文化主要是一種觀念形態(tài),它以一些社會公認的價值準則為內(nèi)核,來指導(dǎo)和制約著人們的個人行為,因而也具有社會規(guī)范的作用。法律層面的文化與道德層面的文化不同,往往帶有國家意志屬性和廣泛的約束力,調(diào)整的強度也要大于后者。但某些情況下,二者是可以互相轉(zhuǎn)化的,某些公認的社會道德也可能上升為法律,成為法律層面的文化淵源之一。由此可見,法律與道德之間有著密切聯(lián)系:前者體現(xiàn)的是國家強制的普遍性;后者體現(xiàn)的則是意志自由與自覺的個體性。二者調(diào)整的范圍與方式均有所不同。
著名學者梁治平曾經(jīng)指出中國古代法律隱含了“一個絕大的秘密,即道德的法律化與法律的道德化”。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法往往包括禮儀、倫常等的道德內(nèi)容,刑罰制裁與道德禮教互為表里,道德的內(nèi)在要求被賦予法律的形式而得以表現(xiàn)。這就形成了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基本特征之一的泛道德主義”在法律領(lǐng)域的具體表現(xiàn),而泛道德主義對中國傳統(tǒng)法文化的性格形成有著全面而深遠的影響。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使得法律與其本身所固有的確定性相沖突,另一方面也阻礙了道德的理性化。道德產(chǎn)生于人的思想,必須以自由為前提。但“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的事務(wù),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guān)來主持”困。因此,以執(zhí)行法律的方式來強調(diào)道德,在某種程度上是壓制了道德,從而使得思想的自由沒有發(fā)展的空間。
道德層面與法律層面是文化的兩種靜態(tài)劃分,而學術(shù)思潮和社會心理則是文化發(fā)展過程中兩個密切相關(guān)而又各具特色的階段。學術(shù)思潮是某種具有代表性的學術(shù)觀點在學術(shù)界內(nèi)引起了多數(shù)人的共鳴而形成的思想潮流:而社會心理是指社會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性格、感情、愛好以及習慣等心理特質(zhì)的總和。一般來說,一種文化的發(fā)展與變化以學術(shù)思潮為先導(dǎo),而變化發(fā)展的結(jié)果則體現(xiàn)在社會心理上。
從社會心理的層面來看,決定一個人思維與行為方式的主要因素是內(nèi)在趨利避害的本性和外在環(huán)境的某種規(guī)律性。對文化所作的任何結(jié)構(gòu)性解釋,也是按照個體心理作出的解釋,但他既依據(jù)心理學,也依賴歷史。人們對自己行為的決定一般并不是以所謂“文化”為取向,而是以現(xiàn)實過程中的利害關(guān)系為依歸。而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個民族,將本民族在人類文明進步的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價值觀加以積累,使某種觀念在人們心理中凝聚,經(jīng)過世代相傳從而形成該民族一種“超穩(wěn)定形態(tài)”的民族法律社會心理,成為千百年來民族文化傳統(tǒng)積淀的產(chǎn)物。因此,學術(shù)思潮本身與民族文化之間并無必然聯(lián)系,而民族社會心理才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礎(chǔ)。那么很明顯,不管古代典籍中存在多少體現(xiàn)民主與法治的成分,不管其記載的學術(shù)思想有多么先進,如果它沒能轉(zhuǎn)化為社會心理,則仍舊不能說它是民族文化的體現(xiàn)。
三、出路:在傳統(tǒng)文化與民主法治之間
基于以上兩對范疇的分析,可以得出結(jié)論,在尋求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到民主法治的出路之時應(yīng)當從兩個方面著手。
(一)為法律和道德正位,抑制泛道德主義的影響,推動法律成為最主要的社會控制方式
法律與道德將人區(qū)分為外部行為與內(nèi)在精神世界。法律對人的行為的規(guī)制是直接的、強制性的,制裁力度較大;而道德對人的行為的約束是間接的,非強制性的,制裁力度與前者相比也較小,只能通過自我良心、社會輿論等潛移默化地發(fā)揮作用。因此,法律的規(guī)制才是客觀的、確定的,并具有相當?shù)姆€(wěn)定性,其約束效果明顯優(yōu)于道德。再次,道德的作用需要權(quán)威的支持。在其它一些形式的社會中,宗教組織、社會組織常作為支撐的力量。但在以市場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現(xiàn)代社會中,法律是唯一的權(quán)威,道德規(guī)范對人的有效約束必須借助法律的權(quán)威方可建立。 所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泛道德主義是不能適應(yīng)現(xiàn)代民主法治社會的需求的,也不可能產(chǎn)生適應(yīng)現(xiàn)代民主法治需要的新文化。實現(xiàn)民主法治的過程,必須完成現(xiàn)代民主法治社會的傳統(tǒng)文化更新,而傳統(tǒng)文化的更新和進步也并不意味著完全驅(qū)除道德對法律的作用。換言之,法律和道德在現(xiàn)代民主法治社會是兩種不可或缺的社會控制方式,我們要做的只是擺正二者各自的地位和關(guān)系。由此,筆者提出“法主德輔”的思路,即以法治為價值目標,以法律和道德為共同手段,來推動我國的法治進程。具體的現(xiàn)實途徑主要有:
1.客觀評價道德的規(guī)范作用,加強以法制為支撐的制度建設(shè)。不可否認,目前在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下,有過分高估道德的規(guī)范作用的傾向。在某些領(lǐng)域,對個人行為依靠道德進行自律的方式寄望過高,實際效果也不盡人意。這實質(zhì)上是傳統(tǒng)“人治”遺留下來的影響。而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研究成果認為,人是“經(jīng)濟人”,不僅會作出“利己”的選擇以實現(xiàn)個人福利和效應(yīng)最大化,而且還會作出損人利己的“敗德行為”。因此,必須重新客觀評價道德約束的實際效果,改變過分倚重個人道德自律的現(xiàn)狀,加強以法制為支撐的制度建設(shè)。該用法律規(guī)范的地方堅決壁律,該用制度規(guī)范的地方堅決用制度,這樣社會秩序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個人行為才能得到有效約束。
2.充分利用利益激勵,正面引導(dǎo)遵紀守法的行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上講,動機“是指引起個人行為,維持該行為,并將此行為導(dǎo)向某一目標(個人需要的滿足)的動力”。它體現(xiàn)著所需要的客觀事物對人的行為的激勵作用,并把人的行為引向一定的、滿足其需要的具體目標。個體利益動機的形成和發(fā)展既有個體內(nèi)在因素的作用,也有客觀環(huán)境的制約。在我國,要使大多數(shù)人主動遵守客觀上已經(jīng)建立的法律制度,就要大力加強其對形成個體利益動機的內(nèi)在因素的作用,特別是對個體需要和個體價值觀的作用。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對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協(xié)調(diào)來強化個體的法治觀念。如此,個人在按法律規(guī)范去行使權(quán)利和履行義務(wù)就能在滿足自己利益的同時也維護了社會利益。例如,國家為了鼓勵人們消費之后索要發(fā)票而推出了有獎發(fā)票,起到了很好的激勵作用,索要發(fā)票的人較之以前普遍增多,有效地減少了逃稅漏稅現(xiàn)象。這實際上是法律對是非的一種評價,而這種評價向也個體傳達了法律所體現(xiàn)的價值觀。如果個體接受了這種觀念,并反復(fù)實施法的規(guī)范要求,其價值觀就在個體意識中逐漸得到強化。
(二)促進先進學術(shù)思潮向社會心理轉(zhuǎn)化
事實上,不管社會心理在多大程度上與傳統(tǒng)文化相一致,都與積極維護傳統(tǒng)文化認識的努力基本上不相干,其原因在于從學術(shù)思潮到社會心理的過渡缺乏一種有效的轉(zhuǎn)化機制。“認為西方與中國之‘精華’的結(jié)合將產(chǎn)生一種很好的新文化的看法將是錯誤的。因為,那些能被現(xiàn)代人重新肯定的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將依然是符合現(xiàn)代人各自的標準的價值,其中包括甚至對傳統(tǒng)一無所知的人所肯定的價值。社會心理中所遺留的傳統(tǒng)性糟粕與這種努力同樣無關(guān),而只是由于這些糟粕產(chǎn)生的外在條件目前還未徹底改變。
文化是政治、經(jīng)濟的集中體現(xiàn),其形成和積淀只是果,而非因。文化在政治與經(jīng)濟的長期作用下自然形成,而不是由專家直接設(shè)計出來的。因此,即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今天依然給民主法治事業(yè)造成了影響,也不能(其實也不可能)通過就“文化”論“文化”的方式來消除這種影響。要使得學術(shù)思潮向社會心理有效轉(zhuǎn)化,筆者認為主要途徑有兩個:
1.利用國家強制力進行引導(dǎo)。利用國家強制力推行來促進學術(shù)思潮向社會心理的轉(zhuǎn)化實際上是通過制度改革來間接進行的。美國的亨利·埃爾曼教授曾經(jīng)從法文化的角度提出的改革觀念認為:作為法文化制度層面的法律的變化不能過于迅速和頻繁,其變化要同社會成員的心理、習慣、文化觀念等狀況有基本的接近和適應(yīng);另一方面,要充分看到法律制度對于社會關(guān)系變化過程的調(diào)整和規(guī)范作用,不能消極地等到觀念更新之后再去變革法律制度。應(yīng)當說,埃爾曼的這一分析擴展到整個文化系統(tǒng)都是基本適用的。對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要實現(xiàn)其現(xiàn)代化,其轉(zhuǎn)換機制最終要建立在整個國家、社會、公民的意識和觀念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chǔ)之上,而人們行為習慣和心理觀念(也即社會心理)的改變需要通過制度的變革來推動和引導(dǎo)。因此通過制度改革來推動社會心理的轉(zhuǎn)變需要抓住兩個大的方面:通過改革建立完整的、規(guī)范的市場經(jīng)濟體系。換句話說,市場經(jīng)濟正是現(xiàn)代民主法治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也是推動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由傳統(tǒng)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形態(tài)轉(zhuǎn)變的現(xiàn)實經(jīng)濟基礎(chǔ)。就其本質(zhì)來說,市場經(jīng)濟是一種“契約經(jīng)濟”。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交易雙方對意志自由、公平競爭、誠實交易、權(quán)利平等等“契約意識”的要求更為迫切,而這些要求實質(zhì)上也是現(xiàn)代民主法治對人的要求。因此,完整、規(guī)范的市場經(jīng)濟體系建立的過程,同時也是契合現(xiàn)代民主法治的社會心理形成的過程。(2)通過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權(quán)力制衡體系。權(quán)力制衡是現(xiàn)代民主法治的政治基礎(chǔ),而“權(quán)力制約和權(quán)利保障(或以權(quán)利制約權(quán)力)是法治的根本和核心”。中國民主法治的重心選擇也應(yīng)當是法律制度中的權(quán)利保障以及權(quán)力的規(guī)范與制衡。確切的說,中國民主法治的政治基礎(chǔ)就是依法治權(quán)。而目前我國權(quán)力機制缺乏相互制約與相互平衡,且人們并不習慣以權(quán)利來對抗權(quán)力的違法擴張。只有通過改革,以法律規(guī)范權(quán)力,以法律約束權(quán)力,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權(quán)力制衡體系。實現(xiàn)在法律統(tǒng)治下以權(quán)利約束權(quán)力。
2.加強大眾法治觀念教育。要向社會心理轉(zhuǎn)變,就必須拓寬其受眾范圍。加強大眾法治觀念教育,一般也有兩個主要途徑:(l)日常生活幣耳濡目染的“教育”。主要是指大眾傳媒的正確評價和引導(dǎo),如報刊、雜志、電視廣播、網(wǎng)絡(luò)等對重大、典型案例以及事件的評論、分析、探討、訪談;思想觀念上較為優(yōu)秀的影視劇等。迄今為止比較成功的范例有《南方周末》的熱點報道,電視劇《走向共和》等。(2)學校教育。學校教育的重大意義顯然不可忽視,因為“青少年一代的成長,正是我們事業(yè)必定要興旺發(fā)達的希望所在”。我國在校學生現(xiàn)在有兩億多,約占人口的六分之一,他們的法治觀念狀況,直接決定著中國民主法治的前景。各種層次的學校教育,則為先進學術(shù)觀點和學術(shù)思潮的傳播提供了最佳的現(xiàn)實條件和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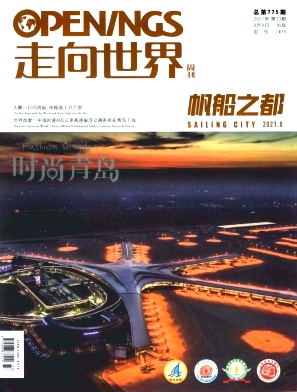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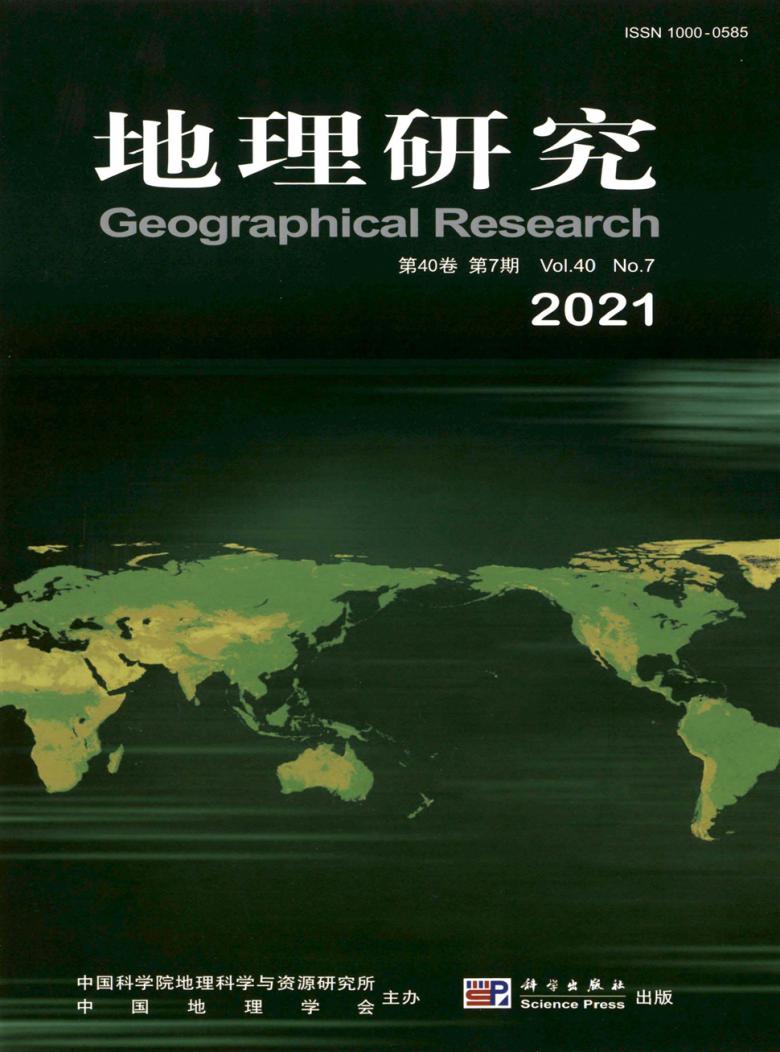
學.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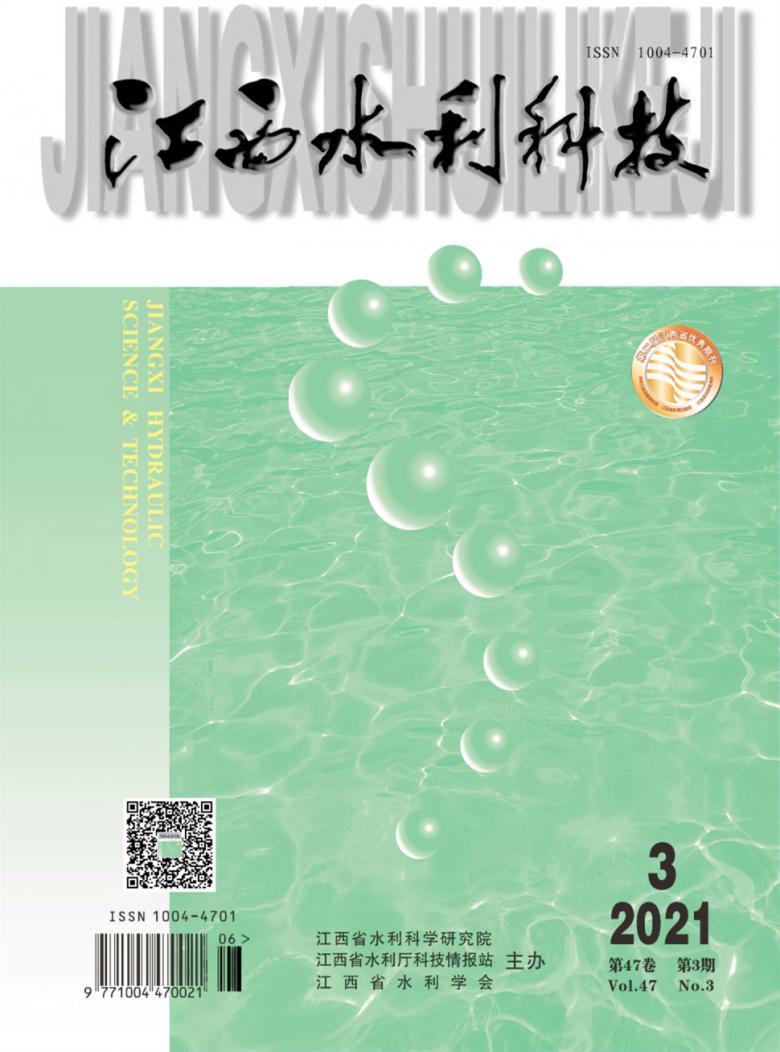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