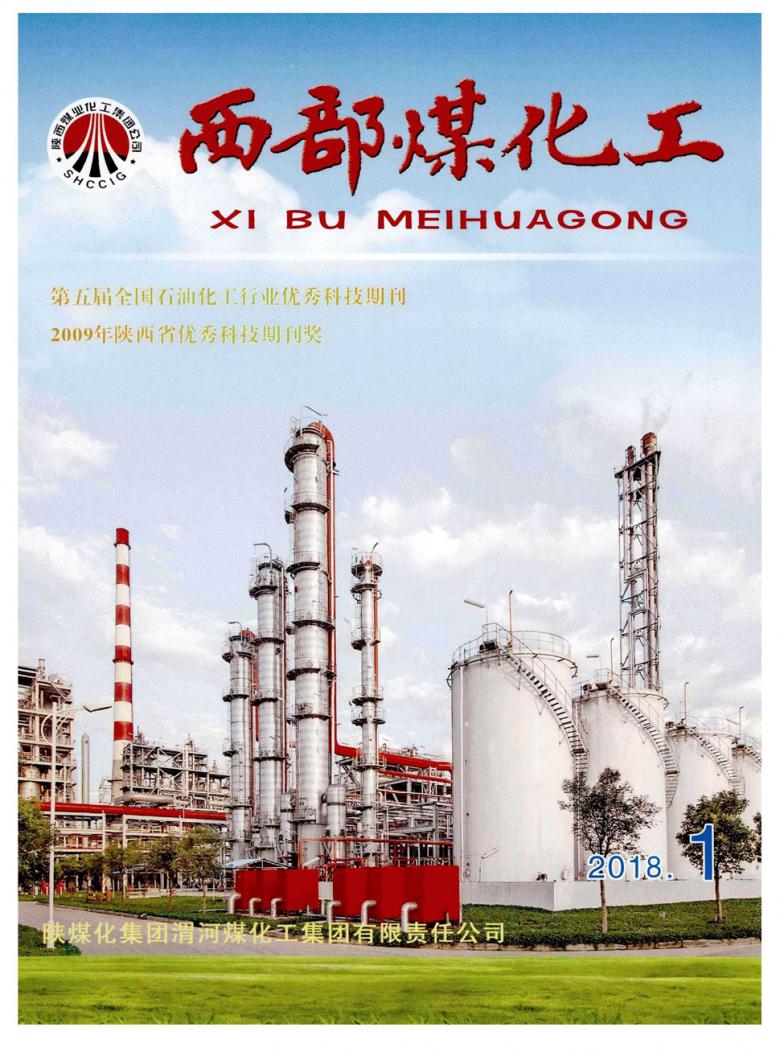別吵,開始管理吧!--也談中國式管理與后現代管理
許家崖
現代管理在管理學發展史上是“理論叢林”時代,到了中國就成為喧囂的超級農貿市場。中國經濟發展這幾十年來所出版的管理書籍浩如煙海,甚至一個還沒有學過什么管理的人都可以在短短幾年寫上數百萬言的管理文字,直至尹傳高先生等一批管理人士大聲疾呼:是垃圾,還是真學問?
也有學者私下里根本不認為管理學是一門學科,甚至認為管理學本身沒有什么理論,都是其他學科的伴生物。于是管理學就成為一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形成近幾年扎堆靠管理學的浮躁場面。筆者今年春天報考人民大學商學院的管理學博士,十三個考生里只有兩個企業考生,而本應更多關注公平的政府考生卻是占據半壁多江山。
其實,任何學科存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依據標準,直白的講也可以說叫游戲規則,就像微觀經濟學的三大假設:稀缺性假設,利己主義假設,理性假設,而貝克爾對人類行為進行經濟學分析的三大假設,則是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管理學的研究假設與前提在哪里,有多少國內管理學人真正的考慮過?與目前中國的經濟學相比,管理學研究中存在著一定的自我懷疑傾向甚至是學理上的混亂,就出現了張羿先生獨摯“后現代管理”大旗直面“中國式管理”的慘淡景象。
當然,這種自我懷疑的根源不在于管理學本身是否為科學,而在于處在社會劇烈轉型時期的中國管理學,正在遭遇著管理移植所帶來的困惑和迷茫之中。同時,這種困惑和迷茫也表明中國管理人的可貴的自我批判精神,也意味著中國管理學自我重塑的學術品格。
無論是哪門學科,一般都由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結論和對結論的驗證等四個基本的環節性要素所構成。西方文明最早的科學只有一門,就是至今作為一般學科主要研究方法的哲學。哲學是所有西方一切科學的根基和樹干,就像國人心靈皈依黃河一樣,它構成以后各種科學的母親。這個偉大的母親又有一個指導一切科學的手段:邏輯,主要內容就是亞里士多德大師所發明的三段論,如:所有人都會死,許家崖是人,所以許家崖會死。
大體上,凡是真正的科學,沒有不從哲學邏輯上獲取假設的--這種假設是科學研究得以進行的大前提。因此,哲學思辨和邏輯推演就構成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其他包括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多從這個基礎中派生出來。絕大多數中國學者到海外留學,不管你的專業如何,都要經過導師連續數月的“分類”洗腦訓練,對任何東西從各種角度分門別類,以便更好地掌握這種研究方法。
最早的科學管理也就是按照這種分析方法思維傳統對生產活動過程所進行的一種理解和解決方案,它的最大特征是把生產活動過程進行動作分解,從而發現對有效率的動作并推廣之。有學者就認為,現在中國管理學的浮躁,是因為在具體的研究中,這種學理邏輯幾近演變成為一種純技術層面的文字游戲──由于人為地無視環境因素的真實存在,前提假設就往往來源于一種感性色彩濃厚的主觀臆想,成為一種隨機的偶然,因而這種邏輯盡管可以從技術角度精益求精,卻也從起始就注定了其結論只能飄游于半空而很難腳踏實地。
回頭再看看那些獨領風騷幾月的“偽書”,能以幾十萬甚至數百萬銷售占據排行榜前列,引領一個國家最為核心的管理潮流,許多讀者就像我這等的看客,是否又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如果說前段時間朗咸平等人炮轟中國經濟學者是因為這些學者身份錯位的話,那么管理學經驗派與學院派的相互爭斗與不屑與這種邏輯混亂不無關系。管理學如果不能在運用管理杠桿最高限度地發揮企業的資源優勢和能力優勢,打造企業競爭力,維持企業的競爭地位,那就是管理學人的失職。
從跨越式發展談管理學風
管理學一直講究科學性與藝術性的同體統一。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豐富的精神資源,有很多可以挖掘并升華為優秀的管理藝術,甚至上升到戰略層次考慮。不光從曾仕強先生等人的系列中國式管理的書上所列舉的,事實上,歐、美、日、韓、甚至非洲等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少人在研究和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體現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如果我們據此認為原來最優秀的管理就在我們的故紙堆里,就大錯特錯了。想想“勾三股四弦五”這個簡單的但引起無數國人自豪的勾股定律,祖先們只是認識到一個特例,其實沒能給出普遍性的規律。客觀地講,目前我們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管理科學(包括技術基礎、方法手段,如:計量、質量、標準化、看板管理,走動管理、扁平管理、多元化經營,PDCA戴明環、市場細分、ISO9000、6δ、零庫存、卓越績效模式、搏奕論等等),就是管理藝術也沒有多少進行現代化主流改造,還沒有與管理科學進行有效的融合。管理藝術與管理科學是互相依賴的,沒有管理科學支撐的管理藝術是華而不實的空話,借用一些比較清醒的國內管理學人的話說,這樣的管理,是似是而非的襳語,是曇花一現的美麗光環……這不是負責任的管理人之所為!更不是有歷史感的管理人之所思!
管理學遵循從管理科學、管理藝術到管理回歸這樣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閉環演進過程。如果試圖簡單地用跨越式發展、搶占戰略制高點的思維做研究搞實踐,就要付出成長的代價。道理就像二十多年前國家領導人決定非要回頭補經濟建設的課以便更好的發展社會主義一樣簡單。國家從1978年引進日本TQM,一步把中國質量管理水平提高到企業文化的層面上,每年全國注冊的質量管理小組超過了2000萬個,創造的經濟效益達3500多億元人民幣。雖然把PDCA循環這個質量管理思想貫徹下去,提升了企業員工隊伍的素質,培育了大批人才,塑造了全員參與管理、改進的企業文化。但是由于群眾性管理基礎的薄弱,無法很好的利用數理統計的工具進行有效管理,在最近今年又重新補課,2004年開展主題為“應用統計技術,提高活動實效”的QC小組活動,從最近幾年的評分標準來看也在不斷加強數理統計工具的應用,努力向基于事實的決策方法上靠攏,都是在惡補管理科學的技術基礎的課。管理的藝術和科學這種一體性存在特點,可能體現為一個人的管理水平:從科學向藝術升華,也可能表現為一本管理教科書:先講解最基礎的技術基礎,后講解抽象的管理藝術;也可能表現為一個組織:先建立最基本的規章制度后升華為文化管理,最后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回歸到管理的最初狀態:不管!
管理學同時又是一門有龐大的枯燥基礎工作需要腳踏實去夯實的苦力活,科學管理階段很多學者都是用秒表現場測量分解動作的,結果造成工人的極大反感,演藝界還給管理學者編排了很多丑化故事,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就是一例。一般受過傳統東方經典熏陶出來的人,閱覽西方的管事學著作,往往覺得其幾為常理并無妙言,并且還夾雜著一些“淺顯”、“簡陋”的表式或圖解,比起我們的兵法書和武俠書上那種激動人心的奇招妙招,比起我們精言妙語的經典,似乎顯得有點兒小兒科。
殊不知,這種反差正反映著我們傳統智慧中的某些病謬。我們不少傳統的大智慧往往病于華而不實,而西方的一些細理常識往往優勝在腳踏實地;我們不少傳統的精言妙語往往謬在行之無效,而西方的一些質言素辭往往巧在遵行有益。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在管理實踐中,我們由深厚的經典熏陶出來的管理者,常常干不過人家手持“淺陋”武器的企業人。
同時,每一位中國管理學人又必須高度警惕國外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學習借鑒的問題。眾所周知,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引進外國文化(這里是廣義文化,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需要。一般來說,引進外國文化有多種情況,一是只學皮毛,不學精髓;二是邯鄲學步,迷失自我;三是全盤照搬、原汁原味;四是消化吸收、創新改進。對于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情況,其弊端人所共知。真正的問題是第三種情況,這是因為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學習外國文化要原汁原味是天經地義的絕對正確的,我認為這可能正是中國人引進外國文化的最大弊病所在。
德魯克大師說過一句名言:“管理沒有終結的答案,只要永恒的問題”,中國管理人目前在學習國外管理上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區分取舍的問題。對西方管理學如饑似渴地學習過程之中的中國管理人難免發生諸多的混亂,哪些可能照搬?哪些需要揚棄?哪些需要創造性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沿用中國文化中固有的“非此即彼”思維模式,或者簡單地進行一分為二辨證看待,都無濟于事。最好是明確認識中國與西方管理學各門派所在的歷史背景、企業發展水平與當今中國的社會狀況與企業發展水平存在的時間與空間的位移。在明確了這種位移之后,分析鑒別再次確認,這樣就會非常明白清楚的知道,西方某個管理學派反對的未必是我們應該反對的,同樣道理,他們主張的未必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如果僅僅從這一點上講,我還是贊成發展有中國特色管理的)。明確了這種位移,我們不但不會簡單地肯定誰或者否定誰,相反,我們還會把我們“否定的人”身上抽取出精華的東西,我們就會用批判、研究和學習的方法,進行分類、鑒別,從而為我所用。
有效是檢驗管理的唯一標準
管理是一個實踐性強的學科,當我們以歷史觀的視角去探討管理學的沿襲時,就會很容易的發現許多管理理論以及管理“專家”的錯誤,而他們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們割裂的看待事物,就管理談管理,把它做成了一門學問,一個系統的課程,而非解決現實問題的利器--也就是說,這種“學問”成為他們謀生致富的手段。
中國式管理也好,后現代管理也罷,只要能逮到老鼠,能幫企業解決好問題,你就是好貓!就像黑格爾三段論的正反合一樣,不分中外古今,你只要“有效”就行。在市場轉型的的特定時期,在一個絕大多數企業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國度,在一個企業的規范化治理結構還不十分完善的國度,究竟如何來經營管理好我們的企業,中國的管理學人們你準備好了嗎?
我堅信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文化肯定是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盡管這種特色不等于就可以簡單貼“中國式管理”標簽。我們應當自由、平等、公平、善意地合作和/或競爭,而不應當互相歧視和/或貶低:你指我為“唯科學主義”,我指你為“反科學主義”。應當有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胸懷,而不應當像白衣秀士王倫式地狹窄。
目前,中國管理人共同的責任和使命還是高度關注管理的藝術、科學一體屬性,走出管理的藝術與科學分離的“怪圈”,共同開創中國管理藝術與管理科學同步發展的新局面。別吵了,開始管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