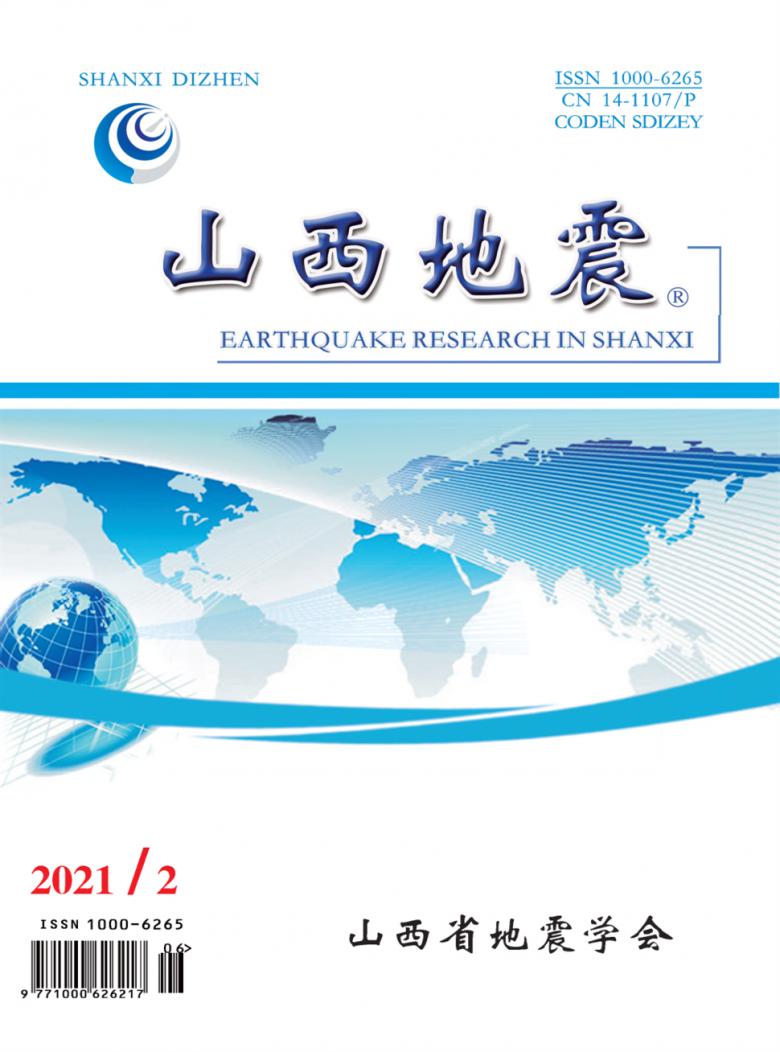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對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社會經(jīng)濟的影響①
曹 玲
[摘要]明清時期美洲糧食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傳入我國,對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本文從耕地面積擴大、糧食畝產(chǎn)量提高和糧食總產(chǎn)量增加及糧食作物結(jié)構(gòu)變動情況考察它們對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影響;又從山區(qū)開發(fā)、糧食商品化、經(jīng)濟作物種植及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等幾方面考察它們對我國社會經(jīng)濟的影響。
[關鍵詞]美洲糧食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糧食生產(chǎn);作物結(jié)構(gòu);社會經(jīng)濟
明清時期原產(chǎn)美洲的糧食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傳入,不但增加了我國作物的種類,同時對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不僅有利于我國缺糧問題的解決,使人口壓力有所緩和,也使我國糧食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新的變化,對我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長期以來,關于這些作物的傳入和傳播問題,有很多學者如何炳棣、陳樹平、郭松義、曹樹基等[1]做過研究,但專門探討它們對我國社會各方面產(chǎn)生影響的論著寥寥無幾,多數(shù)是在研究傳播問題時涉及某一個方面或只是限于簡單的結(jié)論,缺乏深入分析。本文旨在綜合多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全面客觀地進行分析,對這些新作物的傳入所產(chǎn)生的影響做出正確評價。
一、美洲糧食作物在我國的傳入及傳播過程
明清時期我國人口增長很快,與此同時耕地面積增幅不大,由此造成人均耕地急劇下降,糧食短缺問題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此時也正是中西交通相對發(fā)達時期,原產(chǎn)美洲的糧食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自明中葉開始陸續(xù)被引入我國。
玉米約于16世紀中葉分3路傳入我國,分別是西北陸路自波斯、中亞至我國甘肅,然后流傳到黃河流域;西南陸路自印度、緬甸至云南,然后流傳到川黔;以及東南海路由東南亞至沿海閩廣等省,然后向內(nèi)地擴展。從明中葉到清乾隆前,這近兩百年時間里玉米僅限于在我國個別省份小范圍種植,尚處于被大眾認識階段。乾隆中期到嘉慶、道光年間,是玉米大規(guī)模推廣時期,此時人們開始認識到玉米的廣泛適應性和高產(chǎn)意義,紛紛種植。嘉慶以后,玉米在全國普遍栽培,其中流民在玉米傳播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清后期到民國年間,除了南方各省山區(qū)玉米栽培深入發(fā)展之外,華北平原玉米種植進入大發(fā)展階段,玉米代替了舊有傳統(tǒng)低產(chǎn)作物的一部分面積,成為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人民的主要糧食作物之一。清代玉米傳播,大多先在山地丘陵地區(qū)栽培,然后漸及平原地區(qū);先在不發(fā)達地區(qū),后發(fā)達地區(qū);南方多于北方,山地多于平原。清代玉米集中產(chǎn)區(qū)是中部的陜鄂川湘桂山區(qū)、西南的黔滇山區(qū)、東南的皖浙贛部分山區(qū),華北和東北的玉米集中區(qū)主要在清后期至民國年間形成。
—————————————
①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明清時期美洲作物的傳播及其對中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影響”,項目批號為03BZS034,特此致謝。
番薯是16世紀后期,分多次從東南亞傳入我國東南沿海的閩廣兩省,第一條途徑是陳益、林懷蘭從越南分別傳入廣東的東莞和電白縣;另一條是由“溫陵洋舶”經(jīng)南澳島傳入福建泉州;再就是陳振龍由菲律賓攜種至福州。番薯于明萬歷年間引入我國后,局限于閩粵將近一個世紀,17世紀后期開始向江西、湖南等省及浙江、江蘇沿海地區(qū)擴展,18世紀中葉遍及南方各省并向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qū)擴展。清代番薯分布較集中的地區(qū)有閩廣兩省、閩浙贛皖低山丘陵區(qū)、鄂南湘南山區(qū)、四川盆地及山東中南部。
由于史料的缺乏,馬鈴薯傳入我國的時間和路線尚未有統(tǒng)一定論,可以肯定的是同番薯、玉米一樣,馬鈴薯是多次多途徑地被帶到我國。本文贊同的觀點是:一是17世紀中葉荷蘭人把馬鈴薯帶到臺灣,然后傳到我國東南沿海地區(qū);一是18世紀由傳教士、商人將馬鈴薯普通栽培種從歐洲帶到我國;以及進入20世紀后,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又多次傳入馬鈴薯的新品種。馬鈴薯傳播范圍直到19世紀初仍非常有限,進入清后期及民國時期,隨著各地引進時間的延長、推廣面擴大及人們認識的加深,初步有所發(fā)展,但其真正擴大種植面積,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起重要作用還是到了建國后。清代馬鈴薯的集中產(chǎn)區(qū)有以川陜鄂甘交界的山區(qū)為中心并向周圍傳播形成的西南馬鈴薯生產(chǎn)區(qū)、以晉北為中心的華北馬鈴薯生產(chǎn)區(qū),東北馬鈴薯主產(chǎn)區(qū)是在民國后形成的。[2]
玉米、番薯傳入我國后,到清乾隆、嘉慶年間在各地迅速推廣,發(fā)展到清末,已經(jīng)躍居我國主要大田作物行列,它們?yōu)槲覈霓r(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馬鈴薯由于受生態(tài)適應性的影響,多是種植在我國的部分高寒山區(qū),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大規(guī)模發(fā)展,因此,相對于玉米和番薯,清代馬鈴薯發(fā)揮的作用還是十分有限的。
二、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對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影響
玉米、番薯、馬鈴薯這些高產(chǎn)糧食作物的傳入,對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具有重要意義。這些作物適應性強,產(chǎn)量高,有利于我國耕地面積的擴大,也對糧食單產(chǎn)和總產(chǎn)量的增加起了一定的作用。隨著它們栽培面積的不斷擴大,我國傳統(tǒng)的糧食作物結(jié)構(gòu)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動。
(一)對耕地面積增加的作用
玉米、番薯、馬鈴薯這些適應性較強、耐旱耐磽的作物引進,使過去并不適合糧食作物生長的砂礫瘠土和高崗山坡地成為宜農(nóng)土地。玉米具有耐瘠耐旱的特性,“不擇磽確”,“但得薄土,即可播種”[3],適宜在山區(qū)生長,“雖山巔可植,不滋水而生”[4],“盤根極深,西南山陡絕之地最宜”[5]。清人包世臣在《齊民四術》中稱:“玉黍,……生地瓦礫山場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宜勤鋤,不須厚糞,旱甚亦宜溉,……收成至盛,工本輕,為旱種之最”。隨著玉米栽培面積的擴大,使長江流域以南過去長期閑置的山丘地帶和不宜種植水稻的旱地被迅速開發(fā)利用,同時在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qū),也逐步取代了原有的低產(chǎn)作物,成為主要的旱地農(nóng)作物。
番薯同樣具有抗?jié)场⒛秃怠⑦m應性強的特性,明人何喬遠《閩書》中稱番薯“瘠土沙礫之地,皆可以種”,王象晉《群芳譜》也稱“人家凡有隙地,但只數(shù)尺,仰見天日,便可種得石許”,番薯能夠“不與五谷爭地,瘠鹵沙岡皆可以長,大旱,不糞治亦長大”[6],且“薯苗人地即活,東、西、南、北無地不宜,得沙土高地結(jié)尤多,天時旱澇俱能有秋”[7]。在耕地少、人口密集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區(qū),農(nóng)民在作物布局上充分利用番薯的適應性,以提高土地利用率,“邑人于沃土種百谷,瘠土則以種苕,無處不宜”[8],“山坡土埂屋畔隴頭盡堪布種”[9]。由于番薯的推廣,我國東南各省大量濱海沙地和南方山區(qū)的貧瘠丘陵山土得到開發(fā)利用。
馬鈴薯更是“高山冷處咸蒔之”[10],那些土壤貧瘠、氣溫較低、連玉米都不易生長的高寒山區(qū),只能種植耐“地氣苦寒”的馬鈴薯,“其深山苦寒之地,稻麥不生,即玉黍亦不殖者,則以紅薯、洋芋代飯”[11]。總之,這幾種作物,對沙地、瘠壤、不能灌溉的丘陵、甚至高寒山區(qū)的利用,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有關當時山區(qū)墾殖種植玉米、番薯的記載很多,如湘贛山區(qū)“斜坡深谷,大半辟為藷(番薯)土”[12];鄂西山區(qū)也是“巨阜危崖,一望皆包(玉米)也”[13];在浙西山區(qū)“外來之人租得荒山,即芟盡草根,興種番薯、包蘆(玉米)、花生、芝麻之屬,彌山遍谷,到處皆有”[14];道光陜西《石泉縣志》也說:“乾隆三十年,……,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此處不一一列舉了。
有學者推測,如按乾隆時有9.5億市畝耕地、糧田8億畝計算,玉米占6%為0.48億畝,番薯占2%為0.16億畝,共計占地0.64億畝。[15]其中一部分是因栽培玉米、番薯而新辟的耕地如山地、丘陵、濱海沙地等,另一部分是改種玉米、番薯的舊有耕地,由于不知道新辟和改種各占多少,目前我們很難確定當時因推廣美洲糧食作物所擴大耕地面積的具體數(shù)字。
但由于乾隆時期墾荒的重點是南方各省山區(qū),特別是華中和西南各省的許多山區(qū)和丘陵都在此時相繼得到開發(fā),我們可以通過華中和西南幾省耕地面積的擴大情況,來估測其中玉米、番薯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從表1可以看到,從清初至乾隆、嘉慶的一百多年間,華中、西南各省耕地面積擴大近1倍(增加了約0.64億畝),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玉米、番薯在這些省份迅速推廣。因此可以說在擴大耕地范圍的過程中,墾荒種植玉米、番薯發(fā)揮了較大作用。相對而言,從嘉慶到光緒年間,耕地的增幅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嘉道后,人口增長的趨勢減緩,咸豐后甚至下降,對耕地的需求不再像乾嘉時期那么強烈,另外,此時南方山區(qū)可供開墾的耕地基本已于乾嘉時期開發(fā)殆盡,耕地擴大趨勢放緩,耕地面積增幅不大。
(二)對糧食畝產(chǎn)量提高的作用
玉米、番薯在清代大量推廣后,對提高單位面積產(chǎn)量具有一定的作用。作為高產(chǎn)作物,玉米本身的畝產(chǎn)量已經(jīng)較高,平均畝產(chǎn)可達180市斤,折合粟2石,相當于春粟中產(chǎn)量較高者。在玉米大量推廣后,便在大田上作為與小麥、春谷或高粱等輪作倒茬的一種重要作物,其單位耕地產(chǎn)量將比不種玉米或復種低產(chǎn)雜糧將提高得更多。番薯是絕對的高產(chǎn)作物,畝產(chǎn)鮮薯可達千斤,相當于稻谷500斤或3.84石,粟谷417斤或3.09石,這是甘薯本身的高產(chǎn),如與麥、春谷、豆、稻復種,則單位耕地產(chǎn)量的提高更為顯著。[17]
在清代生產(chǎn)技術條件下,由于種植玉米、番薯使當時的糧食畝產(chǎn)量提高的斤數(shù)大致是玉米使畝產(chǎn)增加10.37市斤,番薯使畝產(chǎn)增加10.77市斤,在這增加的21.14市斤中有2.38市斤是明代就增加的(玉米1.3市斤,番薯1.08市斤)。歸納言之,乾隆時畝產(chǎn)比明代所增加的:玉米番薯約占一半,其余為南北耕作集約化程度及復種指數(shù)提高的作用共占一半。[18]可以看出,玉米、番薯對糧食畝產(chǎn)增加的作用是較大的。
(三)對糧食總產(chǎn)量提高的作用
玉米和番薯這兩種作物在清代大量推廣的直接結(jié)果,使許多山地沙地得到開發(fā),從而增加了耕地面積,同時也對提高單位面積產(chǎn)量具有一定的作用,兩方面合起來,促進了糧食總產(chǎn)量的提高,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糧食,對緩解長期因缺糧而產(chǎn)生的矛盾,起了一定作用。
關于玉米、番薯濟食作用記載很多,如:道光《建始縣志》卷三:“居民倍增,稻谷不給,則于山上種苞谷、洋芋或蕨薯之類,深林幽谷,開辟無遺”;雍正閩浙總督高其倬說:“福建自來人稠地狹,福、興、泉、漳四府,本地所出之米,俱不敷民食,……再各府鄉(xiāng)僻之處,民人多食薯蕷,竟以充數(shù)月之糧……”等等,但農(nóng)民利用玉米、番薯濟食的具體數(shù)量如何,我們很難從簡單的文字描述中得知。
下面以清代玉米、番薯種植較多的兩湖地區(qū)為例,考察玉米、番薯在解決民食問題上的功用,據(jù)龔勝生估計,到清末,兩湖玉米耕地面積為100萬畝,番薯耕地面積為180萬畝,以0.6石的玉米單產(chǎn)和6石的番薯單產(chǎn)計,清末兩湖每年可產(chǎn)玉米60萬石左右,番薯1080萬石左右,合計增加糧食1100多萬石左右,按每人需4石計,約可養(yǎng)活280萬人。[19]咸豐元年(1851年)兩湖人口數(shù)已達5 400多萬,[20]玉米、番薯可提供6%的人口所需酌糧食(作者按:此處玉米的產(chǎn)量估計有些偏低,正常情況下,養(yǎng)活的人口應該更多),可以說,玉米、番薯對緩解清后期兩湖的人口壓力起了一定作用。
從全國范圍講,一方面要看到玉米、番薯對解決民食問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們對其作用要有正確估計,畢竟其種植面積的比例到解放前為止還不很大。據(jù)珀金斯的統(tǒng)計,到20世紀初,玉米的播種面積只占所有各種谷物的全部播種面積的6%左右,番薯約占2%(見表3)。如果所有栽種玉米的土地在不種它的時候是拋荒不用的,那么玉米的傳入就能造成糧食700萬到800萬噸的增加,番薯在1918年以前大約使糧食產(chǎn)量增加了400萬噸。[21]
(四)對糧食作物結(jié)構(gòu)的影響
清乾嘉年間,美洲糧食作物在全國范圍迅速推廣,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從而使糧食作物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變化。明代,我國糧食構(gòu)成基本延續(xù)宋元以稻麥為主的格局,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說:“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來牟(麥類)黍稷居十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四海之內(nèi),燕、秦、晉、豫、齊、魯諸道,烝民粒食,小麥居半,而黍稷稻粱僅居半,西極川、云,東至閩、浙、吳、楚腹焉,方長六千里中,種小麥者,二十分之一。”可以看出此時的糧食作物結(jié)構(gòu)是水稻占70%,小麥占15%強,黍稷(粟)粱等作物共占15%弱。這種稻麥占絕對優(yōu)勢的作物結(jié)構(gòu),由于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引進和傳播,開始發(fā)生了變化。
玉米的傳入使傳統(tǒng)作物黍、稷的種植量大為減少。受經(jīng)濟條件所限,我國自古以來著力發(fā)展產(chǎn)量高的糧食作物,勞動人民以果腹為首選目標,質(zhì)量口味放其次。清乾嘉年間,玉米隨著大批流民涌入地廣人稀的山區(qū),人口的迅速增長,使糧食需求顯著增加,低產(chǎn)的黍粟類作物已不能滿足需求了。在這種情況下,產(chǎn)量高、適應范圍廣、具耐旱耐瘠特性,有救荒裕食之功的玉米,以很快的速度在廣大山區(qū)普及開來。嘉慶《漢中續(xù)修府志》道:“數(shù)十年前,山內(nèi)秋收以粟谷為大莊,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22],曾一度在陜南山區(qū)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的粟谷,至十九世紀已讓位給玉米。
另一方面,清后期至民國年間,華北平原上玉米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其他傳統(tǒng)雜糧作物的種植面積則迅速縮小。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政府中央農(nóng)業(yè)實驗所《農(nóng)情報告》中的一系列數(shù)據(jù),證明了這一點,從表4中可以看出,20世紀30年代前七年玉米的平均栽培面積小于谷子和高粱,十年后的1946年,玉米的栽培面積上升,而高粱下降,玉米超過了高粱,位于谷子之后。[23]
番薯的傳入和推廣則迅速取代了蔓菁和傳統(tǒng)薯類如芋、山藥(薯蕷)等糧食功用,使它們退居蔬類行列。番薯甜美可口、適應性強、產(chǎn)量高,“種之利勝種谷”,在國內(nèi)傳播很快,不久就以其獨特的優(yōu)勢壓倒傳統(tǒng)薯類,不僅在薯類作物中占絕對優(yōu)勢,而且在糧食作物中躍居重要地位。馬鈴薯在我國的發(fā)展,如前文所提,主要得益于解放后政府的大力提倡。
經(jīng)過近四百年的發(fā)展,玉米、番薯終于成為我國主要糧食作物,并與其他雜糧作物一起,共同構(gòu)成全國糧食產(chǎn)量的1/3。目前,我國糧食作物按栽培面積和重要性排列,形成稻、小麥、玉米、番薯、谷子、高粱、大麥、馬鈴薯的構(gòu)成次序。
科學.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