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甲午戰(zhàn)后清政府經(jīng)濟(jì)政策的變化
佚名
一、國家資本的維持、改造與擴(kuò)張
政策變化的之一,是維持和改造原有的,同時(shí)向新領(lǐng)域擴(kuò)張國家資本。 首先,對(duì)官辦軍用,主要是維持與擴(kuò)充并進(jìn)。
甲午戰(zhàn)后,軍工生產(chǎn)是"籌餉練兵"的重要一環(huán),是作為"急務(wù)"之一來對(duì)待的。此時(shí),清政府采取了維持與擴(kuò)充并進(jìn)的措施。所謂維持,是延續(xù)舊的經(jīng)營管理機(jī)制,略加整頓之后,繼續(xù)開工生產(chǎn)。所謂擴(kuò)充,既有原有企業(yè)的規(guī)模擴(kuò)大,也包括新建一些企業(yè)。整個(gè)看來,舊的體制并無多大變化。
當(dāng)然,朝臣之中,有人也有一些新的設(shè)想。胡燏棻有"令民間自為講求""托民廠包辦包用"之議[3];給事中褚成博也主張將各省船械機(jī)器等局招商勸辦。[4]清政府根據(jù)戶部"仿照西例,改歸商辦"的議復(fù)諭令將原有局廠"招商承辦",要求有關(guān)省份的督撫派人赴海外招徠華商,"該商人如果情愿承辦,或?qū)⑴f有局廠令其納貲 認(rèn)充,或于官廠之外,另集股本,擇地建廠。一切仿照西例,商總其事,官為保護(hù)。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維持"。[5]
乍一看,似乎軍用工業(yè)都可交由商辦。實(shí)則不然。從實(shí)際措施來看,武器制造這部分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方式,仍是完全官辦的老辦法,靠增加經(jīng)費(fèi)投入來維持,毫無"變計(jì)"可言。主張"多設(shè)局廠"自造軍火的張之洞,一面為朝廷出謀劃策,一面身體力行,對(duì)他"竭力經(jīng)營"若干年的湖北槍炮廠,制訂了一個(gè)擴(kuò)充計(jì)劃。核心是增加常年經(jīng)費(fèi),引進(jìn)德國技術(shù)設(shè)備。他仗著甲午戰(zhàn)后自己地位的上升,力求解決數(shù)年來"經(jīng)費(fèi)有限,力量未充"的難題,要求朝廷允許他"由江南籌款,再加開拓"。[6]經(jīng)他爭取,湖北槍炮廠的常年經(jīng)費(fèi)便增加到75-76萬兩之多。經(jīng)過張之洞的大力擴(kuò)充,湖北槍炮廠為最大的軍工廠。雖然它是清政府的維持與擴(kuò)充措施中較為成功的一例,但此時(shí)清政府財(cái)政已困窘至極,無力加大投入;加之生產(chǎn)經(jīng)營方式也一成不變,軍火生產(chǎn)無論是維持還是擴(kuò)充,都困難重重。其它一些老的局廠,規(guī)模的擴(kuò)充都很有限,更無論新建的幾家軍工企業(yè)了。
當(dāng)然,在"整頓"之中,也有過"招商承辦"的嘗試。例如,閩浙總督邊寶泉曾會(huì)同兩廣總督譚鐘麟奏請(qǐng)將福州船政局招商承辦,但因各種原因,招商的設(shè)想并未落實(shí)。御史陳璧建議"為船政開之利",開煤鐵礦、鑄造洋錢、設(shè)招商局、兼造民用品,搞商品化經(jīng)營。[7]但在官辦體制下,商品化經(jīng)營的成效并不明顯。
至于官辦、官督商辦形式的民用企業(yè),清政府在維持的同時(shí),也采取了一些整頓、改造措施。
清政府曾用招商承辦的措施來改造和維持困難重重的洋務(wù)企業(yè)。甲午之后較有的舉動(dòng)有漢陽鐵廠交由盛宣懷承辦。從漢陽鐵廠招商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招商的主要目的是解決投資方面的嚴(yán)重困難(因"戶部必不撥款","羅掘已窮")。而承辦商盛宣懷"并無如許巨款",他的如意算盤是"鐵路若歸鄂辦,則鐵有銷路 ,煉鐵之本,可于鐵路經(jīng)費(fèi)內(nèi)挹注"。當(dāng)清廷命王文韶、張之洞督辦蘆漢鐵路時(shí), 盛氏立即"甚踴躍"地表示"愿招商承辦"。[8]拿計(jì)劃中的鐵路作他個(gè)人承辦鐵廠的"信用",再拿承辦鐵廠來染指計(jì)劃中的鐵路,以空對(duì)空。這種"招商",并沒有招來了多少私人資本,卻招來了一堆后患。最明顯的是,并無多少資本的盛氏,以不斷向日本借債度日,使后來的漢冶萍公司一步步落入日本資本的魔掌。 而標(biāo)榜恤商惠工、官為保護(hù)的清政府,對(duì)這么一家重要的企業(yè)落入外人控制的嚴(yán)重之事,竟無動(dòng)于衷!另一家老的民用企業(yè)輪船招商局,在這一時(shí)期中,清政府不但沒有采取任何資助、維持的措施,相反,它卻增加了對(duì)招商局的勒索。
甲午戰(zhàn)后值得注意的一大"變計(jì)",就是國家資本向銀行領(lǐng)域的擴(kuò)張。
1897年10月,盛宣懷奏請(qǐng)仿辦銀行。[9]此時(shí)他已將鐵廠、鐵路抓在手中,以"今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10]為由,又不失時(shí)機(jī)地向銀行伸手。這樣,清廷于11月"責(zé)成盛宣懷選擇殷商,設(shè)立總董,招集股本,合力興辦,以收利權(quán)"。[11]半年之后,即1897年5月27日,中國通商銀行總行在上海開業(yè)。實(shí)行的基本上是官督商辦的組織形式,得到清政府不少的"護(hù)持"。如撥存生息公款200萬兩(該行本金共500萬兩);要求京外撥解之款交該行匯兌;公中備用之款交該行生息。[12] 不過,既然有商股,該行經(jīng)營方式還是想與西式銀行慣例合拍。"用人辦事悉以匯豐為準(zhǔn)參酌之,······除卻官場(chǎng)習(xí)氣"。
可見,甲午之后,國家資本并未收縮,而是有所擴(kuò)張。尤其是向金融銀行領(lǐng)域的擴(kuò)張,影響深遠(yuǎn)。
二、民間資本的倡導(dǎo)、寬允與扶持
清政府在采取措施維持、改造和擴(kuò)張國家資本的同時(shí),也放寬了對(duì)私人資本的限制,鼓勵(lì)和允許他們?cè)谝恍╊I(lǐng)域中的發(fā)展,個(gè)別的還給與一定的資助與扶持。這多多少少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上"設(shè)廠自救"和"商辦"呼聲的順應(yīng),也是迫于《馬關(guān)條約》給予外商設(shè)廠制造權(quán)和財(cái)政困難的沉重壓力而采取的一個(gè)"變計(jì)"。
清政府中有些大臣,對(duì)民間的呼聲確有"順應(yīng)"的表示,對(duì)商民投資設(shè)廠確曾顯示出倡導(dǎo)的態(tài)度,如張之洞、胡燏棻 、劉坤一、褚成博等。清政府也終于允諾"以恤商惠工為本源",并把招商承辦作為"從速變計(jì)"的首要舉措。這些,自然會(huì)在社會(huì)上造成一些寬松的氣氛。當(dāng)時(shí),"官為商倡"是官方文件中常見的用語。
官方的"倡導(dǎo)",也有一些具體措施。1895年7月,清廷令張之洞招商,多設(shè)織布織綢等局,廣為制造。[13]同年底,又就蘆漢鐵路興建一事頒諭,允許能集資千萬兩以上的富商設(shè)立公司筑路,贏絀自負(fù)。[14]1896年,總理衙門又根據(jù)王鵬運(yùn)準(zhǔn)民招商集股開礦、官吏認(rèn)真保護(hù)不得阻撓的奏折,咨令有關(guān)省份厘定章程,地方官不得勒索。[15]1897年初,褚成博奏請(qǐng)籌畫抵制洋商改造土貨,主張官府對(duì)華商"力為護(hù)持","痛除向來官商隔膜錮習(xí)",總署議復(fù),表示應(yīng)官商合力、官助商辦,推廣制造。[16]1895年7月,清廷還電令張之洞"籌款購備小輪船十余只,專在內(nèi)河運(yùn)貨以收利權(quán)"。[17]
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還在維新運(yùn)動(dòng)的推動(dòng)下,嘗試"變祖宗成法",以期扶持工商的活動(dòng)能逐步制度化。張之洞、王鵬運(yùn)先后奏請(qǐng)?jiān)诟魇≡O(shè)立商務(wù)局。[18] 從總理衙門的奏復(fù)來看,商務(wù)局除了由官方設(shè)立,它的職權(quán)性質(zhì)并不 是一個(gè)行政機(jī)構(gòu),而是向督撫提供信息的咨詢機(jī)構(gòu),主要工作就是調(diào)查,宣傳提倡。[19]但各省的商務(wù)局又可從事經(jīng)營活動(dòng)。1896年初,張之洞奏準(zhǔn)動(dòng)用息借商款60 萬兩,另加息借官款,作為設(shè)立蘇州商務(wù)局的股本。[20]山西商務(wù)局也有招商集股的職責(zé)[21]。這樣的商務(wù)局,又像是一個(gè)官督商辦的公司。1898年,在康有為的呈請(qǐng)下,清廷諭令劉坤一、張之洞試辦商務(wù)局事宜。兩個(gè)月后,張之洞奏準(zhǔn)設(shè)漢口商務(wù)局,并擬定了8條"應(yīng)辦之事"。[22]同年8月,清廷在北京設(shè)農(nóng)工商總局,任命端方等人為督理,"隨時(shí)考查"、具奏農(nóng)工商事務(wù)。[23]雖然農(nóng)工商總局不具備統(tǒng)一管理全國農(nóng)工商事務(wù)的權(quán)力,它卻是清政府第一次設(shè)立的新型經(jīng)濟(jì)部門。此外,清廷還諭令沿海各省設(shè)立保商局,保護(hù)回國僑商。1898年,清政府還頒布《振興工藝給獎(jiǎng)?wù)鲁獭贰24]這是封建政府首次制定專門獎(jiǎng)勵(lì)發(fā)明和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法規(guī)。
這些措施,對(duì)民間的投資活動(dòng)是有倡導(dǎo)、激勵(lì)作用的。雖然官為商倡一般多屬表態(tài)性質(zhì),但也有得到扶持、資助的。像業(yè)勤、大生、通久源、通益公等紗廠,在創(chuàng)辦之初,有的就得到過官款的扶持。這些機(jī)制紗廠一般享有關(guān)稅上的優(yōu)惠待遇,按照上海機(jī)器織布局從前的成案,在海關(guān)報(bào)完正稅一道,其余厘稅概行寬免。[25]但到后來洋紗進(jìn)口沖擊等原因?qū)е乱恍┘啅S陷入危機(jī)時(shí),清政府并未采取切實(shí)措施予以扶持,而是聽其出售給洋商或招洋股。結(jié)果,民族紡紗業(yè)的發(fā)展陷入低潮。當(dāng)然,這也與清政府沒有關(guān)稅自主權(quán),無法運(yùn)用稅率的調(diào)整來控制洋紗進(jìn)口量大有關(guān)系。或許一些大的紳商如張謇等得到的扶持要多于普通商人,在競爭中占有優(yōu)勢(shì),甚至帶有壟斷的成分,但平心而論,當(dāng)時(shí)華商間的競爭所產(chǎn)生的不良后果,遠(yuǎn)遠(yuǎn)比不上洋商挾特權(quán)而來所造成的沖擊。換言之,洋商與華商間的不公平競爭,嚴(yán)重制約了華商的正常發(fā)展。中國商人希望有公正的中外經(jīng)濟(jì)秩序,以便與洋商平等競爭,而清政府卻無能為力。
不過,清政府的一番倡導(dǎo),在一定程度上順應(yīng)了廣大商民的利益要求,再加上《馬關(guān)條約》訂立不久,外資尚未大規(guī)模進(jìn)入中國,種種因素,使甲午戰(zhàn)爭后民族工業(yè)的興辦,出現(xiàn)了一個(gè)短暫的高潮。但在視作"要政"的路礦部門,在執(zhí)行中卻搖擺不定。
三、路礦要政的提出及特點(diǎn)
對(duì)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有些官員認(rèn)為鐵路太少是一個(gè)重要原因。加上俄、法兩國的鐵路已展筑到中國邊境,將侵入中國腹地,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立即籌畫鐵路的興建工作。至于開礦,則是清政府解決戰(zhàn)后財(cái)政困難的一項(xiàng)可興之利,既是通商惠工的需要,又是籌餉急務(wù)的重要。于是,路政、礦政就成為戰(zhàn)后清政府的要政。這兩項(xiàng)要政,在集資和經(jīng)營管理方式上的特點(diǎn),值得注意。
鐵路、礦山都是需要較大投資和較高技術(shù)的產(chǎn)業(yè)部門。尤其是巨大的投資由何而來,是擺在清政府面前的首要難題。在筑路上,清政府打算官辦、商辦并存。但華商籌集巨額資本不易,商辦受阻,清政府只得采用借款官辦的措施,企圖"利用"外資與招集商股并行。1896年9月,受命主持蘆漢路的張之洞、王文韶會(huì)奏,主張暫借洋債造路,陸續(xù)招股分還;設(shè)鐵路總公司,官督商辦,以盛宣懷為督辦。[26]此議得到清廷同意。
盛宣懷的計(jì)劃是由鐵路總公司出面借洋債2 000萬兩,招商股700萬兩,入官股300萬兩,借官款1 000萬兩,先筑蘆漢,再辦蘇滬、粵漢等路。[27] 由于招集商股沒有成效,作為官股的南北洋存款300萬也沒有落實(shí),最后只有借洋債一條路可走了。清廷設(shè)想商借商還,權(quán)自我操,但前提是外國平等對(duì)待中國。而正乘中國戰(zhàn)敗力衰、大舉掠奪中國的列強(qiáng),豈能放過侵奪中國路權(quán)的時(shí)機(jī)!結(jié)果,外國公司通過商業(yè)性的合同,攫取了大量權(quán)益,并為列強(qiáng)瓜分勢(shì)力范圍服務(wù)。
在開礦問題上,如何集資、投資,清政府的措施同樣也是搖擺不定的。1896年初,御史王鵬運(yùn)奏請(qǐng)通飭開辦礦務(wù),建議清廷"特諭天下,凡有礦之地,一律準(zhǔn)民招商集股,呈請(qǐng)開采,地方官認(rèn)真保護(hù),不得阻撓"。[28]戶部和總署雖然議奏照準(zhǔn),但又擔(dān)心"股款能否湊集,有無弊混,應(yīng)由臣部再行咨令各產(chǎn)礦省份厘定章程,切實(shí)奏明報(bào)部"。[29]最后結(jié)果,一是允許民間集股開采;二是要求有關(guān)省份制訂章程加強(qiáng)管理。
較諸鐵路,采礦業(yè)中的商辦效果差強(qiáng)人意,私人投資較為活躍。據(jù)統(tǒng)計(jì),自1896-1900年,資本額在萬元以上的商辦采礦,新增14家,[30]遠(yuǎn)遠(yuǎn)超過甲午戰(zhàn)前20年的數(shù)量。同時(shí),官辦、官督商辦采礦企業(yè)也有15家。[31]
不過,中國本國的資本仍然有限,管理和技術(shù)水平都較落后。加上外資闖入中國采礦業(yè),已勢(shì)不可擋。一些官員也企圖利用外資,變不利為有利,并有"朝廷主之"的設(shè)想。[32]但實(shí)際并不如愿。如山西的晉豐公司、河南的豫豐公司,以招集中外資本的名義成立,但華資多徒有其名,外商卻享有調(diào)度礦務(wù)與開采工程、用人理財(cái)?shù)榷喾N權(quán)利。[33]至于德國奪占山東膠濟(jì)鐵路沿線礦權(quán),則純屬赤裸裸的暴力強(qiáng)制。1898年頒行、宣稱要"示洋股之限制"的《礦務(wù)鐵路公共章程》,規(guī)定須先有己資或華股十分之三,才能借用外資。[34]但這也意味著外資有可能占到十分之七。經(jīng)修訂后的章程,仍給外商留有一半股權(quán)的可乘之機(jī)。[35]更何況,與列強(qiáng)爭奪中國勢(shì)力范圍有利害關(guān)系的礦權(quán),清政府的法規(guī)毫無約束力可言。像德國在山東、俄國在東北的礦權(quán),就是如此。
總之,"利用"外資的結(jié)果,是中國權(quán)益的大量外泄。礦山、鐵路,莫不如此。
經(jīng)營管理上的變化,主要有兩個(gè)方面。一是經(jīng)營方式上采用公司組織,向市場(chǎng)化靠攏;二是宏觀管理上嘗試運(yùn)用法規(guī),并試圖集權(quán)于中央。
甲午后,清廷要求企業(yè)組織"一切仿西人成例"。在路礦要政中,也出現(xiàn)了公司化的經(jīng)營管理形式。
在鐵路方面,本欲商辦的蘆漢路,由官督商辦性質(zhì)的鐵路總公司承辦,野心勃勃的盛宣懷被王文韶、張之洞保薦為督辦。按設(shè)計(jì),總公司不是一個(gè)官衙門,而是獨(dú)立的商業(yè)公司,具法人資格,可以招商集股,舉借外債。公司組織悉照公司章程辦理,初具近代股份公司的組織形式。[36] 到后來,商股沒有著落,只得靠借外債筑路。債權(quán)國比利時(shí)藉列強(qiáng)的強(qiáng)權(quán)干預(yù),通過借款合同攫取了蘆漢路的大量利權(quán)。這樣,原先的公司組織形式,成了一紙空文。實(shí)際情形是,"代為營造"的比國工程司,擁有海關(guān)稅務(wù)司那樣的事權(quán),"一切購料、辦公、用人、理財(cái),悉資經(jīng)理",總公司不過加以"核定"而已。[37]公司化經(jīng)營打上了半殖民地化的烙印。
不僅如此。鐵路公司也是盛宣懷積累個(gè)人力量、實(shí)現(xiàn)其辦大事、做大官野心的工具。李鴻章失勢(shì)后,盛氏迅即投入張之洞的保護(hù)傘下,承辦了漢陽鐵廠。鐵路總公司本為造蘆漢路而設(shè),而盛氏為把"東南商股"也控制起來,得寸進(jìn)尺地要求承造蘇滬、粵漢等路,不再另設(shè)公司。[38]但華東華南地區(qū)的華商、僑商并不買帳,最后盛宣懷只能完全依賴外債。在當(dāng)時(shí)華商資本還不充裕、商人對(duì)官方督辦的公司心存疑慮的情況下,盛氏的作法,只會(huì)使商人望而卻步,失去投資的積極性。而盛氏反倒指責(zé)華商"眼光極近,魄力極微"。[39]
采礦業(yè)中,也有它的經(jīng)營管理機(jī)構(gòu),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礦務(wù)總局和礦務(wù)總公司。1895年冬,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設(shè)官礦局,又設(shè)南路、西路、中路三家公司,組織形式有官辦、商辦、官商合辦三種;商辦礦山也歸礦務(wù)總局,實(shí)為官督商辦[40]。礦務(wù)總公司則晚在1903年前后設(shè)立,管理全省礦產(chǎn)(官礦仍歸礦務(wù)總局)。[41]但在甲午戰(zhàn)后幾年,其他省份未見有全省性的礦務(wù)局或總公司存在。
與此同時(shí),一個(gè)統(tǒng)一管理全國路礦的機(jī)構(gòu),也在清政府考慮決定之中。1898年8月,礦務(wù)鐵路總局在北京成立。[42]11月,路礦總局制訂了《礦務(wù)鐵路公共章程》22條,[43]奏準(zhǔn)頒行。章程在吸收國內(nèi)資本、利用外國資本和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作出了規(guī)定。
嘗試運(yùn)用法規(guī)來指導(dǎo)、管理全國的路礦工作,表明在新形式下,清政府試圖建立起保障重大建設(shè)的制度。
四、政策變化的停滯與變法機(jī)遇的喪失
總起來看,甲午戰(zhàn)后清政府為實(shí)現(xiàn)籌餉練兵、恤商惠工的目標(biāo),不得不調(diào)整過去的政策,采取一些"變計(jì)",維持、改造和擴(kuò)充官辦、官督商辦企業(yè),以期國家資本延續(xù)下去,并向新領(lǐng)域擴(kuò)張;寬允私人資本的,給予有限扶持,對(duì)商辦要求作一些順應(yīng);將鐵路、礦務(wù)視為富強(qiáng)要政,以支撐衰弱的經(jīng)濟(jì),并在集資、經(jīng)營和宏觀管理上嘗試新形式;在護(hù)商之政、保商之法方面,也采取了設(shè)置近代經(jīng)濟(jì)職能部門、制訂獎(jiǎng)勵(lì)章程等措施,在形成振興工商的激勵(lì)機(jī)制方面,邁出了一小步。
然而,這些措施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實(shí)際效果也不如設(shè)想的好。恤商惠工的活動(dòng),總要受籌餉練兵的制約。19世紀(jì)末期,清政府面臨甲午戰(zhàn)爭、戰(zhàn)敗賠款和瓜分狂潮的戰(zhàn)時(shí)或準(zhǔn)戰(zhàn)時(shí)局面的重壓。它既要不折不扣地償還外債和戰(zhàn)爭賠款,又要整練軍備,就不得不羅掘全國的財(cái)力,能用于振興工商的資源極為有限。
不僅籌款的"急務(wù)"使資源難以向經(jīng)濟(jì)發(fā)展流動(dòng),而且通商惠工的政策也未能認(rèn)真落實(shí)。清政府采取過某些振興工商的措施;但如何能使個(gè)別的、具體的政策調(diào)整向全面的、制度性的變革推進(jìn),清政府卻舉步不前。進(jìn)步的知識(shí)分子一直要求設(shè)商部、定商律。康有為提出設(shè)商官、商律,[44]有一個(gè)直接管理全國工商事務(wù)的機(jī)構(gòu)。但農(nóng)工商總局不是這樣的機(jī)構(gòu)。"戊戌政變"后,農(nóng)工商總局遭裁撤。"變成法"的措施中,更沒有定商律的影子。所以,標(biāo)榜護(hù)商之政的措施,并沒有完全滿足恤商惠工勸農(nóng)的要求。至于各省商務(wù)局的工作,也沒有完全達(dá)到"實(shí)力講求"的要求。宣稱"隨時(shí)推廣"可興之利的山西商務(wù)局,卻在巡撫胡聘之的指令下,出面舉借洋債,使山西礦權(quán)嚴(yán)重受損。[45]
進(jìn)而言之,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本可以在"變計(jì)"上邁出更大的步伐,因?yàn)榇艘粫r(shí)期是"變祖宗成法"的較好時(shí)機(jī)。當(dāng)時(shí)中國的有識(shí)之,都在積極推動(dòng)維新變法,寄希望于清政府;反清革命還沒有形成燎原之勢(shì)。相反,民族危機(jī)激起中國人變法自強(qiáng)的緊迫感和決心。先進(jìn)的知識(shí)分子,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jí),都積極推動(dòng)維新變法,部分官僚也涉足其中,甚至慈禧太后起初也對(duì)變法活動(dòng)持默許態(tài)度,多少有些"上下一心"的氣象。此時(shí),變法維新,建立富強(qiáng)的制度基礎(chǔ),正是時(shí)候。不幸,慈禧太后為維護(hù)個(gè)人的絕對(duì)權(quán)威,在頑固勢(shì)力的鼓噪下,竟不顧大局,扼殺了變法運(yùn)動(dòng),斷送了大好機(jī)遇!進(jìn)入20世紀(jì),形勢(shì)劇變,清朝政府淪為"洋人的朝廷",國內(nèi)階級(jí)矛盾已不可調(diào)和,反清革命已勢(shì)不可擋。此時(shí)再談變法,已失去了基礎(chǔ)。這樣,戰(zhàn)后若干年的種種"變計(jì)"遠(yuǎn)離"變法"的要求,百日維新時(shí)期的短兵相接又以維新派慘敗而告終,由重大挫折和危機(jī)引發(fā)的維新變法契機(jī),終于喪失。腐敗的清政府,需要再經(jīng)歷一次更慘重的打擊,或許會(huì)拿出一些新的舉措。
[1] [4][5][14][15][18][19][23][29][41][42][45]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總頁3631、3631、3637-3638、3688、3744、4365、4160、4128-4130、3744、5109-5110、4150、4051(中華書局1958年版)。 [2]關(guān)于清末政策的目標(biāo)與導(dǎo)向的形成,本文限于篇幅,不擬討論。 [3]沈桐生輯《光緒政要》卷21,頁18(宣統(tǒng)元年上海南洋書局刊行)。 [6]《張文襄公全集》卷37,奏37,頁26--28; 卷47,奏47,頁18--19、14--15。北平文華齋1928年刊行。 [7]陳璧:《望巖堂奏稿》卷1;《光緒政要》卷22。 [8][40]汪敬虞編:《近代史資料》第二輯上,頁471、540。出版社1957年版。 [9]]盛宣懷:"條陳自強(qiáng)大計(jì)折",《愚齋存稿》初刊(100卷本)卷1。 [10]《寄王夔帥、張香帥》,《愚齋存稿》卷25。 [11]《清實(shí)錄》第57冊(cè),頁173。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 [12][16][24][27][36][39]中華書局1991年《強(qiáng)學(xué)報(bào)、時(shí)務(wù)報(bào)》合訂本2,頁1263、1805-1807、3267-3268、1179-1187、1179-1187、1179-1187、1179-1187、1179-1187。 [13][17]《清實(shí)錄》第56冊(cè),頁830。 [20]《籌設(shè)商務(wù)局片》,《張文襄公全集》卷43,奏43。 [21]麥仲華編《皇朝經(jīng)世文新編》(21卷本)卷10下,商政,頁38-39。上海譯書局光緒戊戌年印。 [25]參見"通海設(shè)立紗廠請(qǐng)免稅厘片",《張文襄公全集》卷42,奏42。 [26]"蘆漢鐵路商辦難成另籌辦法折",《張文襄公全集》卷44,奏44。 [28][44]《戊戌變法》(二),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頁291;246、249。 [30][31]見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附錄之四十三、四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2][33][34][35][43]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礦務(wù)檔》,頁2255-2256,1404、2979,47,50,44-49。 [37]《愚齋存稿》卷2,頁34--38。 [43]汪敬虞前引書,第二輯上,頁540,《礦務(wù)總局章程》見《時(shí)務(wù)報(bào)》第20冊(cè)。 [44]《礦務(wù)檔》頁2414、2379;《光緒朝東華錄》總頁5109--5100。 [48]參見胡聘之奏:"晉省籌辦礦務(wù)擬先修鐵路折",《變法自強(qiáng)奏議匯編》卷8,頁9,上海書局1901年;《光緒朝東華錄》總頁4051。
大法律評(píng)論.jpg)
代中國文學(xué)論叢.jpg)
品安全與召回.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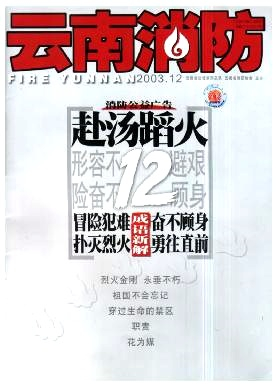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