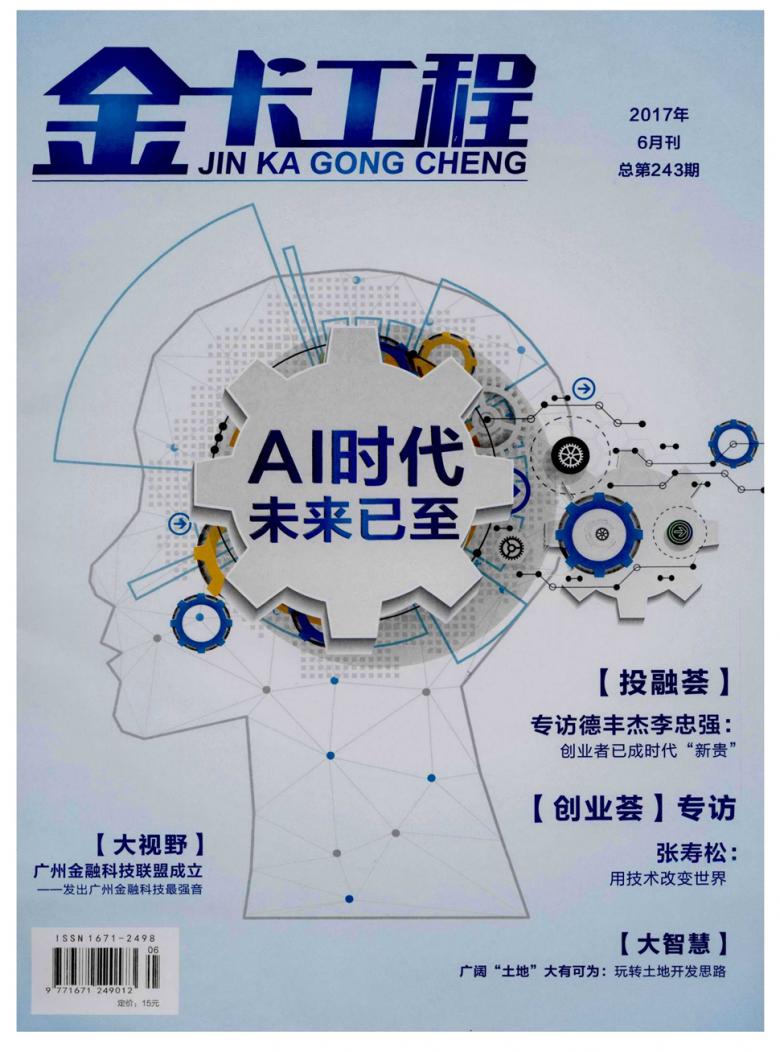影響經濟體制轉型的中國文化信念分析
呂余生 蔣神州
[關鍵詞]經濟體制;轉型;文化信念
[摘要]文化信念影響制度選擇,是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影響因素。“仁”是中國文化信念的主導,其核心是“事親”思想。泛家文化又馴化出對權威的盲目服從。但由于中國信仰缺失,人與人之間交往更多地傾向于血緣、地緣和業緣等,逐步發展成一種關系文化,遵循“禮治”的觀念。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化應充分考慮現有的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并能盡快順應這些文化信念與現代制度相沖突時所引起的修正。
文化是由社會產生并世代相傳的傳統集合,亦即指規范、價值及人類行為的準則。“文化信念是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是社會全體成員共有的觀念,它不能通過實證和分析去證明。文化信念影響制度選擇,是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被社會成員所共享和內化,能激勵和引導人們采取某種在特定社會情形中有技術可行性的行為,并引導后續的制度發展。制度產生的行為使得新制度下形成新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是對以前文化的包容,也可以是一種修正。因此,一個社會的制度的運行不論是高效率還是低效率的,對它的研究都離不開文化信念。
不同的文化信念使不同的社會特征的人產生不同的經濟行為,進而導致在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的交易有不同的效率和盈利關系,所以不同的文化信念會導致不同的體制轉型發展路徑。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國體制轉型走向了與東歐各國不同的路徑。但是,中國體制轉型的未來路徑選擇仍存在很多的未知因素。只有將特定背景下的歷史信息及其形成的文化信念與經濟學慣用的分析框架相結合,才能較好地預知制度發展的特定路徑選擇。中國有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歷史發展軌跡,有自己源遠流長的文化信念,研究中國特色的制度變遷路徑,需要充分理解這些文化信念因素,進而給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提供文化信念上的邊際修正的指引,加速體制轉型的步伐。
一、“仁”是中國文化信念的主導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其核心信念當推“三綱五常”。“三綱”則是后面述及的泛家文化思想的先驅,它與“五常”的核心理念也是一致的。“五常”思想的形成和相關的權威表述如下:“惟《易·文言》始有‘仁、義、禮’三字,而無‘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為四德”(《四書改錯·貶抑圣門錯》卷二十,頁三)。“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中庸》)。“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孟子·離婁上》)。后董仲舒又加人“信”,從此,形成“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賢良對策》)。這“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由以上引述也可知,“仁”的思想是“五常”的核心,而“仁”最核心的思想則是“事親”。加上“克己復禮”和“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的診釋。總結起來“仁”也就是順從人倫差序的教化思想。可見“仁”也是個很狹隘的概念,其思想也并非利他性的。“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論語·雍也》)。可見,儒學思想認為要是真出于“利他”思想去做事,那就不是仁而是圣了。因此,可總結說,儒家思想的核心信念是在保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遵循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主導,尊卑有別的信念內化賦予了中國領導者無上的權威,形成了一種“泛家文化”。
二、泛家文化
臺灣李亦園提出中國文化是“家的文化”。“家族不但成為中國人之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為政治生活的主導因素”。家族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并圍繞公共財產而組合的全體人,他們的統一性由家譜賦予合理化,這些群體內的關系是信賴和合宜的問題,他們相互給予忠誠和相互支持。近年來改革開放的沖擊,由家庭中學到的經驗類化到其他組織中,形成了泛家族主義或類化的家族主義。中國家文化亦演進為“泛家文化”。這里的泛家文化主要是指基于血緣的家文化社群按差序格局的方式外推出,包容了摯友、地域、同學和生意伙伴等關系人群的一種文化。
Redding和鄭伯壎,采用了主位的研究路徑,對中國香港、印尼、新加坡、中國臺灣等華人家族企業中的高階領導議題進行了探討,并指出華人企業的高階領導擁有清晰而鮮明的特色,可以稱為家長式領導。家長式領導是一種類似父權的作風,擁有強大的權威,但也有著照顧、體諒部屬以及道德領導的成分在內。家長式的作風不僅在家族企業中出現,也常會在非家族企業和政府機構中發現。這種泛家文化是一種與西方契約文化相對的文化,它催生了人們對權威盲目服從的信念。在制度的增強過程中,這種信念不斷內化,形成泛家文化中的餡媚思想。如:“人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閩。過位,色勃如也,足蹬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闔闔如也。君在,椒踏如也,與與如也。”(《論語·鄉黨》)
三、信仰的超越
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信仰缺失。這實際上是因為中國歷經了對信仰的失望后,已經在意識形態上超越了信仰。它可追溯到商周文化對儒家思想的影響。殷周的社會變遷可視為一場宗教改革運動。周王朝初期的歷代帝王鑒于夏、殷失敗的歷史教訓,對傳統宗教進行了一次深刻、徹底的反思,并對商朝的宗教文化進行了改造。周公針對殷商“神授王權”的思想提出王朝存續的實質在于敬德保民。《尚書·蔡仲之命》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泰誓》也說:“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摒棄天命,依賴人事,周時的中國文化已經上升到對殷商宗教否定和批判的高度。周時已將“天命”與“民之所欲”直接聯系起來,順應民意已成為執政目標。后演進成儒家思想“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論語·學而》)。在西周末年,自民間也興起一股反對宗教的潮流,“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蹲沓背憎,職競由人”(《詩經·小雅·十月之交》)。人們開始懷疑宗教的奴役性質,認為自己的悲慘命運不是天賜,而是人為。儒家也自此擺脫了宗教信仰的束縛。“西方之路開于基督,中國之路開于周孔,而以宗教問題為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也基于此因,“中國逐漸轉進于倫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延續于后。西洋則以基督教轉向大團體生活,而家庭為輕,家族以裂,此其大較也”。宗教信仰的缺失使得西方的團體格局在中國不能產生,而形成了一種基于倫理本位的關系格局。 四、關系文化
信仰的缺失和泛家文化的信念使得關系在中國乃至整個華人社會都十分重要,不管是對企業的經營行為還是其他社會行為,都有深刻的影響。關系在現代社會已經超越了血緣和地緣,擴張到了業緣關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際關系具有特殊意義,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共享按照關系強弱進行。在關系文化的影響下,信息集中于一個關系鏈的核心人物即首領,他是建立在一種人際關系等級結構基礎上的,這樣的等級結構一般是人格魅力型。在這個關系型團體內部,其成員有趨于一致的信仰和價值觀,減少甚至消除成員之間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機會主義。一旦這種關系依存的等級結構與權力等級融合后,這種等級將生成更加牢固的關系官僚結構,可產生極強的凝聚力,使得交易的信任度更加高。且交易的次數是隨著關系的建立更加頻繁,這樣就會產生一個趨于無窮次的重復博弈,可以使得即便是博弈參與人的懲罰機制是雙邊的,一樣也能巨大的約束力。
馬克斯·韋伯指出:“儒家君子只顧表面的自制,對別人普遍不信任,這種不信任阻礙了一切信貸和商業活動的發展。“在中國,一切信任,一切商業關系的基石明顯地建立在親戚關系或親戚式的純粹個人關系上面,這有十分重要的經濟意義。倫理宗教,特別是新教的倫理與禁欲教派的偉大業績,就是掙斷了宗族紐帶,建立了信仰和倫理的生活方式共同體。
五、禮治文化根深蒂固
“禮”是儒家文化極為重要的核心內容之一。“孔子之學,由‘禮’觀念開始,進至‘仁’、‘義’諸觀念。故就其基本理論言之‘仁、義、禮’三觀念,為孔子理論之主脈,至于其他理論,則皆可視為此一基本理論之引申發揮。 “禮者,貴賤有 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富國》)“禮”的核心要義是要教化人們接受貴賤、貧富的等級思想,遵守統治階級制定的規則,安于接受統治階級的剝削。
禮治和法治思想有很大差別。“禮”治通過教化,奴化被統治階級的思想,傾向于事前控制;而法治思想傾向于事后懲罰。故《大戴禮記·禮察篇》認為:“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禮云,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敬于微吵,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因此,“禮只教人依禮而行,養成道德的習慣,使人不知不覺的‘徙善遠罪’。故禮只是防惡于未然的裁制力。“禮”這種思想具有很強的制度穩定性。它使得獨裁和專制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56個民族且沒有宗教信仰約束的渙映大國,在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通行無阻。這種思想的適應能力和統治能力之強,可窺一斑。即便朝代更替和外族人侵都沒有動搖這種文化信念。中國要徹底實現法治,消除人倫差序的等級觀念,可謂是任重道遠。集體行動的邏輯也使得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很難打破這種信念慣性。
六、結論
行為信念有一定的慣性,只要人們一旦形成特定的行為信念,那么就不想嘗試形成新的信念。即使某個新的文化信念有更好的社會整體福利,但是只要他認為其他人會采取原有的文化信念行事,那么依照信息瀑布效應,他最佳的博弈策略還是按照原有的文化信念行事。當一個人預期到其他人都是對領導絕對服從時,自己的最佳博弈策略也是選擇服從,即便自己知道領導的決策是錯誤的。
只有當信念與社會反應聯系在一起以及預期的規范行為產生行為規范時,制度才能成為內在的東西。在中國可以不經過民意測驗就能頒布法令,進行體制轉型,但這很難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有足夠數量被認為會遵守規則的人相信其他人也會遵守規則。只有當每一個人都必須相信信念和規則的協調作用,并且相信規則的頒布影響著行為和信念,那么才會切實遵守它。如果堅持原有信念,即使新規則已經頒布,人們也將不會遵守。因此,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社會上逐步形成了大量的潛規則。沒有文化信念上的正確修正作為指引,潛規則將對中國經濟體制的轉型帶來極大的負面效應。上述種種文化信念,是阻礙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應充分考慮現有的這些文化因素,引導建立與現代社會制度相一致的文化信念,并能盡快順應傳統文化信念與現代社會制度沖突時所引起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