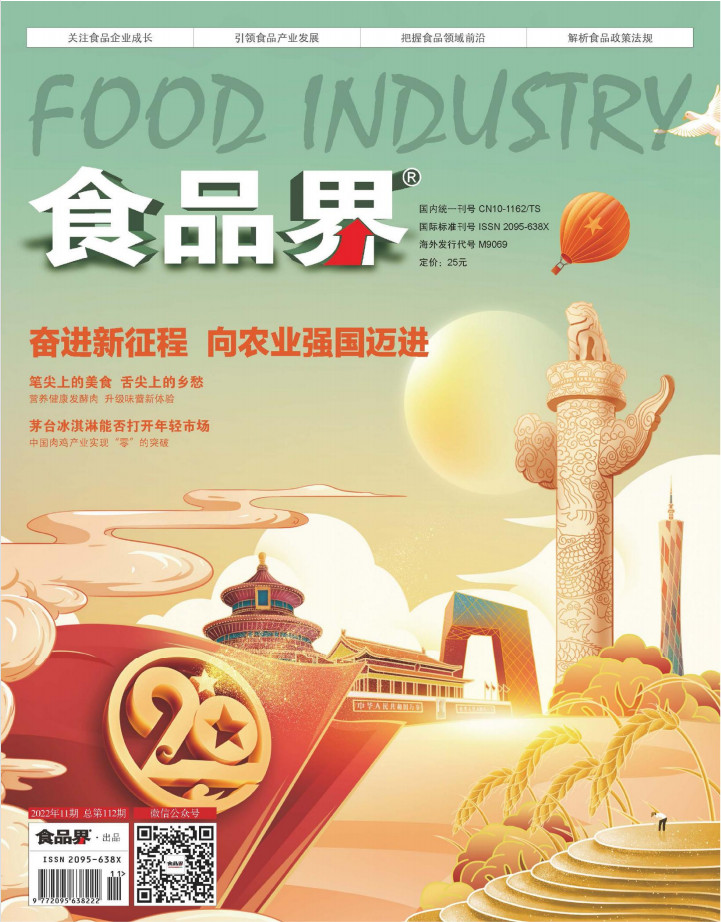試析《殘月樓》中的女性形象—加拿大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雙重影響
劉克東 段儒云
論文關鍵詞:李群英《殘月樓》女性中國傳統文化加拿大文化
論文摘要:《殘月樓》作為一部反映加拿大華裔移民歷史的小說,將故事的背景設定在一個大家族,通過對王家四代女性命運的講述,深刻地反映出了華裔女性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加拿大文化相互沖突中生存的艱難狀況及其艱辛的成長歷程,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加拿大華裔女作家李群英的第一部小說《殘月樓》( Disappearing Moon Cafe, 1990)一出版即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先后獲得了“溫哥華市圖書獎”和總督文學獎提名,從而奠定了她在加拿大文學史上的地位。
《殘月樓》作為一部華裔小說,主要描述了從1892年到1987年移民到加拿大生活的王家四代女性的命運,以及她們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加拿大文化的相互沖突下的思想歷程。每一代的成長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兩種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在特定的時代,不同的生活背景下四代女性也具有不同的特征。
第一代女性李木蘭(1880一1951)是傳統中國女性,對于加拿大文化全然不了解,她只是生活在移植的中國傳統禮教中,命運是悲慘的。在古老的中國,女人毫無地位,一切服從于男性。在男性主宰、男尊女卑的世界里,她們惟有屈從,才能生存下去。為適應父權制家庭的穩定、維護父權及夫權家庭利益的需要,“三從四德”被視為婦女應有的道德行為規范。儒家經典《儀禮喪服—子夏傳》中提出了“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之說,意思是說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聽從家長的教誨;出嫁之后要禮從夫君,與丈夫一同持家執業、孝敬長輩、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堅持好自己的本份,想辦法撫養小孩長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這就使得中國傳統女性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權,只能夠呆在家里主持家事,并且逆來順受。
李木蘭就是在這種教育理念下成長起來的,接受并且推崇這種思想。她在中國的時候,因為貴昌在外,無論什么苦都自己扛著。到了加拿大之后,不能融人當時的社會,千辛萬苦從中國為兒子娶來中國媳婦芳梅,只要求能夠為自己家續香火。當芳梅和崔福結婚五年之后還未有孩子時,李木蘭認定芳梅無法生育,開始刁難芳梅,惡語相向,并打算強制休掉她,同時慫恿王崔福與女侍宋昂茍且。不久之后宋懷孕,李木蘭暗中安排芳梅外出,并試圖上演貍貓換太子一幕。當計劃失敗之后,木蘭依舊關心孩子的去向,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讓基曼認祖歸宗。但是由于大家族的面子觀念極重,要求門當戶對,所以李木蘭的計策只是權宜之計。她想讓基曼認祖歸宗,但是絕對不會接納宋進人自己的家庭,這一點也深刻地反應了她身上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
可以說,李木蘭雖然自己也受到了中國傳統理念的迫害,但是她卻并沒有打算要改變這一現狀,而是接受了這種命運,并將這種思想轉嫁到兒媳芳梅身上。在此期間,芳梅懷孕,隨著孩子的出生,因為“母以子貴”的觀念,木蘭也開始退居二線。家庭的重心也開始轉向芳梅,但是這卻并不是她最終的結局。對于木蘭來說,因為堅守中國封建的傳統文化而拒絕接受加拿大的文化,經濟重心的轉移并不是她最悲慘的結局。當她風燭殘年的時候,本該頤養天年的她卻得知了基曼并不是自己親孫子的事實,也就是說她這么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夢、所固守的傳統,最終卻因為她自己而破滅了。在這位老人的心里她已然成為了王家的罪人。在這種中國封建傳統的思想的禁錮下,她的余生也不能得到解脫。
第二代女性陳芳梅(1902一1962)身受加拿大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影響,開始有了一些抗爭意識,卻為經濟利益和權力誘惑所困,沒有勇氣沖破婚姻的牢籠,犧牲了自己的愛情。在中加文化的沖突下,陳芳梅從一個惜懂少女逐漸成長為殘月樓精明強干的老板,并將殘月樓的生意經營得有聲有色。初到加拿大的陳芳梅任勞任怨,但在融人加拿大文化和社會后開始覺醒,自立自強。從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年少時的陳芳梅單純善良,在殘月樓中安靜地忙碌,屬于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傳統女性。即使剛開始的時候遭遇了婆婆的不公平待遇,在給家里寫信的時候也從來不吐露半分,而是將所有的苦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咽。婆婆木蘭決意要休掉自己的時候,芳梅也表現出了中國傳統女性的特點,畏懼權威,同時也是一種生存之道,休掉之后就意味著給娘家蒙羞。但是當遭遇了老公的外遇和婆婆的侮辱之后,芳梅與王廷安產生了感情,并為其生下了三個孩子,可以說這個時候芳梅的選擇是一種女性意識的覺醒,在加拿大文化的影響下她已經不會再做逆來順受的中國傳統女人。
是什么導致了陳芳梅女性意識的覺醒?一方面可以說是為了在異地生存,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加拿大文化的影響。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文化與美國相似。他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因而男女具有一樣的權利。同時他們信仰自由和個人主義,人并不是為別人而活著,而是為自己而活著。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后,西方女權主義開始了第一次發展,主張婦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應當平等,在經濟上與男性平等,要求從經濟上解放婦女。生活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芳梅自然會逐漸意識到自己作為女性所應有的與男性一樣的權利。這就與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婚姻和丈夫決定女性的命運相違背。憑借著母以子貴,芳梅開始凌駕于婆婆之上,成為這個家庭的女主人,并且選擇了物質,選擇了權利,選擇了像男人一樣獨立自主地生存。
陳芳梅放棄了與廷安之間的愛情,并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將殘月樓經營得蒸蒸日上,取得了經濟上的真正獨立。可以說從一開始的少經世事到后來的感情和肉體的出軌,再到對感情的放棄,對物質、經濟的選擇,芳梅的選擇與成長無一不是在生存危機與加拿大文化的雙重影響下產生的。但是在陳芳梅后期的思想中,她對故土和遠在家鄉的親人的思念卻對她的生活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她在逐漸地適應新環境,并在事業上獲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得不到下一代和加拿大主流文化的認同,她依舊想回到生養她的土地,想回到親人身邊,結束這場夢魔。同時她還把自己的孩子送回中國,希望她們能夠接受中國的文化與思想。
第三代女性碧翠絲(1926一)和蘇珊(1934一1951)是在加拿大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具有獨立意識且叛逆的一代,也是對自我身份最迷茫并且最矛盾的一代。她們在學校接受著純粹的西方教育,會說流利的英語。她們自以為是加拿大人,但是卻因為生理特征而飽受歧視,被視作二等公民。雖然1947年加拿大取消了排華法案,但是這種事實上仍存在的歧視卻表現在方方面面,導致急于融入主流文化的她們無法被加拿大人接受。而當她們想要從家庭中尋找溫暖與認同的時候,她們卻發現祖母和母親那一代所持有的中國傳統觀點與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堅信的觀點完全不同。同時長輩的整腳英語與勾心斗角也讓她們無法接受。這樣,她們無法被加拿大文化所認同,同時也不能夠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種對自我認同的迷茫與失落中,她們變得叛逆乖張。正如管平說過的一樣,隨著女權主義在北美的發展,第三代女性成了職業女性,在兩性關系上也有了更多的解放和對自我幸福的追求,因而母女間出現了意見的分歧。
當然面對這樣的無法認同,中國和加拿大文化的相互沖突,碧翠絲和蘇珊的反應劇烈程度和結局也都不同。作為乖乖女的碧翠絲愛上了貧民街區的基曼,無論母親怎樣反對也沒有退縮,但是她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卻更符合中國女性的特點。當面對母親的強烈反對和祖母干涉的時候,在不知道真實原因的情況下,她并沒有選擇私奔,也沒有像蘇珊一樣,小小年紀就和摩根發生了肉體關系并懷孕。對于她來說,當決定要和基曼在一起的時候,她想到的是通知雙方父母,先得到父母的允許。碧翠絲遭到母親芳梅的反對后,基曼去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碧翠絲則被母親帶著離開了是非之地,去了香港。但是像中國歷來的癡情女子一樣,這樣的分離卻并未能夠拆散她們和愛人。對于碧翠來說,不忍違背母親,堅持保守貞潔是中國元素的作用,而最終決定不向母親屈服,在基曼以戰斗英雄的身份歸來后,她毅然決然地離開父母和基曼結婚,則是受到了加拿大文化的影響,是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表現。 蘇珊則有別于碧翠絲。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女權主義在這個大動蕩的時期風起云涌。無論是“激進女權主義”還是“自由女權主義”都在“性”方面訴求女性的“解放”,而年幼的蘇珊接受的正是這樣一種教育。所以蘇珊愛上了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摩根(當時不知情),巧歲的時候便與其發生了性關系并且懷孕。知道真相之后,依舊要求摩根帶自己私奔。盡管摩根對她并不好,但是她卻甘愿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去追隨摩根,離開這個充滿中國封建禮教的家庭。這一切都表明,在第三代,中國傳統思想已經逐漸在她們的思想中消褪,甚至完全消失。在傷心與無奈中,蘇珊最終選擇了自殺,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是卻真正脫離了母親的掌控,脫離了白人的歧視,脫離了中加文化的沖突,也脫離了身份認同的矛盾。雖然悲慘,卻仍是一種解脫。
第四代女性凱瑩(1950一)是一個知識女性,也是受加拿大文化影響最深的女性,但是最終卻也理解了中國文化。同時理解兩種文化,證明了凱瑩的成熟。
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歐美女權主義的影響,加拿大的婦女運動也掀起了高潮,而這一次也使得“性別”問題顯得特別突出。女權主義者開始意識到女性不僅要關心男女不平等的問題,更要思考其本質原因。隨著運動的發展,70,80年代的加拿大,“性別”問題成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人們開始意識到很多社會現象都是以男女不平等為基礎的。女權主義者呼女性的聲音,支持女性的解放。而作為第四代女性的凱瑩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女權主義盛行的社會背景下的,加上她所接受的教育,加拿大的這種女性獨立自由的文化已經完全滲透到了她的思想中。
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幫助凱瑩了解了家族史,理解了女性長輩。她的母親碧翠絲出生在加拿大,接受加拿大文化,因而并沒有過多地對凱瑩進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對這個家族的過去、對中國文化,凱瑩了解得并不多,并且她只會說英語而不會漢語。當然,凱瑩的中國文化的缺失并不僅僅表現在她不認識漢字,不會說漢語,還表現在一些對習俗的不了解上。凱瑩誤認為“中秋節”是“August Moon Festival",而對中國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坐月子也很不理解,她會以加拿大白人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認為這樣會有“腥味”。同時碧翠絲也并沒有過多地干涉自己女兒的戀愛自由。在這樣的環境下,凱瑩成長為一個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并且嫁給了亨利·李。如果沒有摩根的出現,凱瑩永遠也不會深人了解這個家庭曾經的歷史和矛盾。正是由于摩根的介人,凱瑩開始對家庭沉默、神秘的歷史充滿好奇,到中國去學習漢語,閱讀那些泛黃的家書,并結識了中國朋友。凱瑩此舉使得她找到了自己家族文化的根源,更加清楚地認識了自己的身份。和中國朋友的交往也使得她對外祖母和曾外祖母的行為更加理解。凱瑩的孩子的出生揭開了家族歷史之謎。孩子出生之后,碧翠絲立即檢查孩子是否發育正常,這一怪異舉動終于揭開了那段緘默的歷史。而在母親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凱瑩通過了解做母親的快樂與痛苦,才逐漸理解母親、祖母和曾祖母的往事,并且意識到中國女性在加拿大的曾經痛苦的生活和偉大之處。
對于中加文化的理解,幫助凱瑩在自己的婚姻和性取向上做出重要決定。了解家庭的歷史并沒有把凱瑩轉變為一個擁有中國傳統文化意識的女性,相反,她更具有那個時代的女權主義意識。她決定不對這段家族的不光彩歷史諱莫如深,而是用自己的話語寫出這段歷史,讓大家都來了解生活在加拿大社會邊緣的中國女性的生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女性的生活贏得更多的權利和利益。同時,在故事的最后,凱瑩并沒有留在自己的丈夫身邊,相反,她給自己的莫逆之交、遠在香港的女醫生赫米亞掛了電話,并投奔她而去。總之,凱瑩所受加拿大文化的影響要遠大于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是,中國文化幫助她了解了自己的家族史,認清了自己的身份。她是家族中第一個敢于放棄婚姻的人—這一點比她的外祖母陳芳梅進步許多—也是第一個表現出同性戀傾向的人。這種反叛是她看清歷史,確立自主身份的結果,也是中加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
總的來說,李群英的《殘月樓》是一部反映加拿大華裔女性在加拿大生活的歷史和現狀的小說。小說中涉及到很多主題,包括歷史(排華政策)、政治(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父子關系、夫妻關系以及母女關系和移民文化等,但作品最成功之處在于它真實地再現了生活在加拿大文化邊緣的華裔女性的生存狀態,即她們如何在中加文化的沖突的動態平衡中尋求出路的痛苦過程。通過李群英的描寫,我們對加拿大華裔女性有了更多的了解。雖然《殘月樓》中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沉重的歷史,但是這段移民歷史中女性的形象及女性的成長卻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