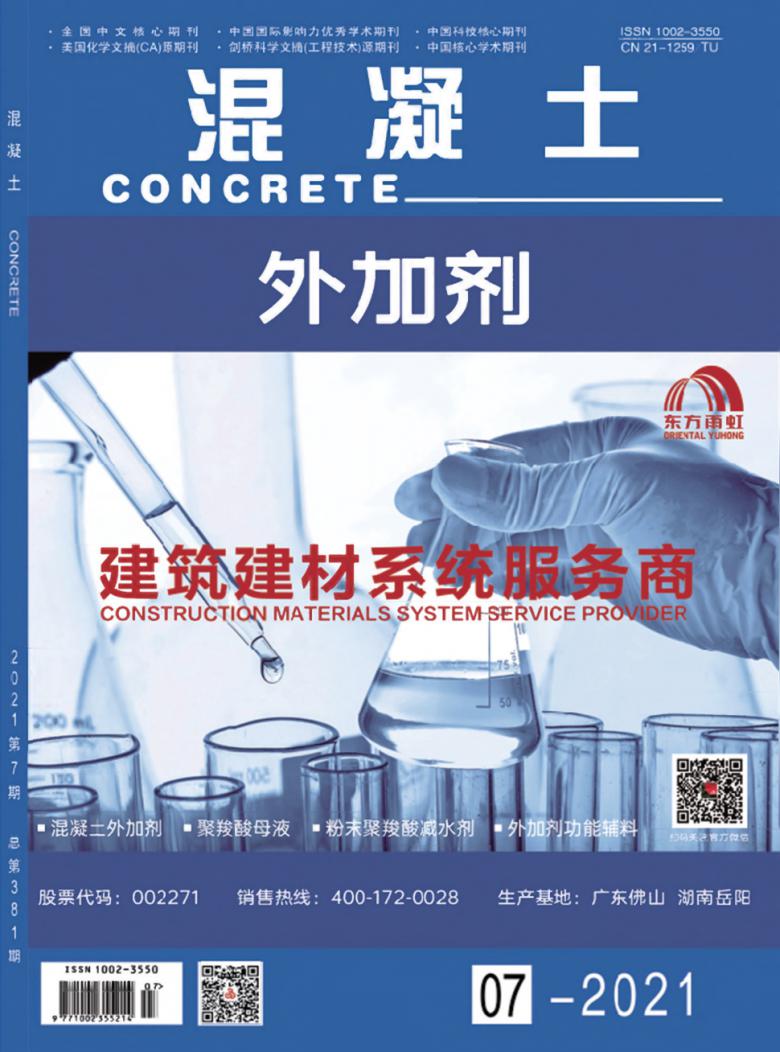日本STS研究的文化審視
王秋菊 殷國梁
摘 要: 對日本而言,STS是外生型學科。早在傳入日本之前,日本社會中就已經存在著與STS研究相關 的文化因素,為STS研究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奠定了基礎。從歷史文化視角探析STS研究在日 本傳播的文化背景,不難看出:日本歷史上注重吸收外來科技的文化傳統成為STS研究傳播的 文化基礎,而20世紀初對科學技術的理論研究為STS研究的傳播作了理論準備;二戰后,理科教 育重心的調整-由偏重“技術”教育向重視“科學”教育的轉變-則是STS研究傳播 的內在驅動力。同時,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舉國上下對環境教育的重視,從現實角度對STS研 究的傳播提出了要求。
關 鍵 詞:日本;STS;科學技術;文化
STS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國,是在因科學技術空前發展而對社會的正面作用和 負面影響日益明顯的情況下,人們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進行理性思考的產物。正由于它深 刻地反映了時代的需要,所以一經產生便迅速擴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圍。20世紀80年代初,ST S開始在日本傳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規模,并產生了較大影響。對于日本來說,STS是一門外 生型學科,同歷史上吸收、消化外來新事物一樣,STS的傳播過程也是一個慢慢地融入日本既 有的社會文化土壤的過程。同時,回顧日本的科技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實在STS傳入日本之 前,日本社會中已經存在一些便于STS傳播的文化因素,為STS的到來和傳播作了事先準備。本 文試從社會文化基礎、理論準備、理科教育、環境問題等角度對日本STS傳播問題進行探討 。
一、 歷史上注重吸收外來科技的文化傳統-STS傳播的文化基礎
STS于20世紀中葉產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發展,并且日益滲 入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人類的物質文明獲得空前的提高和發展,科技成為人們謳歌和依賴的力 量;另一方面,在經受了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環境與生態危機之后 ,人們面對日益暴露出來的科技對人類生活的負面影響,開始對科學的價值、技術的作用產生 了疑慮和困惑。20世紀60年代,形成了歐美學者所謂的“一種激進而出于理性的當代反科學 現象”或“反科學的文化運動”[1],讓人們越來越關注現代科技可能帶來的社會和 文化問題,從而促使人們對科技的反思。
從上述STS產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發端于科技發達的西方國家,因為近代以來是以科技 發展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業文明主導的時代,科技已經滲透至西方社會生活的內核和基質;西 方社會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時,也同樣關注科技的負面效應。而作為近代東方第一個依靠科 技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日本,雖然近代科技發展起步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來先進文化 (包括科學技術)的特點,所以科技對日本社會的影響迅速加大和深入,成為日本社會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來科技發展本國國力的歷史傳統,因此,當科技的 負面影響日益顯露時,日本社會自然就產生出引入解決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理論-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個在中國大陸文化影響下發展的后進國家,雖然早在繩紋式文化時代就 有了陶器、石器、紡織等原始的生產技術,卻不曾擁有自己的科學。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識 到,“島國的命運使日本沒有獨創文化的能力,只能貪婪地吸取外來文化,經過取舍、選擇 ,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文化”[2]。從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為和異種民族、異質文 明的接觸、同化而努力著”[3],這一點也突出表現在科學技術的發展進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術革命,起源于農業技術的變革。但是,日本農業技術的變革主要不是依靠 自身的緩慢積累,而是在先進的漢族大陸文化的強烈影響下發生的。公元前3世紀末,早已 跨入鐵器時代的漢民族,把金屬文化和農耕技術傳入日本,使日本列島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 銅器時代,從新石器時代的繩紋式文化直接進入鐵器時代。公元6—9世紀,中國古典科學伴 同佛教文化傳入日本,在明治維新(1868)以前,屬于漢學體系的中國古典科學在日本科學 史上居統治地位達千年之久。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中國文明在日本歷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難以估計的。”[4]依靠輸入外來文化去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是貫穿在整 個日本文化史中的一個重要特征。
從16世紀開始,日本開始接觸西方近代科學。在“鎖國”的背景下,日本以荷蘭為渠道來吸 收西方科技文明,成為日本近代科學的胚胎-蘭學興起的契機。蘭學家們通過翻譯西方科 學書籍、結成學術團體以及進入西方學者在日本開設的學校學習等方式,不僅掌握了近代自 然科學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成為變革日本社會的一支積極的革 命力量。明治維新后,以蘭學家為代表的新知識階層在國家的引導下,大規模地引進、發展 近代科學技術,促進了日本社會的再次飛躍發展。
在近代以來的國家發展歷程中,日本政府與國民深刻地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立國之本,它不僅影 響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而且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當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而要 求對之重新審視時,擁有融合外來文化悠久傳統的日本社會具備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礎。
二、 20世紀初期以來對科學技術的理論研究-STS傳播的理論準備
STS是一門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相互關系的新興學科。在此之前,已經有其他學科從不同角 度把科學技術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比如從歷史的角度研究科學技術,就是科學史和技術史; 從哲學的角度研究科學技術,就是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科學技術,就是科 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雖然STS與上述學科有著區別,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學科的研究為ST S研究作了理論準備。從20世紀初期開始,日本學者就已經從哲學角度來解釋科學技術。
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日本,其嶄新的歷史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為研究科學技術論提 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被稱為“日本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的《唯物全書》(66冊),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發行的。1935年,戶坂潤發表的《科學論》被認為代表了戰前日本 科學論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學是“歷史的社會的客觀存在”,“是知識在社會上被 普及,在歷史上被繼承的事實本身”[5]等觀點,為日本科學技術論的研究和發展奠 定了基礎。
在技術論方面,在20世紀40年代,日本展開了關于技術定義的討論,出現了相川春喜關于技 術是勞動手段的體系的“體系說”和武谷三男關于技術是對客觀規律的有意識的應用的手段 的“手段說”。無論是“體系說”還是“手段說”,都只是局限在生產實踐的狹隘領域里討 論問題。隨著戰后勞動手段的進步促成了社會技術結構、產業結構的重大變革,日本的技術 論研究也隨之深入到技術發展與社會結構的關系、技術發展與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的關系等 方面。
從歷史角度研究科學技術方面,日本學者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注重科學史研究,做了許 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為了探究科學史的本來面目,以便針砭時弊-抵制帶有 國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色彩的通俗科學史宣傳,一些進步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研究者創立 了日本科學史學會,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科學史、技術史研究的發展,并為保衛和發揚健康的 科學精神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彈危害后,日本學者就開始關 注科學社會學,著重研究了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價值。
20世紀60年代末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長足發展,日本出現了科學技術與自然之間、與社會之 間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會物質財富空前豐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會公共問題嚴重威脅著人 類社會的穩定和安全。科學技術的發展向何處去?圍繞這一課題,日本學者開始拓展自己的視 野,從自然、人類、社會的廣闊背景中對技術作統一的考察,把研究領域推向現代社會中的各 種實際問題,比如未來技術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系等。由此可見,在STS傳入日本之前,日 本學者已經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刻的闡述,為STS的到來奠定了理論基礎。 三、 由偏重“技術”教育向重視“科學”教育的轉變-STS傳播的內在驅動
關于STS的學科內容,日本學者起初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作為教育內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為學術研究領域的STS”-STS研究[6],后來又加上了第三 部分,即“作為管理領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學者很重視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 視STS教育。他們認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廣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進行宣傳和普及,使他們形成STS意識和相應的價值觀,是具有自我 意志決定力的一種運動[7]。從世界范圍來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領域中,STS教 育活動在科學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會科學教育中比較明顯。而對于日本來說, 在STS傳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經歷了由重視“技術”教育向重視“科學”教育的轉變, 在一定程度上為STS教育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迄今為止的100多年間,日本貫徹“教育立國”的方針,通過教育改革努力引進西方科學 技術,并在引進方向上進行過兩個選擇。一個是重視“科學”,即重視作為自然科學基礎的 西方科學的精神,以培養國民科學的自然觀、科學的社會觀;另一個選擇是重視“技術”, 即把自然科學只看做技術的手段,僅僅學習作為科學成果的技術,并以此作為引進的方向。 在上述的兩次選擇中,日本曾一度選擇了第一種引進方向,主要是因為當時福澤諭吉等有留 學背景的啟蒙運動家強烈主張在每個國民的意識中培植西歐式的科學的精神,對初期的明治 政府產生強大的影響。
但隨著對國家意識形態控制的加強,并出于擔心科學的精神、合理的思考會批判現行的體制 ,明治政府通過教育制度的變革,把“修身”(即傳授國家主義道德科目)作為最重要的學 科,縮短理科的教育時間,其內容由培養科學的精神、科學的自然觀轉向傳授零散性的科學 成果的片斷,開始重視實用性的“技術”教育。對“技術”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視效率 ,追求效率,講究實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識的積累。二戰后,受美國占領軍當局的指令,日 本開始了徹底的教育改革,廢除了國家對教育的統制,尊重教師和學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 省強調,“培養科學精神,使合理主義、實證主義深入地滲透到國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識中, 更新國民的教養,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設新日本文化的基礎”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在實施新 教育制度的同時,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課時間,實現由重視“技術”教育向重視“科學”教育 的回歸。
STS作為一門跨世紀的新興學科,對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其主要表 現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觀,其顯著特點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系和整體化,科學 技術和社會的密切結合,其宗旨是培養具有科學技術素養,全面發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顯然,STS教育觀要求人們具有一定的科學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對“科學”教育的重 視,一定程度上呼應了STS教育的要求,為更好地理解STS、傳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礎。
四、 20世紀60年代以后環境教育的重視-STS傳播的現實需要
二戰以后,迅速發展的科技提高和發展了人類的物質文明,各參戰國也依靠科技來實現 國家的復興。20世紀60年代以前,人們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積極作用,因為它的負面影響還沒有 大到引起人們重視的程度。20世紀60年代以后,產生了一些全球性的問題,人們就不能不重 視這個問題了,即科技是把“雙刃劍”,有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其中,環境污染就是 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紀60年代以后環境污染相當嚴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擴大到全球性的 環境污染,已經到了威脅人類生存的地步。這也是STS興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許多國家一 樣,日本也開展了環境教育運動,由于環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許多環境問題與科技有很密切的 關系,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環境教育為STS教育作了鋪墊。
從歷史上看,日本的環境教育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經濟開始 高速發展,與此同時,以污染為代表的公害問題也隨之發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俁病事 件、四日市廢氣事件、愛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訴訟為標志,公民反對公害 運動達到了高潮,促進了環境行政變革。在政府的規劃下,日本學校教育中以公害問 題為契機開始了最初的環境教育。70年代日本環境教育進入環境教育理念導入與實踐 的探索時期。1975年,在日本創立了全國中小學環境對策研究會,同年,以大學為中心,成立了 環境教育研究會。在1977年的小學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學大綱的修訂中,對保護人類 的生存環境、資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與環境相關的教育內容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20世紀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日趨嚴峻,日本政府和國民更加深刻 地認識到進行環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從1993年開始文部省開展了努力推進學校、家庭 、地區一體化的環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陸續編輯出版了《環境教育指導 資料》,標志著日本中小學環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經確立。同時,日本大學的環境學科數量大 大增加,基本覆蓋了人與環境關系的各個領域。
由此可見,日本在STS傳入之前,就進行了長期的、廣泛的環境教育。通過這種環境教育,日本 民眾較之以前對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與STS所提倡的重視科學 素養的教育觀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顯然,在教育層面,日本的環境教育已經為STS做好了準備 。
以上從日本吸收外來科技的文化傳統、對科學技術的理論研究、重視“科學”教育的理科教 育、因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而興起的環境教育著手,簡單分析了STS在日本傳播的有利文化 背景。但是,STS畢竟是一門新興交叉學科,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如何與具有民族特征的 日本文化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是一個需要長期探討的問題。
[1]吳永忠,孫紅巖,劉麗萍,等. 后現代主義科技觀探析[J]. 自然辯證 法研究, 1997,13(3):5-8.
[2]中清元. 日本人與日本傳統文化[M].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9: 30.
[3][HTRWM]永井享. 新日本論[M]. 三笠:三笠書房, 1937:275.[HTSS][ ZK)]
[4]湯因比,池田大作. 展望21世紀[M].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82-296.
[5][HTRWM]戶坂潤. 科學論[M]. 東京:社會思想研究會,1954:10.[HTSS ]
[6]小川正賢. STS教育概述[J]. 張明國,譯. 哈爾濱師專學報, 1996(2 ):64.
[7]張明國,殷登祥,甫玉龍,等. 中日兩國學者的STS觀[J]. 科學技術與 辯證法, 2001,18(4):72.
[8]殷登祥. 試論STS的對象、內容和意義[J]. 哲學研究, 1994(1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