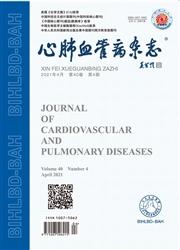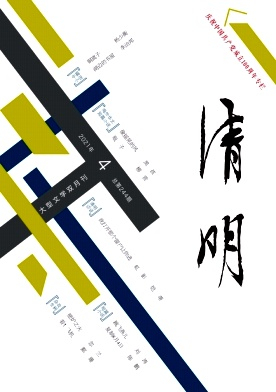三國魏晉南北朝三峽鹽業與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論
任桂園
摘 要: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三峽地區井鹽業由于戰爭與移民的推動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并促進了該地區經濟與文化的發達,從峽江流域城鎮建設與變遷的狀況即可窺知這一點。從文化視角看,由戰爭所導致的連續不斷的移民活動反而使中原、荊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該地區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其中,鹽業經濟則起著十分重要的支撐作用。
關鍵詞:戰爭;移民;鹽業經濟;三峽城鎮;文化大融合
三峽地區井鹽業,在歷經秦漢數百年穩步發展之后,及至東漢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經形成,巫縣(轄今重慶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東、建始等縣地)、朐忍(轄今重慶市云陽、開縣及萬州和湖北利川部分縣地)、臨江(轄今重慶市忠縣、梁平、墊江及萬州部分縣地)、涪陵(轄今重慶市彭水、武隆、酉陽、黔江及貴州沿河縣地)等縣井鹽業的產、運、銷均納入到國家正常運轉體系之中。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狀態下,居民居住亦相對穩定,大規模的移民現象不復出現。
但自東漢末年以后,中國社會卻進入到一個漫長的政治大分裂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內,割據政權林立,王朝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與軍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華夏大地涌動不止,地控人蜀長江黃金水道的渝東三峽地區,則又成為軍事進攻以及峽內峽外移民進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峽江地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受到猛烈地沖擊。作為該地區社會經濟主要支撐的井鹽業,在戰爭頻仍、移民進出不斷的過程中,亦受到強有力的刺激,呈現出不同于秦漢時期的面貌,并帶來了整個三峽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與發展。
自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漢獻帝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劉焉據蜀之際,全國各地的官僚、百姓紛紛避亂人蜀。史載:“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人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①南陽一帶流民勢必多取峽江水道人蜀,其中當亦不乏滯留峽江地區者。
興平元年,劉焉卒,朝廷下詔任命劉璋為監軍使者,接替其父劉焉領益州牧;而當時控制朝廷的董卓舊將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義,直接任命趙韙(原為益州帳下司馬)為征東中郎將,要他帶兵去攻打荊州。時“巴郡沈彌、婁發、甘寧(《三國志·吳志·甘寧傳》云:‘甘寧,巴郡臨江人也。’)反,擊璋不勝,走人荊州”②。甘寧等人率眾沿江而下,實際上投奔了東吳政權。而趙韙接到詔書后,卻另有圖謀。雖然立即帶兵沿江東下,但卻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陽新縣城東二十余里大江北岸舊縣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趙韙又向劉璋建議“分巴”:以墊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為巴郡,以江州(重慶)至臨江(忠縣)為永寧郡,朐忍至魚復(奉節)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趙韙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統朐忍、魚復兩縣地,大有借助是地井鹽之利以養精蓄銳、擴充軍事實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趙韙自以為一切準備就緒,遂起兵回攻成都,結果兵敗身亡。趙韙屯兵朐忍長達六年多時間,其所率軍士部屬長駐朐忍、魚復等地,可謂一種短暫性的軍事移民,而且與朐忍、魚復兩縣地井鹽之利有著密切的關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③范嘩:《后漢書·劉焉傳》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陳壽:《三國志·蜀志·劉焉傳》卷三十一(注引《英雄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據《華陽國志·巴志》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魚復蹇胤白璋,爭巴名”,劉璋又改永寧郡為巴郡,固陵郡為巴東郡,原巴郡為巴西郡,“是為三巴”。參見常璩:《華陽國志·巴志》(劉琳校注本)卷一,巴蜀書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劉備主荊州之際,將鹽泉涌流之地(今巫溪縣地)從巫縣分出,設置為北井縣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漢政權的劉備軍事集團,為獲取鹽泉之利以資軍用而對是地鹽業生產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視。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備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數萬人經峽江水道至江州(今重慶),“北由墊江水詣涪(今四川綿陽)”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諸葛亮、張飛、趙云等將兵沂流,定白帝(今重慶奉節)、江州、江陽(今四川瀘州),惟關羽留鎮荊州”③。可見,諸葛亮等也是經峽江水道入川的。劉備、諸葛亮等分別兩次率軍人川,亦勢必有不少荊州人馬留守峽江地區。此可視為一種軍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劉備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縣地置羊渠縣,又分朐忍西北部分縣地置為漢豐縣。與此同時,劉備還將朐忍、魚復、漢豐、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縣再次置為固陵郡④。劉備這一分縣置郡的舉措,除了說明蜀漢政權由于軍政上的需要而強化同為產鹽重鎮之六縣的鹽業管理外,還表明當時朐忍等地,隨著過境移民和軍事性移民的連續不斷,居民已大為增加,其中,從事鹽業生產與運輸的民眾必當相應增多,為加強對三峽地區東部的控制,故而繼分巫縣置北井縣之后將該地區縣級單位行政區劃范圍再次縮小。
蜀漢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慮、魚腹蹇機以失‘巴’名,上表白訟”,劉備為籠絡地方勢力,乃將固陵郡名恢復為巴東郡⑤。是年,劉備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七月,遂率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蜀)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東吳大將陸遜,火攻蜀軍營寨,破四十余營,大敗劉備于歸州獍亭,死者萬數⑦。其后,劉備“自猶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還巫”⑧。當此之際,“巴西郡太守閻芝,遣馬忠將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強永安駐防兵力。從蜀、吳交戰之史實,尤可見當時魚復、巫縣、秭歸一帶,由于軍事原因,過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漢為曹魏所滅,其后蜀人又大規模外遷,“并三萬家于東及
關中”⑩,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也是經渝東峽江水道東下的。是年冬,時已把持曹魏大權的司馬氏為加強對巴蜀地區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巴西、巴東”七郡⑾,時屬巴郡、涪陵郡、巴東郡的三峽地區即已劃置梁州以內。人晉以后,北方戰亂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遷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戰亂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東移,三峽地區人口呈現出從三峽地區西部向東部移民的趨勢。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權的建立,則更導致巴蜀地區人口大規模的遷徙。史載:“晉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萬戶徙荊州。李特之亂,三蜀民流并南人東下,城邑皆空,野無煙火。其人荊州者十余萬戶羈旅貧乏,鎮南江軍劉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東下荊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滯留在三峽地區東部從事經濟開發,本為流民,而實際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從事鹽業生產與轉運之人。由于戰爭的需要,隨著外來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時期,三峽地區的井鹽業生產得到了進一步開發。北魏酈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當于南朝宋齊梁之際,所著<水經注》一書即真實地記載了當時三峽地區腹心地帶北井縣、朐忍縣、南浦僑縣以及臨江縣等處井鹽生產之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按:楊守敬《三國郡縣志補正》云:“北井,《郡國志》無此縣,據《華陽國志》,縣故屬宜都,先主復置固陵時移來,疑先主領荊州時所置。”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云:“漢末,劉備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時分巫之北境為北井縣.與巫還屬巴東。”劉琳《華陽國志校注》云:“北井,《續漢志》無,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劉備改臨江郡為宜都郡時置。”楊、任、劉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測北井自巫縣分出置縣在建安十五年劉備主荊州之時,而非劉備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說。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鑒》卷三,巴蜀書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陳壽:《三國志·蜀志·蜀先主傳》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華陽國志·巴志》(劉琳校注本)卷一,巴蜀書社,1984。
⑩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劉琳校注本)卷八,巴蜀書社,1984。
⑾《資治通鑒·魏紀》(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經注·江水》載曰:
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監江縣也。《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即今之重慶市忠縣[洽+甘]井河),有鹽井菅戶,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東,會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縣界,謂之陽溪,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硤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為桶,徑五尺,修煮不絕。溪水北流注入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陽溪口②。
(江)左則湯溪水(今云陽境內湯溪河)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歷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矣③。
江水又東,巫溪水(即流經重慶市巫溪、巫山二縣于今巫山縣城東側流入長江的大寧河)注之。溪水……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水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④。
又,南朝劉宋時代盛弘之所撰《荊州圖記》則對當時巴東郡治所在地魚復縣⑤有記云:
八陣圖下東三里,有一磧,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為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⑥。
從酈道元所云北井縣所產井鹽為“建平一郡之所資”、朐忍縣湯溪水濱“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南浦僑縣西溪硤側有“鹽井三口,修煮不絕”和臨江縣“自縣北人鹽井溪,有鹽井營戶”,以及盛弘之所記魚復縣八陣圖下磧壩“昔常取鹽”等等情況來看,三峽地區腹心地帶的井鹽業并未因蜀中戰亂而衰減,相反卻因外來移民的增多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于這一點,從巫縣、北井、魚復、朐忍以及南浦僑縣等縣地城鎮的建設與變遷亦可窺知到這一點。
據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巫縣故城,城“緣山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溪深谷,南臨大江”⑦。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三峽工作隊對巫縣故城進行了調查、勘探和試掘;1997—1998年,又對巫縣故城北城墻作了進一步的發掘,通過綜合前一次的調查發掘情況后,已得出結論,巫縣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現代巫山縣舊城區巫峽鎮范圍內,并進一步推斷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當在西晉時期。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三峽工作隊還在今巫山縣大昌壩雙堰塘遺址的西南部大寧河東岸的河灘地上,發現了一處分布范圍較大的漢晉時期墓地,并發掘清理出漢晉時期磚、石室墓十余座,獲得了包括銅、陶、鐵、銀、琉璃等質地的一大批隨葬精品,表明此處在漢晉時期是一處規模較大的家族墓葬區,亦暗示了漢晉時期的雙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華生活區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晉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設置的泰昌縣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該處。而北井縣,則于漢末由劉備自巫縣分置,及至南北朝時期,其縣北鹽井所產食鹽,已為“建平一郡之所資”,由此亦可知,時北井縣治(即今巫溪縣城),由于縣北鹽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縣寧廠古鎮)鹽業生產的興旺發達,實際上已成為人口較為集中的城鎮。巫縣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處城鎮在峽江中出現并不偶然,它說明自入晉以后的一段歷史時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縣城已成為鹽業管理與販運的中心城鎮,這勢必出現相對繁榮的商業集市;而背離大江的北井縣和泰昌縣,其古城鎮雖處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當時鹽業經濟的活躍而自然集結成鎮的。這兩個古城鎮由于皆位于大寧河畔,寧河峽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見當時該地區及峽江東部一帶鹽業生產與販運的繁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②③酈道元:《水經注·江水》(陳橋驛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酈道元:《水經注·江水》(陳橋驛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據《華陽國志·巴志》卷一載:“魚復縣,郡治。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復。”案:魚復縣即今重慶市奉節縣。
⑥轉引自(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影印本,1987。
⑧鄭若葵:《重慶市巫山縣考古學文化的發現與研究》,《三峽文化研究》第三集,汕頭大學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荊州記·建平》中“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語以證“郡少農桑”之古俗①,則可從一個側面說明,西晉以后歸屬建平郡之巫縣、北井、泰昌、建始、秭歸、興山等地,從事鹽業經濟活動及由此而生發的其他商貿活動的人員之多。
又,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所云朐忍縣湯溪水濱有“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之地,即今重慶市云陽縣云安鎮所在處。由于湯溪水經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湯口注入大江,鹽運出井甚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為加強對該地鹽業生產與運銷的管理,有效的實施官營專賣,朐忍縣治即由“跨其山阪、南臨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陽新縣城東去二十余華里之舊縣坪)東遷40多華里至湯口右側(今云陽舊縣城),并逐漸建設成為一座新的縣城,且改朐忍縣名為“云安縣”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縣城西遷彭溪河口東側以前,將近1500年時間,均一直是該縣縣治所在地。由朐忍縣治東遷湯口建城,亦可得知,當時湯溪水濱及大江口岸鹽業生產和運輸業已繁盛多年,隨著外來移民的滯留,從事鹽業生產與轉運的人員也已逐漸增多。
又,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所記“南浦僑縣西溪硤側有鹽井”之地,即今重慶市萬州江南五十多里處的長灘鎮。發源于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杉樹坪的磨刀溪,流經長灘鎮,于今重慶市云陽縣江南新津口(即酈道元所說之“陽溪口”)注入長江。迄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由長灘至新津口絕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運基本可連通大江。筆者根據實地調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連續在該鎮磨刀溪兩岸生基坪、水井包、劉家螃、瓦窯壩、石龍門、官林、瓦莊屋等處挖出二十余座東漢磚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幾何形圖案的青色榫卯磚和釜、罐、缽、豆等青銅器、陶器、鐵器工具及五銖錢等文物,這很可能說明,東漢末年,隨著長灘井鹽的開發,此地已逐漸成為經濟開發較早、人口亦較為集中的地區。故劉備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縣,縣治即設于今萬州長灘鎮河東故城區。晉平吳后,省羊渠置南浦縣,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鎮。其后,蜀中大亂,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僑縣。羊渠縣及所謂南浦僑縣,其縣治均設在萬州長灘鎮河東故城區,至今河東故城區西側磨刀溪兩岸山麓水畔仍有多處古鹽井遺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為集中。筆者認為,長灘古鎮能成為當時渝東萬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區并兩次置為縣治③,不僅僅是由于水上交通較為方便,更關鍵的原因卻在于此處溪硤側有鹽井而“修煮不絕”!在戰亂頻繁的年代里,長灘古鎮正因為有“修煮不絕”的井鹽之利,方才成為不少移民逃亡遷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處城鎮建設亦勢必相應地得到發展,由上述該地墓葬出土的情況即可說明這一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祝穆:《方輿勝覽·歸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影印本,1987。案:據《晉書·地理志》卷十五載: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吳、晉各有之建平郡為同一建平郡,統“巫、北井、泰昌、信陵、興山、建始、秭歸、沙渠”八縣,計13200戶。時巴東縣尚未自巫縣分置。
②《隋書·地理志》卷二十九“巴東郡云安縣”下注云:“舊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陽”。
③楊守敬認為:“蜀先主置羊渠縣,晉省羊渠,置南浦,屬巴東郡,宋、齊、梁因,即今萬縣治,在江北。南浦僑縣在江南,未詳何時置。”其門人熊會貞疏“南集渠”及“陽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萬縣東南人江。” (見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三十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筆者認為,楊、熊二人所說,與筆者實地考察所知和萬縣置縣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廢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僑縣,又分朐忍縣大江北岸西北部分縣地,共置為魚泉縣,并徙治于江北苧溪河(即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說之“北集渠”)口左側,即今萬州老城區環城路南門口一帶,此為今萬州建城并置為縣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間(公元566--571年),魚泉縣又改名為安鄉縣,旋改稱萬川縣,后又置為萬川郡。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僑縣專名又改縣名為“南浦縣”。自唐以后,或為州治,或設為縣治、市治。方多帶有“萬”字頭。劉琳《華陽國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萬縣”,又用括號注為“《蜀鑒》謂蓋在萬縣西南五十里羊飛山下,《紀要》謂即今萬縣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鑒》說羊渠故城“在萬縣西南五十里羊飛山下”,與筆者所考察認定的長灘鎮河東故城區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慶市萬州城區到長灘鎮計有58華里車程,但需說明的是,長灘不在萬州西南而在其東南。引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羊渠縣治即今萬縣市治(今萬州老城區)則誤矣。又,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龍駒壩”。但龍駒壩尚在長灘以南60里。
劉備又分朐忍西北部分縣地置為漢豐縣。漢豐縣故城即今重慶開縣治,井鹽產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華里的溫湯峽谷中。溫湯峽谷地處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屬開縣溫泉鎮),此即酈道元所說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縣,又西人峽,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峽,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謂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陽縣新縣城西頭)①。經實地考察得知,溫湯峽谷全長不足4華里,古鹽井即分布在峽谷東西兩岸,至今亦有遺址可尋。當地有民間傳說云:“古時一獵者見白羊于河邊舔食鹽泉,嘗而味咸,遂刨砂為坑,取其鹽鹵。”②這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時朐忍縣東湯溪河畔早在西漢初年即已開始鑿井取鹵煮鹽,朐忍縣亦因此而置有鹽官,而劉備卻將同樣擁有井鹽產地的朐忍縣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區又劃置為漢豐縣,很明顯,這一舉措亦完全是出于對該地鹽業生產與運銷進行強化管理的實際需要。正由于該地鹽業的興旺與發展,不但所建漢豐縣治成為了該地人口集中的城鎮,而且在檀井溪與清水交匯的地方(即緊靠溫湯峽谷之處)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漸集結成鎮。
至于巴東郡郡治所在之魚復縣,由《荊州圖記》所記“昔常取鹽”一語可知,該地井鹽業的開發并非始于南北朝時期。由于其地夔門天險“當全蜀之口、控荊楚上游”,故自遠古以來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地位。秦漢之際,已置為魚復縣。及至東漢末年置為巴東郡治以后,隨著軍事性移民的增多,軍用需求量的增大,該處井鹽業已逐步得到了開發。而巴東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為了三峽地區腹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對集中,其城鎮規模亦相應得以擴大。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里許,江山迂闊,人峽所無,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說明,劉備兵敗退還魚復并改魚復縣曰“永安”之際,白帝故城業已擴展到其西面平曠地帶(即今奉節縣舊城區,現已撤遷)了。
峽江水路,自遠古以來即是四川盆地連通峽外廣大地區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隨著戰爭的需要,造船業已大為發展,及至三國以后,方舟可直下荊吳,完全可為食鹽運銷峽外提供方便的水運條件。北井、大昌、朐忍、漢豐、羊渠、臨江等縣井鹽產地雖然地處群山之中,但由于與大江相去不遠,且有支流相與連通,這實際上為鹽運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縣、魚復、朐忍、臨江等縣治所在地更是地處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著本地鹽運出境之咽喉,隨著鹽業的發展,/這些地方勢必成為人口集中、經濟發達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城鎮。如果說,三峽井鹽之利與峽江水路,在先秦時期是引發戰爭與移民迭起的緣由,那么到了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三峽地區的井鹽業和水道運輸卻由于戰爭與移民的推動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又反過來促進了該地區經濟與文化的發達,其中,鹽業經濟則起著十分重要的支撐作用。
三國時期,魏、蜀、吳鼎立相爭,實際上既是中原、荊楚、巴蜀三大經濟區的較量,也是中原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盡管秦漢時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長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觀念的存在,故自東漢末年以后,又漸次顯現出各自的地域特色來。而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峽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險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為各個王朝統治者視為國之大寶的鹽業經濟,它不但成為了歷代王朝用兵過境之通道,而且也為迫于戰亂而逃亡遷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塊較為理想的避亂謀生的滯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戰爭而引發的這種涌動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統治集團軍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該地區的鹽業經濟能長期活躍不息,并能得到進一步發展。從文化視角看,由戰爭所導致的連續不斷的移民活動反倒使中原、荊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該地區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質直、素樸、神秘而詭譎的巴文化不僅與秀美、絢麗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謹嚴、清奇、靈巧風格的楚文化緊緊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氣勢磅礴、豐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進一步滲入其中,這既充分地層示出三峽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質,同時亦使三峽文化的內涵變得更為豐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③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卷三十三(陳橋驛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參見拙文:《渝東古鹽井探訪錄》,載《今日重慶》,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warfare and immigrant, salt industry in the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was farther developed and it in reverse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the towns beside the river, we can find i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view, uninterrupted migration resulting in warfare made three great cultures of Zhongyuan, Jinchu and Bashu impacting and mixing each other. Among them, salt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