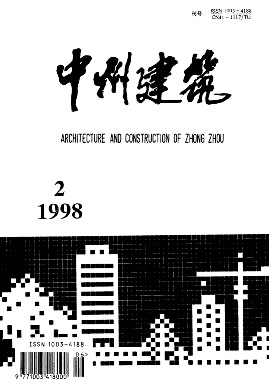關于《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民間潛在意識遞嬗的探討
葉鑄漩
【內容提要】 《三國志通俗演義》以其通俗性承載了民間潛在意識,同時又以其成書過程“歷史積累性”完成了民間潛在意識的遞嬗。由隋唐至元末明初,在民間三國故事的演變發展過程中,其所承載的民間潛在意識大致經歷了隋唐時代的單純心理娛樂性的需求,宋代的善惡意識,元代前中期的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幾個階段,在民間潛在意識系統中“以繼承為主體的遞進關系”構架上通過揚棄的方式完成了以對“‘仁政’、‘德義’回歸”為實質內容的元末明初民間潛在意識的建構。 【關鍵詞】 《三國志通俗演義》 民間潛在意識 遞嬗
The discussion about transmission of civil awareness vast potential in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bstract : The popularity of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ears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Meanwhile, the book also complet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with its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The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it bears , generally experiences the demand of psychological happines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onsciousness of good and evil in Song Dynasty, the concerns about the state of popular live in the early and mid of Yuan Dynasty,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Kingdoms Story”. This awareness comple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about the return to “Good Policy” and “Moral” by the framework of adopt-ting the previous in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System..
Key words : "Popula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ivil awareness of vast potential Transmission
《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在長期歷史積累中形成的通俗長篇小說。就其通俗性來說,它與民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抑或說它是民間土壤的直接產物。其長期歷史積累的形成過程又在另一層面指出了,《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是在長期的民間三國故事的積累過程中逐步演變并最終于元末明初這一歷史時期形成,而伴隨這一成書過程的則是民間三國故事中所蘊涵的深刻的民間潛在意識。這一意識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過程中以演變中的三國故事為載體實現著其自身的遞嬗。所以,本文旨在借助《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書,通過對其成書過程中民間潛在意識的發展流變的探討,來考查元末明初的民間潛在意識的形成過程。
(一) 概念的界定
這里所需要界定的概念是民間潛在意識。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市井文化形成之后,為了在古代文學思想的研究視閾內更好地把握影響文學發展的潛在的社會因素,故我將影響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潛在社會因素分為民間潛在意識與文人士大夫意識兩個系統。文人士大夫意識以其內容和形式的“雅”的特點成就了其“精英性”,這種“精英性”決定了此種意識只能存在于知識分子之間,不可能下落到民間。而民間潛在意識則是以“俗”為特點,它呈現出迥異于文人士大夫意識的狀態。所謂“民間潛在意識”是指潛伏并廣泛流行于民間的意識形態,是民間“集體無意識”的表現形式,它于主流意識形態是相對獨立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其相對獨立性使之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視閾中自成一個系統。但由于中國古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文人士大夫化,促使民間潛在意識不得不與文人士大夫意識構成影響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社會因素的兩個不可忽視的系統。
但無論是民間潛在意識還是文人士大夫意識都是通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在中國古代社會,文人士大夫意識多是以詩文辭賦這些形式表現出來的,故這些文本形式也就自然的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而民間潛在意識與文人士大夫意識的相對對立則使民間潛在意識失去了主流的文本表現形式,只能力辟蹊徑。充當民間潛在意識載體的則是被文人士大夫們斥為小道的小說和民間其他藝術形式。民間潛在意識的需求使這些藝術表現形式具有了“適民性”,這一“適民性”在其后就發展為直接認同于市民的思想行為和審美趣味,滿足聽眾的娛樂要求。①而另一方面,較之其他民間藝術形式,小說由于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及其“史余”的特點,又使小說在市民文化中具有了雙重特點。這促使小說在創作過程中不得不將“適民性”與“史余”合而為一,并使史余的中心由歷史的補充轉向到對當下,現實的關注。而這種轉向的動力則是“民間潛在意識”,也正是民間潛在意識才使小說在現實社會中得以生存和發展下去。由于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在現實語境中特殊的狀況,可以認為,民間潛在意識是更多的蘊涵在小說之中的,抑或說小說是以表現民間潛在意識為旨歸的,故而通過小說也便可以窺見一個時代的民間潛在意識,同時,小說的流變也伴隨著民間潛在意識的流變。因此,可以認為小說是鏡窺民間潛在意識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窗口。
(二)《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民間潛在意識的遞嬗
小說興于唐宋,而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傳達民間意識功用的小說則是形成于元末明初,具體的說則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②《三國志通俗演義》由于經歷了歷史積累而最終成書,所以,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它是最先以長篇文本成書過程表現民間潛在意識流變的小說,對于探討元末明初民間潛在意識具有典型的意義。下面就以《三國志通俗演義》為個案來考查元末明初的民間潛在意識的遞嬗過程。
三國故事在民間的流行,據文字記載,最早可以上溯到隋煬帝時代的雜戲表演,其后又發展到晚唐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③以此可見,這一時期對于民間來說,三國故事多只是選取三國歷史中驚險,滑稽的內容加以演繹以滿足民間娛樂的要求,而大眾所需求的則也只是感官上的愉快。三國故事對于他們來說則是一種對于感覺的補償,一種純娛樂目的的心理需求。這一時期民間潛在意識并沒有特殊的指向,三國故事僅僅是這一僅僅是人們娛樂的材料而已。到了北宋,三國故事逐漸被賦予了一些明確的指向。蘇軾《志林》載:“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④由此可以看出,三國故事在北宋的民間已經形成了“尊劉反曹”的思想傾向,也就是說,北宋的民間潛在意識在三國故事純粹的心理娛樂需求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民間自覺的“善惡意識”,這種“善惡意識”是統攝在“善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的理念之下的。這也正是在宋代心性之學與理學合流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普遍的民間意識。而自六朝以來,儒釋道三教的合流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主導趨勢,到宋代這種文化發展已進入完全成熟的階段。⑤這種思想上的狀態則進一步加強了宋代民間潛在意識的道德傾向,并且將隋唐時代單純的心里娛樂需求轉化為內心的共鳴。在民間則表現為以心會心,以心體物的風尚,這也是北宋時代“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的原因。
而到了金元時代,三國故事則被搬上了戲劇舞臺。這一時期出現的三國故事戲也更多的繼承了宋代出現的“尊劉反曹”的民間潛在意識,以及唐宋以來一直有的娛樂性。但是,金元時代特別是元代社會的現狀使民間潛在意識的載體呈現出濃厚的歷史感和社會感,而對于三國故事來說,則更多地將民間潛在意識中的理想貫注其中。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代雜劇四大家之一的關漢卿的雜劇《單刀會》:
[第三折·慶東原]有意說孫劉,你休目下翻成吳越。
[第四折·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別,我覷這單刀會似賽村社。
[第四折·駐馬聽]水涌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傳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帶云)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來流不盡的英雄血!
從以上所引《單刀會》的片斷來看,關漢卿所極力塑造的關羽形象是一個英勇無畏,關心社會穩定,人民生死的英雄形象。而元代中葉出現的《三國志平話》中的“關公單刀會”也表現了類似的內容:
關公:“單刀會上必有機見,吾豈懼哉!”至日,關公輕弓拈箭善馬熟人攜劍五十余人,南赴魯肅寨,吳將見關公衣甲全無,腰懸單刀一口。關公視魯肅從者三千,軍有衣甲,眾官皆掛護心鏡。君侯自思:賊將何意?茶飯進酒,令軍奏樂承應。其笛聲不響三次。大夫高叫言:“宮商角徵羽!”又言羽不鳴,一連三次,關公大怒。捽住魯肅。關公言曰:“賊將無事作宴,名曰單刀會,令軍人奏樂不鳴,爾言羽不鳴,今日交鏡先破。”魯肅伏地言道“不敢”。關公免其性命,上馬歸荊州。⑥
以上二者都是元代三國故事的代表,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于關公的極力塑造和推崇。關漢卿的雜劇《單刀會》更多的是從社會意義入手來塑造關羽的形象;而《三國志平話》中的“關公單刀會”更多的從歷史意義入手來塑造關羽的形象可以認為關羽的形象是元代社會民間潛在意識中“理想”的集合,同時,也由于這一“理想”集合形象的確定而使關羽在民間更具有深沉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從關羽所代表的民間潛在意識中的理想來看,元代社會民間潛在意識除了宋代以來“善惡意識”及隋唐以來的心理娛樂的需求之外,這一時期又加入了對于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英雄的呼喚。這其中的意義就在于自覺要求改善生存境遇的意識的覺醒。造成元代這種民間潛在意識的原因,筆者認為,是元代社會的現實狀況。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他們以強大的鐵騎踏破了中原原有的文化形態,而帶來的卻是草原游牧民族粗糙而蒙昧的文化形態。在這種文化形態中,中國歷史上儒家一元主體的文化形態隨之解體,各種意識形態得以并存,形成了文化多元的局面。思想禁錮也較之前代有所放松。同時,元代統治者政治上的一系列的措施又加速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社會由此而發生了極大混亂,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間因此而與上層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對立。為了獲取最后一塊生存空間,民間不得不在這種現實處境中抗爭,而這種抗爭在民間潛在意識中則隱晦地以“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和“對能夠拯世救民的英雄的呼喚”的形式表現出來。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民間潛在意識已經與主流的文人士大夫意識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對峙。另外一點,從元代當下的語境來看,文統與道統的分離態勢也促使了元代社會民間潛在意識的形成。“元中期學者們探討文章的本源,大多數人認為文章并不是源于人世的道,而是源于天地自‘氣’。至元末,更有人強調文章就是文章,文章就是或僅僅是要表達作者的意思,文章是要‘明理’,但不是明圣人之‘理’,而是‘論實理’。”“這‘實理’無疑是關注當下的,現實的,實踐的事理,物理,常理。”⑦在整個元代社會文道分離和注重現實當下的風氣影響之下,元代民間潛在意識也進一步由宋代的“善惡意識”轉向了“對自身生存境遇的關注”。
元代社會的“文道分離和注重現實當下”的風氣自元初形成愈演愈烈,到了元末發展到了頂峰。而元末社會的動亂,同時也使民間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程度達到了頂峰。“文道分離和注重現實當下”的社會風氣與民間“對自身生存狀態關注的程度”,這兩個發展極端促使元末民間潛在意識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添加了更為深刻的內涵。而此時的三國故事也在經過隋唐時的說唱,宋代的說話,金元的戲劇和平話之后愈加豐滿,并最終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章回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同時,這一時期的民間潛在意識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結合也空前緊密,甚至可以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正是此時期民間潛在意識的圖解。這里,仍然以“單刀會”這一材料為例來考查這一時期的民間潛在意識。《三國志通俗演義》(李卓吾先生批評本)第六十六回“關云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辰時后,見江面上一只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展,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云長青巾綠袍,坐于船上,傍邊周倉捧著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挎腰刀一口。魯肅驚疑,接入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云長談笑自若。……肅云:“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于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念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托足,以圖后功。而皇叔愆德隳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為天下所恥笑。唯君侯察之。”云長曰:“此吾兄之事,非某所宜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云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
以上這一段較前面元代關漢卿雜劇《單刀會》,元代中葉的《三國志平話》中“關公單刀會”來說,雖然所述內容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其所反映出的民間潛在意識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元末明初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單刀會”中關羽雖仍是英勇無畏的英雄形象,但卻已不是作者所要極力突出的對象了,而真正敘述和張揚的對象卻是關羽拒還荊州所表現出來的“義”,以及周倉之言“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中的“德”。這里,元代前中期民間呼喚英雄的潛在意識已經被極大得消解了,并且逐漸由此轉向一個更深層次的命題——“仁政”。在這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仁政意識”,“德義精神”是超越了一切而成為貫穿整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主導思想。而這也正是元末明初這段動蕩社會的民間潛在意識的核心。這一民間潛在意識仍然是出于民間對自身生存境遇的關注,從而作出的無奈的反應。同時,這種民間潛在意識也是由元代前中期的“個體自我拯救”向元末明初的“群體自我拯救”轉化的結果,這深刻地表明了社會環境和生存境遇的進一步的惡化。這一時期民間潛在意識中出現的崇德尚義以及“仁政”的思想就其在《三國志通俗演義》這一文本中的表現來但則是向著“文以明道”的方向回歸。這里所言之“道”雖然與儒家所倡導之“道”相合,但是其實質卻仍然是民間潛在意識。而這一時期的民間潛在意識與儒家傳統之道的相互契合,則使民間潛在意識在社會層面成為主導意識。此時的民間潛在意識已超越了其上限,成為與主流意識并駕齊驅的的社會意識,也由此而緩解了與文人士大夫意識之間的對峙態勢。但筆者認為,元末明初出現的這種以“仁政”,“德義”為核心的民間潛在意識是特殊社會環境的產物。它與主流意識的契合是在這種社會語境下對于儒家“君子人格“的呼喚和重構,這是社會混亂狀態下,社會思想的常態,但就民間潛在意識自身的發展來說,元末明初的民間潛在意識雖是自然而成,但卻脫離了民間潛在意識的正常狀態。
(三)《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各時期民間潛在意識之間的關系
由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所蘊涵的民間潛在意識是經過了隋唐單純心理娛樂需求,宋代“善惡意識”,元代前中期“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以及元末明初“崇德尚義和仁政”的發展歷程。這些民間潛在意識是相對獨立的。但就民間潛在意識這一系統來說,則又是相互影響,相互關系的。在民間潛在意識這一系統中各個時期的民間潛在意識是在以繼承為主體的遞進關系中發展流變的。這具體表現為前一時期民間潛在意識自然地成為后一時期民間的“集體無意識”,同時,后一時期的又以特殊的社會歷史狀況而形成的新的意識不斷豐富和完善這來自前一時期的民間潛在意識。《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所蘊涵的民間潛在意識正是在民間潛在意識這一系統中的“以繼承為主體的遞進關系”架構內發展的。從隋唐到宋代,心理娛樂需求是一直貫穿始終的,是一直作為三國故事“適眾性”的民間“集體無意識”存在下來的。宋代由于心性之學的流行與儒釋道三家的通融,而使隋唐心理娛樂需求得以補充;同樣,由宋代入元代也是在繼承了隋唐,兩宋的民間潛在意識之后,由于元代前中期社會歷史狀況的突變而補充進了民間對自身生存狀態的的關注這一內容。是以,可以認為,元末明初民間潛在意識是歷史上民間潛在意識的集合,并且,這一時期民間的潛在意識也同樣地被置于民間潛在意識系統中“以繼承為主體的遞進關系”架構內運作,以成就后世的民間潛在意識。
(四)《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民間潛在意識遞嬗的方式
《三國志通俗演義》所體現出的民間潛在意識系統中“以繼承為主體的遞進關系”架構,直接決定了民間潛在意識遞嬗的方式應為“揚棄”,即在繼承的基礎上的補充。這一方式不僅是以繼承為主體的遞進關系的內涵,同時,也是民間潛在意識發展的唯一手段。這一方式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方式是基本一致的。但民間潛在意識遞嬗的方式卻于《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方式又有所不同。首先,民間潛在意識的遞嬗方式并非人工的自覺去添,而是社會歷史的自然選擇。具體來說,由隋唐單純的滿足心理娛樂需求到宋代“善惡意識”,其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繼承隋唐單純滿足心理娛樂需求基礎上又根據宋代的時代需求加以補充;從宋代“善惡意識”到元代前中期“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以及從元代前中期“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到元末明初的“崇德尚義與仁政”,大率都是如此。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方式則是有意識的對歷代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進行搜集和整合,是人工的創作選擇。但這種人工的創作選擇卻又是為民間潛在意識的傳達服務的。可以說《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方式也是隨著民間潛在意識的揚棄而揚棄的。
(五)綜述
以上通過對《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所蘊涵的民間潛在意識的探討揭示了民間潛在意識的遞嬗過程,民間潛在意識系統中“以繼承為主體的遞進關系”架構,以及民間潛在意識的遞嬗方式。由以上論述,可以認定,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最終成書的元末明初,民間潛在意識是通過《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書表現出來的。同時,這一時期的民間潛在意識也是在經歷了隋唐單純的心理娛樂需求,宋代“善惡意識”,及元代前中期“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并以揚棄的方式形成的。
參考書目及文獻
[1] 張毅 《中國文學思想通史?宋代文學思想史》[M]第六章“南宋后期的文學思想” 中華書局 1995年4月第一版 , P304
[2][3][4]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四卷》[M]第七編?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第一版 ,P25
[5]張毅 《中國文學思想通史?宋代文學思想史》[M]結束語“宋代文學思想發展中的幾個理論問題” 中華書局 1995年4月第一版 ,P334
[6]曾良《明清小說研究》[M]“史實與虛構——兩種‘單刀會’的比較”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P63
[7]查洪德老師《中華文史新刊?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M]第一章“文道離合與元代文學思潮變遷”中華書局 2005年8月北京第1版,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