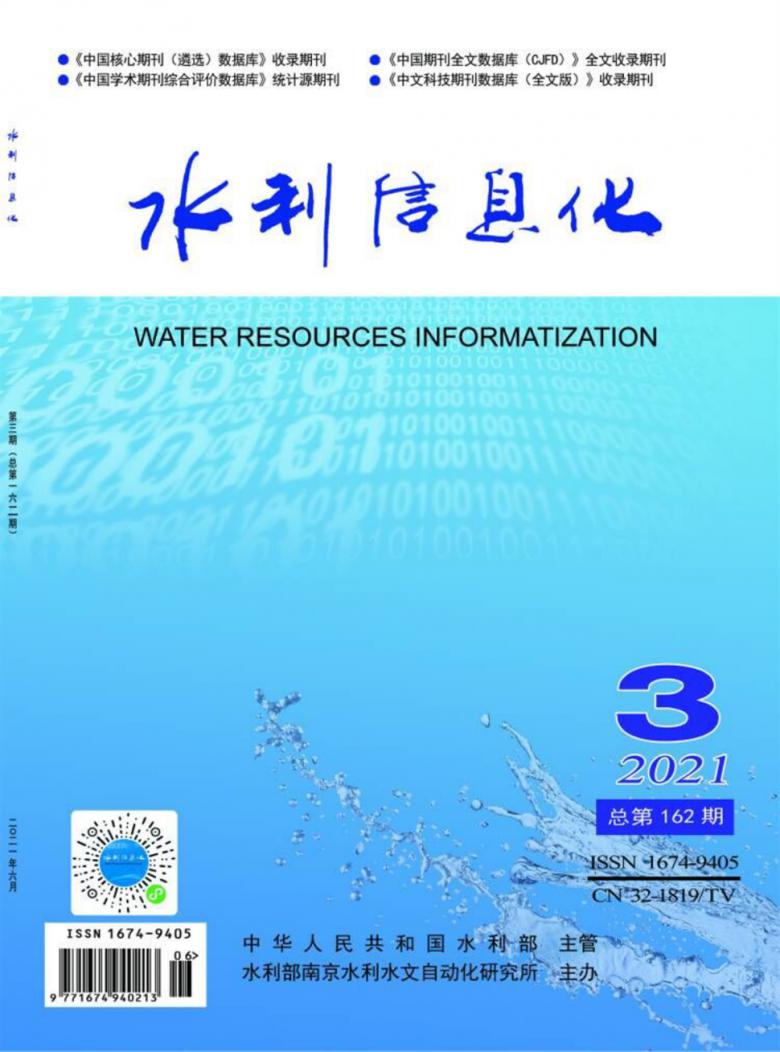明代贛南的風水、科舉與鄉村社會“士紳化”
黃志繁
[摘要]自明中期起,贛南社會掀起一股造風水、興科舉的熱潮。在這股熱潮中,地方官的倡導、地方紳士的響應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贛南社會出現這股熱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來中國傳統社會追求“士紳化”的心態。把風水和科舉聯系起來,雖然是中國人祈福求祥心態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單純是風水術上的一個發展問題,更不是贛派風水發源地贛南獨特的社會現象,而是宋以來南中國整體社會變遷的一個過程和結果。風水這類看似游離于官方意識形態的民俗觀念,其實蘊藏著非常復雜的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應放置于整體社會變遷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The Movement of Integrating Geomancy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 ofSouthern Jiangxi and Gentrifica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Ming Dynasty;Southern Jiangxi;geomancy;imperial examination;gentrification
Abstraet:A fashion of gentrification of local people initiated by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ry emerged in Southern Jiangxi region in the mid-Ming dynasty which indicated the gentrification of rural society of Southern Jiangxi, as more and more local people changed geomancy in order to make progress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 Though it is the natural reflection of Chinese ideology of seeking happiness and luck that integrated geomancy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was not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omantic magic arts rather than as a result of the special folk custom of Southern Jiangxi. It i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whole social change of southern China from Song dynasty.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ersonal in the folk customs like geomancy, which seemed to have no relation with official ideology. So we should research it on the background of whole social change.
自郭璞提出“風水”概念以來,風水就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觀念之一。除了從理論和技術上對風水進行闡述的大量著作以外,迄今為止,關于風水與社會生活的研究,大多從民俗層面論述風水與喪葬、居住環境、改變命運等方面的關系,尚未從區域社會變遷角度進行關注。①實際上,風水術的流行與傳播,和具體區域社會變遷聯系甚緊,并隨時代變遷而注入新的內涵。贛南是贛派風水的發源地,民間講求風水有較長的歷史,風水之說有相當的影響。特別是明清時期,贛派風水術不僅和贛南人民生活密切相關,而且還流布天下,影響及至皇陵的構造。②就明代贛南社會而言,比較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風水之說和科舉興旺聯系在一起,興起一股造風水以興科舉的熱潮。本文擬以明代贛南為中心,結合區域社會變遷歷史,對這一熱潮進行闡述,以期揭示風水與區域社會變遷之關系,并藉此洞察明代社會變遷的一個側面與時人心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關于風水的研究文章很多,就筆者所及,從民俗角度研究風水的主要成果有:張邦煒《兩宋時期的喪葬陋俗》,《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萬陸《楊益的風水文化觀及其實踐》,《江西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廖鴻《風水大著于世的六朝喪葬習俗》,《中國社會工作》1998年第6期;雷玉華《唐宋喪期考——兼論風水術對唐宋時期喪葬習俗的影響》,《四川文物》1994年第3期;關傳友《中國古代風水林探析》,《農業考古》2002年第3期;曾建平《潮汕民居的美學意義——以陳慈夤橋宅個案研究為例》,《汕頭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黃艷燕《風水與古代小說中的改運主題》,《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李黛嵐、柳云《客家風水民俗芻議》,《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1期。
② 韓振飛、姚蓮紅《淺談楊筠松及贛派風水術》,見《贛文化研究(總第4期)》,南昌大學《贛文化研究》編輯委員會1997年編;林忠禮、羅勇《客家與風水術》,《贛南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
一 引言:王陽明倡學贛州與贛南科舉的相對落后
正德十二年(1517),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就任南贛巡撫。王陽明在南贛巡撫任上,不僅在軍事上鎮壓地方盜賊,安撫民眾,確立官方社會秩序,而且還在南贛巡撫治所——贛州大力宣揚其“心學”,一時之間,贛州云集了大量的往來學者和王門信徒。由于學者眾多,王陽明專門建濂溪書院以住學者,史稱:“(正德十三年)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1](卷三三《王陽明年譜》)
贛州城中學者云集的盛況促進了贛南的求學之風,“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眾,而講學不廢。……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為善良,而問學君子亦多矣”[1](卷三八《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的贛南籍弟子中,何廷仁、黃弘綱名滿天下。羅洪先記載說:“嘉靖戊子余計偕北上求友,四方咸日:君不聞,陽明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浙有錢王’。蓋指雩都有何善山秦、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渚山寬、王龍溪畿也。”[2](卷八《明故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君墓志銘》)之后,又有一批學者以其為師,傳其學術。例如雩都在何、黃二人去世后,建有濂溪、陽明、善山三先生祠并有祠田,“皆鄉大夫袁君沂、周君文、胡君夷簡,予先族祖喬、崇等營度之。諸君子復為之期,率諸后進詣新建、善山兩祠,以其講之何、黃諸公者,討論而服習之”[3](卷上《濂溪、陽明、善山三先生祠田記》)。雖然后來吉安等地的江右王學遠比贛南發達,但王陽明在贛南宣揚“心學”的歷史以及贛南江右王門這一群體的出現,使贛南成了士大夫筆下的王文成公“息馬論道過化最久之地”[4](卷一一《祠廟》)。
然而,與“姚江之學,學在江右”的說法形成對比的是,明代贛南科舉并不興旺,人才寥寥。①正如嘉靖《南安府志》所言,“南、贛二府每大比于鄉,類不及吉、饒、臨、信得士之眾,以為下邑荒陋,則未免寡昧”[5](卷一六《學校》)。萬歷年間時人楊守勤對贛州的科舉現狀表示疑惑:“自王文成昭揭圣修,倡學茲土,至今士品為他邑冠。乃舉制科者,往往遜他邑,青衿詫語:祀弗專與?文弗耀與?抑赭堊不滿于景純之目也?”[4](卷二四《學校》)
事實上,如何采取措施,振興贛州、南安二府的科舉,一直是明代贛南地方官和紳士在努力解決的問題。早在王陽明就任南贛巡撫之前,贛南就已有試圖通過改造風水以興科舉的活動,影響所及,幾乎所有的府州縣學都進行過改遷與重建,大量風水塔也由官方和民間合力興建。
二府州縣學的改建與風水塔的大量出現
以贛州府學和縣學為例(贛州府城所在地為贛縣),就先后在成化四年(1468)、嘉靖四十一年(1562)、萬歷三十二年(1604)進行過三次搬遷,而且每次搬遷的理由都是學校的風水不利于科舉。
關于成化四年贛縣府學(包括縣學)的搬遷,明人彭時有如下記述:
贛于江西為巨府。其城據章貢二水合流之處,山川雄秀,風氣固密,形勢概可知矣;然郡、縣二學,自宋以來俱在城內之東南,面壁城垣,未足以當其勝。入國朝百年之久,教養具備,而科目乏人。或者以為地有不利,而有司憚難,莫之能改。成化丙戌,山東曹侯凱來知府事,厭其卑陋,既以改遷為己任,乃相其宜,得學之西北偏景德寺,其地隆高亢爽,后接郁孤臺,前對崆峒山,山勢聳拔如卓筆狀。喜曰:建學育才,莫宜于此。即召寺僧以府學易之,并縣學遷焉。……
二學成,規模宏壯觀麗,有以出塵囂而挹清曠,加于其舊遠甚。始遷之歲,諸生名鄉薦者二人,明年進士及第者一人,邦人父老咸喜。……乃寓書翰林編修董越俾征予文,越即及第者也。[4](卷二三《學校》)
按彭時的說法,贛州“科目乏人”的原因是“或者以為地有不利”,而知府曹凱把學校遷到一所佛寺,在當時并非輕易之事。上文中提及的進士及第的郡人董越就說:“學本景德寺基,談者皆以其當崆峒之勝,顧或惑于利害,無敢易之。曹侯為贛之三年,有言及者,遂慨然日,作養人材,維持風化,于學當先。浮屠但有地以容足矣,彼豈得專是勝邪?”[6](志一一《藝文》)曹凱之所以堅持把學校搬遷到景德寺的重要理由乃是景德寺地理上的“當崆峒之勝”,“山勢聳拔如卓筆狀”。就在贛州府縣學搬到景德寺的當年,贛州“名鄉薦者二人”,明年,董越進士及第,后官至兵部尚書,遷學的效果似乎非常明顯。
有意思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南贛巡撫陸穩又把贛州府縣學從景德寺遷出,陸穩把贛州府縣學從景德寺搬遷走的理由也是“堪輿家弗之善,思復其舊”[7](卷二○《紀言志二》)。萬歷三十二年(1604),南贛巡撫李汝華等地方官,因為贛州“乃舉制科者,往往遜他邑”,而“相與質之形家,僉謂景德舊址,豐隆宏敞,延袤正方,北亙郁孤,南瞰崆峒,鳳池匪遙,翠玉可枕,如彭學士所稱洵吉壤”。[4](卷二四《學校》)結果,嘉靖年間“堪輿家弗之善”的景德寺地址又成了“吉壤”,李汝華等又把贛縣縣學遷到景德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有學者認為,江右王學的發達沒有推動江西的科舉,甚至可能對科舉還有一種反作用。參考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后期江西教育的發展》第360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但筆者目前還沒有發現有確實的材料證明此種說法。
在明代贛南,類似贛州府縣學這樣多次搬遷儒學的例子并不少見。筆者根據地方志有關修建儒學的記載,制成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贛南大部分縣都改建了儒學,各縣改建的理由,基本上都解釋為風水不利,導致科目乏人,而雩都縣儒學也和贛縣一樣,經歷了三次搬遷。
明代贛南還出現了興建文峰塔的風潮,目的也是為了振興當地科舉。以瑞金縣為例,該縣在明末就建了二座文峰塔,動員了全縣許多紳士耆老。康熙《瑞金縣志》記其事曰:
龍珠塔,縣西南五里。本縣峰巒聳秀,江水環帶,亦稱佳麗。惟是西南少秀拔峰。故議以西南赤硃嶺為縣水口,位屬辛,宜建天乙貴人峰。以南面方巾嶺,位屬巽,宜建云霄狀元筆。久議未就。萬歷壬寅冬月,知縣堵奎臨酌合邑議,申詳道府。首先倡俸,更募邑人,會同邑紳鐘譔、賴聘、朱善卿、鐘彥、許宗謨、楊永皋,舉人楊以杰,監生劉希善、劉選、楊正學,庠生謝元璇、李汶、許繼廉、楊以任等總督其事,慎選耆老謝仲誨、楊可儷……(下列23人名字,引者注)分理其事……扁曰:龍珠塔。庶幾風氣秀發,人文振起。[8](卷三《建設·臺塔》)
興建龍珠塔完全是由于風水上的理由,建塔的過程驚動了從知縣到舉人、監生、秀才、耆老等地方上的各色人等。隨后,瑞金又興建了“與龍珠寺塔相對”的“巽塔”,名為“文興塔”。瑞邑人士對二塔寄予厚望:“巽、辛二塔對峙,屹然凌霄,后日必有人文振起,秀甲寰區者矣。”[8](卷三《建設·臺塔》)
興建文峰塔的并非瑞金一地,現略引幾段相關史料如下:
(大庾)東山望旭,西華倚空,萬古巨瞻,一方雄鎮,顧以巽峰少銳,堪輿家致有異言,必須文筆增巍,經學士取為吉兆……建石塔于龍華院之東。[9](卷三二《重建文峰塔疏》)
(上猶縣)盧公塔,在縣東五里,本府同知盧洪夏……見猶邑科目寥寥,由水口文峰低小,乃建七層浮屠于巽山之巔,自是人文頓盛,邑人呼日:盧公塔。[10](卷三《寺觀》)
據文博專家介紹,贛南明清時有古塔40余座,沒有一例屬于佛教意義上的塔,全部為文峰塔,[11]從中亦可見贛南當時改造風水以興科舉的熱潮。
三 紳士的參與和民眾的響應
在明代贛南出現的改造風水以興科舉的活動中,地方官的倡導固然十分重要,但我們可以看到,地方紳士也積極地參與其中,他們或親自倡導,或捐款捐物,或董事監工,成為保證活動進行的重要力量。特別是興建學校和風水塔都需要不菲的經費,僅靠官府的“公帑”是遠遠不夠的,地方紳士和民眾在經費上的捐助亦十分關鍵。
從上文的《明代贛南府縣學修建表》可以看出,大部分府縣學修建的經費,除了官府開支外,還有來自地方士大夫、父老等民眾捐助的部分。當然,在美其名曰“義助”的背后,應該也有攤派的可能。不過,科舉的興盛直接關系到本地民眾的升遷和地方的政治格局,地方士大夫的傾力支持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說,許多府學與縣學的建立經費尚可來自于“公帑”的話,眾多文峰塔的建立經費則基本來自紳士和耆老等地方士人的捐助。
在一些宗族聚集之地,則可能會以宗族為單位建設文峰塔,其建設經費自然來自于宗族。請看如下事例:
(雩都縣蜚英塔)塔當先師廟巽址,是為文明之統,命曰:蜚英。……予問費從所出入,父老謝文魁等曰:吾儕世居茲土,倘賴天靈,自今以迨千百世,諸宗子姓,蔚為國華,則當各以其宗助。[3](卷上《蜚英塔記》)吾鄉名營前,里日:村頭,陳、蔡二姓卜居斯地,自宋末由元明以迄清,數百載矣。前明天啟間邑侯龍以公事來登臨覽勝,竊嘆東方文峰低陷爰斜,兩姓建造寶塔,嗣是游泮登科者相繼而起。[12](《胨蔡嗣孫仝撰序》)
很明顯,以上二地文峰塔的興建和地方宗族自身的興旺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這也揭示了地方紳士為何熱衷于改造科舉的原因。
地方民眾對風水的信心和對科舉的熱心是和地方紳士的積極倡導密不可分的,許多民眾則是隨著紳士的倡導而被卷入。明末清初寧都地方名流魏禧在與友人書中回憶了自己于明末主持的建修風水的活動,他說:
適聞邑中有議拆大東、小東新城,而兄將主其事,弟笑嘆驚怖,甚以為不可也。……居民尚賴此為屏障。一旦以莫須有之風水勞民傷財,以壞生民萬世之利,吾不知其何心也。……又聞將起塔于巽峰。吾意說者必謂移城砌塔,一舉兩得。不知工費出辦何所?……猶記壬午場后,吾邑以連科不得第,有建修風水之說。弟少年不經,妄聽輕作,遂同令弟毅然任之。結怨費財,日營無益。[13](卷七《與友人》)
寧都清初建城砌塔之舉,可謂明代贛南地區造風水、興科舉活動的繼續,新城要拆毀的原因是“謂衙背受新城直沖,東門一帶送水,于形勢為不利”[14](卷四《城池》)。親自主持過崇禎十五年(1642)壬午場后造風水、興科舉活動的魏禧,仍清楚地記得當年的沖動與熱情,而力勸友人不可重蹈上一次的覆轍,不應“主其事”。可見,地方紳士往往是這類活動的主持者,但像寧都拆城建塔這種涉及面很廣的活動,沒有大量民眾的支持要完成同樣也是不可想像的,而地方民眾的支持則來自于對風水的信心和對科舉的熱情。
正是基于對民眾熱心科舉的認識,地方官才有意識地加以引導,倡導民眾改造風水,振興科舉。明人楊守勤解釋贛南地方官熱心于以風水之說來搬遷學校的舉動時說:
予為諸君子之心,豈惑堪輿,總為贛士。蓋人情無與萃渙則不專,無與激昂則不奮。工之肆,齊之莊岳,專故也;下流而邑醪,決勝終食,奮故也。今士專且奮矣,而纘成大道,步趨文成者,又方為爾贛士鵠,宜何省惕,以仰副上人立學意耶?倡率而鼓舞之,是誠在子。[4](卷二四《學校》)
按照楊守勤的解釋,地方官就是利用堪輿學說來“倡率而鼓舞之”。
這種地方官首肯或提議、紳士積極倡導、普通民眾積極響應的運作模式是當時大多數風水建筑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原因。上引的許多事例都顯示出了這種運作模式的存在,現再舉一例。康熙《瑞金縣志》卷三《建設·臺塔》記曰:
壬田塔,招召鄉一里。壬田為瑞金沃壤,山水環抱,一望平衍,實為秀區。而雙流合匯之際,殊覺低陷,以故文士層出,科目少興。知縣潘舜,歷過其地,諸生攀轅而請。以形家言,于坤方宜建一塔。鄉紳朱善卿、許宗謨,生員朱國卿、朱文紹等呈詞,愿捐貲倡義,不動官費,鄉人喜助如云,朱統與等董其事,其塔遂成,扁曰龍見。
壬田龍見塔的修建經過仍是紳士倡導——知縣首肯——民眾響應,經費則“不動官費,鄉人喜助如云”,從中亦可窺見明代贛南社會整體對造風水、興科舉活動的熱心。
四 造風水、興科舉現象與社會變遷及社會心態
我們注意到,六朝以來,風水之說漸漸流行,風水多和喪葬禮儀、住宅選址等活動聯系起來,在求“利”觀念的驅動下,人們企圖通過對風水的追求來獲得命運的改變,祈福求祥。①在科舉日漸重要的明代,把風水和科舉聯系起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并非贛派風水起源地贛南獨有的現象。但是,宋元時期特別是宋代,也是科舉相當發達的時代,為什么贛南沒有出現明代那樣官方與民間共同推動的造風水、興科舉的社會熱潮呢?筆者認為,明代贛南普遍出現的造風水、興科舉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和南宋以來贛南的社會變遷緊緊聯系在一起的。②
贛南由于處于閩、粵、湘、贛四省邊界,加上地形以山地為主,歷來是令統治者頭痛的盜賊多發區。北宋治平年間,王安石在論及虔州(贛州)風氣時說:“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奸,視天下為多。”[15](卷八《虔州學記》)南宋初年,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言:“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16](卷一○一)在宋代士大夫眼中,贛南由于山區尚未開發,盜賊問題嚴重,是一個士大夫不愿履任的偏僻地區。
文人們固然以傳統輿地學的“山水孕育人文”的觀點解釋贛南的盜賊問題,但宋代贛南山區開發尚未展開,社會風氣未被士大夫“教化”也是事實。直至明初,贛南部分地區仍被描述為“地曠人稀”的“煙瘴之地”,明初曾任石城訓導的楊士奇言:“贛為郡,居江右上游,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煙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常什七八。”[4](卷六六《藝文·明文》)
不過,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贛南的開發也在不斷地進行,據曹樹基估計,南宋時期,特別是淳熙年間,官府所控制的人口有明顯的增加,比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增加了三倍多。[17]同時,贛南社會也正在發生變化,人文景觀亦有所改變。由于著名理學家程頤、程灝曾在贛南向周敦頤學習,贛南作為“先賢過化之地”、“理學發源地”得到強調,南宋時期興建了許多書院,著名的有南安軍的道源書院、興國的安湖書院等。元代除了繼續宋代興建書院的趨勢外,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某些大族祖先的“賢良祠”修建于州縣學附近,著名的有寧都的孫氏和黎氏等。
自明代中期起,大量流民進入贛南,一方面帶來山區的開發,另一方面則引發了非常嚴重的盜賊問題。根據曹樹基的研究,明中期以后,贛中、廣東、福建流民逐漸進入贛南開發山區,至清初達到高峰。流民大量進入,使贛南山區得到開發,形成了今天贛南的農林生產格局。③但明代贛南仍是盜賊頻繁、風氣勁悍之地。嘉靖《虔臺續志》載:“宦途言:江西諸郡,率贛難治也。”[18](卷一《贛州府十縣略述》)明人有記曰:“(興國)民氣近悍尚斗”;會昌“山竣水駛,民質剛勁”;安遠“山峻水激,人多好勝”。④弘治八年(1495)朝廷專門在贛州設立南贛巡撫,負責彈壓閩、粵、湘、贛四省邊界的盜賊活動。與此同時,贛南的地方社會也開始轉變,特別是正德年間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就任南贛巡撫后,一方面實行鄉約和保甲等措施進行基層控制和教化,另一方面則大力提倡社學、宣揚“心學”,試圖以儒家的理念來改造基層社會。王陽明的做法基本被后來的南贛巡撫所沿襲。經過地方官和本地士大夫的努力,儒家理念在贛南地方社會影響漸大,具體表現為地方社會中宗族組織勃興、地方社會追求科舉成功的心情日漸急切、神明信仰“正統化”等等。因此,在縣學普遍被改建、大量風水塔出現的現象背后,反映的是儒家理念在地方社會影響的增大。這應該是宋以來贛南社會變遷的一個結果,其背后蘊藏著贛南社會整體變遷與轉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張邦煒《兩宋時期的喪葬陋俗》,《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雷玉華《唐宋喪期考——兼論風水術對唐宋時期喪葬習俗的影響》,《四川文物》1994年第3期;黃艷燕《風水與古代小說中的改運主題》,《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② 筆者曾以《12—18世紀贛南的地方動亂與社會變遷》為題完成博士論文(中山大學,2001),以下關于贛南宋至明代社會變遷的論述未注明出處者均來自于本人的博士論文。
③ 曹樹基《明清時期流民與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第3期;萬芳珍、劉綸鑫《客家入贛考》,《南昌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萬芳珍、劉綸鑫《江西客家入遷原由與分布》,《南昌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饒偉新《明代贛南的移民運動及其分布特征》,《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④ 轉引自《贛州府志》卷二○《風俗》,同治十二年(1873)本。
正因為如此,便不難理解,與造風水、興科舉的舉措同時進行的是毀淫祠、拆道觀的活動。雩都蜚英塔的地基,就是知縣用“所辟淫祠易之”而得到的。[3](卷上《蜚英塔記》)更有意味的是,在雩都,原本是佛塔的重光塔,在這場活動中轉化成了文峰塔。明末贛南另一位著名學者李淶記其經過曰:
塔雖因緣釋氏,然當邑治右,纏逆江流而屹然砥柱,固足善也。……歲壬辰,靜齊黃侯來宰是邑……乃告于眾日:塔之就圮也,風氣漓矣!邑之有龍舟會也,以尚鬼,然而侈且狂矣!吾亦烏能坐視夫厚儲黷鬼之資以益狂?孰與移之葺塔。……邑之人文昌乎,物力阜乎,生齒繁乎
雩都縣令以龍舟會的費用來修葺重光塔,并賦予佛塔以文峰塔的功能,正是具有“正統性”的儒家觀念影響擴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