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地圖編繪意向的初步考察(下)
未知
一部方志需要多少輿圖才能夠達(dá)到其相應(yīng)的政治目的,不同的方志作了不同的陳述。嘉靖《太平縣志》(注:嘉靖《太平縣志》,卷首《太平縣志圖》。) 認(rèn)為有縣境和縣治兩圖便可。嘉靖《吳邑志》(注:嘉靖《吳邑志》,曹自守序。) 認(rèn)為需要疆域、城郭、官署、儒學(xué)四圖。嘉靖《儀封縣志》(注:嘉靖《儀封縣志》,圖考。) 也認(rèn)為應(yīng)該有縣境、縣城、縣治、縣學(xué)四圖。而嘉靖《威縣志》(注:嘉靖《威縣志》,卷首,威縣志圖經(jīng)敘言。) 認(rèn)為需要星象、縣境、縣治、縣城、儒學(xué)、書院六幅。無論對(duì)輿圖圖幅的陳述在數(shù)量上有多大的差異,但是其陳述的核心在于疆域、城池、官署和儒學(xué),其陳述意圖都是為了突出圖的政治功能,然而各種陳述對(duì)不同輿圖政治功用的認(rèn)識(shí)卻并不一致,顯然也不會(huì)一致。 如嘉靖《威縣志》卷首《威縣志圖經(jīng)敘言》認(rèn)為: 按《周禮》九州之圖掌于夏官,此后世圖經(jīng)所由出也。志紀(jì)事而先以圖,義亦如此。圖分星象,天文也。圖縣境,比地理也。仰觀俯察,事從出也。圖縣治而別為城圖,事從理也,篤近以舉遠(yuǎn)也。圖儒學(xué),重育賢也。圖書院,寄正道也。賢才自出之關(guān),事從以敘焉者也。六圖縣而志之事概可考矣。故詳為圖,列之左方。 而嘉靖《儀封縣志》《圖考》則認(rèn)為: 二氣末剖,萬品亡形。亡形亡象,害圖害名。形象既立,圖數(shù)始存。龍馬負(fù)之以出,伏羲則之而畫。凡得名必得象。仿輿圖志圖考志曰:縣必有境,匪圖無以觀廣輪。縣必有城,匪圖無以觀向背。縣必有治,匪圖無以觀其政。縣必有學(xué),匪圖無以觀其教。繪圖于冊(cè),展卷而視,不問不步,舉在目中。 而嘉靖《吳邑志》曹自守序又有差異: 始得王吳二先生所作《姑蘇志》,繼得楊南岸先生所作《吳邑志》。而楊志則專于吳邑者也。惜其詞例頗善而有書無圖。夫疆域曠狹,道里延袤,非圖莫見也。乃請(qǐng)助于太學(xué)吳君補(bǔ)作疆域及城圖。二以有官必有署,署所以臨民而出政者也;有邑必有學(xué),學(xué)者聯(lián)之師儒,使業(yè)有定所者也,亦不可無圖。是故四圖既具而各為之說焉。說者所以盡圖之蘊(yùn)也。夫觀疆域則勝概風(fēng)景在目矣;觀城郭則金池閭闔可識(shí)矣;觀治署與學(xué)知有以繹之。則吏可循而士可賢矣。然則圖其可以已乎?說其果皆迂言妄說乎? 上面這幾段引文所包含的縣級(jí)地方志輿圖的內(nèi)容雖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都有縣境圖,縣治圖,縣城圖,儒學(xué)圖,而對(duì)這四種類型輿圖作用的陳述卻有著一些差異:以縣境圖為例,嘉靖《威縣志》從傳統(tǒng)地理學(xué)理論的角度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區(qū)域內(nèi)地理景觀所以然之理,而嘉靖《儀封縣志》則只是表達(dá)了反映其管轄區(qū)域地理范圍大小的意圖,嘉靖《吳邑志》則更為特別,認(rèn)為縣境圖(疆域)反映的是區(qū)域內(nèi)地理景觀的呈現(xiàn),尤其要呈現(xiàn)具有美學(xué)觀賞價(jià)值的地理景觀。撇開各自所繪地圖精粗不論,我們從這些對(duì)地圖的陳述出發(fā)的話,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三者的陳述旨趣有著明顯的差異,分別體現(xiàn)了三種不同的知識(shí)和價(jià)值取向。一種是中國古代早期地理知識(shí)興起的傳統(tǒng),是對(duì)自然現(xiàn)象的直接的體察和認(rèn)知,并依據(jù)一定的規(guī)則進(jìn)行推理。一種是相對(duì)較為籠統(tǒng)的,被簡(jiǎn)化了的,日常化的地理空間知識(shí),并不追求準(zhǔn)確,精致的空間和地理認(rèn)知,只是要獲得一種大致的地理空間形象和概念,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的是有點(diǎn)“懶惰”的知識(shí)。一種是有著一定“新”義的知識(shí)興趣,即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反映地理景觀真實(shí)的自身,尤其是突出地理景觀的美學(xué)價(jià)值。這一知識(shí)興趣和價(jià)值取向雖然并不是始自明代,它在中國古代地理學(xué)中也有著比較悠遠(yuǎn)的傳統(tǒng),但是在明代它在一定程度上達(dá)到了頂峰。它雖然還沒有完全脫離泛政治化和權(quán)力化的樊籬,但是它已經(jīng)開始緩慢地發(fā)展出具有“新”的,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可能產(chǎn)生“知識(shí)型”變革的科學(xué)興趣的匯聚。 從上述引文和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明代方志在陳述有關(guān)地方輿圖編繪意圖時(shí)除圍繞著政治和權(quán)力表述以外,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差異,正是這些差異向我們展示了明代方志地圖編撰意向中所流露的豐富的一面。它也是我們深入全面地閱讀、理解明代方志輿圖的興趣和警惕所在。下文對(duì)這種豐富性作一初步的呈現(xiàn)。
二明代方志地圖編繪中值得重視的其他意向
首先值得我們給予充分關(guān)注的是,有部分明代方志輿圖的編繪陳述注重于表達(dá)讓輿圖描繪區(qū)域自然地理的真實(shí)和優(yōu)美的風(fēng)景名勝。如崇禎《吳縣志》輿圖即注重于區(qū)域自然地理的圖繪,而且經(jīng)過比較認(rèn)真的野外測(cè)量和勘測(cè)。據(jù)該志卷首鄭敷教《重修吳縣志序》云:“繪圖書策,使瀏覽斯篇者收百里于幾席,則布衣徐霖度量地勢(shì),繞山涉水之力亦末可泯也。”又知縣牛若鱗所作的序中記載該志纂修經(jīng)過時(shí)說:“纂修經(jīng)始于崇禎辛已孟春之溯,脫稿善本于壬午仲春之望,周一歲逾四十有五日,寒暑晝夜無間。編摩摹寫各圖則辛已孟夏月溯出郭,繞境涉湖,舟中吮墨,再扃戶,凡兩閱月五易楮始成。布衣徐霖竭心目之力多焉。”由此:(1)該輿圖的繪制首先作了實(shí)地勘察,前后經(jīng)歷整整兩個(gè)月。(2)在實(shí)地調(diào)查中,對(duì)局部地區(qū)進(jìn)行了測(cè)量,并隨即繪制了草圖。(3)野外工作后,又經(jīng)過室內(nèi)清繪,且五易其稿才最后成圖。(4)野外勘察與實(shí)際繪圖主要由徐霖主持操作。這表明崇禎《吳縣志》輿圖的繪制是在野外實(shí)地勘察的基礎(chǔ)上繪制草圖,最后經(jīng)過室內(nèi)清繪成圖。其輿圖的成圖過程已經(jīng)和現(xiàn)代實(shí)測(cè)地圖的繪制相近。這在明代方志中是難得的精品,具有相當(dāng)高的歷史地理研究價(jià)值。 這種追求真實(shí)形象地反映區(qū)域地理景觀的意圖,在當(dāng)時(shí)并非孤懸。如嘉靖《江陰縣志》之《凡例》即云:“志有圖有表,圖仿唐十道,著山川境土城廓廂舍。”而嘉靖《太康縣志》《圖敘》更為明確:“人物戶賦類非言無以盡其詳,惟言已記之,無事于繪狀。若夫集店之坐落,疆域之界限,山川城池之巍睿,至于景致之物色,非圖無足以見其真。故以列于志,復(fù)繪圖于其首。邑境總繪一圖,后分繪諸圖。先之以城池街巷壇撣一圖,次以縣治學(xué)校二圖,行司二圖,府館置郵二圖,又次以景觀八圖。俾閱志者一邑之規(guī)模指掌(/)(/)于斯矣。” 明代方志輿圖注重地方風(fēng)景名勝并不僅僅表現(xiàn)在所謂的地方八景或十景的陳述和圖繪上,而且直接表現(xiàn)在輿圖編繪者的主觀陳述中。如《天啟平湖縣志》卷首《平湖縣志圖引》即云:“志有經(jīng)必有圖。吾湖介三山九水之間,坦遠(yuǎn)疏秀視他邑尤勝,善畫者莫能圖。顧使拙筆為之,山川有靈,不且笑我唐突乎。用是不敢以己意點(diǎn)綴。聊于歷覽之余,略紀(jì)其梗概如此。姚瑞楨識(shí)。”依據(jù)該志輿圖繪制者姚瑞楨的這段夫子自道,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繪圖的目的并不在于體現(xiàn)地方政治、權(quán)力、治理與教化,而是試圖突出表現(xiàn)地方上秀美的自然景觀,而且他的圖繪是建立在“歷覽”的基礎(chǔ)上的,與上述崇禎《吳縣志》輿圖的繪制有著同樣的實(shí)地考察的基礎(chǔ)和追求真實(shí)的意識(shí)取向。顯然它與一般方志中程式化的八景圖十景圖有著很大的區(qū)別。這種強(qiáng)烈的自然地理景觀意識(shí),雖然與他自身的鄉(xiāng)土感和士紳審美意向以及晚明士風(fēng)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但是這種地方圖繪去政治化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于彌漫著濃郁的政治意圖的明代方志輿圖無疑是一種強(qiáng)烈的沖決。這種陳述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duì)泛政治化社會(huì)的沖決。這種意識(shí)在明代方志輿圖中的表現(xiàn)并非孤例。上引嘉靖《吳邑志》曹自守序即云“夫觀疆域則勝概風(fēng)景在目矣”,已經(jīng)潛在地表露了這一意識(shí)。 其次,地圖的一個(gè)重要作用就是反映地理景觀的變遷。我們可以通過繪制當(dāng)下的地圖來記載地理變遷,也可以通過繪制歷史地圖來反映地理變遷。在明代方志中用歷史地圖的形式反映政區(qū)地理變遷和城市地理變遷的情況比較多見。 用歷史地圖的形式反映政區(qū)地理變遷。一般認(rèn)為裴秀《禹貢地域圖》可能是最早的歷史地圖集,但現(xiàn)存最早的歷史地圖集則是北宋時(shí)稅安禮所編之《歷代地理指掌圖》,圖的質(zhì)量雖然較差,但是對(duì)此后的歷史考證地圖集的編制有著較大的影響(注:前揭盧良志《中國地圖學(xué)史》,1984年,第204頁;《中國古代地理學(xué)史》,第292頁;唐錫仁、楊文蘅主編:《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地學(xué)卷》,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第258頁。)。明代,利用歷史地圖集編纂自己所需的地圖,在方志輿圖的編纂中得到表現(xiàn)。正德《潁州志》(注:劉節(jié)纂修,(正德)《潁州志》。) 凡例“引用”下列有《二十一史》,《一統(tǒng)志》《中都志》以外,還列有《歷代輿地圖》,這表明該志地圖的編繪過程中已經(jīng)注意到對(duì)當(dāng)時(shí)有關(guān)歷史地圖研究成果的利用。該志現(xiàn)刊天一閣本已無輿圖,無從考見其詳情。但明代方志卷首所列地圖往往有稱“古今圖”“圖考”者,亦可為之旁證。有些方志卷首列的地圖篇幅較多,其地圖包含古今,可視為該地的歷史地圖集。如嘉靖《惟揚(yáng)志》(注:朱懷干修,盛儀纂,(嘉靖)《惟揚(yáng)志》。)、隆慶《儀真志》(注:申嘉瑞修,李文纂,(隆慶)《儀真志》。)。嘉靖《惟揚(yáng)志》卷一《古今圖》后的“圖說”對(duì)此有明確的陳述:“益地括地圣德肇圖,司徒司空周官載籍。漢收秦藏而知扼塞,魏據(jù)縣志以決紛爭(zhēng)。唐列國要國照之名,宋存方域方物之曲。遠(yuǎn)概全物之舊跡,近睹寶佑之遺編。揚(yáng)州代起夏商,儀真朝自南北。宋之府域,雖悉推之,州縣猶遠(yuǎn)。因列繪于篇端,用存羊于既往。揚(yáng)子雖廢,一跡尚留;海門屢坍,三遷互見。考今古而縣參,庶展閱之了然。豈曰沈括圖草之成適符興國閏年之貢云爾。” 這一類型中表現(xiàn)較為突出的是其轄區(qū)同屬今安徽境內(nèi)的嘉靖《寧國府志》(注:李默纂,(嘉靖)《寧國府志》。) 與嘉靖《池州府志》(注:王崇纂修,(嘉靖)《池州府志》。)。兩志所列輿圖皆起于秦終于明。嘉靖《寧國府志》卷一《郡地圖》列明以前地圖七幅:秦鄣郡縣圖、漢丹陽郡縣圖、晉宣城郡縣圖、隋宣城郡縣圖、唐宣州縣圖、宋寧國府縣圖、元寧國路縣圖。嘉靖《池州府志》卷首列明以前地圖共六幅:秦鄣郡圖、漢丹陽郡圖、隋宣城郡圖、唐朝始立池州圖、宋池州圖、元池州路總管府圖。比較兩志,其中秦漢圖幅的地物描繪與圖注說明基本相似,而隋唐宋元各圖則隨政區(qū)變遷而依次變化,兩志所圖內(nèi)容也因政區(qū)所轄不同而大異。然依據(jù)其秦漢兩圖,我們似可推測(cè)兩志在編輯方志地圖時(shí)所參考的歷史地圖資料是相同的,或?qū)儆谕粴v史地圖系統(tǒng)。
三小結(jié)
通過上文對(duì)明代方志地圖編繪意向的初步考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shí)地方志的編撰者和地方志輿圖的編繪者對(duì)于地圖編繪的態(tài)度和認(rèn)識(shí)是豐富多彩的,是生動(dòng)活潑的。在他們的陳述中,我們既可以發(fā)現(xiàn)某些共同之處,如相當(dāng)數(shù)量的陳述突出地強(qiáng)調(diào)了輿圖的政治功能,同時(sh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的差異,如對(duì)輿圖的政治功能的認(rèn)識(shí)就各不相同。而更值得考察的是在此之外的差異,如對(duì)區(qū)域地理景觀自身的關(guān)注。通過對(duì)明代方志地圖編繪意向的重新呈現(xiàn),我們已經(jīng)可以大致地得到從中所體現(xiàn)的當(dāng)時(shí)人的地理知識(shí)的不同傳統(tǒng)和一些雖然微弱但卻是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變革萌芽的知識(shí)興趣。這些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一般的地理學(xué)觀念與知識(shí)系統(tǒng),同時(shí)表現(xiàn)出方志地圖在地理學(xué)史和地理學(xué)思想史中所可能具有的地位和意義。這些還有待于我們從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背景、知識(shí)背景以及世界圖景中做更為細(xì)致的考察。
村工作通訊.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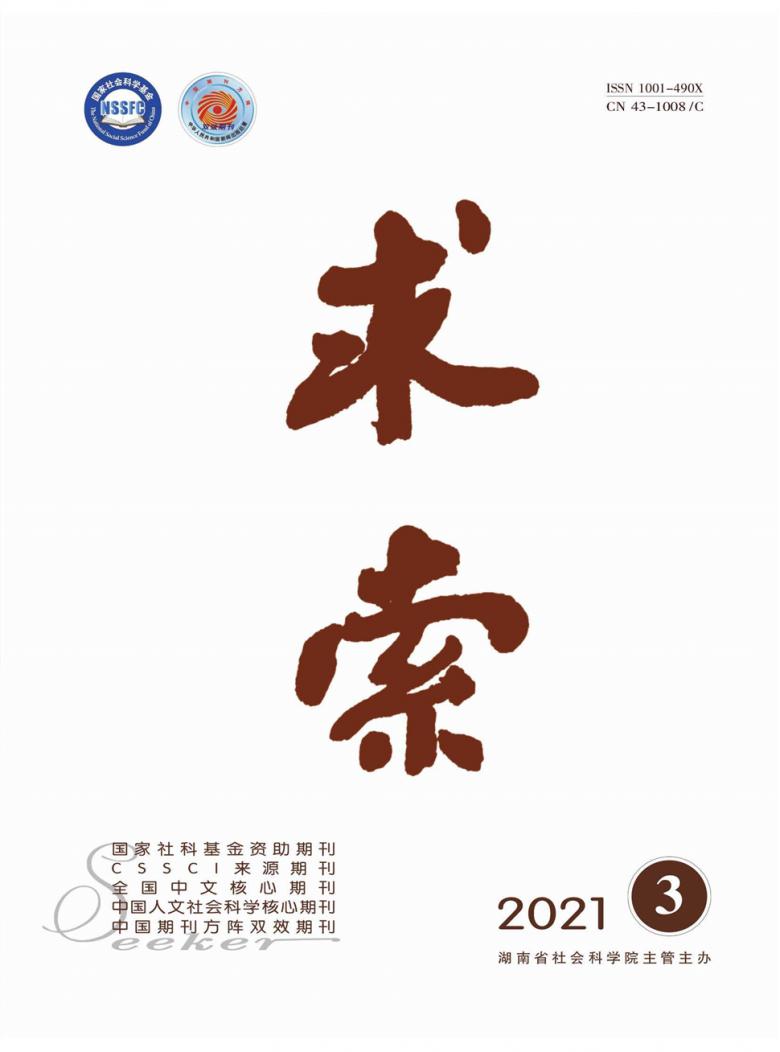
蒙古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jpg)
械研究與應(yīng)用.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