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批契與其法律意義
阿風(fēng)
在現(xiàn)存的大量徽州文書(shū)中,保存著一些被稱之為“批契”的契約文書(shū),同時(shí)還有許多徽州土地買賣文書(shū)在述及土地來(lái)源時(shí),有“承祖批受”、“承故夫批受”、“承妻伯批撥”、“承外祖批產(chǎn)”、“承父批受”等各種情況〔1〕。批契作為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的一種法律文書(shū), 它書(shū)立的方式、反映的內(nèi)容、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具有什么特點(diǎn)?它主要發(fā)生在哪些領(lǐng)域?本文擬利用徽州文書(shū)中的批契以及有關(guān)的土地買賣文書(shū)對(duì)以上問(wèn)題做一個(gè)簡(jiǎn)要的說(shuō)明。
一、現(xiàn)存的明代批契
批契是土地所有者為將土地批給指定的繼承人而立的文契〔2〕。以“批受”的形式轉(zhuǎn)移財(cái)產(chǎn),宋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名公書(shū)判清明集》中多次出現(xiàn)過(guò)“批貼”、“批付”等稱呼〔3〕。 明代的文獻(xiàn)中暫時(shí)還見(jiàn)不到關(guān)于“批契”的記載,但現(xiàn)存的明代徽州文書(shū)中則有一些保存完整的批契。
本文選錄了《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的七張批契,茲臚列于下。
批契1 建文元年祁門謝翊先批契〔4〕
十西都謝翊先臨危之時(shí),思知有女嚴(yán)娘須出事他人,衣被并無(wú),又兼妻胡氏圓娘終年衣被無(wú)得錯(cuò)〔措〕辦。今本里周家山,與顯先相共,本宅肆分中合得叁分,批付與妻胡氏、女嚴(yán)娘二人名下,其山地東至田,西至降,南至深坑,北至塢心,下至溪,上至長(zhǎng)彎口,從小嶺上降至長(zhǎng)彎頭。自批之后,一聽(tīng)變賣用度,諸人不可言說(shuō),如有言說(shuō),赍此文付官陳告,準(zhǔn)不孝論。外又將吳坑南塢山地一片,東長(zhǎng)嶺及自山,西鐵釜塢,南降,北坑,添批付胡氏發(fā)賣用度。今恐(無(wú))憑,立此批契為用。
建文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批契
洪武三十二〔5〕 謝翊先(押)
外許有淮常以根〔跟〕隨胡氏圓娘,應(yīng)辦柴炭食及胡氏供,他侄男,不許使喚,如違,準(zhǔn)不孝論。再批(押)
批契2 建文元年祁門謝翊先批契〔6〕
十西都謝翊先,自嘆吾生于世,幼被父離,值時(shí)更變,艱辛不一。緣我男少女多,除女榮娘、嚴(yán)娘已曾聘侍外,有幼女換璋、注娘未曾婚娉〔聘〕。見(jiàn)患甚危,心思有男淮安年幼,侄訓(xùn)道心性綱〔剛〕強(qiáng)。有妻胡氏,年逾天命,恐后無(wú)依,是以與弟謝曙先商議,令婿胡福應(yīng)依口代書(shū),將本都七保土名周家山,經(jīng)理唐字一千三百八十九號(hào)夏山肆拾畝,其山東至田,西至大降,南至深坑,下至謝一清田,北至嶺,上至降,下至雙彎口小坑,隨坑下至大溪及謝閏孫田末。其山與謝顯先相共,本宅四分中合得叁分,計(jì)山叁拾畝。又將七保吳坑源,土名南塢,經(jīng)理唐字二千五十六號(hào),計(jì)山五畝三十步。其山東至長(zhǎng)嶺,下至坑口大溪田,西至坑心,上至降,下至塢口坑,南至降,北至正塢坑。今將前項(xiàng)二處山地,盡行立契出批與妻胡氏圓娘名下管業(yè),與女換璋、注娘各人柴米支用。候女出嫁之后,付與男淮安永遠(yuǎn)管業(yè),諸人不許爭(zhēng)占。其未批之先,即無(wú)家、外人交易。如有一切不明及侄〔秩〕下子孫倘有占攔,并聽(tīng)赍此批文經(jīng)官告理,準(zhǔn)不孝論,仍依此文為始。今恐無(wú)憑,立此批契為用。
建文元年己卯歲十二月十九日謝翊先(押)批契
洪武三十二
見(jiàn)人謝曙先(押)
依口代書(shū)婿胡福應(yīng)(押)
這里要說(shuō)明一下,批契1與批契2都是謝翊先所立,批契1 是謝翊先于建文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親筆所書(shū),從原契可以看出字跡歪斜無(wú)力,似為病重時(shí)所書(shū),且只有一人畫押。批契2書(shū)于十二月十九日, 由其婿代書(shū),并有其弟謝曙先為“見(jiàn)人”,內(nèi)容更為詳細(xì),形式更為正規(guī)〔7 〕。
批契3 成化二十一年祁門王仕昶批契〔8〕
十四都王仕昶,今不幸妻故。生有三女,賢真許與本(都)陳仕訓(xùn)為妻。思女年幼,母故,無(wú)人管顧,自情愿將標(biāo)分得山一號(hào),坐落本都三保,土名七公塢,共計(jì)山壹拾貳畝,內(nèi)取四畝,出契批與女賢真,以準(zhǔn)衣被等件,聽(tīng)自女婿陳仕訓(xùn)永遠(yuǎn)同共管業(yè)。本家子孫即無(wú)異言爭(zhēng)占,如違,準(zhǔn)不孝論,仍依吾批契為始。所有上手文書(shū)、老契,本家收留,日后赍出一同照正〔證〕,今恐無(wú)憑,立此批契為用。
成化廿一年十一月廿日立批契王仕昶(押)
中見(jiàn)親兄人王仕英(押)
批契4 嘉靖二十一年祁門盛浩批契〔9〕
三四都盛浩,今因無(wú)子,自情愿將自己分下田山盡數(shù)立契批與侄世靖、世仁、世四弟兄為業(yè)。一處土名椑樹(shù)塔,本身六分中該得一分。一處土名李家灣里截,本身三分中合得一分。一處土名李家灣外截,浩用價(jià)己買。一處土名大塢,十二分中本身合得一分。一處土名大塢口山一備,己買山。一處土名松毛塢山,本身三分中合得一分。一處土名中樹(shù)塢山,本身合得一半。一處土名冢塢山,本身六分中合得一分。再又冢塢基地田二畝,本身六分中合得一分。一處土名中樹(shù)塢田,荒熟田,一畝貳分。又中樹(shù)塢外截田九分五厘。一處土名小塢口田二丘,再坐在坑邊田三丘,盛家翹上荒田一丘,共田一畝。今將前項(xiàng)各處田山一概批與侄世靖弟兄三人永遠(yuǎn)管業(yè),亦不許家、外人變賣,即無(wú)。倘有他人、盛正回家,亦不許爭(zhēng)論、變賣,聽(tīng)自世靖赍文告理。今恐無(wú)憑,立此批契文書(shū)為照。
嘉靖廿一年二月廿日立批契人盛浩(押)契
中見(jiàn)人周五孫(押)盛田(押)盛正(押)盛世祿(押)
家見(jiàn)房弟人吳永英(押)吳琴保(押)
代書(shū)人謝擢(押)
批契5 嘉靖三十五年汪于祚批契〔10〕
龍?jiān)赐粲陟瘢懈竻⒄蹋形遄印6苡谙椴恍以鐨懀苡诙Y病在危篤,身思手足之情,不能享無(wú)故之樂(lè)。參政翁存日,與身納監(jiān)之需,是系眾貼備。四弟于祜在學(xué),日后納監(jiān),眾將板溪田租叁佰秤貼備。今思于禮倘有不測(cè),預(yù)憑中將土名板溪田租叁佰秤批與二女淑音、瀾音,以為嫁妝之需,以敵納監(jiān)之費(fèi)。自立文約,并無(wú)異言。今恐無(wú)憑,立此為照。再批:貼備于禮二女田租,隨聽(tīng)收租,以備逐年衣服針線之用。只此。
嘉靖卅五年正月初五日立議約人
汪于祚(押)約 汪于禮(押) 汪于祜 汪于祍
主盟母親章氏(押)
中見(jiàn)人汪永保 汪棠(押)
批契6 崇禎三年祁門程宗堯批契〔11〕
立批契親叔程宗堯,今因親侄程良儒侄孫程甡、程喆家貧業(yè)儒,不能生理,自思生平輸田備賑,尚念貧乏忍視親侄父子讀書(shū)無(wú)資。……今托親族程宗禹等眼同立契出批與親侄程良儒父子名下收租管業(yè),以為燈油紙筆、考費(fèi)之資,此系作養(yǎng)義舉。自立批契之后,我子孫永遠(yuǎn)無(wú)得生端異說(shuō)。倘有違逆,聽(tīng)侄赍文告理,準(zhǔn)不孝論,仍依此批契為準(zhǔn)。所有稅糧隨契扒入侄良儒名下供解,再不另立推單。今恐無(wú)憑,立此批契為照。
今將批契內(nèi)土名、租數(shù)、佃人開(kāi)具于后
(略)
崇禎三年十月初十日立批契親叔程宗堯(押)
中見(jiàn)親弟程宗尹(押)堂弟程宗禹(押)程宗伯(押)
依口代書(shū)親侄程良輔(押)
準(zhǔn)受業(yè)
批契7 崇禎十五年程池立扒產(chǎn)批文約〔12〕
今將芥字九千三百十七號(hào),土名楊樹(shù)園,計(jì)稅捌分壹厘,佃人金婢切、吳三、吳冬旸。又將芥字六千七百貳拾一號(hào),土名大溪邊店屋,地稅叁分,佃人程社蔭、吳華、六仂。又將果字一千六百四十七號(hào),土名瑯木塢,山稅壹畝肆分一厘八毫,守山人吳和保、汪黑鐵。以上叁號(hào),眾議扒與伯杰名下為業(yè),為讀書(shū),以托府薦之資,父批。
崇禎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父程池(押)
這幾張批契大都來(lái)自當(dāng)時(shí)的徽州府祁門縣(只有批契7 不敢確定為哪一個(gè)縣的),既有明朝初年的,也有明朝中后期的,因此可以基本上反映出有明一代當(dāng)?shù)匾浴芭堋毙问睫D(zhuǎn)移財(cái)產(chǎn)的情形。
首先看一下立批契的原因。從以上的7 張批契可以看出立批契的緣由有3種。第一,安排后事。從批契1、批契2 可以知道謝翊先書(shū)立批契的原因是:臨危之時(shí),想到女兒未嫁,兒子年幼,妻子終年無(wú)有依靠,恐怕自己故后,財(cái)產(chǎn)為他人(契中寫明了“侄訓(xùn)道心性剛強(qiáng)”)所奪占〔13〕。批契3則是因?yàn)椤八寂暧祝腹剩瑹o(wú)人管顧”, 所以將山地一號(hào)批給女兒(女婿),“以準(zhǔn)衣被等件”。批契5 是因?yàn)椤坝诙Y病在危篤”,預(yù)先將財(cái)產(chǎn)批給其女,以為“嫁妝之需”。這幾張批契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對(duì)后事的安排。第二,財(cái)產(chǎn)無(wú)承分人。批契4是盛浩“今因無(wú)子, 自情愿將自己分下田山盡數(shù)立契批與侄……為業(yè)”,盛浩無(wú)后,其財(cái)產(chǎn)沒(méi)有承分人,所以將土地批給三個(gè)侄兒。但這張契約沒(méi)有說(shuō)明為什么盛浩沒(méi)有立繼子。一般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人們?yōu)榱搜永m(xù)宗祧和養(yǎng)兒防老,依據(jù)“同宗則可為之后”的禮制原則,規(guī)定“無(wú)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dāng)之侄承繼”〔14〕。作為繼子,則享有與親子同樣的權(quán)利,成為財(cái)產(chǎn)的合法“承分人”。但從這張契約中可以看出,盛浩僅是把財(cái)產(chǎn)分給三個(gè)侄兒,而并沒(méi)有選其中一個(gè)侄兒作為他的繼子而繼承他的財(cái)產(chǎn)。也許這背后隱藏有財(cái)產(chǎn)的爭(zhēng)端,但限于資料,無(wú)法解釋清楚。第三,將財(cái)產(chǎn)批給子侄,作為教育投資,“以為燈油紙筆,考費(fèi)之資”(批契6 ),“為讀書(shū)以托府薦之資”(批契7),以期子侄讀書(shū)入仕, 光宗耀祖。
其次看一下立批契人與受批人的關(guān)系。有的是丈夫批給妻子,有的是父親批給兒子、女兒(女婿),有的是伯父、叔父批給侄兒、侄女。以“批契”形式轉(zhuǎn)移財(cái)產(chǎn)多發(fā)生于親威之間,常常是長(zhǎng)輩“批”給晚輩。其中批契5有些特殊,批契是以汪于祚的名義書(shū)立, 但最后卻稱“立議約人”,兄弟四人同時(shí)畫押,并由母親出面主盟。這是因?yàn)榧尉溉迥陼r(shí),父親參政翁雖已去世,但汪家并未分家〔15〕,汪于祚以長(zhǎng)子為家長(zhǎng),恐怕三弟于禮“倘有不測(cè),預(yù)憑中將……批與二女淑音、瀾音,以為嫁妝之需”。這其實(shí)是將未曾分析的家產(chǎn)中應(yīng)該屬于汪于禮的部分事先進(jìn)行批付,但因?yàn)橥艏也⑽捶治觯荒芤酝粲陟竦拿x書(shū)立。
第三,看一下批契的內(nèi)容。批契一般都寫明田地、山場(chǎng)的位置,如所在的都保、土名、字號(hào)、四至等等。同時(shí)對(duì)田土肥瘠、面積、租額以及所批付的份額都一一書(shū)寫清楚,有的批契還將佃戶姓名寫在契中(如批契7),或開(kāi)具于后(如批契6)。有的契約還注明“其未批之先,即無(wú)家、外人交易”(批契2),以避免日后發(fā)生糾紛。 對(duì)于受批人而言,女兒常常成為接受批產(chǎn)的對(duì)象。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的習(xí)慣是“男承家產(chǎn)、女承衣箱”,父母有為女兒備置嫁妝的義務(wù),但一般說(shuō)來(lái),土地等不動(dòng)產(chǎn)是輕易不能分給外姓人家的,例如批契2 明確規(guī)定:“候女出嫁之后,付與男淮安永遠(yuǎn)管業(yè)。”但與此相反,批契3 則是王仕昶將土地“出契批與女賢真,以準(zhǔn)衣被等件,聽(tīng)自女婿陳仕訓(xùn)永遠(yuǎn)同共管業(yè)”。特別是現(xiàn)存的一些徽州土地買賣文書(shū)中在述及土地來(lái)源時(shí)有“承外祖批撥”、“原有妻伯……批撥”、“承岳父批產(chǎn)”之類的說(shuō)明〔16〕,可見(jiàn)批受是婦女(以丈夫名義)占有家庭(娘家)不動(dòng)產(chǎn)的一種重要方式。
最后看一下批契的書(shū)立方式與保證。批契的書(shū)立方式有自書(shū)與代書(shū)兩種方式。批契1是謝翊先病重之時(shí)自書(shū)的批契, 但他考慮到這張批契字跡歪斜不清,又沒(méi)中見(jiàn)人在場(chǎng),所以四日后,謝翊先又讓其女婿胡福應(yīng)代書(shū),重新書(shū)立一張批契(批契2), 其弟謝曙先作為中見(jiàn)人在批契上畫押。可見(jiàn),無(wú)論是自書(shū),還是代書(shū),中見(jiàn)人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見(jiàn)人是確保批契法律效力的重要保證。批契的中見(jiàn)人一般都是同族人,有的就是親兄弟。在這7張批契中,批契3、4、6經(jīng)官投印,蓋有官府的紅印,批契7并有官方“準(zhǔn)受業(yè)”的批示。剩下的4張批契中,除了批契1、批契7書(shū)立的比較簡(jiǎn)單(沒(méi)有中見(jiàn)人畫押)外,批契2、5都只有族人或兄弟作為中人當(dāng)場(chǎng)畫押,而沒(méi)有經(jīng)由官府。這是因?yàn)橐环矫妫诩易灞疚坏墓糯袊?guó),所謂社會(huì)的承認(rèn),首先是族人的承認(rèn),只要取得族眾的同意,官方是會(huì)承認(rèn)其法律效力的。另一方面,當(dāng)時(shí)在交通不便的徽州,經(jīng)官投印是比較費(fèi)時(shí)、費(fèi)力、費(fèi)錢的麻煩事,徽州文書(shū)中存在的大量白契就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特別是對(duì)于這種發(fā)生于家族內(nèi)部的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更是如此。對(duì)于違反批契所規(guī)定的行為,批契中一般都規(guī)定以“不孝罪”作為違反立批契人意志的懲罰。 二、批契的特點(diǎn)與其所發(fā)生的領(lǐng)域
根據(jù)以上內(nèi)容可以看出,以批契形式進(jìn)行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主要發(fā)生以下三個(gè)領(lǐng)域。
(一)從批契1、批契2可以看出,這兩張批契帶有明顯的遺囑文書(shū)性質(zhì)。它們是謝翊先臨終之時(shí),對(duì)于其后事(主要是財(cái)產(chǎn))的安排。它是以謝翊先個(gè)人意志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單方面法律行為,批契采用的是單契的形式。從這一點(diǎn)可以看出批契與徽州文書(shū)中大量存在的分家書(shū)是不一樣的。分家書(shū)(又稱分書(shū)、標(biāo)書(shū)、標(biāo)單、分家合同等)是必須經(jīng)由族眾、長(zhǎng)輩合議,按照習(xí)俗、慣例進(jìn)行分割,它是由多人共同畫押,常常采取合同契方式。而批契則是以個(gè)人意志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將財(cái)產(chǎn)批給指定的繼承人而書(shū)立的文契,以保護(hù)指定繼承人的權(quán)益,避免日后“爭(zhēng)訟”。因此批契1、批契2具有遺囑文書(shū)的性質(zhì)。
(二)批契是一種預(yù)先處置家產(chǎn)的文書(shū),帶有“生前繼承”的性質(zhì),批契3、4、5、7就是這種性質(zhì)的文書(shū)。這幾張契約都是立批契人在世時(shí),預(yù)先將其財(cái)產(chǎn)的一部或全部批給其兒子、女兒、女婿或者侄兒,使其子侄在批契人在世時(shí)就擁有一部分家產(chǎn)。在傳統(tǒng)禮制下,一般家庭“父母存,……,不有私財(cái)”〔17〕,理論上不存在著生前繼承問(wèn)題。秦漢時(shí)期,生前繼承曾一度合法化〔18〕,唐律則明文規(guī)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cái)者,徒三年,”又規(guī)定:“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后者,徒二年,子孫不作。”〔19〕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生前繼承”行為。元朝時(shí)規(guī)定:“如祖父母、父母在,許令支析者聽(tīng),違者治罪。”〔20〕到了明代,法律規(guī)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cái)產(chǎn)者杖一百,”同時(shí)還規(guī)定:“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21〕元明兩代,法律并不限制受父母之命而“別籍異財(cái)”的行為,所以清人薛允升評(píng)論明律時(shí)說(shuō):“以別籍異財(cái)為無(wú)足輕重之事矣!古今風(fēng)氣不同如此。”〔22〕正是基于這個(gè)背景,當(dāng)時(shí)民間父母尚在,而子孫自己擁有財(cái)產(chǎn)的現(xiàn)象也是很多的。當(dāng)然,這種以批受形式獲得的財(cái)產(chǎn),受批的子侄在處置該財(cái)產(chǎn)時(shí),還應(yīng)得到立批契人或相關(guān)之人的同意或認(rèn)可。例如,成化十一年,休寧縣胡瑾在出賣其父親批與的“無(wú)糧荒塘”的賣契中,胡瑾的父親胡家祥作為“主盟”在契約中簽字畫押〔23〕。還有“建文三年休寧胡社賣田赤契”,由于胡社出賣的土地來(lái)源于“妻伯朱鐵干批撥”,所以契中寫明了“同妻母李氏商議”〔24〕。可見(jiàn),處置“批受”而來(lái)的財(cái)產(chǎn),常常會(huì)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就批契6而言,這是一種家族內(nèi)部的捐贈(zèng)行為。批契6是程宗堯想到其侄兒和侄孫家境貧寒、讀書(shū)無(wú)資,因此將其田產(chǎn)的一部分批給其侄兒與侄孫,“以為燈油紙筆、考費(fèi)之資”,這是一種“義舉”。這種“濟(jì)弱撫貧”的行為,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徽州地區(qū)是屢見(jiàn)不鮮的。而批受成為實(shí)現(xiàn)贈(zèng)與行為的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的方式之一。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批契作為實(shí)現(xiàn)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的法律文書(shū),它的主要特點(diǎn)在于其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的無(wú)償性,因此,“批受”多發(fā)生于家族內(nèi)部,親戚之間,它既不同于土地買賣,也與家產(chǎn)分析有著許多不同。從現(xiàn)存的大量徽州文書(shū)中可以看出:有明一代,至少在徽州地區(qū),“批契”作為一種成熟的法律文書(shū),在財(cái)產(chǎn)(主要是不動(dòng)產(chǎn))轉(zhuǎn)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6〕此類文書(shū)見(jiàn)于《明清徽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資料叢編》第1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的有:“宣德元年祁門縣謝楨詳?shù)荣u山赤契”、“正統(tǒng)四年休寧縣汪存義賣田赤契”、“正統(tǒng)十一年休寧縣吳云賣田赤契”。見(jiàn)之于《明清徽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資料叢編》第2 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的有:“建文三年休寧胡社賣田赤契”、“永樂(lè)十三年祁門李永成等賣山赤契”、“成化十一年休寧胡瑾賣塘赤契”、“正德七年黃鎰賣田赤契”、“嘉靖四十二年王興旺等賣山白契”、“萬(wàn)歷十年鄭天章賣田白契”。
〔2〕周紹泉:《徽州文書(shū)的分類》,《徽州社會(huì)科學(xué)》1992 年第2期。
〔3〕《名公書(shū)判清明集》中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載。 試舉幾例:“羅柄戶計(jì)稅錢伍拾余貫,正室無(wú)嗣,有婢來(lái)安生子一人。嘗以批貼付之,謂吾年六十,不為繼室所容,逼逐在外,女使來(lái)安有子護(hù)郎,寄在田舍,將及一歲,今以平心庵處之,撥龍巖田三千把,以充口食。”見(jiàn)卷之四“羅柄女使來(lái)安訴主母奪去所撥田產(chǎn)”。“石居易念其侄女失怙,且貧無(wú)奩具,批付孟城田地。”見(jiàn)卷之六“訴奩田”。“柳璟兄弟四人,久矣分析,……。璟死之日,家業(yè)獨(dú)厚,生子獨(dú)幼,遂以四侄貧乏,各助十千,書(shū)之于紙,歲以為常。今才五七年,而璟之妻子乃渝元約,諸侄陳論,意欲取索,就其族長(zhǎng)索到批貼,系璟親書(shū),律以干照,接續(xù)支付,似可無(wú)辭。”見(jiàn)卷之八“諸侄論索遺囑錢”。以上選自中華書(shū)局1987年出版的《名公書(shū)判清明集》。
〔4〕《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1卷第42頁(yè)(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版)。這里需要說(shuō)明的有兩點(diǎn):一是原契無(wú)標(biāo)題,標(biāo)題為編者所加。二是原契中簡(jiǎn)寫、俗寫之字,今以規(guī)范漢字列出,契中錯(cuò)字、別字在其后以“[]”列出正字,契中缺字以“()”補(bǔ)上,原契中模糊不清,無(wú)法識(shí)讀之字以“□”標(biāo)出。下引文同,不再一一說(shuō)明。
〔5〕洪武只有三十一年,朱棣“靖難”之后,不承認(rèn)建文年號(hào),故將建文一、二、三、四年改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批契1、批契2原寫“建文元年”,后將“建文元”三字涂掉,在旁邊書(shū)“洪武三十二”五字。見(jiàn)周紹泉《明清徽州契約與合同異同探究》,《中國(guó)史學(xué)》第三卷(1993年10月25日發(fā)行)。
〔6〕《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1卷第43頁(yè)。
〔7〕欒成顯:《明初地主積累兼并土地途徑初探》, 《中國(guó)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1卷第230頁(yè)。
〔9〕《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2卷第123頁(yè)。
〔10〕《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2卷第240頁(yè)。
〔11〕《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4卷第297頁(yè)。
〔12〕《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4卷第480頁(yè)。
〔13〕永樂(lè)四年,謝翊先的妻子胡氏圓娘將其“承故夫批受”的山地以賣契的方式“賣”給其子謝淮安,以確保其財(cái)產(chǎn)不致落入外人之手。見(jiàn)《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1卷第62 頁(yè)“永樂(lè)四年祁門胡氏員孺人賣山地白契”。
〔14〕薛允升:《讀例存疑》“戶律”之“立嫡子違法”條。
〔15〕《徽州千年契約文書(shū)》“宋·元·明編”第2卷第385頁(yè)有“嘉靖四十五年汪于祚戶分業(yè)合同”。從中可以知道,汪家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因戶役重疊、家事紛紜、難累一人支持。同弟侄商議將家分析各便”。
〔17〕《禮記》曲禮上。
〔18〕中國(guó)傳統(tǒng)禮制要求“父母在,不有私財(cái)”,不準(zhǔn)生前繼承;秦國(guó)頒《分異令》,全盤否定“父母在,不有私財(cái)”禮制;漢“異子之科”接秦之緒,法律上仍然承認(rèn)生前繼承。見(jiàn)葉孝信《中國(guó)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23頁(yè)。
〔19〕《唐律疏議》卷第一二《戶婚》。
〔20〕《通制條格》卷三《戶令》。
〔21〕〔22〕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卷一二。
〔23〕〔24〕《明清徽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資料叢編》(第2輯),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407、21頁(yè)。
絡(luò)安全.jpg)
建材.jpg)

醫(yī)藥.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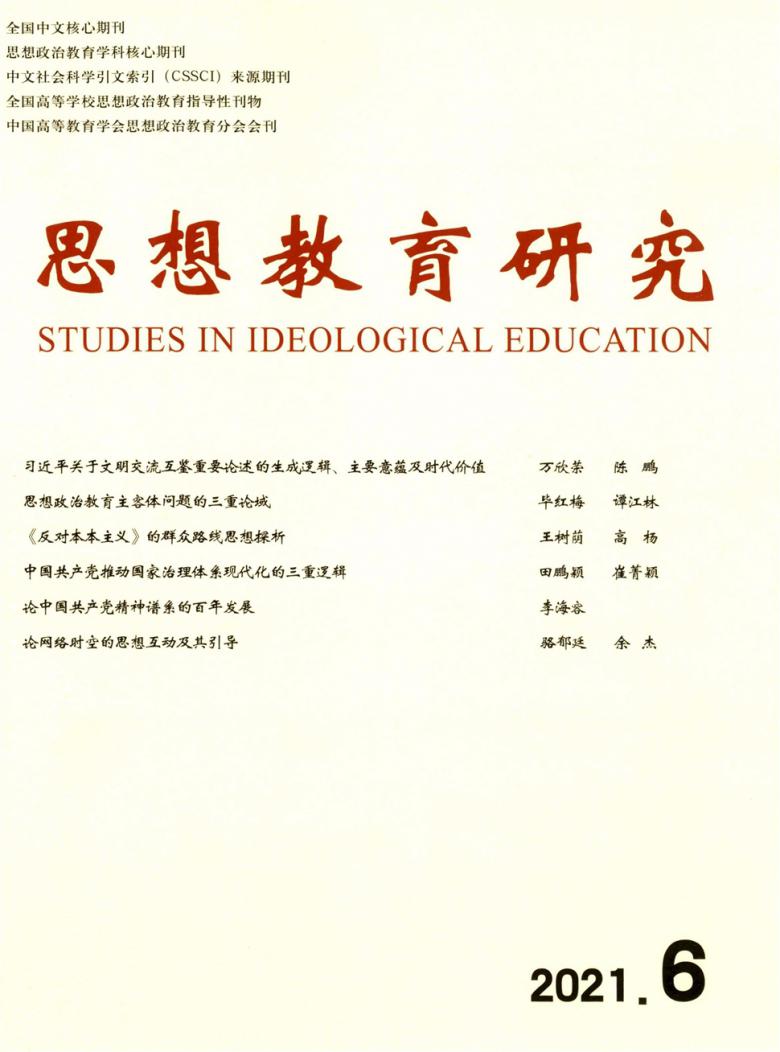
科雜志.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