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仿古制作的“樣本”問題
韓巍
宋代對古代青銅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審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還寄托了士大夫階層“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古器物學在上層與禮制改革相結(jié)合,逐漸滲入禮學傳統(tǒng)之中,改變著士大夫?qū)Α肮拧钡恼J識,導致徽宗和高宗兩朝大規(guī)模的復古運動,最終使古器形制成為國家祀典用器的標準。同時,古器物學的成果也向民間擴散,并與民間固有的工藝傳統(tǒng)相結(jié)合,創(chuàng)造出一批獨特的仿古器物[1]。在制作仿古器物時,必須有具體的“樣本”根據(jù),當時人稱之為“樣制”、“樣式”或“圖樣”。宋代仿古制作的“樣本”究竟從何而來,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為“樣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發(fā)揮作用,這些都是本文著重討論的問題。
北宋時期,朝廷制作禮器的樣本是宋初聶崇義的《三禮圖集注》。聶氏《三禮圖》繼承了漢唐經(jīng)師對于“三禮”名物制度的認識,其特點是從文獻出發(fā),通過經(jīng)文和歷代注疏來復原上古禮器。這樣就難免出現(xiàn)很多望文生義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看來,其中荒謬可笑之處比比皆是。宋初將《三禮圖》定為朝廷禮樂制作的范本,并圖繪于國子監(jiān)講堂之壁,享有權(quán)威地位,但學者范圍內(nèi)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息。《三禮圖》的問題,在傳統(tǒng)經(jīng)學體系內(nèi)是無法解決的,必須求助于新的知識背景。宋代金石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因此從一開始就擔負起了更新傳統(tǒng)禮學的任務。 宋代古器物學的先驅(qū)劉敞就是一位禮學專家,“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數(shù)十件,經(jīng)常說:“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2]他在《先秦古器圖》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禮家明其制度”應是古器研究的目標之一[3]。劉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學家呂大臨,是理學家程頤的弟子。他博學多識,“通六經(jīng),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4]。他曾“集諸家之說補《儀禮》”,又在家廟祭禮中使用古器,穿著古禮服[5]。可見他的古器研究更是與復興古禮的實踐相結(jié)合。呂大臨的《考古圖》雖然沒有直接批評《三禮圖》的錯誤,但是他確立了根據(jù)器物“自名”來為古器定名的原則,實際上已經(jīng)在很多方面否定了《三禮圖》,在當時的學者中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隨著崇古之風的盛行和古器物學知識的積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直接對《三禮圖》提出質(zhì)疑。比劉敞稍后的沈括,就已根據(jù)出土的“黃目彝”、“谷璧”、“蒲璧”等物,指出“《禮圖》亦未可為據(jù)”[6]。受學于王安石的陸佃,撰寫了《禮象》十五卷,“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遺物,與聶圖大異。”[7]可見在徽宗改制之前,士大夫中間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摒棄《三禮圖》,根據(jù)古器實物來繪制新《禮圖》的嘗試。 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學傳統(tǒng)的支撐,眾家古器圖的導夫先路,以及士大夫階層高漲的復古熱情,才有徽宗朝規(guī)模空前的禮樂制作。大觀元年(1107),徽宗于尚書省設(shè)置議禮局,作為推行禮制改革的專門機構(gòu)。二年十一月,議禮局詳議官薛昂上奏:
“臣竊見有司所用禮器如尊、爵、簠、簋之類與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蓋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間,無慮千數(shù)百年,其規(guī)制必有所受,非偽為也。……今朝廷欲訂正禮文,則茍可以備稽考者,宜博訪而取資焉。臣愚欲乞下州縣,委守令訪問士大夫或民間有收藏古禮器者,遣人往詣所藏之家,圖其形制,點檢無差誤,申送尚書省議禮局。其采繪物料,并從官給,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騷擾。……”奉圣旨依所奏。[8]
當時使用的禮器仍然依照《三禮圖》制作,要制作新禮器必須有新的樣本,但是除《三禮圖》之外,朝廷手中并無其他圖樣。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雖然早在皇祐三年(1051)就已有圖錄編輯[9],但規(guī)模畢竟有限。此后半個多世紀中,皇家藏器始終沒有得到系統(tǒng)整理和研究,更沒有刻意去搜集民間古器。李公麟、呂大臨諸家《考古圖》收錄的器形,雖然可供士大夫賞鑒考究,但器類并不完整,無法與禮書完全對應;摹繪刻印也比較粗劣,器形失真較大。為了給新禮器提供可靠的樣本,編纂一部高質(zhì)量的“古器全集”就成為當務之急。徽宗一方面采納薛昂的建議,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繪圖形;另一方面,將皇家收藏的古器編繪為《宣和殿博古圖》,即后來《重修宣和博古圖》的前身[10]。因此,《博古圖》修撰的初衷,應該是為改造禮器提供一部“圖樣”集;在后來的實踐中,它也的確發(fā)揮了這樣的作用[11]。 隨后,出于收藏鑒賞和制禮作樂的雙重需要,徽宗開始大規(guī)模從民間搜集古器。到政和年間,內(nèi)府藏器增加到六千余件,宣和年間更是“累數(shù)至萬余”[12]。從傳世品和歷代著錄的銘文看來,徽宗朝的仿古禮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至七年之間,這與古器“樣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開的。隨著大批新制禮器被用于祀典,《三禮圖》已經(jīng)失去了存在價值。政和五年六月,校書郎賈安宅上言:
“崇義圖義皆諸儒臆說,于經(jīng)無據(jù)。國子監(jiān)三禮堂實存圖繪,下至郡縣學間亦有之,不足示學者。宜詔儒臣編次方今禮樂新制,器用儀繪于圖,著其義具,后成書頒焉。”詔《三禮圖》及郡縣學繪畫圖象并改正,舊所繪兩壁《三禮圖》并毀去。[13]
此前,議禮局于政和三年(1113)編成《政和五禮新儀》,頒降于地方州軍,取代了奉行多年的舊禮。但由于當時大規(guī)模的禮器改造尚未展開,《五禮新儀》中并未包括新的禮器圖樣。在賈安宅的建議下,《三禮圖》被徹底廢棄,國子監(jiān)及地方州縣學墻壁上所繪的圖樣都被毀掉。但是,他提出的將新禮器圖樣編纂成書的要求,卻遲遲沒有實現(xiàn)。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數(shù)地方州軍仍然沒有得到新的禮器圖樣。《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興軍路安撫使董正封言:“竊惟朝廷講明祀事,頒降五禮,規(guī)矩儀式具備。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籩豆簠簋之類,或有未應法式去處。如臣前任知鄆州及今來永興軍,釋奠祭祀所用禮器一切損弊。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樣制造上件禮器,與今來逐處見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畫式樣,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貴上尊朝廷奉祀之禮意。”詔送禮制局繪圖頒降,令諸路州軍依圖制造,內(nèi)有銅器者,以漆木為之。[14]
據(jù)董正封所言,當時個別州軍(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頒降的“式樣”,并依樣制造了新禮器,這或許就是賈安宅上書的效果。董正封上言之后,朝廷曾有詔命禮制局繪制禮器圖樣,頒降諸路州軍[15]。不過從以后的事實看來,這次下詔恐怕并沒有造成廣泛影響,甚至朝廷有沒有將新禮器圖樣編輯成書都不無疑問。如果徽宗朝已經(jīng)有編輯成書的新禮圖,或者地方已普遍得到新圖樣,那么高宗初年制造禮器時,就不會因為無圖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禮圖》的舊樣了。 徽宗朝在大規(guī)模改造禮器之后,為什么沒有用新的《禮器圖》來取代《三禮圖》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兩點。第一,根據(jù)大觀二年薛昂箚子,當時派畫工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繪圖樣,用的是彩繪;而據(jù)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頒降地方的新禮器圖樣,用的也是彩繪。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圖》的原本,應該也是彩色繪制的[16]。之所以用彩繪,應該是為了更真切的傳達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術(shù)發(fā)明之前,這是最高級的方法。但是當時的印刷技術(shù)無法實現(xiàn)彩色套印,這就決定了《博古圖》和新禮器圖樣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復制。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繪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內(nèi)普遍頒降于地方。第二,徽宗制禮作樂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國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圖》已經(jīng)很好的起到禮器圖樣的作用。至于地方禮器的滯后,朝廷并不急于解決,也就沒有刻印新禮圖的迫切需要。 徽宗沒有想到,他費盡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禮作樂的輝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難中毀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間沒有及時將新禮器圖樣編輯成書,使得高宗朝重建禮樂制度面臨著極大的困難。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際,急需通過國家祀典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詔令東京所屬搬取起發(fā)祭器、大樂、禮神真玉、朝祭服、儀仗法物,赴揚州行在,應副郊祀大禮。”[17]這次大典,使用的是東京搬來的金人劫余之物;這些禮器多是徽宗時改作的產(chǎn)品,南宋人稱之為“新成禮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倉皇渡江,禮器儀仗盡皆拋棄。待到紹興元年(1131)舉行明堂大禮時,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時朝廷手中甚至沒有任何“新成禮器”的圖樣,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禮圖》[18]。經(jīng)過徽宗朝轟轟烈烈的復古運動,卻又回到《三禮圖》的老路上,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無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計搜尋“新成禮器”樣本,就成為高宗朝禮制建設(shè)中最重要的任務。 紹興四年(1134),又值舉行明堂大禮之年。四月,禮部侍郎陳與義等上奏:
“今來明堂大禮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畫樣,令臨安府下諸縣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禮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繳納到簠并壺尊、山、犧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籩豆爵坫并簠之類,并無樣制,亦無考古圖冊照據(jù)。今來未敢便依紹興元年明堂大禮例,畫竹木祭器樣制。”詔依紹興元年明堂大禮所用《三禮圖》樣制造。[19]
可見,當時南宋朝廷已經(jīng)致力于從民間搜集流散的“新成禮器”,但數(shù)量極為有限。陳與義等提到的“樣制”,應該是指“新成禮器”的圖樣;而“考古圖冊”指的應是古器圖錄,尤其是《宣和博古圖》[20]。這也從側(cè)面說明,當時的確將《博古圖》等圖錄當作禮器圖樣來使用。這次明堂大禮仍然和紹興元年一樣,依《三禮圖》樣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這也是因陋就簡的權(quán)宜之計。 不過國子監(jiān)丞王普等人還是對當時的禮器樣制提出了批評:
按祭器實仿聶崇義《三禮圖》制度,如爵為爵形,負盞于背,則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為龜,則不可以卻蓋。此類甚多,蓋出于臆度而未嘗親見古器也。自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歐陽修著《集古錄》,李公麟著《古器圖》,呂大臨著《考古圖》,乃親得三代之器,驗其款識,可以為據(jù)。政和新成禮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銅者,嘗有詔外州以漆木為之。至主上受命于應天,郊祀于維揚,皆用新成禮器,初未嘗廢止。緣渡江散失,無有存者。昨來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義《三禮圖》,其制非是,宜并從古器制度為定。其簠簋尊罍之屬,仍以漆木代銅,庶幾易得成就。[21]
從這段話不難看出,在百余年來《三禮圖》與金石學的較量中,后者最終獲得了勝利。經(jīng)過徽宗一朝的復古運動,《三禮圖》在士大夫心中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權(quán)威性。他們所推崇的,是仿照古器制造的“新成禮器”。在他們看來,形制合于“古器制度”是第一位的,至于材質(zhì)是用銅還是漆木則是次要問題,可以根據(jù)條件權(quán)宜處置。 王普的建議由于朝廷沒有“《博古圖》本”而被擱置,但以他為代表的聲音卻在不斷推動朝廷向著政和新禮的方向回歸。紹興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詔命東京留守搜集殘余的“新成禮器”[22]。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銅爵的建議:
今遵依指揮討論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紹興四年已得指揮外,其所用爵以木為爵形,而背上負尊。按《郊廟奉祀禮文》謂許氏說“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昨來臣僚看詳,以謂不應古制,欲仿古刻為爵形,鑿其背以實酒,以應《說文》“中有鬯酒”之義。又考《禮象》銅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正得古制。兼昨來政和年間,已曾依此改正鑄造,緣渡江之后,類皆散失。兼昨紹興七年明堂大禮,御前降到古銅爵,依得《禮象》制度。今來合將木爵并行改正,用銅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樣制造銅爵并坫。[23]
據(jù)此段史料,紹興七年明堂大禮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銅爵”。《郊廟奉祀禮文》為神宗元豐年間太常陳襄等人所詳定,陸佃亦曾參與其事[24]。有趣的是,這次禮官在論證古爵形制時,還參考了陸佃《禮象》中的圖樣。在朝廷缺乏新禮器圖的情況下,私家撰述的禮圖發(fā)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這次討論能夠?qū)⑽墨I、禮圖、古器實物相結(jié)合,說明古器物學已經(jīng)深深的滲入到禮學的傳統(tǒng)中[25]。
雖然新禮器已用于國家祀典,新的《禮器圖》也已成書,但是要推廣到地方,對整個社會產(chǎn)生影響,還需要一個過程。光宗紹熙初年,朱熹在一份申狀中指出:
淳熙頒降儀式并依聶崇義《三禮圖》樣式。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為后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樣制開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為得。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令州縣依準制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行毀棄,更不行用。[37]
紹興十五年(1145)奉圣旨“開說印造”的,應該就是《紹興制造禮器圖》。印制此圖,除了方便朝廷使用外,更重要的是“頒付州縣遵用”,將新禮器向地方推廣。但不知為何,這次的圣旨與徽宗時一樣,未能貫徹實施,州縣仍未得到新圖樣。早在孝宗淳熙六年(1179)以前,朱熹就請求朝廷將“《政和五禮新儀》內(nèi)外縣臣民合行禮制,鏤版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深淺尺寸行下,以憑遵守。”[38]但是淳熙六年編纂的祭祀儀式參考的卻是“大中祥符頒降州縣釋奠祭器制度”[39],祭器仍用《三禮圖》樣式。在朱熹的要求下,紹熙五年(1194),太常寺將改正后的州縣釋奠儀式“行下臨安府鏤板,同《紹興制造禮器圖》印造,裝背作冊,頒降施行”。這就是流傳至今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通過它,我們?nèi)阅芨Q見《紹興禮器圖》的部分原貌。《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頒降于地方,使新禮器樣式得以普及,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40]。 新禮器向地方擴散的另一個途徑是家廟祭器的頒賜。紹興十六年(1146),新禮器大部造成之后,高宗還命禮器局依政和年間舊制,為太師秦檜制造家廟祭器。此后,重臣由朝廷頒賜家廟祭器遂成定例,韋淵、吳益、楊存中、吳璘、虞允文等人都享受過這種殊榮。但是,由于鑄錢所需的銅資源匱乏,從紹興二十八年(1158)開始,朝廷多次收繳銷毀銅器,并厲行禁止民間私鑄。這樣一來,頒賜祭器的定例也無法順利執(zhí)行。淳熙六年(1179),朝廷命工部文思院為中興功臣韓世忠制造家廟祭器,但有司卻提出了缺乏銅料、工匠等困難。此后,一些大臣多次就此事上書,反對和支持的意見不相上下。直到淳熙八年(1181)十月,才有了最終的解決方案:由文思院制造木爵、木勺各一,其余祭器由太常彩畫式樣,一同頒賜,“聽其自造,并用竹木”[41]。此后,多數(shù)大臣的家廟祭器大概都是由朝廷頒賜圖樣,自行制造。太常彩繪的圖樣,與印刷本《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相比,應該會更加精致準確。而圖樣的傳播要比實物更容易,這樣一來,也促進了新禮器在民間的擴散。 與此同時,金石學傳統(tǒng)仍然在向前發(fā)展,北宋時期的金石著作得到更廣泛的流傳。據(jù)翟耆年《籀史》記述,他有一次偶然造訪葉夢得的書齋,發(fā)現(xiàn)案頭擺放著呂大臨的《考古圖》。從《考古圖》在當時的影響看來,很可能已經(jīng)有刻本流傳。而據(jù)李邴為王俅《嘯堂集古錄》所作序言,當時《宣和博古圖》“流傳人間者才一二見而已”[42]。代表當時最高水平的《博古圖》,由于原本是手工彩繪,且深藏于皇宮秘府,其在民間的流傳范圍遠遠不如《考古圖》等私家著作。直到元明時期,《博古圖》印本普及之后,它才成為民間仿造古銅器的“樣本”寶庫。 重南宋時期,民間的銅器制造業(yè)雖然屢遭禁止,卻仍然相當興盛。建康府句容縣自唐代以來就以出產(chǎn)銅器聞名,北宋以來,在收藏古物之風的帶動下,開始制造仿古銅器。紹興十年(1140),文思院承旨改造銅爵坫,因“本院全闕鑄 工匠”,“詢問得建康府句容縣多有銅匠,造作古銅器貨賣,制作精致。乞朝廷指揮建康府下句容縣計置,依樣鑄造。”[43]可見,當時句容的仿古銅器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以致朝廷制作禮器不得不求助于當?shù)毓そ砙44]。而這些民間工匠在為朝廷效力的同時,也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古器和圖樣,把這些“樣式”帶回民間。此后,無論地方州縣制作廟堂禮器,還是官僚世家制作家廟祭器,都要借助這些民間匠人。紹興新禮器的“樣式”也通過不同渠道匯聚到民間的工藝傳統(tǒng)中。 因此,南宋時期民間仿古制作的“樣本”來源是異常復雜的。其中有刊刻流傳的各種古器圖錄,有朝廷頒降地方的禮器圖樣,有官僚世代相傳的家廟祭器,也有士大夫家收藏的古器實物。這些因素在傳世和考古發(fā)掘的實物中都有所反映。下面,我們就結(jié)合1996年四川彭州南宋銅器窖藏出土的器物來做一下具體分析[45]。 該窖藏所出銅器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仿古銅器,比如琮、甗、鼎、尊、盤、蒜頭扁壺等;第二類是仿照當時的生活用器,尤其是瓷器,比如執(zhí)壺、長頸壺、瓶(包括八棱瓶,“組合式”瓶)等;第三類是將古器造型與日常用器相融合的產(chǎn)物,比如三足壺、鬲形瓶。這批器物的一大特點是多“組合式”器,也就是整器分成兩個可拆卸的部分,這可能是由于制作工藝的限制;同時也說明,這些器物大多不是實用器,而是儀式所用的陳設(shè)。多數(shù)器物是靠錘揲成形而不是鑄造,而且是各部件分別成形后再焊接成一體,導致很多本應有耳的器物(鼎、甗)將耳省去了,僅有一件甗有靠鉚釘連接的附耳。器物的紋飾多采用鏨刻和錘揲工藝,說明當時的銅器制作工藝已經(jīng)與古代有天壤之別,而且受到了金銀器的很大影響[46]。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器物中甗的數(shù)量很多(完整器共有6件,另有不成套的鬲形足兩件,器口4件),但甗并不是國家祀典中規(guī)定使用的器類。其中體形最大的一件甗(CPJ:14)在頸部和腰部都有附耳,形制與呂大臨《考古圖》卷二收錄的“圓篆甗”非常相似[47]。一件鬲形足(CPJ:30)的內(nèi)底有陽線篆書銘文:“圓篆甗漢□男平永寶用”,“圓篆甗”這個名稱顯然是從《考古圖》搬來,而本器頂部平面的紋飾與《考古圖》所描繪的“圓篆甗”甑底部隔箅的形狀一模一樣。另外一件殘存的甗甑部(CPJ:40),其方唇、外鼓的圓肩也與“圓篆甗”如出一轍。甗的足部都是用銅片彎曲而成,而且多外撇,其側(cè)視效果與《考古圖》中缺乏立體感的圖像非常相似。紋飾中的獸面紋、云雷紋等都有很大變形,如云雷紋多是僵硬的圓形、回形,與《考古圖》也很接近。因此,《考古圖》應是這些器物的主要“樣本”來源。而且制造者基本不了解“樣本”的原有意義,只求外觀相似,于是省去了原本具有特定功能的部分,卻在某些細節(jié)上一味模仿。 該窖藏還出有一件“組合式”尊(CPJ:10),僅存上半部分,也就是商周時期“三段式”尊從器口到肩部以上的一段,其形制、花紋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和三年山尊極其相似[48]。經(jīng)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紋飾的細節(jié)幾乎一模一樣,僅頸部龍紋的排列方向與宣和山尊相反。可見本器的“樣本”應該就是宣和山尊。如果制作者參考的是圖樣,不太可能達到如此精確的程度,他們應該看到了實物或高精度復制品。這件器物很可能是仿照朝廷頒賜的家廟祭器來制作的。前文提到,紹興十五年段拂等人改造禮器時,有一件從街市收買的山尊被當作“樣本”。因此,南宋時期的“山尊”很可能是由宣和山尊一脈相傳而來。
[1]對于宋代古器物學與仿古制作的關(guān)系,學者已有較深入的研究。可參看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shù)史研究集刊》第十期(臺北),2001年;王世民《北宋時期的制禮作樂與古器研究》,收入《揖芬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英)羅森《過去在中國的多種含義》,收入《中國古代的藝術(shù)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shù)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臺北),2003年;李零《鑠古鑄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2]《宋史》卷三一九,《劉敞傳》,中華書局,1977年。 [3]劉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5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4]《宋史》卷三四○,《呂大臨傳》。 [5]參見《朱子語類》卷八十四、八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 [6]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九,“器用”,參看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政和五禮新儀》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7冊。 [9]翟耆年《籀史》:“皇祐三年,詔出秘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修太樂所,參較齊量,又詔墨器窽以賜宰執(zh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1冊)是為《皇祐三館古器圖》,乃宋代皇家編纂古器圖之始,它的出現(xiàn)也與樂制改革有關(guān)。 [10]據(jù)蔡絛《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1997年),大觀初年內(nèi)府收藏的大小禮器只有“五百有幾”,與《重修宣和博古圖》的八百余器還有相當差距。《宣和殿博古圖》應該是在這五百多件器物中遴選編輯的,當然很可能還收入了到民間藏家摹繪的圖樣。 [11]《宣和博古圖》對一些器物的定名,如“著尊”、“壺尊”等,完全是按照當時祭器的名稱,而且這些器物的圖像也完全被南宋時期的《禮器圖》繼承,參看前引許雅惠文。 [12]蔡絛《鐵圍山叢談》。 [13]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六,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 [14]中華書局,1957年,第1冊。 [15]《玉海》卷五十六亦載:“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詔諸州祠祭器,令禮制局繪圖頒降,依圖制造(銅器以漆為之)。”按:此處應是將董正封上奏的日期誤當作降詔的日期。 [16]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三:“北方好事者收《紹興稽古錄》二十冊,皆高宗時所收三代古器,各圖其物,或青或綠或紅,各撫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證,如《宣和博古圖》加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1冊)這里提到的《紹興稽古錄》應是南宋高宗時仿照《博古圖》編繪的古器圖錄,又見于(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下,稱其“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6冊)。由此亦可推知《博古圖》原本應為彩繪。 [17]《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續(xù)修四庫全書》第8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8]參看《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續(xù)修四庫全書》第822冊。 [19]《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0]據(jù)《中興禮書》卷九,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禮部上奏:“四年親祀,議者以新成禮器為合于古,請復用其禮度。事下,禮官謂無《博古圖》本,遂不果行。”指的應即此事。可見陳與義等所說的“考古圖冊”主要是指《博古圖》。 [2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七十四,中華書局,1986年。《玉海》卷六十九亦載王普之言,較為簡略。 [22]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一:“壬戌,詔東京留守同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當行大禮,上以渡江后所作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焉。”(中華書局,1956年) [23]《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4]參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七、二九六,中華書局,1979-1986年。 [25]《中興禮書》卷五十九:“(紹興)十年二月一日,工部言,據(jù)文思院下界申契勘,近承指揮改造將來明堂大禮合用銅爵醆并坫,依古爵《禮象》制造四百五十二只,爵坫合依本寺見管《禮象》內(nèi)樣制造四百七十二片。”可見這次改造爵坫最后是依照《禮象》中的圖樣。 [2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七。 [27]《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28]《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八一,《玉海》卷六十九。 [29]《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30]《文獻通考》卷一○四:“時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權(quán)領(lǐng)樞密院事童貫并以此給之。” [31]《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32]《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傳》。 [33](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下:“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壺盤權(quán)鉦,各有銘,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翟汝文所撰各種銘文見《忠惠集》卷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9冊。 [34]《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35]關(guān)于宋代朝廷所作仿古器物的藝術(shù)特色,前引陳芳妹文有詳細分析,本文不再綴述。 [36]尤袤《遂初堂書目》收有此書,稱為《紹興禮器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其后亡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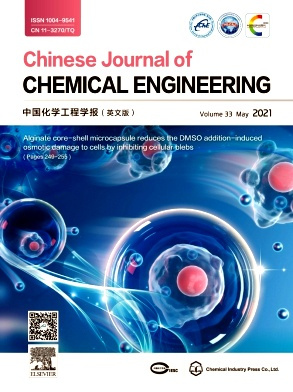

秀作文選評.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