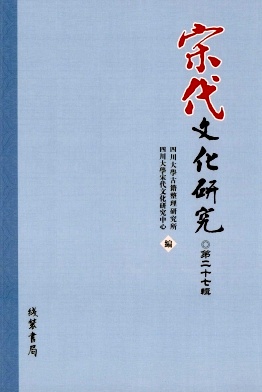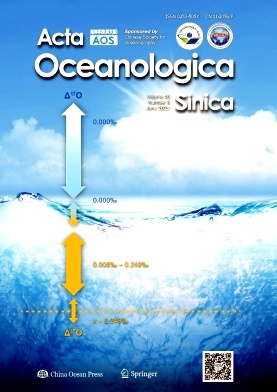從原始工業化進程看宋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一):序言、上篇
葛金芳、顧蓉
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究竟產生于何時?作者有兩條思路:一條思路是從定義入手,搞清楚究竟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另一條思路是從資本主義萌芽賴以生成的歷史條件入手,看哪個時段正在出現這樣一些條件。
這樣就從兩個方面論證了我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于宋代的結論。
序言:討論歷程的簡略回顧
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關于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先后有過三次熱潮。如果說本世紀30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激起人們對于這個問題的首次關注,[(1)a]那么50年代中葉因《紅樓夢》論爭而引發的明清社會性質的大討論則是第二次熱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探究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之原因的過程中,資本主義萌芽再次成為熱門話題。[(2)a]海外有人對此問題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大陸學者套用馬克思主義附會中國歷史的“假問題”,其實問題并非如此簡單。我國封建社會究竟有無資本主義萌芽,如有,又產生于何時、有何表現,其后有無曲折、命運如何等等,關涉到我國現代化演進歷程的歷史考察,這是一個真問題,而且關系重大。
數十年來,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我們今天對于資本主義萌芽在農業、手工業各部門中逐步生長的途徑、方式、程度、地域及其曲折的歷程有了清晰得多的了解,但在資本主義萌芽究竟產生于何時的問題上,諸家說法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多數同志力主明清說,鄧拓、呂振羽、尚鉞侯外廬、傅衣凌等史界前輩倡言在先,[(3)a]黎澍、李之勤、許大齡、洪煥春等先生證明在后。[(4)a]1985年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1)b]可以視為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說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持有不同意見。主張元代出現說者有劉文娟女士,[(2)b]唐中葉出現說者有孔經緯先生,[(3)b]胡寄窗、傅衣凌甚至上溯至戰國秦漢時期。[(4)b]還有一些同志力主宋代出現說,除上述孔先生外,50年代首倡宋代說者有束世澂、柯昌基、華山等先生。[(5)b]柯先生則因發表了異于正統觀點的文章而屢經磨難,英年早逝,誠為學界的一大損失。與此同時,范文瀾先生也說過“宋朝生產力的順利進展,很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6)b]傅筑夫甚至認為,宋代的商品生產遠較14、15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發達,因而“宋代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產生時期。”[(7)b]。
筆者亦持宋代出現說,但論證方法與以往不同,全文以美、德新馬克思主義者于本世紀70年代創立的原始工業化理論為切入視角,上篇臚列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宋代啟動的種種表現,下篇分析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歷史條件,試圖由此達致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于宋代的結論。
上篇: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宋代的啟動
顧名思義,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當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其產生初期的原生形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個概念可以從兩個維度加以把握:從形態特征上看,它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化機器大生產;從內部結構上看,它又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的有機結合。資本對于勞動的剝削關系當然集中體現在機器大生產中,但在初始階段,則是萌發于作坊、手工工場、乃至商品性農業的某些分支之中。經濟史家們發現,早在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分布在城市、鄉村地區小型、分散的工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集中表現為從資金、企業主、工人、技術乃至市場等方面,為其后的工業革命準備了條件。意大利學者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為數最多的生產單位便是在那些不可勝數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鄉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帶著他的幾個助手或親戚,從事打鐵、操作織機、印刷機或絲帶織機這樣的工作。”[(8)b]美國學者門德爾斯(Frenklin F.Mendels)為此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Proto-Industrailization),把人們的視線導向傳統社會即前工業化社會內部的經濟變動。[(9)b]在門氏看來,工業化進程可以分為原始工業化和工廠(機器)工業化這樣兩個階段,所謂原始工業化進程就是“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10)b]為與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業相區別,門氏指出原始工業化由區域經濟內同時并存的三種要素構成,這就是鄉村工業、外部市場、以及與鄉村工業相輔相成的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同時由于城市是批發商人的基地,技術、資本密集,小商品生產者的產品向城市匯聚,再由商人發運各地出賣,城市甚至通過商人資本開始參與、支配鄉村地區的某些手工業生產,這樣城市就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進程的第四個要素。其后不久,德國歷史學家P·克里特、H·梅迪克和J·施盧伯姆吸取了門德爾斯的研究成果,把原始工業化稱為“工業化前的工業化”,并以此為書名,合著成又一本關于原始工業化的理論著作。[(1)c]他們把原始工業化定義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為區間市場或國際市場進行大批量的工業商品生產的農村地區的發展。”[(2)c]其意義在于把人口作為第五個要素引入了原始工業化理論,而且由此引發出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孕育的歷史過程及其內部機制。
原始工業化進程的意義在于它為工廠工業化鋪路搭橋,推動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經濟向以工業為主體的近代經濟轉變。因為正是在原始工業化進程中,資本逐步增殖,企業主開始成長,雇傭工人日漸增多,機械使用不斷推廣,市場賴以擴大,雇傭勞動、包買制等作為慣例隨之成長,預示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漸鮮明起來。正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適當地轉換為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問題,當然還要謹慎從事,以免削足適履之譏。在我看來,門氏、克氏的原始工業化理論,在精神實質上與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馬克思說,“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3)c]“商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4)c]門氏特別強調市場,認為原始工業化與傳統家庭手工業的區別是,處在原始工業化進程中的手工業,是為市場、其中包括本經濟區域之內的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是海外市場提供產品的,而家庭手工業則主要滿足農戶本身的需要,只有小部分剩余產品,才間或投入本地小市場出賣。所謂“為市場而生產”,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生產。門氏特別強調“鄉村地區的工業發展”,馬克思亦曾指出,“在這些商業大城市以外,工場手工業起先不是以城市為基礎,而是以鄉村為基礎,在一些沒有行會之類的農村里邊的。”[(5)c]應該說從原始工業化進程這個角度來考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原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就難怪西方學術界要把門氏、克氏等人歸入“新馬克思主義”學術流派了。
如果說在18世紀開始的工廠工業化階段,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的確滯后于西方特別是西歐地區,那么這并不等于說為工廠工業化準備條件的原始工業化進程我國也無足稱道。恰恰相反,由于我國封建社會歷史悠久,封建文明高度發達,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不僅在時間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國家和英倫三島,就是在規模和水平上也毫無遜色之處。在煤鐵革命推動下民營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就是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宋代啟動的主要標志。
(一) 煤鐵革命和民營鐵冶中的雇傭關系
北宋以鐵產量的激增和灌鋼法的推廣為標志,迎來了我國冶鐵鑄造業的第二個重大變革時期。這個變革是由煤的規模開采和工業利用所激發的。我國先民雖然早在漢代就認識到煤的燃燒功能并曾用于煉鐵,[(6)c]但正式進入規模開采和用作工業能源則在北宋,其時河東、河北、陜西等路的煤炭采掘業相當發達。[(7)c]考古發掘表明,今天河南鶴壁市中新煤礦至遲北宋中葉已進入規模開采階段,當時已有較大的巷道4條,總長500余米,通向8個采煤區,作為升降通道的圓形豎井深46米,排水井深5米,附近有木制轆轤和宋元瓷器。據此估計,這座煤礦當時擁有數百名礦工,其開采范圍和生產規模與現在的中新煤礦大致相當。[(8)c]在煤炭產區,不僅居民的生活用能開始向煤傾斜,而且冶鐵鑄錢、工具制造、陶瓷燒制等業亦大受其惠。神宗元豐元年(1078)十二月,徐州白土鎮發現豐富的煤炭蘊藏,開采后用來“冶鐵作兵,犀利勝常。”[(9)c]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大鐵冶基地即徐州利國監、兗州萊蕪監、邢州棋村冶務和磁州固鎮冶務,除兗州一地無采煤紀錄(但靠近河北煤田)外,其余三處都在產煤區。[(1)d]煤、鐵產地在空間分布上的疊合,帶給我們一個重大信息,這就是煤已成為冶鐵業的新能源。我國科技史工作者利用金相、硫印和化學分析方法,檢測過若干冶鐵遺址出土的鐵器,結果發現北宋以降的部分生鐵含硫量較高,認為這是用煤煉鐵所致。[(2)d]因為木炭不含硫,煤炭則含硫量較高。至于陶瓷業中以煤為燃料,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例如陜西銅川市黃堡鎮宋伐耀州瓷窯的窯體火膛內有煤塊遺存,[(3)d],河北定窯亦以煤炭為主要能源。[(4)d]
北宋煤炭采掘業的興起和這種新型能源的工業利用,對當時的冶金生產意義有二,一是緩解了傳統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鐵的產量;二是因爐溫和冶煉效率的提高而推動了鑄造技術的變革和各類工具的進步。據《宋史·食貨志·坑冶》和《文獻通考·征榷(五)》所載數據,宋代鐵課在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達到最高點,為824萬余斤,相當于唐宣宗元和初年(806)207萬斤的四倍。其實北宋鐵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間(1068-1085年),但元豐元年(1078)的鐵課只有550萬斤,原因在于此時宋廷把北宋中葉興起的“私人承買”制推廣到宋轄全境,官營鐵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營鐵冶只需交納20%的產量作為鐵課,[(5)d]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6)d]如按550萬斤鐵課的五倍計,則當年產量達2750萬宋斤,合今3300萬斤,即1.65萬噸。日本學者吉田光邦估計,宋代鐵的年產量當在3.5萬-4萬噸之間。[(7)d]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Hartwall)估計更為大膽,他說北宋中葉年產300萬緡鐵線,即需2.9萬噸鐵,僅此一項即相當于18世紀初法國全部產量的四分之三;到1078年,每年約生產7.5萬噸到15萬噸。這個數字是164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產量(3萬噸)的兩倍半到五倍,并且可與18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總產量14.5萬噸至18萬噸相比擬。[(8)d]漆俠和筆者亦曾從消費角度估計過宋代的鐵產量,結果表明宋代全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9)d]與此同時有色金屬產量亦急劇增加,據筆者推算,神宗元豐年間(11世紀70、80年代)僅銅(3.33萬噸)、鉛(2.1萬噸)、錫(0.52萬噸)三項合計即近6萬噸,相當于鐵產量的三分之一強。[(10)d]概而言之,新型能源的利用,鋼鐵產量的激增,冶鐵技術的提高,特別是灌鋼法的推廣,[(11)d]以及作為這一切之必然結果的農具和各類工具之熟鐵鋼刃化等,這些就是宋代煤鐵革命的重要內容。
自熙寧年間實行“二八抽分制后”,民營礦冶業得到極大發展,史稱“抽收拘買之數外,民得烹煉,于是諸縣爐戶籍于官者始眾云”。[(12)d]那么民營鐵冶又是如何經營的呢?神宗元豐年間蘇軾所言徐州附近利國監鐵冶的情況可資參照:[(13)d]
“州之東北七十余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近者河北轉運使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奸滑破膽而不敢謀矣。”
利國監遺址在今徐州市銅山縣東北約80公里的盤馬山下,今隴海鐵路利國驛東站附近。這一帶煤鐵資源十分豐富,北宋初年設官營鐵冶工場,稱“邱冶務”。[(1)e]北宋中葉,發展成利國監,下設8個冶務。[(2)e]到元豐時,已是“三十六冶”了,發展迅速。位于鄉村地區的36個民營鐵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說是手工工場亦無不可。這些爐主以鐵冶致富,“藏鏹巨萬”,可見資本雄厚。他們購置冶鐵設備和雇傭工人的投資,只有在賣出鐵制產品后才能收回并賺到利潤,所以政府關閉河北市場,即有“失業之憂”;反之,使“鐵得北行”,冶戶們“皆悅而聽命”,可見這是商品生產,且已擁有區間市場。“爐主”們雇工經營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為了增殖墊支在這上面的資本的價值。”[(3)e]也就是“以生產商品的目的來剝削勞動者。”[(4)e]可以說已經具備了產業資本的主要特征。而總數達三、四千名的冶鐵工人,多是“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他們不僅已經脫離土地,從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中掙脫出來(“饑寒亡命”),而且已經從封建的政治統轄關系中游離出來(“強力鷙忍”)。至少在受雇為工期間,無論對地主、對國家,均無人身依附關系之束縛,從而獲得了“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處分”[(5)e]的自由。蘇軾此奏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鐵冶工人按其所屬爐主重新編制起來,納入政府監控系統,以收維持地方冶安之效。因此封建痕跡也是有的,如市場的存在取決于政府的恩準,工人們又被編制在地方保安系統中等。但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其萌芽時期的正常狀態;如果一點封建痕跡沒有,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之下,宋代民營手工業各部門呈現蓬勃發展態勢,其商品生產性質極為鮮明,鹽、茶、書籍等民生用品不僅在宋轄境內擁有區間市場(當然也有封建性限制),而且是宋、遼、夏、金間官方榷場貿易和民間走私貿易的主要商品;陶瓷、銅鏡、漆器、絲織品等甚至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更為重要的是,雇傭勞動、包買制度作為習俗、慣例也在成長之中。現按行業擇要分述如下。
(二) 川蜀地區民營卓筒井的崛起及其經營方式
自晚唐以還,鹽、茶禁榷成為中央財政的重要支柱,宋初仍是“鹽利皆歸縣官”。但自仁宗慶歷八年(1048)推行范祥鹽法以來,政府逐步開放商旅貿易,食鹽通商成為穩步增長。[(6)e]大約就在慶歷年間,四川井鹽區發明了深井開掘技術,民營卓筒井因此而如雨后春筍,短短二、三十年間就遍布于陵州、嘉州、榮州一帶,“連溪接谷,灶居鱗次”,星羅棋布,數以千計。神宗熙寧年間,文同任陵州知州,據他調查所見,至少井研縣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也已存在帶有近代色彩的雇傭關系:[(7)e]
伏見管內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漏。在昔至為山中小邑,于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歷以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煉鹽色。后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眾。……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憑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群黨嘩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奸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為業。況復更與嘉州并樟州路榮州疆境甚密,彼處亦即有似此卓筒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溪接谷,灶居鱗次,又不知與彼二州工匠移人合為幾千、萬人矣。
這百余家筒井作坊,大者擁有10-20個井,中等也有7-8個井,據此全縣當有千余筒井。作為作坊主的“豪者”,或由商人、地主轉化而成,或由小商品生產者上升而來,身上不免烙有封建印記,但他們與受雇工人、販鹽商人已是赤裸裸的貨幣關系。數萬工匠,絕大多數來自“他州別縣”,已與土地脫離關系,其謀生方式是“傭身賃力”,即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受雇期間如有意見,就互相串聯,集體抗議,所謂“遞相扇誘,群黨嘩噪”,或者即與主人算帳,索取工錢,退雇之后另謀高就,顯然來去自由。這些情況說明,他們既無生產資料,又無人身依附關系,是雙重意義上的自由勞動者。郭正忠先生認為,這些“豪者”,即是資本家的前身,“豪者”和“工匠”之間的關系,在其基本性質上可以看作是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出賣者之間的貨幣交換關系,筒井業中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大約是第一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1)f]
(三) 陶瓷業的商品生產性質及其日趨擴大的海內外市場
陶瓷生產在宋代進入成熟期,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當時瓷窯遺址,遍布全國17個省份和130余縣。中原地區形成定、耀、磁、鈞四大窯系,各窯精品迭出,各具特色。江南地區后來居上,其中以龍泉窯、景德鎮窯最為著名。南宋蔣祈《陶記》稱,“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饒玉之稱。”[(2)f]“交易之際,牙儈主之,……運器入河,肩夫執券,次第件具,以侔商算。”[(3)f]顯系民窯性質。浙江龍泉窯以青瓷聞名于世,在甌江兩岸和松溪上游,現已發現窯址200余座,遍布今龍泉、麗水、遂昌、永嘉等縣,形成長達五六百華里的瓷業地帶,規模極為可觀。除了章氏兄弟主持的哥窯、弟窯系官窯性質外,其余亦是民窯性質。[(4)f]前述河南鈞窯雖系官窯性質,但是“在禹縣的神垕鎮、方山、花石等處及河南的臨汝、郟縣、安陽、鶴壁、新安、魯山,河北的磁縣和山西省的一些地區,都陸續發現了燒制鈞窯瓷器的窯址,數量達幾百處,皆為生產民間日用品的民窯。”[(5)f]而福建的德化窯和晉江、廈門等地瓷窯,以及泉州磁窯,安溪、南安、同安等窯,則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銷瓷器的生產基地,產品以軍持、執壺、盒子、瓶、罐、碟等日用品為主,主要運銷海外,[(6)f]深受各國人民喜愛。在有羅盤針導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7)f]這是當時陶瓷外銷情景的真實記錄。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廣西桂林地區陸續發現的十多處瓷窯遺址,產品以青白瓷為主,胎質潔白,釉色滋潤,現已確定為宋代瓷窯。[(8)f]這批瓷窯目前尚無統一名稱,筆者暫仿宋代以地名器之成例,稱之為“桂窯”,其產品稱“桂瓷”。桂窯主要集中在桂東南的北流河流域,多系斜坡式龍窯,容積大,產量高,以適應外銷量大的需求。日本學者三杉隆敏曾多年沿“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實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在第二章《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瓷器》中,分地區詳述其考察結果。[(9)f]據他介紹,現在陳列在新加坡、印尼雅加達、越南西貢(今胡志明市)等博物館的瓷器中,有不少產品在今廣西容縣、永福、桂平等地均有出土,顯系桂窯產品。此外在印度邁索爾邦、馬德拉斯邦,巴基斯址首都東部的班布爾遺址,西亞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北的薩馬臘遺址,北非埃及首都開羅近郊的福斯坦特等地,出土物中“有南宋寧宗慶元通寶,理宗紹定通寶等錢幣,同時出土大批青瓷類,包括越州余姚青瓷和龍泉窯青瓷,以及景德鎮白瓷、廣東仙山(今佛山,窯青瓷。”[(10)f]南韓學者崔淳西也說過,“朝鮮發現的中國瓷器,以宋瓷、特別是北宋產品數量最多,并主要分布在朝鮮半島的中南部沿海地區。就品種而言,輸入高麗的宋瓷,有越窯、汝窯、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和定窯、景德鎮窯的青瓷、白瓷和黑瓷,幾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窯的制品。”[(1)g]史實表明,宋代陶瓷業就其主體部分而言完全具備商品生產性質,并擁有廣闊的國際市場。
(四)機戶和包買商:紡織業中資本主義經營慣例的初現
從生產形態上看,紡織業在宋代之重大進步,就是“機戶”的大批涌現。所謂機戶是指由家庭成員組成的、專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屬小商品生產者范疇。如浙東金華縣“城中民以織作為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2)g]更多的機戶是在城郊以至鄉村地區,如南宋洪邁說,他家鄉饒州附近的“白石村民為人織紗于十里外,負機軸夜歸。”[(3)g]可見也有少數機戶實行雇工生產的。北宋仁宗時(11世紀中葉)四川梓州有“機織戶數千家”,[(4)g]漆俠先生據此估計北宋各路約有10萬機戶,[(5)g]但其中應有部分尚未成為專業紡織戶。如果脫離土地的專業機戶占50%以上,則亦有五、六萬之眾,數目可觀。北宋哲宗元箬元年(1086),政府歲入絹帛2445萬匹,[(6)g]相當于盛唐最高額740萬匹[(7)g]的三倍多,機戶應有功焉。因為作為獨立手工業者,機戶的生產效率當更高。問題是這些機戶分布在城郊乃至農村地區,他們的產品需要由中間人將之集中起來,才能運銷到市場上去,真正成為商品——這就是包買商。列寧說,包買商將自己的商業資本投入生產領域,“把小批的、偶然的和不正規的銷售,變成大宗的、正規的銷售。”[(8)g]這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又一條產生途徑。馬克思也說過,“從封建生產方式開始的過渡有兩條途徑。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支配生產。”[(9)g]我國學術界常把明清時期紡織業中的“帳房”,以及商人對茶農實行的“先價后茶”,對糖民先放“糖本”,對煙民“給值定山”,對紙坊“以值壓槽”等慣例,視為“商人支配生產”類型的資本主義萌芽,其實這些現象在宋代同樣存在。洪邁《夷堅志》卷五所載《陳泰冤夢》,即是反映江西紡織業中存在包買商慣例的典型事例。這段材料亦保存在《永樂大典》中,語言更為清晰,移錄如下:[(10)g]
“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貨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戶,達于吉之屬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斂索,率暮秋乃歸,如是久矣。
淳熙五年,獨遲遲而來,盡十月不返。妻頗以為念,夜夢其披發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樂安曾家,為所戕殺,盍(蓋)丞為我雪此冤!”……遂訴于郡太守。……
后五日,里正報“嚴陁村道側有臥尸”,牒尉檢視。曾(小陸)坐以甲首往會,曰:“非也”。又五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殺陳泰,埋于舍后竹林中,于是捕送獄。才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為作屋停貨,今積布至數千匹。因其獨來,妄起不義之義。醉以酒隨行只一仆。詐主人之命,使先歸語其妻云:‘掊索未就,尚須小淹。’仆去少時,追斃之于山下……”。
這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間事,時在12世紀70年代。冤主陳泰原是撫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樂安、金溪、還有吉州屬縣的織戶發放生產性貸款,作為其織布本錢;到夏秋之間去這些地方討索麻布,以供販賣。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陸等“駔主”、“甲首”作為代理人,為陳泰放錢斂布。僅樂安一地就積布數千匹,為建倉庫就化去陳泰500貫錢,有一定規模。再從“如是久矣”看,這種經營方式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續相當時日了,并非偶發事件。這就是說,布商陳泰的商業資本,通過給織戶發放帶有定金性質的生產性貸款而進入生產領域,而分散在城鎮鄉村的細小織戶的產品,則先由曾小陸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來,再由布商陳泰販賣到外地而成商品。事實說明,陳泰所為,在其本質特征上已與明清“帳房”無異,均屬包買商性質。郭正忠先生曾經指出,在兩浙絲織業、四川綾錦業中,也有“收絲放貸”、“機戶賒帳”以及“預俵絲花錢物”等慣例,[(11)g]包買商正是從這些慣例中生長出來的。其實,宋代紡織品亦如陶瓷業然,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史稱北宋初年的出口商品就有“金、銀、緡線、鉛、錫、雜色帛、精粗瓷器”[(12)g]等數十種。宋代不時重申禁止銅錢出口的敕令,至南宋絲織業與瓷器同為大宗出口商品,寧宗(1195-1225年在位)時規定出口商品“止以絹帛、綿綺、瓷器、漆器之屬博易”,[(1)h]此后精妙絕倫的絲織品外銷量更大,深受域外各國喜愛,所以有學者將宋元時代的海上貿易航道干脆稱作“海上絲綢之路。”[(2)h]由此看來,宋代絲織業中包買商慣例的存在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五)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制茶、造紙、印刷等行業中的啟動
在制茶、造紙、印刷等行業中,到北宋時期同樣是民營作坊(有些已成為手工工場)占據主導地位,從事商品性生產,擁有可觀的市場,在其內部并可見到雇傭勞動的存在。
例如制茶業,據北宋丁謂所言,僅福建建安一地,“官私之培千三百三十有六,而官培三十有二。”[(3)h]民營制茶作坊占總數的99%以上,其他各地大率如此。茶葉生產季節性強,每年三、四月份采茶培制大忙季節一到,制茶作坊必得雇傭大批工匠。建安茶坊“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4)h]建溪茶坊“采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文足。”[(5)h]
我國古代造紙業到兩宋時期迎來了它的極盛期,紙張產地幾乎遍及宋境各路,兩浙、四川和福建是當時的三大造紙中心。成都西南郊浣花溪一帶有上百家專以造紙為生的“槽戶”,所造“布頭箋”,據蘇軾說“此紙冠天下”。[(6)h]陜西鳳翔府郿縣一帶,“今人以紙為業,號紙戶。”[(7)h]閩北地區“山青多竹林,水秀紙透明”,每年農歷谷雨前后,竹農、紙工便上山“殺青”。春夏之交,山村“槽戶”進入造紙繁忙季節,“沿溪紙碓無停息,一片舂聲撼夕陽”,[(8)h]場面壯觀。浙東剡縣所產剡紙以藤皮為原料,剡溪兩岸“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辟剝肌膚,以供其業”,致使當地古藤“方春且有死色”。[(9)h]此紙行銷全國,享有盛譽,所謂“異日過數十百郡,東雒西雍,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10)h]可見市場廣闊。那些“以紙為業”的“槽戶”、“紙戶”當屬獨立手工業者(即小商品生產者)無疑。
至于雕版印刷業在宋代的興起和發展,則為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壯了行色,其于經濟、社會、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影響,更為中外學者所公認。北宋中葉,從京畿到嶺南,從浙東到四川,官、私刻書作坊遍地林立。中央的國子監、秘書監和地方各路轉運司、茶鹽司均設刻書作坊,主要承印官頒歷書和歷代經史,時稱“官刻”。然而數量更多的是私家刻書作坊,時稱“坊肆”,即“書坊”和“書肆”的合稱,各地又有“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房”、“經鋪”、“經坊”、“經書鋪”、“書籍鋪”、“文字鋪”、“經籍鋪”等不同名稱。[(11)h]它們多半是集雕版、印刷和售書于一身的民營作坊型店鋪。宋人吳澄摹畫當時盛況,說“鋟板成市,板本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12)h]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評論。
通過以上的簡要勾勒,我們看到,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全方位的。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造紙、印刷等業在內的手工業各部門一度呈現出全面繁榮態勢;民營手工業普遍崛起,除軍工、鑄錢等少數行業外,其主導地位已確立無疑;并程度不等地擁有區域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海外市場;其間帶有近代色彩的雇傭關系、包買制慣例亦在逐步生長,緩慢地但是頑強地擴大著自己的地盤。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手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個為近代工業的發生準備條件的時期,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提供歷史前提的時期,我們稱之為前近代化時期。這個勢頭如果不被宋金、宋元之際的戰亂所打斷,如果沒有金元時期被周邊部族帶入中原的前封建制乃至奴隸制因素(例如“驅口”、“驅丁”、“人市”、“投下戶”、“投下軍州”和“匠局制度”等)的干擾,亦即這個勢頭如能保持二、三個世紀的持續發展的話,那么它必將為其后的工廠工業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注釋
(1)a 高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資料選輯)》,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a 田居儉、宋元強:《中國資本主義萌牙研究述略》,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巴蜀書社1987年版。
(3)a 鄧拓:《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曲折歷程》,載鄧著《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三聯書店1959年版。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書店,1937年版;《中國歷史研究提綱》,載呂著《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耕耘出版社1940年版;《簡明中國通史》,大連光華書店,1948年版。
尚鉞:《中國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展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三聯書店1956年版。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a 黎澍:《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歷史研究》1956年第2期。
李之勤:《關于清初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發展水平問題》,《教學與研究》1956年第2期。
許大齡:《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3期。
洪煥春:《論十五一十六世紀江南地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歷史教學問題》,1958年4月號。
(1)b 《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參與該書撰寫的還有汪士信、石奇、方行、方卓芬、簡銳、胡鐵文諸先生。
(2)b 劉文娟:《從(織工對)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載《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第2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b 孔經緯:《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載《新史學通訊》1955年12期。《關于唐宋時期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事實》,《新史學通訊》,1956年第3期。
(4)b 胡寄窗:《論中國封建經濟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載《經濟研究》1981年第6期。
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5)b 束世澂《論北宋時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56年第3期。
柯昌基:《宋代雇傭關系的初步探索》,《歷史研究》1957年第2期。
華山:《從茶葉經濟看宋代社會》,《文史哲》1957年第2-3期合刊。
(6)b 《中國通史簡編·緒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b 《有關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中國經濟史論叢》(下冊),三聯書店1981年版。
(8)b 〔意〕卡洛·M·奇拉波主編:《歐洲經濟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50頁。
(9)b 劉蘭兮:《門德爾斯原始工業化理論簡述》,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0)b 《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載《經濟史評論》第32卷1期,1973年3月。
(1)c 《工業化前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哥廷根,1977年德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史建云《(工業化前的工業化)簡介》對其觀點作過評述,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c 《工業化前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哥廷根,1977年德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史建云《(工業化前的工業化)簡介》對其觀點作過評述,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c 見《資本論》第1卷,第167頁;第3卷,第36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c 見《資本論》第1卷,第167頁;第3卷,第36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c 《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第55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6)c 參見《河南鞏縣鐵生溝漢代冶鐵遺址的發掘》,《考古》1960年第5期;《河南漢代冶鐵技術初探》,《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7)c 見許惠民:《北宋時期煤炭的開發利用》,《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2期。
(8)c 《河南鶴壁市古煤礦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60年第3期。
(9)c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25《石炭詩·引》。
(1)d 請參拙著《宋遼夏金經濟研析》七章二節“六·宋代煤炭產地的空間分布”,第178-179頁,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
(2)d 《中國冶金簡史》第103、152頁。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
(3)d 《陜西銅川耀州窯》,第56頁。科學出版社1965年版。
(4)d 李國肖:《定窯考略》,《河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
(5)d 參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第581-58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d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一六,中華書局影印本。
(7)d 《宋代的鐵》,載〔日〕《中國科學技術史論集》,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2年版。
(8)d 《北宋時期中國煤鐵工業的革命》,《亞洲研究雜志》1962年2月號。有楊品泉先生譯文,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5期。
(9)d 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第462-555頁;拙著《宋遼夏金經濟研析》第185-188頁。
(10)d 拙著《宋代夏金經濟分析》第198頁、188-189頁。
(11)d 拙著《宋代夏金經濟分析》第198頁、188-189頁。
(12)d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4《爐戶·坑冶附》。
(13)d 《蘇軾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書》,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二冊第759頁,孔繁禮點校,1986年版。此段材料柯昌基先生首先引用,宋史專家漆俠亦十多重視,請參前引漆俠書和柯昌基文。
(1)e 《太平環宇記》卷15,鈔本。
(2)e 慶歷年間張方平說:“利國監總八冶,歲賦鐵三十萬(斤)。”語見《樂全集》卷39《李宗泳墓志銘》。四庫珍本初集本。
(3)e 《資本論》第3卷,第356頁,1955年版。
(4)e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216頁,1975年版。
(5)e 《資本論》第3卷,第356頁,1955年版。
(6)e 拙著:《宋遼夏金經濟研析》十六章一節“二、從完全禁榷到不完全禁榷的宋代鹽法”,第437-438頁。
(7)e 文同:《丹淵集》卷34《奏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此札約撰于熙寧四、五年間。四部叢刊本。
(1)f 郭正忠:《宋代四川鹽業生產中的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6期。
(2)f 《江西通志》卷93《陶政》。據陶瓷史專家白珪、傅振倫兩位先生的研究,蔣祈是南宋人。傅文見《湖南陶瓷》1979年第1期,白文見《景德鎮陶瓷》1981年第1期。
(3)f 《江西通志》卷93《陶政》。據陶瓷史專家白珪、傅振倫兩位先生的研究,蔣祈是南宋人。傅文見《湖南陶瓷》1979年第1期,白文見《景德鎮陶瓷》1981年第1期。
(4)f 浙江文管會《浙江省龍泉青瓷窯址調查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63年第1期。
(5)f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644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6)f 《晉江縣磁灶陶瓷史調查記》,《海交史研究》第2期,1982年。
(7)f 朱彧:《萍州可談》卷2。叢書集成本。
(8)f 羅大堅:《試論宋代桂東南的陶瓷業》,《玉林師專學報》1987年第4期。
(9)f 此章譯文載《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1983年),白英譯。
(10)f 此章譯文載《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1983年),白英譯。
(1)g 《南朝鮮出土的宋代瓷器》,載《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1輯(1981年6月)。
(2)g 劉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狀》,叢書集成本。
(3)g 《夷堅志乙》卷8《無頦鬼》。中華書局排印本。
(4)g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二三。
(5)g 《求實集》,第14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g 《文獻通考·市糴考(一)》。
(7)g 《通典》卷6,《冊府元龜》卷487。
(8)g 《列寧全集》第3卷,第320頁。
(9)g 《資本論》第3卷,第373頁。
(10)g 《永樂大典》卷13136《送韻·夢字·夢夫令訴冤》。中華書局影印本,第6冊,第5676頁。
(11)g 《宋代包買商人的考察》,《江淮論壇》1985年第2期。
(12)g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
(1)h 《宋史》卷185《食貨志》(下、七)。
(2)h 參閱陳炎:《略論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及前引三杉隆敏文。
(3)h 丁謂:《東溪試茶錄》,載《百川學海》壬集。
(4)h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7《嘗新茶呈圣俞》。
(5)h 莊季裕:《雞肋編》卷下。
(6)h 《東坡志林》卷11,中華書局本。
(7)h 畢仲游:《西臺集》卷13《朝議大夫賈公墓志銘》。
(8)h 參閱周志藝:《華夏圖書之府與八閩古代造紙》,載《紙史研究》第一輯(1985年)。
(9)h 《剡錄》卷5,載舒元輿《吊剡溪古藤文》。
(10)h 《剡錄》卷5,載舒元輿《吊剡溪古藤文》。
(11)h 參閱李致忠:《宋代刻書述略》,《文史》第14輯(1986年)。
(12)h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19《贈鬻書人楊良輔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