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仆名分”與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變革時期階級結(jié)構(gòu)研究之一
戴建國
提 要:新發(fā)現(xiàn)的《天圣令》有關(guān)令文,反映了北宋時期還存在著良賤制度,這種制度到南宋時才完全消亡。在階級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過程中,原來舊的針對賤口奴婢的法律無法適用于具有良人身份的雇傭奴婢,宋統(tǒng)治者通過立法,對雇傭奴婢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確規(guī)定。在“主仆名分”制約下,雇傭奴婢被納入家族同居范圍,與雇主結(jié)成密切的依附關(guān)系。雇主侵害雇傭奴婢依常人法處置,雇傭奴婢侵害雇主,則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懲處。即使是主雇關(guān)系已解除,“主仆名分”的影響仍然存在。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隨著良賤制度的存亡而上下波動,有所變化。
關(guān)鍵詞:唐宋變革 良賤制度 雇傭奴婢 法律地位 唐宋之際,中國傳統(tǒng)社會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唐中期以降,尤其是宋代呈現(xiàn)出與唐前期迥然不同的態(tài)勢,從政治生活、經(jīng)濟關(guān)系到社會結(jié)構(gòu)都發(fā)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這些變化給后世以很大影響。日本學者對唐宋之際的社會變化給予了高度重視,早在20世紀初期就開展了深入研究和激烈的爭論,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相比之下,中國學界長期以來顯得比較沉寂。雖然嚴復、王國維等早就指出了宋代的變化,但并未展開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張其凡認為,不應(yīng)避開或不提“唐宋變革期”學說,他呼吁正確分析、認識這一學說,進一步開展研究。①2002年,廈門大學和浙江大學先后召開了“唐宋制度變遷與社會經(jīng)濟學術(shù)研討會”、“唐宋之際社會變遷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這兩次學術(shù)討論會的召開,表明唐宋社會變革研究逐漸引起中國學術(shù)界的重視。 —————————— * 本文是在日本東洋文庫和大阪市立大學演講的基礎(chǔ)上修改而成。感謝大澤正昭、斯波義信、池田溫、岸本美緒、平田茂樹諸先生及齊霞女士的建設(shè)性意見和所給予的幫助。 ① 張其凡:《關(guān)于“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2001年第1期。 唐宋之際,中國傳統(tǒng)社會發(fā)生變革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階級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門閥士族退出了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階級。奴婢、部曲、佃客,這些社會最廣泛的下層勞動者的身份發(fā)生了變化,法律地位有了明顯提高。關(guān)于宋代奴婢、佃客的研究,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已有豐厚的研究成果。自20世紀30—40年代以來,宮崎市定、仁井田陞、周藤吉之、草野靖、柳田節(jié)子、朱瑞熙、王曾瑜等一批國內(nèi)外學者相繼作了研究,①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取得了基本相近的看法。但對宋代包括奴婢在內(nèi)的雇傭人身份和法律地位卻有不同的認知。仁井田陞和周藤吉之認為雇傭人和奴婢屬同一經(jīng)濟范疇,他們與雇主或主人的關(guān)系是一種有“主仆之分”的身份關(guān)系;而宮崎市定和草野靖則否認這種身份上的隸屬關(guān)系,認為雇傭人和奴婢都屬于自由民。高橋(津田)芳郎則批評了把屬于經(jīng)濟范疇的奴隸與法的身份上的奴婢混同起來的觀點,認為身份和階級必須予以區(qū)別,奴婢乃因犯罪或被俘虜,由國家剝奪了良民的身份。這種身份僅限于通過了法的手續(xù)者,屬于國家性質(zhì)的身份,宋代不存在這種法的奴婢身份。②柳田節(jié)子認為,由雇傭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奴婢、人力、女使,在階級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中是父家長制的家內(nèi)奴隸,從其身份來說,類似于與良相對的賤身份的部曲。③此外,有不少學者認為漢唐以來的良賤制度到宋代消亡了。④奴婢,一般來說,是指佃客之外的家內(nèi)勞動者。宋代奴婢依其來源的不同主要可分為三種:良人因犯罪而籍沒為官奴婢(其中一部分轉(zhuǎn)為私人奴婢),這部分奴婢是真正法律意義上的奴婢,身份低賤;迫于生計,良人自賣為奴婢,或被雇傭為奴婢,這部分奴婢的身份在法律上是良人,宋代雇傭奴婢至遲到仁宗嘉祐時,法律上已被稱為“人力”和“女使”;⑤良人被掠賣為奴婢,掠賣奴婢,在宋代始終是一種違法行為,為國家法律所禁止,盡管事實上是存在的。本文著重討論的是宋代良賤制度和奴婢的法律地位,主要通過新發(fā)現(xiàn)的《天圣令》有關(guān)令文,并結(jié)合一些史料的解讀,對宋代奴婢作進一步的研究。 ———————————————— ① 日本學者的主要成果有:宮崎市定:《從部曲走向佃戶》,《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5冊,中華書局,1993年;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重版;周藤吉之:《中國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草野靖:《宋代的頑佃抗租和佃戶的法律身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8冊。中國學者主要成果有: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中州書畫社,1983年;柯昌基:《宋代的奴隸》,《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王曾瑜: 《宋朝階級結(jié)構(gòu)》,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郭東旭:《論宋代婢仆的社會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宋東俠:《試論宋代的“女使”》,《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② 此據(jù)柳田節(jié)子先生總結(jié)歸納,見氏著《宋代的雇傭人和奴婢》,《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此文柳田氏后有修訂,收入氏著《宋元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創(chuàng)文社,1995年。高橋(津田)芳郎的觀點詳見其所著《宋一清身份法的研究》,日本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刊行會,2001年。 ③ 柳田節(jié)子:《宋元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第81頁。 ④ 高橋(津田)芳郎:《宋一清身份法的研究》,第177頁;楊際平:《唐宋時期奴婢制度的變化》,《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4輯,商務(wù)印書館,2002年,第57—64頁。 ⑤ 《宋會要輯稿·刑法》1之33建炎三年四月條。關(guān)于此,楊際平《唐宋時期奴婢制度的變化》一文有不同看法,認為人力、女使與一般雇傭勞動者仍有一定的差別。 一 宋代的官奴婢和良賤制度 因罪而籍沒為官奴婢者,世代為奴,律比畜產(chǎn),身份自不待言。從宋代文獻記載來看,有關(guān)因罪而沒為官奴婢的例子并不很多,不像唐代那樣動輒將罪犯及家屬大量沒官。如記載沒官為奴婢資料較詳細的北宋編年史《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有關(guān)史料也是屈指可數(shù)。神宗熙寧四年(1071),慶州發(fā)生的兵變被平定后,叛兵家屬應(yīng)沒官為奴婢者,配江南路、兩浙路、福建路為奴,“諸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⑥這是宋代文獻中惟一可見的一次大規(guī)模將犯人家屬沒為奴婢的記載。由于文獻記載不多見的緣故,易使人得出宋代奴婢制度崩潰了的結(jié)論。然而少見并不等于沒有。事實是,在北宋,法律意義上的官私奴婢這個階層是存在的,只是這部分奴婢并未構(gòu)成宋代奴婢的主體而已。 研究奴婢的法律地位,或者說法的身份,我以為最主要的依據(jù)應(yīng)當是國家的法律規(guī)定以及文獻記載的司法案例。法律的制定與修改,既決定于社會物質(zhì)生活條件的變化,又集中體現(xiàn)了當時的物質(zhì)關(guān)系。新近發(fā)現(xiàn)的《天圣令》殘本為我們研究北宋奴婢的構(gòu)成和身份變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天圣七年(1029)修成的令典《天圣令》,“凡取唐令為本,先舉見行者,因其舊文,參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隨存焉。”①換言之,《天圣令》由兩部分組成:宋代在行之令與不用之唐令。②天一閣現(xiàn)存《天圣令》僅存10卷,檢視其中奴婢有關(guān)的令文大約有25條。我們先看其中17條廢棄不用的唐令:③ —————————————— ⑥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辛丑。 ① 《宋會要輯稿·刑法》1之4。 ② 詳見戴建國《天一閣藏明抄本(官品令)考》,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令文校正字及脫文用方括號標明,原錯別字用圓括號標于前。 《倉庫令》:諸官奴婢皆給公糧,其官戶上番充(后) [役]者,亦(人) [如]之,并季別一給,有剩隨季折。 《廄牧令》:諸官戶奴充牧子,在牧十年,頻得賞者,放免為良,仍充牧戶。 《捕亡令》:諸奴婢逃亡經(jīng)三宿及出五十里外,若度關(guān)棧捉獲者,六分賞一;五百里外,五分賞一;千里外,四分賞一;千五百里外,三分賞一;二千里外,賞半。即官奴婢逃亡,供公廨者,公廨出賞,余并官酬。其年六十以上及殘廢不合役者,并奴婢走投前主,及鎮(zhèn)戍關(guān)津若禁司之官于部內(nèi)捉獲者,賞各減半。若奴婢不識主,榜召,周年無人識認者,判人官,送尚書省,不得外給,其賞直官酬。若有主識認,追賞直還之。私榜者任依私契。 諸捉獲逃亡奴婢,限五日內(nèi)送隨近官司案檢,知實評價,依令理賞。其捉人欲徑送本主者,任之;若送官司,見無本主,其合賞者,十日內(nèi)且令捉人送食。若捉人不合酬賞,及十日外承主不至,并官給衣糧,隨能錮役。 諸(促)[捉]獲逃亡奴婢未及送官,限內(nèi)致死失者,免罪不賞;其已人官未付本主而更逃亡,重被捉送者,從遠處理賞。若后(促) [捉]者遠,三分以一分賞(府) [前](促) [捉]人,二分賞后(促) [捉]人。若前(促) [捉]者遠,中分之,若走歸主家,理半賞。 諸逃亡奴婢身犯死罪,為人捉送,會恩免死還官、主者,依式理賞。若遂從戮及得免賤從良,不理賞物。 渚計逃亡奴婢價者,皆將奴婢對官司評之,勘捉處市價,如無市者,準送處市價。若經(jīng)五十日無賞可酬者,令本主與捉人對賣分賞。 《醫(yī)疾令》:諸女醫(yī),取官戶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無夫及無男女,性識慧了者五十人,別所安置,內(nèi)給事四人,并監(jiān)門守當醫(yī)博士教以安胎產(chǎn)難及瘡腫傷折針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醫(yī)之內(nèi)業(yè)成者,試之。年終醫(yī)監(jiān)正試,限五年成。 《獄官令》:諸放賤為部曲、客女及官戶,逃亡經(jīng)三十日,并追充賤。 《營繕令》:諸營造雜作應(yīng)須女功者,皆令諸司戶婢等造。其應(yīng)供奉古陂可溉田利民及停水須疏決之處,亦準此。至春末使訖,其官自興功,即從別敕。 《雜令》:在京諸司并準官人員數(shù),量配官戶、奴婢,供其造食及田園驅(qū)使,衣食出當司公廨。諸官戶、奴婢男女成長者,先令當司本色令相配偶。 諸官戶皆在本寺分番上下,每十月都官案比,男年十三以上,在外州者十五以上,各取容貌端正者送太樂(其不堪送太樂者,自十五以下皆免入役),十六以上,送鼓吹及少府監(jiān)教習,使有工能。官奴婢亦準官戶例分番(下番日則不給糧)。愿長上者,聽。其父兄先有技業(yè)堪傳習者,不在簡例。雜戶亦任本司分番上下。 諸官奴婢賜給人者,夫妻男女不得分張,三歲以下,聽隨母,不充數(shù)限。 諸官奴婢死,官司檢驗申牒,判計埋藏,年終總申。 諸雜戶、官戶、奴婢主作者,每十人給一人充火頭,不在功(果)[課]之限,每旬放休假一日,元日、冬至、臘、寒食、各放三日,產(chǎn)沒及父母喪,各給假一月,期喪,給假七日。即戶奴婢老疾,準雜戶例。應(yīng)侍者,本司每聽一人免役扶持,先盡當家男女。其官戶婦女及婢夫子見執(zhí)作,生兒女周年,并免役(男女三歲以下,仍從輕役)。 諸官奴婢及雜戶、官戶,給糧充役者,本司(名)[明]立功課案記,①不得虛費公糧,其丁奴,每三人當二丁役,中[奴若丁婢,二當一役,中婢三當一役]。② 仔細分析這些令文,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在廢棄不用的唐令中,有12條是關(guān)于官奴婢的,諸如官奴婢分番制度,官奴婢作為財產(chǎn)賞賜制度,官奴婢死亡后的驗實申報制度,官奴婢勞役制度和供給制度。以唐令為本的《天圣令》將與官奴婢有關(guān)的唐令廢棄不用,充分反映了北宋前期官奴婢數(shù)量的減少,這與官奴婢來源的枯竭應(yīng)該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唐末五代以來許多因戰(zhàn)俘而成為奴婢的人,受到國家干預(yù)而被釋放。例如后唐同光二年(924)莊宗曾頒布敕令:“應(yīng)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③既釋放私奴婢,則因戰(zhàn)俘而為官奴婢的人也由此減少,官奴婢已不再是奴婢的主要組成部分,官奴婢在國家經(jīng)濟活動中的作用大為減弱。高橋芳郎曾指出,宋代不實行官奴婢給賜制度。④上述不用之唐令則是一個例證。從《天圣令》廢棄的唐令來看,宋仁宗天圣前后,宋代逐漸減少把罪犯大量配沒為奴婢的做法。從宋代實際情況來看,亦是如此。如從仁宗嘉祐時起,宋實施嚴厲的重法地分法,對強盜及窩藏犯人之家判以重罪,然對犯人亦只是實行配隸法和編管法,而沒有將犯人及其家屬籍沒為奴婢的法律規(guī)定。《長編》卷344元豐七年(1084)三月乙巳條載:“自嘉祐六年,始命開封府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寧中,諸郡或請行者,朝廷從之,因著為令。至元豐,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zāi)傷減等者,配遠惡處。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yīng)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處,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論。”這條材料詳細記載了重法地分法,卻絲毫沒有籍沒罪犯及其家屬為官奴婢的內(nèi)容。 ———————————— ① “明”字據(jù)日本《養(yǎng)老令·雜令》(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令義解》)校正。 ② “奴若丁婢”以下諸文據(jù)《唐六典》卷6補。 ③ 王溥:《五代會要》卷25《奴婢》。 ④ 高橋(津田)芳郎:《宋—清身份法的研究》,第165頁。 其次,在廢棄不用的唐令中,有五條是關(guān)于捕獲逃亡奴婢的酬賞問題。宋令為何將與捕捉酬賞相關(guān)的法令刪去不用呢?我的解釋是這與宋代賤口奴婢的減少,雇傭奴婢的大量增加有關(guān)。奴婢逃亡已不成為危害社會穩(wěn)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建立在捕捉逃亡奴婢上的酬賞法,自然就沒有實施的必要。 再次,關(guān)于奴婢放賤為良,唐代是分成三級,逐級進行的。《唐六典》卷6云:“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人良人)。”宋代不存在唐之意義上的番戶、雜戶,①奴婢放賤為良,一免即為良人。既已成為良人,就不存在逃亡被抓獲的問題。因此,唐舊令“諸放賤為部曲、客女及官戶,逃亡經(jīng)三十日,并追充賤”,自然便被廢棄。 最后,隋唐以來,法律規(guī)定奴婢“當色令相配偶”,奴婢不能與奴婢以外的人通婚。②《天圣令》將唐代的這一法律規(guī)定廢棄不用,這就意味著宋代奴婢可以與奴婢之外的人通婚,這是歷史的一大進步,是宋代奴婢身份提高的一個標志。

境.jpg)

技術(shù)學院學報.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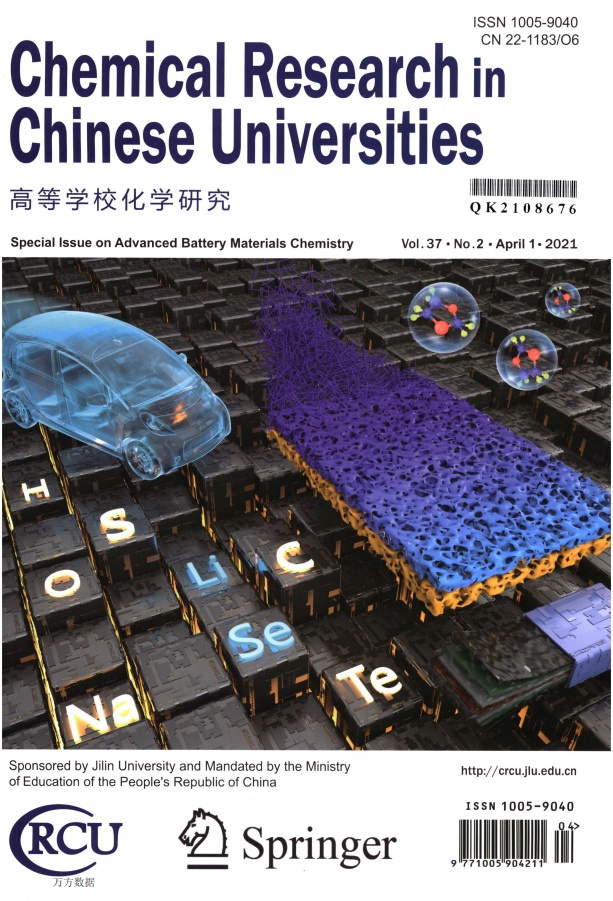
于我們.jpeg)